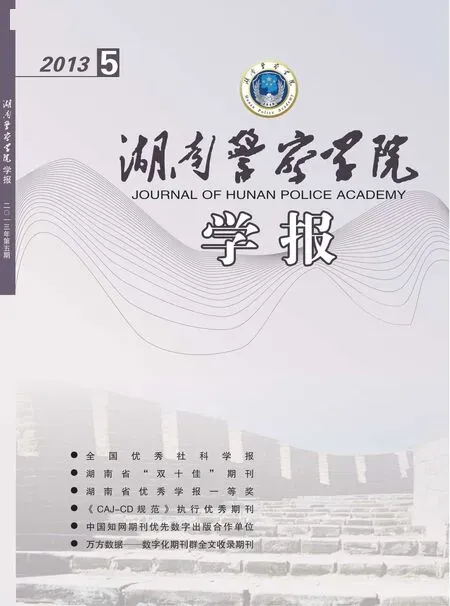论高校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资格
——以田永案、甘露案等系列案件为视角
赵正群,刘珍香(南开大学,天津 300100)
论高校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资格
——以田永案、甘露案等系列案件为视角
赵正群,刘珍香
(南开大学,天津 300100)
近年来,随着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案件数量的攀升,高校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司法实务界的认可,然而,无论是田永案开启先列,抑或是甘露等案再度确认,学校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资格在理论界和实践中依然未达成一致的共识。通过分析最高法院公报的系列案件,以确认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合理来源与现实情形。同时,结合国外的系列先进经验并对之加以引进,以实现我国司法统一的最终目的。
高校;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公法人
一、案例引入
1996年2月29日,北京科技大学二年级学生田永,在一次课程补考过程中因涉嫌夹带作弊被监考教师发现。该大学在一周之后,对田永作出退学处理决定。并于该决定作出一个月之后,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并对所作出的处理决定公布于学期教学简报和报告栏中。然而,田永的学生身份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并以在校生身份在被告处继续学习,完成了该校的教学计划,且学分及毕业论文均满足该校对毕业生的要求。然而就在原告即将毕业时,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却以原告田永事实上并不具有学籍为由而拒绝向原告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基于此,原告田永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提出要求被告向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等诉讼请求。法院于1999年2月中旬对案作出判决:“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田永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召集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田永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第一审宣判后,北京科技大学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第4期公报上刊登了此案。
时隔六年,最高法院仍然以公报的形式刊登了杨宝玺诉天津服装技校不履行法定职责案[2],在该案中,原告以被告未按时发放毕业证书为由对其提起行政诉讼,法院根据《教育法》的规定,认为受教育者享有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的权利。教育机构没有直接向其准予毕业的受教育者发放毕业证书的行为,构成违法,从而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同样,最高人民法院在2012年第7期的法院公报上刊登了甘露不服暨南大学开除学籍决定案[3]。该案中原告甘露以暨南大学做出的开除学籍决定案没有法律依据及处罚太重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最终,最高院以被告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依法撤销了被告的处理决定。该案的裁判摘要指出,学生对高等院校作出的开除学籍等严重影响其受教育权利的决定可以依法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当以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参照相关规章,并可参考涉案高等院校正式公布的不违反上位法规定精神的校纪校规。以上案件如今已然划上了句号,但是,案件中存在的问题似乎没有被根本解决。高校是否具有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法院认定被告资格的依据何在?为什么在相类似甚至相同的情况下其他法院会出现与已有裁判相反的裁判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讨和加以解决。
二、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法律分析
高校作为现代社会一类极为重要的社会组织,其不仅符合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特征,同时也具有法人主体所应当包含的资格特点。然而,从这两方面来看,只能得出高校是以一个公益性组织的性质而存在,其所具有的亦是民事主体的特征,参与的是民事活动,并受到民事法律的调整。但是,现实中高等学校浓厚的官方色彩及其所行使权力所具有的管理特征等种种迹象都表明民事主体这一定位并不能完全涵盖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因而必须对高等学校民事主体之外的其他法律地位加以必要的探究[4]2。根据法人成立所依据法的性质,法人可以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两类,公法人是根据公法的规定而成立的法人,以公共事务为其成立目的;私法人是根据私法而成立的法人,以私人事业为成立目的[5]1。从以上分类及其设立的目的来看,高校可被划入公法人这一范畴。然而,基于目前我国对公私法人定位的不明确和意见的不统一,高校的公法人资格并未得到学界一致的认可。也正是高校这种模糊不清的法律地位,导致了高校与学生、高校与教师在纠纷解决中权利救济的混乱,常常出现适用救济程序的错误,本应由行政诉讼解决的事却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而本应属于民事法律领域的纠纷又常常夹杂着过多的行政力量;这种救济程序的错误,不仅影响到了被侵害人的权益的补救,同时也对公立高等学校权力滥用的监督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4]1。
基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传统行政学和行政法学认为,所谓公行政也就是国家行政。换句话说,由国家作为行政的唯一主体,并基于公益目的来对社会进行管理。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传统的行政法学理论已不再适用。行政不再是国家行政,而应当是公共行政;公共行政除了包括传统的国家行政以外,还包括社会行政,即由社会主体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行使部分行政权力,社会行政是利用社会的自治来实现社会管理,以减少政府负担,解决政府垄断行政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4]2。有学者认为,行政权是指国家赋予的,运用国家强制力对公共利益进行维护和分配的权力,它与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权利存在根本上的不同;行政权力具有国家赋予的强制力量,可以通过国家强制力自行达成行政目标;而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权利则是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不具有国家强制力,在权力的行使遇到妨碍时只能求助于国家机关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6]7。以上对行政权的表述,强调的是国家权力的分配,而不同于以往以主体自身性质来定位行政主体并将其局限于国家行政机关。通过以上我们可以发现,行政权力的本质不在于其所分配的机构本身,而在于它所分配的力量是否以公益为目的。通过对行政权的重新定位,毫无疑问,高校日常的教育和管理活动及其招生行为均是在国家授权的情况下,运用国家权力来对教师、学生进行管理,进而达到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分配的目的,因而高等学校的内部行政管理权力也应当被看做为一种特殊的行政权力[5]2。
在司法实践的推动下,学术界对于高校的法律性质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并逐渐引入了国外的相关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借鉴法国的公法人理论,而有的则认为为了全面反映高校这类组织的特征,应借鉴“第三部门”理论[7]。然而,在我国的实务界,则认为高校应被认为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8]3。其中,作为大陆法系的典型国家之一,法国采用了公法人理论。在法国,承担公共服务事业管理,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除了国家机关、地方单位以外,还有公务法人。“公务法人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它具有法人资格;也即它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有自己全部、独立的财产,并实行独立核算。第二,它是一个公法人;它从事国家规定的某项公共利益活动,并接受国家的监督和控制。它也因此享有某些特权,如公用征收权、其财产不能被扣押、强制执行权等。第三,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享有一定的自主权。”[8]2“第三部门”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提出,主要用来概括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不明地带,换句话来说,“第三部门”与政府机构一样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是一个与“私”相对的具有公共性的权力组织;与政府机构所不同的是,政府作为官方,行使的是“特殊的公共权力”,而“第三部门”则来自民间组织,行使的是原始的、具有普通意义的公共权力[9]1。也就是说,政府机构作为一种官方代表,行使的是体制内的权力,而“第三部门”作为一种代表公共服务的民间组织,其行使的是体制外的力量。如今,该说法在我国也已被学术界广为接受。由于各国内部体制的不同,对于“第三部门”的界定也有所不同。“第三部门”作为一类中间组织,正如前面所述,其与政府具有不同的特征,换句话来说,它们还具备政府和企业所不具备的特性。这些特性集中表现在非营利性、自主性、专业性以及低成本等方面[9]2。所谓非营利性,是由“第三部门”所追求的目的公益性而决定的。“第三部门”作为中间组织,其以公益为成立的核心,基于社会公益管理而存在。自主性,是指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也就是说,“第三部门”自主管理部门内事务,不受政府的干扰和限制,具有自主决策和自主管理权。而“第三部门”名称的来源就是人们相信它们能够独立地筹措自己的资金从而不受政府支配,独立地实施工作计划,进而在自主管理的方向下独立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此外,“第三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它具有一般整体所具有的多样性特征[9]2。不仅如此,这些出于公益而存在的组织本身也独具专业性。成立之始,它们对目标的定位十分明确,如学校是给人们提供受教育机会的组织;医院是救死扶伤的组织等等。与政府组织依靠大量国家资金维持不同,“第三部门”在运作过程中可以依靠志愿人员为其提供免费服务,而且还能够得到私人捐款的赞助来缓解对外的经费,因此具有低成本的特质。为了突现“第三部门”的这些特质,西方国家在法律上对第三部门的地位大都作了特殊规定,如“志愿者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等。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指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行政管理活动、参加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非政府组织。在田永案中,法院最后判定: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某些社会团体或事业单位不属于行政机关的范畴,但是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享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这些团体或单位与其成员或相对人之间基于管理而产生的关系不是民事关系而是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因此而发生的纠纷,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畴,而是应当通过行政诉讼来加以解决。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诉讼的被告应当是行政机关,然而为了监督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从而更好地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赋予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在行政诉讼中一定程度上的被告资格,对于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发生的行政纠纷依照行政诉讼法来处理,这样不仅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还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我国《教育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国家实行学位证书和学业证书制度,由国务院授权高校对符合条件的高校大学生授予学士学位并颁发相应的学位证书。在本案中,原告田永诉请被告向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正是由于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以高等教育机构法人的身份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及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时引起的行政纠纷,因而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然而,结合我国的现状来看,即便是田永案、甘露案已被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公报案例刊登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但由于我国目前并不是一个判例法国家,没有确立判例制度以及指导案例在法律上的效力,公报案例并没有对司法实践造成足够的影响,各地的司法审判依然无法达成共识。有些法院依然认为高校作为事业单位,不是法律规定的行政诉讼的被诉主体,因此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并基于此对于学生对高校所提出的行政诉讼不予受理,如2003年北京某大学经管学院会计系98级女生严某由于考试作弊被勒令退学,该学生以处分没有法律依据为由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然而,法院在审查后认为因严某所在大学对其作出的勒令退学处分决定所产生的纠纷,不在人民法院所应受理的行政案件的范围之列,因此对严某的起诉不予受理。有的法院则在受理案件之后,以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为由,驳回当事人的起诉,如2002年10月重庆某大学生因在校期间怀孕而被学校以“道德败坏,品行恶劣”为由给予开除学籍处分,两大学生以“定性错误,于法无据”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这一行政处分。然而,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对此做出了驳回起诉的裁定。从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对于高校的行政诉讼被告地位并未达成一致的认可,相反,对于相类似或相近的案例,不同法院往往会给出不一样的回答。因此,为保障学生等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司法实践的统一,为确立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达成学界和实务界对高校定位的统一认识迫在眉睫。
三、推进高校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在我国的确立
从以上案例来看,不同法院之所以对相类似或相近的案件给予不同的判决结果,在于法院审判依据的不统一。正如田永案,法院虽然将高校解释为《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可起诉机关,也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但实为勉强。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要解决目前我国司法上的不统一现象,必须先对我国高校进行法律地位的明确,从而进一步解决司法实务中所遇到的难题。
首先,借鉴国外“重要性理论”。德国的“重要性理论”是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换句话说,该理论一方面继承了特别权力关系中对特殊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关系的明确,另一方面,则摒弃了特别权力关系下对司法救济的不当排除。根据“重要性理论”,公务法人与其成员或相对人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因此不能完全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基于维持公务法人正常运转的目的,应当赋予特别权力人在一定程度上的行政管理职权[6]7。同时,基于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特别保障,对于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事项的,应当由法律进行规定,并赋予公民在权利被侵害时向司法寻求救济的权利。也就是说,“重要性理论”不仅承认了公务法人在行政权上的主体地位,还提升了特别权力关系中所不具备的对公民基本权利司法救济的法律保护。
在田永案中,法院根据我国《教育法》等法律的规定,认定了高校的行政管理权。然而,《教育法》第二十八条对学校的授权极为广泛,从招生权、奖惩权、学籍管理权等,几乎涵盖了学校与学生间关系的各个方面。设想一下,学生对于高校基于法律法规授权进行的奖励表彰或记过处分不服的,是否可以将高校推向行政诉讼的被告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学校如何进行自主管理,自治权又应当如何加以保障?如果不能,又应当如何解释这些行为不是经过法律法规的授权。毫无疑问,仅仅依据法院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显然无法解决现实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然而,如果根据“重要性理论”对事业单位的管理行为进行区分,来处理被告资格问题,会产生怎样的效果?首先,当事业单位对相对人作出不利影响的决定,足以改变其单位成员身份权或剥夺学生受教育权等权利时,受影响的公民可以其基本权利受到侵害为由对此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换句话说,对高校作出的有关招生、不予颁发学业证书、不授予学位及退学、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处分不服的学生,可以以此为由把高校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而对于为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管理秩序,且并没有影响到学生受教育权利以及单位成员身份权利的其他决定,则应当由高校通过校内救济渠道来加以解决,不能提起行政诉讼[10]。通过这种“区别对待”的处理方式,一方面,不仅尊重了高校的自主管理权,有利于高校的管理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充分保护了学生的受教育权以及单位成员的身份权。
其次,确立正当程序下的高校行政诉讼主体地位。行政诉讼中的正当程序的审查主要包括是否履行了事前告知义务、是否做到了基本的程序公正等[11]。作为事业单位的高校,要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只能在关乎学生受教育权等切身利益时的情境下方可。因此,高校在实施相应的行政管理行为时应该严格按照正当程序原则来办事,以充分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12]。法院可以应用“正当程序”的标准来审查高校对相对人的重大合法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行为。在英国,基于一定的自治性要求,国王和议会会授权大学等高等教育实体来制定一些与其自身运转相匹配的“大学相关法”。如果该教育机构的成员或者相对人对其作出的行为不服而起诉的,那么此时法院可以在“公共职能”理论的引导下来对该行为进行判断,从而决定其是否属于司法审查的范畴。可见在英美法系国家,确定某个社会团体、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行为是否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并非由该组织本身的身份和地位所决定,而取决于该组织行使的“职能性质”本身。只要它的行为涉及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具有公共性质,此时该组织就不能免除司法审查,而应当以被告的身份参与到所涉的行政诉讼当中。并且,若该组织不按照正当程序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那么就将可能因此而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然而,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并未确立正当程序原则,而仅限于合法程序,也就是说要发展高校在正当程序上的诉讼地位,还必须依赖我国法律对正当程序原则的建立。但欣喜的是,尽管我国法律并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正当程序原则在我国的案例判决中已有雏形,甚至已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作为指导案例来进行司法指导,例如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教育行政确认案、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决定案等就涉及到正当程序在行政诉讼中的运用,由此可见,对于正当程序原则在我国法律上的确立已然不是遥不可及。
最后,明确高校特殊公法人地位。从行政法的发展方向来看,用法律、法规授权的方式界定行政诉讼被告并非长久之计;因为现代社会各行各业均需要法律的规范,并不能说,只要法律规定了某一组织的权利义务就一般认定其为授权组织,而在于法律对其授权的目的,被授权的权利之所以具有公权力的性质,关键是此类组织本身具有管理公共事物的职能[13]。因此,从扩大行政诉讼的范围,规范这些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团体等事业单位的行为,更好地保护被管理者的合法权益的角度讲,我们可以引进外国的“公务法人”这个概念[14]。正如前述,高校作为公共行政中的社会行政,其有不同于国家行政的特性,这也是由高校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高等学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很少能找到一种机构,既是那么统一,又是那么多样,无论它用什么伪装都可以认出;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它和任何其他机构完全相同。”埃米尔·涂尔干所描述的这种机构正是高等学校[6]12。高等学校是由高深知识和围绕这些高深知识而工作的群体所组成的,这是高等学校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独特特征;知识的专业性、累积性以及自主性和长期性决定了高等学校内在的学术活动应该以学术价值为导向,要避免功利主义的倾向[15]。这些特点要求高校保持一定的科技自由、学术自由和精神自由。“尊重与保障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不仅对于一个健康的教育体制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在我们看来,还是确保其他自由及努力发展与维持民主的必要前提。”[16]尽管单方面性、强制性等是行政权的属性,但并非所有具有这些属性的权力都是行政权[17]。也即虽然高校在管理行为上具有行政行为的特点,但基于高校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其实施的管理行为并非皆为行政权的行使,对于高校的不同行为应根据其性质和目的的不同加以区分开来。因此,根据高等学校的这些基本特点,应保持高校和教师一定的学术裁量权,保证一定的教学民主、学术民主,使得高校、教师以及学生可以在自由的空气下创造出新鲜的科技和学术成果。与此同时,对于严重侵犯学生受教育权及教师身份权等公民基本权利的,则赋予相对人寻求法律和司法救济的可能,从而充分的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结语
高校作为特殊的公共法人,应在行政的监管和司法介入的同时,适当保持高校独有的学术特性。因此,学术自治从而衍生的管理自治不容忽视。在未来的法治发展过程中,司法统一成为必然。不断完善相关的行政法学和诉讼法学理论,引进国外“重要性理论”及“公共法人”概念,进而完善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合法法律依据,推进司法实践的进一步统一成为必然的趋势。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4).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7).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7).
[4]赵勇,赵永行.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行政主体法律地位[J].行政与法,2005,(11).
[5]申素平.论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的公法人地位[J].中国教育法制评论,2003,(00).
[6]马怀德.公务法人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00,(4).
[7]王绍光.多元与统——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6.
[8]刘艺.高校被诉引起的行政法思考[J].现代法学,2001,(2).
[9]郭道久.第三部门公共服务供给的“二重性”及发展方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2).
[10]任学强.论事业单位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资格——以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为参照[J].行政与法,2008,(7).
[11]何海波.司法判决中的正当程序原则[J].法学研究,2009,(1).
[12]戚建刚.论公益机构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J].法学,2003,(7).
[13]汪旭鹏,章红华.高校学生权益法律保护机制研究[J].湖南警察学院学报(原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6).
[14]王岩,密启娜,刘峰.学校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法律分析[J].当代法学,2002,(8).
[15]胡发明.我国高等学校性质的行政法分析[J].时代法学,2004,(3).
[16]World University Service,Academic Freedom 2:A Human R ights R eport,edited by John Daniel,Frederiekde Vlaming, NigelHartley,ManfredNowak,ZedBooksLtd.,1993,“Introduction”.
[17]袁明圣.解读高等学校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资格——以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为范本展开的分析[J].行政法学研究,2006,(2).
TheDefendant Qualification of Universitiesin the AdministrativeLitigation──TakingTianyongandGanluCasesasExamples
ZHAOZheng-qun,LIU Zhen-xiang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100)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rising number of universities as the defendant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universities as the defendant in judicial practice appears to have been recognized.However,whether Tian Yong case opened the first column,or other cases reconfirmed,the dispute in theory or practice have been still existed.Through a series of case analysi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Bulletin,in order to confirm the reasonable source of universities as the defendant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nd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At the same time,combined with foreign advanced experience and introduce it,in order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unity of justice in china.
universities;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the defendant qualification;public agency
D915.4
A
2095-1140(2013)05-0048-06
(责任编辑:天下溪)
2013-05-03
赵正群(1953-),男,辽宁沈阳人,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诉讼法、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刘珍香(1990-),女,江西九江人,南开大学法学院2012级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行政诉讼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