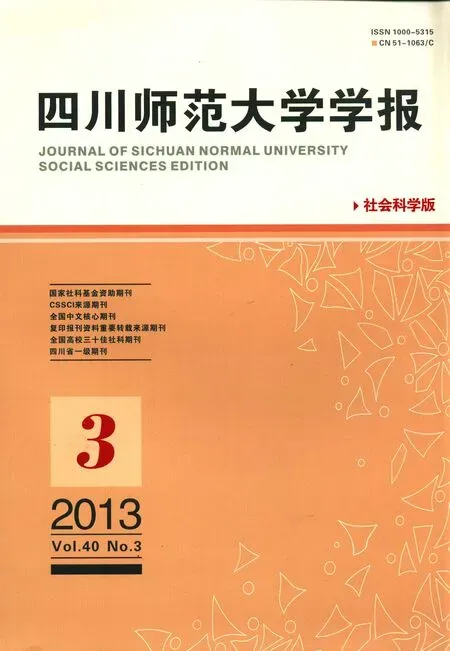当代美国土著文学中的自然观探析
——以斯科特·莫马迪的自然书写为例
秦 苏 珏
(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成都610101)
当代美国土著文学中的自然观探析
——以斯科特·莫马迪的自然书写为例
秦 苏 珏
(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成都610101)
文学创作中的自然描写在现代生态批评中已经凸显为意识形态的显性文化表征,以斯科特·莫马迪为代表的当代美国土著作家的自然观及其描述传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拥有的亲密关系,并指引他们在自然世界和传统叙事中追寻自己的文化身份。
美国土著文学;斯科特·莫马迪;自然观;自然书写;身份认同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曾提出,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历经了第一浪潮和第二浪潮,其中第一浪潮主要关注自然书写,“环境实际上就是指自然环境”[1]21,也就是对自然环境的书写;而在第二浪潮中更多涉及城市与自然的对话,学者们在生态文学研究中已经不仅仅将研究文本拘泥于对自然的书写,并且“不仅仅研究与地域相连的隐喻和概念在如何作用,而是不同的文本如何改变地域(反之亦然),以及不同地方或空间的形式如何限制或扩展我们对不同文本、方法、人群、文化和整个世界的理解”[2]2。在文学创作中非常普遍的对自然的描写在现代生态批评中已经凸显为意识形态的显性文化表征,不同的文化就必然产生不同的自然观,而不同的自然书写也必然观照出不同的文化特征。
作为当代美国土著作家的代表之一,西蒙·奥尔蒂斯(Simon Ortiz)表达了印第安传统文化与书写的关系,他直言写作对于自己来说就是“口述传统的延续,而口述传统就是对于某些形式、参与和主动的责任的表达”[3]203。他认为,“传统知识真正传达的就是责任,就是我们作为社会的团体和群落对生命之源——大地的责任的实践”[3]194。对于土著作家来说,他们承担着这种向族人传承人类责任感的使命,并且强调通过实践履行责任,“不仅在乎说了什么,还要实践并完成”[3]196。因此,他们在自然书写中既表达了对自然的关注,更多的则是通过书写传达责任,并敦促族人行使职责,成为有效的“大地的维护者”[3]197。在土著作家群中,这种将客观描写转化为主动参与的写作实践非常普遍,在许多当代美国土著代表作家的作品中,主人公都是在游离于族群的传统家园与现实的城市生存空间时陷入困境,又在对于自己的责任的重新认识和实践中获得新生。而这个过程,总是与土著人传统知识中一再传达的自然观紧密相连的。
一 印、白文化中自然观的异同
作为北美大地的外来入侵者,欧洲人很主观地认为,那里的土著居民并未在肥沃的美洲土地上耕作,只是以游牧为主,由此否认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自西方诸如洛克(Locke)等哲学家们对耕种土地和采集土地的人的区分,他们认为,“从道义上讲,只有前者才对土地拥有所有权,他们应该从那些不耕作土地的土著人手里拿回土地,耕种它,让它增值”[4]60。他们能肆无忌惮地利用先进的科学仪器测量美洲土地并加以瓜分,就在于对于土地的所有和责任只有利益的考量,而没有情感的参与,这也就“支持了西方人将自己入侵美洲看作是西方文明的使者,而将土著人看作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的观点”[4]60。这样的观点同样也证明了欧洲人长期保持的文明与生态的二元对立的观念,在实际社会活动中,则表现为将人与景观分离,运用自己的知识体系,例如现代形式的人本主义和所谓理性科学来阐述甚至强化人类理智对于自然的权威,而弱化了人对于自然,尤其是自然景观的心灵体验。随着机器时代和批量消费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城市的无限扩张,人类的生存空间在功能上似乎显得更加有效,但是人们生活的自然空间却成为了“无地区、无灵魂的新空间的牺牲品”[4]101。摒弃种族优越感、通过正确的政治姿态在生存空间中重新找回“家园”,成为一个当代人不得不面对的有待解决的难题。
斯科特·莫马迪(Scott Momaday)在《第一个美洲人眺望他的大地》一文中提到,土著人很早就知道大地与自己有着亲密、重要的联系,“一种蕴含着权利和责任的错综复杂的网状关系”[5]32。在他们的世界观中,自然成为核心,因为他们的信念就是大地是母亲,天空是父亲,这种对于自然世界的信任成为一种道德伦理上的表达和约束。而对于为什么土著人会有这样的信念,莫马迪认为,“也许这开始于对美的认识,领会到自然世界的美好”[5]33。在对于美好事物的领会和赞美中,人类懂得了信任和热爱,土著人在传说、仪式以及生活所用的器物、工具中将这种信任和热爱表达出来,并以一种有形、持续的方式传承着这种道德规范。
语言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载体是文艺美学研究者们广泛讨论的话题,其中,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和批判与诗歌的碰撞对于生态存在论美学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他在《“……人诗意地栖居……”》一文中曾以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歌为例,阐释了语言对于普通人和诗歌创作对于诗人的意义所在:“在我们人可以从自身而来一道付诸言说的所有允诺中,语言乃是最高的、处处都是第一位的允诺。语言首先并且最终地把我们唤向某个事情的本质。”[6]199诗人荷尔德林在诗歌中畅想人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通过语言表达出人与大地的本质关系就是委身于大地,“作诗并不飞越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毋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6]201。因此,“诗意地”并不表示一种假象,而是一种通过语言允诺、筑造的栖居之所,并能在一种恰当的关系中得以体现。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一文中也曾说过,“存在者并非首先和仅仅作为被意愿的东西存在,相反,就存在者存在而言,它本身便以意志之方式存在。只是作为被意求的东西,存在者才是在意志中具有自己的方式的意愿者”[7]291。因此,土著作家在现实的生存空间中寻求“家园”的过程,也就体现为他们通过文字表达愿望并能实现愿望的过程。土著文化传统教会他们理解了自然是一个整体意义上的存在,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植物存在的基础。这个基础对于一切都是同一的,因此诗人、小说家不过是作为存在的人通过语言表达着一种意求、一种允诺,同时也必须执守人与其他存在的同一关系。如果如荷尔德林在最后一首诗歌中所讲,人能够人性地栖居在大地上,那么“人的生活就是一种栖居生活”。在万物同一的理念中,这样的栖居就会如同他在《远景》一诗中所描绘的那样:
当人的栖居生活通向远方,
在那里,在那遥远的地方,葡萄季节闪闪发光,
那也是夏日空旷的田野,
森林显现,带着幽深的形象。
自然充满着时光的形象,
自然栖留,而时光飞速滑行,
这一切都来自完美;于是,高空的光芒
照耀人类,如同树旁花朵锦绣。[6]215
作为现代文明的重要表征,现代科技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在带给人类物质享受的同时,也让人类陷入了生态崩溃的险境。海德格尔在批评人对自然的统治的同时,也期待着通过“诗”,通过艺术美学从根源上影响导致生态危机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进行技术批判,“把诗和艺术视为存在之真理的澄明,把人的生存理解为诗意地栖居,即对天地人神共同构成的完整生存世界的看护”[8]161。而诗人所进行的创作就是要在空洞、危机四伏的流浪中“通过生命体验寻觅最合适的意象、词语,让对常人来说隐蔽陌生的本源通过熟悉的生活形象发出声音,或者说让在世俗生活中已经疏离本源而黯淡的事物、语言通过接近存在之本源而重新散发出光彩”[8]173。这个存在之本源就是大地,如果没有意象、语言等建立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大地就无法被人所理解,而文学家具有主动进入意义世界,向世人昭示本源并向其靠拢的可能性和责任。因此:
诗意地栖居不仅是爱护和保养自然之物,人作为自然生命的辅助者而不是征服、统治者登场,同时还意味着爱护和保养人自身,让人学会像自然之物一样自在地生存,这种“自然”并非抛弃文明和意义世界,而是努力使世界和大地的斗争通过存在而最终达到和谐,不会因为斗争而导致大地的彻底沉默。[8]176
只有以这样的思维重新审视人类与其他存在的关系,人类才能在获得审美体验的过程中同时获得生存之道,通过意义世界的建构发掘和实践存在的真谛。与欧洲哲学家们的这些理论思辨相并行的是当代土著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反复诠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传统文化力量的引导下,他们笔下的主人公都有着摆脱城市孤寂的灵魂之旅,通过回归本源——自然,理解自然以及一切存在物的生命力,在大草原、沙丘、荒漠的游历中进行着家园的审美,在与自然的交流中达成和谐。在语言所能建构的意义世界中,土著作家就如诗人荷尔德林一样,投射出了一束既能照耀人类,也能帮助人类赞赏与人类平等的“树旁的锦绣花朵”的智慧之光,只有在这样的审美历程中,人类才能最终解决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在满足物质需求支配一切的思维模式下,以西方文明和逐利心态为主导的自然之旅中呈现出的大多是征服者,而不是栖居者的真正的自然之旅,无法创造出感动人心的家园感和审美效果,而北美大草原的土著居民们作为真正的主人正在向世人昭示着这样的审美与回归。
二 莫马迪的自然书写与身份认同
从1980年开始,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推出了一套开放性的系列丛书《世界文学名著教学手册》,由美国著名学者肯尼思·M·罗默主编的《莫马迪的〈通向阴雨山的道路〉教学手册》在1988年作为第一部美国土著作家的代表作进入这一系列,在美国的教育界成为被广泛关注的对象。在这个被关注的过程中,莫马迪代表着在北美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三千多年、现在仅存的150万土著人向来自欧洲的白人主流文学传统展现了不一样的印第安的价值观和美学观,对主流经典文学的视角进行了挑战和修正,也对传统经典进行了扩充。正如罗默在该书的前言中所说,莫马迪的文学创作,尤其是《通向阴雨山的道路》(The Way to Rainy Mountain,1969)一书,向读者提供了一些另类的视角,“这些视角包括将大地视作形成个人身份认同和人类生态学的决定性因素;发现解决20世纪个体和社会问题的个人关系的概念——尤其是与祖先的关系;认可美国土著人关于神圣、美丽与和谐等观念的影响力;尊崇涵盖了整体、愉悦、惊叹和内部能量的口头叙述和表演性的风格”[9]Ⅸ。美国读者对这些视角的关注证明美国土著的观念不仅作为土著人的文化遗产指导着他们在现世的生存,也与非土著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为当代美国土著文艺复兴的领头人,莫马迪曾经多次在访谈中谈到他在创作中重复讲述某些主题、人物甚至内容的习惯,对此他向采访他的凯·博内蒂(Kay Bonetti)解释道:“我想我在讲述一个故事,它很长,我无法一次讲完……但它就是一个故事。”在另一次访谈中,他也曾对约瑟夫·布鲁查克(Joseph Bruchac)说:“我就关注着将这个故事讲下去,我打算坚持同样的主题,通过每次讲述传递开去。”[9]4这个他喜爱不断重复的故事就是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通往阴雨山的道路》就是追随基奥瓦祖先的足迹,在记忆和心灵深处再次踏上从蒙大拿到俄克拉荷马的迁移之路。在不断的重复叙述中,莫马迪坚信,“语言文字激发我们的想象,使我们自己、他人以及这片土地真正存在”[9]4。在与劳拉·科尔特利(Laura Coltelli)的访谈中,莫马迪一再强调土著口述传统与土地的重要关系,并坚定地表达了自己对大地之灵(the spirit of the land)的信仰。北美土著人作为这片大陆最初的主人,对它有几千年的体验和感受,对这片土地的感知对于土著人来说“就是一种对地域的精神投入,因为他有这样的体验,他就能用一种独特的方式看待自己,看待自己与大地的关系,他就能给自已一个明确的地域感和归属感”[10]91。在祖先的口述故事中,族人对土地的感知被不断加强;在当代作家的创作中,“令人牢记不忘的大地”(“remembered earth”)也总是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视角被反复展现,在对这片永久家园的颂扬声中,莫马迪的《通向阴雨山的道路》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成功之作。
莫马迪在作品的“开场白”中就明确表示这是一次在平原上跨越时空的历史之旅,“这次旅行在北方平原的边沿上开始了。这是一次历经许多代人,行程好几百英里的旅行”[11]3。这里记叙的旅行就是他的祖先基奥瓦人的迁徙之旅,在整个旅程之中,他们目睹了野牛群的消失,也“获得了马匹、大平原上的宗教以及一种对开阔土地的热爱与拥有。他们的游牧精神被释放出来了”[11]4。莫马迪在对先人的缅怀中,开始了一次历史的再叙,用得以保存的口述传统、传说中的画面、祖母的回忆以及自己作为当代作家所富有的想象力,在一种权利和责任的驱使下,再现了“一片无可比拟的景色、一段永远过去的时期,以及持久的人类的精神”[11]5。同时,《通向阴雨山的道路》“首先是一种‘思想’的历史”,基奥瓦人作为一个民族抱着对前途的美好想象开始了这段旅程,“他们敢于想象和确定自己是什么人”[11]4,而作者莫马迪通过文字再叙的这次旅程也无疑帮助他完成了确定自己的身份认同的创作初衷。
《通向阴雨山的道路》包括“开场白”、“序言”、“出发”、“继续前进”、“围拢”、“尾声”,外加开始和结尾的两首诗歌《源头》和《阴雨山公墓》。书中的第一个声部是基奥瓦人的古老传说,第二个声部中以莫马迪的祖母阿霍为代表的族人的历史叙述与古老传说相互交映,表达了族人对天与地的崇敬,以及对处于天地之间的基奥瓦人与宇宙的特殊关系的理解。例如在“序言”中,祖母讲述了传说中的七姐妹为逃避变成了熊的兄弟的追逐而被大树带到天上变成北斗七星的故事,“只要这一传说存在一天,基奥瓦人在夜空中就有一些亲属”[11]10,这解释了族人坚信的天地合一的宇宙观以及人与天地的亲缘关系,同时也解释了族人对自然神性的直观理解。
《通向阴雨山的道路》与其他白人作家的自然书写或欧洲传统的神话传说研究不同的地方主要体现在第三个声部,即莫马迪作为当代土著人的代表,如何结合传说、通过自然书写传达族人的文化内涵,在寂静中发出强音,在平凡中凸显智慧,从而对白人的强势文化进行反拨。如果将莫马迪的自然书写与白人的自然书写进行比较,其中的差异立刻突显。莫马迪认为,受欧洲文化传统熏陶的自然诗人大多专注于研究植物学、动物学和天文学,将自己与自然拉开距离,从而获得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距离美,而土著传统却认为“自然是个体生存的一部分,他生活于其中就如同我们生活于空气中一样”[12]85,刻意拉开距离不仅不会产生美感,还会产生令人窒息的疏离感,而这已经成为现代人普遍的病症。为了克服这种疏离感,土著人选择了回归传统,在精神的寻根之旅中,在土著文化的生发力中寻找药方。《通向阴雨山的道路》中的第三个声部就展现了当代土著人如何在故土上经历了一次这样的重生,他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力如何在传统故事和对先人的追忆中渐渐恢复,在大草原上或巨大、或微小的事物和景象中一步步增强。“只有根植于大地他才能坚守自己真正的身份认同”[13]14,因此,这次旅程必然就成为了作者的自我追寻之旅。
在故事的开始,“我”站在清晨的平原上,“想象力又苏醒过来了”,从这“天地万物开始的地方”[11]6踏上旅程。但是,莫马迪在启程阶段就强调,这是一次1500英里的“朝圣”,就如祖母能将“大陆内部的壮丽景色像回忆那样存留在她的血液里”,能讲述她从没见过的人与物,“我想要亲眼目睹一下她心眼里更为完整地看到的一切”[11]8。因此在这次心灵之旅中,莫马迪作为第三声部的讲述者,他所亲眼目睹的一切就代表着他心灵的变化,而紧随着他的描写的变化,就能发掘出这次旅程的真正意义。在“序言”的开始部分,“我”所看见的都是宏大的远景,“许多深邃的湖泊和幽深的林地、峡谷和瀑布的地区”,“大地延展开来,土地的界限退却下去。一丛丛树木,还有在远处吃草的动物,使视线伸向远方,并使人心头感到惊讶”[11]9。这样的描写不禁让人想起欧洲移民初来北美大陆时的情景,他们对这片广袤土地的惊讶之情应该就是如此吧。旅程之初的“我”在回归部落传统之前,对于展现在眼前的大地也只有这样的惊讶而已,并没有情感上的依托。但是“我”逐渐从基奥瓦人关于大地的古老传说中发现,他们对于自然谈论更多的不是贪婪的掠夺或占有,而总是赋予大自然中的事物以神性,就如与天上北斗七星相联系的山峰魔鬼塔的故事,总能让族人找到与自然相连的亲情。当北方的大山无法承载他们时,他们选择出发,来到了大草原。这时,通过“我”的心灵之眼所看到的山下的平原是“平静的、阳光灿烂的”[11]21,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东西——“牲口群、河流和小树林……全具有完整的生命”[11]21,而这才是“大地的实际情形”[11]21。此时,宏大的远景变为细致的静物写生,这种物理距离的改变也标志着情感的贴近,而这样的改变正是跟随着族人对这片土地的熟悉和适应而慢慢展开的。在“继续前进”和“围拢”部分,伴随传说中的制箭人、战士、水牛猎手、骏马的故事,“我”将目光转向了自己的先人——“我”在阴雨山公墓的墓石中走来走去,追忆起自己的父亲、祖母、老头儿切内、艺术家卡特林笔下挺拔而随和、风度优雅的基奥瓦男子汉肖像以及百岁女人科-山(Ko-sahn),他们将族人世代居住的大地融入了他们的血液,在他们谈及“太阳舞”、“泰米神药”时,言语中表达的已经是对于整个宇宙的理解,“这是她(科-山)对于自己与地球、太阳、月亮的生命之间关系最本质的表达”[14]49。同时,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想象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与读者“你”的对话,“我”在对族人的追忆中认识自己的同时也让“你”感受到了这种无法摆脱的约束力,将“我”和“你”奇妙地合而为一。莫马迪认为自己的心灵之眼看到的是“一个象征印第安世界中人与大地真正和谐的缩影”[14]37。他在谈到这次通向阴雨山的旅程的奇妙之处时说:“对于我的族人来说,这次旅程是在悲伤、失意中结束,但对于我却是一次非常愉快的经历,因为它充满了我的想象,成为一次满是愉悦的朝圣。”[15]3
也许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进行这样愉悦的朝圣,尽管寻根之旅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表现,这样的主题重复出现说明了不同地域、种族的人都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在有根难寻的情况下,这样的旅程就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对此,莫马迪认为寻根之旅并不根基于事实,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种“通过想象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的愿望,“需要对于自己的起源保持相当的神秘”[15]4。就像他在故土上、在传统故事、在历史叙述中重新找回自己一样,所有的人,不管是白人还是土著人,都能从像他这样的心灵之旅中认识到“他去往阴雨山的旅程是一次在自然世界和祖先的传统中对个人身份的追寻”[15]120。这是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中永远无法获得的认同,因此,这次成功的旅程应该对每一个现代人都具有启发意义。
莫马迪的自然书写与英美文学中最具代表性、备受推崇的亨利·戴维·梭罗相比,在对自然的尊崇上两者相差不大,但原动力却不尽相同。梭罗是在浪漫主义浪潮高涨的时候选择了远离社会,回归自然,追寻个人的纯洁,是一种对自然与野性的浪漫主义的感受和表达,是对自由和个人主义为核心精神的浪漫主义的精彩演绎,是对19世纪高速变化的社会伦理的一种暂时性的反叛。他放弃众人赞扬并认作成功的生活方式,独自走向瓦尔登湖时:
待发觉我的同镇同胞不大愿意在法院、教会或任何其他地方给我一个职位,我只得自己转向,比以往更加义无反顾地面向森林,那儿的山水草木对我更青睐些……我去瓦尔登湖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图个廉价的生活,也不是为了图个奢侈的生活,而是想去做些私人营生,在那里,各种麻烦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免得我因缺乏一点点公共常识和商业才能,加之生产规模又小,闹出一些伤心好笑的蠢事来,到头来一事无成。[17]12
他为此选择的短暂离开成为他对“发达的文明”犀利的实践性的批判,是对“心灵和大脑成了大粪似的肥田之物”[17]125的社会生活的逃离,只能无望地企盼着“如果可能——我决不愿生活在这个动荡的、歇斯底里的、混乱的、繁琐的19世纪中,宁愿站着、端坐着、深思着,任由这个19世纪逝去”[17]209。但是显然他无法端坐着避过整个19世纪,只能在短短两年后又回到了这个污秽的世界,而到来的20世纪的境况则更为恶劣。
原野成为以梭罗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者们遁世和隐居的理想家园是因为它具有“中断一个人的社会责任并激发起完全的自由感这样极具诱惑力的特点”[16]117,但这种假定的无政府状态下个人的自由以及与自然的和谐关联必然会被现实版的社会因素所打破。大自然绝不应该仅仅是个人追求自由而归隐的暂时的避难所,而应该是与整个人类和世上的其他存在一样、如空气般不可分离的长久的相容。跟随莫马迪在大草原上游历,读者更多地感受到人类与自然中的花、鸟、虫、兽以及太阳、星辰、山川、河流之间“相互拥有”的亲密关系,“这种相互拥有是指人类投身于大地,同时在最本质的经历中与大地合而为一”[12]80,而不仅仅是一个提供个人沉思、内省的安静、平和的外在物。只有在这样的相互拥有而不是占有中,人类才能真正具有审美的体验,也才能感受到与自然长久的和谐、自由的相容感。
[1]BUELL,Lawrence.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M]. 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5.
[2]DOBRIN,Sidney I.KELLER,Christopher J.“Why Writing Environments:An Introduction”[M]//Writin g Environment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5.
[3]DOBRIN,Sidney I.KELLER,Christopher J.“Writing the Native American Life:An Interview with Simon Ortiz”[M]// Writing Environ ment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5.
[4](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第2版.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MOMADAY,N.Scott.“A First American Views His Land”[M]//The Man Made of Words:Essays,Stories, Passage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
[6](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7](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8]王茜.生态文化的审美之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9]ROEMER,Kenneth M.“Preface to the Volume”[M]//Approaches to Teachin g Momaday’s The Way to Rain y Mountain.New York:MLA,1988.
[10]COLTELLI,Laura.Win ged Words:American In dian Writers Speak[M].Lincoln: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
[11](美)斯科特·莫马戴.通向阴雨山的道路[M].主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12]MOMADAY,N.Scott.“Native American Attitudes to the Environment”[M]//Ake Hultkrantz.Walter Holden Capps ed.Seeing with a Native Eye:Essays on Native American Religion.New York:Harper,1976.
[13]MOMADAY,N.Scott.“I Am Alive….”[M]//Jules B.Billard ed.The World of the American In dian.Washington D.C.: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1974.
[14]MOMADAY,N.Scott.“An American Land Ethic”[M]//The Man Made of Words:Essays,Stories,Passage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7.
[15]WOODARD,Charles L.Ancestral Voice:Conversations with N.Scott Momaday[M].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9.
[16]PAPVICH,J.Frank.“Journey into the Wilderness: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Way to Raining Mountain”[M]//Kenneth M.Roemer ed.Approaches to Teachin g Momaday’s The Way to Raining Mountain.New York:MLA,1988.
[17](美)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M].戴欢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A Study on the View of Na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QIN Su-jue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101,China)
The nature writing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has been a dominant cultural emblem of ideology in the modern ecocriticism.The world view and the description of nature of the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 writers,taking Scott Momaday as an example,reveal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of mutual belongings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nd guide them as well to pursue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natural world and the traditional narration.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Scott Momaday;view of nature;nature writing;identity
I712.07
A
1000-5315(2013)03-0126-06
[责任编辑:唐 普]
2012-07-20
本文系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生态批评视野中的当代美国土著小说研究”(项目批准号: 10YJC752032)的阶段性成果。
秦苏珏(1970—),女,江苏泰县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及西方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