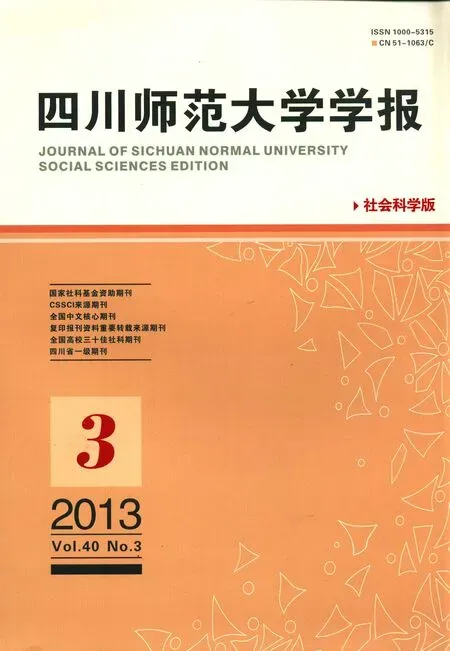历史与距离的探讨
郭 华 榕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1)
历史与距离的探讨
郭 华 榕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1)
我们探讨历史时遇到许多困难,因为我们与那些已经消失的人和事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例如地理距离、时间距离、社会发展水平差别、文献掌握与否等等。距离在探索者和历史之间发挥着广泛的作用:如冷却性,帮助我们客观地对待过去的人和事;隐匿性,造成永久之谜或搞乱真相;揭示性,揭露事实,哪怕是痛苦的真实。距离是可能克服的,我们应该努力防止绝对化,冷静地对待主导的潮流,并承认某些永久之谜。
距离;历史;历史文献;历史研究
历史,消失了的往昔。距离,出现于面前的沟壑。历史与距离,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让我们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做一初步的探讨,同时求教于读者和专家。
请看1855年9月2日的一封私人信函:“巴黎,这是一座奇妙的城市。”“你想像一下,将十个法兰克福连在一起,到处是开设着商家店铺的街道……然后在它的四周围,再加上十个比较安静的法兰克福。”这是德国的“铁血宰相”奥托·俾斯麦(Otto Bismarck)写给他的妻子约翰娜·普特卡默尔的家书片段①。那时,俾斯麦一家已经定居在波美拉尼亚的克涅普霍弗(Kniephof)的庄园,它位于奥得河口的东侧,离柏林约170公里,柏林距巴黎约1000公里,估计克涅普霍弗至巴黎大约1200公里之遥。
就德意志而言,法兰克福毫无疑问是一个大城市。当时,德意志尚未统一,它分裂为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萨克森、巴登等38个邦国和自由市②。全德的“同盟(Bund)议会”在法兰克福召开。俾斯麦是一个十分认真甚至刻板的人,他“一本正经地”“视察”巴黎的市区和郊区,踱步于香榭丽舍大街,观看工业宫与绘画展览,参加凡尔赛宫的舞会……。在巴黎的逗留和见闻,使他的心灵受到强烈冲击,法兰克福与巴黎之间差距之大,出乎他的意料,他在家书中表述出朴实的心情。
这一封家书给我们展露了什么?距离,三重意义的距离!(1)地理的距离,约1200公里;(2)当时法兰克福与巴黎的发展水平,进而德意志与法兰西的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差距);(3)俾斯麦不是世事不懂的、土头土脑的庄园主,他是德意志同盟议会的著名议员、普鲁士驻法兰克福的代表。他见过世面,例如曾访问英国。一个周末,当他在街上吹口哨时,曾遭到英国警察的呵斥,因为破坏了街道的安宁。他的思想中,原来对于法兰克福和巴黎的差距的估计,与实际状况之间存在着未曾想到的巨大距离。
俾斯麦还曾说:“德国中心地带发生的大事,100年后,才能传到罗斯托克。”此说法有所夸张,但信息难通乃是实情。法兰克福与罗斯托克相距约500公里。此外,俄国作家爱伦堡(Эринбург)曾说:俄国人模仿巴黎的时髦,年年学,年年迟了50年。这些都是距离的说明,地理的距离、信息的距离、商品运输的距离、人们追赶时髦所反映的距离……。距离和我们研究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距离,便难于真正认识历史——已经消失了的活生生的现状。
一 我们与历史的距离
距离是一种不依赖我们的实实在在的现象,我们每日每时皆有所感受,都在体验着它。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一)地理的距离
中国与欧洲相距千万里,来往不易,过去人员与信息的交流相当困难,现在也还有些困难,计算机也不是万能的。这是地理位置造成的距离。欧洲的面积大体相当于中国,法兰西的面积大体相当于四川省加重庆市。了解如此大面积地域的历史,并非易事。直至今日,作为法国的领导人,如国王、皇帝、总统、总理等,唯独路易十四一人骑着马走遍了法兰西③。这是法国各地区之间的距离。可见,开口法兰西,闭口欧罗巴,说来轻而易举,而真正了解它们则颇为不易。我们研究法国史时,必须面对两种地理的距离:中法之间的距离,法兰西各地区之间的距离,毕竟巴黎不等于法兰西。
地理的距离,人们曾用双脚和牲畜(马、牛、毛驴、骆驼)克服它,后来借助机械(马车、汽车、火车、轮船、飞机)走向遥远的地域。地理的距离,妨碍人们对于现状与历史的了解。它也不利于各国民众之间的交流,不利于世界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二)时间的距离
数年、数十年、百年千载……时间,总是横隔在历史与研究者的中间。人们常说,50年之内的人与事不是历史。但是,另有说法:现代史之后为“当代史”。无疑这是相对而言,如果档案禁止查阅、秘密文件仍旧封存、当事人物尚未撰写回忆录等等,恐怕真相,至少部分真相,很难大白于天下。一般而论,时间越久,了解难度越大。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流失了过去岁月的若干真实。
由于法国外交部档案的开放,克里木(Крым, Crimea,Crimée,另译克里米亚)战争的开端的秘密,才给人以清晰的印象与解释。从1853年2月起,俄国重臣缅希科夫(Меншиков)率领的使团已在君士坦丁堡“访问”,对奥斯曼帝国政府施加压力。那时,法英两国暗中设下圈套,一步一步地迫使缅希科夫暴露俄罗斯帝国对外扩张的意图。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斯特拉福(Stratfort)与法国驻那里的大使拉库尔(Lacour)、两国外交部秘密约定:首先,主动表示完全不了解俄国使团来到君士坦丁堡的目的;第二,宣称相信俄国方面的说明,即所谓该使团仅仅为了“圣地”与黑山国的事件而来;第三,法英与土耳其政府协调,证明土耳其与黑山的战事(在奥地利压力下)已经停止,素丹同意从那里撤回军队,同时他准备就“圣地”问题尽可能地做出让步。如此措施将造成缅希科夫的任务已经完成、他必须回国复命的局面,或者他将另外提出新的苛刻要求,从而暴露俄方的真实意图。5月5日,缅希科夫束手无策,发出最后通谍,强硬要求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结盟,素丹表示拒绝。7月3日,俄军队不宣而战地入侵,占领奥斯曼帝国所属的两公国(摩尔多瓦与瓦拉几亚)。10月4日,奥斯曼帝国被迫对俄宣战,俄国迟至11月1日才对奥斯曼帝国宣战。1854年2月9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威胁法国,他在给拿破仑三世的信函中宣称:“1854年的俄国,将如同1812年那样显示自已的力量。”④众所周知,1812年俄国打败了法国。1854年3月27、29日,法英两国对俄国宣战。
当时,俄国官方完全不知晓法英之间的上述密谋,俄国使团没头没脑地落入了法英外交当局所设立的圈套,国际舆论界也不了解内情。数十年后,档案开放,时间造成的距离(即不了解)才渐渐地失去它的作用。
(三)社会发展的距离
欧洲各国社会发展的速度与水平历来不曾一致,始终无法同步前进。同时,一个国家内的各个地区也基本如此。19世纪中期的克里木战争,充分暴露了英法与俄国之间社会、经济、交通、军事的发展水平的悬殊差别。
克里木战争是了解距离与历史的一个范例。1855年9月8日,俄军吞下战败苦果,被迫放弃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俄国作家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当时任炮兵军官,曾目击俄军的撤退:“塞瓦斯托波尔的(俄军)队伍像动荡不安的黑夜里的大海,时而汇合、时而散开,全体人马都小心谨慎地蠕动着,沿着海湾附近的一座桥向北街移动,穿过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缓慢地离开这个浸透着他们鲜血的地方。”⑤
参与撤退的另一个军官的记载:1855年9月8日夜,俄军通过一座长桥,跨越海湾,撤回北岸,放弃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苏泊涅夫(Супонев)如此继续回忆:“俄军悄悄地行动。难于描绘此时塞瓦斯托波尔守卫者们的心情”,“许多人的眼眶里转动着泪水……老水兵们哭得如同孩子一般”,“炮弹在渡桥两侧爆炸,夜空中闪烁着星星,房屋与工事在明亮的火光中燃烧,火光使星星黯然失色……整个队伍静静地、无声无息地、互不拥挤地走去”⑥,这也是关于俄军战败和撤走的记载。
此次战争中,法国主要出动陆军,英国主要派遣海军,它们的联合兵力战胜了俄罗斯帝国的军队。俄军失败的原因之一,为装备的落后:旧的帆舰、无来复线的滑膛枪、善于正步行进而不会很好利用地形作战的步兵。法英远征军依靠蒸汽机驱动的舰队、舰上装有螺旋桨而行动迅速、先进的来复枪、射程很远的大炮、供应充足的军火,工业革命的成果给英法联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战争双方技术装备的差距显而易见。参加了战斗的俄国中尉列斯利(Лесли)在给他姐姐的信中表示:“我们射击一次,法国人向我们射击十次。我们的工厂无力生产如此大量的弹药……此外,大车运输远不如轮船运输。”⑦上述亲历者们的“证词”,无需多加解释。
论地理条件,英法远离克里木半岛,而克里木的北方就是俄罗斯帝国的大地。但是,论交通运输方式、军事技术的水平,交战双方差别太大,这是社会发展造成的距离的一种表现。
(四)历史文献的距离
历史文献的有无,十分重要。我们从事历史研究者,无法凭空臆造。能否读到档案、文献与专著等等,能否掌握可靠的信息,对于了解历史真相的意义不言而喻。
1852—1870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对于罗马教廷的政策,在许多著述中未见清楚说明。考虑到大多数法国人程度不同地信仰天主教,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过去,由于未曾找到档案,真实情况如何?实在难于把握!
有关政策变化的证明,一直保存在“梵蒂冈秘密档案馆”(Archivio Segreto Vaticano)内。一位外国同行告诉笔者,从前她请求进入这个秘密档案馆查阅档案时甚为困难,必须写信表示“跪在教皇面前”,恳求恩准。1994年,笔者以欧洲大学教授的身份进馆阅读档案时,只需办理通常的入馆手续。有关档案揭露了上述问题的实况。
1856年4月4日,拿破仑三世致函教皇庇护九世,明确表示:“照顾天主教教会,这是我最为严肃关注的事务。”⑧从1859年开始,为了抗衡另一个大国奥地利帝国,法国支持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因而改变了对罗马教廷的政策,因为后者奉行不利于意大利统一的方针。1859年,经拿破仑三世的授意,法国出版《教皇与会议》一书,指出教皇国的“领地不必十分广阔”,它“有限而够用”便已足矣;法国方面认为:“土地越小,君权越大!”(Plus le territoire sera petit,plus le souverain sera grand!)⑨1860年2月28日,拿破仑三世致函教皇:“在我的心中,一直蕴藏着两种情感,即支持意大利的独立自主和维护教皇的世俗权力。”⑩事实上,这并非拿破仑三世个人随心所欲地变更国策,改弦易辙是出自法国的利益,即反对宿敌奥地利与支持意大利独立的需要。
法国著名的奥尔良主教迪潘卢(Dupanloup)的例子,也能表明历史文献与距离的重要。此人的政治思想具有天主教主义的色彩,人们常说他主张“主教会议”(公会议)的权威高于教皇、反对教皇的“永无谬误”,较多强调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学术界虽有不同说法,但是影响甚小。珍藏于“梵蒂冈圣廷档案馆”(Vaticano Archivio della Sacra Congregazione)的一封亲笔书信,即1869年7月10日迪潘卢的一封信函,说明了真相。在信中,迪潘卢对教廷的一位高官表示:“我刚刚收到教皇的演说词(指1869—1870年梵蒂冈第一届主教会议前关于永无谬误的演说),这是对于主教们的答复”,“我自愿跪在教皇的脚下,表示我的激动、感谢与仰慕之情”,“教皇……真是非凡无比”⑪!这封亲笔信不容置疑是一份珍贵的记录。此前,该信函未见公布于书刊。
另一档案使笔者感到震惊!1814年3月18日J.B.A.先生的一份手写的家庭记录,记载了奥地利帝国的军队在法国南部波若莱(Beaujolais)地区的利马村(Limas)的掠夺行径。J.B.A.先生的私人档案记载了奥地利军队对于他的家庭造成的损失:“公牛2头、母牛5头、肥肉4公担(400公斤)、母鸡36只、车辆5辆、干草100公担、葡萄酒26件(约5850升)、暖床器1个、大勺子1个、牛奶桶16个、大理石桌1个、床头柜1个、羊毛毯10件、男衬衣84件、女衬衣30件、女裙7条、童裙3条、玻璃杯20个、被单与床单60件、打碎玻璃2块、损坏梳妆台1个……”⑫当时,拿破仑一世及其法军战败,反法联军中的奥地利军队入侵该地区,他们从这一个家庭抢走了总共约1000件物品。如果未见上述史料,难于具体了解反法联军掠夺法国百姓的罪行。私人提供的记录,同样可以帮助我们“跨越”为时久远的历史距离。
文献的公布也能够使我们克服距离,了解往日的法国历史。例如古日女士(Olympe de Gouges)的《妇女权利宣言》。过去,笔者仅仅了解1789年8月6日的《人权宣言》,无意识地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法国大革命中女性的积极活动。1981年,笔者到了法国后才“发现”:1791年9月,《妇女与女公民的权利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a femme et de la citoyenne)已发表,它的作者为奥林普·德·古日。大革命开始时,她积极支持革命。1792年,她拥护共和制度,但是反对处死国王。她的思想接近吉伦特派的政治观点,于1793年11月3日被山岳派专政处决。《妇女权利宣言》大力主张“妇女生而自由,并与男子权利平等”,“权利为自由、所有权、安全,尤其是反抗压迫”⑬。毕竟,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不仅是男人制造的革命,吉伦特派的“灵魂”罗兰夫人、德·古日等女性也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在研究中,借助《妇女权利宣言》等文献,可能克服对于女性缺乏了解的距离,认识到这一次革命乃是男女老少一同参加的重大事件。
历史文献的距离,即信息的距离。研究者对于历史文献应进行认真查阅与考证核实,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
(五)语言的距离
懂一门外语(多为英语)搞世界史(外国史),现在已经比较普遍。但是,就探索欧洲史、非洲史、亚洲史而言,仍有较大的难度。欧洲史的真正深入研究,需要知道英、法、德、俄、意、西以及北欧等语言文字。
这从一个例子中可以汲取教训。如果仅仅阅读中文翻译的普鲁东(Proudhon)著作,便以为“所有权就是盗窃!”这一警句是他于1840年首先提出,他曾在许多场合强调自己的首创权。然而,在普鲁东之前60年,布里索(Brissot)在《关于所有权与自然界和社会中盗窃的哲学探讨》(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 droit de propriétéet sur le vol dans la nature et dans la société)一书中已经明确提出这一名句名言:“所有权即盗窃!”(la propriété,c’est le vol!)⑭1780年,该书在巴黎公开出版,当时为欧洲学术界所知晓。
关于“长时段”(la longue durée)这一名词,又是一例。前些年,人们以为专有名词“长时段”是由年鉴学派首先提出的。如布罗代尔(Braudel)的著作《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La longue durée.Paris,1958)。实际上,雷斯枢机主教(Retz,1613—1679)早已使用“长时段”这一词语,请见1717年巴黎出版的他的《回忆录》(Mémoires)⑮。此人的政治思想属于开明的绝对主义,他否定专制主义,同时主张变革求新。
上述数例足以说明:每当涉及事物或专有名词的首创权时,必须小心谨慎,认真核实,并且考虑后来可能另有发现。笔者不懂德语,肯定对于德国史的许多问题只能知道皮毛,举出“长时段”这一例子,仅仅希望对于流行的东西、人云亦云的说法,如谁人首创XX等,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为克服有关的距离留有余地。
(六)国际史学局限性的距离
一定的历史时期,国际史学研究中通常存在某些占据强势的学派、潮流或研究的重点。过去,曾较多研究政治历史;后来,注重经济、日常生活、文化、心态;现在,法国史学相对地“平淡无奇”,年鉴学派已经明显弱化与失去力量。我们企盼法国史学的新的“雄起”!潮起潮落,派别兴衰,史学探索者的生死更替……这些都是自然现象,不必杞人忧天!
在某一种潮流汹涌澎湃的年代,另一些学派、问题、观点、事件与人物通常遭到贬损、忽视。他们(它们)处于弱势,但是还在延续,不显山不露水地存在着。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其实更应该习惯于后浪推前浪、斗转星移,这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的景象。史学探索中,等待,有时既是身处弱势时的一种求生良策,也是蓄芳待来年掀起新浪潮的准备。
关于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学界已有许多研究,1940—1970年的“西方文字书目”已汇集和发表⑯。研究这一次战争的目的,在于探讨当时法英俄奥等大国对于欧洲优势和中近东的争夺。正是从这个理由出发,国际史学忽略了1854年的“波罗的海之战”。如果法英联军夺取博马松德(Bomarsund)要塞,则可以控制波罗的海,进而严重威胁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此举具有战略意义:可能直接以陆海军队扑向敌国的心脏。1854年8月8日,法军在英国海军的支持下,攻克了博马松德要塞,俄国受到巨大震撼。后来,由于冬天将临,俄军死守芬兰湾,法英军队只得撤离。就威胁俄国心脏地区而言,在波罗的海夺取博马松德要塞的军事与政治意义,明显超过在克里木半岛上攻克塞瓦斯托波尔。忽略波罗的海之战的重要性,原因在于缺乏一个欧洲优势的全局观点,对于欧洲的核心地区的认识不够充分,并且受到“圣地”之争、克里木战争军事水平甚高的过多影响⑰。
国际史学经常为国际局势或国家权势所左右,它的“兴趣”相对地、甚至过分地集中于某些热点,克里木战争因此成为众人关注的研究课题。同时,人们便将热点(克里木地区)之外的课题,视作不值得一顾的历史枝节。我们如果从另一方面观察,恰恰由这里爆出冷门——博马松德的陷落,进而可能突破近代历史研究中的已定的阵势,“撕裂”现存的近代战争史的通俗版的“马赛克图案”,克服国际史学偏颇造成的缺乏了解的距离。
(七)社会环境容许与否的距离
研究历史者生活在社会之中,不论主观愿望如何,他们无法脱离所在的社会大环境,包括国家与国际的大环境。法兰西有着颇具典型性的例子。
在法国,由于第二帝国(1852—1870)的统治形式,尤其帝国前期的“专制帝国”政策,以及1870年对德战争失败后的投降割地与赔款,另一方面由于共和派抨击帝制的大力宣传以及对于拿破仑三世的肆意丑化……这一切导致法国社会舆论在很长时间内简单地否定第二帝国的历史⑱。那时,法国的有关历史研究者们处境十分困难。人们对于19世纪50—60年代法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巴黎等大城市的建设、帝国政治体制逐渐向议会机制演变等等,通常无法正面对待。那时,谁敢于公开表示肯定或部分肯定第二帝国,必然遭到遣责……于是,形成了一种传统舆论的桎梏、社会上主导潮流之下的常见的思想禁锢。
由于上述情况,共和主义政治倾向对于史学研究产生了若干妨碍作用。同时,因为人们公认共和主义的思想与政治体制具有进步性,它的负作用便难于得到重视。法国史学、欧洲史学研究中的单一倾向性,对于主流的唯马首是瞻的趋势,已是众所周知、司空见惯的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投降,法国成为战胜国并且收回了阿尔萨斯和洛林……此后,法国社会上对于第二帝国与拿破仑三世的攻击贬损逐渐衰减,档案陆续开放,研究第二帝国的社会环境不断改善。即使这样,对于第二帝国的某种兴趣或某些肯定,仍旧需要一定的胆量。直至1981年,笔者在巴黎时,还多次听到同行们的如下言论:你研究第二帝国?好勇敢!不容易啊!
20世纪30年代,随着社会环境的良性改善,对于第二帝国历史研究的冲击已经开始出现。1930年,让·莫然(Jean Maurain)出版专著《第二帝国的教会政策》(La politique ecclésiastique du Secon d Empire),书中的陈述比较客观,引人注目。1933年,波尔·盖里奥(Paul Guériot)出版《拿破仑三世》(NapoléonⅢ),作者竭力为拿破仑三世恢复名誉,字里行间溢散出波拿巴派的学术气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述新的趋势进一步加强。1950年,马赛尔·布朗沙尔(Marcel Blanchard)的学术著作《第二帝国》(Le Secon d Em pire)问世,论述比较全面与客观,至今受到师生们的欢迎。1952年,路易·日拉尔(Louis Girard)的博士论文《第二帝国时期公共工程政策》(La Politique des travaux publics sous le Secon d Empire)问世,主要涉及内政⑲。1954年,夏尔·普塔(Charles Pouthas)撰写的《第二帝国的政治史》(Histoire politique du Second Empire)出版,作者比较注意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1955年,皮耶尔·吉拉尔(Pierre Guiral)出版的博士论文《普雷沃-帕腊多尔, 1829—1870年,第二帝国时期一位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与行动》(Prévot-Paradol,1829—1870,Pensée et action d’un libéral sous le Secon d Empire),主要研究内政尤其当时报刊的历史。1956年,克洛德·佛朗(Claude Fohlen)出版的博士论文《第二帝国时期的纺织工业》(L’In dustrie texille au temps du Secon d Empire),得到同行们的肯定。1973年,阿兰·普勒西(Alain Plessis)撰写的《从帝国欢庆至公社战士墙》(De la fête impériale au mur des fédérés,1852-1871)一书出版,获得较好的评价⑳。
上述种种著作各具优缺点,彼此也有争论,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不曾简单地否定第二帝国、谩骂拿破仑三世,而是表示程度不同的肯定,并且进行了不同的批评。数十年之内,法国史学界逐渐地改变对于第二帝国的看法,有关史学研究获得了进步。如果法国的社会环境不发生巨大变化,第二帝国史学研究恐怕还在受到沉重的政治压力、舆论压力。
(八)个人努力与否的距离
档案、文献、回忆录、专著……皆为研究者人手可及的东西。研究者必须努力了解已开放的档案、已公布的文献、出版了的回忆录和专著,对此义不容辞,这是职业的道德。这方面可举三个例子。
1799年雾月十八日政变之前,西哀耶斯(Sieyès)与拿破仑·波拿巴将军等人准备政变。众所周知,西哀耶斯曾说:“我们需要一柄剑,由谁来佩带它呢?”此处,实指拿破仑·波拿巴将军。后半句的出处,可见莫卢瓦(AndréMaurois)的《拿破仑画传》㉑。此书,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早在40余年前已经收藏和提供借阅,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借来阅读而已。塔尔列(Tapлe)在他的《拿破仑传》(俄文版, cтp.75)里只引用了西哀耶斯的前半句话。如果仅仅满足于早年在大学里得到的知识,必然落后于时代,并且不断地重复陈词旧调。
关于米拉波(Mirabeau),他是法国大革命开始阶段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卷1,第943页)指出:米拉波是“革命的狮子”。如果不想阅读或不仔细阅读《资本论》的有关内容,便不可能了解这个令人信服的评价。
关于拿破仑三世及其头顶上的老鹰。过去,史学界有人反复描绘:拿破仑三世的头颅上空,常有老鹰盘旋。为什么?因为他在帽子里、头顶上安放了香肠,而香肠变质便产生臭味,此时老鹰就闻之而来在他的头上盘旋。真相如何?早在百多年前,法国史学界已经取得共识:这种说法并无事实根据,它传播的用意在于抨击拿破仑三世。实际上,这一切可能吗?腊肠变质溶化,脏水从头上流下,首先进入脖颈……正常的人能够长久忍受吗?此传说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那时法国共和主义的党派、史学与文学为了批判帝国制度而竭力丑化拿破仑三世。法国史书早已不再重复这种传说,我们也不应继续转播,而应及时了解法国史学研究的发展状况㉒。
历史远离探索者,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必须勇敢地、坦然地接受。当我们进行探讨时,需要具体地弄清每一次所面临的是何种距离,以便尽力去克服。距离并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研究者在努力探索方面所保持的那种距离!主观上的自我满足,可能使那种距离无限期地存在。
二 距离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显而易见,距离发挥着作用。上文似乎给人以距离较多负面的印象,其实不然,它的作用相当广泛。距离的主要价值体现于下述三个方面:冷却、隐匿、揭示。
(一)距离的冷却性
时间、地理、国籍、派系、家族、个人等因素造成的距离,可能具有积极作用。这些距离使研究者避免成为当事人,他与当事人并无直接关系,不是当事人家族的成员或同一国籍、民族、派别,即他无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得失,从而可以比较冷静地寻找史料,比较客观地面对各种学术解释与政治色彩的证词,可能坦然地得出结论,而不必考虑与他人、党派、国家等的复杂关系。
在法国大革命临近200周年之际,1989年以前,山岳派专政已经受到许多批评,档案早已开放(例如“陈情书”尚存6万余份),有关研究相当深入,吉伦特派终于得到平反。1793年的惨案,接近1989年才结束。
1793年10月31日,布里索等20余名吉伦特派议员,死于断头台;临刑前,他们高唱《马赛曲》(稍作改动)。逮捕、审讯与判决时强加给他们的“罪行”为搞“联邦主义”阴谋活动,即反对大革命所坚持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一基本原则。拉马丁(Lamartine)曾以文学的笔调,描写吉伦特派受难之前凄惨的一夜。吉伦特派是大革命的一批领导人。法国史学已经公认他们从来不是“联邦主义者”,仅仅比佐(Buzot)一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偶尔表示倾向于“联邦式政权”。孔多塞(Condorcet)提出的“宪法草案”的第一条为“共和国统一与不可分割”,国民公会曾表决通过了这一条。当时的山岳派、后来的“亲山岳派的史学”(左翼史学的一部分)对于指责吉伦特派为联邦主义者负有主要责任㉓。百多年前的沉冤,终于因为时间的推移、档案的开放、研究者的冷静而昭雪于天下。
笔者曾应邀去德国讲学,内容包括法德关系等。他们认为我是中国人,不亲法也不亲德,能够比较客观看待例如1870年的法德战争。笔者回答问题时,指出法德双方虽然不同,皆负有责任,当时听众们报以掌声。这也是距离带来的好处,使人不会轻易头脑发热。
恩格斯在评论法国1851年12月2日政变时,表示对于路易-拿破仑这个人物,可以发表各种意见,包括否定的意见,但是“不应该加入……骂街式的合唱”㉔。史学研究中的各种评判、众说纷纭,不论过去的或当今的争论,都是自然的、传统的、普遍接受的实际。骂街式的合唱,则出自私人、家族、派别,甚至国别的种种利益,这是情感的放纵。情感浸润越多,脱离真实越远,自我制造的距离越大。如此状况对于距离的冷却性的发挥,将产生阻碍作用。
不卷入“骂街式的合唱”,便可能让距离的冷却性发挥威力。它使后人冷静地治史,如同法国史学家米什莱(Michelet)所说“复活”历史真实,或“完整生活的恢复”(résurrection de la vie intégrale)。“复活”,恐怕较多属于基本上的“复活”,这已是相当艰难的工作!
(二)距离的隐匿性
由于距离的存在,后人或研究者难于了解过去的事件或人物的真像,此种隐匿性可以表现为:永久之迷与搞乱真相。
1.永久之迷
不仅法兰西历史如此,它是一种世界现象。产生此类状况的原因在于:当事者高超地隐埋了各种痕迹,有关档案的流失,参与者或知情人未撰写或尚未出版回忆录式的文字,文献遭到天灾人祸的损毁,因时间过久与多次继承转手保存而失传。此外,不同文献提供了多种说法,它们互相矛盾,后人难于甄别。总之,确凿证据无处可寻,判断无据可依。永久之迷是历史身上的大大小小的伤痕,或许同时它们可能使探索者眼前出现飘渺虚无的幻景,它们始终蕴藏着诱惑力。
例如,拿破仑三世(1808-1873)的出生问题,他的生身父亲是谁?法国若干学者竭力计算他的父亲老路易·波拿巴(1778—1846,拿破仑一世之弟,荷兰国王)与母亲会面的日期㉕。第二帝国后期、第三共和国时期,上述问题对于波拿巴派和法国政坛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争论不休。随着时间的推移,共和制度在法兰西的确立,直接利益相关者与派别陆续退离政治搏击的前台,争论逐渐失去重要的、现实的政治价值。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个次要问题,无论如何拿破仑三世曾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第二帝国的皇帝,他是一个历史人物,是曾经领导法兰西的国家领导人。同时,这个问题依旧是个迷。争论,无形之中实际上主要留给了波拿巴家族,对于他们这是一个大难题。家族继承的要害之一是继位者的血统的纯正与可靠,否则便是旁人篡权、政权易手、江山变色。
永久之谜的又一例:1851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总统政变时的“卢比孔”计划(Rubicon)㉖。该年12月1日深夜,爱丽舍宫中绝大多数地方已经熄灯。23时,路易-拿破仑等6人在他的总统办公室内开会,决定次日政变的最后措施。此时,路易-拿破仑拿出一个文件夹,上面用兰色铅笔写着“卢比孔”,其中包括已准备就绪的命令、声明等等。12月2日3时,政变开始,军队迅速行动,完成了政变。但是,这个“卢比孔”文件夹却消失了,后来也无法找到,至今仍然如石沉大海㉗。当代,还有法国学者关注这个问题。虽然,政变的基本事实早已清楚,但是找到“卢比孔”文件夹依旧是历史研究的需要。
一个政治人物值得提及:克雷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他是法国著名的总理、倒阁能手,绰号“老虎”。他出生于法国西部的南特市,属于纯旺代地方的血统。但是,他生而具有“蒙古人的脸形”、黄皮肤、带蒙古褶的眼睛与高高的颧骨。他的姐姐曾说:他可能为公元5世纪时入侵高卢和定居于旺代地区的“蛮族”的后裔。他是亚洲人种因素与欧洲人种因素的交融的结果吗?谁能解答?寻找他的DNA?只有翘首以待。
还有那个著名的“铁面人”(Masque de fer),他究竟是谁?此人于1681年被囚于皮涅罗尔国家监狱(Pignerol,今在意大利都灵市的西南,当时属于法国),1698年转入巴黎的巴士底狱,1703年死于狱中。有关探索的假设多达十数种,其中比较可能者如“铁面人”为路易十四的一个大臣、某个仆人,事实上,至今仍然无法确定该囚犯的真实身份。
距离的隐匿性造成了永久之迷,这是一种“无底洞”,它增添了人们对于了解历史的兴趣。幸好,法国历史中,重大事件的基本脉络、重要人物的基本情况无法隐匿,而且是清楚的。
2.搞乱真象
这也是隐匿性的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出现类似事例。1940年6月14日,德军占领巴黎。7月10日,维希卖国政府成立。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谁最早公开发出“抵抗”的号召?
二次大战后,某些著述宣称:“1940年7月10日”在法国国内的某个政党首先“发出宣言(《告法国人民书》)……号召建立一条为法兰西的自由和复兴而斗争的战线”,该书作者竟然宣称:后来“7月18日,戴高乐将军才在伦敦广播,并且仅仅说明‘我是戴高乐将军,现在在伦敦……请法国的士兵和军官们……尽快和我联系’”。1962年出版的未见署名的《法国共产党史》(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一书,披露“1940年7月10日的《告法国人民书》不曾表示反对德国占领”,认为“该文件实为法国解放后伪造的”。那么,号召抵抗德国侵略的真相究竟如何?
请看那时的事实,也即国际社会已经公认的事实:戴高乐将军于1940年6月18日在伦敦发表《号召书》:“法兰西抵抗的火焰决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19日,他又发表声明:“所有掌握武器的法国人的绝对的神圣责任,就是继续抵抗!”㉘
数十年来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有关戴高乐首先号召抵抗的事实遭到隐藏,从而混淆了视听,功过难辨。然而,法国近现代历史中,重大的秘密可以隐藏数十年、百余年,但是很难匿迹于永久。就此类问题而言,大多数情况下,隐匿仅具有相对性,而真相早晚可能暴露于公众的眼前。
(三)距离的揭示性
若干人与事在当时的条件下,或在随后的一定时间内,不同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以讹传讹,使谎言变成了“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是当事人、利益不相关的研究者,有可能发现充足的事实、数字、回忆……,对历史进行深入的探索,从而比较客观地揭示出真相,甚至总结经验教训。经过了时间的磨炼,真实面目终于出现。
坊间书刊习以为常地重复: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说“朕即国家!”(L’Etat,c’est moi!)㉙实际上,法国史学早已否认了这是一句出自路易十四口中的名言。无疑,我们可以看到,路易十四的头脑中存在着此种政治思想。例如,1661年3月9日,辅佐他的大臣马扎然去世,其他的大臣们发问:“今后,有事时,我们应该找谁请示?”路易十四当即回答:“应该找我!”不久,他宣布:“国王是绝对的主人”,“法出于我”,“永远不要首相”㉚。路易十四确有这些思想,但是未讲上述流传至今的那一句话语。
关于路易十五,过去不少书刊认为他说了“在我们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法兰西因此迅速走向衰败。尽管对于路易十五的统治和个人,可以发表各种或褒或贬的意见,但是,法国史学至今仍然无法证明这一句话确实由这个国王所讲。数十年来,法国的史学著述已经不再提及这一段话了。阿兰·德戈(Alain Decaux)等的著作说明:“人们认为他(路易十五)说了‘在我之后,将洪水泛滥!’”(Après moi le déluge!)㉛实际上,1774年,路易十五临终时,他看到了自己死后王位继承将面临困难的问题:他的儿子路易已于1765年去世,孙子为后来即位的路易十六、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他们当时年纪不大,路易十六刚刚20岁,此外王后玛丽亚-列欣斯卡(Marie-Leczinska)还生了8个女儿。研究者有权批判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但是不该扭曲原来的话语,将坊间流传的名言强加于古人。
当代,开放的档案和出版的专著(借助档案撰写)揭示出法国大革命期间西部滥杀无辜的暴行,这又是时间的距离在发挥作用。1794年初,蒂罗(Turreau)将军率领拥护革命的军队出征旺代(Vendée)地区,目的在于恢复秩序。2月28日,他们攻占吕克斯村(Lucs),共处死564人,其中110人为未满7岁的儿童,包括1岁以下的婴儿7人,后者当中未满月的婴儿2人。未满1岁的男女儿童死难者的姓名:古安(Pierre Gouin)1岁,马丁(Véronique Martin)1岁,米尼昂(Jean Mignen)1岁,爱利奥(Thomas Airiau)10个月,达维奥(Marie Daviaud)1个月,贝利奥(Etienne Beriau)15天,米诺(Luise Minaud)15天㉜。
距离的存在与它的克服,使我们了解到:这些婴儿与幼童,因“株连九族”而骤然丧命。他们对于当地政局的变化毫无责任,却遭到了残杀!这也是法国近代历史的内容,它在档案馆的深处存放了许多时年,终于为世人所知晓。
山岳派专政(雅各宾专政)时期,总共处死了多少人?一直为史学界所关注,虽然分歧继续存在,终究出现了多种数字的记载。如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可能是七八十万人,一般认为约30万人,其中“宣判”处以死刑者约1.6—4万人,另有“未经宣判”而处死者近4万人;判处死刑者的社会成分:84%为第三等级(25%资产者、28%农民、31%无套裤汉), 8.5%为贵族,6.5%为僧侣;他们的罪名分别为:叛乱与背叛78%,“思想上的犯罪行为”(包括“联邦主义”)19%,贪污等经济犯罪10%㉝。第三等级揭竿而起,推翻了封建专制,不料自己成为超激进的政权以及派别的主要打击对象!当时,被处死的各类各派的领头人、骨干及其亲属等,多数是无辜的牺牲者。这些人中不仅包括被罗伯斯比尔等处决的“敌人”,也包括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库东这些人。法国大革命造成了若干教训,例如无休止的内斗、日益严重的极端化、鼓动与滥用暴力等政治“疾病”,使法兰西受到了重创!
距离对于人类历史,不可避免地发挥着它的正面与负面作用,给后人提供了经验教训。当代,如果仔细阅读、观察、感受法国人关于大革命的著述、展览、发言等,仍然可以看到各种学派的见解与分歧,但是人们不再如同过去那样怒气冲冲、恶言相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群体心态已经明显地减弱。大革命渐去渐远了,距离好似流水,冲淡了如同马蒂耶(Mathiez)等那样专业化的超强度的激情。
距离的揭示性,既可能帮助研究者找到可靠的事实,也可能帮助他们稳定情绪,以理性超过情感的心态去面对历史,认识哪怕令人十分痛苦的真实。
三 距离的克服
恩师索布尔教授(Albert Soboul,1914-1982)曾嘱咐笔者:“应该忠于历史科学!”这是30年前的教诲!笔者认识到,努力克服距离是我们历史探索者所肩负的重任。
(一)克服距离的途径
法国的往昔与当代之间存在着长短不一的距离,这就是她的历史。为了认真研究法国的历史,必须设法克服距离。我们的态度是:耐心等待与积极争取。等待有关档案的开放、文献的公布、回忆录的问世、学术专著的出版;一旦可能时,自己主动地求索,设法办好有关手续,查找当时的档案与文献,掌握必要的语言,经常与同行们交流,诚恳求教于人。历史人物不会穿过千百年的岁月,返回人间,来到我们的面前握手相识。过去的事件不会跨越千百年的时局,重现于社会,让我们也去体验。唯一的办法:必须努力追寻与思考,以求弄清他们(它们)的踪迹。
(二)应该注意的原则
克服距离并非易事。我们进行探索时应该注意什么?法国史学家菲斯特尔-德-库朗日(Numa Denys Fustel de Coulange)指出:“过去(消失的岁月)对于人来说永远不至于销声匿迹。人固然可以忘记其过去,但过去会潜伏于人身内”,如果“以近代人的眼光与事物来看待古人,误解他们就在所难免了”㉞。这个见解值得尊重。与此同时,研究历史也无法离开探索者所生活的社会现实,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弄清法兰西社会所经历的途程,也是为了理智地汲取经验教训,以利于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发展。为了克服距离,必须保持学术探讨的清醒头脑:努力防止绝对化、冷静对待主导的潮流、承认少数永久之迷的存在。
1.努力防止绝对化
必须坦然承认法兰西社会过去与现在的多样性、复杂性,尤其应该警惕法国历史中人物和事件的神圣化问题。
我们不否认孟德斯鸠等人的重要作用,他们为启蒙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们也留下了低级错误,例如孟德斯鸠曾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狡黠的民族。”㉟知晓这一方面的内容,才能构成对于孟德斯鸠等人的全面了解,才能认识启蒙运动的全貌。
同时还应看到,启蒙运动并不等同于一切、涵盖一切,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大潮流。社会的大潮流实际更加宽阔、深刻、强大、复杂,它的多种要素在长、短时段中有着或主或次的变化,这些要素既彼此区别,也有共同的特征与要求。社会大潮流,就是芸芸众生的活动及其当时首要的、核心的意愿。民众如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此乃贯穿法兰西历史的常规。正是这个社会大潮流的发展,催促革命的爆发,掀翻了波旁王朝。只有了解这些,才不至于将启蒙等运动不断地神化。法国历史上与启蒙运动相类似的运动,依笔者之孔见,也应做相同的理解㊱。
法国近代史研究中,人们普遍肯定议会制度。如果将它和形形色色的专制制度相比,的确应该予以赞赏,议会制度优于专制制度。但是,请看近代法国的议会里,坐着的各种政治色彩的议员!例如“社会主义议员”,他们往往打着工人阶级的旗号,积极活动,为自己谋求权力和利益。1918年,克勒孟梭(激进主义者)在议会讲台上无所顾忌地指责“社会主义议员们”:“先生们,工人阶级并非是你们的私有财产。勒诺代尔先生和阿尔贝·托马先生手上的老茧决不会比我多……他们和我一样,也是资产阶级!”㊲因此,议员们的实际身份和政治目标可想而知。这是法兰西议会的另一种政治面貌,它使议会机制失去了若干幻美的景象。
2.冷静对待主导的潮流
在法国,一定的时年,常有某个学派处于强势,处于正在流行的状态。流行,有它的理由,但它不代表绝对的真理、终极的圣旨。例如,工业文明值得肯定,而无限颂扬则导致过度贬低甚至完全否定农业文明。在肯定年鉴派的学术成就时,同样不可以否定政治历史的研究,以及研究政治历史的学术传统。不可能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年鉴派的“粉丝”。政治,无疑是法国社会的、历史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作为政治国家的法兰西,向来得到世人的较多关注。
流行,流来也流去。历史的真实如同激流中的岩石,一直受到它的冲刷,但是不会被它卷走。可见,随波逐流很难适合我们对于法国历史的认真探讨。
3.承认某些永久之迷
必须坦然承认:某些距离不可克服,不应为了某种利益和学术自尊,而硬做选择与论证。不可克服,因为构成当时历史实事的基本因素(如各种历史文献)早已不复存在(销毁、流失等)。我们不必过度陷入与孤注一掷,那样将无力自拔、烦恼不断。对于不能克服的距离,不必太过遗憾,或许这是历史女神克里奥(Clio)的安排。无奈!只有尊重历史与距离,同时企盼着有朝一日某些永久之迷能够显露出它的真容!
历史与距离这一课题,确实具有探讨的价值!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距离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应该以辛勤努力去克服距离,这就是笔者的心愿!
注释:
①19世纪后期,中译为“毕驷马”。参见:帕麦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8、316页。
②另说为39个。请见:拉夫《德意志史》,波恩国际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帕麦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0页等。
③Louis Bertrand.LouisⅩⅣ.Paris,1923.p.342.
④Archives Nationales de la France.Correspon dance politique.№211.1854.p.66-68.Jacques Welliquet.NapoléonⅢet l’Europe.Bruxelles,1966.p.18.A.Debidour.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l’Europe.Paris,1891.t.2.p.95-96.
⑤托尔斯泰的随笔。转引自:鲍格斯洛夫斯基《屠格涅夫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41页。
⑧⑩Archivio Segreto Vaticano.Correspon denza epistorale di S.S.PioⅨcon Sovrani et Patricolari.ⅡFrancia.№21,№26.
⑨Le Pape et le Congrès.Paris,1859.p.10-11.此处“Congrès”所指为1859年2-3月英国出面调停意大利争端,俄国建议召开国际会议,协商解决意大利问题。该书由意大利著名教授Salvo Mastellone先生所赠,笔者怀念着他的深厚友情。
⑪ Vaticano Archivio della Sacra Congregazione.degli affairi ecclesiastici straordinari.Francia,1860-1869.pos.638-649. Fasc.339.
⑫承蒙收藏者的允许,笔者使用该文件,并允诺不公布这一私人档案拥有者的姓名。笔者在此特向老友J.B.A.先生致谢!
⑬ Cahiers de doléances des femmes.Paris,1981.p.209-223.请参见:郭华榕《法国〈妇女权利宣言〉的重要历史价值》,《史学月刊》1993年第4期。
⑭请参见:郭华榕《法国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8、635页。
⑮ Retz.Memoires.Paris,1717.p.15.
⑯由维也纳经济大学(Wirtschaftsuniversität Wien)于1961、1971年出版。
⑰参见:郭华榕《1854年波罗的海之战的重要历史价值》,《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⑱请参见:郭华榕《法兰西第二帝国史》,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⑲ 1980年代,在研究第二帝国史方面,路易·日拉尔、皮耶尔·吉拉尔与阿兰·普勒西三位教授曾给予笔者以支持。笔者衷心感激并且怀念他们!
⑳中国学术界对于法兰西第二帝国研究甚少。1984年,笔者发表论文《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重要历史地位》(《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批评帝制,同时肯定当时法国社会的经济、文化等的发展。
㉑ AndréMaurois.Napoléon,A pictoral Biography.London,1963.p.18.
㉒波拿巴家族,拿破仑一世和三世皆以雄鹰为标志,象征强大的权力。第一帝国之鹰高耸双肩,显示出攻击性。第二帝国之鹰绝大多数双肩平置,企图给人以平和的印象。
㉓请参见: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116页。
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5页。
㉕ Ferdinand Bac.NapoléonⅢinconnu.Paris,1932.p.1-33.
㉖卢比孔河,古罗马时为意大利和高卢的界线。如果未有元老院的命令,军事统帅不准率兵过河南下。公元前50(49)年,凯撒渡过卢比孔河,挥师南下,去罗马夺权。
㉗ Paul Guériot.NapoléonⅢ.Paris,1980.t.1.p.161-162.AndréCastelot.Napoléon Trois,Des prisons au pouvoir.Paris, 1973.p.641.Louis Girard.NapoléonⅢ.Paris,1986.p.145-146.Octave Aubry.NapoléonⅢ.Paris,1929.p.67.
㉘ Charles de Gaulle.Mémoires de la guerre.Paris,1957.t.1.p.331-333.克罗泽《戴高乐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31-132页。
㉙米盖尔《法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页。
㉚ Jean-Christian Petitfils.Louis XIV.Paris,1995.p.708.Françoise Hildesheimer.Du siècle d’or au Gran d siècle.Paris, 2000.p.44.François Bluche.Louis XIV.Paris,1986.p.965-967.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6页。
㉛ Alain Decaux et AndréCastelot.Dictionnaire d’histoire de France.Paris,1981.p.605.ПодредакциейПоршнева.Hовая
uсmорuя.Москва,1953.том.1.стр.223.从法语译成俄语时,译者明显加重了语气:“在我们之后,那怕洪水滔天!”(После нас—хотьпотоп.)
㉜ Elie Fournier.Turreau et les colonnes infernales ou l’échec de la violence.Paris,1985.p.82-83.
㉝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5页。
㉞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导言”第4、1页。说明:“库朗热”应译为“库朗日”。
㉟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27页。
㊱有关著述甚少,如:Odile Krakovitch.Les femmes bagnardes.Paris,1990.Jeannine Charon-Bordas.Ouvriers et paysans au milieu du 19esiècle.Paris,1994.Frédéric Chauvaud.Les passions vilageoises au 19esiècle.Paris,1995.
㊲埃尔朗热《克雷孟梭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19页。说明:“克雷孟梭”应译为“克勒孟梭”。
On History and Distance
GUO Hua-r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The most difficulties when we look into history lie in the distances between the things or persons of the past and us.Those distances include geographic distance,time distance, the differenc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s,the master of historical document and etc.Distance plays an intensive role between the explorer and historical facts.It helps us to regard the things or persons of the past in a positive way,hides or even messes up the facts so that they turn into permanent mysteries,and reveals the facts,even those miserable facts.Distance is not unconquerable so that we should try to avoid being too absolute,treat main stream calmly and admit those permanent mysteries.
distance;history;historical document;historical research
K06
A
1000-5315(2013)03-0138-11
[责任编辑:凌兴珍]
2012-10-26
郭华榕(1934—),男,福建长汀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名誉会长,主要研究法国及欧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