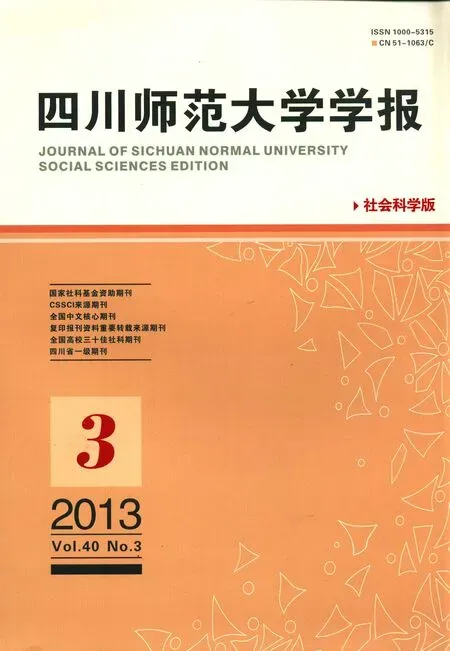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国王与城镇商人的商业关系
张 松 韬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6)
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国王与城镇商人的商业关系
张 松 韬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6)
早期斯图亚特时期,英国国王与城镇商人之间建立起一种互惠的商业关系。对于国王而言,可以通过出售某些特权而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对于城镇商人而言,有的时候必须接受这种商业关系,否则自身利益受损。双方商业关系的确立和维系,往往需要大臣作为中介才能得以实现,这就为腐败行为的盛行创造了条件。国王的一些做法也鼓励了腐败行为的蔓延,损害了与城镇商人之间的商业关系,促使城镇商人内部进一步分裂,并加重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国王;城镇商人;商业关系
17世纪上半期,英国国王与城镇商人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涉及许多方面,其中包含经济上的往来。国外学者对双方经济联系的阐述很多。如:坎宁安认为这个时期国王和商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对立,国王的政治野心损害了商人的利益,因此激发出宪政意义上的斗争[1]171-193,285-312。布伦纳把双方看成是一种伙伴关系,国王为商人提供经济特权,而商人则为国王提供贷款、税收和政治支持[2]200。格拉斯比则将双方的关系视作纯粹的利益交换,几乎与地域差别、政治动机等无关,并且商人们对于垄断权等问题的争论也只是因为机会不均等而已,而非对经济特权本身存在政治成见[3]205。这些观点都指明了双方存在利益上的纠葛,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也比较充分。赵秀荣认为“商人与王国政府互相支持,商人的目的是求富,国王的目的是求强,因此双方互惠互
利:国王能够并且实际上已经为商人创造了经济特权,商人为王室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主要换取的是种种贸易特许权”[4]177-178,187。张卫良也提到商人进入到政府部门或者议会,以此来巩固自身的地位,从而获得特殊的经济利益,或者通过议会斗争,来争取自己的权益[5]215-225。刘景华着重强调了外来商人对英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国王为达到这种目的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从中反映出双方各取所需的特点[6]。国内这些研究虽然都涉及双方的商业联系,但普遍没有突出双方的商业关系,而恰恰是这种比较纯粹的利益交换关系,给英国带来了大量的社会冲突,并成为多种政治矛盾的共同原因之一。另外,国内先前的研究往往对双方经济关系造成的社会道德层面的损害着墨不多,这也是一个不足。本文尝试在这些方面予以探讨,以期对该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晰完整。
一
17世纪上半期,英国国王与城镇商人间的商业关系首先表现在经济特权的授予与获取方面。经济特权至少包括专利权、特许权和垄断权。这些权力是行政权力延伸到经济领域而形成的,属于强制力的范畴。因为国王在行政方面具有权威性,因此就具备了颁授这些特权的权力。
这些特权能够满足商人们的需求。当时的商人经营范围广泛,他们关注的是市场而非产品,只要有利可图,便会将资金投入到高利润领域或地区[7]79-80。因此,一旦发现获得专利权、垄断权等经济特权便能够取得更大收益,商人们很乐意主动与王室建立某种关系。在那个通过技术创新很难获得丰厚利润的年代,国王的这种做法尤其能够吸引投资[8]141。除此之外,国王难以提供更具吸引力的交换物。所以,城镇商人对经济特权的投资是双方商业关系得以确立和维持的一个前提条件。
实际上,商人对经济特权的投资是一种寻租行为。都铎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国王创建了一种更加有利于寻租发生的新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寻租行为通过三种途径得以实现:其一,从亨利八世开始增加管理经济活动的规则,王室因此扩展了政府在规范经济行为中的作用;其二,通过推动各种经济项目企划(project)来增加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其三,增加国家非正式机构的权力[9]134。于是,从1580年代开始,经济特权不断通过贿赂和出售的方式被颁授给城镇商人个人或团体。
国王在授予经济特权时,考虑的因素会比较多。比如,为了提高收益,国王通常不会将经营同一种商品的特权固定出售给同一个个人或团体,而是会引入竞争机制。1637年,原先独立的制皂工匠们出资4.3万英镑购得肥皂公司(Soap Company)的特权,创建了自己的新公司,他们要为制造和销售肥皂的权利向国王支付每吨8英镑(肥皂公司原来支付4英镑)的费用[10]284。即使在同一个特许公司内部,也存在不和谐的利益关系,如商人冒险家公司内部大商人和小商人之间便不时产生矛盾[11]390-391。与之相类似,东印度公司大股东的核心利益是贸易,重视保有贸易垄断权;而小投资人的利益却不太固定于某一方面,他们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而选择退出以寻找更有利的机会,如1630年代考廷经济项目企划(Courteen project)就吸引了东印度公司一些成员的加入[8]144-145。从中可以看出,通过引入竞争机制,不仅增加了国王的收入,而且也扩大了经济特权的受益面。
即使扩大了受益面,能够获得经济特权的商人仍然是少数。1600-1625年间,担任市议员的伦敦商人当中约半数都将主要资金投入海外贸易[12]15-16,其余的致力于国内贸易;而国内贸易是由官员管理[1]298,所以“寻租行为并不是所有早期斯图亚特商人的特征”[9]153。经济特权,特别是贸易垄断权减少了其他商人的贸易机会,但这种侵害不应该被夸大,因为遭受垄断贸易之苦的很多城镇的外贸仍然是发展的。例如,桑维奇的商人对国王赋予伦敦商人的垄断权感到不满,当时规定东地公司所辖地区或波罗的海地区的商品只能由东地公司经营,实际上禁止了桑维奇商人向这些地区自由进出口大麻、毛线、松脂、沥青、绳索的权利。尽管如此,桑维奇的海上贸易仍有发展,港口所属船只的总吨位从1561年的463吨增加到1629年的1684吨,粮食出口量从1626年的2400夸脱上升到1640年的5369夸脱,这些船只虽然不仅限于停靠桑维奇一个港口,但至少会参与到桑维奇的贸易当中来。1595年,桑维奇港口的关税收入为3126镑,在郡一级的港口中排第二位,仅次于埃克斯茅斯(Exmouth),超过布里斯托尔、赫尔(Hull)、纽卡斯尔和南安普敦;城镇的收入也不错,1626-1640年间的大部分年份里都有盈余[13]164。贸易垄断没有对地方城镇的普通商人造成毁灭性打击。
另一方面,没有特许权的商人们也不会坐以待毙,会想尽办法弥补损失,长期而有效的方法是走私。大规模的走私始于16世纪晚期。1558年,国王为了增收,重新修订了《税率簿》(Book of Rates),使得走私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走私商与海关官员(有时自身便是走私商人)串通现象流行开来。到了1733年,英国、荷兰和法国之间贸易量的1/3都是走私完成的[14]137-139。还有一种方法是打擦边球,有意无意地扩大经营范围。例如,1626年,东印度公司获准使用自己进口的硝石生产黑色火药,但是只能局限于自己使用;然而,公司随意扩展了特许权的运用范围,擅自将火药投入市场,这种做法侵害了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销售黑色火药的垄断权[8]143。从这个角度看,特权商人购买经济特权是有商业风险的。
几乎任何买卖行为都存在风险,城镇商人和国王之间的交易也不例外。商人们寻求国王的支持、继续维持与王室的紧密联系的代价是高昂的,绝非仅仅缴纳购买经济特权费用那么简单。除了冒被侵权的风险之外,特权商人还需要向国王提供贷款,这甚至成为他们的义务。东印度公司就曾因为拒绝向国王提供贷款,使双方关系恶化。国王虽然没有取消东印度公司的特权,但却以授权私掠船远征的方式严重损害了东印度公司的利益。直至1640年“胡椒借款”(pepper loan)的出现,双方关系彻底恶化。国王的借款虽然带有强迫性,但却不是无偿的,需要偿还本金和利息,这又构成了双方的一种经济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国王用经济特权交易得到贷款;或者说,经济特权与贷款一样具有商业价值。
除了出售经济特权来换取借款,国王还可以通过其它几种方式贷款:实物抵押、土地抵押、税收担保、依靠王室信用[15]62-169以及强制等,其中强制借款更像是一种税收而不是借款[16]2,容易引起民众的反感,不能常用。由于财政缺口很大,单纯一种或几种借款方式难以满足国王的现金需求,因此任何可以获得资金的方法都不能轻易放弃。所以,即使遭到议会的反对,并且经济特权一旦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便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国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控制[4]178-179,但是这些缺点都没有妨碍国王继续推行出售经济特权的政策。
二
从长远来看,出售经济特权不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最佳方式,更稳定更合法的收入方式是税收。为了提高税收效率,国王采用了包税方式。由于关税是英国国王最重要的税收收入,并且是不必征得议会同意便可征收的税种[17]40,50,因此包税对王室财政必然会产生重大影响。当国王们逐渐认识到包税比委派官员征税要划算得多、收益也更高的时候[18]129-155,他们才逐渐接受把包税当成一门生意的做法。税收的承租人是城镇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和财力承揽这种大生意。为了使包税具有吸引力,国王需要向包税商让渡一些收益。国王与城镇商人就某种或某些商品的关税总额做出估算,以双方均能接受的价格进行交易,在确保国王及时获得大量关税收入的同时,也能够带给包税商足够丰厚的利润。这样,包税便成为一种双方均能获利的商业买卖。
随着包税规模的扩大和包税的长期化、制度化,包税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交易体系。一些联系紧密的有实力的城镇商人组成辛迪加,根据往年关税征收情况以及对未来外贸发展情况的预测,确定未来几年包税租金,以此作为与国王进行包税谈判的基准。一旦包税成功,辛迪加将整个包税租金分成很多股份,一部分由主要发起人持有,剩余部分则从市场上吸引投资者。风险和分红都依据投资人的投资比例,即所持股份的数量来分配。辛迪加的股份可以多次买卖,随着股份的转手,成员资格和所持股份的数量很容易改变。这样既可以吸引投资,又确保了投资的流动性,使包税成为一种优质的交易品。
尽管包税辛迪加对包税秉持开放的态度,但开放是节制的,对开放对象是有选择的。包税商们都清楚,“在收税的时候维持一个势力范围是非常重要的”[8]143,因此,他们不会轻易让他人涉足其中。北安普敦伯爵支持的辛迪加连续两次都没有竞争成功大包税(Great Farm),这些商人因此多年被排除在这项业务之外[15]90。
排挤竞争对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独享包税的高额利润。1612年,据莱昂内尔·格兰菲尔德(Lionel Cranfield)估计:在过去的七年里,大包税税收总额达到1081359英镑,除去包税租金824800英镑以及每年的管理费用大约8000英镑,净利润超过20万英镑;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算,国王每年至少因此损失高达157697英镑[19]134。国王失去的便是包税商得到的。
然而,国王损失的远没有表面上那么严重。国王并非不知道包税制度存在漏洞,他也清楚包税商利润丰厚,但现实中存在的一些情况增加了包税的可接受性。一方面,政府直接征收关税的方式效果并不好,其中除了行政效率不高的原因之外,商人和海关官员串通偷漏关税也是重要原因[18]136-140。另一方面,国王通过采用竞争方式提高了包税租金。北安普顿伯爵商人集团虽然竞价大包税失败,但却没有放弃,不断提出新的报价,迫使对手也不断做出让步,向国王支付2万英镑的罚金,并且从1614年起将包税租金上调至每年14万英镑[20]333。再一方面,国王还可以获得包税商提供的贷款。包税本身也是一种借贷行为,与出售经济特权的方式相类似,国王以授予包税特权的办法获得商人的贷款。商人根据对某项关税的预估,每年向国王预付包税租金。这些租金实则是商人对国王的贷款,国王可以预支本年度的预估关税收入,而实际的关税收入则被作为应偿还的本金和利息由商人自己去征收。这样做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为国王提供了稳定的收入,便于国王有计划的安排支出,并且借款期限往往可以延长、额度可以追加、数量也比较大。以上这些因素都说明了国王从包税中得到了好处。
对于国王和商人双方而言,包税是一桩各取所需的生意。国王可以从中获得稳定的收入,还能够确立起一个可靠的借款途径,从而满足了王室的财政需求;国王借助商人的经验和才能,提高了关税管理的效率,至少是减轻了国王的行政负担,这也弥补了当时国王政府行政能力的不足。而包税商从中得到的利益是丰厚的经济回报,以及建立起与国王政府更加紧密的联系以便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在双方紧密合作的时期,包税的效果很好,国王也减少了对议会的依赖。
三
国王通过出售经济特权的政策和实行包税制,与城镇商人建立起一种商业关系。然而,这种关系的确立不能够仅仅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还需要依靠中介来实现双方的沟通和互信,国王的大臣便充当了这个角色。
大臣担当中介的基础是庇护制[21]。国王政府中的显贵利用他们的政治地位庇护具有专长的人士为其服务,也为政府出谋划策。尽管这个时期的枢密院成员普遍缺乏经济方面的专门技术,但他们的幕僚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北安普顿伯爵的智囊团当中不乏经济方面的专家,使他对英国的经济状况有相当的了解。他清楚英国经济过分依赖于毛纺织品贸易,结构单一,于是接受顾问的建议,鼓励创建一批经济项目企划,以增强经济活力、减少进口、引领经济新的发展方向。这些顾问来源广泛,有包税商、贸易商、手工业作坊主等[19]123。虽然有些幕僚从自身利益出发提出局限于本行业的一些建议,但并不代表其没有可行性。托拜厄斯·金特曼(Tobias Gentleman)是一名造船主,他曾强烈建议扩大英国本土的捕鱼业,最终实施效果显著[22]138。被庇护人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协助庇护人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同时也体现了自身的价值。
经济领域的庇护对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城镇大商人。他们不仅财力雄厚,而且具备丰富的外贸经验,这些对大臣乃至国王都具有吸引力。作为庇护人的大臣,“关注的中心是检查王室的行政管理……以及确立合适的方案,使得国王得到最大的实惠,而对臣民的伤害最小”[19]130。大商人的经济管理能力对实现这些目的大有裨益。
在为大臣服务的过程中,个别商人从庇护网络中脱颖而出,甚至被擢升为朝廷重臣。莱昂内尔·格兰菲尔德就是个典型。他长期从事海外贸易,遍及欧洲多个贸易中心,积累起大量资财。他利用这些资金结交了一批朋友,这些朋友往往是声名显赫、非富即贵的人物。比如,托马斯·斯迈思爵士(Sir Thomas Smythe)掌管3个公会,是另外两个公会的司库,还是其他两个公会的成员,驻在伦敦的半数大臣经常出入他的宅邸;尼古拉斯·索尔特爵士(Sir Nicholas Salter)是承揽1604年第一次大包税的辛迪加的领袖,并且长期享有后来出现的某些类似业务[7]82。通过这种关系网,格兰菲尔德与国王政府上层建立起有效的联系,成为北安普顿伯爵的顾问。1608年,在买卖王室土地的生意中得到赏识,成为北安普顿伯爵的主要顾问。他的从商经验对国王政府的价值在1610年代的贸易战中得到充分体现[19]126-129。从此以后,他更加受到北安普顿伯爵的器重。1612年,他开始步入政界,担任政府官员,成为王室重臣。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商人而言,与国王及其大臣建立密切联系的最主要目的是赚取商业利润。王室和商人之间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一旦确立,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且往往不局限于一个项目,比如获得1604年大包税的商人辛迪加也同样得到了1607年法国和莱茵葡萄酒包税。因此,商人们有必要建立与国王及其大臣的紧密联系。
为了建立并维持这种合作关系,商人们不但需要向国王支付分红、交纳租金、提供贷款,而且需要向作为庇护人的大臣支付不菲的费用。通常情况下,大臣们会加入特许公司或辛迪加,成为其成员,以分红的形式获得这笔收入。例如:白金汉公爵从1618年到1628年一直主导宫廷事务,1619年,他的收入总计约1.8万英镑,其中包括关税包税收入3000英镑[23]61-63,211-213,412-413;1622年,格兰菲尔德拥有糖的包税[20]357-358。但是,查理一世时期,大臣开始采取不同的做法,利用便利条件直接取得特许权或包税权,然后再转售给其他商人,这就更加重了商人的负担,而对大臣的交易地位却更加有利。
不管采用上述哪种方式,大臣们都是在利用特殊身份和寻租机会谋利,实则是在腐败。因为政府公职的花费超过收入[24]239-252,332-333,加之腐败行为在当时也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所以杜绝腐败十分困难。实际上,腐败起到了财富再分配的效果,将财富从商人手中转移到乡绅和与王室联系紧密的土地精英手中,维持了土地精英的社会地位。从这个角度看,腐败行为维护了社会原有秩序[9]134,151。即使到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占有社会财富最多的仍旧是原来的社会管理阶层,而非生产者和企业家[25]。因此,大臣们腐败的中介行为,绝非是简单的利益交换,而是适应日益发展的商业社会的举措。整个社会,从国王到普通民众都被迫卷入一个复杂的商业网络之中。
四
综上所述,国王确立并维护与城镇商人的商业关系,是基于现实的抉择。国王担负管理经济的职责,但对国内经济单位收税的权力却受到限制,有时难免出现责权不符的现象。国王鼓励建立新兴工业、提升原有工业的技术水平,一方面达到了进口替代的效果,但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关税收入。比如,盐是大宗进口产品,实现盐的国产化是英国人的愿望;查理一世时期在国内建立起来制盐工场,并且把来自比斯开湾的进口盐挡在国门之外,这样一来就断绝了国王的进口盐关税[10]285。因此,国王以出售经济特权、包税等方式弥补税收损失的行为是具备一定合理性的。
另一方面,国王凭借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对政治资源的控制,采用商业方式解决政治领域的一些事务,以弥补行政能力的不足。这种商业关系突出表现为国王与城镇商人(包含很多官员,因为他们自身往往也是商人)之间的利益交换,与忠诚无关。内战前夕,商业利益集团反对国王的倾向更加明显,他们反对国王并不是因为国王对经济的操控,而是出于对未来收益不确定性的担心[8]159。国王控制经济是英国王室长期施行的政策,并没有招致商人们过多的激烈反对,甚至可以认为他们已经适应了这种体系。查理一世虽然只是对这一传统做出了调整,并没有彻底废除这种做法,但却打破了体系的稳定性,商人们预估自己收益的难度大大增加,经营风险随之增大;而新的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商贸活动不免有陷入混乱的危险,旧体系下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受到损害。于是,国王和城镇商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被打破了。
再者,国王与城镇商人之间的商业联系往往只是让少部分人受益,绝大部分的社会中下层民众却要遭受经济损失,至少会面临种种限制带来的不便。他们对此颇有微词(比如围绕垄断法案的议会辩论),甚至用实际行动(比如走私)来表达不满。他们对保护自身利益的诉求最终演变成民众反对国王的动机之一。
[1]W.Cunningham.The Growth of En glish In dustry an d Commerce(Sixth Edition):Vol.II[M].Cambridge,1938.
[2]Robert Brenner.Merchants an d Revolution:Commercial Change,Political Conflict,an d Lon don’s Overseas Traders, 1550-1653[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3]Richard Grassby.The Business Community of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 d[M].Cambridge,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4]赵秀荣.1500-1700年英国商业与商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5]张卫良.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历史进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刘景华.外来移民和外国商人:英国崛起的外来因素[J].历史研究,2010,(1):138-159.
[7]R.H.Tawney.Business an d Politics under James I:Lionel Cranfield as Merchant an d Minister[M].New York:Russell&Russell,1976.
[8]Robert Ashton.Charles I and the city[M]//F.J.Fisher.ed..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 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 d Stuart England:in Honour of R.H.Tawney[M].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1.
[9]Linda Levy Peck.Court Patronage and Corruption in Early Stuart Englan d[M].Boston:Unwin Hyman,1990.
[10]Samuel R.Gardiner.History of Englan 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I.to the Outbreak of the Civil War 1603-1642: Vol.VIII[M].Longmans,Green,and CO.,1896.
[11]A.Friis.Alderman Cockayne’s Project an d the Cloth Trade:the Commercial Policy of Englan d in Its Main Aspects, 1603-1625[M].Copenhagen and London,1927.
[12]Robert Ashton.The City an d the Court,1603-1643[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13]Jacqueline Bower.Kent Towns,1540-1640[M]//Michael Zell.ed..Early Modern Kent,1540-1640.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2000.
[14]G.D.Ramsay.The Smugglers’Trade:A Neglected Aspect of English Commercial Development[C]//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Fifth Ser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2.
[15]Robert Ashton.The Crown and the Money Market 1603-1640[M].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60.
[16]Richard Cust.The Forced Loan an d English Politics 1625-1628[M].Clarendon Press,1987.
[17]M.J.Braddick.The Nerves of the State:Taxation an d the Financing of the English State,1558-1714[M].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6.
[18]A.P.Newton.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reat Farm of the English Customs[C]//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Forth Series.Cambrides University press,1918.
[19]Linda Levy Peck.Northampton:Patronage and Policy at the Court of James I[M].London:George Allen&Unwin, 1982.
[20]Frederick C.Dietz.English Public Finance 1485-1641:Volume II[M].Frank Cass&CO.LTD.,1964.
[21]龚敏.论近代早期英国庇护制的变化和构成[J].唐都学刊,2006,(5):82-88.
[22]E.E.里奇,C.H.威尔逊(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M].高德步,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3]Roger Lockyer.Buckin gham:the Life an d Political Career of George Villiers,first Duke of Buckin gham,1592-1628 [M].London:Longman,1981.
[24]G.E.Aylmer.The Kin g’s Servants:The Civil Service of Charles I,1625-1642[M].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61.
[25]W.D.Rubinstein.The End of“Old Corruption”in Britain 1780-1860[J].Past an d Present,No.101(Nov.1983), pp.55-86.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Kings and Urban Merchants in Early Stuarts
ZHANG Song-tao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6,China)
In early Stuarts,kings built a reciprocal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with urban merchants.Kings sold some privileges fo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rests,while urban merchants were sometimes forced to accept this commercial relationship,otherwise they would suffer loss of self-interests.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both sides relied often on the courtiers as a medium,which facilitated the corruption.Some behaviors of kings also stimulated expansion of the corruption,damaged the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with urban merchants,promoted divisions between urban merchants,and aggravated common people’s dissatisfaction.
the early Stuarts;king;urban merchants;commercial relationship
K561.4
A
1000-5315(2013)03-0149-06
[责任编辑:凌兴珍]
2012-11-04
四川省教育厅青年基金项目“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经济政策的决策机制研究”(编号10SB010)的阶段性成果。
张松韬(1979—),男,山东莱州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早期英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