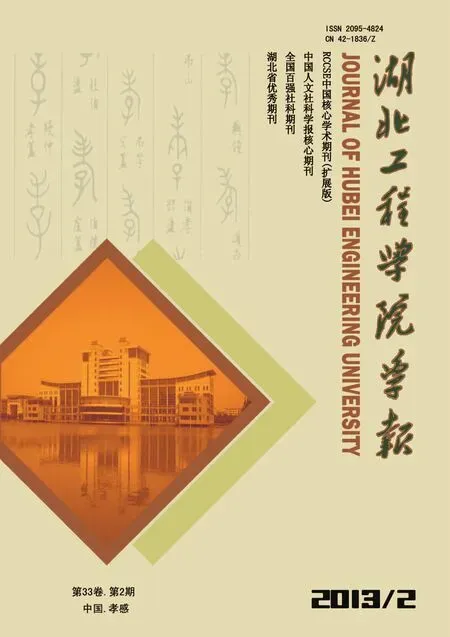大乘佛教慈善理念的特质及现代意义
谭 洁
(湖北工程学院 政治与法律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慈”和“善”两字在大乘佛典里连用时,多指佛或者菩萨有“慈善根力”。如《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五《慈品》讲述如来因具有慈善根力,故示现种种不可思议的神通。[1]卷5在北凉昙无谶译的《大般涅槃经》卷十六《梵行品》中,佛自述种种神通变现,亦云皆是“慈善根力”所致。[2]卷16,457-458《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一更是指出,菩萨以无缘平等大慈,以修身、口、意三种慈善根力。[3]卷41
当然,也有经典对“慈善”一词进行了解释。如《大般涅槃经》卷十五《梵行品》云:“若于一众生,不生瞋恚心而愿与彼乐,是名为慈善。”[2]卷15,454又如《中论》卷三《观业品》云:“人能降伏心,利益于众生,是名为慈善。”[4]卷3这里所说的“慈善”,指的是以己之善心,与众生处理好关系,让众生感到快乐。由于佛典中有“所有善根,慈为根本”的说法[2]卷15,456,因此,大乘佛教慈善理念是以“慈”为首建立起来的。
一、大乘佛教慈善理念的内涵
印顺法师说:“‘大乘佛法’是以发菩提心、修菩提行、成就佛果为宗的。”[5]1菩提心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可以说,没有菩提心,就没有大乘法。而发菩提心的基础是具备“四无量心”。据《大般涅槃经》云:“唯四无量能令菩萨增长,具足六波罗蜜。……菩萨摩诃萨先得世间四无量心,然后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次第方得出世间者。”[2]卷15,452“四无量心”,又称四无量、四等心、四等、四梵住、四梵行、无量心解脱,指的是四种广大的利他心,即能令众生离苦得乐而起的“慈”、“悲”、“喜”、“舍”四种心。《大般涅槃经》卷十五对“四无量心”是这样解释的:“为诸众生除无利益,是名大慈。欲与众生无量利乐,是名大悲。于诸众生心生欢喜,是名大喜。自舍己乐施与他人,是名大舍。”[2]卷15,454“四无量心”是菩萨利益一切众生的存心,是大乘佛教十分重要的自利利他的菩萨法门。“菩萨摩诃萨四无量心,能为一切诸善根本。”[2]卷15,454因此,它也构成了大乘佛教慈善理念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下面就“四无量心”一一加以分析:
1.慈无量心。无量一指能缘无量众生,二指慈心广大无量。慈则是亲爱、与乐的意思。如《大智度论》云:“慈应言‘亲爱’,无怨无诤故,名为‘亲爱’。”[6]卷33,305《大乘义章》亦云:“爱怜名慈”,“爱念是慈”。[7]卷11,686,687而具体落实到修行,则是欲令众生得乐。如《大智度论》云:“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慈者,念令众生得乐,亦与乐事。”[6]卷27,256《大乘义章》亦云:“与乐名慈。”[7]卷11,690
大乘佛教认为,慈最能体现如来自利利他的精神,故有“慈者即是众生佛性……佛性即慈,慈即如来”和“慈者即是一切菩萨无上之道。道即是慈,慈即如来”[2]卷15,456,456之说。就慈而论,诸佛之慈真实最大,而云菩萨大慈者,是因为与佛为小,与二乘为大,此乃假名为大。但菩萨与佛有不即不离的因果关系:佛是修行到究竟圆满者,菩萨是发心、修行者。因而大乘佛教云“慈”,多云“大慈”。在《大方等大集经》卷二十九中,更是历数了菩萨修“慈”之不可尽处。[8]卷29,199佛法认为,“慈”有三种:众生缘慈,法缘慈,无缘慈。其中,众生缘者,“缘于五阴,愿与其乐”。法缘者,“缘诸众生所须之物而施与之”。无缘者,“缘于如来,是名无缘”[2]卷15,452。众生缘指的是我们在生起慈心时,心境上会现出一个个的众生,把他们当成实在的独立自体。法缘指的是生起慈心时,众生还是众生,但已没有了实我,只有诸我因缘和合的假我而已。无缘指的是生起慈心时,既不住众生相,也不住法相。三慈中,缘众生者初发心,缘法缘者已习行,缘无缘者得深法忍。菩萨修无缘慈,因不从缘得,故平等普覆,又称“第一义慈”。大乘佛教倡导培植平等的慈爱之心,施与一切众生。概而言之,慈无量心就是以世出世间的种种善利,利益一切众生,使一切众生同得安乐。
2.悲无量心。悲是哀愍、拔苦的意思。如《大乘义章》云:“恻怆曰悲”[7]卷11,686,“哀伤是悲”[7]卷11,687。又《大智度论》云:“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大悲,怜愍众生苦,亦能令脱苦”[6]卷27,256。慈和悲,都是佛道的根本。大悲如大慈一样,也最能体现菩萨的自利利他精神。佛典中所记载的尸毗王割肉贸鸽,以及萨埵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体现的就是菩萨的大悲心。
菩萨修一切智以大悲为本。本来“四无量心”是平等无二、一体的,但之所以强调悲心,说大悲心为本,是因为佛法说到底是以解脱众生出离生死苦海为最高理想。“所以菩萨的最要处,便是大悲心,见众生苦,好像是自己的苦痛,想办法去救度他们,才是菩萨心、佛种子。”[5]24故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再云:“大悲为上首”[9]卷48。《十二门论疏》也引《华严经》云:“金刚但从金性出,不从余宝生。菩提心唯从大悲生,不从余善生。”[10]卷上《大智度论》亦引《明网菩萨经》云,菩萨处众生中,行三十二种悲,渐渐增广,转成大悲。指出“大悲是一切诸佛、菩萨功德之根本,是般若波罗蜜之母,诸佛之祖母。菩萨以大悲心故,得般若波罗蜜,得般若波罗蜜故得作佛”[6]卷20,211。
《大方等大集经》卷二十九,也历数了菩萨修“悲”的不可尽处。[8]卷29,200菩萨以大悲为上首,故悲无量心是悲天悯人的情怀,冀望减轻或拔除众生的痛苦。当然,仅有悲心还不够,还需具足增上意乐,将悲心化为种种实际行为,救众生出离苦海。
3.喜无量心。喜是见众生离苦得乐,而心生欢喜的意思。《大乘义章》云:“庆悦名喜。”[7]卷11,686《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浅注》亦云:“庆他曰喜。”[11]卷5,35佛教认为,喜与乐是有区别的:身乐名乐,心乐名喜。[6]卷20,210乐是在五尘中所生的快乐,而喜是在法尘中所生的喜悦。如对穷人,先施予财宝,是先给他快乐;然后教导他谋生的技能,则是使他在生活中产生欢喜。欲界乐愿令众生得,是名乐;色界乐愿令众生得,是名喜。因此,先乐后喜。也就是说,乐偏重于自我的感受,而喜则顾及众生的快乐。
《大方等大集经》卷二十九,也历数了菩萨修“喜”的不可尽处。[8]卷29,200喜无量心是见众生的乐而喜,视众生的欢悦为自己的欢悦。这是一种对他人快乐的认同,是不带染著的欣悦心境。
4.舍无量心。舍是心行平等的意思。《大乘义章》云:“亡怀名舍”,“等心是舍”,“平等名舍”。[7]卷11,686,687,690《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浅注》亦云:“于所缘众生,无憎无爱,名之为舍。复念一切众生,同得无憎无爱,无瞋无恨,无怨无恼,亦复无量,故曰大舍。”[11]卷5,35可知,大乘佛教的舍,指的是以平等心对待众生,于亲非亲,于爱非爱,于善于恶,都心无所著,心得清净。
《大方等大集经》指出,菩萨行舍有三种:舍诸烦恼,舍护己他,舍时非时。[8]卷29,201其中,舍诸烦恼是指与世间诸法平等无二,与诸众生得平等心;舍护己他是指观舍己身,心无瞋恨,亦不生诤讼,不害他身;舍时非时指的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平等相待。如此诸法安住戒行,精勤勇猛具足修行,则是菩萨修“舍”的不可尽处。舍,是冤亲平等,不忆念众生对于自己的恩怨而产生爱恶。修慈心、喜心时,容易起贪著心,修悲心时,又容易起忧愁心,因此需要用平等舍来进行对治。舍无量心就是去除一切妄想,且令一切众生都能有平等入佛道之心。
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虽分别说,然本为一体。如《大智度论》云:“慈是真无量,慈为如王,余三随从如人民。所以者何?先以慈心欲令众生得乐,见有不得乐者,故生悲心;欲令众生离苦,心得法乐,故生喜心;于三事中,无憎无爱,无贪无忧,故生舍心。”[6]卷20,211无论谈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中的哪一种,都是以一摄三的关系。因此,大乘佛教的慈善理念是以慈为首,“四无量心”为一体的,为一切诸善根本的思想。
二、大乘佛教慈善理念的特质
大乘佛教慈善理念以“四无量心”为重要内涵,其宣扬的不是独安己身,而是广为众生,济拔勤劳。《大智度论》云:“‘慈’名爱念众生,常求安隐乐事以饶益之;‘悲’名愍念众生,受五道中种种身苦、心苦;‘喜’名欲令众生从乐得欢喜;‘舍’名舍三种心,但念众生不憎不爱。”[6]卷20,208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和道德精神,佛教的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具有独特本质。
1.以平等成就慈观。大乘佛教的慈,是一种爱,关爱世间一切众生。正如《大宝积经》所云:“于诸众生起大慈心”[12]卷85,489,“慈爱众生如己身”[12]卷85,490。这种慈爱,不分阶级、性别、种族、贫富、贵贱、亲疏,是心量无限的大爱。台湾证严法师有这样的名言:“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这三句名言不仅表明了证严法师美丽的慈善之心,而且也说明了佛教的大慈大爱之旨,即“无缘大慈”。
佛教的慈观是建立在缘起的平等性基础上的。佛教认为,一切有为法,皆待缘而起。缘指的是关系或条件,世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生起变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有相对的互存关系或条件,都是相依相成的缘起法。这种缘起法的相关性,即所谓“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13]。基于这种相关性,佛教认为,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都与自己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生死的三世流转来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14]卷2。也就是说,众生即我,我即众生,慈爱众生即慈爱自己。
缘起性的相关性各有各的互存关系或条件,但深入到最里,却是体现平等一如的法性(佛性)。从法性一如去通达缘起法,不再是各自的关系或条件,而是无二无别的平等。大乘佛教认为,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然种种颠倒妄想,不见自性清净。慈爱本发自内心,在通达了一切法空之后而起的慈心,即无缘大慈。它视一切诸法皆空,都是平等的,在平等之中,没有法与众生的自性。此时的慈,是真心本性的自然流露,它舍弃了世间的私爱,即空而起慈,是平等大慈。
2.以分享成就悲观。大乘佛教的悲,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感同身受,即见众生苦同于己苦,故发心济拔众生出离苦海。这种感受,《大般涅槃经》形容为:“譬如父母见子遇患,心生苦恼,愍之愁毒,初无舍离;菩萨摩诃萨住是地中亦复如是,见诸众生为烦恼病之所缠切,心生愁恼,忧念如子,身诸毛孔,血皆流出,是故此地名为一子。”[2]卷16,458-459又如佛告迦叶:“我于是等悉生悲心,同于子想如罗睺罗(佛陀之子)。”[2]卷3,380佛教观一切有情,与己身同体,自他无别,从而生起拔苦与乐、平等绝对之悲心,此悲心即所谓“同体大悲”。
佛教的悲观是建立在分担众生苦痛的慈心之上的。《摩诃止观》云:“见诸众生,颠倒狱缚,不能得出。起大慈悲,爱同一子。今既继惑入空,同体哀伤,倍复隆重。先人后己,与拔弥笃……以己之疾,愍于彼疾,即是同体大悲。”[15]卷6因此,佛教往往慈悲同说。如云“慈悲为本”[16]卷2,“大慈悲为本”[17]卷上,“慈悲,佛道根本也”[18]卷9,406,“慈悲乃入有之基,树德之本”[18]卷9,406,“佛心者,大慈悲是”[19]卷1等等。菩萨见众生沉沦苦海,摄众生于自体,以众生之苦为己苦,于是发起大悲心,愿救众生离苦得乐。
大乘佛教认为,诸佛、菩萨与众生同体。这个“体”指的是自性、佛性,真如本性。众生与佛的自性无二无别,只因妄想分别执著不能证得。迷时佛是众生,悟时众生是佛。体相都为一,都是周遍法界、遍一切处的,即佛的法身遍满一切处,佛的心性也是遍满一切处。既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与自己同一个本体,没有分别,也就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 “同体”意味着共同享有,意味着分担承受。悲心所念在众生之苦欲拔除之,“大悲之兴救彼而起,所以悲生于我而天下同益也”[18]卷4,368。若仅发悲心,而不以实救为悲,则有违佛教悲心之旨。故起大悲心,当以众生苦为己苦,勇敢承当。
3.以感恩成就喜观。大乘佛教的喜,是见到众生的乐而生的欢喜之心。众生如何得乐呢?《大智度论》云:“欲令众生离苦,心得法乐,故生喜心。”[6]卷20,211指明心得法乐,即生喜心。《佛说大乘十法经》则云,发喜乐菩提心有四种境界:第一初喜乐发菩提心,指见佛菩萨、声闻、缘觉,教化劝发而生阿耨多罗多三藐三菩提心;第二喜乐发菩提心,指听闻菩提以及菩提功德,即发阿耨多罗多三藐三菩提心;第三喜乐发菩提心,指见众生孤独无依,贫穷无宅,而心生悲悯,为救困周急而发阿耨多罗多三藐三菩提心;第四喜乐发菩提心,指见如来或菩萨,声闻、缘觉等诸行具足,心生欢喜,爱敬安心,以此发阿耨多罗多三藐三菩提心。[20]卷1
可知大乘佛教的喜心,围绕见闻众生能持正法而生此喜乐菩提心。故鸠摩罗什云:“凡夫及小乘则见众生乐故起喜心,今欲令持正法故起喜心,心于法中生喜也。”[18]卷4,368僧肇亦云:“欲令彼我俱持正法,喜以之生也。”[18]卷4,368可知喜心于法中生起,是乐见众生远离非法,能持正法。若能讲经说法,使众生了悟人生真谛,譬如人处饥渴,给足饮食,则感恩加深。
佛法常云“随喜”,这是因为修行者视他人欢喜为己之欢喜,其中包含了强烈的感恩意识。在佛教教理中,众生轮回六道,人、天、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里的众生,可能是前世的自己或亲人,也可能是后世的自己或亲人。因此,如果能发心使众生俱持正法,离苦得乐,则众生修行即己身修行。若见众生之苦,即己身之苦;见众生之乐,即己身之乐。众生犹如自己的一面镜子,焉能不感恩轮回中自己幸得入人道,能发无上菩提心,与众生随喜呢?感恩众生,即能在面对众生时,劝发其于法中修持,同得法喜,因而“示教利喜”才是佛陀说法的真正目标。
4.以结缘成就舍观。大乘佛教的舍,是于慈、悲、喜三事中,无憎无爱,无贪无忧,平等无二,故名为舍。佛教典籍说舍,多云“平等舍”。大乘佛教说舍有“小舍”和“大舍”。小舍指的是怨亲平等,对一切众生存平等无差别之想。没有怨亲、贤愚、良莠的分别,一视同仁,如此则与众生结缘。大舍则舍于万有,即无喜乐哀乐之情,与佛法结缘。唯有清净佛性,是正智之性。
菩萨行舍,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以其无分别,普结善缘。这是一种极高的智慧,故《注维摩诘经》云:“以摄智慧行于舍心。”[18]卷4,368大乘佛教的“舍”,探寻的是毕竟空义,即破除一切法,令其无遗余,因缘所生法空,因缘亦空。这是一种大平等,没有了私心贪念的大爱。如《大方广佛华严经·离世间品》云有十种“净舍”[21]卷42,661,指出若菩萨摩诃萨安住此舍,则得一切诸佛无上清净大舍。
我们平常有个词叫“舍得”,这是告诉世人放下一切执著,因舍而得,成就佛法。对于尘世中的人来说,最难舍的有钱财、屋宅等私有财产,以及能带来物质享乐的名利、权势等公众资源。因此,舍又常与放下这些执著有关。如所云“舍身”,放下自身,与众生平等;所云“舍宅为寺”,“舍田产为寺产”,舍弃私财,作为公财;所云“舍指供佛”,即燃指供佛,破除我执,顿悟毕竟空义。
“四无量心”的特质彼此并不是孤立的,平等、分享、感恩、结缘四者之间相互融摄。它体现出发菩提心者的慈善愿望,当然解脱众生的心愿还需与解脱众生的实际行动联系起来。
三、大乘佛教慈善理念的践行
大乘佛教倡导发菩提心,修菩提行,因而所有的发心(发“四无量心”)都需落实于世间,才具有最真实的意义。关于修行的方法,有很多,但总体看来,不出印顺法师所说的“净心第一”,“利他为上”。净心就是要清净自性,增长善根。利他就是不离世间,利益众生。如此,则是实践菩萨行,趣向佛果了。
1.修慈以戒杀为首。依佛法说,修习慈心,功德最大。《大智度论》云入慈三昧,得五功德:“入火不烧,中毒不死,兵刃不伤,终不横死,善神拥护。”[6]卷20,211以利益无量众生故,得无量福德,生清净处。《大悲经》更是云:心住慈善,当得十一种功德利益:“一者睡眠得安隐,悟则心欢喜;二者不见恶梦;三者人非人爱;四者诸天拥护;五者毒不能害;六者刀箭不伤;七者火所不烧;八者水所不溺;九者常得好衣,肴膳饮食,床座卧具,病瘦汤药;十者得上人法;十一者身坏命终,得生梵天。”[22]卷5
修慈门道很多,但首在戒杀。所谓“释氏之教义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为重”[23]卷26,292。古往今来,生命都是最宝贵的。佛教所谓生命,不仅指人、动物的生命,而且认为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所有的一切都有生命。生命与生命之间,是一体的、共同的,应当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爱惜。因而佛教修慈首在戒杀,即不杀生害命。而不杀生,除了不轻易夺取生灵性命之意,还提倡素食。早在南朝梁代,梁武帝萧衍就发布《断酒肉文》,云:“经言:食肉者断大慈种。何谓断大慈种?凡大慈者,皆令一切众生同得安乐。若食肉者,一切众生皆为怨对,同不安乐……若食肉者是远离菩萨法,若食肉者是远离菩萨道。”[23]卷26,295对于那些为满足一己口腹之欲,而不惜残害生灵的人,梁代周颙予以痛斥:“况乃变之大者莫过死生,生之所重无过性命。性命之于彼极切,滋味之于我可赊。”[23]卷26,293它反映出大乘佛教传入我国后,对我国知识阶层信众的深刻影响。
2.修悲以救济为重。佛法常说“悲智双运”,“无智不成大悲”。悲心是为了拔除众生苦痛,一要有广大的发心,对众生一视同仁,予以平等的同情。二要能换位思考,把众生的疾苦视同自己的苦痛。当然,最重要的是,悲心虽高妙,但仅发心是不圆满的,还需激发种种有力的行愿,即付诸实际行动,给予众生以普遍的同情和救济。救济也常以施舍进行慈善,但它与布施是不同的。最突出的一点是,救济是众生处于缺乏、困窘状态所施予的援助,而布施则不一定。
我国古代典籍记载了大量百姓因遭受水涝、干旱、地震、冰雹、雷电等自然灾害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天灾人祸带来的瘟疫、传染病大肆流行而陷入困苦中挣扎的悲惨状况。关于地理环境对我国的影响,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先生提出:“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24]这样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格局、经济形态,也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为处在贫穷困苦中的百姓提供衣食、药品,修桥造路,摆渡过河,打井掘水,养老殡葬等等,都是在践行悲心。中国民间慈善救济活动的发起与推广,佛教教化的功德甚深。
3.修喜以弘法为旨。如果说悲心的济拔是“雪中送炭”,则喜心的感念是“锦上添花”。假如用流行歌曲的歌词来诠释的话,悲心是“悲伤着你的悲伤”,喜心是“幸福着你的幸福”,“快乐着你的快乐”。《大方广佛华严经》云:“专心正念诸和敬法。于诸菩萨生如来想。爱说法者重于己身。爱重如来如惜己命。于诸师长生父母想。于诸众生生儿息想。于诸威仪如护头首。于诸波罗蜜如爱手足。于诸善法生珍宝想。于教诲者生五欲想。于知足行生无病想。爱乐求法生妙药想。于举罪者生良医想。摄御诸根无有懈怠。是故名喜。”[8]卷29,200可知让众生离苦得乐,心生欢喜,宗旨就是弘法,让听闻佛法的人,依正法生出喜心。
东晋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离世间品》云,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净喜”:“发菩提心净喜;舍一切所有净喜;于犯戒人不生恶心,教化成就净喜;于一切诤讼众生,悉令和合,得无上智净喜;不惜身命,守护正法净喜;远离五欲,常乐正法净喜;令一切众生不著资生之具,常乐正法净喜;见一切佛恭敬供养,无有厌足,而不坏法界净喜;令一切众生常乐禅定,解脱三昧相续净喜;令一切众生专求寂静,除灭乱想得无上慧,远离邪见满足诸愿,究竟菩萨苦行净喜。”[21]卷42,661归纳起来,就是佛音能起欢悦心,普令众生得法喜。
4.修舍以布施为主。布施原指以衣、食等物施予大德及贫穷者,是佛陀劝导优婆塞等之行法,至大乘时代,为“六波罗蜜”之一,又明确提出法施、无畏施,进一步扩大了布施的含义。佛法说布施有三种:财施、法施、无畏施。财施是把衣服、饮食、卧具、医药,金银、车马、田宅等转赠他人。法施是说法宣经,或印造佛经、法物送给他人。无畏施是以善巧方便开示烦恼之人,使其心无畏惧而得自在。关于布施还有其他多种分类方式,兹不一一述说。
修舍无慈、悲、喜三事,无所执著,平等无二,正与布施相应。因为无论哪种布施,都是为了消除心中执著,解脱众生。佛教认为,施者、受者、施物三者本质为空,不存任何执著,称为“三轮体空”、“三轮清净”。且提出法施功德甚过财施,因为“财施者,除众生身苦;法施者,除众生心苦。财施者,为其作无尽钱财;法施者,为能无尽智。财施者,为得身乐;法施者,为得心乐。……财施者,能与现乐;法施者,能与涅槃之乐”[25]卷2。
无论是修慈的戒杀,修悲的救济,还是修喜的弘法,修舍的布施,都是净心、利他之举,四者之间互摄相融。所为都是为了使众生离苦得乐,获得自在解脱,为了世间的和乐安宁。
四、大乘佛教慈善理念的现代意义
现代社会竞争加剧,科技的飞速发展,全球经济的互生共融,给人类的生活带来福泽和便利,但同时,全球人口基数的逐年膨胀,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不可再生资源的日益匮乏,为各自利益而战的无尽威胁,无疑又使人类面临更多压力和挑战。面对严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大乘佛教慈善理念的推行和普及则显出其积极的社会意义。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以佛法为导,为佛弟子与众生提供世间共修法门。佛教的慈善理念没有狭隘的等级、阶级的界限,超越了利己主义。“四无量心”之慈悲喜舍,都是以佛法为导,以众生的利益为修行前提。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平等喜舍,宣扬的都是对一切众生施予普遍慈悲和平等救护。佛法教导众生,不仅要从情感出发,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悲悯同情众生的苦痛,而且还倡导“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性解脱方法。对于处在贫困中的人,主张不能仅考虑救济,还需教给他们实际技能,以自己的行愿彻底帮助他们脱贫脱困。这种对己力的推崇,有助于激发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可谓为佛弟子与众生提供了世间共修的法门。
2.以生命为本,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佛教慈善理念特别重视慈和悲,慈悲被视为佛法的根本,也是道德的最高准绳。长养慈悲之心,则反对杀生,主张放生、护生。佛教一方面以人和动物的生命为重,提倡人与人之间相互友爱,互帮互助;同时,爱惜和保护奔跑在大自然中的各种动物,不因为贪取其皮肉、汁液、内脏、牙齿、骨骼等而行杀戮,另一方面,更广此概念,认为一切山水草木、河流星辰等,都有生命,皆应爱护。这虽然是一种“万物有灵”的意识,但反映出佛教的慈悲情怀。为社会发展之需要,佛教积极倡导低碳、环保的生活理念,积极宣传爱护环境、保护地球的思想。可以说,佛教的慈善理念彰显了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视。
3.以布施为功,平衡社会阶层的贫富分化及物质分配。乐善好施,也是大乘佛教发菩提心,修菩提道所积极倡行的。佛法教导众生,心常普缘一切大众,因为众生事即个人事。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要充分认识到只有众生获得和乐,个人才有真正安宁。利益众生,就是要使众生同得欢乐。其具体表现一为物质的利他,即财施;二为精神的利他,即法施。法施以正法化导世人,有助于提升精神境界,培养健全人格;财施则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社会物质财富的再分配,有助于平衡贫富分化带来的种种影响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总之,大乘佛教慈善理念的接受、推广以及践行,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人民幸福,乃至对社会慈善公益事业,都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大方便佛报恩经[EB/OL]//大正藏:第3册.CBETA佛典集成版:149-152.
[2] 大般涅槃经[EB/OL]//大正藏:第12册.CBETA佛典集成版.
[3] 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EB/OL]//大正藏:第36册.CBETA佛典集成版:315.
[4] 中论[EB/OL]//大正藏:第3册.CBETA佛典集成版:21.
[5] 印顺:菩提心行要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
[6] 大智度论[EB/OL]//大正藏:第25册.CBETA佛典集成版.
[7] 大乘义章[EB/OL]//大正藏:第44册.CBETA佛典集成版.
[8] 大方等大集经[EB/OL]//大正藏:第13册.CBETA佛典集成版.
[9]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EB/OL]//大正藏:第5册.CBETA佛典集成版:272.
[10] 十二门论疏[EB/OL]//大正藏:第42册.CBETA佛典集成版:178.
[11]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浅注[EB/OL]//续藏经:第21册.CBETA佛典集成版.
[12] 大宝积经[EB/OL]//大正藏:第11册.CBETA佛典集成版.
[13] 即兴自说[EB/OL]//藏外佛教文献:第5册.CBE-TA佛典集成版:49.
[14] 梵网经[EB/OL]//大正藏:第24册.CBETA佛典集成版:1006.
[15] 摩诃止观[EB/OL]//大正藏:第46册.CBETA佛典集成版:75-76.
[16] 七佛所说神呪经[EB/OL]//大正藏:第21册.CBETA佛典集成版:546.
[17] 劝发菩提心集[EB/OL]//大正藏:第45册.CBE-TA佛典集成版:378.
[18] 注维摩诘经[EB/OL]//大正藏:第38册.CBETA佛典集成版.
[19]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EB/OL]//大正藏:第12册.CBETA佛典集成版:343.
[20] 佛说大乘十法经[EB/OL]//大正藏:第32册.CB-ETA佛典集成版:765.
[21] 大方广佛华严经[EB/OL]//大正藏:第9册.CBE-TA佛典集成版.
[22] 大悲经[EB/OL]//大正藏:第12册.CBETA佛典集成版:972.
[23] 广弘明集[EB/OL]//大正藏:第52册.CBETA佛典集成版.
[24]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7:21.
[25] 大藏一览[EB/OL]//嘉兴藏:第21册.CBETA佛典集成版: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