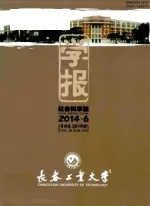自我的探求与接受——对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参与翻译的思考
许一明
(华东师范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200241)
一、前言
在史学界,十九世纪向来被视为现代社会的开端。工业革命带来的不仅有科学技术上的进步,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中包括的方方面面当然没有理由不包括文学。在这一时期,法国文学大放光彩,各种流派层出不穷,时至今日,我们提到法国文学最先想到的一定是十九世纪的作家和作品。
文学的繁荣,既是语言系统日益完善的表现,也是语言发展的动力。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中国,都经历过一个文学盛产、语言长足发展的时期;而在这样的时期中,翻译活动和创作同样活跃:大量的作家主动参与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翻译和创作的距离,并受到后世的认可,例如夏多布里昂翻译弥尔顿的《失乐园》;波德莱尔、马拉美对爱伦·坡作品的翻译等。
这使得我们不禁有所思考:为什么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这么多的作家参与翻译?这些作家参与翻译,又各自持了怎样的立场和态度?翻译对于作家创作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程度又有多深?长久以来,我们关注的是翻译活动对于文化生活其他方面的影响,甚少关注翻译活动对于其内部要素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两个具体个案分析,寻找名作家参与翻译的共同动机及翻译给他们带来的共同影响。
二、作家——译者的自我探求
自诞生之日起,翻译便是一个具有目的性的、能动的活动,而译者是翻译的主体。由于翻译的产生是源于交流的需要,因此人们向来看重的都是翻译活动在交流过程中的“桥梁”作用。同时,由于原作先于译作存在,人们常常将译作——甚至译者——置于一个次于原作的位置:作者、原作是自由的,而处于服务地位、以“仆人”身份存在的译者,则被加以了各种条条框框。以18世纪法国巴特的翻译理论为例,对于一个好的译者的要求一共有12条之多。①巴特的翻译思想主要处理的是翻译中的语序问题,但是其观点仍然立足于翻译相对于原作的“奴仆”关系上。详见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p98-100。由此可见,尽管“不忠的美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一直以来翻译活动背负着的红字依然未被洗脱。人们对于翻译似乎有种天生的不信任。与此同时,随着语言文化的发展,译者本身作为翻译的主体、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存在,已经不再甘于这样一个“桥梁”的定位,其地位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提升。作为文学家同时又是翻译理论家的歌德认为,翻译往往是不完全的,但无论人们怎么揭短,它仍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活动之一,译者是“人民的先知”,因此人们应当重视翻译。[1]法国翻译家安托瓦纳·贝尔曼更是在其遗作《翻译批评论:约翰·唐》中为译者的主体地位振臂高呼,提出了在翻译批评中应“寻找译者”,通过译文思考“译者的翻译立场、译者的翻译规划、译者的翻译视域”。[2]
那么译者究竟应当将自己置于怎样的位置?从主体间性理论角度来看,“翻译”既是原作者与译者主体间共在的场所,也是他们主体间相互交往的方式。原作是他们对话的契机,也是他们对话交流的平台。从对话的角度看,原作是作者和译者对话的议题,翻译是他们的对话过程,译作就是他们交谈的结果。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译者和原作者都是翻译的主体,他们共同完成了翻译的任务。因此,原作者与译者之间,就不应是主次主仆关系,而是平等的主体间对话关系。[3]当译者本身具有作家这一双重身份时,由于其作家身份与原作者身份的一致性,这一平等的对话关系更为明显,也更易出现“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心心相印”的情况。
既然翻译是一种对话关系,那么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的译者希望从中得到什么?作为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实际是在探求自己的内心世界,并通过语言叙述自己、表达自己。由于文学翻译的特殊性,文学翻译本身也是一种创作。所以,在这个以作品为环境的译者与原作者的“对话”中,译者可以获得的是另一种探求自己的方式。
下文中所述的例子只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互译高潮的冰山一角。在这一时期,通过翻译,各国文学相互促进、共同繁荣,而对于作为译者的作家自己的创作生涯,也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三、奈瓦尔和波德莱尔各自的翻译实践
奈瓦尔翻译德语文学,是翻译史上一个颇具特点的例子。他在年轻时期便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根据其传记记载,奈瓦尔“是在1827年夏天和秋初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的”。[4]这一译文,夹杂散文和韵文,而且还存在一些错误。但是,这比他之前发表过的诗歌更使他名声大振。在新版《浮士德》的译序中,他承认了自己翻译上比之前人的差别:“之前的译本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已然足够,但是我希望展现给公众一个与众不同的译文。……我必须承认,我的译文天分充盈而不尽准确。”①原文为法语。〔法〕热拉尔·德·奈瓦尔,译者序言,收录于《浮士德》,歌德悲剧作品,以散文体和诗歌译成的完整新版本,由东代-迪普雷出版社出版,1828年。然而,他同时又写道:“我希望通过这样一篇译文,让世人更好地理解这部德国人自己未必能理解的作品。”
颠覆我们一直以来对翻译的认知的事实是,奈瓦尔并不是德法双语的精通者。作为母语,他对法语语言掌控的天分自然毋庸置疑;但是对于译出语——德语,他的掌握程度只能用“粗通”来形容。但是,他的译文受到了原作者歌德的认可。这源于歌德自己对翻译理论的认识:用散文译诗,更易保留诗歌的精髓。按照歌德对于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的理解,奈瓦尔的翻译“比他自己的原文还要好”。
翻译的成功给奈瓦尔带来了名声和信心。在《浮士德》之后,他又陆续翻译了很多德国作家的作品,以散文诗为主。在他看来,莱茵河的对岸是“一片比政治讽刺诗提供给他的还更为广阔的文学地平线,也更具有个人色彩。”[4]在传记中,特别提到了他坚决地、固执地翻译毕尔格的叙事诗《蕾诺尔》,“仿佛他一定要把他自己的所有秘密全部归还给这部德语作品一般”。这一固执的源头是和他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的:奈瓦尔的母亲的经历和毕尔格诗中所叙述的非常相似。[4]②“[我母亲]二十五岁时死于战争的疲惫,死于她染上的一次感冒,当时,她要穿越一座上面躺满了尸体的桥,她的车差点儿都翻了。”《漫步与回忆》,第三卷,p680。转引自《奈瓦尔传》,余中先译,p76.尽管他自己并不一定认同这一点,它赋予了他一副浪漫主义信徒的外表,给了他从一个阵营走向另一阵营的通行证。今日提到奈瓦尔时,我们对他的评价是“天才加疯子”,更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甚至已经走向了象征主义。他在年轻时期做的工作,正是成熟期的他始终萦绕心头的“梦”的根源。
如果按照今天我们对于翻译立场的简单分类,奈瓦尔的翻译可以说是偏向意译的;这种不完整的、改换文体的译文在今日看来也许并不能被称作“翻译”,更确切的定义应是“编译”。这一现象和他的年龄也是有关系的:他毕竟是一个年轻的译者,对于德语的理解又非常有限。倘若在数十年之后,奈瓦尔重新翻译《浮士德》,或许和他年轻时的译文会有很多出入,会更偏向直译——借鉴下文对波德莱尔翻译的事例,我们可以做出上述大胆的猜想。
波德莱尔对于爱伦·坡作品的翻译,成就瞩目。在1847年,波德莱尔接触到爱伦·坡著作的一些片段,阅读了小说《黑猫》之后,他立刻就被征服了。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波德莱尔不断地翻译出版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波德莱尔翻译爱伦·坡的动机,简单看来是出于“热情”。他曾对好友、里昂批评家阿尔芒·弗莱斯毫不讳言地说:“(在爱伦·坡的著作中)我发现了一些我脑中想写的诗篇和短篇小说,但很模糊、很不清晰,没有秩序,而坡则完美地把它们组合起来,并撰写出来。正因如此,我才产生了如此强的热情,才会有我后来长长的耐心的工作。”[5]这的确是长长的耐心的工作:他的译文从1852年底才开始出现,到1865年在布鲁塞尔完成了《好笑与严肃的故事》这一集子为止,这十数年间,波德莱尔全神贯注于翻译爱伦·坡的著作,以至于他本人的创作深深受到了影响。
但是,在“热情”与“渴望”的背后,也有波德莱尔自我解救的需要。在那一时期,波德莱尔正面临创作的瓶颈。发现爱伦·坡的作品,对于波德莱尔来说,就好似发现了一片新大陆一样欣喜若狂。由于两者的相似,在翻译时更容易心心相印。而波德莱尔也借翻译对自己的美学观点进行再思考。他接受了爱伦·坡哀伤忧郁的美学原则、重视想象力,这些特点在他的代表作《恶之花》中都有所体现。
爱伦·坡能被法国大众接受,波德莱尔功不可没,可以说是波德莱尔成就了爱伦·坡。然而任何作品的出现都面临着褒扬和批评——依然有人对其翻译的策略提出质疑。由下面的列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改写,这也是他被诟病的一点。他的翻译无疑让爱伦·坡作品中晦涩难懂的部分变得易懂,而这被精通英语原文的批评家认为是在“操纵译文”,“违背了爱伦·坡的本意”。[6]

表1 [6]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写呢?在1864年《散文作品》(Euvresenprose)的译序中,波德莱尔写道:“总之,我非常荣幸、非常开心地向尚不认得埃德加·爱伦·坡的法国民众传播一种新的美学;同时,我必须坦白一直以来支撑我工作的动力:那就是向公众介绍一个在某些方面和我有些相似的人,或者说,他就是我的一部分,这一工作给我带来了无上快乐。”[7]我们注意到波德莱尔的用词:“un homme qui me ressemblait un peu”(和我有些相似的人),在这样一个偏正结构的短语中,处于主体位置的是“我”,强调的是爱伦·坡与他——波德莱尔——相似,而并非波德莱尔与爱伦·坡相似。虽然爱伦·坡年长于波德莱尔,但是波德莱尔依然把自己置于一个先决存在的位置。很显然,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波德莱尔将自己置于一个和原作者平齐,甚至更高于原作者的位置。他之所以翻译,是为了帮助他的“美国兄弟”为世人所了解、所理解,从而让他自己被民众所理解、所接受。事实上也是如此。波德莱尔的译文受到了民众的欢迎,特别是在英语国家,他作为爱伦·坡的法语译者被人们熟知;波德莱尔的作品也因此而大卖。
翻译亦是创造。译本的出版,给波德莱尔带来了名声和财富,这便是对他那“长长的耐心的工作”的肯定。然而,在翻译的过程中,无论位置高低,是他自己首先接受了爱伦·坡,并且受到其风格甚至思想上的影响,[8]用爱伦·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实现自我探求与接受。
四、作家——译者的自我接受
综上所述,对于原作,波德莱尔和奈瓦尔选择了不同的立场和处理方式:粗略的看来,波德莱尔采用的方式是“存在改写的直译”,奈瓦尔则采用了偏向意译的方式。但是有一点两者是共通的,那就是他们都和自己翻译的作品有“心心相印”之感,都在翻译活动中通过阅读原作、用自己的话再现原作的方式表达了自己,而后不但使原作被公众接受,自己的创作也受到翻译活动的裨益。对于两位作家来说,翻译活动无疑是值得的,是对自身能力的提升,而不是内耗。从上述两个作家参与翻译的例子也可以看出,译者对于原作的处理方式是多元的,方式的不同源于对自我定位的不同。之前我们有谈到,随着语言文化的发展,译者逐渐从帷幕的背后走向了舞台的前端,和原作者一样成为了这一活动的主体,在对话的过程中用另一种方式探求自己的内心。
探求最终是为了接受。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译者是最初的翻译受众?作为原作的读者,译者首先接受了原作,进而用翻译的方式、用自己的语言“重建”原文所传达的含义,既成为了译作的作者,也是译作的第一读者、最初的接受者。翻译的过程,是一个接受和表达同时存在的过程。接受和表达的对象除了先决存在的原作这一“准线”,也有译者自己。由上面的事例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奈瓦尔,还是波德莱尔,都通过翻译完成了一个自我探求——接受——表达——被公众接受的过程。
所有的文本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都或多或少与其他的文本相联系。也正因如此,在阅读的时候经常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么对作家译者来说,借助翻译,表达的实际是一个存在于世界另一角的“另一个自己”,在翻译的过程中接受自己。既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又是与普遍意义上的“受众”相区别的、主动的“受众”,这一双重身份也使得作家译者比普通的、被动接受译作的受众——读者——对于原作品有更深刻的体会与思考。
五、结语
名作家参与翻译,是十九世纪法国翻译实践的一大特点。由于作家自己就是母语的熟练掌握者,那么处理起译文来自然得心应手,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也因这一双重身份而体现得更加明显。这样的传统延续到今日,使得作家、译者、编辑等文字工作者往往具有双重甚至多重的身份。
然而在文学盛产时期,作家参与翻译根本上是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而在翻译过程中对于自身定位的不同,占据的立场不同,具体处理译作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译作是译者和原作者共同的心血结晶;原作者提供了最初的范例,而译者在翻译在创造的过程中融入了自身的体会,达成了一个“借他言我”的效果。同时,一部译作,首先要被译者自己接受,才能够面世。译者的地位不仅仅是一个传递者,也是一个接受者:接受自己,也接受世界。通过翻译,译者经历了一个自我探求和接受的过程,让自己也受到裨益。
[1]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法〕安托瓦纳·贝尔曼.翻译批评论:约翰·唐[M].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95.
[3]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
[4]〔法〕皮舒瓦,布里.奈瓦尔传[M].余中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5]〔法〕皮舒瓦,齐格勒.波德莱尔传[M].董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6]〔法〕亨利·贾斯汀.波德莱尔:爱伦·坡“短篇作品”的翻译者,还是“奇异故事集”的作者?[J].Loxias,2010,(28).
[7]〔法〕夏尔·波德莱尔.爱伦·坡散文作品·译者序[M].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32.
[8]张丽群.爱伦·坡对波德莱尔的影响[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