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风险社会对法治的严峻挑战
采写/徐娜 金芳翠
季卫东:风险社会对法治的严峻挑战
采写/徐娜 金芳翠

季卫东,1957年出生于南昌市。1983年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毕业后留学日本,获得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90年就任神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996年升任终身正教授到辞职归国为止。1991年至92年期间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自2008年9月起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凯原讲席教授兼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至今。
“法学是实用性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必然会对社会转型发生作用,法学理论需要这样的作用。在国外做个旁观者也好,但还不如做个实践者,直接做个勇士,我希望对这个社会有所影响,对社会的转型有所贡献。”
特约记者(以下简称“记”):季老师好!非常荣幸今天有机会与您品茶畅谈,回忆您早年的经历。在采访之前我们已经了解到,您在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那年正好是26岁。
季卫东(以下简称“季”):对,也还算年轻。
记:也就是说,您在22岁的时候进入北京大学学习的,那在这之前有参加过工作吗?
季:到农村去过啊,我是在1975年高中毕业后下乡的。
记: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带给您什么样的体会呢?
季:了解了中国的现实情况,知道了农民的艰辛和上大学的珍贵。但是,我还是愿意去了解农村并且改造农村。这段经历虽然对年轻人的学习有一定影响,但是对于学社会科学的人来说,这段经历很宝贵。要不然怎么去了解社会?通过到农村,我了解了真实状况,了解了人性的善良淳朴和生活的艰辛,也了解了知识在中国的缺乏,这段经历对于我人生的选择非常大。
记:这段下乡的经历,有没有特别难忘的回忆呢?
季:难忘的是,第一次到农田里干活。我在南昌出生,后来随父亲下放到县城,但是也没有真正干过体力活。第一次下乡干活特别难受,干了一趟腰都直不起来了。刚开始时,当地的小女孩可能都比我干得快。所以,我压力很大,割稻子一不小心还把手指割破了。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记:大学四年中,是否有些记忆犹新的事情呢?
季:记忆犹新的事情很多。比如晨跑和晨诵,到图书馆排队、占座,还有在未名湖畔谈恋爱之类的。那个时候北大学生真是用功,天还蒙蒙亮,图书馆门前就排起了长队,等着进去占座读书。年轻人很珍惜学习深造的机会。即使在宿舍深夜强制关灯之后,仍然有人就着厕所的灯光读书。买饭排队时,也有人拿着英语单词本念念有词。那个时候的学习条件不太好,但求知的欲望如饥似渴。另外,那时的大学生对社会的公共问题、对国家的前途非常关心。大家的确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经常自发地聚在一起讨论。北大的沙龙很多,各种各样的。
再比如,我们同班同学年龄相差很大,最大的一位大姐35岁,最小的才16岁,叫査海生,就是著名诗人海子,安徽人。海子的宿舍离我的宿舍隔了一个房间。有一阵子他生病,我和同学们一同帮忙照料,对他的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海子早慧早熟,读书很广泛,什么书都看,大部头的文学书,古今中外的诗歌,还有《山海经》之类。我的年纪在那个时候正好处于中间,不小不大,但因为下乡耽搁了四年,也有很强的光阴意识,想把失去的四年时间挽回来。这也是很多同学刻苦用功的巨大动力。
记:那您当时学习很刻苦吧?
季:那时大多数人学习都很刻苦。我算是笨鸟先飞吧,不得不更用功些,所以我们班同学给我起了个外号,叫“不食人间烟火”。其实也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很爱吃红烧排骨木须肉,也时不时出去玩的。
记:季老师,在您四年大学学习期间,您感觉印象最深的是哪位教师呢?
季:当时北大有很多老先生都还活跃在讲台上,像芮沐、龚祥瑞、王铁崖,还有沈宗灵、张国华,听他们的课真是一种享受。我记得龚祥瑞教授的比较行政法是77、78、79三个年级一同上的大课。龚教授像位英国绅士,拿着一叠讲稿,娓娓道来。77级的同学到底年龄大些,很懂事,每次上课都有人带着保温瓶去给他的大茶杯里续开水。龚先生精神矍铄,在校园里能骑着自行车四处飞奔,但冯友兰、朱光潜等老先生则傍晚在校园里缓缓散步。我最难忘的是在1993年发表《法律程序的意义》一文后,龚先生特意在他的新著中引用推荐,对一个后辈奖掖有加。还有张宏生教授、赵震江教授、由嵘教授等许多老师都令我难以忘怀。当时的北大教师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煎熬,很长时间不能做研究、不能教学,一旦恢复高考,就想尽量把自己的所有知识都传授给学生。所以,那时的师生互动是非常感人的。
记:在您的专业中,您的观点如何?
季:我个人的观点或者贡献,主要有几个方面:我认为法的本质不能取决于某个阶级的主观意志,要有客观性,那就自然而然地会强调对法律的科学研究。所以,我对法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图用社会科学来打破苏维埃式法律教条主义的窠臼。
在法社会学第一波时期,除了参与研究运动的推进,提供理论研究框架之外,我个人在理论上主要提出了两个基本主张,可以看做我的学术贡献吧。一个主张就是新程序主义,把程序正义的观念导入中国特有
的语境,给法律程序赋予了特定
的涵义。
在1992、93年期间,我的
调具有普遍性的程序公正,另一个
强调具有特殊性的法制多元,这两个
方面是相反相成的。后来,这两个方面被分别发挥,从程序公正到司法改革,再到宪政,从法制多元到本土资源,再到地方语境,进而出现了两种主张的尖锐对立。两种主张各持一端,不能形成基本共识,那么法学理论内在的张力反倒会消失。我希望,在自己的学术思考中保持这种张力,所以一直探讨中国法律秩序原理,并把从中获得的认识运用到法制改革论里。对我而言,传统的重新诠释和后现代理论的借鉴,都只是为解答中国法制现代化几何难题画出的辅助线。在1994年,我发表《法律职业的定位》一文,明确提出了司法权合理化是中国法制转型的关键的命题。几年后,我把其中已有的某些观点进一步展开,试图通过合宪性审查加强司法权的地位和功能。2003年11月发表了网络社会中的有限宪政革命的三部曲,即对抽象行政行为和违法违宪规则的“司法审查”、从党内民主到不同政策的“党内竞争”以及依法严格进行预算审查的“预算议会”。
从2009年起,我开始更加关注风险社会与中国法律秩序原理之间的关系。风险社会的确对法治提出了严峻挑战。但从中国的话语和经验来看,风险性其实与传统的制度设计思路也是有关的。在卡尔·施密特的分析框架里,法律秩序有日常和例外的区分,日常要法治,例外要专制。但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是把日常与例外的关系颠倒过来了,或者说混淆了。在中国,似乎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是把非常状态、例外作为出发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反复推敲的理论切入点。
记:您觉得现在中青年学者浮躁吗?法学界的研究风气怎么样?
季卫东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主要著作有《超近代的法》(京都:密涅瓦书房,1999年。获日本法社会学会首届优秀著作奖)、《法治秩序的建构》(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现代中国的法制变迁》(东京:日本评论社,2001年)、《宪政新论》、《法律程序的意义》、《中国审判的构图》(东京:有斐阁,2004年)、《正义思考的轨迹》(北京:法律出版社)、《秩序与浑沌的临界》(北京:法律出版社)、《法制的转轨》(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法治构图》(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
语文学习,学生不仅要从课堂内获取知识,还要把课堂外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教师还要指导孩子有目的地读书,使他们在“课外”的大海洋中汲取能量。作为小学生,在起始阅读阶段该读哪些书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给他们推荐适合他们年龄特征和认知水平的书籍,甚至给不同兴趣爱好的孩子推荐不同类型、不同书目的书,指导阅读,并提出阅读的相关要求,如指导制作《读书卡》、开展读书会等。以丰富的书籍内容作为阅读的载体,扩大阅读面,拓展视野,提高阅读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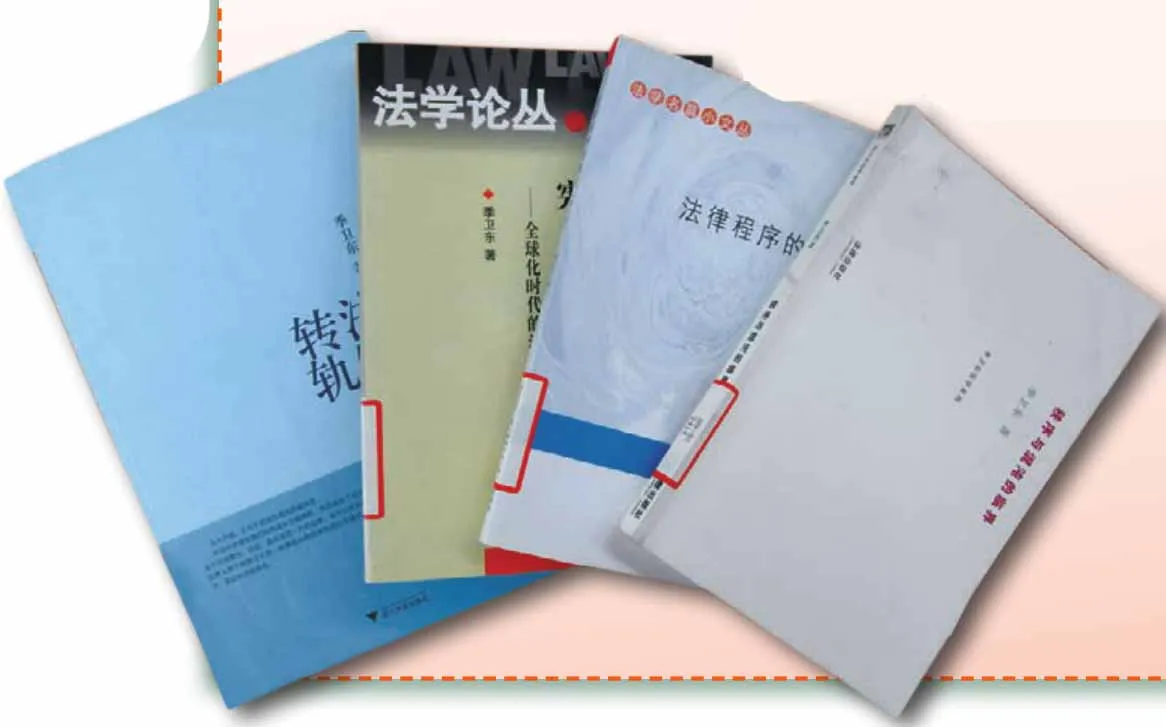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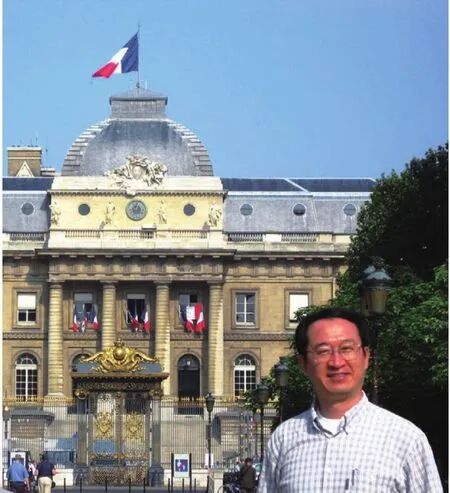
季:我觉得有一批人在真正做学问,但是整体的风气不太好。现在是有些本末倒置。比如说考核制度,考核制度本来是希望促使大家多出一些研究成果,只是手段而已,但现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把它变成目的了。其实这是一个应该出思想家,出杰出成果的时代,但是呢,因为社会变化速度太快,导致实践走在理论前面这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整个社会让人看起来眼花缭乱,很难有人坐下来思考沉淀。我们整个研究环境经过战争或者激烈的社会变革,还有就是重商主义,经商大潮的冲击也让安定的书桌难以安放,再加上科研考核,行政化的管理使学者很难静下心来做研究。这本来是个需要思想积累的时代,但我们看起来却产生不了思想巨人,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实际操作的一些东西,甚至有一些跟着政府决策走的帮忙做宣传的东西,更不要说仅仅是为了换取科研经费而制作出来的文字垃圾。
目前的这个学术状况,为什么会是这样?可以说是行政化造成的。说是行政化造成的原因是这样的,做研究总需要某些支撑,那么这时候研究经费对于学者进行某项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而研究经费的分配是由行政部门掌控的,而行政部门的分配方法,是根据国家的需求啊,学者的建议等等具有很大的主观任意性的标准,然后再加上这个评委的作用,结果造成学者们整个的研究被扭曲了。他们并不是真正选择自己想要研究的题目,也并不一定是为了寻求自己认定的真理,而是在考虑如何获得他人的认可以取得经费。这样很像凯恩斯的“选美理论”,在选美过程中,往往是我认为这个人漂亮,我就为他投票,但是呢,选美带来一些附加价值,比如说,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好处,然后是由评委来决定。那么,这时候我推举人出去参加选美活动,一定要考虑评委能不能够同意,那么这个人就扭曲了,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个人美,而是考虑评委会认为这个人美,会给他打高分。其实,这个机制对学术的扭曲是非常大的,使得学术本身造成一种歪曲。
第二,因为中国是一个赶超型的国家,他要迅速的发展,所以出现了追求数量的倾向,这样构成了压力。我们知道,学术是不能完全用数量来衡量的,不能像卖白菜似的,按斤按两来称的,或者像北大教授李明说的,像是养鸡场似的,给你多少食,你就得下多少鸡蛋。其实,学术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法经济学大家科斯,一辈子就出版一本论文集,获得诺贝尔奖就是两篇论文,但是这两篇论文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这两种学者都是重要的。而我们现在是人为的拉动,最后造成一些学者专门对着这些指标来定自己的计划,定自己的写作,所有的这一切,很多都是在制作文字垃圾。因为他是按照上面的好恶来做文章,怎么样拿到钱,怎么样多发,这样对于我们学术的歪曲是非常大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学术和宣传的混淆,特别在人文社会学科,特别在法学领域。本来学术的事,要求真,他必须是真实的,不管这个话说出来好听不好听。我们学术要求的就是揭示真理,这样的话你才会少走歪路,社会发展才会健全。当写文章不是说真话,而是变成一种宣传,是一种既定方针的宣传,那就等于“花钱买吆喝”了。那就等于说,你的学术水平永远高不过决策者的既定框架。这没有意义,这学术水平怎么可能发展。如果继续这样花钱买吆喝,那不会有真正的学术出来的,只是多了些写手而已,做宣传而已。这些都是非常浮躁的,导致现在的问题都很严重。
还有要求硕士生发表多少篇论文,这都是奇谈怪论。除了少数的例外,在一般情况下,硕士生的文章,本科生的文章是不能指望他有学术价值的。硕士生的文章,在国外是不会要求他发表的,如果强求,就会导致文风和学风的败坏。例如,花钱买版面之类的做法,实际上从源头上把学术的清流弄脏了。
记:您认为现在学术规范执行得好呢,还是不好?
季: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多的,有两个极端的情况。第一个极端的情况就是没有学术道德,盲目地剽窃都有,很普遍。很多文章雷同,抄来抄去,这是一个倾向;第二个倾向反过来,你一讲学术倾向,稍微受到西方一点影响,就说你没有原创性,剽窃。这个是两回事。学过《著作权法》都知道,任何一个结论,它不可能完全凭空产生,必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出现,这个不属于模仿。不可能说我全部原创,绝对不可能,必然在前人基础上,然后你有一点进步,就算创新,你必须吸收前人的成果。
第二点就是说思想不存在著作权侵犯问题,比如说你有好的想法,我把它反映在我的文章里,但是我跟你写得不一样,我是按照我的想法写的,是你的idea。我写了,这个不属于剽窃。当然,我在会上说我正在什么研究,你听了就赶快写出来,虽然我不能说你剽窃,但这样做是不道德的。很讲究学术规范的人,会说在某个会上,我受过启发,或者谁曾经在交谈中提到。那么,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要善于引用。引用他人的成果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假如你看了十本书,提出一个观点来,虽然原创性不算多,但这就是自己的贡献,也属于学术,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记:您对中国的法学教育有什么期待或者建议吗?
季: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法学教育改革已经势在必行,需要从数量转向质量。再拖个两三年或许还行,但不出五六年,绝对需要改变。怎么改,是很重要的。原来是盲目追求规模扩大,不能老是扩大,需要瘦身,可是已经存在的法学院校也无法拿起斧头硬砍。只能通过促进院校之间的竞争,让市场来逐步淘汰。我觉得改革的方向就是小而精、差异化。在综合性大学法学院里,我们要带头小而精,凝练自己的办学特色。其实我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已经预见到法学教育的现状和改革趋势。所以我一回国就推动三三制法科特班的创办和法学教育国际化。
记:最后,能否请您给我们年轻学子讲些勉励的话?
季:我觉得中国法学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你们受过完整的良好的教育。现在资讯条件也不一样。像我们吧,有社会经验了,毕竟我们原来那个条件还是很受影响。当然这个可以通过后天来弥补。国外留学,通过自己不断努力把过去损失的时间尽量补回来。你们现在这个环境还是比较好。我觉得只要奋发有为的话,就一定能成功。法学的发展也好,法治秩序的建构也好,国家的发展也好,希望都是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你们是21世纪的,我们是20世纪的。
栏目主持人:程新友 jcfycxy@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