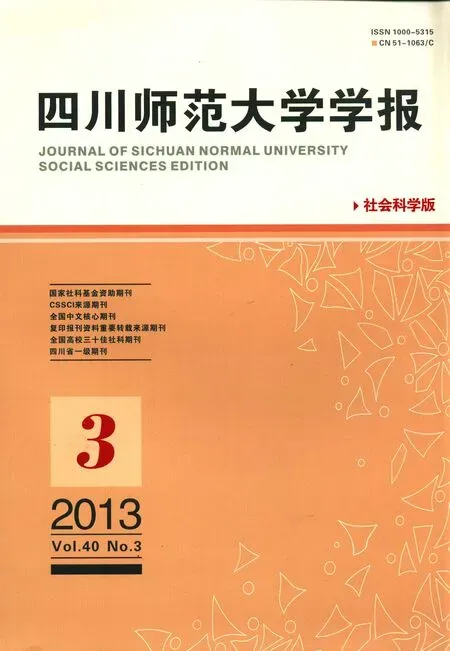论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
纵 博
(四川大学法学院,成都610064)
论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
纵 博
(四川大学法学院,成都610064)
我国目前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是一种形式印证模式,这种模式以其他单个证据与口供印证,但并不能保证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反而强化了口供的中心地位,使非法口供更难以排除。因此,应当对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进行改造,构建推理-印证证明模式,先以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进行证据推理,再以得出的推理结论与口供进行综合审查,最终认定案件事实。这样可以在证据审查中不再绝对依赖口供,促进准确审查单个证据的客观真实性,避免错误认定案件事实。为此,应当改进单个证据的审查方法,在简易程序中进行有效的举证质证,并提高法官的证据推理和论证能力。
认罪案件;形式印证模式;推理-印证模式;证据审查;法官能力
在我国的刑事案件审判中,大多数案件是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这一点在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尤为突出。笔者曾参与一项课题的调研,发现在某基层法院2009年审结的316件刑事案件中,共有被告人449人,其中认罪的被告人有389人,占86.6%;部分认罪(即承认犯罪的部分构成要件或部分犯罪事实)的被告人有16人,占3.5%;完全不认罪(包括翻供)的被告人有44人,仅占9.7%。也就是说,大概90%的被告人在案件中都是认罪的。在这些认罪案件中,除司法解释规定的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外(主要是共同犯罪案件和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其他案件基本上都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然而,笔者经过查阅部分认罪案件的判决书和案卷材料,却发现我国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迥然不同,且与刑诉法的要求和证据法理论的要求都相去甚远,在实践中形成以被告人口供(特别是审前口供)为中心的形式印证模式。这种证明模式虽然对于法官来说易于操作,提高了审查证据的效率,但因为缺乏根据其他证据进行的证据推理,很容易因过度依赖口供而导致错误认定事实。而目前新刑诉法将所有认罪案件均纳入基层法院可适用的简易程序范围内,并且最高院与最高检的司法解释均有再度简化认罪案件举证质证程序的倾向,可能会使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在现有的形式印证基础上进一步变异,更不利于正确认定事实。因此,笔者拟从现有的认罪案件证明模式分析入手,指出其弊端,并提出认罪案件的新的证明模式,以求在实现诉讼效率的同时避免事实误认。另需交待的是,本文所称的认罪案件,是指被告人完全认罪的案件,而不包括部分认罪的案件①。
一 形式印证模式
印证证明模式是龙宗智教授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概括,这种印证证明模式也属于自由心证体系,但与典型的自由心证又有所不同,在证明上重视支持性证据的印证,缺乏支持性证据印证就无法定案[1]。在刑诉法修改前,虽然法律条文未直接对证据印证进行具体规定②,但在证据法理论上,一般都把证据印证作为判断证明标准的要求之一,通常表述为“证据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或者“证据之间能够互相支撑、互相说明,孤证不能定案”③。“两个证据规定”也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印证作为判断证明标准以及单个证据审查的方法,如《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对依间接证据定案的第三项要求明确规定,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另外,对证人证言与被告人供述,也都要求其他证据印证才能采信。近年来,学界对于印证证明模式颇有微词,认为这种证明模式有机械化、形式化的弊端,既不利于顺利追诉犯罪,也不利于防止错案,因此有学者认为应当摒弃印证模式或对其进行改革,至少要进行谨慎的突破,发挥自由心证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④。
虽然印证证明模式存在一些弊端,如对案件证明标准设置了过高的要求、容易导致违法取证以求印证等,但印证方法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物存在的规律,也符合在相互联系中认识事物的认识规律,是司法实践中的经验理性[2]。在证据审查判断中,若仅将印证作为一种判断证据的方法,而不是硬性的形式化规则,还是有其道理的。依我国的司法解释规定及主流证据法理论,无论是认罪案件还是不认罪案件,对单个证据的审查判断都要以印证为标准,对全案证据进行是否达到证明标准的审查判断时,也要以证据之间的印证作为衡量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尺度。
在被告人不认罪或当庭翻供的案件中,在证据印证的基本要求下,具体证明模式较为复杂。法官和检察官都会认真对待证据问题,进行严格的举证和质证。在事实认定的推理和论证方面,法官也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在裁判文书中将各个证据的主要内容列出,逐个审查和阐述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明力,并且对证据之间的矛盾进行排除,实现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同时还要对辩方在证据问题上提出的质疑进行解答,最终综合全案证据进行推理,得出其认定的据以定罪量刑的裁判事实。因此,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证据推理的树状过程,在“零口供”的情况下,这个过程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能够通过证据推理出待证事实,才能进行定罪量刑,否则其裁判结论就无法在法院的行政审批流程中过关,也无法说服当事人及公众。在不认罪案件中,对证据的推理需要法官先从证据推论出一些中间待证事实(主要是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如行为、目的等),然后再从中间待证事实推理出最终待证事实(也即据以定罪量刑的最终裁判事实)。如下面的简图所示,在不认罪案件中,在A、B、C、D等证据相互印证的基础上,要首先从证据A、B、C、D推理出中间待证事实E、F,然后再得出最终待证事实G。因此,不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可以称之为“以印证为基础的证据推理模式”。

因为我国不实行英美法系的有罪答辩制度,所以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理论上也应遵循与不认罪案件相同的证明路线,将口供作为证据之一与其他证据一起进行证据推理,最终得出案件事实,并且对口供还多了一个口供补强规则的要求,必须以其他证据保障口供的真实性。我国刑诉法也对此有明确要求,如新刑诉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2012年12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也规定,证据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共同指向同一待证事实,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可见,无论认罪案件还是不认罪案件,都应查证各个证据是否客观真实,并综合全案证据进行推理,判断是否已不存在合理怀疑。
但实践中,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较为简单,主要是审查口供是否完整、一致,然后用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对口供进行形式印证,但是在实践中,其他单个证据与口供是不可能在所有证据信息上完全印证的,因此在实务操作中,法官只要审查这些证据与口供的内容是否存在一致之处,哪怕仅仅只是有一小部分信息相符,就形成了“印证”,据此就可以认为口供是真实的,也满足了口供补强规则的要求,案件也就达到了证明标准。即使法官此时对被告人是否犯罪依然心存疑虑(依然存在合理怀疑),未能形成内心确信,但有其他证据与口供形成了形式印证,也照样敢于定案。这种证明模式就像是一个围绕着口供的圆圈,在圆周上是其他证据,这些证据实质上起到的是“烘托”口供的作用,而不是进行证据推理的依据。从判决书中的证据论证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来,对于认罪案件,判决书通常采取的是整齐划一的格式:上述事实,被告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认罪,并有× ×证言、扣押物品清单、犯罪现场示意图及指认照片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至于这些证据对口供到底印证的是什么内容、这些证据之间是否印证、这些证据加上口供是否真能合理得出案件事实,则不进行论证,也不进行全案证据推理,只是通过单个证据对口供的印证,形成众证一致指向口供的局面,实际上基本还是直接依据口供内容定案。因此,在认罪案件这种证明模式下,法官认定案件事实践行的还是“口供中心主义”,只不过为了满足口供补强规则的要求,才从证据数量方面以其他证据对口供进行陪衬。正如下图所示,在认罪案件中,证据A、B、C、D、E、F都是围绕着口供G而对其进行印证,因为认罪案件中其他证据不需进行复杂的证据推理,所以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可称之为“形式印证模式”。

之所以称之为“形式印证模式”,是因为其他证据对口供的印证,仅仅是在数量与外观上满足“形式的”印证要求,至于按照口供补强规则的要求,这些其他证据是否足以保障口供的真实性,法官通常不会在裁判文书中加以论证,因此其他人也无从判断案件证据是否足以准确的推理出案件事实。依口供与其他证据的印证情况来判断口供真实性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从证据法理上看,这种印证应当是实质的印证,也就是说,不应以单个证据与口供进行简单的对比,而应在审查单个证据的真实性基础上,综合所有其他证据,形成一定程度的内心确信后,再与口供进行比照印证,判断口供的真实性。这一过程正如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五八二号解释所言,应依其他必要证据之质量,与自白相互印证,综合判断,足以确认自白犯罪事实之真实性,始足当之⑤。
由此可见,认罪案件中的的证据印证,与不认罪案件中有所不同,在不认罪案件中,因为要进行证据推理,所以为了保证推理结论的正确性,首先要保证单个证据的真实性,若单个证据不真实,就可能直接导致推理结论错误,造成错案。因此,在不认罪案件中,法官通常会认真审查证据之间是否印证、印证到何种程度,谨慎对待无法印证或印证不足的证据。而在认罪案件中,因为其他证据不需进行证据推理,只要能够对口供起到形式上的印证作用即可,至于印证的内容、印证的程度,则基本上不多加考虑,只要不出现明显的矛盾,即可定案。
二 形式印证模式的缺陷
(一)强化口供中心主义
降低口供在诉讼证明中的地位是目前法治国家刑事司法的一个趋势,这是基于对专制制度下口供制度的恐惧和反思而出现的一种证明制度改革。如在日本,法律从自白的内容和程序上限制评价自白的证明力,只有自白不得认定被告人有罪;只有在调查有关犯罪的其他证据之后,才能请求调查自白,因为若先调查自白就可能过分评价自白的证明力,所以应先调查自白的补强证据,调查补强证据的程序独立于调查自白的程序[3]253。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英美法系,口供和证明力较弱的证言通常也需要补强,对于在法官面前的有罪供述,可以不要求提供补强证据,但是对于审判外的自白,必须有其他证据担保其客观性[4]153。另外,对于口供,通常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设置了自白任意性规则、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等对其客观真实性予以保障,为公诉机关仅凭口供定罪设置了重重法律障碍。
以口供为中心是我国传统刑事司法中“罪从供定”思维的延续[5]。侦查活动主要围绕着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展开,一旦获取了口供,侦查任务就基本完成,剩下的其他证据即可慢慢补充收集。在审判中,对口供的调查也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从我国法庭调查的顺序也可看出这一点,通常要先对被告人的口供进行调查,有了口供,即使法官未对被告人的犯罪形成内心确信,也敢作出有罪判决,若没有口供,即使其他证据较为充分,法官也不敢轻易判案。在口供中心主义下,以刑讯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就成为普遍现象。因此,为克服口供中心主义的弊端,学界提出要建立以实物证据为中心的新的证明机制,不再将口供作为证据之王;同时,要建立非法口供的排除规则,严格遵循刑诉法规定的口供补强规则等,降低口供在证明机制中的地位。然而,在目前这种认罪案件的形式印证证明模式下,口供的中心地位不仅未降低,反而得到了加强。因为其他证据的价值仅在于对口供的某一方面、某一部分进行印证,而不是靠这些证据形成证据推理体系以证明待证事实,因此绝不可能成为证明过程的中心,最终的定案根据主要还是口供。虽然在形式上,其他证据能对口供起到补强作用,但在形式印证模式下,其他证据的补强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形式化”了,只要被告在庭前及庭审中均认罪,其他证据的补强作用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凑证据数量而已,从法官们在判决过程中的思维来看,也确实反映出这种倾向,即只将其他证据罗列出来,但并不对其如何补强口供加以说明。
由此可见,形式印证模式不仅未能将口供置于与其他证据平等的位置,反而在相互印证的名义下,更加凸显出依靠口供定罪的证明模式特征,强化了口供在证据体系中的中心地位。
(二)容易导致错误认定案件事实
形式印证模式还使得事实认定中的错误更难以被发现。如上所述,这种模式是以其他证据印证口供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部分,但是,仅仅实现了这种印证,认定的案件事实并不可靠。因为这种印证的前提是口供要真实,而口供的真实性受多种因素影响,非法取证、被告人不具备必要的记忆和表述能力、代替他人顶罪等都会产生虚假供述。如果口供本来就不真实,即便实现了印证,也会导致错误的事实认定,所以仅靠单个证据对口供的印证,难以保证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再者因为我国的刑事审判中,案卷笔录是证据审查的中心,控方很容易在案卷中把证据做得相互印证,从外观上看不出任何问题。另外,从其他证据的角度看,对于实物证据来说,这种印证很容易实现,如在涉黑案件中,若嫌疑人做出了通过黑社会性质活动进行敛财的有罪供述,那么扣押或冻结的财物,就在形式上与口供形成印证,但实际上这些财物有可能是合法财产。而在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中,因单个证据所包含的证据信息往往是多个方向的,除了与口供印证的这一方向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方向的信息与口供方向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如某个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在案发现场看见被告人,与被告人口供中承认到过现场可以相互印证,但该证人同时证明在现场看到被告人是在案发前数个小时,与案发时间相隔很久;或者证人证明在现场还曾见到过其他人。如此一来,案件事实就出现了多种可能性,但是在形式印证模式下,因为追求的是单个证据中的部分信息与口供能够印证,因此对于其他方向的证据信息,由于受印证思维的局限,法官就可能会忽视,而径直认定证据之间是印证的,因而是真实可靠的。但因为对其他方向证据信息所形成的可能性的忽视,最终认定的案件事实并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这种情况可以从以下这个案例看出这一点。
某地发生持枪抢劫储蓄所案件,经侦查确定赵某为嫌疑人,赵某到案后也供述自己的持枪抢劫行为,但细节并不明确。除口供外,还有这样一些其他证据:1.证人甲(储蓄所营业员)经辨认认为“赵某很像那个抢劫犯”;2.证人乙(枪贩)称两个月前曾卖给赵某一支五连发钢珠手枪;3.侦查人员从赵某家中搜到一支手枪,证人乙辨认后肯定就是他卖给赵某的那支枪;4.储蓄所被抢3万余元,证人丙证实,赵某在案发后三天向他归还了2万元借款;5.证人丁说赵某案发数月前一次饮酒过程中曾称想抢银行;6.侦查人员能证明赵某在案发后不久离开本市且去向不明,半年后才返回。在这些证据中,几乎每个证据都有一些信息能对赵某的口供形成印证,如证人甲的证言可以对赵某供认自己是抢劫犯进行印证;证人乙的证言、辨认结果及手枪可以对赵某称自己是持枪进行抢劫的这一点进行印证;证人丙的证言可以对赵某供述的抢劫结果进行印证;证人丁的证言则可以与赵某供述中的犯罪动机进行印证。因此,这一案件从“形式印证”的角度来看,确实形成了多数证据印证口供的状态,也符合口供补强规则的要求,似乎可以定案。但这些证据对口供的印证实际上并非牢不可破,除对口供印证的信息之外,每个证据都有一些其他信息需要加以审查和判断,如证人甲的证言,只是证明赵某很像抢劫犯,但是哪些方面像?哪些方面不像?证人乙的证言和辨认可以证明赵某确实从乙处买了该手枪,但该手枪是否是被用于抢劫的手枪呢?即便是的话,有无其他人从赵某处偷用该枪的可能性?证人丙只能证明赵某在劫案发生后归还其2万元,但这2万元的来源如何确定是抢劫所得的赃款呢?若对这些其他方向的信息不予考虑就直接判决赵某有罪,显然是草率的。后来赵某在庭审中翻供,并对上述证据作出如下辩解:1.买枪是为了防身之用;2.归还的2万元是做生意赚的钱;3.他说想抢银行只不过是酒后吹牛;4.案发后离开本市是到南方做生意;5.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刑讯逼供的结果。此案中若赵某不翻供,法官完全可以根据口供和其他证据所形成的形式印证而直接判决其有罪,并且很难对这种错误判决进行纠正,因为在有赵某口供的情况下,其他证据又都能对口供形成印证关系,所以从外观上看,事实认定是没有问题的,但事实上却由于盲目追求印证而忽视证据的全面审查和正确推理,直接导致错误认定案件事实。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像赵作海、杜培武、佘祥林等案件中,除了被告人口供外,其他证据也一应俱全,并且也能形成印证,最终却被证实是错案。实际上这些错案都可归因于我国刑事司法中对认罪案件的这种形式化证明⑥。
(三)使非法口供排除更加困难
自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出台后,我国正式确立了非法口供的排除规则,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不得作为证据使用。新刑诉法也在证据制度改革中正式吸收了这一规则。学界对这一规则抱有较大的期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与美国的自白任意性规则不同,我国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主要规范目的不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自愿性,而是为了保障口供的真实性⑦。这也就意味着,在判断非法口供是否排除时,对非法取证手段、被告人权利所受侵害程度、口供的自愿性等考虑都是次要的,甚至根本不会考虑,而口供的真实性才是是否排除的首要标准。只要经审查,认为口供是真实的,法官一般不会将口供排除,只有经过综合判断认为口供是虚假的,才会将其排除。在形式印证模式下,无疑非法口供更难以被排除,因为在其他证据已经形成对口供的印证的情况下,即便被告人当庭翻供,也无法撼动这一证据印证体系,法官仍然会坚持认为以庭前供述为核心的证据印证体系是可靠的,并据此作出有罪裁判。依据这种形式印证的证据体系进行裁判,对于法官来说并没有多少错案风险,因为对于上级审来说,这在证据印证及证明标准方面是经得起检验的,至少说明一审没有故意曲解证据并错误认定事实。而若在其他证据能够印证口供的情况下将口供排除,就会带来一系列麻烦,如控方的压力、行政的压力、舆论的压力等,因此即使法官内心形成了口供是非法的确信,也不会选择将非法口供排除。
由此可见,在形式印证模式下,一个突出的负面效果就是增加了非法口供排除的难度,排除了口供,就等于排除了证据印证体系的核心,而在形式印证模式下,其他证据本来就只是起到对口供中证据信息的补充和印证作用,若没有口供,这些证据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并进行证据推理以证明待证事实。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对于非法口供的排除只能是奢想。
三 建立认罪案件的推理-印证证明模式
(一)推理-印证证明模式的证明路径
由于目前我国认罪案件的形式印证模式存在的上述弊端,应当对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进行重构。虽然如陈瑞华教授所言,由于我国实行间接、书面的审理方式以及行政审批的案件处理方式,再加上对客观真实的无限追求,我国的刑事诉讼不可能放弃印证证明模式。但笔者认为,即便是在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间接、书面审理模式下,也可以对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进行较大幅度的改良,使法官审查证据时不再以口供为核心,而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证据推理能力,并将证据推理与证据印证方法结合起来,但在证明路径上有一定的变化,不再简单化的将口供与其他证据进行对比印证。通过对证明模式的改良,可以取得比形式印证更好的证明效果,并且也可以与目前的案件审理方式兼容。因此,笔者大胆建议,相对于不认罪案件的以印证为基础的证据推理模式,认罪案件应当建立一种推理-印证证明模式,具体而言,这种证明模式应遵循如下证明路径。
1.无论是庭前、庭审还是庭后的证据审查判断中,法官都在心理上首先将口供置于一旁,而先对除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进行单个审查,判断其客观真实性;这种审查判断不以口供作为判断客观真实性的参照物,而是以庭审中直接言词的调查方式、交叉询问方式、间接相关证据(如证明证人的能力、性格、偏见等的证据)、完善的举证质证制度进行单个证据的审查。这样才能在审查过程中摆脱口供的影响,做到客观、全面的审查,保证对单个证据信息认识的完整性。
2.将经审查确定为客观真实的其他证据进行证据推理,得出待证事实的大致轮廓。在这一步,就像在被告人不认罪案件中那样,由证据推理得出中间待证事实,再进一步推理最终待证事实,看推理结论能否得出控方指控事实的大致轮廓。这一轮廓有可能与控方指控事实一致,也可能会对控方指控事实进行一定的修正(如犯罪的具体时间、手段等),但也有可能暂时无法推理出指控事实,甚至有可能与指控事实完全相反。若根据现有证据进行推理所得的结论与指控事实完全相反,就说明被告人不构成犯罪,或犯罪是其他人所为,控方的指控无法成立,但这种情形通常不多。最有可能的就是得出的结论与指控事实一致,或者暂时无法推理出指控事实。
3.在推理结论与指控事实一致时,将这一结论再与口供进行对照,看关键环节是否一致、是否有矛盾;对于事实轮廓中缺失的细节,口供中是否存在;若是口供中包含细节,加入这一细节后,是否存在无法合理解释之处。对于暂时无法推理出指控事实的案件,则需要将推理结论与口供结合起来,看能否形成一个完整的案件事实图景,前后是否能够连贯、一致。这是证明的关键步骤,与形式印证模式不同的是,此处不是用单个证据去印证口供的相关信息,而是以证据推理得出的结论去对照口供,同时也以口供补充推理结论中的不足之处。若发现推理结论与口供存在若干无法解释的不一致,就说明口供的真实性有疑问,需要对口供和其他证据进行进一步调查。若推理结论与口供基本一致,不存在无法解释的矛盾,就说明口供的真实性基本可以确定,然后可以进行最后一步。
4.将口供与其他证据所得的推理结论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最终认定的案件事实。在这个过程中,要进行证据与所认定事实之间的“往返流盼”,即对于所认定事实的每一部分,都要再回头看是否有相应的证据支持,是否与口供或其他证据有矛盾。最终要达到证明结论的唯一性,排除其他假设存在的可能性。如果能够实现这种证明结果,就说明案件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并且能够实现证据印证,因此在以行政审批的案件处理模式下,案件的处理流程也不会产生什么问题,这就是推理-印证能够与现行制度兼容的优势。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认罪案件中,有一种情形可以例外,无需严格适用这种证明模式,就是《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互相印证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隐蔽性强的物证、书证直接来源于被告人口供,若非如此,控方是不可能获得的,这就说明口供具有较强的可信度,因此在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的前提下,可以直接采信口供及其他证据,并认定被告人有罪,无需经过上述证明步骤。但关键问题是,要明确所谓“隐蔽性很强”,是指在没有被告人口供的情况下,就没有收集到该物证或书证的期待可能性。在个案中,必须排除侦查人员明知该物证或书证存在,而故意不收集,等到被告人供述之后再收集的情形。
(二)推理-印证的证明模式的优势
这种推理-印证模式与形式印证模式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再以口供作为证据体系的中心,也不再以其他单个证据对口供进行印证,而是先以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进行推理,然后再以推理结论作为参照物去审查口供。这样一来,在不受口供影响的情况下先行调查其他证据,就会全面发掘证据信息,不会只留意与口供印证的信息而忽略其他。如在上述赵某抢劫案中,若在没有赵某口供的情况下以证据1至6进行证据推理,在推理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些证据中包含若干对赵某不利的证据信息,但同时也包含对其有利的证据信息,因此,依这些证据进行推理无法得出控方所指控的事实的轮廓,此时再将推理结论与赵某口供进行结合审查,但因为赵某口供欠缺相关细节,结合之后依然难以得出完整连贯的事实图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判决赵某有罪。
同时,这种推理-印证模式也符合口供补强规则的要求,因为只要口供是真实的,以其他证据进行推理所得出的结论与口供的对比印证过程,本身就是对口供的补强过程,只不过不是以单个证据的证据信息去补强口供,而是以所有证据经推理所得的事实结论去补强口供。而若口供是虚假的,则可以通过对比印证发现问题,不会像在形式印证模式下那样容易遗漏和忽略其他证据与口供之间的矛盾,这将有利于最大限度的发掘证据信息,避免错误认定案件事实。
另外,推理-印证模式也使非法口供不再难以排除,因为在这种证明模式下,口供不再是核心,且这种证明模式逼迫控方必须尽量收集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以满足证据推理的需要,而不再强烈依赖口供。因此即使将口供排除,也不会使整个证据体系崩溃,只要其他证据所形成的证据体系经过推理,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得到一个待证事实的完整图景,也可以定案,这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证明路径是一样的。无论对于控方还是对于法官来说,排除非法口供的阻力都比形式印证模式下小得多。
(三)推理-印证模式的配套措施
1.单个证据审查方法的改进
在推理-印证模式中,对单个证据的审查判断是进行证据推理的基础,因此,必须改进单个证据审查的方式和方法。目前法官在审理认罪案件时,对其他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审查主要是通过查阅案卷笔录,审查案卷中其他证据是否与口供相符,能否印证口供内容。这种审查方法容易导致证据审查的形式化,法官只能关注案卷笔录内容的相互印证,而无法对各个证据进行实质性的证据能力及证明力审查。另外,由于案件笔录范围有限,往往不包含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所以在这种案卷笔录内有限证据资源的前提下,即便做到了证据相互印证,也不能说明证据就都是客观真实的,最终认定的案件事实也难以真正排除合理怀疑并难以实现结论的排他性和唯一性[6]。
因此,在认罪案件中,对单个证据的真实性审查不应将与口供印证与否作为唯一标准,而应按照证明规律,建立科学的审查程序和方法,全面审查单个证据所包含的证据信息。具体而言,在程序方面,要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增强法官对证据的直接感知度,使法官的经验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构建科学的询问、对质制度,全面审查人证的可信度;承认间接相关证据在诉讼证明中的作用,使其在判断证据推理的合理性方面发挥作用⑧;改革目前庭审举证质证的形式化弊端,以单个证据为质证对象,而不像目前这样以一组证据为质证对象,保障辩方的质证权[7]。在方法方面,要能够在审查其他证据时从心理上脱离口供而进行,按照分析证据的规律进行审查,如在审查直接证据时,要从证据来源可靠性、内容可信度两个方面进行审查。来源可靠性又包括证据提供者的能力和知识、身份和动机几个方面;内容的可信度则包括内容的可能性、内容的一致性、内容的合理性、内容的详细性几个方面。在审查间接证据时,则要审查证据推理的形式和前提是否合理,在审查过程中要遵循分析间接证据证明力的定律,如以必然真实性判断为前提的证据证明力大于以或然真实性判断为前提的证据证明力,以或然性真是判断为前提的间接证据中,前提为真的概率与证据的证明力成正比[8]18-23。
只有对单个证据的审查在程序和方法上进行改进,才能使单个证据的审查真正脱离口供而独立进行,否则在欠缺合理审查程序和方法的前提下,没有其他有效办法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而只能借助与口供的对比印证来进行,如此一来,在认罪案件中就无从建立起推理-印证模式的证据推理基础。
2.简易程序中有效的举证质证
基于现实的案件压力和对诉讼效率的追求,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所有认罪案件都纳入了可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这显示出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扩大化的趋势。但令人担忧的是,司法机关有通过司法解释再度简化简易程序举证质证程序的倾向。在旧刑诉法与新刑诉法中,对于简易程序的举证质证都只规定不受关于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但最高人民检察院2012年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六十九条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决定是否讯问被告人,是否询问证人、鉴定人,是否需要出示证据。而2012年12月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则规定,对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所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对控辩双方有异议,或者法庭认为有必要调查核实的证据,应当出示,并进行质证。这条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的司法解释明显不同,对举证质证程序作了较大简化。
简易程序虽然“简易”,但只是在诉讼程序和调查证据方法上的简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在被告人认罪的情况下就不调查其他证据,即便被告人认罪,包括证据裁判、无罪推定以及禁止以自白为有罪判决唯一依据等证据基础原则,仍应适用于简易程序[9]202。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的规定,在简易程序中无异议的证据只需就证据名称及证明事项作出说明,那么在被告人认罪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无需对所有的证据进行举证质证了。如此一来,如何有效地保障辩方的质证权?在辩方不质证的情况下,又如何能保证法官能发现其他证据中与口供不一致之处?实际上,在2003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时,就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普通程序简化审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口供有可能以新的形式成为“证据之王”[10]。
因此,若要建立认罪案件的推理-印证模式,就应当保障控辩双方有效的举证质证,因为被告人的认罪有多种原因,可能作出的是虚假供述,若无法对其他证据进行有效质证,就不能从其他证据及其推理结论判断口供到底是否真实。虽然调查证据的程序和方法可以简化,如对于录音录像,可以只播放关键部分,但不得完全不出示,否则就无法保障辩方对单个证据的质证权,法官依然会在庭审后依案卷中的证据寻求形式印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不利于改变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只会进一步巩固认罪案件中口供的中心地位,不利于发现真实、避免错案。因此在简易程序中还是应当将全部证据出示和质证,防止因过度依赖口供而导致错误认定事实。
3.证据推理和论证能力的提高
我国的证明制度有一个特点,就是重视证据的印证而轻视证据的推理和论证,问题在于,实践中不可能每个案件都能真正实现证据的相互印证,在证明过程中证据推理是必不可少的,依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固不待言,在证据与事实之间需要经过许多中介性的推断,即便是直接证据,也需要运用推论性的推理,如对于目击证人的能力就必须进行推论性推理,包括其正确观察该事件的能力,记忆它的能力以及准确对其加以描述的能力,这些问题都属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自然推理解决的问题[11]156。在案件中总是会出现缺乏足够的印证证据,而必须依靠证据进行推理和论证的情况。若法官在认定事实过程中欠缺相应的证据推理和论证能力,认定案件事实就会出现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会出现一些看似合理、实则毫无根据的“想当然”的证据论证,在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进行任意的思维跳跃,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在推理-印证模式下,因为对口供外其他证据的推理是证明的关键步骤,而口供外的其他证据往往多为间接证据,这就需要法官具有较强的证据推理和论证能力,才能正确进行证据推理。具体而言,法官应掌握以图表或概要等辅助性的证据分析工具,以这些分析工具为基础,构建证据推理的逻辑图式,找出每个证据推理线条背后的大前提(也称为“概括”)⑨,并判断该大前提是否属于司法认知范围、是否需要证据支持,然后才能以类似三段论的方式从间接证据推理出结论。在对每个证据的推理链条进行审查并得出中间结论后,再进行全部证据的综合审查,在综合审查中主要是要看各个证据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否能够实现协调一致,是否存在不合理的矛盾。最终的目的是要形成一个初步的事实轮廓,能够反映出案件事实的基本面貌。这样才完成了根据其他证据进行推理的任务,也才能进一步与口供进行对比和印证。
由此可见,若要在认罪案件中实行推理-印证的证明模式,法官必须掌握必要的逻辑、概率、同一认定等知识和方法,并有较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较强的推理能力,否则就无法胜任证据推理的任务,而只能依靠证据与口供之间的简单印证来完成证明任务。因此,加强法官的证据推理和论证能力,这将使我国的证明模式更加科学、合理,克服实践中形式印证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印证证据不足带来的困难,使诉讼证明过程符合证明规律。这在形式上就要求在判决书中要对证据推理过程进行说明和论证,除了在法律适用方面,在事实认定方面也需要进行法律方法意义上的“说理”。
注释:
①因为只有完全认罪的案件,才符合本文所探讨的“形式印证”证明模式,而部分认罪的案件,依然要经过证据推理才能定案,所以与不认罪案件的证明模式是相同的。
②旧刑诉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新刑诉法对“证据确实、充分”作出界定,即第五十三条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③具体论述请参见:陈一云《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龙宗智、杨建广《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
④这方面的论著较多,较有代表性的如: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谢小剑《我国刑事诉讼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6期;陈瑞华《论证据相互印证规则》,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等等。
⑤关于对这一解释的具体评论,可参见:李知远《浅评大法官会议释字第五八二号解释》,载台湾地区《司法新趋势》2004年第15期。
⑥对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形式化问题,陈瑞华教授也有过较为深刻的论述,具体请参见:陈瑞华《论证据相互印证规则》,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1期。
⑦从“两个证据规定”出台的缘由也可看出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两个证据规定”是由赵作海案件而催生的。参见:陈卫东《中国刑事证据法的新发展——评两个证据规定》,载《法学家》2010年第5期。
⑧所谓间接相关证据,即虽然不与待证事实直接联系,但对每一个由直接相关证据(包括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建立的推理链条中的环节起着增强或削弱的作用,因此也称之为附属证据,它们虽然不能直接证明待证事实,但仍是相关的,如证明证人的视力、记忆力的证据。具体请参见:(美)特伦斯·安德森等《证据分析》,张保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⑨按照特伦斯·安德森等的观点,在证据的推理过程中,尤其是推理链条较长的间接证据的推理过程中,经常需要进行概括(generalization)。所谓概括,也即以一个命题或陈述证明证据与假设之间联系的正当性。概括与从证据到待证事实的推理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相联系,因此,这些概括又称为“凭据”(warrants),为每一个推理环节提供理由。概括通常是“如果……那么”的命题形式,本质上是归纳性的。具体请参见:(美)特伦斯·安德森等《证据分析》,张保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
[1]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J].法学研究,2004,(2).
[2]李建明.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合理性与合理限度[J].法学研究,2005,(6).
[3](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M].刘迪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龙宗智,杨建广.刑事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闫召华.口供何以中心——“罪从供定”传统及其文化解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5).
[6]陈瑞华.论证据相互印证规则[J].法商研究,2012,(1).
[7]谢小剑.我国刑事诉讼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J].现代法学,2004,(6).
[8]何家弘.证据的审查认定规则——示例与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
[9]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0]许建丽.对“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的反思[J].法学,2005,(6).
[11](美)罗纳德·J·艾伦,等.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M].张保生,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On the Proof Mode of Confession Case
ZONG Bo
(Law School,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China)
The proof mode of confession case in China is a kind of formal corroboration mode, in which all other evidences are corroborated with confession.However,the accuracy of fact finding can’t be guaranteed,and the central status of confession is on the contrary strengthened. Therefore the new proof mode,i.e.,the mode of inference-corroboration should be set up.In that mode,other evidences besides confession are sifted first,then the result of inference and confession are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and at last find out the case facts.In this way,by avoiding the complete dependence on confession,the accuracy of fact finding is boosted and thus mistakes in fact finding can be prevented from happening.The sifting method of evidences should be bettered,and effective adducing and confronting evidence should also be carried out in summary procedure.Moreover,judges should have better evidential reasoning and argumentation ability.
confession case;formal corroborate mode;the mode of inference-corroboration; evidence review;judges’ability
DF713
A
1000-5315(2013)03-0033-09
[责任编辑:苏雪梅]
2013-02-23
纵博(1980—),男,安徽宿州人,四川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