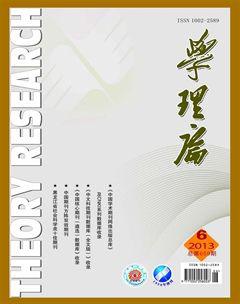民国初年东北社会下层女性生存状况探微
黄巍
摘 要:民国初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阶段,南京临时政府积极倡导革除社会陋习,改变生活习惯,对当时良好的社会风尚起到了引导作用。民初,东北地区亦受到文明之风的洗礼,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然而,对于处于社会下层的东北普通女性来说,由于受传统观念和缺乏教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她们的自我保护意识非常薄弱,其生存状况与现代文明几乎绝缘,仍然在生死线上挣扎徘徊。
关键词:民国初年;东北社会;生存状况
中图分类号:K82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223-03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不断传入,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逐渐开启了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但是,在以男性话语权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的巨大穿透力,广大女性的实际生存状况改善幅度并不是很大,特别是对于民初东北社会的下层女性来说,由于所处地域的相对偏远与社会地位的低下,其生存状况令人堪忧。
一、民国初年东北社会拐卖妇女案件时有发生
民初,华北地区由于兵匪的横行,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使原本生活就很艰难的人们难以承受,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东北地区因地广人稀遂成为华北各省人民想要移民的地区之一。民初,山东、河北、河南等省不断有民众向东北地区移民,移民使东北社会人口数量增多,劳动力的增加,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社会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移民的增多,也使东北社会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在正常的婚娶中,女性人数的相对减少,给人们正常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再加上民初东北地区社会治安秩序的混乱,拐卖妇女案件时有发生。
民初,东北社会拐卖妇女案件时有发生,仅1912年至1913年,辽宁省档案馆记录在案的拐卖妇女案件就达7起以上[1]。在被拐卖的妇女中,通常都是下层女性,这其中既有未婚女性,也有已婚女性,而拐卖她们的几乎都是熟人。如1912年11月,辽宁盖州人董相吉状告邻居郭德福拐卖其妻子董刘氏,董刘氏19岁时就嫁给董相吉,已有十六年之久,并生有一子一女。1912年春天,董相吉出外包工,嘱妻刘氏向邻居郭德福讨要欠债240吊。谁料郭德福窥董相吉家中无人,心怀不良,将董刘氏骗至大岭于家炉,并以1600吊的价钱将董刘氏卖给当地住户于腾云,并有媒证四人和卖字手押为证。董刘氏闻言,怒骂不休,自死未允,情急雇人连夜给董相吉送信。董相吉得信,即赶赴大岭报明该地巡警,郭德福闻知远逃[2]1562。
由于此案件的主犯郭德福外逃,使此案审理出现困难,当地的司法机关竟是严重的不作为,并没有积极派巡警去寻找郭德福,相反却把和此案相关的于腾云等人取保候审,唯把董刘氏关押在堂,并令董相吉自行寻找郭德福到案,否则还得交钱1600吊,才允许领回其妻董刘氏。“县尊田令不但不究于腾云霸买人妻等罪,反逼身自行寻找郭德福到案,再行核断。否则令身交钱一千六百吊,始准领回本妻。身百般分诉不听,现在于腾云等均已取保在外侯讯,唯身妻仍行看押不放,凌辱难堪。似此盗卖人口,霸买有夫之妇逍遥事外,而有夫之妻有妻之夫不得自由冤枉,何极万出,无奈只得来辕泣诉跪恳。”[2]1562此案件中,董刘氏因讨要邻居郭德福之欠债而被拐卖,通常拐卖妇女的人都是熟人,因熟人说的话,容易使妇女相信,使拐卖的成功率提升。这一方面说明女性缺乏教育,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另一方面也说明民初东北地区社会治安混乱,人们缺乏法治观念,社会伦理道德意识薄弱,很多人会在利益面前背信弃义,铤而走险。
由于受教育程度的匮乏,社会伦理意识的薄弱,有些女性被拐卖后,很快就能接受买她的男人,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意愿去寻找原来的丈夫,对自己命运的归属感几乎无意识。如1912年7月,吉林人鞠廷禄之妻陈氏被辽宁昌图刘永清拐走为妻,并带走鞠廷禄钱财四千余元,此后陈氏与刘永清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后来,鞠廷禄将刘永清与其妻陈氏一起告发,“嗣经身来昌,报知警务长派马队巡官,前往缉拿该奸夫淫妇”[3]1633。
上述两个案例,被骗的两位妇女都是有夫之妇。拐卖妇女在当时是犯法的,而拐卖有夫之妇的人多是他们的邻居或朋友,他们既要冒着犯罪的危险,又要背负着良心的谴责,而究其缘由,这和当时人们恶劣的生存状况和男女性别比例不平衡都有关系。由于经济水平的低下,生存问题成为制约人们生活幸福的重大障碍,而女性在这个过程中,遂成了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加之当时法律对女性的实际支持不力,使民初东北社会下层女性的基本生存问题受到威胁。
二、民国初年东北社会下层女性自杀案件频发
民初,东北社会由于经济水平的低下,加之难以预料的天灾人祸常常剥夺了民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处于社会下层的东北女性,其生存状况更是令人堪忧。为了生存,有沦为娼妓的,有被卖为婢女的,也有因生存不下去而自杀的。
民初,东北社会女性自杀案件频发,从1912年至1914年,仅《盛京时报》就报道女性自杀案件33起[4]。在女性自杀案件中,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有因夫妻吵架自杀的;有因受不了公公、婆婆虐待自杀的;有因贫困自杀的;也有因个人名誉受损害自杀的。笔者对1912年至1914年的《盛京时报》进行统计,统计结果显示《盛京时报》共登载33起女性自杀案件,其中因夫妻吵架而自杀的女性案件有12起,居女性自杀原因之首,占女性自杀原因的36.6%[4]。据《盛京时报》报道,1912年8月15日,辽宁奉天大西关小什字街住户孔某之妻陶氏年方十八,秉性端正,平日间夫妻甚为和睦,昨日晚间不知因何细故起口角,孔某手持木棍将陶氏暴打数下,不料陶氏竟含泪投入门外之井,当有他人看见大声呼喊,已气息俱无矣[5]。此案例中,陶氏因和丈夫口角,并遭到丈夫毒打后而投井自尽。这显示出民初东北社会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当遇到困难无法解决时,常常会想到用自杀的方式解决问题。
在笔者统计的1912年至1914年《盛京时报》上登载的33起女性自杀案件中,其中因名节受损而自杀的女性案件有4起[4]。如1912年4月,辽宁旅顺居民陈万才之女年仅19岁,其容貌秀丽,性格贞静,因被邻居散步谣言败坏名节,遂吞服火柴头十数盒毙命[6]。虽然民初社会制度进行了变革,文明之风也逐渐影响到东北社会,但是传统文化观念却仍然在束缚着人们的思维,名节观、贞洁观仍然是束缚女性的严重障碍。这反映出社会制度和文化思想之间有时并不能同步,特别是对于社会下层的人来说,其接受社会制度变革后的文明之风更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虽然民初以后,文明之风已逐渐影响到东北社会,也有东北女性产生自主离婚的意愿,如1914年11月,《盛京时报》报道了吉林省的离婚案件,“近年来吉垣离婚案件不可胜数。”[7]但是,民初的法律规定,夫妻离异必经夫妻双方同意才能准予离婚,夫妻因殴打行为要求离婚的,也必须打到折伤以上,“夫妇离异之规定除夫妇不和谐而两厢情愿者准其离异外,其他以虐待等事为理由者非合于法定条件不可。”[8]“如有妄冒已成婚者离异,又妻妾殴夫,夫殴妻非折伤者勿论,必至折伤以上,夫妇如愿离异者离异。”[8]从大理院判例中可以看出,夫妻之间殴打行为必至折伤以上才准予离婚。在笔者统计的因夫妻吵架而导致妻子自杀的12起案件中,妻子都不同程度的遭到了丈夫的殴打,由于民初的法律对女性的实际支持不力,所以对于民初东北社会的女性来说,想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实际上也肯定了家庭暴力的合法性,进一步强化了男性的家庭地位。由于民初东北社会经济不发达,就业机会很少,加之几千年来传统观念的束缚,下层女性在社会上很难找到受人尊重的工作,她们多是在富裕人家从事帮佣、婢女等社会地位低下的行业。所以,对于民初东北社会的下层女性来说,其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都是非常低的,一旦唯一可以充当其避风港湾的家庭地位遭到撼动,则往往会撼动其生存欲望,自杀往往是她们的终极目标。
三、民国初年东北社会虐待儿媳现象比较普遍
在笔者统计的1912年至1914年《盛京时报》上登载的33起女性自杀案件中,其中受公公、婆婆虐待而自杀的女性案件有5起[4]。据1912年11月19日的《盛京时报》报道,辽宁东平南门里住户沙雨舟因其子在某署充当书吏,故敢私卖大烟,其儿媳素有贤名,不知如何与翁姑不和,时被凌虐,旧历九月二十四日该媳妇因殴打难堪,遂吞服烟土,被翁姑瞥见又复暴打,立时毙命[9]。还有案例如1914年辽宁奉天有刘姓住户,儿媳妇王氏甚贤淑,其婆婆严加虐待,遍体鳞伤,每食不饱,衣不蔽体,时有哀痛之声,昨晚不知何故又将王氏用大棒痛打不堪,嗣经左邻王永泰前往拉动,始行释手云[10]。这两个案例都报道说两位儿媳妇素有贤名,但是却都遭到了公公、婆婆的残忍虐待。前一个案例沙雨舟之儿媳妇被发现吞烟时,作为公公、婆婆不但不去积极救助,反省自己虐待儿媳妇的言行,反而又去暴打,最终致儿媳妇死亡。后一个案例中王氏非常贤惠,但却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时常受到公公、婆婆的虐待。甚至有些公公、婆婆也会怂恿儿子去“管教”自己的媳妇。
中国传统文化就提倡孝道,而孝顺公公、婆婆也是合乎传统伦理道德的。但是,在民初东北社会的有些家庭中,公公、婆婆却是唯我独尊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传统文化观念仍然在牢牢束缚着他们的思维,他们认为儿媳妇除了要替家族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以外,就是要无休止的做所有的家务劳动,儿媳妇是很难有话语权的,一旦反对他们,就会背着不守孝道和妇道的罪名。此刻,婆婆虽然也同为女性,但是却和其丈夫、儿子一起压制着儿媳妇,共同维护着男权社会的绝对权威。由于年龄的增长,时间的推移,婆婆自身的女性性别意识在家庭中逐渐被淡化,多年的苦熬使她逐渐树立起家庭威信,性别已经被权力所置换,所以年轻的儿媳妇首当其冲成为民初东北社会家庭中最受压制的群体之一。
四、余论
民初,虽然社会制度进行了变革,文明之风逐渐兴起。但是,对于地域相对偏远的东北地区来说,由于信息的不发达,文明之风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影响到这些地区。民初,由于东北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加之灾荒的频繁发生,把家庭经济推向了风雨飘摇的境地,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很低,一旦家庭遭遇变故,女性便不得不支撑家庭生活。为了生存,有些丈夫甚至逼迫妻子卖淫来维持生计。即使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女性的实际生存状况也令人堪忧,经常会遭到丈夫、公公、婆婆的共同虐待。而民初的法律对夫妻离婚又有诸多条件的限制,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受教育程度的匮乏,女性抵御困难的能力非常薄弱,一旦遇到困难,便觉得无路可走,常常用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同时,民初东北地区社会治安秩序混乱,拐卖妇女的案件时有发生,所以从总体上看,民初东北社会下层女性的生存状况令人堪忧。而男权社会的绝对权力和不易改变的传统习俗,都是制约女性自我幸福的巨大障碍,女性成为父权和夫权制下可以任意牺牲的工具,成为他们换取钱财的可利用资源,而最可悲的是女性对自身恶劣的生存状况几乎丧失了话语权。所以,要让女性真正意识到自我的价值和尊严确实需要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而改善民生也是各个历史时期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拐卖妇女目录[Z].辽宁省档案馆,全宗目录号,JC10-1,1912—1913.
[2]董相吉呈郭德福等伙谋诓骗霸买人口案[Z].辽宁省档案馆,全宗目录号,JC10-1-16884,1912-11.
[3]吉林府民鞠廷禄控昌图府民刘永清奸霸妇女[Z].辽宁省档案馆,全宗目录号,JC10-1-25266,1912-07.
[4]女性自杀案件[N].盛京时报,1912-1914.
[5]少妇轻生[N].盛京时报,1912-08-15.
[6]处女被谤服毒自尽[N].盛京时报,1912-04-06.
[7]离婚者何多[N].盛京时报,1914-11-22.
[8]大理院判例要旨[J].司法公报临时增刊,1915,(43).
[9]凌虐儿媳吞烟毙命[N].盛京时报,1912-11-19.
[10]虐待儿媳[N].盛京时报,1914-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