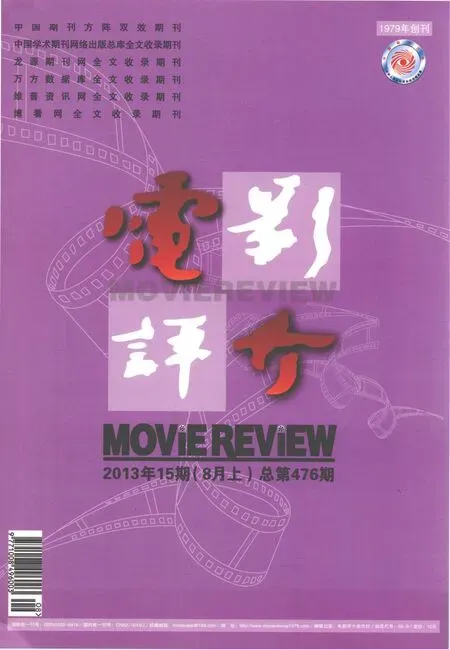“求索”——浅析电影《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中对生命的诠释
□文/沈幸运,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学生

电影《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剧照
阿莫多瓦是西班牙著名导演,其电影色彩感强,情节紧凑,雅俗共赏,且往往跌宕起伏的故事之下埋藏着对人性的深刻思索。《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则可以说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除了商业上收获颇丰外,更是囊括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戛纳最佳导演奖等各大国际奖项。
一切荣耀或许都会随时间流逝渐渐隐去光环,然而撇开所有的鲜花掌声,影片中浓郁的生命思索、深沉的人文关怀却是值得人们一再挖掘的。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作为一部得到艺术上广泛好评的电影,其主旨自然不会是单一维度的,一篇论文篇幅所限,无法面面俱到。因此,笔者仅讨论在影片中所反映出的阿莫多瓦对生命的理解。笔者以为,影片中,阿莫多瓦将生命分为三个层次:求生、求爱、求恕。
一、求生
叔本华认为生存是人最基本的欲求,而且“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著,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427页)在《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中,我们看到,阿莫多瓦也将求生看作生命最重要的欲求之一。
就如人在一呼一吸之间已是在求取活着,阿莫多瓦也会不动声色地将生命求生的本质镌刻在影像中,甚至可以不与片中角色的主要戏剧活动产生太大的联系。如影片第一个镜头就是输液袋大特写的摇拍,然后一直以特写的景别展现了医院中的器械。医院是病患求生的地方,在这里,生存倒真有可能是人的全部本质。何况,特写具有夸张强调的功能,导演连续使用特写把求生的欲望凸显了出来。
阿莫多瓦将主角曼纽拉的职业定位为护士,还是器官移植局的联络人。其实如果换一个职业,对她的主要情节活动不会有大的影响,想来这一设计也有暗示人求生欲的作用。
把视角转向剧中人物的情节活动,影片中表现出的生存欲求就更加明显了。且不论几个主人公,只看一位做心脏移植手术的病人。他是一个小角色,曼纽拉的儿子艾斯德班出车祸身亡后,其心脏被移植给了这个病人。影片表现了从这位病患者接到医院电话通知,到心脏空运至病患者所在城市,直至出院的一系列过程。
首先,这一情节拍摄镜头极简,漫长而广阔的时空被浓缩在8个镜头、不足两分钟内。这固然有不脱离主情节线,节省镜头以关注曼纽拉的用意,但也体现了求生欲的急切,以银幕时间的迅速表达求生的强烈,一刻也不可耽搁。其次,人物表演与音乐烘托极好地契合了迫切紧张的心态。
然而,个人的求生虽然普遍,没有人能摆脱得了,但若发展到极致也会产生病态,伤人伤己。譬如电影《霸王别姬》中段小楼为求取自己活命,背叛了半生的搭档程蝶衣。阿莫多瓦在肯定求生欲的同时,也为这一生命本质提供了一个更高层次的阐释。
所谓推己及人,既然求生是自己生命的欲求,也应尊重他人相同的欲求,而不是毁灭他人来满足自身。所以,曼纽拉在儿子身亡后忍住悲痛,签署了器官移植家属同意书,使生命在另一个躯体上延续。
二、求爱
人与其它动物不同,无法止步于生存,仅仅满足活着并不能正常维持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关于我母亲的一切》认为,人的生命在求生之后,便会求爱。
从生存的角度来讲,曼纽拉暂时是得到满足的,然而影片开始不久,我们就看见她依旧有着鲜明的欲望。曼纽拉带着孩子去看话剧《欲望号街车》,这部话剧贯穿影片始终,显然是有一定象征意义的。
《欲望号街车》女主角布兰奇在南部被解除职务之后,乘坐“欲望号”街车来北方投靠妹妹和妹夫。她南方的亲人曾“一个接一个死去,最后连庄园也失去了,她是一个被遗忘的人,一个完全孤立无援的人。”(宋秀葵:《欲望号街车——一部现代精神悲剧》,载《电影评介》2006年第10期)因此她渴求在北方重获关爱,摆脱孤独。这无疑是布兰奇的欲望,却也与曼纽拉的欲望相类似。
曼纽拉带儿子看话剧时,等在《欲望号街车》的大幅海报之下。画面在儿子艾斯德班的主观镜头之后,切到了母亲的中景。曼纽拉作为前景,后景是话剧的巨幅海报,绘制鲜艳的红唇就在曼纽拉身旁,与她火红的衣服相得益彰。红色,尤其是红唇,象征着情欲,或者说是对爱的欲望。曼纽拉自怀孕以来,一直离开丈夫独自生活。虽说阿莫多瓦所表现的女性与传统观念上的家庭妇女迥然相异,但一个只与儿子相依为命的独身妇女,孤立无援下对爱的渴望是古今相同的。只不过曼纽拉渴望的情爱并不一定是男女之间的爱恋。
母子俩进入剧院,镜头却切换到了海报上布兰奇扮演者嫣迷的双眼特写,并且以缓慢的速度叠化至剧院内的情景,双眼虚虚实实地停留了良久。眼睛是内心的写照,它凝视观众,诉说布兰奇乘坐欲望号街车的往事,也隐射曼纽拉的故事……
《欲望号街车》在影片中既是象征,也是人物命运的暗示。布兰奇独自走向北方,寻找亲人的所在、爱的归宿;当艾斯德班死去后,曼纽拉也踏上了旅程。如果说有艾斯德班陪伴之时,曼纽拉追求关爱的欲望尚不强烈的话,儿子的身亡则彻底将孤独作为她的徒刑,她再也没有理由停留在凄凉的故土,只能离开失爱的地方,寻找可能的希望。
除了曼纽拉,片中其余人物同样展现出了对爱的求索。最明显的莫过于嫣迷,她是布兰奇的扮演者,海报上那充满欲望的鲜红嘴唇可以说是布兰奇,也可以说就是嫣迷。她爱的欲求,指向合作者妮娜。嫣迷对妮娜有着难以自拔的迷恋,没有她,嫣迷表示自己几乎演不了戏。
曼纽拉的丈夫罗拉同样也有对爱的欲望。虽然他是异装癖,明明更喜爱成为一个女人,却在妻子离开后,又与另一个女性生下儿子。与女性生儿育女,本该是一个男子的做法,他想做女人,却又愿意也乐意成为丈夫。其中看似悖论,却反映了他渴求拥有妻子的爱,原配曼纽拉走了,他便去寻找其他女性。
当然,可惜的是,罗拉未能将心比心,予人以同等的关爱,这暂且不论。
三、求恕
生命存在,会求生、求爱。如果说生存只是基础,在大多数的社会形态中,个体追求生存是不会威胁到他人的,但求爱就不同了。爱,是精神上的追求,并不容易满足。正因不易,在求索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会伤害到他人。由此,阿莫多瓦告诉我们,求生求爱之外,若想获得健全的生命,我们还会为这些伤害之举求取他人的宽恕。
如前文所述,罗拉虽然与曼纽拉有婚姻关系,却并没有给她作为丈夫的爱。故而曼纽拉离开罗拉,自己抚养孩子。罗拉于她而言是爱的反面,所以她抗拒,甚至拒绝告诉儿子关于父亲的信息。然而对艾斯德班来说,他并不在乎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他只想知道自己完整的身世。曼纽拉如此简单的爱的追求,竟无意中致使儿子直到死去都不知父亲是谁。
曼纽拉是想求得儿子宽恕的,她离开故土固然是因为没有了孩子之爱,但她选择巴塞罗那作为目的地却有另一层含义。巴塞罗那是她与丈夫共同居住的地方,影片中她明确独白“要再去找他”,寻回儿子那一半失落的身世。
当曼纽拉与罗拉重逢时,她求恕的心态展现得最为明显。接近片尾,曼纽拉告知罗拉自己曾有他的儿子,却不幸撞死时,老泪纵横地说着对不起,请求原谅。罗拉未能给妻子丈夫的爱,曼纽拉也知道他不会给孩子父爱,所以她离去并不能算是错。然而,间接的,曼纽拉这一行为确实伤害孩子,也剥夺了丈夫有儿孙之爱的权利。她求恕,也就不难理解了。
求恕,虽也是一种欲求,然而现实生活中不乏伤害他人却无动于衷的人,求恕是经过反省的欲求,也可说是更为高尚的欲求。故而在影像中,导演阿莫多瓦表达了他对求恕的颂扬。
本片多数镜头是内景,即便是外景也显得空间狭小,多多少少有些许压抑沉重。而这一场戏,环境非常开阔,微风徐来,使得虽然曼纽拉在伤心诉说儿子身亡的往事,给观众的心理感受却并非压抑的。而且切到曼纽拉特写时,光线尤为美丽。主光源来自曼纽拉左侧,后侧也稍有些轮廓光,塑造出来的人物视觉形象立体丰满,几乎是整部片子中曼纽拉最优美的时刻。导演正是在用开阔的环境表达对曼纽拉求恕之举的欣慰,用美丽的光赞扬这相对伟大的欲求。
结语
叔本华所言或许是有一定合理之处的,人一生难免在欲求中沉浮,少不了痛苦与挣扎。阿莫多瓦用《关于我母亲的一切》表达了他的看法,生命既存,便会求生;生却不是生命的全部,要活得更好,便会求爱。但阿莫多瓦却不似叔本华那样将生命看得如此痛苦,他展现了理想生命状态的另一层欲求,便是求恕。求恕,令生命更值得人敬佩,欲求也不再全是挣扎,而只是永不停息的求索。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求生、求爱、求恕,虽是三层不同的欲求,但导演阿莫多瓦并未将它们表现为生命不同的阶段。同一时期,它们可以同时存在,譬如艾斯德班死去后,曼纽拉离开远行,这是在求爱,也在求恕。只不过,如果生命没有足够的阅历,或许很难去接触到求恕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