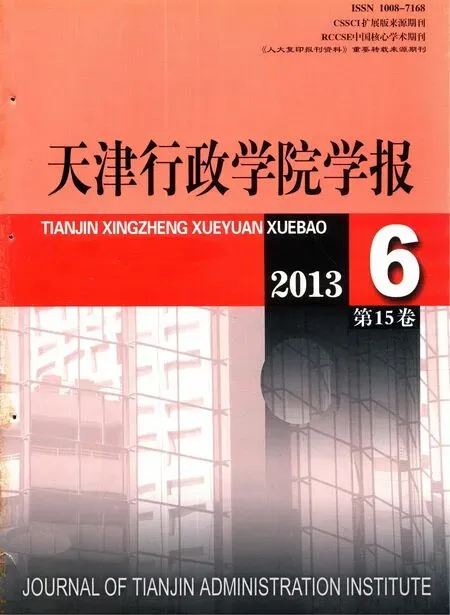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一般性解释及其解决策略——基于博弈论和“搭便车”视角的分析
丁云龙,王胜君
(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一、引 言
当代公共产品理论在讨论政府治理效率时,大都隐含一个基本假定,把政府视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而把政府之外的社会公众和其他群体视为公共产品的消费者[1][2][3]。这一假定并不完全符合复杂的政府治理现实,更不完全符合转型期中国政府组织的运行特征。比如,在中国政府架构上,存在着多个从中央部委一直贯穿到地方政府的纵向行政执法部门,这类组织具有一个共同的运行特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都可以代表政府独立开展治理活动[4][5]。当多个不同的政府部门对某一领域同时拥有管辖权时,对其中的某个政府部门来说,不再单纯是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也是其他政府部门提供这类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具有了典型的双重身份。
对于公共产品的消费,当供给者卷入其中并成为客观上的消费者时,政府治理的效率和性质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比如在食品安全领域,《食品安全法》中明确委托了9个政府部门对其进行治理,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即便如此,大到“三鹿奶粉”,小到不时出现的“地沟油”、“瘦肉精”、“毒胶囊”等一系列事件,表现出来的问题是:政府期望通过多部门“齐抓共管”的治理方式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但问题还在不断涌现,并伴随大量的行政不作为现象。政府治理效率与公共需求之间存在着落差,通常被媒体解读为“九龙治水天下旱”。
一般说来,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属性[6],决定了社会成员可以策略性地采取“搭便车”行为而无需付费,这对提高政府治理效率是有帮助的。但在上面的事例中,我们发现,政府治理效率不但没有有效提高,反而处于某种紧张状态[7][8][9]。也就是说,政府治理过程出现了某种效率损失,我们有理由追问,是什么导致了政府治理的效率损失?具体的成因和条件又是什么?
二、模型分析:效率损失的发生机制
既然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了“搭便车”现象不可避免[10][11],那么沿着这个脉络,多部门的政府治理行为实际上则演化成一种集体行动,部门的双重身份特征具体表现为:他们既可以主动地提供某种公共产品,又可以策略性地选择“搭便车”从而免费享用该公共产品。为了研究方便,首先,我们把涉及的政府部门抽象为一般参与人,赋予人格化涵义;其次,选取一个责任博弈矩阵,直观地讨论参与人之间的博弈状态。在这样一个模型框架下,讨论具有双重身份特征的政府部门的具体行为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审视这种改变所导致的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发生机制。
(一)假设

表1 博弈支付矩阵
博弈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并假设:
1.在政府治理过程中,A、B为N个政府部门中的任意两个,他们都观察到某一企业的不当行为,如制售假冒名牌产品。作为利益相关者,由于他们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因此,都希望有部门采取查处行动并制止这一不当行为。
2.如果不当行为被制止,可以使观察者的支付增加10;但每个政府部门都有“搭便车”的心理,都希望最好是别的部门采取行动,而自己不采取行动,因为查处过程遇到的周折,会使自己的支付减少2(可以理解为“搭便车”的初始心理预期),即,A是否采取查处行动与B的行为相关,也就是,如果A确信B能采取查处行动,那么A就不行动。
3.每个参与人以同样的概率ε选择等待,则行动等待的概率就是1-ε,参与人i的支付表示为πi,为(A,B,L)N个参与人中的任意一位。
4.A、B及任意参与人i之间,在自然信息状态下参与博弈。
5.查处过程遇到周折所减少的支付,可随具体情况变化而变化。
很明显,在上面的模型中,除了存在两个非对称的纯策略纳什均衡(表1数字部分的右上角和左下角)以外,还存在一个对称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在讨论混合策略均衡时,我们将分析的视角从A、B两个参与人博弈扩展到N个参与人。相对A而言,若无人行动,则支付为0;若A自己采取行动,则支付为8;若其他N-1个参与人中任意部门采取行动,则A的支付为10。若所有参与人都以同样的概率ε选择等待,则除A以外,其他N-1个参与人都选择等待的概率为εN-1,所以,在他们中间有人采取行动的概率就是1-εN-1。在计算博弈均衡时,我们采用标准的支付均等化法,即,参与人i的期望支付与他所选择的纯策略支付设为相等,则:

一般来说,只要参与人采取理性的效用最大策略,则(1)式在逻辑上一定成立。本模型的基本思路就是在参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1)式的前提下,检视在“搭便车”初始心理预期变化和参与人数变化的情形下,政府治理行为的一般变化规律和一般均衡效果。
(二)推论
1.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影响因素之一:初始心理预期的变化
将表1中的数据代入(1)式,可得:

由(2)式可得:

在初始心理预期给定的情形下,(3)式中的常数0.2,它的政策含义是描述了参与人采取“搭便车”的可能性大小。显然,参与人“搭便车”的可能性与参与人“搭便车”的初始心理预期相关联。除此种情形以外,为简化研究问题并不失一般性,我们另外再增加两种情形的讨论,当常数等于1或0时,政府治理问题被简化为总是搭便车还是不再搭便车的问题。政府部门采取“搭便车”的可能性可以通过比较三种情形下所获得的一般情况进行判定。
当查处过程遇到的周折所减少的支付(搭便车的初始心理)上升为10,即参与人采取等待策略或行动策略所获得的支付都为0时,此时参与人采取“搭便车”的可能性就可以写成:

当查处过程遇到的周折所减少的支付(搭便车的初始心理)下降为0,即参与人采取等待策略或行动策略所获得的支付都为10时,此时参与人采取“搭便车”的可能性就可以写成:

(4)式和(5)式分别代表总是“搭便车”和不再“搭便车”两种特殊情形,与(3)式相比较可以得出,“搭便车”的可能性与“搭便车”的初始心理预期的涨落相关联,初始心理预期越高,“搭便车”的可能性越大,初始心理预期越低,“搭便车”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
推论1:参与人采取“搭便车”的可能性,与“搭便车”初始心理预期正相关,初始心理预期对“搭便车”行为可起到助涨助跌的作用。
上述推论为研究我国政府治理中存在的一些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有法不依、违法不究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政府治理中广泛存在,仅从文化和传统的角度解释这一问题的成因难免有些说服力不足,但在我国类似食品安全领域的有法不依、违法不究问题的比例显然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事实。上文从“搭便车”初始心理预期涨落的角度得出一个新的解释是:在西方法制相对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涉案企业的违法事件很容易被查处,即可以理解为政府查处过程遇到的周折所减少的支付少,与此相对应,违法企业所面临的诚信代价、市场禁入、赔偿金等方面的违法成本相当高昂,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企业不敢有法不依或违法经营,政府治理效率相对较高。相反,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诚信、市场禁入、赔偿标准等配套法制制度仍不完善,有的问题企业经常“打一枪换个地方”,或“穿马甲”,或与政府管理部门玩“猫捉老鼠游戏”,在模型中表现为政府查处过程遇到的周折所减少的支付高,即“搭便车”的初始心理预期高。因此,政府部门采取搭便车的可能性或动机就比较强,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等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最终体现为政府治理效率不高。
2.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影响因素之二:参与人数的增减
由(3)式可得:

由(6)式可知,当只有A、B两个参与人,即,当N=2时,A的选择等待的概率为0.2,由于,A的期望支付与他选择等待这一纯策略的支付相等,始终等于8,并没有改变,随着参与N数量的增加,例如,当N=30,等待的概率上升到约0.95(0.21/(30-1)),也就是,N越聚越多时,每个参与人选择等待的概率,已经从最初的0.2开始上升,并越来越接近于1,即,参与人越多就越期望别人采取行动。
推论2:在理性的策略下,参与人采取“搭便车”的可能性,会随着参与人数量的增加而得到传导和强化,由此产生强烈的“搭便车”效应,类似于社会学中的“群氓运动”。
上述推论为研究我国政府治理中的“九龙治水天下旱”等行政不作为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在美国,食品安全治理主要是由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和农业部(USDA)两个政府部门作为具体执行机构进行日常管理,并与各企业食品安全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现出较高的政府治理效率。而我国负有食品安全职能的政府部门多达9个,在模型中体现为,参与人数量越多,越希望别人履行政府职责,而自己能够躲避监管责任。虽然我国公共支出中行政成本一直很高,但最终体现出的政府治理效率不是很理想。
3.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影响因素之三:博弈策略的选择
由于所有参与人都不行动的概率为ε*N,自然,有参与人行动的概率为1-ε*N,由式(4)得:

(7)式显然是个减函数,随着参与人N的增加而减少,例如,当N=2时,有参与人行动的概率是0.96(1-0.22/(2-1)=1-0.04),而当参与人N=30时,有参与人行动的概率约为0.81(1-0.230/(30-1)=1-0.189)。博弈结果表明,在自然博弈状态下,参与人N越多,不当行为被查处的概率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
推论3:参与人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过程中,通过混合策略虽然可实现纳什均衡,但均衡的结果并不好。
这个推论意味着,在自然状态下,每个政府部门采取效用最大化策略,本身虽无可厚非,但最终达到的治理效果并不会理想。在模型中直观地体现为:混合策略下的纳什均衡点效用(表1中数字部分的右下角)劣于纯策略下的纳什均衡点效用(表1中数字部分的右上角和左下角)。只有采取积极的政策干预,才能推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点向纯策略纳什均衡点方向移动,最终达到“聚点”(Focal Point)——纯策略纳什均衡点,从而实现政府治理效用最大化的合意结果。
三、模型解释:效率损失的制度诱因
以上模型分析表明,政府治理效率的损失存在三个诱发条件:“搭便车”初始心理预期的涨落、参与人数的增减和博弈策略的选择,这是宏观层面的表现。在微观机理上,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在我国政府治理效率低下的一些领域,已有的制度设计与上述三个诱发条件是什么关系?我们在原初的制度设计上是否存在着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制度诱因?
(一)委托代理关系扭曲
在行政过程中,政府需要将所治理的各种事项委托给不同的执法主体。为此,作为典型的制度安排之一,政府与不同类型的执法主体之间就构成了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我国政府治理领域,各种委托代理关系广泛存在,覆盖了政府治理的各条主线和各个层面。
我国现阶段政府治理领域的委托代理关系,早已突破单一事项简单委托的初级层面,主要有以下多种形态。1.多主体委托代理。对同一行政管理事务可能通过多种法律形式进行授权。2.多层委托代理。处于中间链条位置的组织和官员,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3.不完备委托代理。各层级之间的授权往往是“粗线条”的,很难穷尽所有的可能性。4.弱监督委托代理。行政法规和国务院部委规章的制定,并不需要报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而国务院部委规章仅需向国务院备案。5.名义委托代理。全体公民是一个政治概念,仅是名义上的委托人,实际上很难真正行使委托人的权力。
从制度安排的角度进行观察,上述5种委托代理关系,有的是通过人大授权完成的,有的是通过专门的法律法规配置完成的,而有的是通过政府之间的层级命令完成的,等等。在一些重要治理领域,尤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都会成为各种委托代理关系关注的焦点。由此引发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各种委托代理关系重叠区域,如果初始条件界定不清,则很容易造成委托代理主体的交叉、委托代理边界的重复、委托代理事项的重置和委托代理规则的冲突。进而可以理解为,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情况下,委托代理关系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扭曲。这种扭曲最终会损害到委托人的利益,并具体表现为政府治理效率上的损失。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会发现,针对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某些管理主体有时显露出“熟视无睹”的姿态。究其根本,恰恰是在于缺少对各类委托代理关系初始条件方面的有效界定和相关制度安排,以致造成程度不一的主体不明确、事项不完备、规则不严密、边界不清晰等委托代理关系扭曲现象。所以,在政府治理重叠领域,有管辖权的执法机构,受一些扰动的影响,加之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等倾向,他们宁愿多看少动,“不越雷池一步”,期待其他主体“挺身而出”。尤其在对待一些社会“敏感”问题上,这种“搭便车”初始心理预期会进一步加重。按照推论1得出的具体结论,最终一定会传导为政府治理效率上的损失。
(二)纵向事权配置方式
在明确了基本的委托代理关系前提下,为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能,需要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对政府部门进行相应的事权配置。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政府部门的事权配置主要是围绕以下几条主线构建:1.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2.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3.国务院各部委等机构制定的部委规章;4.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5.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这些法律法规相互之间存在效力上的差别,基本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其中前三项,基本法律、行政法规、部委规章是在全国范围内按统一的模式进行配置,而后两项主要是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某些事项做一些必要的补充和细化,仅在本地的行政区域内有效,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以外,均不得与前三项相抵触。因此,我国政府部门的事权配置主要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纵向事权配置模式。
纵向事权配置模式虽然有利于政令畅通,但无可否认,这种模式却隐藏一个问题,即带来了政府事权主体过多问题。以前面谈到的食品安全领域为例,在《食品安全法》中,分别划分出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卫生防疫、出入境检验检疫、农业、畜牧、公安和专门委员会等9个事权主体,都可按纵向业务分工对食品安全进行相应的治理。显然,这种方式属于典型的纵向事权配置。
将一项业务委托给多个事权主体,本意是强化食品安全管理,强调政府部门“齐抓共管”。应该说,表面上的事权配置十分明确,通常情况下,也不会出现问题。但在实际运行中,围绕9大主线产生许多业务交叉和业务缝隙。在“三鹿奶粉”、“瘦肉精”、“毒胶囊”等事件中,涉及的“奶站”、“瘦肉精”、“明胶”的分属领域如何确定,由谁来管,上述这些事权主体,既有可能都涉及,也有可能都不涉及。在业务交叉和业务缝隙地带,按照推论2得出的具体结论,9大事权主体在效用最大化的驱动下,将导致严重的“搭便车”效应,反而降低了政府治理效率。可见,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已经成为政府治理的一个顽症,与纵向事权配置方式造成多事权主体管理交叉有着直接的关联,存在着制度上的诱因。
(三)博弈策略选择不当
委托代理关系扭曲和纵向事权配置模式下,存在着博弈策略选择问题。我们知道,委托代理关系确立了我国政府治理结构的科层制属性,纵向事权配置方式使事权主体表现为一一对应的纵向同构关系。科层制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通过行政规章等纵向事权配置方式对科层制进行强化,原有的委托代理主体与事权主体将“合二为一”,对事权主体的博弈策略选择将产生重要影响。
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如果想优化委托代理结构,需要突破已有的制度性壁垒,无疑会加大行政体制改革的成本负担。事实上,一些地区曾经做过一些尝试,精简、合并了一些政府部门,力度也很大,但结果是大部分都走了“回头路”,基本上又回到原有模式,究其根源,恰恰在于无法逾越这种“规章效应”①所带来的制度性壁垒。如推论1所述,“搭便车”的初始心理预期对“搭便车”效应起到助涨助跌的作用,如果克服制度性壁垒会使支付大幅减少,则地方政府理性的策略都会选择“观望”;另一方面,如果选择处于“等待”状态的地方政府个数越多,则按照推论2的结论,数量越多,越期待别人进行委托代理关系的结构优化,选择“搭便车”的策略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而事实上,各地方政府对行政体制改革持有浓重的观望策略,正是推论1和推论2揭示的微观机理共同作用的结果。按照推论3得出的具体结论,最终形成的均衡状态并不理想。
四、解决策略:效率损失的补偿
有人认为,为了提高治理绩效,应该向管理要效率。问题是管理并不创造效率,管理所能解决的问题是,把价值预期与价值兑现之间的那部分“应收”拿回来,拿回“应收”就是“挣值”(Earned Value),属于补偿性收益。最大限度地把“应收”部分拿回来,正是解决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的关键所在。在策略上必须克服原有的路径依赖,坚持通过制度创新来提高效率补偿水平。
(一)调适委托代理关系,降低“搭便车”初始心理预期
在前面的论证中,我们发现,政府治理中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扭曲问题,是政府治理效率损失一个重要的制度诱因,它会提高参与人“搭便车”初始心理预期,会对政府治理带来不利的后果。为此,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可以从调适委托代理关系上入手,从源头上消除推论1中的微观基础。
可以考虑加大地方人大的立法权,通过有针对性的地方性立法,逐步完善委托代理关系,填补委托人缺位,明确“谁可以成为委托人,谁可以成为代理人”[12]。这种做法的实质是明确地方人大的委托人地位,突破原有科层制结构中,委托人缺位的结构性障碍。当前,尤其需要建立委托人缺位的替代机制,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可考虑施行扩大人大代表的常任制范围,而不局限于仅靠定期年度代表大会履行委托人的事后监督,需要增加事中监督和事前监督。
明确了地方人大的委托人地位,实际上也就明确了委托代理主体、完善了委托代理事项、严密了委托代理规则、清晰了委托代理边界,最终的落脚点是降低地方政府“搭便车”的初始心理预期。事实上,调适委托代理关系将会与扩大地方事权联系到一起。重构委托代理结构,就需要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进行合理划分,适度分权给地方,鼓励和支持地方政府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确保行政体制改革不因体制和制度障碍而走“回头路”。据观察,发展较快或者说是政府治理绩效较高的地区,一般都与扩大地方事权有关。
(二)优化事权配置,降低参与人数量
政府治理效率损失另一项重要的制度诱因,在于政府的事权配置方式存在着问题,它会造成政府治理参与主体数量过多,并会对政府治理效率造成严重影响。为此,提高政府治理效率,还需要从优化事权配置方式入手。
优化事权配置虽不能彻底推翻原有的纵向事权配置模式,但可以在立足原有纵向事权配置模式基础上,适度降低事权主体的参与数量。以此避免事权主体在职能定位和管理领域上出现交叉和重叠,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推论2中的微观基础,从而减少因“搭便车”效应所造成的效率损失。
可选择的策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避免事权的人为过度分割。事实上,在我们所列举的食品安全事例中,将食品安全划分为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既不科学,也不规范。二是要合并事权责任主体。尤其是在某些政府治理问题出现争议时,要迅速通过合并事权责任主体的方式,变多个事权主体为一个事权主体,可以很好地避免“搭便车”效应的发生,同样有助于政府治理绩效的提高。
(三)设定责任分割机制,改变混合博弈策略
从推论3和对政府治理博弈策略选择不当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政府治理需要设计一种责任分割机制,使得某一纯策略均衡能够成为“聚点”(Focal Point)。无论是1个还是30个,由于参与人的期望支付都是8,设定有且仅有一个人的举报机制,在这种纯策略均衡下,平均支付由1个人时的8上升为30人时的大约9.9[=(1×8+29×10)/30]。如何界定“聚点”,已经被很多学者关注,比如Finkelstein指出,可以考虑引进新的激励,改变市民的效用支付,如先举报者奖励[13];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也曾提出依靠“第三条道路”(Third Invisible Hand)[8][14]进 行 应 对;Achilles等人提出,应设定利益相关者的初始责任[15]。
应该说,我们所讨论的改变政府治理中存在的混合博弈策略问题,与J.Hudson和P.Jones的讨论接近,关注的都是“搭便车”效应可能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16]。在解题思路上,A.Mani和S.Mukand提出了运用“搭便车”提高治理绩效,即,一旦“公共产品”产生,社会成员“搭便车”消费这种产品,符合“公共产品”的本性,对于社会而言,则是有效的[17]。在“美国政府诉美国烟草行业案”中,美国各烟草公司最终与50个州政府达成《和解协议》,自1998年起,未来25年内赔偿高达2千多亿美元,以基金的形式作为对患病的吸烟者及与之相关的利益群体的补偿。这个案例表明,通过设立责任分割机制,可以推动某一纯策略均衡成为博弈的“聚点”。而反观国内,在政府治理能力需要提升的情况下,还没有发现通过改变原有混合博弈策略来提高政府绩效的事例,更少见通过设定责任分割机制弥补政府治理的效用缺失。
事实上,以上讨论的几点解决策略是相关联的,其中,前两项解决策略属于重置“挣值”过程,旨在通过制度创新挽回政府治理效率损失;第三项设定有效责任分割机制的解决策略,不但能改变政府治理主体的混合博弈策略,还能策略性地利用“搭便车”;这些策略都指向一个目标: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走向善治。尽管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但我们欣喜地发现,在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业已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扩大特别行政区范围,推行大部制改革,推行强县模式,表明我们的政府正在通过优化事权配置、调适委托代理关系和调整博弈策略,为实现一个可预期的目标而努力。
注释:
①周雪光的研究认为,国务院部委规章是这种现象的一个制度诱因,称之为部门利益法律化。参见周雪光:《基层政府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1] 俞可平.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能力[J].公共管理学报,2005,(1).
[2] M.R.Montgomery,R.Bean.Market Failure,Government Failure and the Private Supply of Public Goods:The Case of Climate-Controlled Walkway Networks[J].Public Choice,1999,99(3-4).
[3] R.Wendner,L.H.Goulder.Status Effects,Public Goods Provision and the Excess Burden[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8,(92).
[4] 王贤彬,聂海峰.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10,(4).
[5] 傅勇.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公共性物品供给[J].经济研究,2010,(8).
[6] Kosfeld,M.,A.Okada and A.Riedl.Institution Formation in Public Goods Gam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9,(99).
[7] 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权补贴有效性[J].经济研究,2010,(3).
[8] 吕鸿江,刘洪.转型背景下组织复杂性与组织效能关系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10,(7).
[9] 卫武,李克克.基于政府角色转换的企业政治资源、策略与绩效之间的相互影响[J].管理科学学报,2009,(2).
[10] M.J.Bailey.Lindahl Mechanisms and Free Riders[J].Public Choice,1994,(12).
[11] Grossman,Sanford and Oliver Hart.Takeover Bids,the Free-rider Problem,and the Theory of the Corporation[J].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83,(1).
[12] Holmstrom Bengt,Paul Milgrom.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Analyses:Incentive Contracts,Asset Ownership and Job Design[J].The Journal of Law,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1991,(7).(Special Issue).
[13] Finkelstein.Power in Top Management Teams:Dimensions,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2,(3).
[14]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余逊达,陈旭东.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
[15] Achilles A.Armenakis,Stanley G.Harris.Reflections:our Journey in Organizational Change Research and Practice[J].Journal of Change Management.2009,(2).
[16] J.Hudson,P.Jones.Public Goods:An Exercise in Calibration[J].Public Choice,2005,(3-4).
[17] A.Mani,S.Mukand.Democracy,Visibility and Public Good Provision[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