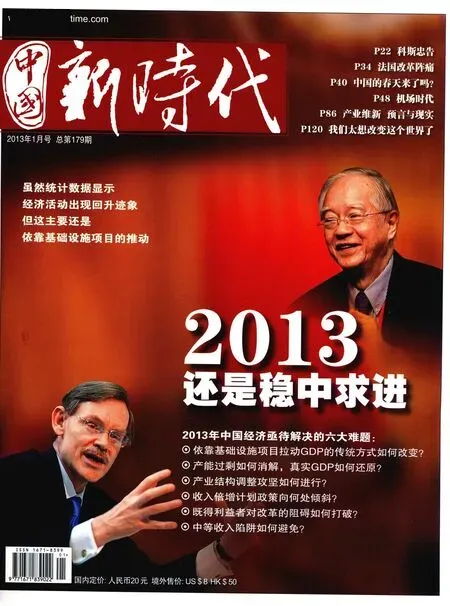看《旧制度与大革命》札记
崔人元
据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说,“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般认为中国已经从革命时代进入建设时代,王岐山同志却多次在不同场合推荐这本书,有何深意?这书有啥看头?
托克维尔在完成《论美国的民主》之后,十五年间没有重要著作问世,直到1856年才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开头就指出,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各章节的标题,也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作者想探讨哪些问题,例如,为什么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为什么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为什么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为什么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为什么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却加速了革命?
托克维尔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等史料,凭着对原始材料扎扎实实地深入研究,得出了至今令人惊叹的结论,而且其论述深刻到触目惊心,甚至会让你怀疑这书:这些情景如此切近,真是150多年前的法国人在论述20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吗?若说是我天朝上邦之人所写,可谁敢有这样的洞见?掩卷长太息!谓予不信,请允许我在此寻章摘句(借用1980年代的一句流行语:理解万岁!),虽然我早已过了崇拜格言警句的年纪,认识到再精辟的格言警句都有其上下文或特定的语境条件,不能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否则可能后果很严重。
如彼世道人心

托克维尔像
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为了让人们不再注意权力的腐败和个人的境遇,政府总是鼓励人们以追求财富为中心,金钱成为新的信仰。专制和拜金主义的社会使人们走向孤独。个人在受到不平等对待时只能默默忍受,不会有人理会他的遭遇,更不会有人因为正义和他站在一起。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他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专制制度下,所谓公权力(国家、政府)越来越强大,表面看这种权力什么都hold住,而其实不然。托克维尔也给出了对治上述世道人心的纠错之方——自由,一如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自由的推崇。他说:
“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看看别人,反观自身,我们应当高呼万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条文中,中国公民可享有的自由,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宪法规定的都要多;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赫然写着“自由”二字。
而在落实自由中,大众要注意了——托克维尔指出:
“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为自由而生的民族,它们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恶果本身。”
“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对自由的热爱是由于人们只见到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因为这种看法常常使人模糊。的的确确,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总会带来富裕、福利,而且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
“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另一些民族在繁荣昌盛中对自由感到厌倦,他们任凭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自由,惟恐稍一反抗,就会损害自由赐予他们的那些福利。这些人要保持自由还缺少什么呢?什么?就是对自由的爱好。不要叫我去分析这种崇高的志趣,必须亲身体味。它自动进入上帝准备好接受这种爱好的伟大心灵中,它填满这些心灵,使它们燃烧发光。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爱好的平庸的灵魂,就不必试图让他们理解了。”
这不由让人想起了裴多斐的诗句:“自由价更高。”
彼邦的大革命
与一般课本中革命是因为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叙述不同,托克维尔在史实中发现:“(法国)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路易十六一生都在搞改革(他为了维稳,甚至对断头台进行了技术改革以提高其效率,可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他统治的时期是经济增长最迅速的时代,“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工商业在发展,农民负担在减轻,“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人人都在发财的路上狂奔,法国政府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但人民却把仇恨情绪集中在专制的中央政权和国王身上。任何哪个阶级都无法和另一个阶级和解。

《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个“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再细看一下导致大革命的彼时彼刻的情势:
一是前面说过的,广大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话语权都被代表了,人们相互孤立,社会陷入极端自私状态,最后成为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成为“暴民”。“法国是很久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列,开辟和扩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二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大革命前在经济上处境有好转,“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农村陷入荒芜状态。将他们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也就把他们推向了闹革命的可能。
三是作为社会稳定期的中间阶层难以生存。大革命前,贵族乡绅(中产阶级)作为连接上层统治者与下层被统治者的中间势力,被专制政权迫使退出了政治舞台,能够制约中央集权的力量也随之消失。“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所以人们应当预见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人们能够预测,不是坏法律分别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取代法国的古老政体。……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想,从这个时刻起,这场彻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对我来说,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想起清末梁启超的感慨:“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甚至,法国大革命的暴力,也是专制政府教的。托克维尔说:“我掌握事实,所以敢说……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是革命者陷入“民主专制”:“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贵族公务员;只有一个唯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人民”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拥有名义上的一切权利,而单个的具体的人民却仍然没有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大革命最后是拿破仑的个人专制独裁,个体的人民就此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
同一本书 不同看法
鲁迅先生曾指出,对同一部《金瓶梅》,“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对同一部《旧制度与大革命》,亦有不同的看法,此举两种——
其一,前接报道中说:《旧制度与大革命》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如此报道的表述,联系其上下文,其意思应当不是反省已经发生的影响中国的某场大革命,似乎是用心良苦地警告大家注意避免法国大革命的盲动:然因此报道截取片面观点,让读者自然地理解为,这似是主张:还是维持观状的稳定好,不要折腾出乱子来啊。
其二,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不吸取,《旧制度与大革命》启发我们,面对改革攻坚,一定要有更大的智慧、理性、决定和勇气去沿着正路、朝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地渐渐推进改革,建立符合人类公道、普世价值、真正遵守宪法的社会,否则,万一再革命事起,玉石俱焚,就有负国家、人民和历史所托。——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少,其中一部分的意思是,同志们要稍加抑制贪暴,不能杀鸡取卵、涸泽而渔,要“可持续发展”,以稳坐江山长保富贵;其中另一部分是草民或良心未泯的几个非草民的真诚希望,但草民人微言轻,不在其位而不掌握相应的资源,虽心焦如火,又能怎么办?
再读一下托克维尔的论述吧:“绝不能轻信法国人在他们最大的痛苦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轻松愉快(你幸福吗?);轻松愉快只不过说明法国人相信他们的恶运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自寻开心,不去想它,而绝不是完全忘怀。给这些人打开一条出路吧,让他们摆脱他们似乎不介意的苦难,他们立即会朝那个方面飞快地跑去,势头暴烈,要是你挡住他们的道,他们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就从你的身上踏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