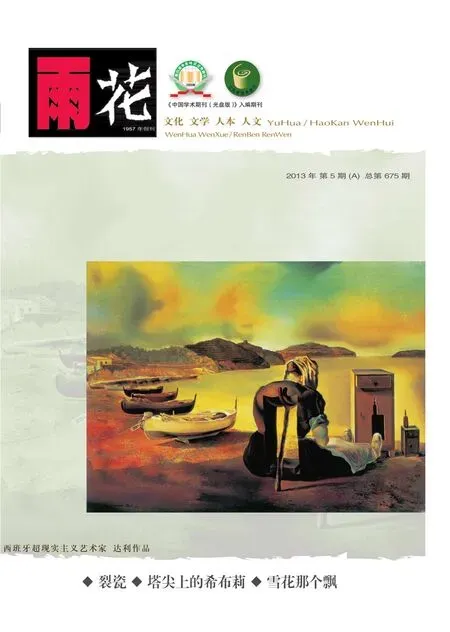做针线活的女人
● 赵文辉
秋旮旯,是庄稼人的一段闲时光。稻子锄过二遍,细草也拨弄干净了,男人们收了锄就闲得一点事都没了。庄稼人天生就是出力流汗的命儿,稻子玉蜀不用侍弄了他们便侍弄起自己的女人,在床榻间吭吭哧哧奋力飞锄。女人们被侍弄得脸色红润,肢体饱满,一个个目光湿漉漉的,连走路的姿式都有些娇弱不堪了。她们见了面相互感慨:男人呵,这些贪嘴的男人呵。说话的时候,她们目光中潮润多情的汁液四处飞溅。
之后,女人们就要开始忙活她们女人的事了。她们要趁这一段闲时光,拆洗一家人的被子和棉袄棉裤,该缝的缝该补的补,小孩腿长了棉裤就加一截,实在不能穿了不能用了就做一套新的。做活儿时多是几家结合,谁家屋里宽敞就到谁家,地上铺几张凉席,在上面飞针走线润色光阴,提前置下全家人一冬的暄和。女人们刮天扯地的笑声在院落之间穿梭飞扬,她们一边飞针走线一边把男人们的本事搬来消遣,常常逗笑得直不起腰来。女人们刮天扯地着,心里却在抻着劲。一个个漫不经心的样子,手里的银针却半点马虎都不敢。九月的日子里,女人们比的不是家里的粮圈有多高,牛羊有多肥,脖子上的项链有多重,长得肉多肉少腰粗腰细讨男人喜欢不喜欢。她们比的是针上的功夫,掩边掩得齐不齐,针脚走得匀不匀,棉衣棉被缝出来平展不平展,穿在身上合身不合身。村里偏偏就有生得花骨朵一样的女人,一见针就头晕,手伸出来比脚还笨。在九月的日子里,这些花骨朵一样的女人不得不收敛起她们平日的娇气和傲慢,向针线功夫好的女人投去敬佩的目光,甚至极力讨好她们,为她们买一些瓜果啦熬一碗绿豆汤啦,把一份平时见不到的殷勤献了出来。她们害怕自己做的活计拿出来,全村女人会把嘴搬到脖子上;她们害怕自己的男人听了那句著名的讽刺,“真是青花红涩柿——容看不容吃”,便认为她们是笨婆娘而冷落她们。谁摊上这么个评价,不管你生得几多姿色,在全村人眼里都要大大掉价,自己的家人脸上也跟着没光彩。
秋旮旯,有多少女人在担心和不安中消磨时光呵。
今年三婶家的活计迟迟没有动势,春花不提,三婶也没催。春花是去年冬天过的门,之前在县里的纱厂做挡车工,一结婚三婶就不让她上班了。一是挡车工吸入肺里的花絮太多,真落个肺病什么的可要后悔一辈子啦;二是年轻人在外面太不注意收敛自己,真跑疯了那可比肺病还要叫人后悔,这个原因三婶嘴上自然没说。既然是新媳妇,进了门处处都要表现表现,春花抢着刷碗,给婆婆盛饭,上地里跟男人干一样的活,尤其是一句一个“妈”,比亲闺女喊得还热乎。三婶只是奇怪,人家的活计都开始了,有手快的甚至已经收尾了,又懂事又能干的春花对此却只字不提。三婶嘴上不说啥,心里却有些急。
这天吃早饭的时候,三婶见儿子小明两只眼圈发黑,一个劲打哈欠,便有些心疼儿子。小明放下碗,说要去床上眯一会儿。只剩下了三婶和春花,见春花要去刷碗,三婶喊住了她:“春花,小明眯一会儿,醒来你带他去山上扯些山韭菜,给他摊韭菜馍吃。”
男人走得早,拉扯这个家不容易,作为一家之主,三婶说话从来都是命令式的。但三婶的严厉之中又不乏温情,从春花一进门,她就把春花当亲闺女待了。
“嗯。”春花很愉快地答应三婶,收拾起碗筷往灶房去。三婶叫她等等,又吩咐她:“随便采些野枸杞,泡一坛酒叫小明喝了。”
“泡酒?妈,小明不大喝酒的,你也知道。”春花一脸不解,又把碗筷放到了饭桌上。
“照我说的去做。”三婶不容春花多问,“我还能害恁俩?”
春花伸了一下舌头,大声应道:“听妈的,我一会儿就去扯山韭菜,采野枸杞!”三婶又叫住了她,春花有些纳闷,妈今天怎么了,没完没了的,不像平日的爽快脾气呵。
三婶说:“别让小明累着了。”
春花一怔,却不解:“地里活干完了,家里也没活,这几天俺俩就去拉过一车麦秸,麦秸轻得跟棉花一样,小明没累着呵。”
三婶又说:“别让小明撑着了。”
春花有些迷茫:“没让他吃啥呀?”
三婶嗨一声,一拍大腿,把话攮透了:“你瞧他的眼圈,黑成啥样了?你俩几天一回?”
这下春花明白了,脸一下红成了山里的野柿子。婆婆怎么问这个呀?她指头绞着指头,脸越发红了。春花不说话。三婶很不满,又问她:“几回?”
“一天两回。”春花低着头小声回答,声音跟蚊子哼哼似的。
“呵?”三婶大吃一惊,怪不得小明吃过早饭还要去眯一会儿呢。她很着急,声音就粗重了一些:“春花你给我记住,把男人累坏了撑坏了都不行,你该忍忍就忍忍,往后三天一回,最多两天一回。”
春花勾着头,声音低得只有自己能听见,“叫我忍忍?是他天天要的!”
三婶冲春花摆了摆手,叹了一口气,眼里满是担忧。
九月的山峦,丰满得让人眼热,成熟得让人心醉,就像城里的超市一样,一进去,商品琳琅满目沉甸得让你迈不动步了。刚摘下一捧野葡萄,一转身又有一簇山枣在树丛中向你微笑。春花卷起自己的汗衫放山枣,白白的一截肚皮露了出来,九月的阳光透过枝桠打在上面,支离破碎中雪白一片,小明心里不由一热。他们从树丛中返回那条窄窄的山路,有一只篮子在等待收藏他们的战利品。春花蹲下来,哗一下把山枣倒了进去,肚上的一片雪白眨眼间没了。小明从两只鼓囊囊的裤袋里一把一把往外掏枸杞、野柿子,他的裤袋好像两只聚宝盆,总也掏不完。
篮子几乎满了,春花说还没扯山韭菜呢,妈让给你摊韭菜馍吃,哼,还不胜吃点肉哩。小明从小与妈相依为命,春花对妈的微词使他很不满,说:“你懂个啥?山韭菜是壮阳的,枸杞泡酒是补肾的,妈是嫌我太亏了。”
春花撅起小嘴,扯了一片枣树叶放在嘴里噗噗地吹,“哼,就她知道疼你,我这个做媳妇的就不心疼你呵。”
小明不理她,径直往一处坡上走去,坡后生长着一丛一丛碧绿碧绿的山韭菜。空旷旷的山静极了,春花有点害怕了,赶紧撵了过去,“等等我!”
小明走得很快,几片树叶闪动之后,竟没了影儿。春花更害怕了,“等等我……”嗓子里已带了哭音。
“让山怪把你掳走当押寨夫人吧!”小明的声音在树梢之间回荡,却不见人。这时真的有一声山鸟凄惨地叫,很瘆人,春花蹲在地上,哇一声哭了。
几片树叶急速地抖动着,小明从树丛中闪了出来。他一把抱起春花,像抱一个小孩一样,把春花抱到了一块平展的石头上。给春花抹眼泪,又胳肢春花。春花终于破涕为笑,一把抱住了小明,俩人的嘴唇紧紧挨在了一起。春花的手无意间碰住了小明的激动之处,身子不由一抖,说不敢呀不敢呀妈不让呀。不管不顾的小明像头牛一样喘着气,把春花平放在石头上,动手掀她的裙子。他才不管那么多呢,反正有枸杞和山韭菜替他顶着呢。
回到家,却见四婶趔着腰站在当院跟三婶唠嗑。四婶个不高,又生得圆胖,偏偏腿勤,一会儿村东一会儿村西,一会儿这家一会儿那家,像个石磙一样在村子里滚来滚去。四婶是个热心人,谁家有事找不找她都要去帮忙,乡下的各种礼数也晓得很多,但众人偏不太稀罕她。四婶坏就坏在自己一张嘴上了,好笑话个人,好评论张三眼小李四腿短。尤其是小喇叭的功能发挥得太张扬,你给她说个事,一转身就给你播放得全村人都知道了。用三婶的话说,嘴比屁眼还松,兜不住个事。四婶嗯哟哟迎上来,一把拽住春花的手:“俺这媳妇多勤快,上山采补品了?补,小明得补,补得小钢钻儿一样才好!”三婶从背后捅了她一指头,示意她作为长辈把话说过头了。四婶反应很快,马上转口夸起春花的身材好,啥衣裳穿身上都能挺起来,好看。她忽然发现春花的裙子上满是泥土,“咋,在山上跌了?”
三婶的眼里也是一片狐疑。这时小明气呼呼往屋里去了,还把当院一只小板凳踢飞了。四婶扭头问:“小俩口生气了?”
春花咕咕笑着趴三婶耳边悄悄说了几句,三婶顿时眉开眼笑:“好闺女,就该这样,可不能全顺着他。”三婶夸完媳妇就说开了正事,“你四婶来,想跟咱家合伙拆洗被子做棉衣裳,她的腰疼病犯了,妈的眼神也不太好使,今年可全指望你了。”
一脸喜气的春花顿时变得呆傻起来,好像点头了,又好像没有。
四婶接上了话,“要不早来找你了,这几天腰疼得下不来床,我腰上的肉都让火罐烧焦了,你瞧——”说着,转过身子搂起衣裳,只见腰部布满了火罐拔过之后留下的圆圈圈,一个压一个。见春花癔怔着,四婶又一把拉过春花的手端详着,瞧完就夸:“这手长得,十根指头又细又长,比仙女还巧,做针线活一定又快又好。这下好了,我不发愁了,春花你替婶多做点呵!”春花心里着急,正不知道如何回答呢,小明从窗户里探出脑袋,“四婶,她在纱厂评过技术能手,还得了一个奖品:太空被!”春花听了,只想进屋踹小明一脚。
四婶乐得几乎忘记了腰疼,“要不明儿个就开始?”
春花一激灵,还是点了点头。
第二天,刚放下碗四婶就来了,还端了一只针线筐,里面放的是女人的宝贝家什:剪刀、尺子、顶针、大中小三号针,各种颜色的线,还有一只瘸腿老花镜,用红头绳系着。四婶站在当院和三婶叽叽喳喳地,三婶手里端着一盆鸡食,好像是在说先拆你家的吧。春花在屋里隔着窗子看见了,身子不由一阵发凉。
“春花,春花!”四婶在院子里喊起来,“你妈让先拆俺家的!”
帘子叭哒一响,春花出来了,手里握着一团卫生纸急匆匆往厕所去。四婶的目光迎着春花,“咋了,咋了,莫不是身上来了?”
春花从厕所出来,向三婶四婶汇报,果真是身上来了,今天是第一天。四婶一屁股坐在凳子上,“那咱的活儿可得推推。”四婶是个老迷信,生怕春花身上的东西弄脏了她家的被子,可是要背时的。三婶接上话,“等几天吧怕个啥?又不是抢收麦子,怕雨淋怕炸在地里。”
不能做活,四婶也不走,握着脚脖开始跟三婶扯上了闲篇。四婶的主要话题是谈论村里年头过门的几个新媳妇,四婶就像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节目里毕福剑邀请的嘉宾一样,对这几个新媳妇一一评头论足,就差没有打分了。四婶说,老姬家的媳妇一天换一身衣裳,脸上的粉抹得铜钱一样厚,风一刮跟撒了面粉一样簌簌往下掉;宋二鹏家的那媳妇,说话吐字不清,腿还不直,没个女人样;南头文来家的那个,听说以前在城里给人洗脚……说着话,四婶还不时拍三婶一下,生怕三婶没注意听走神似的。三婶心里烦四婶,又不好意思撵她走,只好耐着性子听她说,尽量把四婶的话题引开。引了半天才发现自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四婶不管从哪个话题说起,绕来绕去,最后又绕到对人的评头论足上。三婶只好作罢,任由四婶唾沬星乱飞,胳膊划来划去,点评村事。
春花在屋里都听见了,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四婶这张嘴,厉害着呢!
小明从小卖铺买烟回来,告诉春花,村里人见了他都问:你媳妇在纱厂当过技术能手,手巧得能闭上眼认针,你和四婶两家的活她一个人包了?春花知道,这肯定都是四婶的小喇叭广播的效果。四婶呀四婶,你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呀!春花那个恼,恨不得跑院里把四婶掀个屁股墩才解气。这时小明又猴着脸上来,把手伸进她的衣裳里,春花杏眼一瞪,啪一下把小明的手打了下来。小明捂着手一蹦一跳的,嘴里咝咝哈着气:“你个小娼妇,下手真重,想谋害亲夫呀!”
一连几个晚上,小明都让春花掀了下来。小明软硬法用了个遍,春花就是不让,让他滚一边去。小明气得把扯来的山韭菜和野枸杞全倒进了猪圈,气咻咻地扬言要去少林寺当和尚。春花才不理他呢,说你去吧,明天就给你买火车票。
四婶呢,仍旧天天来,扭扭摆摆地,仿佛一个老农去田里查看墒情一样。一来就问:“还有几天?”要不就是,“结束了没有?”问得春花心里猫抓似的。最后一回,春花只好硬着头皮说,还得一天。四婶一下子喜笑颜开,说后天咱一准儿开始,也叫四婶见识见识你的针线功夫。
这几天,三婶亲自刷锅洗碗,说春花碰不得凉水,还关照小明要学会心疼自己的媳妇。春花也就顺水推舟,把自己弄出一副慵懒的样子,对小明指手划脚地,要小明一会儿干这一会儿干那,一刻也不得消停。仿佛这样,才能缓解内心的紧张。
秋旮旯,雨水比较勤,老天总是抽抽泣泣的。天一阴,地皮就泛潮发湿。三婶天天都把烧过的煤碴撒到屋地上扫来扫去,把地皮上的水分吸去,为铺席做活作准备。三婶检查了针线筐里的各式家什,又去小卖铺更换了两只顶针。就像一场村戏一样,舞台搭好了,幕布拉开了,锣鼓家什也敲起来,就等演员出场了。春花在一边看了,几乎手脚冰凉,两眼发花,不知道该怎样迎接那一天的到来。
也就是开工的头一天,春花正在屋里叹着气,忽听院门吱一声响,一个高门大嗓亮起来,“家里有人吗?”是大哥来了!春花一下子精神起来,好像溺水的人捞到了一截木筏。她迎上去问候大哥,原来大哥是去镇里修麦耧路过他们家,随便进来看看。
来了客人,还是这么重要的客人,三婶一家都停下手里的活儿,全力以赴接待春花的大哥。三婶去拍鸡蛋水,一会儿竟端上两盘菜:一个韭菜炒鸡蛋,一个凉拌木耳。小明去小卖铺拎了一捆啤酒,用牙咬开一瓶,咕嘟咕嘟往碗里倒,要和大舅哥喝几杯。春花的大哥被三婶一家的热情弄得很不好意思,说:“这算咋的,这算咋的,又不到饭时候?”
过了半个时辰,春花的大哥撑得实在喝不下了,就提出告辞要去镇上修麦耧。一家人送出门,三婶安插,“中午拐咱家吃饭,可给你准备了。没啥好的,就大米烩菜了。”
大哥扛上麦耧,春花多送出几步,低声对大哥说:“你回去让咱兄弟来一趟,对婆家人说咱家的棉衣活儿做不过来,要我回去帮忙。”大哥把麦耧换了一个肩膀,有点惊奇地问:“咱家的棉衣活儿娘和你嫂子都做完了,再说——”春花急得要掉下泪来,狠狠掐了一下大哥的手,让他无论如何按她说的办,要不她就得跳井上吊,娘家人等着来给她收尸吧。
这话说得重了,吓了大哥一大跳,他走出了多远,又回头望了一眼春花,很不放心地去了。
第二天,四婶端着她的针线筐,哼着《朝阳沟》:亲家母,你坐下,咱俩说说知心话……晃晃悠悠地他进门来。三婶吩咐春花扫地铺席子,说至少得三张席。平时利脚利手的春花今儿却慢慢腾腾,半天工夫才从床下抽出一张席子。等她去抽第二张席子的时候,娘家兄弟急匆匆来了。
春花的娘家兄弟把来意一说,四婶急得直跺脚,说这可咋办,这可咋办?三婶倒是很开通:“叫春花去吧,娘家叫咋能不去?先紧着娘家的活做,咱再搁几天。不打紧,不打紧。”春花满眼满脸关不住的笑,立即去拾掇东西。四婶屋里屋外跟着春花,一再关照春花:“你可早点回来,我们等着哩,要不非把你娘和我累垮不可。”
春花心里偷偷笑着,跟娘家兄弟去了。
过了七八天,春花才从娘家回来。三婶铺席子,四婶拿剪子,两家开始做活。先拆被子、晒棉絮,再缝。三张席子铺地上,被子里铺下边,絮棉方方正正往上一压,被子表再压住絮棉。三婶和四婶把一头,春花一人把另一头。只见春花左手戴着顶针,右手一根银针灵巧飞快地在棉被上蜿蜒蛇行。春花掩边掩得笔直,针脚走得又匀又密,还不时往破损的絮棉处添点弹好的新棉花。而且气匀神定,鼻尖上不见丁点儿汗星。在一旁半天认不上针的四婶早已汗流满面,一边骂自己老不中用手伸出来跟猪脚差不多一边夸春花手快手巧,还歪过头对三婶说:“我没看错人吧,一瞧春花的手就知道了,跟仙女一样。”拆洗完被子又拆棉袄棉裤,都做完了,春花对三婶说:“娘,我绐您做一件夹袄吧,您好犯咳嗽,天凉了加件夹袄。”春花连裁带缝,掖、掩、抻、拉,飞针走线,两天就做好了。四婶见了说,好好,也让给她做一件,春花笑笑算是答应了。
活计结束那天,四婶端着她的针线筐扭扭摆摆出了院门。目送四婶离去,春花心里长出一口气,多少天的紧张总算过去了。一回头,三婶却在身后怔怔地望着她。春花又陡然紧张起来。三婶上来一把拽住春花的手。春花往回缩,三婶拽住不放,只见春花的指头又红又肿,还有好几处被针扎过的疤点。三婶眼里霎时盈满了泪花,“春花,娘啥都知道了,你真是个要强的闺女呀!”春花不觉红了脸,心说,自己还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呢,咋就没瞒过婆婆呢。
做完了棉衣,稻子也该收割了。慵懒了一秋的男人们再次振作起来,磨刀石找了出来,马驹驴驹喂饱了,颈上的鬃毛幽幽发光。不知是马驹还是驴驹率先嘶叫了一声,闷了一秋的庄稼地哗一下热闹开来。一地的人,一地的镰刀,还有四处扑散的稻香,在手指和刀把之间缭绕。男人们女人们都俯下了身子,小心翼翼地收割这一地的稻香。
割稻可是春花的拿手好戏,在娘家就没服过输,一起割稻的人让她一个一个丢到了后面。特别是小明,累得呼哧呼哧地,春花割三垄他的一垄还不到头。春花笑他慢得像头驴,小明不服,说春花使的镰刀是今年新买的,他手里这把呢,有好几个年头了,上边还有一个豁口。三婶在一边笑,指责小明是不会浮水愣说肚脐眼碍事。四婶早把春花的针线活夸了出去,现在村里人又见识了她的割稻功夫,路过地头时都冲三婶道喜:“您真找了一个好媳妇!”三婶一边捆稻子,一边心里乐开了花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