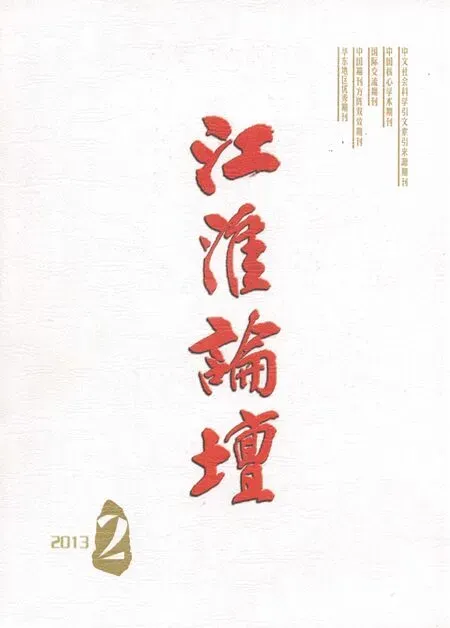论学与兴:被制度化学校教育遗忘的儒家传统*
彭正梅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62)
论学与兴:被制度化学校教育遗忘的儒家传统
彭正梅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62)
在儒家教育传统中,学包括学和习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学和习的无尽辩证。为了唤醒和支援学习者走向这种终身的不断超越的自我生成之道,儒家还设计了一种源于诗歌的兴发精神,一种审美性的唤醒,以作为学的援助,作为学的目的,即培养一颗同情性的心灵。把“教”置于中心的制度化学校教育,只有为学习者插上“学”与“兴”的双翼,把“教”、“学”和“兴”统一起来,才可能培育出我们孜孜以求的创新人才。
学;兴;教;创新人才的培养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制度化学校教育在我国获得了长足发展。学校已然成为了一个日益庞大和完备的社会机构体系,并被赋予这样一种根本使命:教育。国家为此雇用了数量庞大的教师,并为其投入数量更加庞大的财政性教育经费。这种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为我国社会发展提供大量合格的人力资源,但仍然给人这样一种遗憾:没有培养出一定数量的创新人才和少量富有创造性的大师。我们的学校教育似乎成了 “庸才的摇篮”,“灭杀”了在统计意义上存在于我们民族的潜在的杰出人才。人们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甚至各种“大师班”和“创新人才速成班”也被列于各种病急乱投医的良方之中。但在作者看来,其原因之一在于这种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过于强调自己的教育职能,从而忘记了我们所期许的人才从来就不是学校教育出来的,而是这些潜在的人才通过自己自动的艰苦的学习造就的,特别是在学校之外的社会生活中磨炼出来的。在这一点上,被制度化学校教育日益遗忘的“学”以及与之相连的“兴”的儒家传统,也许会给人一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发现,甚至震撼。
一、学的传统
学是儒家教育思考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相对于康德所说的“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儒家传统更加强调“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成为人”。
1.学即学与习的辩证
儒家传统中“学”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学与习。它不仅有我们今天意义上从不知到知、从不能到能的“学习”的意思,还有“践习”的意思,甚至“践习”的意思更多一点。也就是说,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学习主要是看他有没有良好的践习和习惯,是否“择善而固执之”。一个人如果“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那么“虽曰未学”,孔子也“必谓之学矣。”孔子之所以如此强调这种意义的“学”,是因为他所倡导的“仁”不仅是一个理论,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的事业即“爱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孔子的“习”理解为学习,而且,正是因为“(学)习”才使得原本拥有相近之“性”的人们拉开了距离,即所谓的“性相近,习相远”。
从这个意义上,儒家把学习的目的定义为“修己安人”,把“学而优则仕”视为学的另一端,即“习”。既然“仕”被认为是一种优良的“习”,那么,必然是学的一种指向;既然“性相近,习相远”,那么,“习”就不能是一种胡乱盲目的作为,而是要通过学来加以觉解和援助,所谓“学然后知不足,学然后知困”。因此,“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孔子的弟子赤也把“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等描述为“非曰能之,愿学焉”。因此,儒家不仅强调“学而优则仕”,同时也强调“仕者必如学”,不仅强调“学而时习之”,也强调“习而时学之”,也就是说,强调“学”与“习”的辩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学”被界定为一种经国之大略。《学记》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的政治学习的惯例中可以体会到其流风余韵,甚至堕落官员的口头禅也经常是“忽视了学习”。
其实,儒家把这种既“学”且“习”的辩证过程界定为广义上的学,进而把“学”称为“为己之学”,即自我的持续不断地生成和提升,而非为了迎合他人的需要,或为了外在的功利。荀子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小人之学是把学习视为“敲门砖”和“晋身之阶”,而放弃了学是为了自己的自我发展。《大学》把这种为己之学界定为一种止于至善的如琢如磨的自修和自新。按照《大学》的观点,这种为己之学并不是与他人无关,恰恰是在他者中得以真正的实现和落实,恰恰是一种成己(“明明德”)与成物(“亲民”)的持续过程。朱熹看到了为己之学中的“成己”与“成物”的关系,他借用程子之言指出:“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因此,儒家的为己之学不仅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还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这一点与西方的学习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希腊就把没有“习”的纯粹沉思视为“学”的最高境界。
2.人是学的存在
既然天命之性“先天地相近”,但学习使得人们“后天地相远”,那么,学习就是成人的关键。“学而时习之”之所以“不亦乐乎”,就是因为它是符合我们本性的事业。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孟子和荀子都相信,人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出身和血缘造成的,而是学习造成的;人生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潜质,但由于后天的学习,个体才出现差异;人的完善是向着每个勤学之人开放,圣可学而致。
孔子本人就是这种学习理想的践行者。他自从15岁“志于学”,每隔10年一个境界,以至于70岁时优入圣域,“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在解释自己与他人差异时指出,其他人“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在晚年还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
尽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但在他看来,人的德性并非自发产生,而是需要学习和求取,因为这些善端很容易丧失,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因此,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他警告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从禽兽中超拔出来,关键在于“存养”即学习。他强调通过自己的学习,人皆可以为尧舜, 可以跨越从 “善”、“信”、“美”、“大” 而进入“圣”和“神”的境界: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
荀子相信人性中存在着不良倾向,因此“化性起伪”的学习对一个君子来说更加必要,需要终身地“学而时习之”。对此,《荀子·大略》有一段悲剧性的描述:
子贡问于孔子曰:赐倦于学矣,愿息事君。孔子曰:《诗》云: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事君难,事君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事亲。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事亲难,事亲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妻子。孔子曰:《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难,妻子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于朋友。孔子曰:《诗》云: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朋友难,朋友焉可息哉!然则赐愿息耕。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耕难,耕焉可息哉!然则赐无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圹,皋如也,颠如也,鬲如
也,此则知所息矣。”
对于倦于学的子贡来说,学而时习之是其一种无所逃脱的宿命,只有那起起伏伏的坟,才是他停止学习的地方。在相信“涂之人可以为禹”的荀子看来,通往“禹”的道路显然更加艰难。这就是为什么《荀子·劝学篇》开头就指出“学不可以已”。
因此,在先秦儒家看来,人是学习的存在,他的存在与否,存在的广度和深度,都与学联系在一起,反映了一种对“人性进步的乐观主义”。《中庸》更是指出,如果能“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自强不息的精神,那么,“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朱熹解释说:“人性虽无不善,而气禀有不同者,故闻道有蚤莫,行道有难易,然能自强不息,则其至一也。”相比而言,西方是在文艺复兴之后,才出现这种人性的乐观主义。梅因也把西方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这种进展归纳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
3.学是对困厄的克服
尽管儒家对人性的可完美性持有乐观主义的信仰,但儒家也清醒地认识到,为学之道、成人之道并不平坦,而是充满坎坷,需要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因为学习是对困厄的不断克服。
这里的困厄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实际的困厄。在“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中,儒家更加强调困知,强调把贫贱忧戚视为玉汝于成和天将降大任的契机。第二,除了对现实的困厄的克服,儒家还十分强调对想象的困厄的预见和准备。这是一种忧患意识。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臣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但君子虽有终身之忧,却无一朝之患。第三,真正的困厄在于止于至善之学即中庸的不可能性。这主要体现在《中庸》之中的一个悖论:《中庸》一方面宣称“(中庸之)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另一方面又引用孔子的话指出:“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之道既“不可须臾离也”又“不可能也”的矛盾性,显示学习同样会面临这种矛盾:学之不可已与学之不可能。这种矛盾显示了儒家对成人之途的艰辛的预见和认识,并不是说是真正的不可能。从逻辑上来说,既然人皆有“明德”,那么“明明德”必然是可能的。《中庸》的意思是,学习的这种困厄就在于日常生活坚持中庸的艰辛以及难以避免的偏离。因为有些人即使“择乎中庸”,也“不能期月守也”。这也是孔子为什么对颜回赞赏有加:择乎中庸,得一善言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还历数了小人、民、智者与愚者、贤者与不肖者、索隐行怪者、遵道之君子对中庸的偏离:“小人是自暴之恶人,民则不知有中庸之庸众。智愚、贤不肖,乃欲学中庸而陷于气质之偏,不能尽力以择执者。索隐行怪,乃用力择执而偏者。遵道之君子,则所遵者正,而不能静存动察以致中和者。”这些人或因陷溺于风俗之中,或因气质之偏不能在日常生活中革新和发展自我。“中庸”的不可能性或艰难性,是儒家之学的真正困厄所在。
为了把人从学的困厄中解救出来,迈向“学”与“习”的无尽的辩证的征途,儒家的教育传统中还有另一翼即“兴”的传统。
二、“兴”的传统
在儒家传统中,学习对于成人来说是必要的,但又是艰苦的,这就会产生一种倦怠和退隐之心。如何从倦怠困厄中奋发挺立出来,勇猛地寻求自我,这就需要“兴”来不断地唤醒和鼓励。
1.何谓兴
“兴”,最初是《诗经》创作的一种修辞方法。在《诗经》中,赋是直接铺陈,而比兴则较为间接委婉。朱熹认为,“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虽阔而味长”,追求的是象外之象的大象,味外之味的至味。王夫之更是指出:“诗言志,歌咏言,非志即为诗,言即为歌也。或可以兴,或不可以兴,其枢机在此。”因此,《诗》的秘密“全在于兴”。兴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法,更是《诗经》的本体。这种本体又被称为“诗兴”。
在“诗兴”的称谓中,《诗》的“观群怨”的功能被弱化或隐去了,《诗》处于六艺之教之首,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朱熹解释说:“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兴”就是唤醒个体的一种生命感,使其不能自已,追求更加完善的自我。
《诗经》的经常吟咏,易于感发人的“志意”,这说明,诗兴不是一种理性的论证,而是一种感兴,但它可以引发理性的论证。《论语》曾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在这段对话中,由于诗的兴发作用,“绘事后素”被用来阐发仁内礼外、仁先礼后以及“人而不仁,如礼何”的道理。
《诗》的真正韵味就在于兴,读《诗》就是要获得《诗》之兴。对作者来说,是“托物起兴”,对阅读者来说,是“兴于诗”。鉴于《诗》的这种感发生命的作用,中国古代把它作为教育的基本方面,即所谓的诗教。
2.能兴是一种超越能力
诸葛亮指出,一个有志于学的君子若志不坚毅,意不慷慨,则会“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免不了要居于下流。但孔子却教诲说,君子耻居下流。那么,如何超越凡庸的状态呢?当然是靠学习,但在儒家看来,学习的发动和维持,则需要有一种源自《诗》的兴发能力,从而使志坚毅,使意慷慨。
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在王夫之看来,豪杰之为豪杰就在于他 “能兴”,而 “能兴”来自于《诗》。他解释道:“能兴者谓之豪杰。兴者,兴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益挫其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起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以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诗教是圣人拯救世道人心的一个重要设计。王夫之认为,若是没有诗教的荡涤和震发,个体就会中断“学”与“习”之间无尽辩证的成人之道,沉沦于庸众之中,斤斤计较,琐碎狭隘,消极迟钝,充满暮气。这种“为人之学”,“终至于丧己”。只有诗兴这种非功利的审美体验,犹如一种升腾,打破个体狭隘的自我格局,唤醒和激活去实现我们的“天命之性”,走向学与习的辩证之道。可以说,诗兴就是一种超越能力。
因此,诗教的目的并不仅仅教人成为一个诗人,而主要是培养人的这种感兴和超越能力。有了这种感兴和超越能力,李白就会写出“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的句子;金主完颜氏就会钦慕江南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而起“投鞭渡江之志”;毛泽东则“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会在不断地挫折之后不断地“而今迈步从头越”。
正是诗兴唤醒了沉沦中的个体的超越能力,使他更敏感,更易感,也更易产生理解和移情,从而有助于把他从风俗和怠惰的水泥中解放出来,迈上自我提升的学习之道。有了这种超越能力,个体就会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和自我,把平面的自我和世界重新转变三维的生命体,使之呈现出深度与实质、意义与复杂性、价值与美,而这些是不能依靠距离化的理性分析,而只能依靠理解和同情。因此,诗教所滋养的移情与理解,为个体认识自我和他者提供了丰富的强有力的可能和体验,使之感受到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感受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个体在这种非理性的直观中,还会产生一种天人合一、与道契合的神秘体现,感受到一种刚健不已、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和宇宙精神,感受到随处充满,无少欠阙,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豪迈气象,从而消除物我、人我以及自我内在的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的紧张关系。因此,“天地之际,新故之迹,荣落之观,流止之几,欣厌之色,形于吾身以外者化也,生于吾身以内者心也。相值而相取,一俯一仰之际,几与为通,而勃然兴矣。”如果没有诗兴的感染和唤醒,个体难以从根本上理解他人的痛,难以产生浑然与物同体、廓然而大公的仁心。而恰恰是“这点灵明”才是个体为学之路的动力源泉,从而更加自发和真实地寻求自己,发展更高级的灵性,打开自己的全心智。
3.诗兴是中国人的宗教
这种诗兴精神所激发的主客不分、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被认为是中国人的独特的宗教,无神论者的宗教,或审美的宗教。这在林语堂和蔡元培那里认识得比较明显。
林语堂指出,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通过谚语的诗卷深切地渗入社会,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了人们心灵的创痛,诗歌通过享受简朴生活的教育,为中国文明保持了圣洁的理想。它时而诉诸于浪漫主义,使人们超然于这个辛勤劳作和单调无聊的世界之上,获得一种感情的升华,时而又诉诸于人们悲伤、屈从、克制等感情,通过悲愁的艺术反照来净化人们的心灵。”正是诗歌所引起的兴发力量给予了困厄中的人和民族以抚慰和安顿,给予他们自强不息的生的决心。林语堂指出,假如没有诗歌,中国人就无法幸存至今。
针对辛亥革命后的人心沦丧和信仰危机,蔡元培提出了很独特的“美育代宗教”的命题。他认为,宗教是科学不发达的产物,随着科学的发达,宗教的各种原有价值便逐渐消失,另一方面,宗教侵犯人的信仰自由,侵犯人权,而审美则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是相对于理论之必然和实践之必然的主观的必然性,体现了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因此是宗教的恰当的替代物:“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 ”
对于当时急功近利的启蒙运动,蔡元培认为有可能会产生以下三种流弊:第一,个人私利的羁绊,启蒙者自己不能落实启蒙理想。第二,用启蒙理想作护身符,行卑劣,自由,变成了嫖妓的自由,从而给自由本身带来消极影响。第三,启蒙者急于实现自己的主张,经受不住挫折,容易失望,甚至自杀。只有审美,才可以提供一种宗教般的超功利的真正的韧劲和内在的精神。
蔡元培指出,现代化过程被理解为人们只往“科学路上跑”,追求最大可能的功利,“似乎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只为了吃面包”,从而导致了所有深刻情感的衰颓和人类之间的隔膜,甚至是互相残杀。对此,蔡元培认为,必须通过审美教育来加以救治。美育的目的 “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了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存在必然会唤醒人产生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不仅仅是要使人人有饭吃,有衣裳穿,有房子住,他同时还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以外,还能去享受人生。知道了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便知道了人生的可爱,人与人的感情便不期然而然地更加浓厚起来”。也就是说,审美具有宗教的作用,但却无宗教的偏狭和迷信。
值得注意的是,“兴”义的来源被认为与原始祭祀活动有关,是一种原始人集歌、乐、舞于一体的宗教或庆典的抒发活动,是天、人、神相互契合的时刻。因此,诗兴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也是其原始的宗教意义的复归。
三、迈向教、学和兴的统一
《论语》开篇的“学而时习之”宣示了儒家对于学习的重视,模仿《论语》结构的《荀子》也在第一章进行“劝学”,儒家的经典之一的《大学》没有被称为《大教》,儒家的教育经典的《学记》而非《教记》,这些都从形式上说明了儒家更强调自我修炼的“学”而非来自他者的“教”。“学”这个汉字也产生于“教”之,或,它们同时产生(因为“学”字有可能是“教”字的假借)。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学也是先于教,因为没有教的情况,学也是可能的。
近代以来,儒家教育传统中学及其所要求的兴的思想连同其所附丽的传统一起在制度化的教育中衰弱了,甚至被遗忘了。教育、教师和教学成为了制度化学校教育的中心。先于教而存在的学与兴的两翼,被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剪除了。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教的越多,学的越少;教的越努力,学的越无聊。针对这一点的历次的学校改革,也总是不断地强调“教学”和“教师”。
但是,学生的学,源自其对世界的经验和反思,这是教所无法替代的。教永远不能直接决定学生的学,而只能引发和帮助学生对世界的经验和反思。学习者所学的东西是那些最初被经验为不能的东西,然后在教的必要支持之下,通过学生自己的努力,才被掌握的。因此,教具有促进那些没有外在帮助就不能成功运作的学习过程的功能。在有教的支持的学习方面,学习者最初面临一个超越其理解力的事物和问题,因而需要一种教的支持,才能对问题进行学习性的处理和加工。但是,凡是学习者自己能够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地方,就不涉及教的过程,而只涉及学的过程。
在教的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的。一个人施教,就是说他不在受教;一个人受教,就是说他不在施教。相反,学的过程则是在与他者和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发生的。学的过程不能由教来替代,教的过程来不能由学来替代。与教的过程不同,学可以发生在所有年龄阶段,并且没有终点。但是,教为了保持自己的合法性,就必须预料到自己的结束。也就是说,教的目的就是使自己成为多余,这在德语中被称为“教育自杀”。那种使学习者总是依赖教育者的教育,不是一种好的教育,甚至是一种控制,即便它是一种温柔的控制。阿伦特指出,教与学不一样,必须预见自己的终点,即结束于成长中一代可以自我思考、可以自己负责地行动之时,否则就会带有一种邪恶的意味。相反,学习可以发生于教育之前、之中或之后,带有终身特性。
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不仅表现为对学的遗忘,同时还表现为对兴的能力的遗忘。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把意识和事实限制在当下规则和权力关系之内,主要是培养学生对现状的适应。尽管适应有它自己的价值,但它是不完整的,有限的。如果教的理想是对现状的适应,那么其成功可能仅就那样,不会更多。实际上,我们不仅能够理解我们生活的事实,也能够超越它们,这才是教育中最为深层的时刻所在。
兴的超越特性所激发和滋养的同情性和理解性的心灵,会使我们产生惊异、敬畏和智慧,使我们更加开放,更深层次地审视自己,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找到自己独特的心灵之歌,更加真实和自发地界定自我。而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知道如何真实、自发地界定自我,既不是把一个关于世界的预先设定的模式强加于他们,也不是让他们任意地加以界定。
那么,在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中,如何把教、学和兴统一起来呢?借用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的观点,即,对世界的审美展示是教育的主要任务。我们知道,制度化的学校教育是一种人为的学习方式。在这种学习方式之中,世界主要不是直接呈现(presentation)出来,而是通过教育者来加以展示(representation)。那么,如何加以展示呢?赫尔巴特指出,“这世界是一个充满形形色色生命的丰富且开放的圈子……这种对于世界的(审美)展示……可以被正确称为教育的主要任务”。教育是对世界的诗意展示,表面上是一种内容的展示方式,但就所有的教学法在根本上也是学习法这一点而言,它所导致的结果却是学生的一种审美能力的发展,即所谓的“能兴”。
再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制度化学校教育所强调的教对于培养大量人才是成功的,但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来说,却是不够的。因为创新人才不是教出来的,不是学校毕业出来的,而是依赖于在社会实践中的 “学”与“习”的持续辩证,依赖于不断的自我唤醒和自我超越。在这方面,制度化学校教育之弊,恰恰是表现在对学与兴的儒家传统的遗忘:教育结束了,学习就结束了,而且,学习结束时缺乏一种使之唤醒的兴发力。从根本而言,学校教育不是培养模仿者和追随者,不是批量产生顺从和迟钝的民众,而是帮助他们创造性发挥和使用内在的力量。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对学与兴的遗忘,实际上就是一种其本真目的的遗忘。而“回望古典教育理想实际上就是……使教育更多地回复到其本真的使命,那就是培育健全的心灵,促成德性主体存在的完满”。
因此,如果学与兴的传统被重新激活起来,那么,教的双眼就必须一方面必须关注将学生的学习放在视野之内,使得学生离开学校之时拥有自我学习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关注培养学生的诗兴精神,以发动、维持和提高学生习得的学的习惯和能力。这样就使制度化的学校教育本身不仅仅是庸众的产地,而且还是英杰的土壤。
在创新人才的修炼中,兴的地位甚至高于学。因为只有兴才能发动学习,才能培养一颗易感知的心灵,使学习走向深度,走向质量。诗兴悬置了我们异化了的目光,把我们的欲望抛开,把我们从自己设定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能够强烈地扩展和整合我们的视角,使我们超越恐惧、自私和困厄来看世界,从更高的高度来审视世界和自我,超越眼前的利益和功利,走上自我提升的成人之道。
有趣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的成人之道却是学与兴的儒家传统的典型。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之所以能够“学而时习之”和“习而时学之”,其关键在于他“能兴”,在于他能够在人生的不断的困厄中都能生发出一种“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的诗兴精神。但是,人们也不仅要问,即使学校教育提供了一种学与兴的精神和能力,那么,我们的环境允许创新人才展开这对“学”与“兴”的双翅而自由飞翔吗?因此,抱怨培养不出创新人才的人们,除了拷问今天的学校教育外,还应该去拷问今天学校教育所根植的环境。
[1]康德.论教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
[2]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95.
[4]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12.
[5]Winfried Boehm:Theorie und Praxis.Eine Einführung in das pädagogische Grundproblem Königshausen& Neumann,1995,S.25-28.
[6]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7]梅因.古代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97.
[8]陈赟.中庸的思想[M].上海:三联书店,2007:100.
[9]朱子语类(卷三)[M].岳麓书社,1997:1858.
[10]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1]诸葛亮集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111.
[12]林语堂.中国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212.
[13]高平叔.蔡元培美育论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5.
[14]杜成宪.以“学”为核心的教育话语体系——从语言文字的视角谈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重“学”现象[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3).
[15]彭正梅.如何通过强制来培养自由:赫尔巴特《论对世界的审美展示是教育的主要任务》之研究[J].基础教育,2010,(10).
[16]刘铁芳.重新找回教育的烛光[N].中国教育报,2009-4-26.
(责任编辑 焦德武)
G40
A
1001-862X(2013)02-0182-007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制度化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10YJA880113)
彭正梅(1969—),安徽六安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