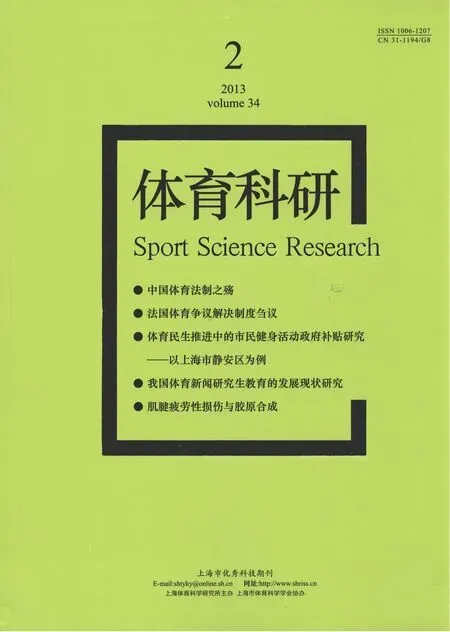论《体育法》中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从澳大利亚体育案例出发
肖卫兵
说到体育活动,不得不提及其风险。桑兰、王燕等在运动中受伤的例子引起了大家对体育运动安全性的密切关注。加之学校体育、社会体育活动中受伤害事件时有发生,制约了我国体育事业健康发展。1995年颁布的《体育法》当中没有确立体育活动中应坚持的原则。考虑到这点,2012年7月20日所推出的《体育法》修改草案当中确立了在体育活动中贯彻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该草案并将这一原则贯彻到了具体的条文当中。但是目前有关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的系统研究还停留在初级阶段,系统研究相对缺乏。一些体育法律关系主体的降低风险、安全参与法律责任也没有明确。本文结合澳大利亚体育方面的有关案例,就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做一阐述,供未来修改《体育法》时参考。
1 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概述
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源自体育活动存在一定的风险性。该原则是对各类体育法律关系主体提出的一项原则性的义务要求。它鼓励各类体育法律关系主体积极应对,而不是消极懈怠。
1.1 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之缘起
体育活动,无论是竞技体育还是学校体育,对举办者和参与者等各类体育法律关系主体都存在一定风险。首先,从学校体育来看,据教育部、公安部和卫生部等部门的初步统计,意外伤害事故已成为我国中小学生第一死亡原因,其中60%的意外伤害事故与体育活动有关[1]。学生在学校体育课或体育活动中发生的体育意外伤害事件不在少数。这其中有学校疏于管理而承担责任的。河南洛阳某高中学生在上体育课期间,体育老师因接电话而令学生自由活动,结果造成正在做单杠动作的一学生不慎摔成了左股骨下段骨折。也有因学生过错导致学校和学生共同担责的例子。在北京房山某中学组织的一场足球赛中,门将扑上前去抱球倒地,但被随后赶到的对方前锋补射的一脚踢中腹部,导致失血性休克。还有因体育活动中各方都无过错但发生伤害事件后共同担责的例子。高中生王某和孟某在上体育课打篮球时,孟某转身投篮时不慎将王某右眼撞伤,法医鉴定为十级伤残[2]。
其次,在竞技体育中发生风险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体操是其中一项。1998年7月,来自浙江宁波的桑兰在纽约参加第四届友好运动会,进行鞍马比赛的热身时,头部着地,颈椎严重受伤。喀麦隆体操选手阿里姆·哈桑在2003年7月的喀麦隆体操锦标赛中不幸头部着地,最终不治身亡。2004年雅典奥运会高低杠比赛中,波兰体操女选手乔爱娜·斯科瓦伦斯卡在训练时掉杠,造成了颈椎第七节折断。2005年欧洲体操锦标赛女子个人全能比赛上,英国名将特维德尔在参加第二项高低杆比赛热身中出现意外,颈部受到重伤。2006年11月,在美国一个私人体操馆里,一名男体操教练给自己的学生演示空翻动作时发生失误,不幸身亡。2007年6月,在全国体操锦标赛暨奥运会选拔赛女子高低杠的比赛中,浙江小将王燕在做“后屈两周下”时也不幸受伤[3]。
不仅体操运动员受伤事故屡见不鲜,其他运动项目中运动员受伤甚至死亡的事故也有不少。如水上项目,2007年4月,法国著名自由式跳水明星勒费尔姆因为发生事故不幸身亡。还有马术运动,2006年12月,韩国马术运动员金亨七在参加多哈亚运会马术3日赛第2项越野比赛途中被掀翻落马,头部受到撞击造成颅骨骨折身亡。再有是足球运动,2006年10月,在切尔西与阿森纳队比赛中,亨利在没有够到球的情况下用右膝撞向切赫的太阳穴,造成其头骨骨折。2007年2月,在切尔西和阿森纳的联赛杯决赛中,特里头球攻门,被阿森纳门卫迪比亚抡起的右脚踢到了头部,造成其当场休克[4]。
最后是因为体育用品的不合格所造成的安全隐患也屡见不鲜。器材、场地等体育设施的不安全是造成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事故的主要原因。这些不安全因素有体育器材质量问题,也有因年久失修没有及时更换原因,还有因安装不牢固、放置不合理、场地不平整等原因[5]。只要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可发现类似广州龙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扭腰踏步机、乐登袋鼠体育用品骆驼童装、忍牌羽毛球拍、红棉滚轴溜冰鞋、福建卡丁儿童用品、美国蓝猫国际集团、泉州菲克体育用品抽检不合格等的报道不胜枚举。
这一系列分散在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当中的风险事件对当事人的伤害是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它提示我们降低风险和安全参与在体育活动过程中是何等的重要。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作为我国未来体育法修改所提倡的一个体育活动的原则也就应运而生。
1.2 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之界定
目前并没有学者对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进行界定。简单来说,它是指各类体育法律关系主体在体育活动中,通过采取各种措施降低体育活动中的风险,并在体育活动中提倡安全参与之原则。该原则主要由3种要素构成。其一是降低风险、安全参与的体育法律关系主体。这些主体包括政府、学校、体育活动组织者、体育用品提供者、运动员、裁判员和观众等。其二是降低风险、安全参与的措施。不同体育法律关系主体所采取的措施有所不同。对于政府而言,主要从宏观和制度层面落实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包括制定并公布高风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制定体育用品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实行体育用品产品认证、加强体育设施、器材质量监管。对于学校而言,则应建立体育场地和体育活动安全管理制度,对体育教师进行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加强学生安全意识教育,建立学校体育伤害风险防范与处置机制。其三这一原则由降低风险和安全参与两项构成。降低风险主要针对学校、公司等团体组织而言;而安全参与更多对参与体育活动的个人而言。如对于特殊群体,应结合自身情况,参加适合自己的体育活动。其四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立法宗旨[6],实现从保障公民体育权利角度构建新型体育法律体系。
准确理解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需要意识到:一是为降低风险、安全参与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是一种义务性规定,所以是强制的,体育法律关系主体不能随意放弃。二是降低风险、安全参与所采取的措施应是积极的。意外事故的频发导致部分学校采取了消极态度,取消了一部分体育教材中有一定危险系数的运动项目,如单杠、跳山羊、平衡木和跨栏等[7]。这种为安全考虑而取消一些危险项目以及减少学生的运动量和难度的消极应对措施不应是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的本来涵义,这从某种意义上剥夺了公民的体育权利,不符合现时代以人为本的体育立法宗旨。
2 从澳大利亚体育案件管窥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的适用
澳大利亚没有体育基本法。体育立法随着不同阶段的体育发展需求而产生。各类体育案例也不断发生,为体育立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这些体育案例出发,我们可以审视出澳大利亚在降低风险、安全参与方面的一些具体考虑。
2.1 澳大利亚体育立法概述
澳大利亚体育立法缺少像我国那样的体育基本法。它的体育立法是由不同历史阶段所出台的不同领域的法律所构成。在20世纪30年代,先是为保障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建设,各州相应出台了一些制度,如南澳大利亚州1931年颁布的《娱乐场地(规章)法》和维多利亚省1933年颁布的《墨尔本板球场法》。后来是在二战后全民健身主导思想的影响下,澳大利亚政府1941年通过了《全民健身法》。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60年代制定了体育协会、体育俱乐部的规范方面的制度。典型例子有1967年新南威尔士州颁布的《纽卡斯尔国际体育中心法》和1964年塔斯马尼亚州颁布的《协会成立法团法》。还有就是体育管理机构的规范,在1 9 8 5年体育委员会(Sports Commission)成立基础上,1989年颁布了《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立法》,明确了体育委员会的设立、目标和职能。最后是各类和体育健康发展相关的立法,如颁布了反对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法规、药物滥用问题规制、体育教育和体育赞助方面立法等。典型代表有新南威尔士州在1995颁布的《体育药品检验法》和维多利亚州在同年颁布的《体育药品检测法》,1995年颁布的《体育学院法》,1992年颁布的《联邦烟草广告管制法》。总的来说,澳大利亚这些不同阶段体育事业发展特点产生了不同的立法需求,政府更多的是适应这些立法需求,进而推动本国体育事业的发展[8]。
2.2 从澳大利亚体育案件审视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的贯彻
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的具体贯彻可以从澳大利亚体育案件予以具体分析。这些案件可以分为7类。本部分内容主要参考了内维尔·特纳的研究成果[9]。第一类是体育活动举办者对受害观众的责任承担标准。最初的标准是通过区分不同观众类型而对体育活动举办者设置不同的赔偿责任。在Watson v South Australian Trotting Club Inc.(1938)一案中,受害者被视为受邀人士(Invitee)。体育活动举办者对其承担比仅是被允许进入体育场地的观众有更多的注意义务。问题是,体育活动举办者或体育建筑所有者能否因观众是在自担风险的情况下进入场地而免责。在Australian Racing Drivers Club Ltd. v Metcalf (1961)一案中,一名观众在观看赛车比赛时被失控的赛车撞伤。法院认为虽然观众应意识到观看赛车比赛存在一定风险,但是该活动举办者还是应对此负责。一系列案例的发生,使得澳大利亚最终确立了对受害观众的保护标准,这个标准不应区分观众类型,体育活动举办者都应对所应合理预见的风险承担法律责任。维多利亚州1983年颁布的《占有者责任法》就取消了基于观众类型区分体育活动举办者责任大小的规定,确立了基于一般谨慎责任(Common duty of care)要求体育活动举办者担责。
第二类是运动员对其所造成的伤害责任承担标准。很久之前发生的Regina v Bradshaw (1878)一案就认为因铲球犯规杀害了竞争对手可被控谋杀。不能对因运动员犯规而造成其他运动员丧失生命的情况提供救济的法律是没有公信力的。1967年的Rookesv Skelton (1967)案件推翻了那种认为参加运动本身就应承受某种被伤害风险,从而使得行使了伤害行为的运动员可以免责的观点。后续的案件进一步支持了该观点。在McNamara v Duncan (1971)一案中,被告在原告已经掷球后仍旧犯规铲倒原告,致使其受伤,法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原告所受到的伤害应是其所应承受的。这些案例为那些因严重犯规的运动员承担责任确立了标准,即主观上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是这些运动员承担责任的前提。
第三类是对俱乐部等体育运动团体组织的伤害责任也确立了一些标准。俱乐部可能因其对职业运动员的不当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同样,学校甚至教育主管部门,也可能因其教师或教练的侵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1987年发生的McHalev Watson (1987)案例当中,新南威尔士一学生起诉当地的教育部门,原因是其在学校打橄榄球时受伤因而致瘫。教师没有注意到其脖颈长的事实却任其在扭打过程中争球。法院最终判决当地教育部门向受害者赔偿200万澳币。这种巨额赔偿可能导致澳大利亚学校反思其对学校体育活动的态度。一些学校减少甚至取消了那些风险系数较高的、有身体接触的体育活动。
第四类是对教练员的伤害行为也确立了一些责任承担标准。教练员,尤其从事指导未成年人的教练员,在体育活动过程中如果鼓励暴力行为,是要为此承担责任的。强调指导未成年人的教练员的法律责任是因为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可能被教练员当作训练工具使用。1985年的O’s Brien v Mitchell College of Advanced Education案当中,某高中橄榄球教练发明了一种违反了该项体育活动规则的楔形强攻战术,并在实践过程中指导球员进行对抗训练。结果导致一学生被撞倒在地,尔后瘫痪。法院认为教练为此需要担负法律责任。
第五类是那些在体育运动当中承担监管、服务等方面职责的人士的伤害行为在承担法律责任方面的标准。这些人士对那些能够合理预见,但是却不能采取合理措施避免伤害的行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第六类是那些体育场地周边住户免受体育活动所带来的伤害方面的保护标准。在1970年发生的Lester-Travers v Frankston (1970)案件中,当地居民起诉某理事会。源起该理事会批准了离其居住地太近所开展的高尔夫训练课程,结果导致高尔夫球散落到其居住区域,带来安全隐患。对于这类涉及非法妨害方面的侵权案子的判断标准就是比例原则,这里存在双方的互谅互让(Give and take)的程度问题。过度侵害到其他人享受安居乐业的权利时是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的。当然也存在体育组织起诉住户非法妨害的案件。在Victoria Park Racing v Taylor (1937)案件中,被告居住在比赛场地附近,自行搭建了可以高过俱乐部所建围墙的平台,造成该俱乐部门票损失。当然,法院认为俱乐部不享有隐私权保护,因此判其败诉。
第七类是公司对员工在公司组织的体育活动当中受伤害时公司的法律责任问题。1962年Commonwealth v Oliver(1982)案件中,某雇员在其雇主建筑物内玩板球时受伤。法院认为该体育活动虽在中午午休时间进行,但是仍旧属于该受害员工在其工作期间发生,雇主因此应该承担责任。在1979年Commonwealth v Lyon (1979)案件中,某海关官员代表其所属部门外出踢足球时受伤。法院认为虽然该官员不是在其所属部门的建筑物内进行体育活动,但是该伤害属于其在工作期间发生,该海关部门应承担法律责任。
从这七大类体育案件我们可以得知,澳大利亚实际上从不同的体育法律关系主体出发,确定了其不同的承担法律责任的标准。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对于不同的体育法律关系主体设置了承担法律责任的不同标准。比如,对运动员、教练等个人所造成的伤害强调其主观上的故意。而对学校、企业等单位主体则从无过错角度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二是同一体育法律关系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法律责任的标准也存在一个渐趋科学合理的发展过程。如体育活动举办者对受害观众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从最开始区分不同的观众类型到后来的不区分观众类型,而转移到体育活动举办者的一般谨慎责任。这更有利于保护作为观众的弱者权利,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体育立法宗旨[10]。
3 完善我国《体育法》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的若干建议
随着时代的发展,1995年颁布的《体育法》已经落伍,亟需修改。可修改的地方有很多,从降低风险、安全参与这一体育活动的原则出发进行具体完善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3.1 我国《体育法》修改的背景介绍
1995年颁布实施的《体育法》已经实施了将近20年。它在保证我国体育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旧的《体育法》行政色彩比较浓厚。已经不能适应体育的市场化、职业化、产业化和社会化的需求。进一步促进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则需要对旧有的《体育法》进行修改。2009年,国家体育总局就《体育法》的修改专门向国务院进行了报告。2010年成立了由20多位法律界、高校、体育界等人士组成的《体育法》修改委员会,并召开了多次会议进行讨论。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提到要推动现有《体育法》的修改工作,争取早日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议程。同年,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发出了《关于征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有关论文的通知》,并于2011年2月27-28日,在天津体育学院召开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理论研讨会[11]。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和四次会议期间,都有人大代表提出建议修改体育法的议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也积极关注体育法修订进展情况。可谓说,体育法修改工作正如火如荼开展。
有关体育法修改的探讨很多。但具体落实到某项制度方面的系统思考还不是特别完善。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的提出相对容易,但是要在具体制度条款当中充分体现该原则有所讲究。1995年颁布的《体育法》和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相关的条款非常少,只有其中两条和这个原则有点相关:一个是第5条。该条规定国家对青年、少年、儿童的体育活动给予特别保障,增进青年、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另外一个是第22条。该条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标准配置体育场地、设施和器材。
和旧有的《体育法》不同,现有的《体育法》修改草案则有6个条款涉及到了降低风险、安全参与这一原则的具体适用。具体可以分为3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围绕政府作为体育法律关系主体,从特殊群体和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制定、体育产品的国家标准制定等方面落实该原则。修改草案的第10条规定国家对青年、少年、儿童的体育活动予以特别保障,增进青年、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第24条规定全社会应当关心、支持老年人、残疾人参加体育活动。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帮助老年人、残疾人参加与其身体状况相适应的体育活动,增强社会参与能力。第25条规定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调整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开展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活动的指导,制定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活动规范,预防发生危险。第54条规定制定完善体育用品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实行体育用品产品认证,加强体育设施、器材质量监管。
第二方面是围绕学校作为体育法律关系主体,从特殊群体和安全制度方面落实了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第28条规定学校应当创造条件为病残学生组织适合其特点的体育活动。第33条规定学校应当建立体育场地和体育活动安全管理制度,对体育教师进行安全知识和技能培训,加强学生安全意识教育,建立学校体育伤害风险防范与处置机制。
第三方面是围绕运动员管理单位作为体育法律关系主体,在运动员权利方面落实了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第39条规定运动员依法享有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待遇,相关费用由运动员管理单位根据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缴纳。
3.2 完善我国《体育法》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的若干建议
虽然现有《体育法》修改草案规定了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但是在该原则的具体落实上还存在一定的缺陷。这其中主要的问题就是没有围绕“以人为本”的体育立法宗旨,从各种不同的体育法律关系主体角度考虑其在降低风险、安全参与方面的职责。还有就是虽然对政府、学校和运动员管理单位有了一些要求其履行降低风险、安全参与方面的规定,但是却不完整。要进一步完善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的适用,需要从如下几点进行具体完善。
其一,运动员管理单位作为体育法律关系主体,在落实降低风险、安全参与原则方面的义务有待细化。目前针对运动员管理单位只是要求其为运动员缴纳工伤保险,但是对于其所应承担的体育安全管理制度、对运动员的安全意识教育和相应的体育伤害风险防范与处置机制都没有原则性规定。其二,虽然修改草案第54条当中要求制定完善体育用品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试行体育用品产品认证,加强体育设施、器材质量监管,但是该条涉及的职责和相应部门众多,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牵头部门,恐怕达不到降低风险、安全参与的目的。另外,没有考虑到体育用品的特殊性,真正从降低风险角度对之提出更高的事前和事后的监管要求。其三,对于其他主体如工会、共青团、妇联、基层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组织体育活动过程中的降低风险、安全参与方面没有具体要求。不利于这些组织在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中的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也就无法达到在鼓励参与的情况下降低风险。其四,对运动员和教练员这些个体在参加体育活动中所应承担的降低风险、安全参与职责方面没有明确性规定。
[1]马捷,徐孝坤.小学体育课的“安全与风险管理”研究[EB/OL]. http://www.nhczxx.com/Article/jiaoshi/jyky/ktyj/201202/1835.html,2013-03-02.
[2]韩勇.学校体育意外伤害的若干法律问题[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1(4):61-62.
[3]体操赛场意外不断,中体保险何时完善[EB/OL].http://sports.newssc.org/system/2007/06/13/010375017.shtml,2013-03-03.
[4]英霞.不要再来伤害我:从运动安全问题谈起[M].现代职业安全,2008(2):76-77.
[5]周丽英.学校体育意外伤害的法律问题探究[J].教学与管理,2009(1 8):2 6.
[6]贾文彤,梁灵艳.我国体育地方立法的研究[J].体育社会科学,2009(7):1 8.
[7]慈鑫,白岚.安全问题压垮体育 不少学校已取消大型体育器械[EB/OL].http://www.edu.cn/zong_he_news_465/20080731/t20080731_313242.shtml,2013-03-02.
[8]程蕉,袁古洁.美国、澳大利亚、南非、日本体育立法比较研究[M].体育科学研究,2012(5):41.
[9]Neville Turner.(1991).A History of Sport and Law in Australia[J].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Society for Sports History,(2): 177-181.
[10]岳言.浅析国外体育法制建设对完善我国体育法的借鉴[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08(2):37.
[11]田思源.“后奥运”时代我国《体育法》的修改与体育法治建设[EB/OL].http://www.ecmaya.com/article/sort03/sort087/info-21488.html 2013-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