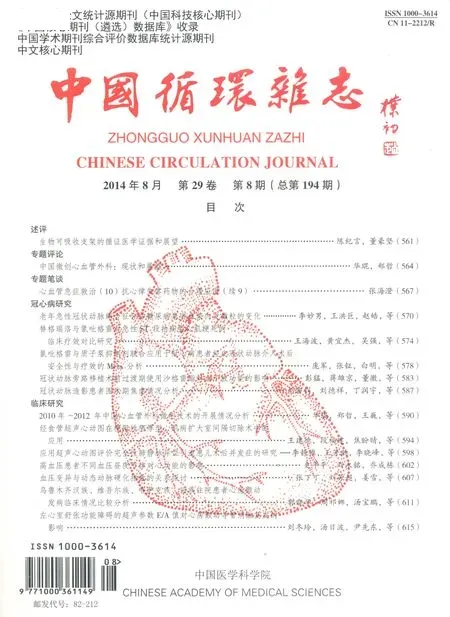生物可吸收支架的循证医学证据和展望
陈纪言,董豪坚
述评
生物可吸收支架的循证医学证据和展望
陈纪言,董豪坚
生物可吸收支架的研发历史可追溯到大约20年前,尽管根据目前的试验结果,还不能肯定生物可吸收支架一定优于目前正应用于临床的药物洗脱支架(DES),需要解决降解时间及支架内血栓、支架通过病变的能力以及支架释放后内皮化速度和炎症对损伤的反应机制等问题,但生物可吸收支架的降低靶部位的再狭窄率,中长期内支架被局部组织吸收从而降低该部位受到的药物及炎症刺激等多种优势已逐渐显现,很可能成为未来的重要发展研究方向。
生物可吸收支架;介入治疗;再狭窄
1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演进
从单纯经皮球囊冠状动脉成形术( PTCA)过渡到支架的广泛应用是质的飞越,大多数随机对照研究(RCT)显示,支架相较PTCA而言,再狭窄率明显降低[1],其机制与减少了术后的血管重构和弹性回缩有关[2]。支架包括裸金属支架(BMS)和药物洗脱支架(DES)。就BMS和DES而言,国外数据显示BMS术后再狭窄率达30%,尽管此数据因地区、种族、医疗中心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其仍被更具安全性和有效性的DES所替代[3]。多种药物涂层于支架表面,如紫杉醇和雷帕霉素等免疫抑制药物保持稳定释放并抑制内皮生长,减少介入干预部位的内皮增生,从而达到预防再狭窄的目的[4]。大量关于上述不同涂层药物优劣的RCT与Meta分析有力支持DES的推广和应用。由于术后具有更低的再狭窄率(5%左右)[5],在支架术中使用DES已成为主流。这种主流的形成并不代表BMS地位的没落,在简单病变如A型病变的患者,或因经济原因而未能选择更高价格的DES的患者,高出血风险人群无法耐受长达6~12个月的双联抗血小板药物治疗,以及计划短期内行外科手术治疗或内科有创操作或治疗的患者均优先考虑行BMS术。
从BMS到DES,同时抗血小板药物剂型的改善,患者预后得到进一步改善,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心脏科医生越来越发现这是一面双刃剑。据统计,DES术后晚期支架内血栓(ST)形成几率随着术后年限的延长而有所增长。Serruys 等[6]发现,多支复杂病变支架术后5年ST发生率9.4%,占总心脏主要不良事件(MACE)的32%。其机制可能与涂层药物造成干预部位和附近的血管内皮结构,功能异常和炎症反应有关[7,8]。随着支架内血栓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并且越来越受到关注,我们希望得到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方法:既在短期内保证更低的干预部位血管内皮过度增生和再狭窄,又在长期的过程中避免因免疫抑制药物的刺激引起炎症及变态反应,保证血管内皮结构和功能的正常化。
因此生物可吸收支架成为现在介入治疗领域的热门课题。理论上短期内生物可吸收支架上涂层的免疫抑制药物可降低靶部位的再狭窄率,中长期内支架被局部组织吸收从而降低该部位受到的药物及炎症刺激,进一步降低了支架内血栓的发生率。
2 生物可吸收支架的发展历程和优势
生物可吸收支架并非新的话题,早在近20年前(1996年)曾有学者尝试在金属支架表面涂层可降解药物,但避免不了异物所致的炎症反应和内皮增生[9,10]。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可降解支架与可降解涂层结合,Yamawaki等学者利用左旋多聚乳糖作为支架,其上具有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动物实验显示可有效抑制血管内皮增生及炎症反应,但由于当时的技术水平限制,均没有再往进一步发展。同时期,DES在替换BMS的过程中收到了市场的极大青睐,当时DES在众多临床研究中也表现出其出色的效能和较好的预后[11],因此生物可吸收支架暂归沉寂。
随着在众多RCT中发现DES晚期支架内血栓形成的发生率升高的问题愈来愈浮于水面,生物可吸收支架再次受到关注。一方面,在TCT 2012上美国心血管研究基金会(CRF) Skirball研究中心的Juan F. Granada表示,“聚合物似乎延迟表面内皮细胞覆盖,血小板激活水平较高,内膜增生反应更高”,但可吸收药物涂层是否可以弥补上述缺陷,尚须进一步的大型RCT支持。另一方面,生物可吸收支架可在体内被逐渐吸收,无残留物,避免支架长期存留动脉中引起不良反应。支架被吸收后动脉收缩和舒张功能改善,表现为正性重构和负性重构影响的减弱(通常利用IVUS可很好的发现这种重构)。吸收后的血管内膜较为完整,可一定程度上保持其接近正常的血流动力学。再者,由于吸收后的涂层药物和支架无残余物遗留,因此不妨碍再次狭窄时再一次或多次进行PCI[12]。
3 新型生物可吸收支架及相关研究
2004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制出聚乳酸(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和可降解性的聚合物,无毒,无刺激性,强度高,易加工成型,在生物体内经酶解最终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置入体内3~6个月可完全吸收)和聚羟基乙酸混合材料DES,可在不同时间向不同方向释放药物,使再狭窄率降至1%~2%[12]。
2005年美国心脏病学院(ACC)发表了来自德国Essen大学的Erbel等学者的生物可吸收镁支架的研究结果。其紧接着在2006年在ACC年会上公布了生物可吸收镁支架的PROGRESS-1研究的结果[13]。该研究纳入了来自8个医疗中心的共63例患者(44例男性及19例女性,平均年龄61.3岁),为多中心非随机前瞻性研究。所有患者在进行生物可吸收支架介入治疗后,进行第4个月的冠状动脉造影复查和血管内超声复查,第6和12个月进行临床资料随访,一级终点为第4个月时的心原性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目标病变再血运重建。研究者发现术后当时目标病变的复张良好,在第4个月,缺血导致的目标病变再血运重建率为23.8%,在术后1年上升为45%。没有证据显示在第4个月入选患者出现了心肌梗死,亚急性或迟发性支架内血栓栓塞和心原性死亡,复查冠状动脉造影和血管内超声的结果也让人较为满意,并且通过心血管内超声(IVUS),研究者发现造成再狭窄的主要机制为血管负性重构和内膜中层增生。
2006年,第18届国际心脏病学会会议上雅培公司公布了ABSORB研究的初步结果[14],主要展示了利用聚乳酸生物可吸收药物洗脱支架进行冠状动脉介入干预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该研究纳入来自多个中心包括澳洲、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新西兰、波兰和瑞士等共30例患者,为前瞻性非双盲研究。入选范围较宽,包括了稳定型和不稳定型冠心病患者,非症状性缺血,并且存在病变适合于使用单个规格为3.0 mm×12 mm或3.0 mm×18 mm生物可吸收支架进行介入治疗的患者。全部30例患者复合终点包括心原性死亡、心肌梗死、缺血导致的目标病变血运重建。26例患者完成了冠状动脉造影的复查,24例完成了IVUS复查,13例患者进行了OCT随访。研究者发现,在介入治疗过程满意的前提下,第1年主要终点事件发生率为3.3%,30例中只有1例出现非Q波性心肌梗死,无因缺血导致的再次冠状动脉血运重建事件发生。没有报道迟发性支架内血栓形成。在第6个月,复查冠状动脉造影发现支架内管腔平均丢失0.44 mm,经过IVUS确认其主要丢失区域为支架区域。以上是该研究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结果令人满意,而在该研究的第二阶段结果显示,在101例患者的3年随访中,使用了Absorb生物可吸收支架3年后主要心脏不良事件(心肌梗死、心原性死亡、血运重建)发生率为10%,与普通金属药物支架效果相当。在亚组中,45例患者进行了IVUS检查,与第1年相比,第3年的管腔获得增加了7.2%。
2013年ABSORB EXTEND研究正在进行中[15],在使用生物可吸收支架的450例患者中第1年主要心脏不良事件略低于普通金属药物洗脱支架。其最终结果正受到心血管介入领域学者的期待和关注。
据国外报道,欧洲一些国家曾在患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利用生物可吸收支架对部分患者进行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并对此进行随访,使用IVUS或OCT检查复查后发现利用生物可吸收支架进行冠状动脉血运重建后,患者血管内壁可保持光滑,血管壁无明显脂类代谢物沉积。
随着Absorb研究良好的初步结果,雅培公司开发的Absorb生物可吸收支架随后于2011年在美国批准上市。这类支架主要以多聚乳酸为骨架,以依维莫斯为涂层药物,可在大约2年时间内逐渐被吸收或自行溶解,一方面减少了涂层药物长期对血管壁和内皮的炎症刺激和损伤,另一方面减少了长期存留的金属支架引起的远期不良事件如支架内血栓形成,或长时间的双联抗血小板药物治疗需求。
对于紧急非择期介入干预的情况而言,如生物可吸收支架在急性ST段抬高心肌梗死(STEMI)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仍存疑。由于缺乏在这类紧急患者上使用生物可吸收支架的临床研究,因此在ACS患者的介入干预中尚未有显著市场。2014-01-12,Peter Widimsky等在欧洲心血管病杂志上发表了一项有关于此的研究结果,研究者发现在对STEMI患者进行介入治疗时使用生物可吸收支架具有安全性和有效性[16]。研究纳入142例患者,所有入选者均进行首次PCI治疗,其中41例患者使用生物可吸收支架,OCT显示管腔重建效果和不良事件发生率均较满意。复合终点包括死亡,心肌梗死,目标病变再次血运重建。研究中比较两者(生物可吸收支架和普通药物涂层支架)的无事件生存率无明显差异(95% vs 93%,P=0.674)。
4 新型生物可吸收支架的前景和展望
多个具有代表性的临床研究均得出了较为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上述研究的支持力依然缺乏,如缺乏RCT,入选患者的样本量不大,入选标准多欠严格等等。但前瞻非随机研究依然能在一定程度说明问题。从现今研究结果来看,生物可吸收支架的短期介入成功率,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远期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晚期支架内血栓发生率并不比普通药物涂层支架高,甚至在一些研究中生物可吸收支架具有更好的效果和更低的不良事件发生率。
由于RCT和Meta分析的缺乏,在循证医学时代,摆在心脏病学家面前的是如何进一步设计更具代表性和样本规模更大的研究来证实生物可吸收支架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更低的不良事件发生率。
[1] Pedersen SH, Pfisterer M, Kaiser C, et al. Drug-eluting stents and bare metal stents in patients with NSTE-ACS: 2-year outcome from the randomized BASKET-PROVE trial. EuroIntervention, 2014, 10: 58-64.
[2] De Luca G, Dirksen MT, Spaulding C, et al. Drug-eluting stents in patients with anterior STEMI undergoing primary angioplasty: a substudy of the DESERT cooperateon. Clin Res Cardiol, 2014. PMID: 24687617.
[3] Abe D, Sato A, Hoshi T, et al. Drug-eluting versus bare-metal stents in large coronary arteries of patients with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Findings from the ICAS registry. J Cardiol, 2014. PMID: 24685689.
[4] Tamai H, Iqaki K, Kyo E, Initial and 6-month results of biodegradable poly-l-lactic acid coronary stents in humans. Circulation, 2000, 102: 399-404.
[5] Lagerqvist B, James SK, Stenestrand U, et al. Long-term outcomes with drug-eluting stents versus bare-metal stents in Sweden. N Engl J Med, 2007, 356: 1009-1019.
[6] Serruys PW, Onuma Y, Garg S, et al. ARTS Ⅱ Investigators. 5-year clinical outcomes of the ARTS Ⅱ (Arterial Revascularization Therapies Study Ⅱ) of the sirolimus-eluting stent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multivessel de novo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J Am Coll Cardiol, 2010, 55: 1093-1101.
[7] Sousa JE, Costa MA, Abizaid AC, et al. Sustained suppression of neointimal proliferation by sirolimus-eluting stents: One-year angiographic and 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follow-up. Circulation, 2001, 104: 2007-2011.
[8] Daemen J, Wenaweser P, Tsuchida K, et al. Early and late coronary stent thrombosis of sirolimus-eluting and paclitaxel-eluting stents in routine clinical practice: Data from a large two-institutional cohort study. Lancet, 2007, 369: 667-678.
[9] Farb, Burke AP, Kolodgie ED, et al. Pathological mechanisms of fatal late coronary stent thrombosis in humans. Circulation, 2003, 108: 1701-1706.
[10] Ong AT, McFadden EP, Regar E, et al. Late angiographic stent thrombosis (LAST) events with drug-eluting stents. J Am Coll Cardiol, 2005, 45: 2088-2092.
[11] Barbash IM, Minha S, Torguson R, et al. Long-term safety and efficacy of the everolimus-eluting stent compared to first-generation drug-eluting stents in contemporary clinical practice. J Invasive Cardiol, 2014, 26: 154-160.
[12] Silvain J, Cayla G, Collet JP, et al. Coronary stents: 30 years of medical progress. Med Sci (Paris), 2014, 30: 303-310.
[13] Erbel R, Di Mario C, Bartunek J, et al. Temporary scaffolding of coronary arteries with bioabsorbable magnesium stents: a prospective, non-randomised multicenter trial. Lancet, 2007, 369: 1869-1875.
[14] Ormiston JA, Serruys PW , Regare E , et al. A bioabsorbableeverolimus-eluting coronary stent system for patients with single de-novo coronary artery lesions (ABSORB): a prospective open-label trial. Lancet, 2008, 371: 899-907.
[15] Ishibashi Y, Onuma Y, Muramatsu T, et al. Lessons learned from acute and late scaffold failures in the ABSORB EXTEND trial. Euro Intervention, 2014. PMID: 24469426.
[16] Kocka V, Maly M , Tousek P, et al. Bioresorbable vascular scaffolds in acute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a prospective multicentre study“Prague 19”. European Heart Journal, 2014, 35: 787-794.
2014-05-03)
(编辑:汪碧蓉)
510080 广东省广州市,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 心内科
陈纪言 主任医师 博士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冠心病临床研究 Email:chen-jiyan@163.com 通讯作者:陈纪言
R541
C
1000-3614(2014)08-0561-03
10.3969/j.issn.1000-3614.2014.08.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