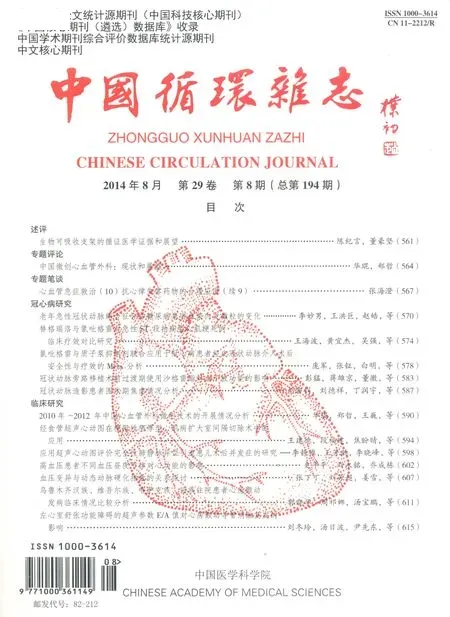中国微创心血管外科:现状和展望*
华琨,郑哲
专题评论
中国微创心血管外科:现状和展望*
华琨,郑哲
微创技术是心血管外科发展的方向之一。微创心血管外科相关技术包括小切口技术、胸腔镜、机器人和复合技术等。近年来,微创心血管外科发展迅速,随着一些新的微创技术的出现,相关研究结果陆续发表,并在某些领域达成一定的专家共识和指南推荐。
微创;心血管外科
微创外科概念的提出是外科学发展中一项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外科学的模式,并已经渗透到外科各个专科领域,与此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心血管外科的发展[1]。由心血管外科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微创是心血管外科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随着微创相关技术如小切口手术、胸腔镜手术、机器人手术和复合技术的蓬勃发展,心血管外科正朝着微创模式进行转化:传统的正中切口转化为各种类型的小切口或孔洞式入口;手术方式也朝着介入方式或复合技术方式发展[2]。中国心血管外科注册登记研究组进行的2010年~2012年中国心血管外科微创技术的开展情况分析显示,微创心血管外科技术在国内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其短期安全性和有效性值得肯定。虽然我国的微创心血管外科技术尚属起步阶段,但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3]。
1 小切口手术
目前,小切口手术广泛应用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瓣膜手术、先天性心脏病修补手术等心血管外科领域,因其术后切口微创美观,受到越来越多患者的青睐。小切口CABG手术多采用胸骨下段切口和胸廓小切口,但是由于受适应证的局限,技术上未有明显地突破,主要完成乳内动脉和前降支(LIMA-LAD)的吻合操作。因此,单纯小切口CABG手术目前只作为复合技术的一部分应用于临床[4]。
小切口瓣膜手术已达成一定的国际共识。2008年,美国心脏协会(AHA)发布声明称,瓣膜外科手术正经历从传统切口到小切口的过渡。微创瓣膜手术是大势所趋,但是在微创技术发展的同时仍需要大量的循证医学证据进一步支持该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5]。国际微创心外科协会(ISMICS)公布的数据提示,小切口瓣膜手术与传统手术相比,短期和长期全因死亡率、住院并发症无明显差别。但在胸骨并发症(0% vs 0.3%)、输血(1.5 U vs 3 U红细胞)、术后心房颤动(房颤,18% vs 22%)的发生及辅助通气时间、ICU和住院时间方面,小切口手术明显优于常规手术[6]。同时Modi P等[7]发表的Meta分析结果也提示,微创二尖瓣手术(包括小切口手术、胸腔镜手术和机器人手术)与传统开胸手术相比,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并可以逐渐取代传统手术成为常规的首选手术方式之一。
中国微创外科行业基金的数据提示,与常规瓣膜手术相比,小切口瓣膜手术的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较低。另外,小切口房间隔和室间隔缺损修补术也成为一些心脏中心的常规手术[3]。近些年,结合外科小切口手术和内科导管介入技术的复合手术也发展迅速,青岛儿童医院报道,经胸小切口下施行室间隔封堵术适用于膜周部室间隔缺损的修补[8]。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应用小切口手术结合介入导管的复合技术治疗室间隔完整的肺动脉闭锁也获得了成功[9]。
2 胸腔镜手术
1993年,Laborde首次将电视胸腔镜应用于动脉导管结扎手术中,此后Benetti和Carpentier分别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胸腔镜辅助CABG和瓣膜手术。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于1997年在全国首次开展电视胸腔镜辅助下微创CABG联合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进行冠状动脉多支血管病变的治疗[10]。目前国外最大的一组胸腔镜辅助下CABG报道结果提示,术后30天死亡率为2%,LIMA-LAD 5年通畅率为95%,5年平均生存率为92%。由于传统胸腔镜在设备和操作上的局限性,外科医生不能利用胸腔镜直接进行精细的血管吻合,血管吻合还需在直视下操作完成。因此,胸腔镜在CABG手术中只能起到改善视野的作用。在欧美大部分心脏中心传统胸腔镜已基本上被机器人平台所替代。对于胸腔镜瓣膜手术,既往Meta分析报道,胸腔镜瓣膜手术与常规手术无明显差别。Wolf等首次将胸腔镜应用于房颤射频消融手术。相关研究显示,胸腔镜技术治疗阵发性房颤和持续性房颤的成功率分别达91%和70%,其结果均明显优于导管介入方法[11]。目前,国内开展较多的是胸腔镜下简单先天性心脏病的修补手术,西京医院、四川华西医院和聊城市人民医院等先后报道了全胸腔镜下行房间隔缺损和室间隔缺损修补术,这些创新性的报道引起了国际学者的高度关注[12,13]。
3 机器人手术
机器人手术的优势在于能够进行精细的血管吻合操作,在欧美国家,全腔镜下CABG(TECAB)便是在机器人平台上完成的。马里兰大学数据提示,该大学附属医院2008年至2011年,机器人手术增长了375%,其中36%为复合技术。其中两支和三支病变使用机器人手术方式的例数逐年增加。Meta分析的结果提示,停跳下机器人CABG围手术期无死亡,二次开胸止血发生率6.8%,脑卒中发生率1.1%,肾功能衰竭发生率0.5%;非停跳下机器人CABG围手术期死亡率为1%,二次开胸止血发生率2.2%,脑卒中发生率0.58%,肾功能衰竭发生率1.6%, 可见机器人手术是相对安全有效的。
但是机器人手术仍存在许多问题,可谓弊大于利。①开展少。在美国,机器人瓣膜置换手术占机器人手术量的1.3%,CABG手术比例更低,仅占0.97% 。②费用效比低。全美国有265个机器人中心,每年心脏手术大于50例的不到4%,65%的中心无一例心脏手术。平均每年一台机器人系统只能完成7例心脏手术。③安全性问题。2011年,达芬奇机器人系统引起的不良事件为211例,2012年增长至282例,增长率34%。截至2013-03,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已接到达芬奇机器人设备引起的不良事件报道已达62例。④与其他微创技术相比费用高。⑤学习周期长。外科医生需完成一定数量的开胸手术,再接受机器人手术训练。⑥仍缺少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缺少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结果,业界对机器人手术的价值存在巨大的争议。很多以前支持机器人手术的专家反戈一击[14,15]。因此,对于机器人技术,我们应该理性面对该技术的普及,并呼唤新一代机器人的问世。
4 复合手术
复合手术结合了介入和外科技术的优点,将是未来微创心血管外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CABG的最大优势是LIMA-LAD桥的最佳远期疗效,10年通畅率达90%以上。PCI的最大优势在于微创药物洗脱支架(DES)的血管再狭窄率下降,1年通畅率达90%。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完成的世界首个复合手术和常规技术(CABG 和PCI)比较研究发现,复合手术对高危复杂冠心病治疗具有优势。3年随访结果提示,对于EuroSCORE>6分和SYNTAX 评分>30分的患者,复合手术疗效优于单纯CABG和PCI[4]。
复合手术的发展较为迅速,不仅仅用于冠心病治疗领域,更多的延伸至大血管外科和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领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复合手术治疗领域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术式,如婴幼儿室间隔完整的肺动脉闭锁;合并侧支循环的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合并肺静脉异位引流;主动脉弓置换术等[16]。采用复合技术进行房颤消融术(联合心内外膜射频消融)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1年成功率为83%[17,18],10年成功率达81%[19]。
5 经皮主动脉瓣置换术
201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首次报道了经皮主动脉瓣置换术(TAVI)能够治疗高危的不能接受传统手术的主动脉狭窄患者[20,21]。此后该项技术在欧洲取得了飞速地发展。2012年,欧洲最新瓣膜病指南进一步明确了TAVI的手术指征。新指南明确指出,重度主动脉狭窄且心脏团队认为不适合进行外科手术的,在考虑合并症等情况后,对预期生存期大于1年、生活质量可获改善的患者,应考虑行TAVI治疗(Ⅰ,B)[22]。TAVI 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目前,国内有5 家医院开展该项技术。从临床手术需求来看,外科医生将越来越多地参与这类手术,发挥的作用也愈来愈重要,这种内外科协作的团队理念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大势所趋。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些新型的微创技术也应运而生。微创技术一定会在心血管外科领域取得长足的发展和应用。对于中国的心血管外科,当务之急是建立微创技术交流的有效平台,加强微创心血管外科专科医生的培养。
[1] 胡盛寿. 关于微创伤心脏外科的讨论. 中国循环杂志, 2000, 4: 195.
[2] Hu S, Zheng Z, Yuan X, et al. Increasing long-term major vascular events and resource consumption in patients receiving off-pump coronary artery bypass: a single-center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Circulation, 2010, 121: 1800-1808.
[3] 华琨, 郑哲, 王巍,等. 2010 年~2012 年中国心血管外科微创技术的开展情况分析. 中国循环杂志, 2014, 29: 590-593.
[4] Shen L, Hu S, Wang H, et al. One-stop hybrid coronary revascularization versus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 and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multivessel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3-year follow-up results from a single institution. J Am Coll Cardiol, 2013, 61: 2525-2533.
[5] Rosengart TK, Feldman T, Borger MA, et al. Percutaneous and minimally invasive valve procedures: a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Council on Cardiovascular Surgery and Anesthesia, Council on Clinical Cardiology, Functional Genomics and Translational Biology Interdisciplinary Working Group, and Quality of Care and Outcomes Research Interdisciplinary Working Group. Circulation, 2008, 117: 1750-1767.
[6] Falk V, Cheng DC, Martin J, et al. Minimally invasive versus open mitral valve surgery: a consensus stat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minimally invasive coronary surgery (ISMICS) 2010. Innovations (Phila), 2011, 6: 66-76.
[7] Modi P, Hassan A, Chitwood WJ. Minimally invasive mitral valve surger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Eur J Cardiothorac Surg, 2008, 34: 943-952.
[8] Quansheng X, Silin P, Zhongyun Z, et al. Minimally invasive perventricular device closure of an isolated perimembranous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with a newly designed delivery system: preliminary experience.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09, 137: 556-559.
[9] Li S, Chen W, Zhang Y, et al. Hybrid therapy for pulmonary atresia with intact ventricular septum. Ann Thorac Surg, 2011, 91: 1467-1471.
[10] 胡盛寿, 郑哲, 孟强. 胸腔镜辅助下微创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附7例临床报道. 中国循环杂志, 2000, 4: 208-209.
[11] Castella M, Pereda D, Mestres CA, et al. Thoracoscopic pulmonary vein isolation in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and failed percutaneous ablation.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0, 140: 633-638.
[12] Wang F, Li M, Xu X, et al. Totally thoracoscopic surgical closure of atrial septal defect in small children. Ann Thorac Surg, 2011, 92: 200-203.
[13] Ma ZS, Dong MF, Yin QY, et al. Totally thoracoscopic repair of atrial septal defect without robotic assistance: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1, 141: 1380-1383.
[14] Robicsek F. Robotic cardiac surgery: time told!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08, 135: 243-246.
[15] Damiano RJ. Robotics in cardiac surgery: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07, 134: 559-561.
[16] Galantowicz M, Cheatham J P, Phillips A, et al. Hybrid approach for hypoplastic left heart syndrome: intermediate results after the learning curve. Ann Thorac Surg, 2008, 85: 2063-2071.
[17] Shurrab M, Danon A, Lashevsky I, et al. Robotically assisted ablation of atrial fibrill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Int J Cardiol, 2013, 169: 157-165.
[18] Pison L, La Meir M, van Opstal J, et al. Hybrid thoracoscopic surgical and transvenous catheter ablation of atrial fibrillation. J Am Coll Cardiol, 2012, 60: 54-61.
[19] Gaita F, Ebrille E, Scaglione M, et al. Very long-term results of surgical and transcatheter ablation of long-standing persistent atrial fibrillation. Ann Thorac Surg, 2013, 96: 1273-1278.
[20] Leon MB, Smith CR, Mack M, et al. Transcatheter aortic-valve implantation for aortic stenosis in patients who cannot undergo surgery. N Engl J Med, 2010, 363: 1597-1607.
[21] Gilard M, Eltchaninoff H, Iung B, et al. Registry of transcatheter aortic-valve implantation in high-risk patients. N Engl J Med, 2012, 366: 1705-1715.
[22] Taylor J. ESC/EACTS Guidelines on the management of valvular heart disease. Eur Heart J, 2012, 33: 2371-2372.
2014-03-10)
(助理编辑:许菁)
公益性行业专项(200902001)
100037 北京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华琨 主治医师 博士 主要从事微创心血管外科的研究 Email: huakun0310@126.com 通讯作者:郑哲 Email: zhengzhe@fuwai.com
R54
C
1000-3614(2014)08-0564-03
10.3969/j.issn.1000-3614.2014.08.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