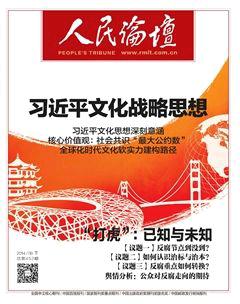海上的棋盘
张承志
海上的棋盘
张承志
我还记着第一次抵达海南岛时的感觉。
怀着一种紧张和欣喜,我记下了海南岛给予自己的新鲜印象:
“……直到海夹着一条笔直又狭长的陆地,后来我想那就是岬——波光粼粼地凸起着开阔起来以后,我才明白,此刻已在南海,我已经置身于大名鼎鼎的琼州海峡之上。
已经是身置有生以来最南的地点,而且还在继续向南。我拼命地把脸挤紧舷窗,竭尽全力地盯着在视野里凸起的,满盈着闪烁光点的海面。突然,迎面突兀地浮起一道陆地的边棱,气势雄大,一字排开。心像是一亮,就这样我看见了海南。
一座大陆般的巨岛——
我不知所措了,它沉默着,逼近而来。”
(《南国问》,1994)
那是我描绘的,二十年前“岛”给我的印象。
二十年过去了。
大概是被自幼成长的环境所束缚,但更可能是自幼熏陶的文化中少了一种对外界的渴望——我们这些北蛮之民,莫说对岛屿,即便对海洋也从来没有什么感觉。哪怕现在,电视上起劲地煽动跨海越洋的话题,并不能改变民族基因中的旱鸭子遗传。
一
我是在经历了一共三次大约七个月的西班牙调查,又经历了四个月的美洲潜入以后——才突然想看一个岛。
当然,只有海重要,它的岛才会重要。在东西方分界的地中海,任凭哪一个海里的岛,都重重刻着历史的擦痕。经过了西班牙和拉美大陆的旅行之后,我有了看岛的强烈欲望。那时我想,比一切更优先的,是至少要去看一个地中海里的岛。于是,在临近西班牙巴伦西亚海岸的马约卡岛上,徜徉寻觅,消磨了一段宝贵的时光。
决定天下大势的地理中心是地中海。
所以地中海上的岛屿——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军事与文化的锋线前沿。
其实我更盼望仔细观察的地中海岛屿,首先应该是塞浦路斯岛(军事的楚河汉界遮盖了彼此渗透的丰满文化。恰如它所要隐喻的一样,这个岛被东方和西方各自占据一半)。其次,当然若能有登临的余裕,我当然愿意随时投身的岛,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克里特岛、罗德岛、马耳他岛,以及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大西洋要冲之上的加那利群岛。它们无一例外,生动讲述着东方穆斯林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彼此纠缠的历史;它们无独有偶,满浸着古代东方文明的甜蜜浓烈的汁液。
我是因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旅行久了,获得了一种观点。岛就如麻雀,解剖它就能看懂整个地中海。我断定不用挑选,任意找随便哪一个岛屿都行。我坚信在那个岛上,立即能够如经过周密普查的考古队一样,发掘出整齐的三文化地层:石筑凯旋门和斗兽场的罗马时代地层、丰满得渗透到社会日常生活的伊斯兰时代地层,以及尚在地表的天主教地层。
——这样,既然是从西班牙出发,兼及费用和时间的考虑,我们就选择了最近也最小的一个群岛:由马约尔卡、梅诺尔卡、伊比萨三个岛组成的巴利阿里群岛;而且一开始就决定,放弃旅游味儿太浓的伊比萨岛(哪怕已经知道那岛上有一个苏非教团),也干脆不去小岛梅诺尔卡,而把时间集中在大岛马约尔卡上。
从西班牙的大陆若想去马约尔卡,只能坐飞机。这真令人遗憾。本来古代海上的交通靠的是船,如果乘船,会多少获得摹仿古代的感觉。可是只有飞机,而且票价昂贵。
唯一的好处是,被迫乘飞机,会让人感受岛的孤立:一座弃儿般的岛,它确实四面环海,真的出路断绝。这么孤单的一座岛屿,会诱人使劲盯着地图看,思索它与外界的关系。
看久了,会发现图上的岛屿,都暗暗循着一些点与线,如大海原上的一块块敷石。这种由地中海上的敷石铺成的线路,相当复杂。但若是做简单的读解,大大小小的岛屿,无非组成了一张东西方的关系网。
马约尔卡岛并不典型,但是也毫不例外。
马约尔卡的首府被旅游业玷污得一派商业味,到达的那个瞬间我就觉得此地不可久留。好在岛很大,沿海一圈都是城镇,我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小镇。
如地中海上普遍的现象,小镇的名字是阿拉伯语Alcudia,意思是“小山包”。地名学系统中的阿拉伯因素,不用说乃是历史的注脚。尤其在西班牙,官方总是竭力回避阿拉伯;于是考古或语言学的痕迹,有时就成为人打开一些秘史的线头。
我们就以Alcudia当作基地,从南端的这里出发,四出探访地中海岛屿的秘密。噢,阿尔古蒂亚,小山包,你这么小,但居然有一座洁净舒适的“客栈”,而且紧挨着沿海的古城墙。谢天谢地,外国佬晒太阳的海滨远在另一个港湾,这样我们就能躲开公开地晒她们粉色大屁股的英国或德国富婆。我们摸熟了公交车路线,周五乘车去马约尔卡的清真寺,吃过晚餐后再返回Alcudia。我们会在印加换乘,在那个穆斯林出没的岛中心市场买东西。我们绕道到了肖邦和乔治桑隐居的小山村芭乐黛莫萨,但是没有为了瞻仰他们的卧室买票。纵横穿行在辽阔的马约尔卡岛上,宛似在北京的海淀区一样。傍晚时分,登上城墙,地中海上浮光耀金,一个个模糊的帆蓬暗影远远逝去,消失在传说的毛里塔尼亚方向。
那一天,完全是无意发现了那个花园。
我那天一早就感到倦怠。一听说“花园”困意就涌上头来,但是此时,我倒觉得只把这花园的事儿写几笔,反而比描述那些反复易手的城堡,或雄踞岛心的宫殿更有意思。
不经意的发现,也许是最有意思的。我随着人群,漫步走入那个阿尔法比亚花园,一边心里还在想,我从小最不懂的就是植物……可是走着,这个莫名的大院子里丰茂滋生的种种巨树丛花,把一股辨不清味道只觉浓烈的气息送来,渐渐人便有些醺醺然。联想的第一个地方,当然是西班牙著名的红宫,来自沙漠的阿拉伯人对绿色、植物,尤其对水的喜爱,曾经令半个世界震惊。
我能想象那样一种喜爱,但是不能想象它能成为自己的气质。真的,人能够对绿色、对植物和水,达到如此的痴迷吗?
在阿尔法比亚花园的一个拐角,我觉察到这儿并没有任何园艺,只是围墙圈住了一大块绿绿的森林草地而已——那一刻我似乎有所参悟:看来他们真是喜欢。什么特殊的种类是不必要的,把高的乔木和矮的灌木搭配成景也是不需要的。无需园艺,不要技术,只要看见这么明亮的绿,他们就会满心欢喜!
他们是谁?
是从地中海彼岸过来的东方人。当然拥有这一座阿尔法比亚花园的,是黛尼亚(就是西班牙巴伦西亚地图上那个突出的角)的埃米尔(首长、司令、诸侯),名叫阿卜杜拉。显然对他来说,地中海上的这个岛,早就是他的后院和别墅。
当参观者习惯了沉浸在绿色里只看植物时,花园里也出现了些白房子。不过建筑只是点缀,阿拉伯花园给人的首要教诲就是:这里只有绿色、植物、水。再沿着盆栽与巨树并排的林荫路,经过绿幽幽的拱形水门,再次走过那随意挖出两个圆窗户的古怪大门时,人们似乎懂了。门厅顶部镶嵌着一个伊斯兰细密画风格的藻井,上面大书:“光荣属于安拉!永恒属于安拉!”
在马约尔卡,穆斯林痕迹的密集令人开眼。且不说城郊山上的摩尔城堡,在大岛中部的印加镇,集市上居然有抱着娃娃的阿拉伯妇女挤来挤去。阿尔法比亚只是一座花园而已,在市中心还矗立着阿尔穆达依纳——那是城中心的一座阿拉伯宫殿。最有意思的是它那座今天引来无数游客的海门,居然就修筑在宫殿的庭院里。后宫佳丽们迈下台阶,就能登上驶往地中海的帆船。我一再地为这样一个判断激动不已:地中海上的岛屿,从来都是东西方角力与渗透的遗址。
如今我为自己对“花园”一语的迟钝感到羞耻。
这个传入许多欧洲语言的词汇的词源,是阿拉伯语hadīgat,“有围墙的花园”。不仅英语的garden源于它,西班牙语jardín更逼真地相似于它的阿拉伯语源头(西语J的发音与阿语H类近)。它的词根是“围绕”,就是那道保护花木的围墙。
学习这个词时,我不断地联想到新疆维吾尔农家的花园。它深刻地反映着古代阿拉伯文化对鲜花与园艺的情有独钟。其实对花园的酷爱习俗一直波及了所有穆斯林民族,唯独在文化上大大中国化了的回族社会却不明显。确实,潜藏的实用主义基因,使我一直很久都对花园文明毫无感觉。
中国人对海洋的生疏是深刻的。既然对海洋陌生,就不可能对岛屿熟悉。天朝大国的正统基因,使人面对浩渺汪洋缺乏感觉。对棋布海面的岛屿只觉得散乱,哪怕登岸上岛,哪怕居住岛上。
所以,自从一种补课意识在我脑中形成,学习一个岛就被提上了日程。我打开了西班牙这本百科全书。
我们只挑了一个最近的小群岛里的一个岛,住在阿尔古比亚,前往阿尔法比亚。再钻过海门,参观阿尔穆拉依纳。这么多的阿尔,念着朗朗上口。阿语的定冠词,就仿佛是历史的陶片,催人感悟那逝去了的、东风强劲的时代。确实,解剖麻雀,一叶知秋,了解了地中海的这么一个岛,就对天下大势有了一丝把握,也对如今的世道明白了些。
不过那是地中海岛屿的特权。像定盘星、平衡点,像棋盘的交叉要冲上那些不动的棋子。其他的海,其他的岛,开启人们心智的使命有所不同,要想看透它们的含义,可能更需要眼力。
二
中日韩三国的关系,近来就像是患上了瘟病。在这样的时候去日本,总想着哪个地方能躲开狭隘的民族主义,找到一个宽阔些的视野。
看一个岛?
我打量着地图,在万顷沧海的东海上下梭巡。不意之间,对马岛、对马海峡、对马藩,次第进入了视野。
好像在一眼读三国故事。不想读得繁琐,只想了解三家彼此不同,但紧密纠缠的心事,只想找一种有益的立场。
也说不定,在对马,我找到了一种中正的,或是俯瞰的立场。这个岛比不上地中海的岛屿,没有那么宏观的文明色彩;但它恰恰被放置在东北亚一隅的海面,恰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这移不走搬不动的地理,决定了它的故事。
此地是对马,韩国的釜山和日本的下关都尽收视野。
脑海里闪过不断的电影镜头,先是《甲午海战》,后来是《日本海大海战》。日本在这儿完成了蛇吞象,不仅毁灭了虚荣的北洋水师,还一举打败了巨人国俄罗斯。对马海峡也因战争的传播,名登世界著名海峡之列。
但是在对马我看到的,却不是赫赫的武功,而是细腻的苦心;不是国家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而是现地存活的人们的和平需求。我们专门坐船从九州前往对马,船在碧波之中,行走得飞快。对马海峡如今就在身边,仿佛能看见三笠舰的炮口火光闪闪,波罗的海舰队正被黑烟吞没。
我行驶在扬名东亚近代史的对马海峡,好像日韩中俄四国都一拥而至。望着这碧波的要冲,注视着要冲上的这个岛屿,我走下舷梯,踩上了对马岛的岩岸。在这块海上通路的大敷石上,我感到,某种真实就摆在眼前,一目了然。
首先,这块大敷石不像海南岛那么紧挨一边,它离日本和朝鲜同样远。它听从日本调遣,但也不敢得罪朝鲜。
历史告诉它,得罪朝鲜是可怕的。1418年,李朝朝鲜国王派船二百余艘、近两万军队侵入对马。对马藩大败,与朝鲜签订降约,承认以朝鲜为宗主国,换来朝鲜每年拨来数百石的粮食。
至于忽必烈的元寇大举来犯,对马岛更是首当其冲。对马藩首先沦入敌手。初代藩主宗氏率领八十余骑冲向登陆的蒙古高丽大军,战死而已。
到了十六世纪,倭寇横行东海,扰乱朝鲜。对马藩曾与倭寇激战,俘虏倭船一只,把这只船引渡给朝鲜,以此举向朝鲜表明,对马藩不是倭寇巢穴,对马藩是贸易的友邻。
尽管对马藩的态度立场如此,但丰臣秀吉仍在1592年和1597年两度侵略朝鲜。对马岛的宗家为避免朝鲜战争,呕心沥血,百般努力,但无力挽救大势于狂澜。秀吉侵略之后,日本同朝鲜、明朝都断绝了外交关系。
在这样的国际政治背景中,对马藩主宗义智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在日朝关系中的表演,给后人留下长久的吟味。
对马藩积极地表达了同朝鲜恢复和平的意向,而朝鲜对日本不能信任。1606年朝鲜提出恢复邻交两条件:一须经德川家康送递国书;二日本方面捕送战争中毁坏朝鲜王陵的罪犯。
两个要求到了对马藩,愁坏了藩主宗义智。首先,毁坏王陵的犯人已不可考,其次,以日本对待朝鲜的傲慢,要低下面子先发一封国书给朝鲜,只怕也是非常困难。
于是对马藩决定:不必费事,就从对马监狱里挑他几个罪犯,灌水银烧坏罪犯的喉咙,然后把封了口的他们当作毁坏朝鲜王陵的犯人,送交朝鲜。同时抖擞文采,再伪造一份幕府名义的国书,即刻送往朝鲜。一根扁担两个箩筐,反正一定要让它两头都晃悠起来!
1607年,朝鲜李朝派出使节团,往江户庆祝德川幕府二代将军秀忠的继位。
使团从首都汉阳出发,由海路经对马,到大阪,对马藩主宗义智陪同到大阪。幕府专人迎,换船到京都。再沿东海道,陆路到达江户。这就是我在釜山和长崎都看到的、被日韩两国至今纪念的、早在四百年前的第一次朝鲜通信使。
但朝鲜使团命为“回答兼刷还使”。回答,是对日本国书回礼的意思;刷还,则是带回朝鲜人俘虏的意思。
所谓国书乃是对马藩伪造,而朝鲜人居然咬文嚼字强调对日本国书“回答”!须知幕府根本不知道自己发出过什么国书呀,奈何?利害之下,勇夫出焉,对马藩一不做二不休,继续篡改了朝鲜的国书,把开头的“奉復”改成“奉書”,据说,还伪造了一颗朝鲜国王印。
1617年,第二次朝鲜回答兼刷还使来江户,祝贺大阪之阵胜利。1624年第三次回答兼刷还使来,庆祝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继位。此外尚有日本向朝鲜的派遣使团。
而到了这分寸火候之上,对马藩已成骑虎之势,欲罢不能了。而且一旦决意,技术问题不值一提。他们早已驾轻就熟,每逢国书过境,他们便和第一次一样,每次都信笔挥毫,以巨大的自信,修改双方国书。
如此的大手笔!……
计伪造篡改总数,约在十多次之多。历史的危机,在这十余次的周旋中,安然度过了。
后来——对马藩的决策核心,传到了第二代。然而二代不如前代,他们一边持续地伪造篡改,一边却闹起了内部矛盾。终于东窗事发,国书篡改的大案暴露了。
江户的日本中央大伤脑筋。
怎么办呢?篡改国书罪不容诛,但是真的杀他们的头?须知这一篡改,可是改出了大好局面。治他们的罪?朝鲜知道了会如何呢?反正不能宣布以前的国书无效,也不能说今日之太平无效。
正是:几纸假文书,一场真和平。
对马藩在日朝外交中行为的深意,此刻才渐渐显现:为了保护这不易得来的朝鲜外交,幕府咬咬牙,决定容忍。处理事件时,给对马藩主的处罚,仅仅是批评教育而已。
随后,幕府向朝鲜提出将使节名称从“回答兼刷还使”改成“朝鲜通信使”。1636年,真正的朝鲜通信使抵达了日本。
我目瞪口呆。
没想到,我在对马岛上开了眼,看到了世界外交史上煞费苦心的一页。毫不夸张,它乃是该得和平大奖的一页,一个岛平衡了两个国家的一页,民间大局战胜国家虚荣的一页。
它余味绕梁,百年不绝。它欲诉又止,如同一个故意留下核心一句吊人胃口的天方夜谭。我只是暗暗称绝,但是不能总结。如此的匪夷所思,如此的逸出常规,究竟反映了什么?
是的,对马岛的历史,几乎在反叛的边缘上,竭力对抗了国家主义的霸道。那曾经是怎样的一种动力,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似乎很少有人追究。
对马岛的启示,其实一直持续着。它也如一本书,静静地摊开摆在海面,含笑望着愚蠢的世人。
今天走在对马岛上,到处可见韩国游客。名所旧迹的解说牌,使人明显感觉到在强调与韩国的交好。没错,它对双方都是第一颗棋子,是海中不沉的安心丸。它没有地中海岛屿的激动与不安;它永远等着远方客来,先一脚登上这块踏脚石,再把脚伸向彼岸。
三
中国如《西游记》所说是“东胜瀛洲”,是一块大陆。
岛对它来说,不仅渺小,而且总被误认成大陆的延长。
比如海南岛,好像人们心目中它更是海南“省”,潜意识中还是广东的一部分,总之是大陆的“天涯海角”。它似乎就在广州旁边,离南宁也不远。尤其如今坐惯了飞机,人更不在意它是否是个岛屿。
琼州海峡?尤其是在海南很少听人谈论它。我两次去海南,都是求人领路专门前往,才看到了琼州海峡。这道海峡在人的心理中,比实际更狭窄。对相当多的海南居民来说,它近乎不存在。
确实琼州海峡缺乏隔断的宽度,当然海南岛更没有独立于大陆的感觉。所以想看懂海南岛,就多少有些难度。
所以,哪怕你登临了海南岛,不消说登上什么南普陀、崇明岛或小长山,眺望着茫茫大海,却想着背后的莽莽大陆。中国背负的近代太沉重了,所以中国的岛上演出的,净是替大陆受辱的悲剧。台湾从荷兰手里夺回来了,但又钻进了美国的胯下。香港因为肮脏的鸦片战争变成了殖民地,谁想它并无洁癖,却为自己是殖民地而变态地自豪。
——当近现代太难以理解的时候,我们只能多观察古代。好在海南岛的历史,唯有古代最为辉煌。
想理解古代的海南岛,先要知道一个常识:在西历第七到第八世纪,世界上有两个遥遥相望的强国,一是唐朝,一是大食(阿拉伯)。唐朝已经是世界中心,接待天下的朝贡求商。阿拉伯一旦崛起,不到百年就统治了从西班牙到中亚的半个世界。
它们彼此的吸引是必然的。新鲜的召唤,使远洋船队扯起了篷帆。
第二个常识是航海。西历七世纪的航海水平,表现在广州至红海之间的大航道上。那时尚未有什么果阿、新加坡、澳门之类的殖民据点,从阿拉伯或波斯出发的船队出了马六甲海峡以后,就沿着长长的越南海岸一直向北,朝着伟大的唐朝进发。
——船队对准的最近的锚地,就是海南岛的南缘。
布罗代尔讲到殖民主义跃居主角的世界史时,仍旧用“近海航行”来概括十六世纪的航海:“辽阔的海域如撒哈拉沙漠一样空阔无人。大海只在沿海一带才有生气。航行几乎总是紧贴海岸进行。像螃蟹一样,从一块岩礁爬到另一块岩礁。甚至战舰也是一样,只在能见到海岸的海面上作战。……航海图,从头到尾只不过是对沿岸海路的描述而已。”
基于“近海航海”这一认识,地中海的蓝色海面上那些岛屿似乎突然密集了起来。我一下子明白了马约尔卡岛的含义,它确实只是地中海无数岛群中的几块石头而已!即便几块敷石上也有那么丰满的东方痕迹……我不断陷入遐思。确实,人的思考随着新知,真是无有穷匮。
现在看来,地中海岛屿与中国不多的岛屿之间,有区别也有一致之处:
“这些大小岛屿所以重要,因为它们是海上航路不可缺少的中途停靠站。这些岛屿是保证海上大动脉畅通的一支静止不动的舰队。”(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红海—马六甲的海上大动脉与地中海有所不同。它的岛屿数量少,但航路夹在狭窄的两岸之间,近岸航行更为方便。
经过红海,经过印度洋,经过马六甲海峡终于望见了中国的古人,在海南岛的南缘一线登了陆。
他们海南岛南缘稳固的第一个落脚点,随着剧烈的世事沧桑,也因为人对遗产的粗糙处理,今天已经很难追寻了。但是三亚一带的穆斯林村庄,无疑是他们几经周折之后坚持守住的世居之地。
接着,船队再沿岛航行,向北抵达海口。生长于斯的海瑞,也许是海南岛北缘最大的历史遗迹。
最后他们溯珠江,进入了大唐的门户、著名的广州。
在广州,信史与传说陡然增多。“学问虽远在中国应前往求之”的著名而奇怪的圣训,异地同声出现各地的“四大贤传教中华”传说,四大贤中名气最大的宛嘎斯就埋葬在广州城,保护碑由国民政府广东省长廖仲恺亲笔书写。不用说,那个伟大时代和真正的大航海留下的最重要标志,当数怀圣寺。那座中国第一的古寺,不是坐落在长安,而是坐落在广州。
接着说还可以延伸到扬州,但那就离“岛”太远了。
大航海的时代结束了。
移民留下了,贸易转移了。
海潮仍然一浪一浪,冲淘着人们的生计。即便明天我再次抵达三亚,我只会和那些老人一起,坐在南国火热的阳光下,谈谈家常,尝尝他们的小吃,而不会多说什么。
今天在三亚、在海口、在广州,虽然能看到从红海船下来的天方来客的后裔,但是已听不见那响彻一条海上大动脉的、伟大的召唤了。
琼州海峡太窄,海南不再是岛,它不过是大陆的一个角落而已。
不可能再幻想古代的重演。伟大的世纪呼唤,就如同千年一遇的海啸,轰鸣一过,就要消失。
岛,还是那么陌生而新鲜。
它作为万顷沧海中的散乱敷石,它作为大陆与海洋之间的点点棋子,在未来的天下变移之中,是否还会演出新的历史剧?它继续拥有特殊的含义么?
不知道。
如果今天谁感到了意义的重大,他若想究明公元七至八世纪世界史上的大航海,如果他又重新把目光转回到中国与阿拉伯这一对东方巨人身上的话——或许为时已晚,能供发掘的古迹已残留不多。
但是考古学的教训就是——遗迹永远在脚下埋藏,无论人什么时候发现。所以包括我在内,对海南岛的求索,还刚刚开始。
就像新考古学的启发,新时代的求知应该循着革命的方法。在对海南岛南缘的沙滩村落进行发掘之前,必须先行发掘的——是人的内心,是需要钻探和翻起的知识地层。
出于这样的考古基因,我习惯了学习。
虽然寄身北方,但我也想触摸岛的含义。虽嫌太少,但体验中也积累了几个岛屿。我喜欢逆着宣传,亲身一处处地登临,在不同的岛上追究寻觅。随着点滴的感受,心里会渐渐有数。
就好像散布的石子,搭建着一个海上的棋盘。
本期摘要
张承志
海上的棋盘
大航海的时代结束了。移民留下了,贸易转移了。海潮仍然一浪一浪,冲淘着人们的生计。即便明天我再次抵达三亚,我只会和那些老人一起,坐在南国火热的阳光下,谈谈家常,尝尝他们的小吃,而不会多说什么。今天在三亚、在海口、在广州,虽然能看到从红海船下来的天方来客的后裔,但是已听不见那响彻一条海上大动脉的、伟大的召唤了。(p4)
于坚
岛上
大海是一座荒凉的教堂,海神波塞冬有时候在波峰上行走,大海是世界的终点,思想从此开始,如果思想有物理空间的话,我确信它的起点就是海岸。中国神话里面没有那种野心勃勃的海神,文化的方向朝向内陆而不是大海。大海对于西方文明乃是天赐的扩张之路,不仅意味着精神的无限也意味着财富的无限,而对于郑和的船队来说,大海只是用来传递中华帝国名片的一只丝绸般的手。(p12)
徐怀平
给儿子的信(2011—2012)
三月份其实是菜花黄的时候,黄色的油菜花一大片,可是好好看的,今年的天气冷,油菜花开得不多,而且前两天还下了霜,油菜花上有霜,看起来倒是别有一番风味。油菜花是一天一天地在变化中,而且你的生日好像就快到了,那生日最好是要爸爸和你一起过了,这个生日有点特殊,因为“新爸爸”也刚好是满一周岁的了。(p70)
王方晨
大马士革剃刀
狮子口街边有个涤心泉,老简去涤心泉打水,路过吴家纸扎店,转头瞥见墙角里蜷缩着个光溜溜的东西。只看一眼,老简就看出来这东西从没见过,甚至世上也从没有过,身上还发着毒焰似的。他怕它,它也怕他。他当时就失声尖叫起来:“妖怪——!”(p132)
张承志,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心灵史》、《敬重与惜别》等。
人文地理随笔小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