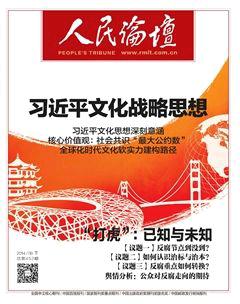本质化剪影:“文革”连环画功能性叙事札记
黄灯
本质化剪影:“文革”连环画功能性叙事札记
黄灯
“文革”已经久远。“文革”的记忆也随着岁月的流转和时代的更替逐渐模糊。关于它的叙述,除了各类文字的还原、表述、阐释外,图像也以独特形式留下了本质化剪影。后人也许无法回复到当时语境以感知它的狂热、荒唐和复杂历史性,但留存的图像却能最大程度将人推回到过去时空,让人切实感知“文革”故事的图像化叙述。
⑨Drezner,D.W.,“Globalization and policy convergence”,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2011,3,pp.53 ~78.
“文革”连环画作为叙事性极强的一种媒介,显示了特殊时代对于本质主义的理解和执行,和文字上所留下的刻板印象比较起来,它同样从视觉层面完成了对于一个时代的叙事表达。本文以“文革”连环画为观照对象,从叙事学角度,同时借鉴现实主义小说“情节、人物和环境”三要素,以此还原“文革”连环画功能性叙事要素。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文革”连环画故事几乎全部蕴含在“阶级斗争”中,尽管涉及题材众多(诸如战争、上山下乡、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批林批孔等),但几乎都离不开阶级斗争的模式化情节(《黄河滩上血泪仇》、《家奴恨》、《盐滩怒火》、《矿工怒火》、《梨园血泪》等作品,光从标题的“血泪、仇、恨、怒”就能让人触摸残酷的阶级斗争气息),因此,本文不讨论“情节”要素,而主要例举“文革”连环画中“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要素,以此透视“文革”美术的气质特征。
江南具体景观在皇家园林中的仿建以园林为主,如常州府无锡县的寄畅园在清漪园中仿建成惠山园,杭州汪氏园、海宁陈氏园和扬州趣园在圆明园中仿建为小有天园、安澜园和鉴园,苏州狮子林被仿建于长春园、避暑山庄,江宁瞻园在长春园中仿建成如园等。
先看典型人物。布雷蒙在《叙述可能之逻辑》一文中,不但用很简单的语言描述了叙事作品各层次之间的关系,而且极具概括性地勾勒了叙事“序列运转逻辑”,“可能性——变为现实——目的达到”,为艺术作品叙事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事实上,“文革”连环画“序列运转逻辑”:可能性(阶级斗争、实际困境、突发困境)→变为现实(党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哺育、阶级斗争的坚持、破私立公、英雄感召)→目的达到(斗争获得胜利、劳动生产成功、最终摆脱困境、牺牲个体获得升华),几乎完全与此吻合。和“可能性”、“变为现实”、“目的达到”三个阶段对应,“人物层”形成了如下阵营:正面人物(英雄人物、让凡人转变为英雄的人物、贫穷的底层人)→反面人物(对立阶级、同一阶级)→中间人物。由此可以推断,对“文革连环画”功能性人物的把握,可以落实到对“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和“中间人物”的勾勒。
王府饭店门口,矗立着一个大大的气囊,上写着:瑞恩·杰克苏婷婷婚礼志喜。一辆挂彩的红色宝马驶来,立刻鞭炮齐鸣,鼓乐声起。车门打开,身着婚纱的苏婷婷和身着礼服的杰克下了车,周围人鼓起掌来。杰克拉着苏婷婷的手,向周围人群连连挥手。彩丝彩带同时在两人头上飘下。
1)分析了铁轮运行过程中噪声构成及产生机理,并根据噪声频谱特性分析结果,运行在60~120 km/h的城市轨道交通中对车厢影响最大的噪声源为轮轨噪声,虽然噪声频带较宽,且频谱随车速、工况等变化较大,但可针对其噪声来源可在噪声控制过程中进行预测.
由此看来,正面人物主要包括“英雄”、“干部代表”、“底层平民”及“底层贫民”。他们作为“好人”的特质尽管来源不同,但在推动“阶级斗争”情节中,承担了目的指向一致的相同功能。因此,从人物阵营划分而言,能够同处一处。
和正面人物相对的是反面人物,反面人物即坏人。尽管格雷马斯在《行动元、角色和形象》一文中,意识到二元对立思维对人物把握的机械局限,“如果说肯定和否定这两个词只是纯粹的叫法而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的话,在有些情况里却很快就会产生混乱。如在具有严格的二元说教性质的民族文学里,肯定和否定的对立具有‘好’与‘坏’的内容,并产生‘英雄’与‘坏人’、‘促进者’与‘反对者’等组对立”。不得不承认,“文革”连环画人物阵营的状况正是他所描述的情况。和正面人物承载了“阶级斗争”必然性,并且必然胜利的结局不同,反面人物则作为“阶级斗争”的斗争对象和反动阶级而存在,并且必然承受失败命运。在序列运转中,他们客观上承担阻碍正面人物前进的功能。反面人物主要由“对立阶级”和同一阶级的“叛变分子”构成。
除了英雄,正面人物还包括引导凡人成为英雄的人物,他们没有明显的阶级分野,判断的标准“不是根据人物是什么,而是根据人物做什么”,换言之,是否提供契机引导或帮助凡人成为英雄,是判定此类人物的关键。其中“干部代表”最为典型,有“党代表”(党支部书记、村支书)、军代表(指导员)。大致说来,“党代表”主要出现在涉及年轻人成长的情节中,一般作为引导者形象出现。《青春火花》中的党支部书记吴庆,就是典型例子。在序列推进中,吴庆生起到了诸多关键作用,不但引导年轻人认清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而且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以身作则,起到了党员的带头模范作用,给年轻人增添力量,坚定他们的信念。其中吴书记在堤坝决口的危急关头,带头跳入水中的画面最为典型。不论脚本“时间还是毫不留情地一分一秒溜走,草包还没运到。岸上的同志想换,在水里的同志坚持着,他们精神抖擞,充满着必胜信心”,还是画面中吴书记手持马灯的高大形象,无不暗示了“党支书”作为党的代言人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通过信念和力量的传递所起到的辐射作用。另外,作为党的代言人,“党支书”具有超出常人的远见卓识,更能预见未来走向,往往成为年轻一代的指路人。这一点,在儿童题材连环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鱼塘边的战斗》中党支书赵春林、《小雷子》中大队党支部书记老洪;《海花》中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大伯、《范小牛和他的小伙伴》中党支部书记李大伯,都承担了同样的功能。有意思的是,在“文革连环画”中,“党的干部”形象很容易升华到英雄程度,其中《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黄妙郎》中的黄妙郎、《为人民鞠躬尽瘁——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杨水才同志的光辉事迹》中的杨水才,就是“党代表”的典型。“军代表”形象常见于战斗英雄成长过程,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榜样黄继光》中,“李同志”的出现意义深远,预示着他苦难命运有了转变契机。在黄继光成长过程中,一旦思想出现波动或者命运面临选择、转机,必然出现相关“高人指点”,以引导者的形象推动黄继光从凡人向英雄转变。连环画中,无论是军代表李同志,还是副指导员,都体现了“党”作为组织对黄继光个体的辐射,并起到了彻底改变个体命运的关键作用,从序列运转看,两者起到了“主要功能”承担的作用。事实上,在儿童题材连环画中,若涉及到军事活动,同样会出现军代表形象,如《小松子》中解放军叔叔陈班长、《海花》中民兵营长陈淇、《铁虎》中武工队队长长山大叔、《火烧“野牛”》中指导员。除了“干部代表”,因阶级优势而具有话语权的“底层平民”也常常承担“引导凡人成为英雄”的功能。这个群体尽管直接经受了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但总是能将个体遭遇转化为鲜明的政治觉悟,能意识到个体遭受的阶级剥削、压迫并不来自偶然个体命运,而是能超越个体遭遇,以阶级剥削见证人的身份给阶级斗争提供原初动力,从而强化了抗争行为的合法性。在序列运转中,他们的出现,更能以亲历者的身份坚定年轻人的信念。如《青春火花》中的贫农老妈妈,从脚本所提供的信息“在一班的棉花田里,贫农王妈妈正在向副班长高云飞传授经验。为了办好国营农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场党委从附近公社请来了植棉能手王妈妈做他们的带路人”可知,王妈妈的出现,不仅因为其高超的植棉技术,更直接的原因是其可靠的阶级性。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榜样黄继光》中,同样配备了此类人物长工陈大叔,在一些儿童题材的连环画中更是常见,如《小松子》中的贫农老山伯,《杏花塘边》中的张大伯。由此看来,无论是“干部代表”,还是“底层平民”,在凡人成长为英雄过程中,起到了正面的促进和引导作用,自然属于正面人物系列。
从多学科远程会诊、溶栓取栓、评估随访,到监护教育、大数据科研,将智慧医疗融入脑卒中救治。他们组织全市体系,力求脑卒中救治同质化、标准化。
不能忽视的是,除了承担引导人物成长的“底层平民”,在“文革”连环画中,还有一部分纯粹作为受害者形象出现的底层人也属于正面人物。和底层平民不同,此类底层人并不见得都能将个体遭受的痛苦自觉上升为政治觉悟,在凡人成长为英雄的序列中,并不能起到引导别人的作用,而是更多以阶级剥削的受害面目出现。在所有“文革”连环画中,此阵营几乎成为必备要素,这一点,《黄河滩上血泪仇》体现得最为充分。在长达七十七页的篇幅中,集中展现了地主梁化之对农民的多重剥削,其中受害人之多、手段之残忍令人印象深刻。脚本“梁家发家三把刀,讹诈、夺契加马跑;穷人土地被夺走,妻离子散往外逃”,直接将底层的贫农推向前台,随后在各类剥削情节中集中展现了底层贫民形象,如在“土地被夺”情节中涉及到的贫农有赵金良、付玉贵和刘二柱;在“农民失地后租地剥削”情节中展现了张明学一家的惨状;在“政治迫害”情节中,通过较长的篇幅突出了丁大爷一家、袁二禾一家和秦万章一家的灾难,可以说,《黄河滩上血泪仇》集中展现了底层贫民在残酷阶级压迫中的血海深仇。这一类人物作为阶级斗争的必要因素和原初动力,在人物阵营中,当然属于正面人物系列。
中间人物指正面人物中曾出现动摇、犹豫,但最后通过教育并没有背叛本阶级的人物。相对正面人物的坚决和命运明确指向性,以及反面人物反动性而言,中间人物最为根本的属性在于尽管过程出现偏离,但最终还是明确回到了正面人物阵营,其中,《青春火花》中的刘三虎就是典型代表。从阶级属性而言,刘三虎和赵凌华一样,为同一战壕中的盟友,但由于喜爱画画的个人兴趣和集体劳动之间的矛盾,加上反动分子殷士贵的腐蚀、拉拢,刘三虎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明显转变,以致差一点就偏离了革命者的阵营。但在正面人物赵凌华、吴书记、高云飞的引导帮助下,刘三虎终于认清了殷士贵的反动面目,终于和其彻底决裂,并回到自己的阵营。尽管在其成长过程中,曾经偏离过正确轨道,但最终结果还是重归了自己的阵营,因此,从人物属性而言,可以归为中间人物。和刘三虎的身份相似,《金色的道路》中的知青小柳同样属于中间人物。尽管和谢盛莲一起下乡,但她目睹现实和理想的差距,终于对上山下乡产生了怀疑,但经过小谢的感化和引导,最终还是重新回到了队伍,走向金色的道路。有意思的是,今天看来,恰恰是这些中间人物的真实内心挣扎,暴露了“文革”期间“理念”对个体情感的遮蔽作用,反而从侧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视时代的窗口。
相对而言,“对立阶级”和“英雄”一样,同样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主要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修正主义衍生而来,鬼子、地主、土匪、资本家、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具体对象。和“好人”的配备成为必需一样,反动阶级同样必然。在《集体主义的英雄邱少云》中,美国鬼子是坏人;《铁虎》中,“四只眼的胖猪鬼子”呈现了其愚蠢丑陋的一面。另外,土匪、坏蛋(说不清楚具体的划分标准,总而言之,和正面人物作对的一切人物阵营,都可简单归入这一类型)也成为表现对象,《小松子》中的匪首歪鼻子,《范小牛和他的小伙伴》中的地主分子老妖婆都是此类形象。但在“文革”连环画中,表现最为充分的反动阶级,毫无疑问属于地主阶层。从“文革”连环画叙事可以看到,随着解放后土改的顺利推进,地主阶级作为受冲击最大的剥削阶层,积累了太多的复仇情绪,尽管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已发生了根本改变,但反扑的痴心妄想愈发强烈。这样,表现地主的反动性就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斗地主”成为“文革”连环画常见情景。在《黄河滩上血泪仇》中,地主梁化之在犯下累累罪恶后,终于得到了应有下场,在公审活动中,受害者丁大爷、秦万章妻子、受害群众集体控诉的出现,显示了明显的力量对比,伴随正面人物彻底胜利的,是反动阶级历史地位彻底沦丧,死刑的执行昭示了梁化之作为个体的惨败,“斗地主”的典型场景暗示了地主阶级必然没落的命运。相对而言,“叛徒分子”辨识度不及反动阶级,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刘胡兰》中的石五则。石五则原本和刘胡兰是同一阵营的同志,但在革命过程中,经受不住考验,最后告密叛变,导致了刘胡兰的悲剧。从承载功能而言,叛徒的变节越发衬托出英雄的坚贞、无畏,起到了正面人物塑造中的陪衬作用。有意思的是,尽管叛徒在未暴露之前,和正面人物属于同一阵营,但因为人物的阶级属性已定,因而在形象塑造时依然落入贼眉鼠眼的模式,以致读者从其坏人样子中就能判定其阶级属性。
概而言之,“文革”连环画中的“人物层”几乎完全按照“序列运转逻辑”的制约配备,呈现出了界限分明的阵营化特征,从以上根据“序列运转逻辑”所梳理的人物阵营(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中间人物)看,决定人物阵营的标准并非来自人性真实的表达程度,而是完全根据阶级属性决定,由此,也可看出阶级斗争情节对“典型人物”塑造的制约作用。
除了“功能性人物”,“文革”连环画中背景的表现同样呈现了功能化特征。背景即环境,既然要塑造典型人物,那就必然要呈现典型人物所依赖的典型环境。“连环画中的背景,也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重要手段。它起着烘托和突出英雄人物形象,介绍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典型环境等作用”。整体说来,“功能性环境因素”实际上呈现了“文革”图像对“文革”母题叙述的整体语境,包括“时代性背景因素”和“偶发性极端环境因素”两方面。由于“文革”连环画涉及到的环境因素非常繁杂,下面择取“文革”气息最浓、最有代表性的“毛主席元素”、“工农业场景元素”及“极端环境元素”进行列举。
“毛主席形象”主要落实在“毛主席像”和“毛主席像章”中。其中,毛主席像最能代表其形象。毛主席作为党的化身,成为序列运转逻辑中促使主人公命运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任何一个普通人成长为英雄,没有一个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照耀,这种思想的渗透几乎成为一切凡人转变为英雄的必备要素。这样,对毛主席像的使用,就成为呈现人物成长原初动力最直接、常见的方式。在“文革”连环画中,毛主席像既包括广泛使用的毛主席照片肖像,也包括毛主席画像,如《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关成富》,就多次出现毛主席照片肖像;但也使用了毛主席画像。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榜样黄继光》为例,可以看出毛主席像主要出现在如下场合:其一,需要表达决心、鼓励和承诺时,如第38页,开完大会后,黄继光和妈妈谈心,妈妈鼓励黄继光去参加朝鲜战争;其二,在集体活动或重要会议场合,需要表征群体共同的阶级取向时,如第40页,入伍后对新战士进行政治教育,第一次课上所举行的诉苦大会,背景出现了毛主席像;同样,当乡亲们一起给黄继光回信时,也出现了毛主席像;其三,个体进行毛泽东思想学习时,必然出现毛主席像,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几乎成为凡人变为英雄获得精神核能最可靠、快捷的途径。在个体隐秘的情感、思维过程中,为了表达对毛泽东思想的坚定和向往,学习毛主席著作成为主人公最大的依赖和精神安慰;毛主席像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主人公对党的向往和忠贞;其四,个体牺牲前,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确认来自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像的出现,不但暗示了个体牺牲和价值升华之间的关系,也暗示了英雄获得英雄品格的关键。除此以外,在正面人物遭受阶级压迫,在等待党的领导、解放军到来的画面中,也经常出现毛主席像,如《黄河滩上血泪仇》第88页,就出现了毛主席像,脚本对此作了呼应,“广大受苦受难的群众,心花怒放,笑逐颜开,含着幸福的热泪,迎接亲人解放军”。毛主席像的出现,意味着遭受剥削的底层阶级命运将会发生彻底改变。另外,主人公政治生命中的重要场合(入团、入党)也必定出现毛主席像,罗光燮、门合、刘胡兰无不如此。至于毛主席像出现的频率,则完全取决于连环画的需要。有的只在几个关键场合出现,如《刘胡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直到入党的场合才出现;有的则使用极其泛滥,最典型的莫过于《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门合》,在一百一十一幅画面中,毛主席像出现了三十七次,几乎平均三个画面不到就要出现毛主席像一次。“毛主席像章”作为毛主席形象的另一种常见表现形式,成为“文革”独有的现象。像章往往依附于人物服饰使用,以表达个体的身份和立场,其中干部、军人和知青造型最为常见,并且总是在封面造型中体现出来。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铁人”王进喜》中的封面造型中,毛主席像章就是一个重要符号,成为王进喜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象征。除了干部造型运用广泛,军人造型同样很多,如《南京路上好八连 继续革命谱新歌》的封面战士的造型要素中,胸部佩戴的毛主席像章极为重要;《胸怀朝阳永向前》中复员军人周青的封面造型也使用了毛主席像章。除此以外,知青造型同样离不开这一元素,如《广阔天地炼红心》封面人物造型中,毛主席像章成为必备因素。很明显,毛主席像章的使用决不能等同当下胸花一般的饰品,而是包含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和个体价值取向。
正面人物,即好人。好人中,辨识度最高的是英雄。事实上,在“文革”叙事艺术中,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始终是其内在最强烈、集中的目标。英雄又依据身份的不同大致分为如下类型:其一,战斗英雄及革命烈士:如黄继光、邱少云、杨连第、杨根思、罗光燮、王杰、张思德、刘胡兰等。这其中的任何一个名字,随着时间的流逝,并未湮没其特有的精神光辉,对新中国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言,都如刀刻般烙在其青春记忆中。此类英雄共有的特征是具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为革命毫不犹豫牺牲了宝贵生命,当之无愧成为英雄中的英雄,闪烁着超越时空的动人价值。其二,无限忠于毛主席路线的英雄,包括干部、工人、红卫兵,如门合、黄妙郎、杨水才、王进喜、盛林法、金训华等。此类英雄的事迹,主要表现在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在具体的工作岗位中,体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每当面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冲突时,总是毫不犹豫选择对集体利益的维护,并且总是在紧要关头,选择牺牲以保全集体和国家的利益,从行动上真正落实“破私立公”思想。不能否认,相对此前的战斗英雄,他们身上的英雄品质带有较深时代烙印,散发着独有的“文革”气息。总体而言,由于英雄群体最能集中代表“文革”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具有很高辨识度,读者对其认同度也高,故不赘述。
“毛主席元素”构成了时代性背景中最为典型的因素,为“文革”气息的渲染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是运用最为广泛、最具代表性的时代背景元素,为“文革”母本故事外化为图像叙事的最佳载体,其分布范围之广、应用之灵活具体,达到了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程度,对领袖神灵般的崇拜在“毛主席元素”的广泛使用中获得了充分体现。正因为“毛主席元素”深深的政治色彩和时代气息,因此,绘画中,“凡有毛主席画像、毛主席语录的画面,必须安排妥当,绘制时要严肃认真,不能草率从事”。大致说来,“毛主席元素”主要包括“毛主席形象”和“毛泽东思想”两大方面,前者主要通过“毛主席像”和“毛主席像章”获得表现,后者则寄寓在“语录”、“红宝书”及“毛体”等形式中。
(1)结构形式对造价成本的影响。结构形式的选择是建筑结构设计的重要内容,结构形式的选择需要符合建筑物主体的使用标准,只有这样,结构形式才能够促进建筑结构安全可靠建设,同时,还能够保证造价成本的经济可控以及建筑物的美观舒适。因此,只有设计人员对所有结构形式充分了解,充分把握每种结构形式的优缺点,才能选择科学合理的结构形式,从而达到减少投资成本的目的。
除了通过“像”和“像章”对毛主席形象的直接表达,“毛泽东思想”同样成为表现重点,连环画中则主要通过“语录”(包括最高指示)、“红宝书”(包括毛主席著作)和“毛体”表达出来。作为毛泽东思想最直接的体现,“毛主席语录”成为“文革”连环画一个有机部分,不但在大部分扉页中出现,而且在正文脚本中频频出场,有时甚至成为画面的重要内容或者背景性标语(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脚本中则经常以黑体标明。“语录”具体内容由题材决定,若反映朝鲜战争中的英雄,“语录”一般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见《特级英雄杨根思》扉页)。若反映知青上山下乡,则会出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等语录。显而易见,扉页中根据题材配备的毛主席语录,实际上规定了连环画的叙事母题,渗透着强烈的本质主义意义约束,体现了“文革”叙事逻辑的强势制约。另外需要补充的是,“最高指示”作为“文革”整体背景经常出现的元素之一,同样属于毛主席语录的重要部分。除了语录,红宝书(包括语录集和毛主席著作)实际上成为“毛泽东思想”更为集中的载体,是毛主席语录、著作在“文革”中的一种独有存在形式,因为封面红色、便于携带、发行量大、影响面广,故被称为“红宝书”。在“文革”连环画中,它和“毛主席像章”一样,常见于干部、军人、知青的人物造型中。
除此以外,“毛体”的运用也较为广泛。“毛体”主要指毛主席手迹,不是印刷字体,毛主席书法具有鲜明个性,题词、语录成为其书写重要内容,因此也被当作毛主席元素中的重要内容,此不赘述。概而言之,无论是体现了毛主席形象的“像”和“像章”,还是承载了毛泽东思想的“语录”、“红宝书”和“毛体”,作为“‘文革’时代性背景因素”中最具辨识度的因素,“毛主席元素”对“文革”“典型环境”的营构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对“典型人物”塑造而言,这一元素的出现,直接对接了人物命运,解决了人物成长内在动力问题。
除了“毛主席元素”为代表的“‘文革’时代性背景因素”外,“文革”连环画中,根据表现的题材,同样形成了工农业(包括知青上山下乡)具体场景的背景元素,“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最为典型,并直接衍生了代表性的“大庆元素”和“大寨元素”。随着大庆油田的开发,王进喜作为“铁人”精神代表,成为“文革”期间工业领域的形象和精神象征。可以说,在工业场景的描绘上,对其表现几乎都以“大庆元素”为蓝本,背景的铁塔、高高的炼油塔、冒烟的火车、使用的铁锹成为常见表现对象,加上孩子们朝气蓬勃的脸庞以及阳光、红旗的映衬,共同完成了工业象征画面中政治意义的承载。在典型的工业题材连环画《“一二五”赞歌》中,类似的场景经常出现,如上册所展现的高高铁塔、忙碌不停的吊车、工地上奔波的工人,还有头戴安全帽、手持指挥旗的工人老大哥,无不营构了“文革”独有的工业气息和氛围。有意思的是,“文革”期间出版的科普类连环画,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工业题材基本要素,如上海市劳动局革命委员会劳动保护组编的《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工厂企业安全用电》、《汽车运输安全》、《钢铁冶炼轧制安全生产》、《起重输送机械安全生产》、《工业锅炉安全运行》,尽管目的在于传播工业领域的基础科学知识,但对工业因素的表现和故事性连环画并无差别。在“工业学大庆”的整体语境下,《“一二五”赞歌》、《大战气老虎》、《造船工人志气高》、《煤海》、《海港工人的创举》等一系列工业题材连环画的出现,构成了“文革”期间工业叙事的重要内容,铁塔、井架、电线、火车头、钻机、轮船、厂房、铁锤、铁锹等构成了工业题材背景表现的基本要素。和“工业学大庆”对应,农业题材背景表现则以“农业学大寨”为母本。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文革”以前“农业学大寨”就已展开得轰轰烈烈,并且出现了专门表现“大寨题材”的连环画,因此,在农业背景基本元素上,“文革”前画面叙述奠定了“文革”“大寨叙事”的基础。以《大寨英雄谱》为例,尽管出版于1965年,但从封面看,层层梯田、威武的高山、巨大的石头、劳作的人群、以陈永贵为核心的英雄群像基本构成了“大寨叙事”的基本场景。到“文革”期间,主要要素并未太多改变,不过增加了一些新内容,诸如招展的红旗和“农业学大寨”标语。随着“农业学大寨”“文革”期间的升温,一系列表现农业题材的连环画纷纷出现,并在场景表现上呈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整体而言,大寨田成为最明显的标志,此外,拖拉机、抽水机、铁锤、锄头、扁担等农用工具也成为常见内容。整体而言,如果说,“毛主席元素”最能凸显“文革”期间的政治生活氛围,那么,“工业学大庆”与“农业学大寨”作为政治生活以外最具代表性的工农业生产活动,毫无疑问从更为具体的角度营构了“文革”的重要场景,两者的配合和交融,共同完成了对“文革”整体性背景因素的表现,为“典型环境”的呈现奠定了基调。
如果说,以上列举的“毛主席元素”和“工农业具体场景元素”更多侧重于整体背景,重在气氛营构,主要为人物出场提供了布景。那么相对“英雄人物塑造”这一“文革”叙事艺术的终极目标而言,如何凸显人物成长的裂变就成为“文革”“典型环境”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而要合乎逻辑地解决这个问题,“偶发性的极端环境因素”就成为必然,这是因为在凡人成长过程中,相比正常的劳动、斗争生活,“偶发性的极端环境因素”往往更能考验人的意志,更能通过环境的渲染突出凡人的英雄品格。事实上,很多时候英雄与凡人的差别也主要体现在能否经受极端环境的严酷考验。依据“文革”连环画的叙事逻辑,也只有通过“偶发性的极端环境因素”,毛泽东思想作为凡人转变的根本动力才能获得表现的空间,两者的合一,才是凡人精神世界发生裂变并获得英雄品格的最终途径。总体说来,“偶发性的极端环境因素”主要有“气候”和“突发危险场景”,气候方面,包括暴风、暴雨、暴雪、干旱、水灾等;突发危险场景则有爆炸、电灾或火灾,其中“水灾”和“火灾”最为常见,下面分而述之。
“文革”连环画中,“水灾”在人物成长过程中成为常见的偶发性极端环境要素,很多英雄的成长都离不开这一环节的考验。在《集体主义英雄邱少云》中,尽管表现的重点是经受火灾的考验,为了突出他英雄的一面,同样设置了山洪暴发时邱少云跳入水中捞农具的场景。在一些体现干部先进性的情节中,“水灾”同样成为最常见的突发性背景,上文提到《青春火花》中支部书记吴庆生带领同志们跳进决堤的水中一幕,就极为典型。一些表现英雄集体的连环画,也通过水灾的场景表现坚贞的革命气节,《团结胜利的凯歌》中战士们纵深跳入冰浪中,筑成一道坚固的人墙堪为代表。可以说,这些情况下的“水灾”场景主要凸显了人物的优秀品德,并未对人物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因此,无论此时“水灾”多么凶险、恶劣,人的力量一定可以战胜它的淫威,并获得胜利。另外一种情况是,“水灾”总是作为个体命运的转折点而出现,并对序列推进过程产生根本影响,人的肉体生命和环境之间的对立、紧张达到极致,在个体和环境的较量中,最后总是以“人”被“水”吞噬作为结局,“水灾”作为人遭遇的对立面,起到了提升个体生命价值的媒介作用。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金训华的英雄故事》和《黄山青松映丹心》。在《金训华的英雄故事》中,金训华和洪水搏斗的场景得到了充分表现,尽管情况凶险,但他高举双手,将个体的渺小置于无边的洪水中,精神的强大却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金训华一次次和洪水搏斗的过程,对极端气候所致的“水灾”与个体牺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揭示:如果能够为集体利益奉献生命,哪怕并未挽回集体损失,这种牺牲因为照亮了英雄内心的“一心为公”的精神,同样具有崇高的意义和超越性的生命价值。陈逸飞曾谈到:“在背景的渲染展开时,我们描绘了咆哮的巨浪、汹涌的漩涡,但更注意努力刻画英雄一往无前、压倒激流的精神面貌。这样险恶的环境就能反衬出金训华同志明知风浪险、偏向风浪冲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气概。”《黄山青松映丹心》根据1969年《解放日报》关于上海市黄山茶林场的11名上海知青为抢救国家财产牺牲洪水中的消息改编。知青画家刘柏荣先后创作了组画《黄山青松映丹心》,关于“洪水”和“英雄”的关系,刘柏荣曾这样表述:“洪水虽然恶浪滔滔,奔腾汹涌,但在我们的英雄面前它是‘失败者’,英雄战胜了‘敌人’,这是事物的本质。所以画洪水是为了表现英雄,是为了刻画和烘托英雄的形象和精神气质服务的。洪水处理得好不好,表现得恰不恰当,对主题的表现及塑造完美的英雄形象是很有关系的。”由此可见,“人”和“水”的关系,即“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无论多么凶险的水情,在红宝书、红旗、毛泽东画像的衬托下,血肉之躯的人体,总能在万能、无穷的精神力量中,获得强大的心理支撑,并获得最终的胜利,“人墙”和水浪之间的对比,凸显了英雄和灾难之间的较量。
除了“水灾”,“火灾”也是突发危险场景中的常见因素。和“水灾”一样,在英雄人物成长过程中,“火灾”也经常成为凸显人物英雄品格的重要媒介。在《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铁人”王进喜》中,王进喜英雄形象的塑造,本来主要依赖其铁人精神,但铁人精神如何建构,则要通过各类考验来实现。这样,面对井喷失火的危急情况,为避免井口随时被炸沉陷,王进喜冲进火海就成为一种必然。很明显,此时“火灾”的设置尽管承担了人物成长的功能,但尚不能对人物命运产生根本制约,在序列推进中,经受“火灾”考验却没有承担人物成长过程中的主要功能。到《集体主义的英雄邱少云》中,“火灾”就承载了“主要功能”的一切作用,在很长篇幅中,重点再现了英雄经受严酷“火灾”的过程中肉体和精神、意志和考验之间的搏斗。在这一常人根本无法忍受的灾难中,正是凭借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以及刘胡兰、董存瑞、杨根思传递的精神力量,邱少云才得以超越肉体忍耐的极限,战胜火灾的淫威,保全了集体利益。尽管壮烈牺牲,但牺牲画面中熊熊烈火伴随的太阳光芒,却暗示个体生命获得了超越性的永恒意义。对金训华和邱少云而言,无论“水灾”还是“火灾”,尽管个体面临的具体考验不同,但两者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凸显毛泽东思想照耀下,人的精神、意志可以超越肉体的极限,凡人可以裂变为英雄,从而最终实现英雄人物建构的叙事目的。说到底,无论是“时代性背景因素”中“毛泽东元素”、“工农业具体场景元素”,还是“偶发性的极端环境因素”中的“水灾”或“火灾”,都是营造“典型环境”的重要手段和依托,最终目的还是为塑造“典型人物”服务。毕竟,“社会主义的连环画创作的背景处理,必须坚决贯彻为突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突出为革命政治内容服务的创作原则,决不要为画景而画景”。归根结底,“典型环境”还是为“典型人物”服务,而两者的共同配合,不过是为了更充分地叙述“文革”“阶级斗争”的母题。这样看来,通过对“文革”连环画“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功能性要素列举,可以发现正是其模式化的因素和本质化的叙述,从根本上决定了“文革”美术简单、粗暴的审美气质。
黄灯,学者,现居广州。曾在本刊发表《今夜我回到工厂》、《对照童年》、《破碎的图景:时代巨轮下的卑微叙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