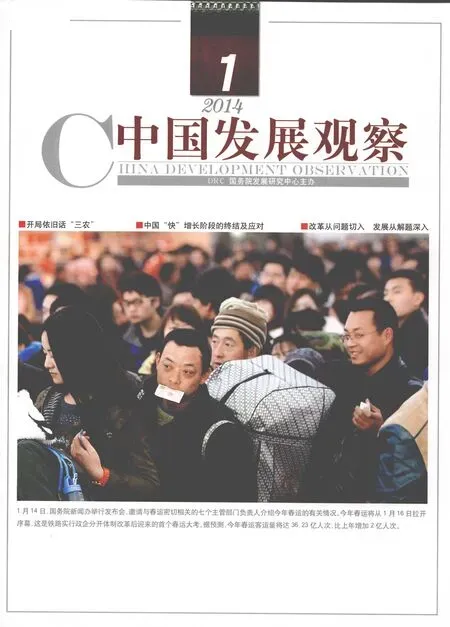西方现代社会的出现
——“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中的现代化转型研究”之十一
◎宣晓伟
西方现代社会的出现
——“中国迈向高收入过程中的现代化转型研究”之十一
◎宣晓伟

人物绘像:罗雪村
宣晓伟,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头等重要的是,开启现代性大门的钥匙必须丝丝入扣;
这不仅是要把每一个零件都弄正确,
而且是要把每一个零件和其余零件的关系摆正确;
所以,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家庭与经济的关系,等等,都必须恰到好处。
这种契合得以首次出现的概率是几千分之一,甚至几百万分之一。
但是它终究出现了。
——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2013年)
如前所述,传统社会是一个层级式结构的社会。欧洲的封建社会也不例外,形成了所谓“国王、公爵、伯爵、男爵、子爵、骑士”一套“金字塔”式的制度安排。然而与其他传统社会相比,欧洲的等级制封建社会又呈现出非常与众不同的特征。
贵族分治、个人主义、自治城市和社会分工
首先,欧洲各国世俗的政治权力事实上是由国王与各级贵族所分享的。也就是说,不像真正大一统的传统社会(例如中国传统社会),欧洲各国国王手中所握有的权力其实相当有限,如上所述他先要受到教会对其的制约。此外,国王与其下级贵族(公爵)之间通过分封的方式分享权力(即类似于中国的周朝),但这种分享是通过比较明确的方式来规定国王与下级贵族之间的权力义务关系,即根据显性或隐性的契约来规范双方的责权关系。也就是说在契约管辖范围内,国王拥有对下级贵族的权力,但并不意味着国王在任何领域都拥有至高无上、不能质疑的绝对权力。超出契约范围,下级贵族就拥有反抗的权力。除了国王与贵族之间的直接契约,贵族之间又形成层层分治的关系,即上层贵族又与其直接下层之间有较为明确的契约型关系,这样逐级分解,一直到骑士。每一层贵族只与其直接联系的上下层发生契约关系,从而成为了“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样独特的欧洲传统社会的组织和治理方式(英国在“威廉征服”后,王权扩张,逐渐突破了这一架构,这也是英国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会在以后的文章中加以论述)。
在这种架构下,世俗权力是高度分散化和碎片化的。就像马克思所说,10世纪的欧洲特征是:乡村——政权分散化到最底下的一层,一块最小的封邑,其主人是“骑士”或“从男爵”,封邑也就是庄园,其中有身份依附于封建主的农奴(顾准(1994)《顾准文集》,第294页,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个个的庄园,构成了欧洲传统社会的最基本单位,“骑士”成为世俗经济生活最底下一层的主人。在这基本单位之上,再通过契约关系层层叠加出不同级别的贵族等级采邑,最后直至国王,因此欧洲封建传统社会是一种契约化、权力高度分散化的组织方式。
其次,欧洲传统封建社会较早出现了脱离亲戚关系的个人主义传统。如前所述,基于生物性基因所产生的亲戚血缘关系一直是社会系统组织和运行最根本支配性力量。在传统社会中,如何有效利用和控制亲戚家族关系,以避免使其危害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国家权力的有效运行,一直是各个传统国家需要面对的难题。从历史经验看,一旦国家力量衰弱,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势力往往就会占据主导性的地位。然而,在西方封建社会中,可以看到的另一个奇特传统是:除了王公贵族在上层还在彼此联姻以加强血缘家族的势力,在社会的基层单位,即前面所说的庄园或封邑中,亲戚或家族已经不能成为社会中支配性的力量。欧洲的封建社会不像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其基本单位是一个个的家族,社会的扩张基于家族的放大和联合,基于血缘的家族关系始终是最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欧洲传统社会,封建主义的本质是指个人自愿屈服于无亲戚关系的他人,仅仅是以服务交换保护。在最小的庄园或封邑中,封建领主提供保护和维持秩序,成为一个个某种程度上的自治单位,在这个单位中,家族势力和亲戚关系不是社会团结的真正来源,个人观念和权力逐渐凸显,不像其他传统社会,英国的个人早就拥有了生前任意处置财产的权力,而无需再得到相关亲戚或家族的同意,而在其他传统社会是很难做到这一点。欧洲封建主义社会的这种个人主义特征,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欧洲社会早期经历了一系列的蛮族征服和战乱,家族和亲戚关系遭到破坏,难以对个人提供足够保护。第二是天主教会的力量推动,在基督教教义中,耶稣宣称,“爱父母超过爱我的人,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子女超过爱我的人,也不配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0:37)。天主教会对个人主义的支持,一方面是基于强化信仰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出于教会自身的物质利益驱动,教会反对“表亲婚姻、纳妾、领养孩子、离婚”,与此同时又支持女子拥有财产,在客观上造成了教徒可以更多地向教会捐出土地和财产。女子有权拥有和处置自己的财产,对教会大有裨益,无子女老寡妇和老处女变成了教会捐献的一大来源 (福山(2012)《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第234页)。第三来自日耳曼的文化传统,以及随之而诞生的骑士文明传统。世俗文化(骑士文明)和教会文化(教士文明)两者并存,共同构成了欧洲中世纪文化的特色,也对欧洲传统社会个人主义传统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欧洲传统封建社会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一批拥有自治权的商业本位城市的形成。欧洲城市的产生更接近与城市的本义,即由市而建城,因此商业贸易的因素在欧洲城市发展中起着最为根本的作用,而在其他传统社会中,许多城市的建立更多是基于世俗权力的需要,例如依据政治权力中心而建。此外,欧洲城市秉持了古希腊和古罗马城邦自治的精神和传统,一开始就有独立于世俗权力的倾向。欧洲传统社会中大小不同的城市,多多少少都具有一点自治权,城市试图摆脱封建主和王朝控制,其主要目标是将它的商业掌握在自己的市民手里。所依据的原则是“只有对本市的自由出过一份力的人才有分享它的特权”。在城市中,不同市民组成商业公会和行会,试图组织起来掌握城市的控制权。14世纪末,伦敦市长是由12个大行会选出的。欧洲封建社会中的城市自治是通过赎买封建主的封建权利而得到的,通常采用购买特许状的方式。12世纪末,第三次十字军兴起之际需要额外的现款,款项筹措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向城市出卖特许状。即城市与领主们签订合同,约定城市交纳一笔总款项,或交纳一笔年租以免除他们的种种义务,领主给予城市一纸特许状 (《顾准文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第316页)。逐渐摆脱封建主和王朝控制(即摆脱私人关系和私人服役制度)的地方自治共同体——城市——的兴起,对于西方社会的演进发生了显著影响。一方面这些基于商业本位城市的建立为欧洲社会的经济贸易增长创造了空间,成为推动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自治城市逐渐成为了一支重要的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后来民族国家的兴起过程中,王权依靠与城市的联合来对抗和打击贵族的势力,自治城市在现代国家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结以上,欧洲传统封建社会的特征是权力高度分散化,天主教会掌握着终极价值关怀的推行;世俗权力在统治者之间的分配呈现等级化和契约化,个人主义凸显,商业本位的城市拥有相当的自治权。根据以前文章所提出的分析框架,从有利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欧洲传统社会权力的高度分散化使得整个社会的自由度比较高,促使社会分工的展开。个人权利的较早确立、法治契约观念的推行、城市中行会组织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都是推动欧洲传统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有力因素。然而,有两大根本性的障碍制约着欧洲传统社会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一是西方教会宗教意识的制约。尽管西方教会为提高西方社会的终极价值观念提供了支撑,对凝聚整个西方社会产生着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它也从根本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就像韦伯所言“各式各样的行业和社会等级是按天命注定的,其中每一种都被分派了神所期望的、或为客观世界的规范所确定某种特定和必不可少的职责,因此,不同的伦理义务都与人们各自的地位连在一起。在这种理论形式中,各式各样的职业各等级被比做一个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基督教终极价值观念尽管是指向彼岸世界的,但却隐含地制约着人们在现实世界的自由选择。在一个统一的终极价值观念下,社会无限分工所需的价值多元化条件是无法得到满足的,人们的职业选择不得不受到统一意识形态的制约。同样重要的是,如前所述西方教会垄断了教育、文化和学术,那么在科学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难免受到宗教意识的最终束缚,宗教不从笼罩一切的地位中退出来,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现代意义的分工也是无法产生的。二是强大统一国家力量的缺乏,从前面的文章分析可以得出,分工的不断深化同时需要社会的“分”与“合”两个方面,在这个角度上欧洲社会在一定程度有利于“分”,但却很难做到“合”,权力分散在一个个基本的封邑内,互相之间难以整合,没有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力量做支持,现代分工是无法展开的。而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民族国家的逐渐兴起,正是推动西方现代社会产生的重要力量,这是下面将要详细讨论的内容。
科学革命、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现代观念的产生
如前所述,基督教终极价值观念既为西方传统封建社会的建立和运行提供了支撑,但也在根本上束缚了科学和经济发展。因此,西方社会要产生现代分工和实现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就需要破除统一的宗教意识形态笼罩社会一切的状态。但绝大多数西方人以之安身立命、传承千年的基督教终极价值观念发生了动摇,对于西方世界而言,这也是千年未有之变局,由此带来观念的转变非同小可,也对世俗的社会制度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直接奠定了现代价值观念和现代社会逐渐产生的基础。
打破西方教会对于价值信仰的垄断基于一系列的因素。首先,是科学的发展迫使宗教意识形态不得不逐渐退缩,哥白尼、布鲁诺与宗教学说关于日心说、地心说的争论成为了科学与宗教激烈斗争的一个典型象征。伴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尤其是培根将实验的方法引入科学理论的建构后,科学武器中除了理性的逻辑推演,又加上了事实的依据(尤其是实验结果的依据),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和思想方法,科学自身的发展突飞猛进,牛顿、达尔文等一批伟大科学家不断涌现,从各个方面逐步拓展和完善了现代科学体系,而在科学不断推进的多个领域,基督教都只能节节败退。其次是宗教自身改革的推行,新教的产生认为人们可以直接面对上帝,无需再像传统天主教那样通过教会的层层等级来接近上帝。新教的改革事实上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的教育文化程度日益上升的社会变化趋势。再次是文艺复兴运动推动。文艺复兴倡导人们突破中世纪宗教意识形态对人们的过度束缚,要求回到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传统,实现人的复兴和对人的关怀。
西方基督教终极价值观念在上述各方面因素的冲击下,日益退缩,它直接带来了西方社会普遍的思想危机和混乱,动摇了西方社会稳定运行和人们安身立命的基础,在这样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背景下,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应运而生,为解决上述信仰危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他们的思想成果,直接奠定了西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也为西方世界率先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扫清了在思想和价值观念上的障碍。这些思想家的代表是康德,他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一方面指出了人类理性的可能性,真正确立了科学自身无限发展的独立空间;另一方面又指出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将人的终极价值观念还留给了上帝;从而在哲学上做到了科学(理性)和宗教(信仰)的分离。康德既强调人要用理性来审视批判一切观念和事物,即所谓现代意义上人的“启蒙”,又同时强调“实然”和“应然”的两分,即“事实如何”不能推出“应该如何”,价值判断(好或坏)不能用事实判断(是或否)来推出,人的终极价值信仰根本上只能是个选择的问题。从而在宗教不应束缚科学的同时,科学(理性)也不能僭越宗教的领域。康德确立的真善二分的二元论成为了西方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基石。从此,以后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无论再对现代社会的展开怎样的思考和批评,都需要从康德的思想出发,以至有人声称:“在哲学这条道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是来自何方和走向何处,他都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古留加(1981)《康德传》,第121页~第122页,商务印书馆)。
为什么真善二元价值观念的产生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形成如此重要?这是因为一方面它为理性(科学)的无限应用拓展了空间,在真善二元论的支撑下,理性(科学)的运用不再受到宗教意识形态的约束。社会的组织和运行也需要在理性的支配下展开。所以,韦伯将传统社会的现代化看作一个“理性化”(或“去魅”)的过程,即通过计算来支配万物(而非求助于神秘力量)的精神在整个世俗社会中的运行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它为社会多元价值观念的出现和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奠定了基础。真善两分的一个结果是宗教层面的终极价值关怀不得不逐渐退回到私人领域,也就是说,价值信仰的选择成为一件个人的事情。如此一来,天主教会更加全面退出世俗领域,政治和宗教的分离更为彻底,尽管基督教的终极价值观念仍然为西方世界绝大多数人提供安身立命的信仰,并凝聚社会共识和维护社会团结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教会已经退到后台,表面上已经与政治权力没有瓜葛,真正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与此同时,个人自主为正当的观念得以真正确立,并成为支配社会运行和国家建构的基础。如前所述,相比其他传统社会,个人权利和个人观念在欧洲传统的出现要早得多,然而整个社会围绕个人权利来建构,却必须是宗教意识形态彻底退出政治领域之后,由此国家被看作是为了实现和保障个人权利而按理性原则建构起来的,这样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就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