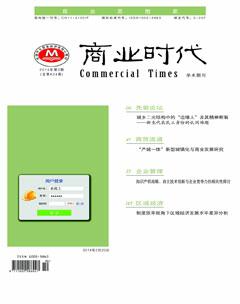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边缘人”及其精神断裂
窦立春
内容摘要:城乡二元结构是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边缘化”及精神断裂的主要原因。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新生代农民工平等地共享现代性成果,既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也是实现人民福祉的重要目标。本文认为身份认同通过个体对共体的承认以及共体对个体接纳的双向互动过程,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政治—伦理生活提供精神关照。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 新生代农民工 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80后、90后农村进城务工的人员。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有自己显著的特征,有学者认为是“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高,工作耐受力低(何磊,2005)。特殊的成长环境、教育程度、生活期望直接影响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满意度低于老一代农民工,而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信息满意度也有显著差异:低学历、低收入、自认为是农民者,满意度较高;学历越高、外出时间越长、无老乡会组织、自认为是市民者,满意度低(陶建杰,2013)。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身份是“农民—工人”的认同度直接影响社会认同度。由此,探究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伦理认同问题,不仅能澄清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模糊观念,还能提升该群体的社会认同度及城市融入度,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边缘人”身份
城乡二元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与以小生产者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在教育、医疗、社会权利、社会保障、就业等诸多领域的二元体制集中凸显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并以“农民—工人”身份,抑或“既非农民—亦非工人”的身份体现出来,这也正是“农民工”这一概念本身隐含的内在悖论。但是,这一悖论引发的不仅是农民—工人不同身份在经济收入、政治权利等方面的紧张与冲突,更为重要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由此产生了身份认同危机,即产生了对于“我是谁”的伦理追问。身份的确证以及对自我身份的认同都需要以共同体为框架,但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到底应该从属于什么样的共同体,属于来自农村的农民,抑或是在城市中工作、生活的市民?他们的身份到底应该如何确证?倘若这一问题无从回答,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行为选择就会陷入迷惑、焦虑的困境。就此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就农村层面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拥有农村户籍却无法在土地中“扎根”,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工人”。在现实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是“脱离了农业劳动的城里人”,较父辈而言,他们更多地接受了城市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并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向工业化生产模式及服务业发展,他们在城市中找到了较为稳定的工作、拥有较稳定的收入,城市的工作状态和生活实践使他们远离了农村、农业、农民身份,他们自以为是城市市民。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城市成长经历使他们无法在农村中“扎根”。
其二,就城市层面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在城市空间中却无法在城市“生根”,因为他们有一种“我是农民”的“相对剥夺感”。与城市居民相比,由于户籍制度、教育程度、专业技能等方面的限制,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在物质层面得不到相应保障,在精神生活中也往往产生无助感以及相对剥夺感。根据格尔的理论,当社会价值能力小于个体价值期待,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强人们反抗的愿望就越大,反抗行为带来的社会破坏力也就越大,格尔把这一过程称之为“挫折—反抗机制”(罗竖元,2013)。城市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的不只是经济、政治等物质条件层面的“有形”限制,还承受着精神层面无根之苦的煎熬,他们在精神世界找不到自己所应当归属的共体,成为徘徊在农村城市化进程“半道上”的孤独存在者—“边缘化”的人。
“边缘人”的精神断裂
“边缘人”身份使其产生了精神断裂。所谓精神断裂是指个体不知道自己如何通过“精神”的努力提升自己,以实现与何种共体的同一?其现实表现是个体行为选择的无所适从:在乡村与城市之间,个体到底应当以何种共体的伦理观为目的,以及选择何种伦理行为?
(一)两种生存方式的冲突
精神断裂的现实体现是无助感,即精神世界的无意义感、孤独感。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的那样,“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觉,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生存的孤独不再是个体与他人的分离,而是与实践一种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须的道德源泉的分离”。在此,可以将个体与“道德源泉”的分离理解为个体与共体的分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是个体与农村这一共体的分离,或者也可以说,是个体与城市这一共体的分离。当个体与作为“道德源泉”的共体剥离开,个体就会陷入精神的“无意义感”和孤独状态。
在此,对于精神的孤独状态,黑格尔关于“精神”在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中的辩证运动以及与之对应的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辩证发展过程或可借鉴。依据黑格尔的观点,伦理世界是精神发展的自然状态,在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个体与共体直接同一、自然同一,个体与实体的直接同一产生了直接认同,或称自然认同。家庭、民族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以及象征符号而出现,儒家将这种基于生命共同体的象征符号概括为“天伦”,黑格尔将其称之为“神的规律”或“家神”。
但是,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展以及家庭成员关系的疏远,必然会产生家庭与民族,即天伦与人伦、神的规律与人的规律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是,家庭成员与社会公民两种身份的对立与分裂,从家庭走向社会的个体在被社会教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异化,从而进入教化世界。“教化是自然存在的异化,因此,个体在这里赖以取得客观效准和现实性的手段,就是教化。个体真正的原始的本性和实体乃是使自然存在发生异化的那种精神”。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个体扬弃了个体与伦理世界的自然同一关系,凸显自我的特殊性,教化世界使个体脱离了原初的自然状态—伦理世界,实现了个体与共体的分离,但个体在脱离共体的同时却使自我陷入“原子式”生存状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