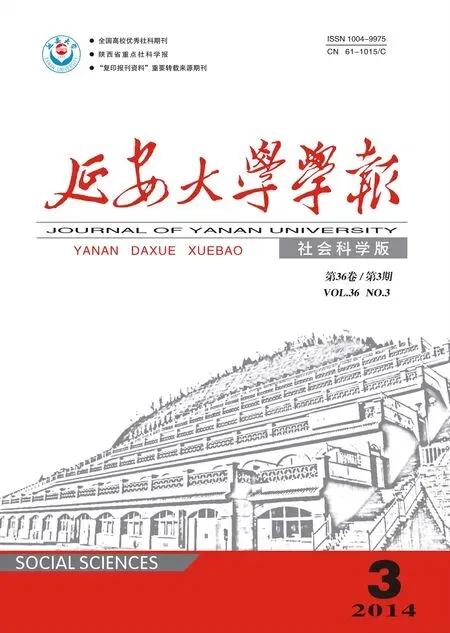论韩邦奇的散曲艺术
周喜存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明代中叶,沉寂许久的陕西文坛迎来了蓬勃的人文气象,涌现出康海、王九思、李梦阳等文学大家。关学思想全面发展,其深度和广度得到进一步拓展,吕柟、冯从吾、马理等人的著述堪称典范。这一时期,诗文酬唱、各逞其艺者层出不穷,为陕西文坛增添了雄深健雅的风姿,韩邦奇就是其中一位学术思想深邃、文学才华出众的文人。
一
韩邦奇(1479—1555),字汝节,号苑洛,明代陕西朝邑(今大荔县朝邑镇)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恭简。《关学编》载“(邦奇)父子兄弟以学问相为师友。”[1]韩邦奇与其弟韩邦靖(字汝庆)同著文名,互相砥砺,在当世享有“关中二韩”之徽号[2]。韩邦奇交游广泛,与前七子阵营中的康海、王九思、李梦阳等均有交往,与王廷相皆为气论学派,亦常以学问相切磋。[3]辞官归乡后,韩邦奇绛帐高悬,聚众讲学,负笈问业者甚众,尤以杨爵、杨继盛最负盛名,时称“韩门二杨”。邦奇既殁,后七子成员李攀龙作《祭韩公邦奇》一文,赞其“既持丰采,亦崇经术。大节屹然,高名茂实。”[4]足见其在当时文坛的影响力。
“苑洛先生”韩邦奇因博于学术、藻于文辞而驰誉海内。《国朝献征录》载:“(邦奇)笃于行谊,学务践实,不为空言,一时学者咸宗之”。[5]韩邦奇博涉学术,涉猎领域非常宽泛,《明史·韩邦奇传》载:“邦奇性嗜学,自诸经、子、史以及天文、地理、乐律、术数、兵法三书,无不通究,著述甚富。”[6]冯从吾赞其“读书探理窟,著作人难企”[7],其理学思想为明代“三原学派”思想的发展与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潜心学术之外,韩邦奇还游于艺文,他的文学作品主要收在其代表作《苑洛集》中。该集收录韩邦奇的序文、志铭、传记、奏议、诗、词、曲等,体现出文学多面手的特点。
近年学界关于韩邦奇的研究,多局限于他的学术思想,关于其文学成就的研究则乏人问津。笔者以为,要客观准确评价韩邦奇在明中叶的学术文化地位,有必要探研其文学特色及成就。笔者从韩邦奇文学价值最高的诗、词、曲三类作品中拈出散曲一类进行深入探析,以窥其文学成就之一斑。韩邦奇存世散曲共计20首(“重头曲”按单首计算),全部收录在《苑洛集》卷十二中。本文所引韩邦奇散曲以嘉靖本《苑洛集》为准。因原刻无宫调名,依谢伯阳《全明散曲》增补。
尽管存世数量不多,但韩邦奇的散曲不乏佳构妙篇,故有必要对其情感抒写、语言表达等进行细致研究,深入揭示其艺术价值和艺术特色。韩邦奇的散曲创作集中在正德、嘉靖年间,与明代散曲走向复兴、艺术技巧日臻完善的时期——弘治至嘉靖[8]基本一致,故研究其散曲艺术将有助于全面深切把握明中叶陕西散曲乃至主流文坛散曲的特点及成就。总体来看,韩邦奇的散曲创作与明中叶散曲创作的时代特点相一致,但又有其独擅胜场之处。整体风格虽属北派,语言却倾向于南派散曲的清峭柔远。
二
相较于传统散曲,韩邦奇的作品既不反映重大社会矛盾,也不描写市井生活、田园风物,题材略显单调,然其特出之处就在于其中流露出的深细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感悟。韩邦奇的散曲题材明朗,归结起来有三类:其一,借咏季节变换寄寓乡园之思或人生叹惋的作品;其二,看透官场与功名的怀古咏史类作品;其三,情意深沉的饯别作品。表面上看线条简单,实则不乏肌理细腻的雕镂,将伤春、悲秋、怀乡、离别、自省等诸多常见的文学母题,以散曲的方式演绎的淋漓尽致。兹分举不同题材的作品来探析。
感知四季流转是文学作品挹之不竭、写之不尽的题材,在韩邦奇的散曲中所占数量最多,“重头曲”《春思》其二和“带过曲”《秋思》颇具代表性:
春雨霏霏,绿柳丝丝春渐肥。看他万花枝上都是春光。蜂蝶休疑,担头春酒陇头诗,风流人是春光主。燕语莺啼,碧阑干外,春光有几。
(〔北双调·驻马听〕《春思》其二)
客窗风雨苦潇潇,几番将离魂惊觉。晚沙秦苑迥,秋水灞陵遥。极目迢迢,又天涯一夜晓。短发彫搔,病不相饶,愁不相饶。为病多减了酒量,为愁多瘦了诗腰。酒量减刘伶潦倒,诗腰瘦庾信萧条。雁下空壕,叶落庭皋。不晓事草砌寒蛩,夜深时絮絮叨叨。
(〔北双调·新水令带过折桂令〕《秋思》)
这两首作品分别以春思和秋思入题,浅吟低唱,可谓笔触细腻。前一首语意新鲜活泼,将春天写得楚楚可人。“绿柳丝丝春渐肥”、“万花枝上都是春光”两句好似以彩笔点染春色,描绘出春天草木抽青、生气勃发、春光流转的喧妍景象;“担头春酒陇头诗”句则以诗下酒,意趣丰沛。后一首围绕“苦”字写秋思,起始便直抒客居之“苦”;继而写梦中惊觉,因晚沙秦苑、秋水灞陵之故园遥不可及,于是彻夜难眠,“迥”、“遥”、“迢迢”等字眼继续强化思乡之“苦”;后半部分写愁病交加之“苦”,以刘伶、庾信之典渲染苦闷之深,寒蛩絮絮鸣声更令人聒噪烦闷,思乡之苦愈发深沉,写情可谓微妙传神。
此类题材中更是不乏构思别出心裁、韵味悠长之作,兹举“重头曲”《晓秋》和小令《秋思》为例:
银箭催更天渐晓,金井梧桐落。西风小阁寒,残月疏簾照。王仲宣此际愁多少。
绿树满庭清气生,宝鸭消银鼎。风传玉雁声,霜没金蝉影。就不是宋玉也愁难整。
楼上残更鸡叫彻,银蜡还明灭。笛飘别院风,砧急长廊月。萧条庾信愁难说。
河汉西倾生白露,三四寒鸦语。黄花月下残,红叶风前舞。张衡到此把愁添作五。(〔北双调·清江引〕《晓秋》)
月娟娟空上海棠枝,风瑟瑟催残杨柳丝,露零零易落梧桐泪。倚西楼看雁归,隔天涯万里相思。休说到梦中是假,暂欢娱还胜醒时,夜迢迢梦也还稀。(〔北双调·水仙子〕《秋思》)
《晓秋》抒发一腔愁怀,匠心独运。曲中描写深秋黎明景象,每首视线皆由室内而户外,嵌入四组绮丽工巧的对偶句,以色彩和声响衬托黎明寂静,犹如凝神专注、屏息谛听的意境,将萧瑟的秋天景色表现得极富美感。每首末尾又以古之伤心人为典,新颖别致。抒情手法细腻,接近诗词味道,耐人咀嚼。《秋思》中前三句先以拟人手法呈现出一幅萧瑟秋景图:娟娟之月“空上”枝头,瑟瑟之风“催残”柳丝,零零之露如梧桐“落泪”,形象表达出望月而感孤独、触风而觉衰飒、见露而生悲凄的心理,未言“相思”,句句暗示“相思”;中二句承题直写因遥隔万里而生“相思”;后三句则更翻空出奇,借梦烘托“相思”之深:梦境虽假,但对相思之人而言梦中的短暂欢愉也聊胜醒时,现实却是夜迢梦稀,将“相思”的失落、怅恨心境反衬得愈发强烈。这样的构思不仅写情细腻且新鲜别致,读来别有一番韵味在心头。
否定王图霸业、看破功名的主题在元代散曲大家的作品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脍炙人口的如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白朴的〔双调·乔木查〕《对景》、关汉卿的〔南吕·四块玉〕《闲适》等。韩邦奇的散曲中也表现出对官场和功名的鄙弃态度,但相较之下韩邦奇的此类作品比上述佳作显得更为深沉,可与同时代散曲巨匠康海、王九思的同类作品相媲美。韩邦奇散曲中没有表现出“一拳打脱凤凰笼,两脚蹬开虎豹丛,单身撞出麒麟洞”(王九思〔双调·水仙子带过折桂令〕《归兴》)式的疏狂豪迈、“花底朝朝醉,人间事事忘”(康海〔双调·雁儿落带过得胜令〕《饮闲》)般的消极玩世;亦不像康海批判时政“昌时盛世奸谀蔽”(〔仙吕·寄生草〕《读史有感》)、王九思喻险恶官场为“龙蛇窟,虎豹营”(〔仙吕·傍妆台〕《无题》);更没有他们“瞻北阙心还壮,对南山兴转狂”(王九思〔双调·水仙子〕《六旬自寿》)般的欲避世归隐又眷恋仕途的矛盾心理。韩邦奇因刚正不阿的秉性,仕途极其蹭蹬坎坷,这种经历赋予他百感丛集的生命体悟。韩邦奇散曲中对宦海浮沉的集中表达,是他仕宦经历中的深切感悟,不仅体现了对官场生活的清醒认识,而且引发了他反思历史上英雄霸业、功名利禄的虚无感与苍凉感。
这类如断片式思考的作品往往词锋锐利,沉雄浑厚。作者将渺小的个体置于广袤的历史长河中,抚事抒怀、感叹兴衰,对历史进行审视和关照,并引发淋漓激荡、深刻醒豁的感慨,表现出洞达仕进的深沉。如:
我也曾披金甲,坐镇玉关。我也曾步玉阶,侍讲金銮。都是一场傀儡闹喧喧。也未必山林好,也未必省台安。得抽身便宜了千千万。
(〔北中吕·朱履曲〕《思归》)
落花不见采莲舟,乱柳难寻沙苑楼。莎青白塚清明后,长春宫,麋鹿遊。把豪华都做了一望荒丘。长扬坂繁烟埋恨,夕阳亭落日生愁。留不住渭水东流。
(〔北双调·水仙子〕《同州道中怀古》)
深秋旅程,邙山云起,洛浦风生。风悲云惨,斜阳映往事。伤情牛羊坂是英雄坟塚,禾黍场是帝王宫庭。今和古,成长梦,只丢下些虚名虚姓,模糊在断碑中。
(〔北中吕·满庭芳〕《洛阳怀古》)
这几首散曲作品驰目远眺,思接千载,慨叹平生,充溢着苍凉悲怆之气。生命个体在历史车轮下的无奈和无助,在韩邦奇笔下充分展现出来。《思归》中看透官场生活原来“都是一场傀儡闹喧喧”,因而“得抽身便宜了千千万”;《同州道中怀古》中更是看到在历史的洪流中“把豪华都做了一望荒丘”,且“留不住渭水东流”,功业名利尽付东流;《洛阳怀古》中指出不管曾经辉煌与否,“只丢下些虚名虚姓,模糊在断碑中”,否定英雄霸业、富贵功名的意味更为浓重。表达类似情感的还有“叹英雄霸业成空,望不尽寒莎烟荻,寻不着汉阙秦宫。只丢下些剩水残山,云物凄凉落照中。”(〔北越调·绵答絮〕《咸阳怀古》)“陈宋繁华,齐梁文藻,王谢流风,都做了一场话柄,还落不得半个虚名。”(〔北双调·折桂令〕《金陵》)他俯瞰世间风起云涌,已超越芸芸众生的平凡境界。在对历史的追问中,他体会到“荣华富贵,古为今样”(〔北双调·驻马听〕《过北邙》),莫大的孤独感和寂寞感萦绕在这些作品中,其中不免流露出悲观、消极的情绪。
三
明代散曲有北调、南调之分。王骥德《曲律》论南北调之别云:“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画地而知也。北人工篇章,南人工句字。工篇章,故以气骨胜;工句字,故以色泽胜。”[9]175龙榆生《中国韵文史》说:“工北调者十九皆北人。”[10]元代后期,散曲创作出现了追求形式美的倾向。李昌集认为明散曲较之元散曲,雅化的迹象更深。[11]从散曲的语言特色来看,韩邦奇散曲也具有追求精致化语言的倾向,曲词整体上呈现出流丽典雅的美感,并不以俗白质朴取胜。他的散曲衬字较少,语句整饬,具有较强的节奏感。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曲词中修辞的经营比比皆是,这无疑对增强语言的秀雅绵渺具有明显作用,这说明韩邦奇有意使散曲语言向诗词的特质靠拢。在曲词的炼字、意象、对偶、用典等方面都能看出他在这一方向上的着力经营。
“意常则造语贵新”,在常见题材中,韩邦奇特别注重炼字出新。如前引〔北双调·驻马听〕《春思》有“绿柳丝丝春渐肥”之句,妙在以“肥”字写春景,几可与李清照“应是绿肥红瘦”之“肥”争胜。韩邦奇把春来万物滋茂、绿意渐浓的景象用一字呈现了出来,似俗实新,正如王骥德所云“(下字)要极新,又要极熟”[9]124。邦奇散曲中用“催”字也极新妙。《边城春到迟》与《边城秋来早》(〔北越调·绵搭絮〕)二首中两次出现“家乡万里,白发还催”,写出了因思乡愁绪而引发人生苦短的慨叹;“见西风才报新秋,赤叶萧萧霜已催”,极有力地表现出了边地的萧条苦寒。又如“风瑟瑟催残杨柳丝”(〔水仙子·秋思〕)、“风瑟瑟催残漏”(〔朱履曲·边城夜雨〕),皆有异曲同工之妙。
意象的经营可以《边城春到迟》为例:
昏昏漠日下荒台,望胡天极目凄凄,春尽边山花未开。对寒杯百感兴怀。家乡万里,白发还催。何处是渭水秦城?雪满红崖雁不来。
(〔北越调·绵搭絮〕《边城春到迟》)
前面部分写边地的春天荒凉寒冷,渲染出一派凄凉的景象,以此衬托戍边将士浓浓的思乡之情,语词浅白,抒情流畅,最后以“雪满红崖雁不来”句结尾,使作品具有了一种绵长悠远的韵味。这一句色彩鲜明,如绘画般为边地的灰寒色调抹上一缕亮色,属于以亮丽的色彩来写哀愁,颇为奇警,余味深长。赵义山《明清散曲史》中评价韩邦奇的艺术时,以此首作为其较有特色的作品,并指出“其借景抒情,为诗词中常法,作者融之于曲,遂使这类作品既有散曲通俗之趣,又具有诗词蕴藉绵长之味。”[12]同样以色彩来装饰意象的例子还有《寄答世宁进士壬申》(〔北双调·驻马听〕)“别意悠悠,又是西风万里秋。那堪云迷白雁,露冷黄花,月满朱楼”几句,以反笔写出鲜明的景色因云迷、露冷、月满而黯然,映衬离愁之浓,可谓是描写凄清伤感主题的新鲜笔法。
工炼而雅致的对偶在韩邦奇的散曲中更是屡屡可见,不仅凝炼了曲词,而且有助于增强意象的美感。仍以上引《晓秋》为例,曲中的四组偶句精致中蕴含丰富美感,如果说“西风小阁寒,残月疏帘照”还属写实之笔,那么“风传玉雁声,霜没金蝉影”、“笛飘别院风,砧急长廊月”、“黄花月下残,红叶风前舞”几句则已是融入了通感手法之后极具空灵意境的虚景了。还可举《别仲华进士辛巳》(〔北双调·新水令带过折桂令〕),曲中把别情借景物描写表达出来,借鉴了词的细腻笔法,如“莺声遥入座,花气细侵帘。梅雨无端,把韶光一夜换”几句,细微的雕绘使离愁具有一种幽微难言的伤感;“苑草芊芊,渭水川川”二句,则以芊芊细草之近景延伸至川川渭水之远景,饱含离别后无限怀想和期待的缜细情思。
典故的密集运用也是韩邦奇散曲的一个特点。嘉靖二年,韩邦奇辞去山西副使一职,创作了“重头曲”《晋阳怀归》(〔北仙吕·寄生草〕),这组曲子中大量运用典故,深切表达看透宦海本质后对自由生活的无限向往。
晚霜遥,玉垒寒,晚云多,金台迥。想蓴鲈,禁不得西风动。对莺儿,弹不出南薰弄。望烟霞,丢不下东山景。急归来,却早是白头人。到此时,看透了黄粱梦。
又不是,贪山水,又不是,爱神仙。人家筵席也终须散。唬杀人,鹤唳华亭叹;愁杀人,鸟尽淮阴怨。聪明人须早过是非关,英雄汉挑不起功名担。
肯排山,山能撼,肯倒海,海可翻。只是我意儿里不要紧,心儿里懒。没来头,无限闲。拘管不中用,多少闲文案。黄石桥收了子房编,玉门关挂起班侯剑。
我本是钓鳌人,做不得攀龙客。千万般怕负了皇恩大,二十年偿不尽经纶债,两三翻空惹得青山怪。归来一啸海天空,醉时节还觉得乾坤窄。
洛阳桥,春柳新;岳阳楼,阴风动。蔓草长,休迷了渊明径。华峰高,还寻着希夷洞。五湖深,系不住陶朱艇。养闲身,猿鹤伴,丹霄铸衰颜,龙虎蟠金鼎。
你看那三杰忙,你看那四皓闲,汉家青史都把名儿显。白楼绿柳,是吾家苑。渭滨河曲与渔樵伴。对知音,还取古琴弹。散幽情,细把羲经点。
曲中划线句汇集的典实有:西晋张翰见秋风而思念家乡鲈鱼莼羹;舜弹五弦琴造《南风》诗,喻太平盛世;东晋谢安高卧东山;卢生借枕而梦,喻不能实现的梦想;陆机兄弟眷恋人生,叹华亭鹤唳不复再闻;淮阴侯韩信未能参透名利;张良圮桥得兵书;班超出使西域,封定远侯;《列子·汤问》“一钓而连六鳌”,喻有豪放的胸襟和远大的抱负;左思“自非攀龙客”,喻不汲汲于仕途名利;乾坤窄,禅宗语,喻放不下名利得失;渊明径,喻隐居处所;希夷洞,传说中道教陈抟老祖修炼处;陶朱公范蠡功成身退;伯牙鼓琴、子期知音。典故的运用或隐或显,不仅大大拓展了作品的内涵,更使散曲具有了诗词含蓄蕴藉的韵味。
明人徐复祚《曲论》枚举明代散曲家,韩邦奇为其中之一。笔者以为,整体而言韩邦奇散曲创造属于北派,但在抒情方面倾向于南派的流丽婉转,语言方面更倾向于南派的华滋清雅。韩邦奇散曲是融合了南调、北调的特点后形成的独具特色的风格。韩邦奇散曲别具一格的精致美追求,表现出其在志情与造语两方面对从元代积淀下来的散曲艺术特质的认同。综上所述,韩邦奇散曲的文学价值实颇足观,其在明代散曲作家中应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冯从吾.关学编(附续编)[M].陈俊民,徐兴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51.
[2]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2418.
[3]葛荣晋.王廷相和明代气学[M].北京:中华书局,1990:271-277.
[4]李攀龙.沧溟先生集[M].包敬第,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546.
[5]焦竑.国朝献征录[M].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卷二十四.
[6]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5318-5319.
[7]冯从吾.少墟集[M].明天启元年刻本:卷十七.
[8]宋浩庆.元明散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1-72.
[9]王骥德.曲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10]龙榆生.中国韵文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7.
[11]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369.
[12]赵义山.明清散曲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