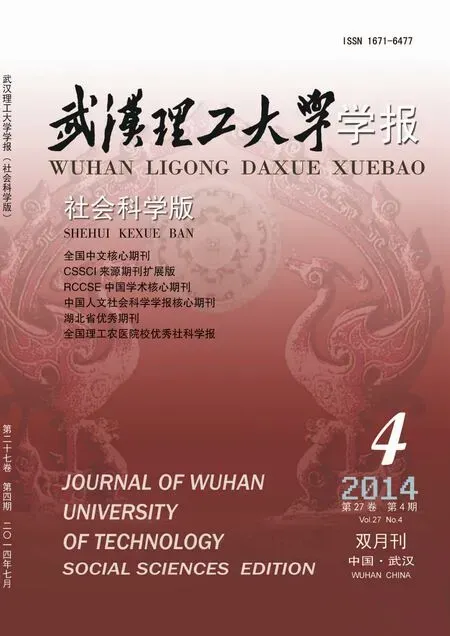现代性语境中的情欲想象*
——从小说《乌鸦》到梨园戏《董生与李氏》
阮礼义
(泉州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福建 泉州 362000)
泉州知名剧作家王仁杰的梨园戏《董生与李氏》①(以下简称《董》),改编自当代著名作家尤凤伟的短篇小说《乌鸦》②(以下简称《乌》),当中所映射的“同”与“不同”,是颇值得反思的戏文事件。遗憾的是,当下论者依旧驻足于其形式特征的外围观照,而没有超越媒介特质,直抵现代性的精神实质。而在笔者看来,其不仅在于由小说改编成戏剧或电影,乃是改编者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经过二度创作,其中体现着不同作家对同类题材的不同处理方式,以及作家的不同审美旨趣和价值追求;同时深刻表征着在现代性语境中想象乡土中国的不同方式。
一、化荒诞之悲为喜剧之美
诚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尤凤伟的短篇小说《乌》讲述的是一则近乎荒唐的、有关“监守自盗”的故事。 小说《乌》所描述的时空,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不知名的小乡村。不到60岁的村支书田木根临终前托付同村的汉子田三月,要他监视他那“还很年轻貌美”[1]401的老婆李青草,如果李青草与什么“野猫野狗”勾上,就“替我施家法,打死人不用你偿命。”[1]409作为交换条件,支书把三月欠村里的钱抹掉。同时,田三月每月要到坟前汇报。在受命监视中,田三月被寡妇“鲜桃子”般的身段所吸引,以致背信弃义,监守自盗。后来汇报时,由于内心恐惧与不安,以致精神恍惚,将坟前榆树上的乌鸦当成是已经死去了田木根的鬼魂。在树上的乌鸦“杀—杀—杀”叫喊声的驱使下,田三月鬼使神差般替“乌鸦”——田木根执行了“家法”——卡死寡妇李青草。结局是,田三月的精神失常了。见了乌鸦就敬礼,反反复复说着同样的一句话:“乌鸦了不得啊,乌鸦了不得……”[1]411
这一外表看似荒唐却蕴涵后现代荒诞内核的乡野故事,藉由尤凤伟的生花妙笔,显现出现实主义的所谓真实,让你了不得、不相信。其中之一,便是对主人公田三月的心理刻画。对田三月来说,田木根死活都惹不起。活着的“乌鸦”——田木根,他当民兵队长处罚田三月扛木头时候,曾令田三月吓得尿湿了裤子;死后的田木根,即树上的“乌鸦”,田三月也认定田木根是“惹不起”的。再加上自己“偷情”,做贼心虚,心里有鬼,正是所谓的疑心生暗鬼。在田木根这个“不死的鬼魂”面前,田三月从肉体到精神彻底崩溃,精神错乱就理所当然了。在一个个看似荒唐的举动背后,都有充足的现实依据,正是那一种下意识的心理驱动力在主宰着主人公田三月的一举一动。《乌》不是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来推动故事情节的,而是借助人物的自我心理暗示,将故事一步一步演化开来。
如果说《乌》第一层面是写有妇之夫与寡妇勾搭成奸的老掉牙故事,第二层面带出这故事本身也仅仅是一场有妇之夫监守自盗的闹剧。那么,第三层面才是其核心。其实,《乌》更像是一篇心理小说,除了主人公自导自演一场监守自盗的闹剧外,在主人公幻觉下杀人的荒诞悲情故事背后是一种令人深思的弱势者的奴性心理。可以说,《乌》反映了乡村社会的一种文化生态,弱小愚昧的田三月不仅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牵制(村支书田木根),还遭到死后的“鬼神”——“乌鸦”(田木根的化身)的胁迫(信仰鬼神)。小说不仅揭示出政治意识形态对人的生存的绝对统治,而且隐含了民间宗教文化思想对人精神的扭曲和摧残。
如果说《乌》是一个悲剧,源自于寡妇死于非命,男主人公精神失常,那么经由王仁杰妙手改编之后,令人难以直视的悲剧变为大团圆收尾的乐见喜剧。为了要切合“董生与李氏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一剧情,首先是改变男主人公的身份,由一个村民,改为一介书生。同时,为避开“偷情”的非法性,将“有夫之妇”改为年过四旬的“鳏夫”,并别出心裁地将一介穷书生取名叫“董四畏”。所谓“四畏”,深刻隐喻着“畏天命、畏大人、畏贤人、畏妇人”,从而规避了主人公的人品失范问题。按彭员外的评价是“君子固穷,信而好古,好德,不好色,年过四旬,尚鳏居而洁身自好……”[2]5与此同时,时代背景也由当代拉回到古代,以契合传统梨园戏的呈现方式。
具体而言,首先 “监守自盗”的情节大致相仿,但由于人物的不同,故事的展开就有些不一样。小说与戏剧都是围绕“监守自盗”的故事展开,其情节结构大体相仿。即“临终托付”—“每日功课”—“登墙夜窥”—“监守自盗”,以时间推进和空间转换的方式逐一展开。在这点上他们是相似的。另外,不同点在于人物的身份不同,他们有各自不同的做法和表现。在《乌》中,村民田三月对受命监视一事,一方面乐此不疲、无所顾忌,另一方面,又将监视当偷窥,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而在《董》中,董四畏是一介书生,受命监视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是怕有辱斯文,二是有顾虑和担心,担心会影响到“节妇”的名声。于是,戏剧在患得患失中,闹出很多可笑的举动。如在《董》中的第四出监守自盗。上一出“登墙夜窥”,将董生内心纠结的矛盾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接着,理智战胜情感,逾墙“捉奸”去。由于有先前的李氏送“榴莲”一事,李氏对董生早就有所期待,才有后面的两人四眼对峙:一个想“不辱使命”捉奸捉双,一个却是少妇守寡期待闯入者。当董生误闯后,担心“闺房变成白虎堂”[2]17,读者在为董生的“闯深闺胡乱猜”而捏一把汗时,李氏却骂董生“你这无用乔生,枉有贼心无贼胆。”[2]17最后,当然是董生“捉奸”捉到自己身上,两人终成好事。两人交好一节,剧作家巧用小锣师与鼓师的对话,以半旁白的方式,一句“你行他不行”,[2]18既含蓄,又淫而不乱。这方面该戏剧写得很文雅。如本集其中的一篇序言所评:“用了窥隙逾墙的鸡鸣狗盗手段来描写志诚君子,却在人情尽世理、括俗态出情趣。”[2]序一
其次,“监守自盗”后的结局,小说和戏剧沿着各自不同的方向发展。在小说里,“监守自盗”后,田三月到田木根坟前汇报。作家尤凤伟是让主人公田三月由“偷情”而“害怕”,由“害怕”导致幻觉,不断遭受精神上的折磨,失去自我,以至于产生自我错位的幻觉,最终在错幻中“杀人”。作家尤凤伟要写的是主体性意识严重匮乏或曰从未有过,故而行动都无法自我控制的这样一个人。 而在戏剧《董》里,“监守自盗”后是第五出“坟前舌争”,凸显主体间性的灵魂抗辩。具体而论,前面的戏从承诺监视到内心冲突,再到双双出轨,这时的戏还是在两人间展开。到了第五出,活人、鬼魂同台:李氏—彭员外(鬼魂)—董四畏三角戏的冲突变得白热化,将戏剧冲突推向高潮。有自觉理亏良心自责的,有提着“鬼头刀”前来兴事问罪的,有“越轨者”想在坟前忏悔的。结果戏幕甫一拉开,将原本“忏悔会”衍化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会”——对彭员外鬼魂的声讨。对着彭员外一句“真真,你不是人!”[2]23一语双关。人死了,却尸位素餐,还要累死活人,要为死人守活寡。李氏和董生从自责和忏悔中走出来,尤其是李氏,首先大胆站出来,“万千事,莫惶恐,自有妾身能担当。”李氏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受人压制的寡妇,而是变成了一位敢做敢当的女性觉醒者。这时的一介书生董四畏,也变成了“董不畏”,加入声讨行列。一起历数彭员外的诸多不是:“将一个寡妇托付给一个旷男,这是不智;留下夫人却要别人为你守寡,这是不仁。而我与夫人,两两厢情愿,礼也,义也,信也!正义在我手,我们才是合情合理的。”[2]23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剧终。这出戏一气呵成,痛快淋漓。
二、化欲望书写为爱情礼赞
《乌》与《董》,除了体裁不同之外,各自所要表达的主题也有所侧重。换句话说,是他们对同一主题——“人的价值”,从正反两个方面的不同表达。如前所述,两部作品题材相似、情节相仿,都是选取“寡妇”的题材,同时围绕“监守自盗”展开,情节线索大致相仿。作家对相关事件的处理上,通过安排不同的结局,表明了他们对生活理解上的不同,于是他们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审美趣味也各有千秋。
表面上看,二者都属于监守自盗的故事;实际上,两位作家对此的处理上各不相同。尤凤伟写得虚幻,实中写虚,重点剖开那紧裹在主人公躯壳里的灵魂,洞悉那被无形的东西扭曲了的卑微世界,将内心恐惧和精神不安推向极致。于是,在小说《乌》中,故事的发展是由主人公的心理状态维系的。小说着重写对鬼魂的幻觉。这幻觉是人物长期受到压抑而害怕,才将“乌鸦”当成鬼魂的化身,甚至受其役使。王仁杰也写鬼,鬼魂是实在有形的,重在突出现实世界,最后在人鬼对峙中,通过对鬼魂的否定,完成了人的价值的重建,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意识与反抗精神。质言之,小说《乌》的主题是批判性的,新时代的气息仍然无法敲开封闭的山野,传统的观念还在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尤其是女性的地位遭遇到严重的侵害。一个有夫之妇的越轨行为,受伤害的却是女性。而所有的根源,就是背后的田木根——封建意识——“不死的鬼魂”的代表。在这个强大观念的压制下,不管是敢怒不敢言的角色(田三月的老婆),还是敢于追求自由的寡妇,乃至同样受害很深的田三月,没有一个可以幸免。
由此可见,乡村的传统观念和势力的影响力有多么的强大。小说重在凸显观念的力量,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扭曲。如果说,小说的表层故事是在写一个寡妇出轨,以及“监守自盗”,实际上重点在写寡妇丈夫的亡灵是如何无时无刻地主宰着生者,精神的奴役往往胜过肉体的指挥,以至于所有的生者都得不到安生。小说《乌》是一出人性压抑下心灵创伤的悲剧。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改编后的《董》,并没有完全按照《乌》的思想来演绎,而是突出一种女性的主体意识与反抗精神。首先,从《董》中,我们似乎很容易找出相关的女性觉醒的主题。当“监守自盗”后,董生自知闯祸了,如何向彭员外交代?还是李氏率先站出来,勇于担当。随后,董生也跟上。从这里,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面对相同的素材和情节,不同作家善于对场面中细微的特殊性进行开掘、改造,就可以立“意”标新,获得新的审美价值。于是,在剧作家王仁杰的笔下,董四畏的“监守自盗”反而促成了有情人终成眷属。《董》除了要否定传统的节妇观外,更在于传达一种新时代的爱情观,尤其对女性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大胆追求自由幸福爱情生活的称颂。旧瓶装新酒,旧戏写出新主题,可以看成是传统梨园戏的一次现代性的创生。由是观之,梨园戏《董》正是通过人物的矛盾冲突,即人物自身的矛盾心理,以及人物之间的情感矛盾,这些矛盾共同推进戏剧情节不断向前发展,最后达到高潮。因而这是一出正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部作品在主题表达上的不同,这样的不同取决于作家对生活理解的不同。由于对生活理解的不同和判断生活现象的差异,就直接影响着他们对素材的取舍和表现角度。而一个作家善于标新立异,就能铸造异彩缤纷的艺术珍品。
三、化单面符码为多维意象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两位作家在主题表达上的差异。其实,他们除了主题表达不同外,塑造出的人物也各有各的特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有他们自身的情感逻辑。文学创作的构思过程中,故事情节的展开总是伴随着人物性格的发展而来的。而人物形象和性格一旦在作家头脑里孕育成熟,就会循着它的内在逻辑,决定着情节发展的主要趋向。《乌》和《董》两部作品情节相仿,作品的情节线索都是围绕“监守自盗”铺开的。
首先是因人而“异”。作家根据笔下不同人物形象的基调和性格,写的是相同的情节,如“监守自盗”,得出的是不同的情节走向。两位作家是严格地按照文学作品中人物塑造的规律来塑造人物的。正如车尔尼雪夫斯所强调的:“在脑子里阐明长篇小说或戏剧的基本思想,深入到那些通过本身行动来阐释这种思想的人物性格的本质,考虑人物的处境……这才是重要的。”[3]232在小说《乌》中,作家尤凤伟刻画出主人公田三月的性格与剧作家王仁杰笔下的董四畏不同。直观上看,是人物身份的不同,而实质是他们的性情不同。田三月是农民,一个有夫之妇。他既有小农意识的因循守旧,又属于生活重负下(欠村里的钱)的弱小一族,还是一个谨小慎微的小人物。田三月蒙昧无知以及过度的胆小怕事,形成一颗扭曲的灵魂。写田三月的“监守自盗”,当他第一次误判,发现所谓的李青草有“异常”时,田三月差点直接跳进去“捉奸”。[1]406还好,及时刹住。第二次就按捺不住,田三月不管三七二十一:“他一步跨在门前,又一下子推开掩着两扇小小的门。”[1]408作者写田三月的捉奸,没有任何的心理波折与自责,一切是如此的简单而又理所当然,无条件执行,不作任何思考。非常符合这个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即惟命是从,头脑简单。当然,作为一个有夫之妇的“偷情”故事,田三月对李青草,更多的是性的吸引,而不是情的召唤,自然也就不会有后面“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反而当情欲与信义冲突时,田三月只好自断情欲,杀死李青草。同样的情节,《董》就不一样。董生是一介书生,知书达理,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加之对李氏有好感(指情感上),“监视”中就多了一份担心和顾虑,董生的内心复杂得多。《董》中对董生心理刻画显得丰富而多样。在监视时,自觉与书生的身份不符,很丢脸。这已经体现在作家对笔下人物的不同态度上。同样是“狗跟屁”,在《乌》里,田三月做起来是认认真真,老实而不含糊。田三月是把“监视”当成美差,乐此不疲。面对着“奸情”,董生在捉与不捉中徘徊不定,矛盾心理反反复复,剧作家王仁杰刻画得相当生动,一个书生“意趣”就跃然纸上。不仅对人物内心情绪的刻画细腻而富有层次,而且人物情绪的波折紧扣人物的命运。最终的结果是,以年近四十的鳏夫——董生的觉醒,将戏剧一起带进高潮。“偷情”的情节相同,各自的性格不同,从性格塑造的需要取舍情节发展的趋向,“监守自盗”的不同转向,避免情节的雷同。正是立足于刻画人物个性形象来选择展现情节的角度,才呈现出各自故事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两位作家的创作,在这方面获得很大的成功。
其次是同中见异。在相同的情节和场景,作家根据人物的不同个性,向不同角度铺开,写出人物的不同性格,突出两个形象思想性格的差异。两部作品中,从临终托付、履行诺言、险些误判直至监守自盗,情节和场景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两位作家在人物处理上就显示出各自的水平和风格。田三月和董生都是在授人把柄,即欠账下接受“临终托付”的“任务”的。田三月接受“任务”时,心里一直惧怕田木根老头,由怕而尽力。活着怕人,死后怕鬼,迷信使他相信,“鬼魂整治活人不用费力气。”[1]406董生接受时,是一百个不情愿:顾忌着读书人斯文扫地,毁掉一世清名。一个是“惧怕”,由于惧怕,影响到自身安危,给人留下的只有心理的不安与害怕;一个是“不甘愿”,担心的是整个“读书人”的斯文,其中隐约透出读书人的傻气。两个人都是身不由己,但两个形象的思想性格不同一般。类似的性格刻画还有:在“每日功课”里,田三月是踏踏实实,诚惶诚恐,在“狗跟屁”中,田三月还觉得“蛮有些越昧儿,就像电影上我方‘地工’跟踪女特务—般”。而且,还在后面的偷窥中占点小便宜。[1]405至于写到董生的日常监视,在《董》里,是用甲乙学童跟着董生口中念念有词,伴随着董生的视线转移来回摆动的动作来显示,写得妙趣横生。其中还是可以看出同中不一样的地方。田三月是将这事当正事,带有更多的实用主义的眼光,一个农民的实诚。董生的“狗跟屁”,跟得无奈而又滑稽,跟出一副书生的穷酸相来。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作家在对情节的开掘中,总是与笔下的人物的人格秉性相吻合,不仅可以回避情节的简单重复,而且还可以在反复的艺术描写中发展和深化人物的性格。同时,这种同中求异的创作追求,充分体现了不同人物形象的艺术生命力。
四、化文字之虚为舞台之实
《乌》与《董》文体不同,尽管它们之间有不少相通的地方,但是,如何围绕各自的文体规范,按照文体规律进行创作,才是其根本所在。
第一,两部作品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涉及“鬼魂”这一话题。不同的是,一个虚写,另一个实写。《乌》采用虚写。“鬼魂”是主人公恐惧心理的自然延展,也是由于主人公内心恐惧与惧怕而导致的一种心理幻影,其中当然包含相信人死后会变成鬼魂的迷信思想。因此,尤凤伟笔下的鬼魂写得很虚幻,但又显得无处不在。鬼魂犹如主人公精神上的心魔,永远挥之不去。以至于在最后,主人公竟然在所谓鬼魂——化身为“乌鸦”的指使下,完成一次杀人行动。鬼魂是虚的,无形的,不存在的,但又是真真切切存在着的,并且可以指使人的。在《乌》里,写田三月的前后两次“敬军礼”的细节,前者是对人——当民兵指导员的木根;后者是对动物——乌鸦(即所谓的木根死后的化身)。通过以实衬虚、虚实对应、前后连贯的细节描写——下意识的动作流露,昭示出一个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非常符合生活真实。由此可以看出主人公内心受伤害的程度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这样,《乌》就构成了一篇心理小说。作为心理小说,重在展示主人公自我的变态心理,而不是故事中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小说的人物正是在这种心理暗示乃至“指引”下,不断地推动故事向前发展。
《董》采用实写,“鬼魂”即是《董》戏中的一个人物角色,具体而又有个性。从开始阎王爷派出甲乙两个小鬼出酆都到阳间捉拿彭员外(魂),到最后“坟前舌争”中的人鬼对峙(从坟中走出的魂——彭员外),每一个“鬼魂”都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冲突是戏剧中心。”[4]271戏剧需要矛盾冲突,由矛盾冲突来推动剧情发展。《董》通过实写,真切地写出人鬼矛盾。问题还不完全在此,问题还在于《董》作为舞台戏,需要的是人物的动作与表演,无法像小说那样,直接对人物自我进行所谓的心理刻画。于是,在《董》中,“鬼魂”则是作家为了增强舞台表演效果加上去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不同的艺术门类及艺术样式具有不同的规范和要求,两位作家都深得其中三昧。
第二是叙事手法。《乌》是以田三月为视点,用“他”来看和想,李青草只是“被看”的对象,处在被动的从属位置。由此写出田三月内心世界及其心理活动。小说集中要表达的也是田三月的精神世界——一颗精神被极度扭曲的卑微灵魂。戏剧《董》与其不同的地方是,剧作家王仁杰充分发挥戏剧舞台的特性,董生和李氏同台表演,处于平等的位置。与小说不同的是,李氏还不时地走向前台,比如主动送“榴莲”,更有甚者,当出现重大危机时,面对着鬼魂彭员外的责难,李氏更是率先站出来,勇于承担责任,一改传统女性的柔弱性格。也就是说,两个不同文本,采用不同的叙事手法,已经不仅只是艺术手法不同的问题,而同时也是为了主题表达和兼顾到文类的需要,技巧和笔法已经成为了文本的生命组成部分。
注释:
① 王仁杰的梨园戏《董生与李氏》获首届曹禺戏剧文学奖,并荣膺2003—2004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称号。
② 尤凤伟的短篇小说《乌鸦》1988年被搬上电视荧屏,叫《白色的山岗》,给人以很大震撼。
[参考文献]
[1] 尤凤伟.短篇小说集:金龟[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2] 王仁杰.三畏斋剧稿:增订本[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
[3] 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论文学[M].辛未艾,译.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1983.
[4] 余上源:余上源戏剧论文集[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