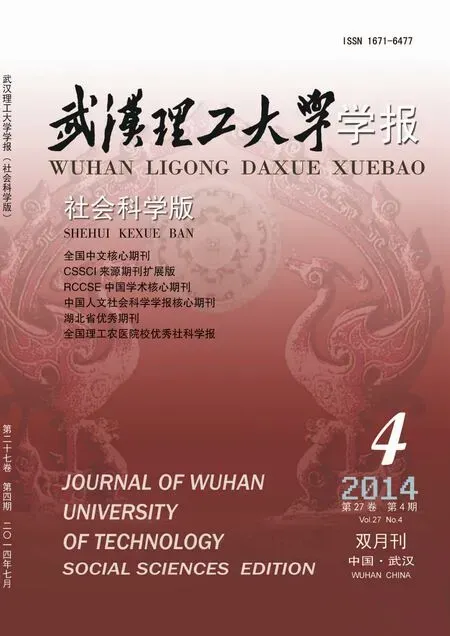唯美与至善: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川端康成与史铁生文学创作之比较
秦 剑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存在主义是西方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它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主观经验。其最先提出的是尼采,在其之后的索伦·克尔凯郭尔、叔本华、雅斯贝尔斯和马丁·海德格尔则可被看作这一思潮的先驱。在20世纪中期它流传非常广泛,法国哲学家萨特和作家阿尔伯特·加缪是其代表人物。存在主义哲学论述的不是抽象的意识、概念、本质的传统哲学,而是注重存在,注重生存和人生。存在主义是把人的存在当作其基础和出发点的哲学,但是,存在主义者所说的“人的存在”,并不是指现实生活中人的客观存在,而是指个人主观的“自我意识”,是指精神的存在,把那种人的心理意识(往往是焦虑、绝望、恐惧等低觉的、病态的心理意识)同社会存在与个人的现实存在对立起来,把它当作唯一的真实的存在。人首先存在着,通过他自己的自由选择而决定他的本质。于此意义上,萨特提出的“存在先于本质”体现了存在主义给予生命最原本的思考和关照。因此,存在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尤为深刻,其中史铁生就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位。无独有偶,生活并创作于异域时空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因其作品中所透析出来的对生命的拷问和冥想在与存在主义殊途同归的同时,也与史铁生及其文学隔海遥对。
川端康成是日本的著名作家,也是继泰戈尔之后东方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一荣耀是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的,获得这一殊荣的川端康成似乎也被束之高阁,成了世人敬仰而无法比拟的神了。而史铁生只是中国当代的一名作家,他摇着轮椅走过属于他的苦难,属于他的荣光,低头沉思的他走过人群时,身后留下的或许只是世人的一片叹息。但是,当轮椅中的史铁生不期遭遇“被束之高阁”的川端康成时,又将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按常理,史铁生似乎无法与川端比肩,但我在这里近乎无理的“拉郎配”,并非要去比较谁取得了更高的文学成就,亦或是谁获得了更高的文坛声誉,只是感动于两位作家都经历过世人无法想象的苦难及他们对生命的思考,对信念的执着。那种抛开一切的最最纯粹而又深刻的思考行为,让仰望他们的我们在内心里除了震撼之外,也有几分沉重和痛楚。
一
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曾经说过:“对于志得意满的人们,文学不会告诉他们任何东西,因为生活已经让他们感到满足了。文学为不驯服的精神提供营养,文学传播不妥协精神,文学庇护生活中感到缺乏的人、感到不幸的人、感到不完美的人、感到理想无法实现的人。”[1]川端康成和史铁生绝不是志得意满的人,尽管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但他们都深刻地体验过来自心理或生理的痛苦,以及经历过特殊历史风云的洗礼。在多舛的命运和混乱的物质世界里,他们是被抛弃的人,无法掌控的宿命和坍塌了的现实,让他们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文学,用一种类似宗教般的虔诚和清静,在文学的世界里建构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家园,文学成了他们精神的皈依。
川端似乎是带着“参加葬礼的名人”这一宿命来到人世间的,而正是这一宿命注定了他童年的悲凉、孤寂及由此带给他永难愈合的心理创伤:幼年时父亲和母亲先后去世,童年时祖母和姐姐相继病故。亲人离去的伤痛在川端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从幼年到少年,川端康成参加的葬礼不计其数,在一次次的葬礼中,他嗅到了太多死亡的气息,而这种死亡的气息在他日后的文学作品中总是或隐或显地飘溢着。
如果说川端的伤痛是在心里,那么史铁生的痛更多的则是来自肉体:21岁时双腿瘫痪,30岁又患上了严重的尿毒症。作为一个普通人,残疾这样一个不幸的事,落到谁的头上,都将是人生的一大不幸。而对于史铁生,身体残疾后病魔又接踵而至,无疑对其是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尽管在肉体上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史铁生并没有就此懦弱地向命运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而是在将文学作为自己精神皈依的同时,又以自己的创作发出对命运的诘问。
如果说,亲人的病故,身体的残疾只是人类自己无法掌控和预料的宿命,那么,当宿命遭遇人祸又将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死亡的气息”尚未消散,川端又走进了更大的死亡阴影——“二战”之中;而史铁生则摇动着属于自己的轮椅,竟“误入”黑白颠倒、人性扭曲的十年浩劫。
“二战”期间,川端一心沉溺于古典文学,好似没有受到战争的干扰,但战后举国浓烈的悲哀氛围,仍就弥漫至川端的心间,外加挚友的相继辞世,他产生了“第二次的孤儿情感”。应该说,川端的哀愁是复杂的,既有对个人前途的忧虑,也有对师友之死的哀伤,但更多的是对战争、战败和战后现实的担忧。
史铁生没有见证过满目疮痍的战争场景,但是他经历过那场民族的浩劫——十年文革。那段苦难,那些留在心间的隐痛,让他在过后的很多日子里一直在反思,并在反思的过程中不断追问着生命的意义,思考着人性的本质,他给予了生命最最深切的关照,那种虔诚,让人感动。
“二战”和文革给人们留下的创伤至今还在隐隐作痛,这些伤口都是人类自己一道一道划下去的,怪不得命运,怪不得上苍。然而,双重的打击并没有让他们就此颓废,反而借助文学仰望苍穹,思考着自己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亲人离去的伤痛是在心间的,川端的孤儿气质塑造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只剩下他一个,那种孤独与悲凉,那在心间留下的沟壑和空白,那充斥着死亡气息的葬礼,让还没好好享受一下人世温情的他过早地看到了生的虚无。承受着病痛折磨的史铁生,伤痛更多的是在生理上,脆弱的身体让史铁生练就了一颗宽容而坚韧的心。史铁生所遭遇的文革与川端康成所遭遇的“二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二战”是人类自己对自己生命的毁灭,让隐居在文学世界里的川端拒绝了对生活对现实的回归,无路可退的他最后选择了自杀——死亡。而在文革中见证了人性扭曲和价值混乱的史铁生,在对生命的积极投入中,重建了他的终极的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
川端康成和史铁生这两个在苦难中的生命沉思者都遭遇过常人无法体会的苦难,虽然二者所处的时代和境遇不一样,但不一样的只是苦难的形式,那种最本质的内核,那些在内心深处留下的伤疤,都是同样地刻骨铭心。
川端的一生都在找寻内心遗失的生命之美,最后甚至放飞了自己的生命去成全这唯一的美;而身体残缺的史铁生,则凭着顽强的意志和对生命的深深眷恋,摇着轮椅走过生命的低迷,用一颗最最宽广和至善的心包容了生死,也还在用自己的日子激励着我们前行。他们在现实的物质世界里所看见、所经历的都是残缺与毁灭,这种类似宿命般的打击和生存的困境让他们无路可退,生命最本能的力量让他们不得不去找寻自我救赎的道路,于是在搁置肉体的物质世界坍塌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文学世界,在那里,他们找到了精神的归宿,构筑了他们渴望的精神家园。但是在两人同样绚烂的文学花园里却开出了不一样的花朵,两人选择的是不同的人生道路,走向的是不同的艺术世界。
二
在川端康成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日本古典文学之美,感悟到了东方之美,他在对美的执着追寻中给予人性以深刻的关照。同样,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他远离尘世的喧哗,用一颗饱经忧患而日益温厚的心去思考人性,在其作品里,我们总能在字里行间看到他对生命的深深眷顾。但是,追求唯美的川端和心怀至善的史铁生在作品中体现的人性观和宗教情怀又是有区别的。
有着不幸童年的川端,人世的温情对于他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在失去了亲情、爱情和友情之后,“情”似乎成了他生命里的一个禁忌,所以对于人性的关照,他投入的情并不深而更多的是在追求一种美,从对美的欣赏和膜拜里不断地丰满着他的精神家园并实现着自己的文学追求和理想。在他的作品中,人性的美特别是女性的美只是作为自然美的一个方面,就是写女性的悲惨命运,也只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停留在对那些弱女子的怜悯和同情上,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呼喊出她们的痛楚和悲伤;偶尔也以轻婉的语言,发出几声哀叹,表现她们的抗争。但这种呼喊是微弱的,抗争也是无力的。他对于这些弱者的希望是抽象的、渺茫的,而悲哀却是具体的、沉重的,这就不可避免地抹上了悲观与虚无的色彩,最终仍然找不到出路。也就是说,川端以唯美的意识和态度来旁观女性的爱,只专注于美,并在唯美的世界里,专注于自己的内心,逃避那些无法解开的生命的死结。
在其成名作《雪国》里,整篇小说都充满着诗情画意,许多场景都可以看做是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川端不仅以生花妙笔描绘了雪国初夏、晚秋和初冬等不同季节自然景色的美,而且将女性的美融入其中,成为自然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雪国暮色和叶子美貌交融的“暮景之境”中,小说写道:“黄昏的景色在镜后移动着。也就是说,镜面映现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好像电影里的叠影一样在晃动。出场的人物和背景没有任何联系。而且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象,景物则是在夜霭中的朦胧暗流,两者消融在一起,描绘出一个超脱人世的象征的世界。特别是当山野里的灯火映照在姑娘的脸上时,那种无法形容的美,使岛村的心都几乎为之颤动。”[2]在这里,叶子的美貌不是单独描绘出来的,而是与自然景色交融在一起呈现出来的;叶子的美貌和自然景色也不是客观地描绘出来的,而是通过岛村的眼睛和感觉“主观地”表现出来的。在岛村的视觉和主观感觉中,女性美与自然美形成一种自然的关联。
其实,对自然的“亲和”是日本文学的一个传统,正如叶渭渠所言:“日本文学对于自然的感受方法与思维模式,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融进投入自然之中,主体的人与客体的自然没有明显的区别,而且把自然看做是相互依存,可以亲和地共生于一大宇宙中。人岂止不需要征服自然、战胜自然,而且要顺从自然,与自然对话,与自然和谐。”[3]应该说,川端康成准确地把握并继承了这一“亲和自然”的传统,致力于描写自然,所不同的是他不是为写自然而写自然,也不是作为作品的点缀而写自然,而是读懂了自然的灵性,感悟到了人和自然的相通。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总是力图将自然和人联系起来,将自然美和人情美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他的作品经常以绚丽多彩的自然风光为背景,以丰富多变的季节转换为衬托,使之与故事情节的推移、人物命运的变化和人物情感的波动巧妙地交织起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川端不仅仅是用笔描写自然,而是用心去玩味自然,用自己的全部感情去理解和领会自然,并赋予自然浓郁的感情色彩。
而史铁生在以个体的生命去体验人生的困境、思索人性的归途时,他突破了个人的局限、时间的短暂和命运的无常,并在精神的引导下,将生命炼成一个永恒的无常。他用一颗宽容和至善的心坦然接受生命所赐予的苦难,也欣然接受生命所赐予的感动。由于苦难他开始思考命运,思考人生,也由此他走进了每一个人的心灵,感受着那份被遗失很久的感动。他曾经说“爱和友谊,要你去建立,要你亲身投入进去,在你付出的同时你得到”,于是他走进了母亲的心灵,读懂了母亲加倍地痛苦着儿子的痛苦;走进了和他一样常来地坛的夫妇的心灵,体味着那份相濡以沫、相依相偎于夕阳中蹒跚的温馨;走进了一个常来地坛唱歌的小伙子的心灵,感悟着陌生而熟悉、相顾无言却已心心相通的真诚;走进了被命运反复捉弄的长跑者的心灵,体会着生命的无奈与坚韧;走进了捕鸟汉子的心灵,感动着艰辛生活中执著等待的那份痴情……史铁生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苦难,走进一个又一个熟悉和不熟悉的人的心灵,以一个富于同情的健全的身心感受着生活无限的机趣,品味着生命存在的全部意义。
与川端康成不同,史铁生不是把人的情感融化在自然之美中,而是把人作为一个有自主意识和情感的独特个体,并用一种感同身受的虔诚,走进世人的心灵,去感受他们的哀伤和喜乐。正因如此,他的眼泪不止为自己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应该说,川端康成和史铁生不同的文学追求,源自于二者不同的人性观和宗教情怀,川端康成是一种超世的生命观,史铁生则是一种入世的生命观。川端深受佛教禅宗思想观念的影响,相信所谓“轮回转世”,生死不灭,生即死,死即生。正如他在《抒情歌》中所说:“佛典所阐述的前世与来世的幻想曲,是无与伦比的难得的抒情歌”,“这个世界,再没有什么比轮回转世的教诲交织出的童话故事的梦境更绚丽多彩,这是人类创作的最美的爱的抒情歌”[4]。死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生的起点。在其作品中,与死亡同时呈现的自然风物也具有别样的美感,死往往被美化为一种生命的新形式,一种超越,且这种超越与人物周围的环境构成了一种和谐的整体。在川端看来,死亡作为一种对生命的自然回归,是最高的艺术,是最美的表现。同时,川端还深受日本传统美学思想“物哀”的影响。“物哀”是人的一种自然感情,同时又是一种唯美感动,超越了是非善恶。它汲取了佛道的“心性说”,将佛教的悲观宿命思想融入了悲哀的情绪之中。因此,在“物哀”的意蕴里,既有着日本民族关于生命欣喜、哀怜的丰富感受,也有着他们对生命如花开花落般短暂无常的沉重悲叹,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关于生命超脱的恒美幻想[5]。在佛教禅宗和“物哀”传统的交互影响下,在生命如流萤般短暂和脆弱的生命体验中,川端似乎更加深刻地体悟到,人之生命和自然万物是一样地轮回着。川端的伤感发端于生命短暂的哀叹,渴念则是哀叹中的憧憬、无望中的希望。
摇着轮椅低头走过人群的史铁生,却是那样的安静,并在安静中思考着忙碌的人们永远也不会在意的事,譬如生命,譬如生死。史铁生的通透,他对人本困境的关怀,他对精神的感悟和执著,他对世事的平和,都不能不让人想到宗教,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宗教精神。在史铁生看来,宗教精神和宗教信仰是有区别的,因为“宗教精神是人们在‘知不知’时依然葆有的坚定信念,是人类大军在落入重围时宁愿赴死而求也不甘惧退而失的壮烈理想”,“是自然之神的佳作,是生命固有的趋向,是知生之困境而对生之价值最深刻的领悟”[6]92。显然史铁生不但坚定地站在终极关怀者的行列,而且把宗教精神看成是救赎的良药。而终极关怀之路永无止境,终极关怀“唯在行愿”,千头万绪都在一个“爱”字上。当史铁生这样思索感悟时,他就走出了困境,并把启示留给人们。
在《命若琴弦》中,史铁生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在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后,他所要面对的是怎样释怀降落在自己身上的种种不幸,怎样救赎自己的心灵,在对人生困境的突围中,他进入审美的境地,获得美的力量,并从中体验到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创造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能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伴随着体验人生困境的大痛苦,史铁生做到了自己期待的那样,“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美着生命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中获得骄傲,从苦难中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7]
史铁生的宗教情怀关照的是生命的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这种以过程为终极意义的信念,让遭遇苦难和不幸的他坚守着虽残缺但坚韧的生命;而川端的佛教轮回思想,看到的只是过程的虚无,因为不管过程怎样精彩,最后都只是殊途同归,而且过程的意义、生命的意义都消解在这生死的循环与轮回中了。
三
如前所述,同样皈依于精神家园的川端康成和史铁生,在他们构建的文学世界里却开出了不一样的花朵,川端的是灰色,而史铁生的应该是绿色。但是,当我们翻开厚厚的泥土刨根寻底时,却发现,用同样的养料——不幸的人生浇灌的文学之花,不一样的只是色彩及色彩呈现的方式,他们的文学之根及文学之实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对生命及其意义的思考和追问。
少时沉思冥想的生活,使得川端没有向人倾吐心声的习惯,即使在他的作品中,在他主宰的艺术世界里,读者也只是略微捕捉到川端的身影,朦胧地体会出川端的思绪。我们可以明确判断出川端作品的特色,但又很难明白那到底是什么。应该说,川端从未将自己彻底释放出来,或许只有孑然孤寂,只有沉思感悟,只有在艺术世界里,川端才能属于自己。所以当成功后的荣誉与声望纷纷潮涌而来时,川端反而厌倦于这些纷扰,并明显地表现出对于喧嚣世界的拒绝。因为再多的鲜花与荣耀也难以愈合他那心灵的伤口,反而由于排异而蛰得很痛很痛。
而史铁生如存在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坚信“人作为一个生命个体,首要的自由选择是生的权利”。身体残疾的他,尽管像一个摔碎的玻璃杯,碎块到处都是,但他没有放弃,因为他遇到了“地坛”,是“地坛”给了他重新将碎块拼凑起来的勇气和决心。当然,这个拼凑的过程是痛苦而漫长的,也许最后还是残缺,也许要用一生的时间,但他似乎都已经不在乎了,因为他知道过程即意义,更坚信前方终归有一团光明在温暖着他孤独的心灵,那光明就是他对前方保留着的依稀的希望,那光明更是他对生命执着的坚守。
拒绝喧嚣尘世的川端选择了拥抱自然,因为在那里,他能静视人生的生老病死,感悟生命之循环,歌吟心中那一抹永不退色的“美”,并最终通过放飞自己的生命,来成全生命永恒之美的悲壮,并向世人诠释了存在的意义。应该说,作为一个唯美主义者,川端毕生都行走在追寻美之踪迹的旅途中,并在追寻中思考,在思考中超越。所以,孤独的他并没有放弃或是厌倦生命,而是在积极地寻找自我救赎的方法,于是,他向世人构筑了一个唯美的文学世界,而他的生命也在这个构筑的过程中,得以不断地升华。
而摇着轮椅走进“地坛”的史铁生,坚信前世的友人在那里等待他,并在地坛的陪伴下,他走进了母亲的心灵,走进了世人的心灵,体验并思考着人生的喜怒哀乐。在体验和思考中,他明白了人生的热度,也从此用一颗愈加温厚宽达的心去坚守生命。尽管在身体倍受病痛折磨时也曾想到过放弃生命,但是,他在死中明白了生的意义,并在死中涅槃而获得重生。在《我与地坛 》中,有两处写到他对“死”的体认:“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边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顺便保证了它们的结果,所以死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8]于是,他不再挣扎于生死之间,而是思考着怎样走完这生死之间的历程,并在《自言自语》中说,“无限的坦途与无限的绝路都只说明人要至死方休地行走,所有的行走加在一起便是生命之途,于是他无惧无悔不迷不怨认真于脚下,走得镇定流畅,心中倒没有了绝路。”[6]87毫无疑问,史铁生超越了生和死的界限,给予存在最大的勇气和力量。
存在主义者萨特认为,人的自由是绝对的,因为人生活在一个孤立无援的世界上,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上帝、科学、理性、道德等对人都不相干,也就是说,它们都不能告诉我们生活的真理、生活的方式,同时,它们对人也没有任何的控制和约束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人有绝对的自由,可以自由地选择生的方式,自由地选择思考的角度。所以,不管是川端康成还是史铁生,不管他们的生命轨迹是如何的不同,但是他们都给予了生命本身最深切的关照,那种对生命最原始意义的探寻,值得我们用整个人生去思考。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人性的光辉,从他们的人生中,我们应该学会的是对美的永不停歇的追求,在苦难面前对生命的坚守。川端的唯美,史铁生的至善,都是对生命之“真”的追寻,路途或许坎坷,过程或许痛苦,结果亦或许悲惨,但这或许才是生命最本来的意义。
论述至此不难看出,由于命运的不幸,使得他们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文学,并从中找到了自我拯救的道路。虽然在他们的文学世界里我们看到了对人性不同的关照方式,看到了不同的宗教情怀,但是他们思考生命的深度却是一样的。应该说,川端的死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对美的成全,他走过的从生至死之间的现实的轨迹,每一步都是认真而深刻的;史铁生的活是一种超越,他思考的从死到生的精神旅途,每一个反复都是人类最原本的生存困境,他在不断的突围中,让我们在充斥着物欲的尘世中,不断逼近自己的灵魂,从而思考着我们存在的意义。
川端用死诠释了生,他的死像是一场隆重的宗教祭祀,庄严而壮美,身边一直萦绕着死亡的氤氲气息的他拒绝了生活,在他皈依的如宗教般纯净的文学世界里,他选择自杀的方式给生命划下了句点,成了世人无法接近的诗性的存在了。东山魁夷在吊唁川端的文章《巨星陨落》里感慨地说:“人们在谈论先生之死时,甚是忧伤,可是我只愿意这样想:倘使围绕先生伟大的生来思考,就会觉得先生的死是安详的憩息。像先生这样的人,毕竟不是世间的凡人,令人感到他是在高处,是一座遥远的孤峰”。史铁生用生来超越死,他的生是在死的涅槃中获得的重生,他痛苦而快乐地活着,用宽广的胸怀拥抱着生活,在他的精神家园里,我们能看到他对生命的信仰和虔诚,他是和我们生活在同样的一个世界里,并在我们遇到生命的困境时给予我们勇气和力量。面对川端的死,我们怀着崇敬肃然而立,但是,平凡如我们,在面对个人或是时代的苦难时,还是应如史铁生一样:“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美着生命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中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7]
[参考文献]
[1] 赵德明.巴尔加斯·略萨谈文学[M].外国文学动态,2003(4):1-3.
[2] 叶渭渠.川端康成小说选[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56.
[3] 叶渭渠.日本古代文学思潮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46.
[4] 吴小华.硝烟中的沉思:论二战时期的冯至与川端康成[M].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0):127-130.
[5] 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M].北京: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6] 史铁生.自言自语[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2.
[7] 史铁生.好运设计[J].天涯,1990(9):23
[8] 史铁生.心的角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