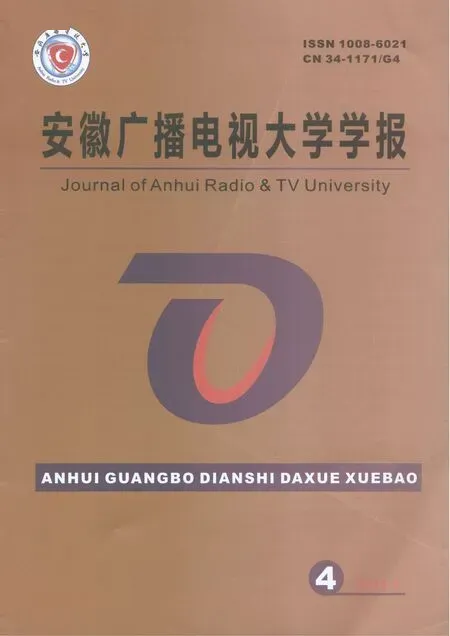“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原则的危机生产
李丹丹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河南 洛阳 471000)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原则的危机生产
李丹丹
(洛阳广播电视大学,河南 洛阳 471000)
对中国当代文学而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最高创作原则的确立有其历史和逻辑的必然,这种创作原则在生产其对文学的正当性同时,也同样生产了无理性。而除却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社会主义文学的危机首先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配合社会主义文学制度化过程中历史势能“自我损耗”和其先锋性褪却的结果。其次,是其生产的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种种二律背反的逻辑推演。最后,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无法为渐趋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类精神图景提供更合理的理由和更深刻的启示的历史局限。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自我损耗;先锋性
据王晓明的考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拉普成员在1929-1931年间从哲学的唯物辩证法移用过来的”[1],其在1932年的苏联正式提出,经斯大林提倡,并以此定名,1934年5月,被写入《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草案》。[2]而这个概念在中国学界传播最早的是周扬在1933年的《现代》杂志第4卷第1期上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之后又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整改、斗争、排斥、净化机制,直到1942 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提出“我们是主张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的”*值得注意的是,1954年,《毛泽东选集》3卷首次出版发行时,“我们是主张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的”这句话,已改为“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此后在国内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的各种版本,凡收有这篇讲话的,都按此修改后的文字刊行。而在此之前,冯雪峰在他为《文艺报》所起草的社论中,业已明确肯定:“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至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才在中国获得了一致认可。,才标志着其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高创作方法的初步形成。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其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准绳才得以确立。而在这个过程中,现实主义前面的定语几经易名,先后经历了“革命的现实主义,浪漫的现实主义”*1939年5月,毛泽东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周年纪念的题词是“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到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程。这个过程与其说是为社会主义文学找到了最合适的创作原则,不如说是社会主义文学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特征为自己量身打造了这个概念。
一方面它极大地修复了经历过五四思想文化洗礼的一代人对自己国家文化无序混乱背后的思想痛苦乃至幻灭感,点燃了一代知识分子对文学秩序的热切期待和重建的向往与希望,统一了文学的理想和信仰,为战时纷乱繁杂的阶级构成确立了较为合理的思想秩序,从而在客观上促成了现代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生成。另一方面,从新文学的发展逻辑上来说,五四新文学并非是包容多元共存的可能性开放体系,对许多作家而言,也并非是理想中的百花文学,它“不仅推动了新文学此后频繁、激烈的冲突,而且也确立了破坏、选择的尺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当代文学并不是五四新文学的背离和变异,而是它的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3]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阶级论”思维最终取代“五四”“人的文学”的“非逻辑性”和“非纲领性”,是中国现代文学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在建立文学的服务宗旨、创作方法、风格基调、题材内容等一系列话语规范的同时,也促生了一个文学秩序的建立,推动了整个文学格局的统一和凝聚,并最终建构了一个时代文学共同的精神内核。所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十七年文学支配性原则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但是任何一种阐释体系都自有其历史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也就是说这个概念在生产其对文学的正当性同时,也同样生产了无理性。也正是这种无理性充分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即使在解除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和造型方法为何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并为现代主义所代替。除却多数学者所论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外,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危机首先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配合社会主义文学制度化过程中历史势能“自我损耗”和其先锋性褪却的结果。其次,是其生产的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种种二律背反的逻辑推演。最后,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无法为渐趋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类精神图景提供更合理的理由和更深刻的启示的历史局限,诚如洪子诚所说:“当革命文学变得同情,靠近现代派,那么革命文学自身存在的理由也值得怀疑了。”[4]
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自我损耗”
洪子诚曾经用“革命文学的自我驯化”来说明“革命文学”走向悲剧性命运的必然性,这就提示我们对此种文学危机和困境的考察,不能仅仅将其归结为政治意识形态单方面的独断强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身的悖论和现实主义与文学体制之间的固有矛盾或许是更需要重视的因素。在洪子诚看来,“‘革命文学’在‘当代’困境的形成,它的过程是一种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自我损害’。”[4]
(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制度的“自我损害”
如果我们承认阿多诺所说的“艺术既是自主的又是社会形成的,这种双重性格不断分布到它的自主性的整个区域”[5]。那么任何一种文学制度都是文学的自律与他律的矛盾结合,既是文学与意识形态弥合和互补的综合性统一物,又是文学与意识形态对立、矛盾、冲突的制衡物。所以文学制度的形成就会始终面临着既要遵循文学自律规律来制定和实施以保障和保护文学发展,又要以其制度化、体制化、法规化的形式对文学进行规范和约束的矛盾悖论。而一个文学制度的良好运转就取决于其始终能够在自身的这种矛盾悖论中寻求一种张力和间距的共生。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其制度化的过程中,因为对“绝对”“纯粹”理性的迷恋,对自己坚守的信仰和概念的强调,不断地生产对感性、个体、审美、差异等经验的不信任,并进行严格地剥离和拒斥,从而使得它内部原本活跃的、变革的思想动力、形式审美之间存在的矛盾张力不断被消弱、僵化,而其最终走向困境,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现实主义先锋性的“自我损耗”
卢卡契在他的《现实主义辩》中通过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将现实主义定义为真正的先锋。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如十七年间那样是保守的、僵化的,而是在配合社会主义制度化的过程中,先锋性不断损耗的结果。这种损耗最主要的就体现在其“批判性”的丧失上。夏中义曾经在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把“批判性”看做是现实主义的精髓。他认为“它是指作家在用人文主义理想来体察现世时的那种清醒智趣或批判意向。”而“现实主义造型法就其精髓而言,本就源于对现存秩序能否永恒这一点深表怀疑或失望。”[6]也就是说,现实主义通过再现现实认识本质的目的恰是要对现实进行批判。可惜的是,现实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制度,并与社会主义结合成新名词进而促进自己“制度化”的过程,正是其“批判性”不断减弱并最终消弭的过程。当然这种先锋性的丧失并不是一个绝对被动的过程,而是一种被洪子诚认为的“自我驯化”的过程,也就是说“‘革命文学’的文学‘原则’、文学方法所蕴含的文学创新,在开始的时候,对原有的文学形态,具有一种挑战性、创新性,在当时的文学格局中,是一种不规范的力量。这种不规范的力量,在它进入支配性、统治性地位之后,在它对其他文学形态构成绝对的压挤力量之后,就逐渐规范自身,或者说‘自我驯化’。”[4]270这种演化应该说是一切先锋艺术的必经过程,因为“先锋”一词本非固定,而是一个向着时间和空间无限开放的概念,所以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的先锋文学,当昔日的先锋在“正典化”“制度化”过程里失去先锋性时,新的先锋元素又会在这种制度中不断生长,从而推动文学的一系列创新,所以与其说这是先锋的悲剧命运,不如说是先锋否定之否定的再创新再生长过程。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二律背反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组成中,“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一个世界观一个方法论,一个意识形态一个创作方法,不仅造成了思维上世界观和方法论两个端点意识形态的矛盾,并且在各自的意识形态中两者又处于不同层面。因此,当两者并列结合,这一概念本身,就携带着缝隙。关于这个缝隙,韦勒克曾做过这样的表述,“在描写和指示之间,真实和教诲之间有一种张力,这种张力逻辑上不能解除,但它正是我们谈的这种文学的特征。在俄国的新术语‘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中,这种矛盾是公开的,作家应该按照社会现在的状态来描写它。但它又必须按照它应该有或将要有的状态来描写它。”[7]这就让这个概念天然地具有了一系列的悖论性。也正如何满子当时的警示,他认为“苏联当年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命题时,究其实际,就是拉普派与反拉普派的一种‘体面’的妥协。”[8]而“文革”文学的出现正是此种悖论不断演绎、激化的结果。
大体说来,这种悖论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真实和教诲之间。现实主义自中国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重教诲、轻真实的倾向。这不仅是传统“文以载道”精神巨大的历史惯性作用,也是基于现代性的焦虑和革命现实的真切需求。所以不仅五四文学“人”的主题和“启蒙”主题,包括“为艺术”的主张,都或多或少地潜藏着深刻的与传统文学牵连不断的社会教化功能,他们都力图将“写真实”与“开药方”“调和”到极致。“从社会的效用,用文艺底感染力这些方面解释……‘真实’和‘感动’只是一件事的两种说法”。[9]如果说,在经典的现实主义观中,真实和教诲并非绝对地不可调和。教诲正是通过对真实的客观描写体现的,写实不是对教诲的放逐,而恰是它的前提。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经过对秦兆阳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统一、李和林“思想性和艺术性”一致,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以及“拨乱反正”时期对“写真实”的重新讨论,当代文艺理论的多次微调不仅没有在真实与教诲之间保持矛盾张力,而且将此张力逐渐夸大,甚至撕裂。其次,现象/本质,普遍/具体,现实/理想,个性/共性之间“典型”的矛盾。在马克思经典的现实主义理论中,典型是链接现象与本质,普遍与具体,现实与理想,个性与共性的桥梁,它通过“忠实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达到对“历史具体性”和“历史规律性”的认识。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人的发展就是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对人的性格的考察也就必然地呈现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具体到文学上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只有描写出呈现“内在规律”的性格,才能达到“历史具体”地描写生活的目的。这与现实主义倡导的客观真实性吻接。但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践中,由于阐释中过于看重社会主义文学的政治功利性,阶级立场上的“典型环境”,对写真实的前提条件的放逐,艺术“典型”的个性化自然也就被忽略了,将个性从本质中抽象出来,“典型”就变成了一些庸俗社会学理论家所谓三阶段论:具体——抽象——再具体的创作公式。“十七年”文学对英雄形象的集中塑造,以及“文革”文学中“三突出”原则的确立,都是这一推理逻辑的延续。
三、现实主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自我损耗”和内部悖论的关注和考察为我们理解其走向“文革”文学的必然性直至最终的困境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如果仅从此出发,也似乎并不能充分解释20世纪80年代之后,现实主义的困境与现代主义的登场之间的逻辑关系。事实上,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现实主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不仅是其加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困境的一个主要动因,也是20世纪80年代经历过“文革”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抛弃现实主义而认同现代主义的主要原因,这主要表现在语言学转向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世界“可知论”“整体性”“本质主义”的怀疑和消解之后不可避免的对现实主义“真实”和“典型”的拆解。
现实主义在19世纪的出现,是伴随着现代性的发生而产生的,它是19世纪启蒙理性、科学、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是建立在对世界可认识论的基础上的,承认现实受科学所构成的规律支配,即世界是一个受因果律、本质律支配的世界,所以现实主义反对浪漫主义的寓言、夸张、想象和古典主义的装饰,进而追求一种客观的现实再现。然而随着人类对人与世界的本质的认识,尤其是到了现代主义时期,关于是否有本质,世界是否按照规律运行,世界和人是否可以被完全认识,这些原来在现实主义看来自明的问题,突然遭到了现代主义、结构主义甚至是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全面质疑。如伍尔芙认为真实远非现实主义所孜孜以求的客观真实,而是关于内心的别一种真实:“生活难道是这样的吗?小说非得如此不可吗?往深处看,生活好像远非‘如此’。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普通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动考察一下吧。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10]如果说伍尔芙对现实主义的否定还止步于以内心真实来对抗,那么法国的新小说派则彻底放弃了现实主义的客观现实和现代主义等的内心意识,而强调物的还原的存在真实:“我们必须创造出一个更实体、更直观的世界,以代替现有的这种充满心理的、社会的和功能的意义的世界。让物件和姿态首先以它们的存在去发生作用,让它们的存在驾临于企图把它们归入任何体系的理论阐述之上。”[11]
此后人们对“真实”的理解趋于多元化,到了20世纪,“语言学转向”之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进而吸纳索绪尔的观点,认为外部现实并不能决定“语言”的意义获得,“语言”也并非人们之前所想象的仅是一个言说和表达反映的工具,而是塑造现实与主体的重要因素。诸如日奈特曾批判说:“述说上的摹仿概念本身显然纯粹是海市蜃楼,人一走近便消逝得无影无踪:语言只能完美地摹仿语言;简言之,话语只能自我摹仿。”[12]也就是说,语言的意义只能是语言而不是它所反映的现实。而对现实主义的“真实”神话进行了更有力解构的是罗兰·巴特。他认为“现实既不是神秘的,也不是荒谬的,而是明朗的,一清二楚的,它时时刻刻被聚集和保持在一位创造者的手中。它经受着创造者的自由的巧妙压力。”因而“现实主义写作远远不是中性的,反之,它充满了书写制作术中最绚丽多姿的记号。”[13]只不过它的隐秘性被叙述者所采用的文学编码程序和读者、意识形态解码程序的高度一致性所掩盖。
所以,当“真实”不复有客观自明性,世界的本质的先验性开始被吊销后,现实主义所谓的“真实”反映客观现实的理论主张就不再有天然的合法性,而尤其是当此种“真实”被证明也依然包裹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人为的操纵性时,“文革”之后对之的遗弃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也正是由于现实主义隐蔽的这种意识形态性和可操纵性,也可以理解同样是20世纪80年代末,“新写实”为何能够借助“现实主义”“真实”这种普通读者最为熟悉也最容易接受的文学理念再一次卷土重来。当然,饶有趣味的是“现实主义”的主战场从当时的权力中心政治领域悄然地位移到了商业领域,然而领域的转变并没有改变“现实主义”所累积的象征资本与文化资本依然处于权力中心的地位。事实上现实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能够继续在“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底层叙事”中顽强存在,本身就说明了现实主义作为当代文坛危机与转型的症候意义。
四、“现实”的多面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深层链接
纵观整个当代文学,可以发现尽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直在努力克服或者遮蔽其生产的无理性,但作为一种客观现实,诸如阶层分化、城乡差异、脑体之别、私人空间、物质追求、个性主义等“异化”现象(周扬曾经提到的经济领域的异化、政治领域的异化和思想领域的异化)却普遍存在,并且越来越突出。而当这些现实被人们越来越普遍地感受到,特别是触及精神层面的,而社会主义依然没有找到很好的疏导或者解决的办法,仅仅把其简单地当做资产阶级思想加以严厉排斥时,这些复杂的感受与西方现代派产生精神上的共鸣和思想上的契合,就不是偶然的。而事实上在严禁时期,学界依然敢于冒险保持对西方现代派的认同姿态,最主要的或许并不是倾慕于其新奇的形式技巧,而是基于现实的一种复杂的精神认同(而此在“文革”后期,地下文学和白洋淀诗人的一些对现代派的认同中,同样可以得到确认)。
事实上,对社会主义而言,现实除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赋予的“集体现实”观,至少也包含着阿多诺所认为的“经验现实”和卢卡契所谓的“异化现实”等不同层面,所以“真实论”才会成为当时文学论争的核心命题。而在“异化现实”的层面上,东西方实际上面临着同样的精神困境和言说对象。特别是当现实已经如阿多诺所言被意识形态“粉饰”成为一种“经验现实”时,现实主义所反映的真实或者现实恰恰就变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瞒和骗”。而“形式主义”的“间离”有可能恰恰是对“异化”现实的批判。诸如现代主义的“孤独的意识通过揭露人的普遍现状便包含了自身消亡的潜在可能性。而这恰恰是真正的先锋派作品所要达到的目标。它们通过自身的形式法则,以审美的方式间接地揭示了社会的本质,以反叛者的姿态对现实存在作了无情的否定,从而使人对这个世界获得更加清醒的认识。”[14]所以在阿多诺看来,西方的现代派所揭示的现实的深度和表达异化的程度,要比现实主义作品有力得多。[15]
而正是在承认和表达真实现实,诸如“异化”以及人在期间的生存状态的描述这一层面上,现实主义和现代派并无根本的分歧(20世纪80年代对现代派的正名实际上正是以此为突破口的),相反基于20世纪更复杂的现代化进程和人的精神脉络的演变,文学精神和文学的现代化和自主意识的内在发展线索上,它们实际上有着更深层的链接。而这也可以解释,当“文革”结束后,现代派之所以成为最有效最受欢迎的叛逆姿态,除了学界普遍认为的对一种精神危机认同的“共鸣”之外,还在于对现代派中人性能够解放、文学能够自由发展的自主意识的向往和追崇。而在笔者看来,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另一种至为珍贵的遗产或许正是文学界这种潜在的文学自主发展意识的始终存在,也就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体化”的文学成规的反抗和突破意识的顽强生存。如现实主义理论在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论争,对现代派的隐秘传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形象思维”的争论中等都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在试图建构新范式的种种艰苦努力,尤其是寻求现实主义和现代派在中国本土道路的可能性的潜在愿望。所以尽管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始终有着一体化的纯净追求,一方面一直存在着对其中异质理念的严厉批判,另一方面却也一直有对文学自主发展追求的存在,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一直没有失却调整和反思自身空间与活力的力量。而当“文革”,当社会主义文学在不断纯化自身阶级教义的进程中,通过对“不纯”因素的剥离而获得了一个纯粹的阶级神话时,也不断抽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内在的血肉和自我调控因素,这既是社会主义阶级论完成其统一文学思想的必然举措,也是它拒绝克服其自身生产的无理性的历史宿命。
五、走向“文革”文学的必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理性的克服实践
从当代文学史的实践过程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其无理性的克服采用的是“阶级论”的思维模式,而当这种思维模式不断地通过其对异质理念的排斥建立起自己的合法化机制时,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优越性和合理性也被纯粹化和抽象化了,同时它也必然埋下了否定自身的种子。因为在“阶级论”的背后,显然是“敌/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关系的严格辨别,并希望通过对这些关系的甄别和清理,来克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在悖论式危机。但是如前所述,阶级论的出现根源于文学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实践的现实需要,某种程度上说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阶级论思维本身的谬误多深,而在于,如果把阶级论思维看作是处理“敌/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唯一有效模式,并进而企图用这一模式解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内外的所有矛盾,就极其危险了。按照蔡翔的说法: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本质性的概念,更多的“是一个各种复杂力量介入形成的生产装置,这一装置既是社会主义的,也是‘现代’的,既是革命的,也是‘革命后’的,既是世界主义的,也是民族国家的……因此,这一装置不仅在生产平等的观念,也在生产新的阶层差别,不仅在生产‘集体’,也在生产‘个人’,既在生产挑战和颠覆的革命冲动,也在生产服从和忠诚的‘革命后’的国家需要,等等。”[16]
所以阶级论的这种危险性首先表现在创作方面,就是“十七年”包括“文革”的众多文本,其实都潜在地隐藏着乡村/城市、集体/个人、私欲/无私、家庭/国家等等矛盾,而当这些矛盾被不加辨析地纳入“阶级论”思维模式,也就是将这些冲突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来自社会主义外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诱惑时,反而掩盖了社会主义内部,特别是社会主义本身生产的这些矛盾的真实利益冲突,因为显然这些牵扯着具体个体生存现实的冲突倘若仅仅依靠对国家、民族、集体等认同,不仅无法获得真正的有效解决,而且还可能积聚起反体制的压抑力量的崛起。而这些,都极可能导致“报复性”叙事心理在20世纪80年代的出现。比如20世纪80-90年代对个性主义、主体自我、日常审美趣味包括个人欲望等的极致展开,或许都部分地源自于此时期“禁忌”心理的反弹。
其次表现在知识分子改造方面,就是在改造和接受之间,不同的知识分子呈现了不同的改造结果,也留下了不同的精神遗产和心理结构图式。陈晓明说:“三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逼迫知识分子舍弃理性的自尊和自持的历史,一部不断逼迫他们向求生的本能屈服的历史。”[17]这种历史境遇使得知识分子可以选择的道路似乎确如其所言的“逃避和依附”。前者如俞平伯等在干校中继承的道家思想,犹如身居世外桃源的逍遥叙事,这种精神上的避险,固然可以坚守人格,却也铲除了反抗思想和实践产生的根基土壤。正因此,王尧也曾说:“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多学问家而少思想家,而这样一种状况就形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大现象: 专制与思想贫弱互为因果。”[18]后者如周扬、郭沫若、茅盾、丁玲等知识分子无论是出于内心的自我选择还是政治权威的迫力,都自觉不自觉地追随政治意识形态对历史的阐释,将建国后的文学紧紧捆绑在政治的马车上,促进了百年来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的形成。但是如果把这些作家精神结构的复杂仅仅简单地等同于历史精神的制约或作家“守”与“退”的选择,也只是涉及了问题的一半,而另一半来自于夏志清认为的中国“传统文人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这一自我暗示性的当代文化指令,这一指令不仅促使作家们情不自禁地将文学作为介入生活、改造社会、完善灵魂的有效工具,也将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当做印证个体存在和书写意义的价值所在。因此在形塑“文革”文学的过程中,革命的价值取向和作家的忧患意识使命形成的某种心理同构,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罹难未尝没有其自身的原因。而这点在20世纪90年代“余杰与余秋雨”关于“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忏悔”的争论中可见一斑。
事实上,如果把社会主义运动理解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内忧外患(内有封建主义、传统旧思想的因袭,外有资本主义的全面渗透)的严峻局势中,摸索前进的艰难实践,那么似乎不难理解社会主义为何有如此强烈的激进的甚至是极端的欲求要求文学、知识分子发挥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数次的整风,大小规模的斗争、批判,与其说是阶级论激进思维的误导,不如说是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文学自我维护的必然趋势,对于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的社会主义文学来说,不断地净化和整肃正是它必须坚持的生产方式。因此每一次的整肃都意味着它朝向自己的目标迈进了一步,也都意味着它是对社会主义生产的危机克服的努力尝试。当然,尽管这种尝试有时可能会偏离原来的目标。所以文学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走到“文革”的极端化,知识分子从正面对抗到“文革”中的集体失语,并不能仅仅阐释为“阶级斗争”的粗暴干涉,而是包含着社会主义自身运动的逻辑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也是对社会主义危机的一种克服和治理手段,当然这一实践也以巨大的牺牲宣告了“此路不通”。但正是因为身后有过“文革”,20世纪80年代的种种设想才有了逻辑起点。至少对文学或者知识分子主体来说,文学作为一个时代先锋的表意形式,或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时代的批判良心,他们所遵循的自身逻辑规律并不可能与政治意识形态同步,有时恰恰是对这种人为的历史实践偏离的纠正。
[1]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75.
[2] 人民文学出版社.苏联文学艺术问题[M].曹葆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13.
[3] 洪子诚.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C]//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卷.上海:上海东方出版社,2003:124.
[4]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81,270.
[5] 阿多诺.美学理论[C]//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陆梅林,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355.
[6] 夏忠义.别、车、杜在当代中国的命运[C]//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249.
[7] 韦勒克.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概念[C]//刘象愚.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36.
[8] 何满子,耿庸.环绕着现实主义[C]//文学对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13.
[9] 俞平伯.文艺杂论[J].小说月报,1923,14(4).
[10] 弗吉尼亚·伍尔芙.论现代小说[C]//论小说与小说家.翟世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338.
[11] 罗伯·格里耶.未来小说的道路[C]//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314.
[12] 杰拉尔·日奈特.叙事的界限[C]//张寅德.叙事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39.
[13] 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C]//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138.
[14] 阿多诺.被迫的调和:评格奥尔格·卢卡奇《反对被误解的现实主义》[C]//柳鸣九.二十世纪现实主义.章国锋,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57.
[15]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讲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2:265.
[16]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25.
[17] 陈晓明.潜流与漩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81.
[18] 王尧.“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J].当代作家评论,2002(1):102.
[责任编辑 陈希红]
CrisisProductionof"SocialistRealism"LiteraryCreationPrinciple
LI Dan-dan
(Luoyang Radio and TV University, Luoyang He'nan 471000, China)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realism as the supreme principle has its necessity in history and logic, but the legitimacy of this principle also produces irrationality to some degree at the same time. Despite the political ideology aspect,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of socialist literature lies firstly in the historical potential energy loss or "self-wearing" and fading of its pioneering in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on with socialist literary institutionalization, secondly, it produces certain logical deduction of antinomy in the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aspects, thirdly, the realism creation principle isn't quite able to provide more reasonable and profound revelation of the growing more complex social reality and human spirit picture.
socialist realism; realism; loss in self-wearing; pioneering
2014-05-15
李丹丹(1982-),女,河南洛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当代文学思潮。
I206.7
:A
:1008-6021(2014)04-008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