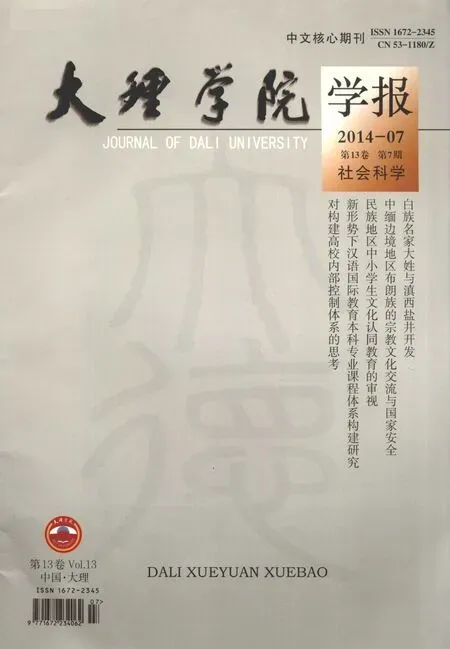白族名家大姓与滇西盐井开发
赵 敏
(大理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滇西横断山纵谷区的沘江、濞水河谷盐井较为集中。在此区域内的云龙县,分布有被称之为“五井”的石门井、雒马井、诺邓井、大井和天耳井。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在云龙设立“五井提举司”作为盐务管理机构,五井提举司下设诺邓、山井、师井、大井、顺荡井、剑川弥沙井、丽江兰州井七个盐课司,五井由此得名。五井因盐井之利,商贾云集,各业盛兴,很早就出现集市贸易。兰州的拉鸡井也曾作为州治及土司府治所。以盐井为中心,盐马古道辐射的地域内出现了剑川沙溪、永平杉阳、云龙漕涧等较为发达的盐市交易集镇。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聚居于此的白族名家大姓成为盐井资源的开发主体。
一、滇西盐井地区的名家大姓
(一)石门井杨氏
盐业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历代外籍人户前来石门落籍,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和盐业经济繁荣。嘉庆十三年举人,曾出任陕西巡抚的石门井人杨名飏就是从石门井走出去的俊才。据清代嘉庆八年《弘农族谱》载:石门井杨氏“原籍山西大同府弘农旧族派衍九隆。前明洪武时始迁大理太和县喜睑上市。”杨氏家族是因盐利而从大理喜洲迁至石门井的。杨名飏在《十二世祖杨当天行述》中记述,“家世以煎盐为业,见有掺和泥土者,切为戒曰:如不足糊口别择一术,不可作此忍心害理之事”〔1〕247。杨氏家族终因盐利而得到兴旺。“先大夫氏杨,讳名飏,字实伯,号崈峰……明初,始祖胜入滇,聚族太和之喜洲。明末,六世祖一诚迁云龙之金泉(宝丰)。国初,九世祖寅儒分支石门”〔1〕243。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杨名飏升任陕西按察使,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任陕西布政使,同年九月任陕西巡抚,授资政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其治秦期间政绩卓著,他主张捐资置田以奖励应试学子,重建书院促进文化教育。筹息谷,修社仓以赈灾荒。因地制宜,发展农业。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他在秦省颁谕《种洋芋法》,要求各府州择地播种。并采买洋芋种一万余斤,分发至延、榆、鄜、绥四府播种,改变了南山一带“多赖包谷以养生”的单一农作物结构。并著《蚕桑简编》以指导秦民,经6年后,栽成桑树64万余株,使养蚕织缣之家获食其利,以厚民生。力主维修“三秦”古建筑,保护文物。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他征集附近官绅士民及桥匠民工,对著名的灞桥进行重建。重修的灞桥在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采用多跨的桩基础石制排墩简支木梁,长近400米,67跨,每跨长6米,宽约7米,基础牢固,造型美观,历120多年而安然凌架于灞水之上。杨名飏离任之时,“秦境士民扶老携幼郊送千五百里”〔1〕248。
回到家乡云龙后,他把“三秦”文化和中原生产技术传播于乡里。他用通俗民歌体写成《劝桑行》在云龙广为流传。诗中道“卒岁无衣怎样好,豳风自有蚕桑道。绮罗岂是天孙裁,全在人工勤织造。”“号寒雪夜空悲迟,劝尔栽桑要及早。盘条最爱春风嫩,采葚须知芒种老。路旁墙下随意插,一片荒郊绿野绕。”这些浅显易懂的农谣在云龙民间深入人心,促进了云龙蚕桑业的发展。由他主要捐资,在同乡马锦文、杨明经两族捐献的田地上建起了“彩云书院”,共置校舍83间,置租谷700余担,共集资银9 420两。杨名飏认为:教育之设“攸治化本源”,故应“以振兴学校为先务”。解职还乡后,他自任彩云书院主讲,为云龙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有《学祀简编》《四书五经字音辨异》《关中集》等著作传世。咸丰元年五月十三日逝世,享年79岁。
(二)宝丰井董氏
云龙宝丰井的董氏为南诏大理国时期的董伽罗尤的后代。据董氏族谱记载:“始祖仙胎伽罗尤,系出大唐。生于洱河东岩上草茅中。仙鸾覆育”〔1〕25。云龙宝丰井《太和寺功德碑记》载:“(宝丰董氏原为)东吴缙绅望族,世家金陵。自唐贞观间筮仕南诏,以咸通元年,奉遗入觐,八年归国,擢布燮官者,鼻祖讳成公也。”光绪十年石门井《重修董氏族谱序》中有:“忆我董氏,自江南金陵县于唐时入滇,始祖董成居大理国,蒙氏举之入朝,赐以清平之官,其后袭职守籍”的记载。咸丰十年宝丰井《宝丰董氏族谱》也对董氏的家世渊源作了记述:“董氏原藉南京应天府金陵县五里桥人氏,始祖府君讳成唐时入滇为南诏清平官”〔2〕72。另据大理喜洲董汝舟家藏《大理史城董氏族谱》记载:“该董氏为唐代南诏国清平官董成后裔,董庆为董成第十二代孙”〔1〕25。综观以上的族谱资料,宝丰井董氏即为大理喜洲董氏家族的后裔。
宝丰井董氏家族的兴起与云龙盐井的开发有着直接的关系。据《宝丰董氏族谱》载:“董庆为云龙石门井及宝丰井董氏的共同始祖。董万章、董万钧均因盐井之利而迁居楚雄黑井,董万卷亦因宝丰井的盐利而迁居宝丰”。宝丰《太和寺功德碑记》说董万卷至探得卤脉灵源,纠合三五大户道事开井。所说的三五大户即包括同宗同姓的董诗、董诏和董诰三支,所以推断当时喜洲董家即为盐业经营大族,不仅开发云龙盐井,还掌握了楚雄黑井的盐利。
董万卷,字宗儒,号怀山,为云龙县宝丰井董氏的一世祖。大约于明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前后,携子董汉纪,孙董邦宪三代从大理喜洲迁居宝丰。董邦宪曾“生平好善,造漾濞云龙桥;建永邑(永平县)之玉皇阁;起太和之宝刹(云龙宝丰太和寺);置报安之小庄,名扬六诏”〔2〕174。
宝丰井的董氏家族于盐井获利后,十分重视公益,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云龙董钦辑《云龙董氏家乘》,比较祥细地记载了时任保山县长的董坊捐资主持在距云龙县一百二十里的沘、沧二江上修建功果桥的事迹。功果桥从民国十一年(1922年)二月动工,至民国十二年二月初步完成。民国十九年(1930年)复修。初次建成的功果桥,桥身长二十八丈五,铁链共十八串,每串连系两头龙窝,约需三十三四丈,地扣平均五斤零,长八寸零。第二次复修,鉴于烈风鼓荡,吹折堪虞,又复添砌一重桥墩,将桥身缩短为二十四丈零,桥墩高四丈二尺,周围约十五丈,铁链系沿旧日龙窝。所耗费用四万多元。功果桥的建造,为云龙盐商行人通往保山等地打通了捷径,解决了澜沧江两岸人民过江难的问题。在功果桥未修造前,云龙盐井商人驮盐销售到保山地区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是经(旧州桥街)飞龙桥过春塘达保山,行程达四百里;另一条是经永平过霁虹桥过澜沧江达保山,行程约三百八十里,而从功果桥上通过,直抵保山则只有二百八九十里。路程大大缩短,且较以上二路平坦,毫不迂回峻岭……功果桥修建主持人董坊去世后,其后裔董泽、董钦呈报民国云南省政府为董坊立祠旌扬,龙云批示“前教育司长董泽之兄董坊,因两度建筑云龙属之功果桥,不惜毁家以达其成,且一生尽瘁开辟狗吊窝及该桥工程,以至于死,实属当代不可多得之人”〔1〕26。
宝丰董氏家族中,深为云龙人所诵扬和铭记的当推董泽。董泽,字雨苍,白族,云龙县宝丰井人,生于清光绪戊子年(公元1888年)。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创建者、首任校长,著名教育家、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教育学硕士,美国伊里那大学经济学硕士,法国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三)诺邓井黄氏
被世人冠之以“千年白族古盐村”美称的云龙诺邓,自古就有“九杨十八姓”之说。“九杨十八姓”现在都是地道的当地白族,但根据各姓氏传下来的族谱记载,由江苏、浙江、福建、湖南、江西、山西等地的汉民陆续迁来,逐渐与当地的主体白族融合成为一个新的群体,他们既保持了中原的文化传统,又吸纳了边地的乡风民俗。是盐利使这里的人口与民族结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生了演化。
洪武年间,明朝中央政府在诺邓设提举司衙门,福建籍黄孟通,江西籍李琼,河南籍李山峰等历任提举先后落籍诺邓。在外来姓氏中,福建黄氏家族对诺邓的发展贡献最为突出。据明代李元阳《明处士黄公孺人段氏墓铭》载:“黄公讳本清,字元杰……世为闽邦邵武郡三十都人。成化二年,公之曾大父黄孟通以乡进士提举五井。”明末,黄文魁首贡并出仕广东提举之后,诺邓文风渐趋鼎盛,形成了“二进士、五举人、贡爷五十八、秀才四百零”的局面。在这些灿若星辰的人物中,黄孟通、黄文魁、黄桂、黄超香、黄翔龙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全都出自黄家。黄氏一门中,又以黄桂最为杰出。
黄桂,字月轩,号清华,生于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黄桂自幼嗜学如饴,熟读经史子集,“挥毫发论,往往别具手眼”“沐其教者,莫不望为山斗。”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年愈47岁赴乡试,中亚元,授昭通府永善县教谕。他学识渊邃,一生留下许多著作,一部分收入《皇朝经世文编》,其中有上书朝廷的靖边之策,受到当朝重视,有的收入《滇系》和《清华文集》。云南最早的诗歌总集《滇南诗略》,收录他的诗词多首,并评论他“诗名噪甚”,是声闻一时的名士,被誉为“滇中一儒杰”。黄桂对振兴家乡教育,培养人才方面可谓功劳卓著。云龙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大井人马锦文曾是他的学生。第二位进士黄绍魁是他的侄子,多受其教益。他和同村贡生杨元复、廪生杨瑗、生员杨秉正等首倡修建了诺邓孔庙和崇圣宫,并设学舍倡教,前后几十年间涌现的大批学子无不因其教侮受益。在开科取士的年代里,黄氏一门的荣耀,古宅纸墨的芳香,曾萦绕过一代代书生的梦,也曾激发过莘莘学子博取功名的热情。
至清康熙年间,诺邓已是“书声响逸、鼓乐喧哗”。乾隆时期,村内建筑及人口已具规模,并在其后的40年里连续出了5位举人。由于大量有着中原文化背景的人士入籍,诺邓人对儒家文化大加推崇,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诺邓人思想信仰的主流。
(四)大井马氏
马锦文,字梅阿,云龙大井人,生于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卒于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原籍江西抚州临川县,据大井马氏族谱载:“远祖来云龙作吏,因爱慕山川之美,落籍金泉(今云龙县宝丰镇),后定居大井。”他“生在异质,聪明绝伦,登乾隆丁卯科举人,壬申科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山东道监察院掌管、广西道监察御史、署户科掌印给事中”(光绪《云龙州志》)。
马锦文入朝供职期间,“正色立朝,敢直抗言,有古名臣风。所上奏章多中时弊。宦官为之敛迹,名震京师。”后人称:“题谏院之名,马侍御直声丕振”,对马锦文为官清正,刚直不阿高度赞誉。马锦文以夙夜勤劳国事,积劳成疾,中年卒于京,为此,乾隆特颁谕“素旗出都门,公卿大臣设酬奠送”,由亲人扶榇归里,所经地方,穿城而过,官绅士民同辞交赞。
(五)沙溪段氏、欧阳氏
盐马古道上的剑川沙溪,历史上曾经是盐马集散的重镇。直至民国年间,沙溪仍是“茶马古道”上的盐茶集散地,南来北往的马帮络绎不绝。沙溪寺登街一带马店、铺台、街面、寨门一应齐备,往日盐马古道上的盐马重镇宏大规模遗迹至今依稀可辨。在沙溪的名家大姓中,江尾村的段氏家族和寺登街的欧阳氏家族最具代表性。
段良(?-公元1585年),沙溪江尾村人,明朝万历年间太学生,曾任万历皇帝太师,被世人尊为“天下贡元”。他告老返乡后,定居在沙溪江尾村,现该村仍保存有段良府第遗址。段良回故里后,整修盐马古道,重整沙溪盐关税卡,征募乡丁,打击盐马古道上的路匪劫贼,加强关、卡、哨的力量,为过往客商和马帮提供安全保证,保障盐马古道的使命通畅。现沙溪四盐卡之一的马坪关上留落下来段姓人家,多为段良的守关人员段氏后裔。段良后裔中学富才高者累世不绝,段良之子段廷用曾任江西建昌知府,段九章曾任海洲知州奉直大夫。
欧阳家族是沙溪有名的“马锅头”世家。“马锅头”是盐马古道上马帮头目特有的称谓。他们是率先在盐马古道盐运中发迹的商人,富甲一方。他们在古道集镇上所建的住宅和马房客栈别具特色,至今保存较为完好。其中,最为知名的有沙溪古镇的欧阳大院。
欧阳家族原为江西人氏,落籍沙溪后其后裔全被白族化。据欧阳家谱载:“始祖子群,江西庐陵明宦官,游至,继承数年则迁于溪……谪垒成金,起房盖屋,生有二子。”家谱中所记“起房盖屋”指的就是兴建欧阳大院,建设者为欧阳景和(见《剑川文史资料选编》)。欧阳景和起初只是盐马古道马帮里的一名普通马夫。由于他善于经营,勤劳节俭,从无到有,从小做大,逐渐发展成为沙溪一带最富有的马锅头。后修建了欧阳大院兼营古道客栈和马店。欧阳大院坐落在沙溪寺登街西北侧,是马锅头欧阳景和于清末民国初所建,为白族典型的“三坊一照壁”式建筑。附属建筑有一排马店,两处花园,整个建筑规模占地1 300多平方米。
欧阳大院门楼为石结构圆拱顶门,上有浮雕石狮装饰。门顶两端雕有花鸟鱼虫,并绘字画,显得优雅而不失大气。门楼两侧的浮雕内容左为农耕,右为读书,衬托有一幅构思精巧的对联:“欧脉钟灵地,阳光丽普天。”将对联首尾四字连起来读便是“欧阳天地”,意喻欧阳天地福光普照,耕读传家。院中的照壁上题写行书“六一家声”四个大字,以唐宋八大家的六一居士欧阳修家门比附,座佑家训,励志后代。为白族民居建筑中不可多得的典范之作。
(六)营盘镇杨氏
澜沧江边的营盘镇东靠拉井,自古就是盐马古道必经的盐市。据1932年缪悔一《沧怒两江见闻录》中记载:“营盘街,是杨武愍公——玉科的故里。为大理、丽江、鹤庆、剑川、维西、兰坪、喇井、泸水、知子罗、上帕等地的贸易中心,是沧江边一大市场……街场周围,瓦房最多,有十字街一条,铺面很多……所有一切洋广杂货,应有尽有”。
杨玉科出生于兰坪县营盘镇,那马人(白族支系)。清同治年间,滇西杜文秀起义军占领了兰坪,控制了喇鸡盐井,以盐利收入作为大理政权的开支。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杨玉科镇压了回民起义,并被清王朝封为将军后返乡兴建营盘街。从剑川等地请来建筑工人,建造住宅,为他死去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垒坟立碑,还为杨姓建造了一所宗祠。他的住宅叫做“爵府”,当地人称为“爵府衙门”,门口挂有“将军第”的横匾,爵府规模宏大,有三个院落,共七十二道门。
他在盐马古道上的家乡营盘街率先修建了两排各约十来间的铺面,邀请剑川、鹤庆、大理等地的白族、汉族商人前往经商,做生意。在杨玉科住宅周围,逐渐形成一个丁字形的街道,杨玉科将此街道命名为营盘街,街道上有大小店铺近百家。使营盘街成为滇西北一带各族人民进行商品交换的较大集市。到这里进行交换的,除了大理、下关、保山、丽江的商人外,还有澜沧江两岸的傈僳族、那马人,碧江、福贡的傈僳族、怒族和勒墨人。当地绝大多数傈僳族和勒墨人。从营盘街形成之日起,就到营盘街交换各种物品,以满足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直到现在,营盘街还居住着不少汉族、回族和剑川、鹤庆的白族居民,他们的祖先大多是从外地迁来的。
与此同时,他举力兴办学校,在营盘街创办了“沧江书院”。他捐献年收地租七十二石的田地,作为书院基金,主要支付教师的薪金和书院的杂费。“沧江书院”在辛亥革命后改成包括初小、高小的小学,经常有学生百人左右。学生可以在校寄宿,伙食自理。学校免收所有学生的的学杂费。
二、白族名家大姓与盐井地区社会发展
洱海区域盐井地区经历了无数风云变幻,有的盐井地曾几易其主。但始终不变的是,在滇西盐井区域生存和发展的族群及其文化互动与调适莫不围绕着盐这一核心物质。各民族正是在盐井地区长期相互调适与融合,走向最终的民族认同。南诏大理国时期,这种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民族融合和调适文化认同的传统就已经形成。南诏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上层分子到统治集团之中,在南诏统治集团中,就有白蛮、汉族、傣族和么些等民族成分。《南诏德化碑》碑阴所载官吏题名,白蛮贵族可见姓或名者64人,其中有段、杨、尹、赵等姓者37人,占总数过半〔3〕。
在近代盐井地及其辐射的盐运盐市集镇的族群结构变化和民族变迁中,这一特点更加明显。许多盐官、盐商在盐井地区长期落籍,孕育出了一大批白族名家大姓。不管他们的祖先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在洱海区域盐井地区,他们已经完全认同于白族之中,并发展了白族的内涵,已然成为了白族中的精英,标画着白族文化发展的方向。明清时期,这一族群以“明家”或“名家”自称。有学者研究认为白族人以“明家”自称,是因为他们的祖先血统中有古“昆明人”成分;有学者认为白族以“名家”自称,是因为他们是西南少数民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从而贯之以汉姓的有名有姓的族群。经过历史融合后的白族既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认识和利用盐泉的“昆明人”的后代,也是较早认同于先进的汉文化特殊民族。“文明没有财富是建造不起来的,而财富本身有两种表现,一是绝对的,另一是相对的。换言之,文明的基础是财富在绝对程度上的累积。很贫乏的文化,很难产生我们在历史学或考古学上所说的那种文明。另一方面,仅有财富的绝对累积还不够,还需要财富的相对集中。在一个财富积累得很富裕的社会里面,它会进一步地使社会之内的财富相对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这少数人就使用这种集中起来的财富和大部分人的劳力来制造和产生文明的一些现象”〔4〕。白族盐井地区名家大姓的出现,就是因为盐这一财富资源导致的必然历史结果。也正因为名家大姓的崛起而推动了白族盐井地区社会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为后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文明印记。
其一是改变与整合了白族盐井区域的人口结构,调适了族群认同内涵。
历史上,滇西盐井地区的汉族移民主要有因担任历代朝庭官宦流寓,因商流寓或因军屯而流寓等情况。“州为彝壤,自设流迁治后,汉人慕煎煮之利,多寓焉”〔5〕。迁入滇西盐井地区的汉民数量有限,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对优势,因而在文化涵化过程中主要体现为汉移民较多地丧失他们的民族特性,变服从俗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但是,这一涵化过程并非单向的汉移民被夷化的过程,汉移民文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继续在盐井地区发挥着其涵化功能。
汉族的移民文化隐去其显在的文化特征来适应白族文化,并逐渐跻身于白族的意识形态圈,潜移默化地发挥着涵化的功能。汉族移民文化强调了土著白族文化中所缺乏的内容,即族群的祖源合法性及社会等级性。在汉文化与白族文化整合过程中,汉族移民文化实现了白族化,白族文化中也带有了汉文化因素,相应地在汉移民被夷化的同时少数民族也因其文化中吸纳了汉文化特质而产生区域性涵化,特别是对汉移民先进的生产技术,劳动工具和参与科举等文化特质的吸纳。滇西盐井地区在名家大姓统领下,关系已经非常密切而很难区别了。汉户最终消失在盐井地的白族之中,夷汉相互涵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关系密切而难区分,至明清时期,大都以“名家人”(或明家人)来称呼这一正在融合中的民族群体。
其二是引进了相对发达的观念和技术,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盐井区域的经济社会结构。
云龙石门井杨名飏回到家乡后,把“三秦”文化和中原生产技术传播于乡里。他用通俗民歌体写成《劝桑行》在云龙广为流传。浅显易懂的农谣在云龙民间深入人心,促进了云龙蚕桑业的发展。宝丰井的董氏家族引进先进技术,在盐马古道必经的澜沧江上修建了功果桥。董泽将私产大栗树嘎窝田庄捐赠给家乡用于发展教育,资助创立云龙县第一所农业职业学校。在县级举办中等专业学校,这在滇省亦为罕见。至1952年,云龙农业职业学校改为公立,并入云南省农校,培养了一批云龙籍的农业技术人才。营盘街的杨玉科在盐马古道上的家乡营盘街率先修建了两排各约十来间的铺面,邀请剑川、鹤庆、大理等地的白族、汉族商人前往经商,做生意。促进了盐井地区民间商贸的发展。
其三是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文化,从而冲击、整合了盐井区域的白族文化。
由于各名家大姓迁居白族盐井地区,且多为“中原衣冠”的名门士族,有的本身就是宿儒名宦。他们一方面严守谱系,完善盐井地区的宗法文化;另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白族盐井地区传播儒家文化,敦进儒学文礼。白族盐井集镇较早地设立了书院庙学。康熙至雍正间,云龙州的义学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康熙二十八年,知州丁亮工始设于福隆寺,后生员尹道南、尹文林捐屋一所,在州治东北。四十五年,知州毕仕魁见其狭隘,捐俸买其旁地,重建书舍,颜曰‘教育堂’。五十二年,知州王氵符捐俸设馆,知州李元英因之。雍正三年,知州陈希芳设传心、修瓴二书院,更于天耳、诺邓、江外分设,训诲子弟,以广文治”〔6〕。剑川州的乔后井、弥沙井亦先后设立书院。“弥沙井馆(义学馆),在城西南一百六十里弥沙井昭应寺。雍正七年,大使闻韶设,每年束修银十两,今就桥头关圣宫,改为和羹书院,束修银十八两……新设乔后义学三馆,皆在乔后井,光绪三年设,由盐井厘金公费内岁共给束修脩银六十两……新设乔川书院,在城南一百三十里乔后井。光绪三年设,由盐井釐金公费内岁给束脩膏火银六十两。新设敷文馆,在乔后大村,同治十二年地方公建,铺面岁收租钱二十四千以作束脩”。“雪斑书院,在兰州求仁甸(今剑川马登镇)”,见光绪《剑川州志》。
白族名家大姓对盐井的经营促进了滇西盐井区域人口、经济和文化这三大过程的整合与变化,使偏于一隅的白族盐井地区社会进入了“略与中夏同”发展层面,为祖国西南边疆各民族的融合与国家认同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1〕云南省编辑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四[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2〕陈云华.董泽〔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
〔3〕孙太初.云南古代石刻丛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59-61.
〔4〕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90:199.
〔5〕黄金鼎,李文笔.千年白族村:诺邓〔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