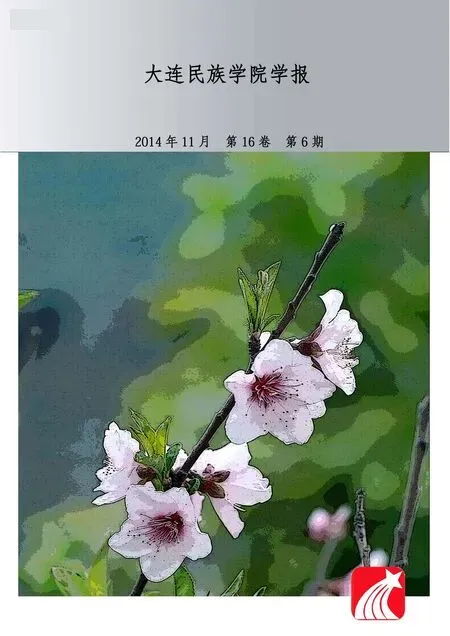盛京文化的形成与特色(之二)
张佳生
(大连民族学院 满学研究所,辽宁 大连116605)
一、起源于盛京的八旗科举
八旗制度建立之后,八旗在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都有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新满文的推行与使用,使八旗中满族人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随着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对文化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急迫。在这种情况之下,皇太极于天聪八年(1635)四月在盛京举行了第一次八旗科举考试。这次考试意义重大,开启了八旗科举取士的先河。出于对不同文化人才选用的需要,这次考试没有规定只许用满文,或者只许用汉字及蒙古文考试,而是三种文字同时使用,考生可选择擅长的文字进行科考。史料记载了此次科举的情况。
取中满洲习满书者刚林、敦多惠二人,汉人(即乌真超哈,后改称汉军——原注)习满书者宜成格,汉人习汉书者齐国儒、主灿然、罗绣锦、梁正泰、雷兴、马国柱、王来用八人,蒙古习蒙古书者博特、石岱、苏鲁木三人,共十六人,均赐举人[1]148。
有些不久即得以重用,如刚林后任国史院大学士,罗绣锦任国史院学士。
在八旗入关之前,还举行了两次科举考试。一次是在崇德三年(1638)八月,这次科考不仅考取举人,也考取秀才(生员)。《清太宗实录》记载,此次科举考试之后:
赐中式举人罗硕、常鼎、胡球、阿济格毕礼克图、王文奎、苏弘祖、杨方兴、曹京、张大任、于变龙等十名,朝衣各一领,授半个牛录章京品级,各免人丁四名。一等生员鄂谟克图、满辟等十五名,二等生员铿特、硕代等二十八名,三等生员费齐、温泰等十八名,名赐紬布,授护军校品级,已入部者免二丁,未入部者免一丁[2]。
此次科考录取的举人、秀才达到71 名,比前次有所扩大,这也说明在八旗中习文者越来越多。
另一次科举考试是在崇德六年(1641)六月,这次科考也是招考生员和举人,史料对此次考中的生员和举人数额没有具体记载,只记载了:
赐新中举人满洲鄂貌图(鄂谟克图)、赫德,蒙古杜当,汉军崔光前、卞三元、章于天、卞为凤,各缎朝衣一领[1]149。
以上新中举人都是原来就在八旗中任职者。如鄂貌图即是在崇德三年科考时取中的生员,并一直在文馆任笔帖式,所以此次考中举人赐给朝衣。这次考中的生员应不在少数。
八旗入关前的科举考试虽然次数不多,取士人数也很少,但是其中不少人都成为了清代名臣。
首次科举考中举人的刚林,中举后任职文馆,崇德元年(1636)授国史院大学士。入关以后赐“巴克什”号,任纂修《清太宗实录》总裁官,很得重用。第二次科举中式者也不乏名臣,如罗硕,正白旗满洲人,中举后任刑部理事官。八旗入关后,官至工部侍郎。
第三次科考中举者鄂貌图,正黄旗满洲人,自幼习文,在前次科举中曾中诸生,此次中举人第一名,任内秘书院学士。在军旅间十余年,有文武才。鄂貌图是最早的满族诗人,著有诗集《北海集》,是被当时诗坛领袖人物王士禛称为“满洲文学之开,实自公始”的人物。
八旗入关之前的科举对入关后八旗科举的兴起和制度化奠定了基础。
在顺治八年(1651)六月,国内局势稍见稳定之时,清廷决定举行八旗入关后的首次科举考试。这次乡试、会试规定了录取名额。乡试取八旗满洲50 名,蒙古20 名,汉军50 名。会试取八旗满洲25 名,蒙古10 名,汉军25 名,随后又增加了25个名额。八旗考试的内容与汉人不尽相同,八旗乡试为八旗满洲和八旗蒙古应试者,通满文者作满文文章一篇,通汉文者翻译汉文一篇。八旗汉军人应试者与汉人科举一致。八旗满洲、蒙古会试考试,则是通汉文者翻译汉文和用汉文写作文章各一篇,只通满文者作满文文章两篇,汉军如汉人之例。会试于次年即顺治九年(1652)三月举行,实际共取中进士70 名,此榜前三甲为满洲麻勒吉、折库纳和巴海。
顺治年间大约每三年举行一次乡、会试。不过八旗只在顺治十一年(1654)举行了乡试,十二(1655)年举行了会试,至顺治十四年(1657)就停止了八旗科举考试。
到了康熙二年(1663)恢复了八旗乡试,但没有举行会试。此后整个康熙和雍正朝的八旗科举考考停停,多有变化。不过康熙三十六年(1697),开创了宗室应试的先例。雍正元年(1723),首次举行八旗满洲、蒙古的翻译科举考试,八旗科举到了乾隆朝才正规起来。从康熙初年开始对八旗应试者作出了马步箭考验合格者才可应试的规定,八旗士子科举的难度有所增加。
八旗科举制度的实行还不仅仅限于文科,康熙四十八年(1709)开八旗汉军武科乡、会试之制,并于康熙五十年(1711)举行了乡试,次年举行了会试。雍正元年(1723),命八旗满洲和蒙古应试武科,此年取中八旗满洲、蒙古武举人24 人,八旗满洲武进士2 人,蒙古2 人。
八旗科举虽然在形式和时间安排上与全国的科举考试相同,但是考试的内容却有区别。八旗科举考试内容是以“国语骑射”为核心,除文科八旗应试者需先考马步箭外,武科也以骑射为主,不过难度要高了许多。而翻译科考试则单为八旗满洲、蒙古而设,主要考满蒙文义及翻译能力,培养专业的满蒙语文人才。这种八旗科举制度为坚持“国语骑射”的民族根本,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八旗的科举制度兴起了盛京,在他们入关之后逐渐完善,既成为了旗人的进身之阶,也促进了八旗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有清一代八旗中涌现出众多人才,便是最好的证明。
二、盛京的八旗教育
盛京的教育尤其是满文教育起始于八旗教育制度,这种不同于汉人社会的教育制度,不仅对提高八旗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对盛京地区乃至整个东北的文化发展和文化走向起到了重要影响,并成为东北特色地域文化形成的一种因素。
盛京的八旗教育兴起于满文创制之后。后金天命六年(1621)三月,八旗攻占了辽河以东包括辽阳和沈阳的广大地区。政权的不断稳固和统治地区的扩大,对文职管理人才数量的需求迅速增加,对八旗的文化素质要求也成为政权发展的一种要求。在这种形势之下,八旗的教育开始兴起。此年七月,努尔哈赤下令在八旗中选派八位师傅教授八旗子弟。《满文老档》记载了这项命令。
命准托依、博布黑、萨哈廉、乌巴泰、雅星阿、科贝、札海、浑岱等八人为八旗师傅。八位巴克什尚精心教习尔等门下及所收子弟,教之通晓者赏之,弟子不勤学不通晓书文者罪之。门下弟子如不勤学,尔等可告于诸贝勒。该八位师傅,无须涉足他事[3]。
从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教育的这样几种情况:第一,当时的八旗社会已经出现了一批精通满语文的文化人才“巴克什”,他们成为实行八旗教育的先决条件。第二,八位师傅是专职教师,只负责教育八旗子弟而无须承担其他工作。第三,“门下及所收弟子”是专职学生,对他们的学业要进行考核。这种教育已经具备了教育制度的基本要素,这也是正规八旗教育的开端。
到了皇太极执政时期,对八旗子弟的教育更为重视,天聪五年(1631)曾严格命令八旗大臣子弟15 岁以下,8 岁以上,俱令读书,如不读书不允许披甲出征。为了强化八旗教育,天聪六年(1632)正月,胡贡明建议正式设立八旗官学,扩大教育范围。他在奏书中说:
以臣之见,当于八旗各立官学,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学读书,使无退缩之词,然有好师傅,方教得出好弟子。当将一国秀才及新旧有才而不曾作秀才的人,敕命一二有才学的,不拘新旧之官,从公严考。取有才学可为子弟训导的,更查其德行可为子弟样子的,置教官学[4]。
胡贡明提出设立八旗官学建议之后,八旗官学开始在盛京建立。然而正规的八旗官学始建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此年建奉天府左翼官学与右翼官学各一所。(所谓左、右翼即八旗分为两翼,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为左翼。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为右翼。)每旗各选10名学生入学,学额共80 名。学生有专习满文者,有满汉文兼习者,并都有马步箭的课程。康熙三十年(1691),设盛京八旗官学,于左、右翼各设八旗官学两所,学额共80 名。这些学生都是各旗选取的俊秀幼童,由朝廷供养。同时又在盛京设立八旗义学。
八旗义学具有普及性。凡八旗子弟十岁以上者,各佐领于本佐领内各选一人。满洲幼童,教习满书满语。蒙古幼童,教习满洲、蒙古书,满洲、蒙古语。汉军幼童,教习满书满语。并教习马步箭[5]。八旗义学的举办使八旗子弟有了更多入学的机会。
盛京宗学始建于乾隆二年(1737),是为在盛京的宗室和觉罗设立的。(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及其兄弟以下子孙称宗室,其他旁系子孙称觉罗。)入学规定为凡宗室、觉罗子弟年20 岁以下,10 岁以上,均可入学,不限额数,学习内容与八旗官学相近。
以上这些八旗学校在清代一直坚持办学,也因此培养了一批东北地区的八旗文化人才。只是到了光绪初年,随着政局的恶化,八旗学校才逐渐衰落下来。至光绪末年新学兴起,八旗各类学校逐渐改建为新式学堂。
清朝在盛京举办各类八旗学校有着许多重要意义。
其一,开创了沈阳地区官办教育的先河。在此之前,沈阳地区从未有过官办教育,在盛京八旗官学建立之后不久,吉林、黑龙江两地也相继设立八旗官学,官办学校遍布东北三省,而盛京的八旗学校最为重要。
其二,坚守了“国语骑射”的民族传统。八旗入关之后,满族传统与文化逐渐淡化,是东北的八旗学校在坚守中延缓了这种趋势的速度。在今天东北包括沈阳地区仍能找到满族传统与文化的种种表现,这应该说与清代八旗学校建立后对文化人才的培养有一定的关系。
其三,为各地驻防及政府部门提供了人才。在八旗学校创立之前,旗人尤其是中下层旗人基本没有受文化教育的机会,而各地八旗驻防和各衙门对精通“国语骑射”人才的需求却亟紧迫。盛京八旗学校的学生同京师八旗学校的学生一样,具有考取生员、举人和进士的资格,考中之后可得到相应职务。
其四,改变了盛京地区文风不振的现象。八旗学校兴办之后,盛京地区和奉天府境内的府学、县学和书院,也都有了相应的发展,这些学校与八旗学校一起为盛京文化的兴盛作出了贡献,直到今天沈阳仍然是东北地区的文化中心。
盛京八旗教育悠久的历史和所具有的鲜明特点,不仅为清代盛京和今天沈阳的地域文化增添了魅力与色彩,而且成为了民族深厚的历史记忆。
三、结 语
盛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特定的历史环境与条件,这种环境与条件与满族的崛起、八旗制度的建立,以及汉、蒙古等民族的积极参与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一种地方文化特别是都城文化的生成,需要方方面面的条件和长时间的积累方能实现,因此促使盛京文化形成繁荣的原因与条件并非仅来自一二个方面,不过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的主要方面,这里所说的几个条件对盛京文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八旗入关之后,盛京仍具有陪都的地位,满族一直将其视为“发祥之地”进行管理和建设。在整个清代,盛京文化即与京旗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同时也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在了解和研究这种文化的时候,应该给予更多理解,应该对这种文化存在的价值给予更多的尊重。
总而言之,在清代形成的对今天仍有影响的盛京文化,是一种经过多民族无数人努力参与,又经过时间的磨练才形成的独特文化,它的存在与否,以及今后的走向决定在今人的手中,在研究这一课题的时候这个问题不能不令人深刻思索。
[1]福格.听雨丛谈:卷7[M].北京:中华书局1984:148.
[2]清太宗实录:卷43[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1.
[3]满文老档: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0:218.
[4]天聪朝臣工奏议[M]. 印本.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1980:11.
[5]奉天通志:卷150[M]. 沈阳:沈阳古旧书店,1983:3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