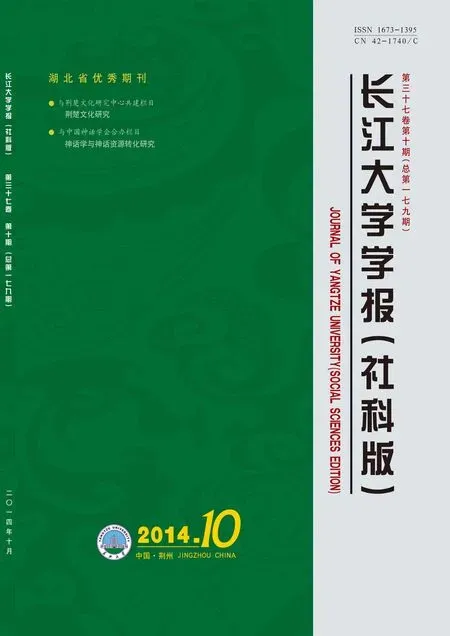《水浒传》与《天龙八部》之比较
刘开田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水浒传》是金庸年轻时最爱读的小说之一。他自己曾说,他的《书剑恩仇录》就是学《水浒传》而写成的。杨兴安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直觉上感到与传统小说接近的是《水浒传》。”[1](P132)《天龙八部》作为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作品,与《水浒传》的关系最为密切。
一
小说以塑造人物为中心,因此,在小说的主要人物身上,往往寄托着作者所要传达的主旨思想。下面试以宋江和乔峰两个人物形象为例,分析《水浒传》和《天龙八部》两者主旨之间的异同。
历史上的宋江与《水浒传》里的宋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历史上的宋江,无论是出现在正史还是野史里,其身份均是“盗”、“贼、”“寇”。宋史卷22《徽宗纪》载:“宣和三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宋史》卷351《侯蒙传》载:“宋江寇京东。”《东都事略·张叔夜传》载:“会剧贼宋江剽掠至海。”至于宋江的性格,元代陈泰《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里有这样简要的记载:“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在《水浒传》里,施耐庵对相关历史进行了改造,宋江的身份变成了山东郓城县一位刀笔小吏,其性格特征则由勇悍狂侠演变为忠义双全。上梁山前,宋江身上主要体现的是义。宋江能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结交天下豪杰。明知晁盖劫取生辰纲,犯下了弥天大罪,宋江仍“担着血海也似干系”,冒险私放晁盖。为了救自己的朋友兄弟,宋江知法犯法,置国家法度于不顾,置个人性命安危于不顾,义字当头。《水浒传》集中描写了三次聚义,分别是第15回晁家庄聚义,34回清风寨聚义,40回白龙庙小聚义。在这几次聚义中,宋江正是凭借其“呼保义”的声望,把众多英雄好汉都鼓动上了梁山,正如第55回所说:“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而在上梁山之后,忠在宋江的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义则退居其次。当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后,他把梁山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进一步明确了梁山队伍“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肱骨,一同替天行道”的基本宗旨。故此,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道:“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是《水浒传》的第一大关键,读者不可草草看过。”受招安后,宋江改“替天行道”大旗为“顺天护国”,接着征辽,讨田虎、王庆,平方腊等,都是他在脚踏实地地实践“一心报答赵官家”的愿望和理想。
《天龙八部》有三个主要人物:乔峰、段誉、虚竹。但毫无疑问,乔峰才是其中的核心人物,金庸正是通过乔峰这个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侠义情怀的。读者对乔峰最为深刻的第一印象便是义。 小说除了主要描写乔峰、段誉、虚竹三个结义兄弟生死与共的情谊之外,还为乔峰设置了一个个感人的情节。第15回杏子林中,丐帮四位长老图谋叛乱,欲杀死乔峰,但事情不谐,被暴露后罪当处死。乔峰以“帮主流血,代人受过”的义举,以德报怨,宽恕了四位长老的行为,化解了帮内的重大危机,而其表现出来的江湖侠义,也感动了丐帮兄弟。在第19回,乔峰为了救一个无亲无故的少女阿朱,只身冒险赴聚贤庄,险些丧命。在27回,乔峰单骑冲入辽营,射杀楚王,生擒皇太叔,解了结义大哥耶律洪基之危。胸襟开阔,意气豪迈,打抱不平,仗义相助,这就是金庸笔下的乔峰。乔峰的义只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而真正感动读者的,则是乔峰的忠,以及因其忠而带来的人生悲剧。41回在少林寺大战情节的结尾,当慕容博以让乔峰报母仇作为复国交易时,乔峰说道:“你见过边关上宋辽互相仇杀的惨状吗?你见过宋人、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景吗?……我萧峰对大辽尽忠报国,是在保土安民,绝不是为了杀人取地,建功立业。”乔峰此等以天下苍生为念之心,连少林寺得道高僧都赞许不已:“天下英雄,惟乔峰是尔。”然而,追求忠义的乔峰,在雁门关外,当不得不胁迫义兄耶律洪基退兵时,说道:“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既不忠,也不义,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最终以箭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而宋江在临死前也曾表白:“我为人一世,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宋江和乔峰,共同演绎了一曲忠义的悲歌。
由此可以看出,《水浒传》与《天龙八部》这两部小说,把侠文化中的义与儒家文化中的忠相结合,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忠义。正如金庸在《金庸作品集·新序》里所说的:“我希望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帮助,重视正义和是非,反对损人利己,注重信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地为了正义而奋斗。”[2](P3)
需要指出的是,宋江与乔峰的忠存在着内涵上的差异。宋江的忠,体现的是其对赵家王朝的尽忠,这是受到封建时期家天下思想影响的结果;而乔峰的忠,既非对赵家王朝,也非对契丹国主,而是对于天下百姓。为了天下百姓的安乐,乔峰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天下一家思想的集中体现。身处元末明初时期的施耐庵,不得不受到家天下观念的影响,而金庸则不同。深受现代文明影响的他,对忠的理解,更多地体现在对天下百姓疾苦的关注上,此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也。
二
《水浒传》与《天龙八部》的情节结构极为相似,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金庸对《水浒传》结构的继承。
《水浒传》的情节结构基本上是单线纵向式。施耐庵吸取了《史记》纪传体的特点,小说的上半部以人物为中心,由数十个独立单元连缀而成,直至第71回梁山英雄排座次而结束。在这些以人物为主的独立单元中,其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方式,是各自为之立一篇小传,如2至3回是史进传,3至7回是鲁智深传,7至11回是林冲传,23至32回是武松传等。如此形成一个个人物分传后,小说再在第71回安排众人啸聚梁山,从而完成诸多人物的合流。同时,这些独立的人物单元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由上一单元的人物引出下一单元的人物,上下贯通,环环相扣。这样就形成了钩锁连环式的结构形式。小说的下半部则以事件为中心,主要写梁山接受招安,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平方腊的故事。《天龙八部》也是由一系列的人物传记排列组合而成,每一篇传记以一个人物为中心,形同《水浒传》中的人物分传式。全书共50回,主要围绕三个主人公乔峰、段誉和虚竹来叙事。《天龙八部》对这三个人物经历的描写,相当于《水浒传》中的108将人物分传。《天龙八部》从第1回到第14回,以段誉为中心叙事,相当于段誉传记;第15回到第30回,转以乔峰为中心,相当于乔峰传记;第31回到第40回,以虚竹为中心,相当于虚竹传记。小说随后描写少林寺大战,乔峰、段誉和虚竹齐聚少室山,寺前结拜,力战群豪。至此,《天龙八部》三大分支汇聚,又类似于《水浒传》中第71回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天龙八部》42回往下,小说的结构形式亦如《水浒》,以事件为线索,演绎三位主人公悲欢离合、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这样,两部小说的情节结构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整体:上半部犹如江河的支流汇成主干,下半部则如江河的主流奔腾而下,直泻大海。[3](P46)
对于《水浒传》这种人物传记式的结构,西方一些学者持批评的态度。蒲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归纳了西方对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的看法:“总而言之,中国明清长篇章回小说在外形上的致命缺点,在于它的缀段性(Episodie),一段一段的故事,形如散沙,缺乏西方Novel那种头、身、尾一以贯之的有机结构,因而也就缺乏所谓的整体感。”[4]罗溥洛在其主编的《美国学者论中国文化》中也说:“108位英雄好汉在一系列乱糟糟的互不相关的故事情节中上了梁山。”[5]这些观点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此简单地把西方传统的叙事理论直接套用在中国小说上,则有失偏颇。《水浒传》之所以运用这种结构模式,除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在于,这种结构模式的运用,与小说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相关。
《水浒传》讲述的是北宋徽宗时期山东、河北一带绿林起义的故事,其主题思想是官逼民反和忠义双全。为了突出官逼民反的主题,施耐庵描写了108位身处社会中下层的官员与普通百姓,在朝廷昏暗、奸臣当道的社会背景下,最终“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的过程。显而易见,这种人物传记式的叙事方式,可以更集中地凸显小说的主题思想。而且,《水浒传》上半部一边在描写众位英雄逼上梁山的同时,一边赞美他们的豪侠义气。小说的下半部,其主题则由上半部侧重描写的义转而重点描写忠,叙述接受招安之后的水浒英雄是怎样顺天护国,尽忠报国的。由此可知,《水浒传》的结构模式是由其主题思想所决定的。反过来说,其主题思想也在这样的结构中得以很好地完成。关于《水浒传》的这一结构特点,洪哲雄、纪德君在《知其二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试绎〈水浒传〉的整体结构逻辑》中曾经谈到过。他们认为,《水浒传》的艺术结构并不是靠简单的拼凑、撮合形成的,从外部到内里,从整体到局部,其中都有一根神理贯通其间;其外部整体由“天降魔星,替天行道”来统摄,局部和整体之间由“官逼民反,赴聚梁山”来关联,内里局部还由“义气为重,忠心为本”来沟通。[6]这贯通其间的神理,即对小说结构起着统摄作用的主题思想。
《天龙八部》的故事背景也被设置在北宋时期,但场景更为辽阔。除了宋朝之外,北到契丹,南通大理,西夏吐蕃,小说均有涉及。在这宏大的背景下,作者叙写了众多身份各异的人物,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千头万绪的各种线索。陈墨曾谈论过他对《天龙八部》结构的感受,说他阅读这部小说,总是担心这部作品徘徊在结构失控的边缘。事实上,小说行文到最后,所有线索一一成功收束,这主要得力于作者采取了与《水浒传》相同的结构艺术,即通过主题来统摄和稳定结构。尽管小说中的人物繁多,故事情节令人眼花缭乱,但其用意都指向了全书的主题:“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是文学批评家陈世骧1966年4月22日写给金庸书函里的话,是他对《天龙八部》小说主题的理解。他认为,要描画出这样一个芸芸众生的世界,其结构就不得不松散,但在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的背后,则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2](P1794)这就是说,《天龙八部》非如此松散的结构不能反映如此宏大的主题。此一结构的选择,是小说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三
《水浒传》中令读者比较感兴趣的内容之一,也是它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可以说,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里,除《金瓶梅》外,像《水浒传》这样对女性持有严重歧视态度的作品,并不多见。《水浒》中前后出现的女性有七十多位,大约占水浒七百多位人物的十分之一。这些女性中的绝大部分,是作为陪衬英雄的角色而存在的。
《水浒传》中一类女性形象是以潘金莲为代表的淫妇,如潘巧云、阎婆惜等。作者一方面描绘了她们外在的美貌,另一方面,又赋予其淫秽浪荡、堕落无耻的内在品行。作者在小说22回中说道:“水性从来是女流,背夫常与外人偷”,“酒色端能误国邦,由来美色陷忠良”。对她们极尽贬低丑化,批判否定之能。《水浒传》中的另一类女性形象则是英雄式女性,如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一丈青扈三娘。对上面提及的淫妇形象的刻画,固然表现了作者对女性的一种歧视,其实,对梁山上的三位女英雄,作者也抱有同样的态度。母大虫、母夜叉、一丈青,这是作者为她们所取的不雅的外号,而顾大嫂、孙二娘、扈三娘等称呼,则是作者对其姓名的漠视。她们虽然武艺高强,但在作者的笔下,仍然改变不了其从属于男性的事实。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跨越了南宋、元、明三个朝代。南宋时期,程朱理学兴盛。理学宣扬的是“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特别强调女性的贞洁观。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女性在那个时代,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毫无地位可言。故此,《水浒传》对女性的歧视态度,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作为现代最具代表性的武侠小说作家,一方面,金庸的《天龙八部》继承了《水浒传》忠义的主旨,以及那种带有鲜明民族特征的结构方式;但另一方面,顺应时代的发展,金庸对《水浒传》里女性形象的负面描写予以了扬弃。这一点,正是《天龙八部》对《水浒传》的超越所在。唯美是金庸在《天龙八部》里对女性形象描写的追求。《天龙八部》描写了很多女性,如王语嫣、阿朱、木婉清、钟灵、康敏、阮星竹、王夫人、甘宝宝、西夏国公主等。不管其性格如何,命运如何,但有一点她们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有着惊人的美丽。如,作为小说里最重要的女性人物,作者为王语嫣的出场,设置了精彩的镜头:
便在此时,只听得一个女子的声音轻轻一声叹息。
霎时之间,段誉不由得全身一震,一颗心怦怦跳动,心想:“这一声叹息如此好听,世上怎能有这样的声音?”
段誉一转过树丛,只见一个身穿藕色纱衫的女郎,脸朝着花树,身形苗条,长发披向背心,用一根银色丝带轻轻挽住。段誉望着她的背影,只觉这女郎身旁似有烟霞轻笼,当真非尘世中人。[2](P401)
先闻其声,再见其背影。金庸用一唱三叹之笔法,借段誉之耳目,写出了王语嫣那种恍若神仙妃子一样的朦胧迷幻的美。除了直接的外貌描写外,金庸还善于营造一种美人出场时情景交融的意境。如阿碧出场时的描写:
便在此时,只听得欸乃声响,湖面绿波上飘来一叶小舟,一个绿杉少女手执双桨,缓缓划水而来,口中唱着小曲,听那曲子是:“菡萏香连十顷陂,小姑贪戏采莲迟。晚来弄水船头滩,笑脱红裙裹鸭儿。”歌声娇柔无邪,欢悦动心。[2](P370)
文雅典丽的语言,吴越文化的气息,吴侬软语,清波绿水,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即便对小说里女性人物的命名,金庸也颇为用心,如木婉清的“婉兮清扬”,钟灵的“钟灵毓秀”,王语嫣的“语笑嫣然”等等。至于那些配角,阿紫、阿朱、阿碧、李秋水等,也都有着和她们性格相配的雅致名字。可以说,金庸《天龙八部》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是唯美的化身。
《天龙八部》里的女子重情,《水浒传》里的淫妇重欲,这是两部小说对女性形象描绘的最大的不同之处。
施耐庵在《水浒传》里,几乎淡化了所有女性情感上的描写。小说中,女性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尤其是那几个淫妇形象,她们身上涌动的更多的是原始的生命力。《天龙八部》则与此正好相反,如果抽取掉书中关于江湖豪侠的内容,整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诡谲浪漫的爱情传奇。阿朱、阿紫与乔峰,钟灵、木婉清、王语嫣与段誉,西夏公主与虚竹,叶二娘与玄慈方丈,阮星竹、秦红棉、王夫人、甘宝宝与段正淳,天山童姥、李秋水与无崖子,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结局,被金庸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演绎到了极致。这样一种描写方式,真正体现了《天龙八部》“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思想主旨。
《水浒传》对女性的丑化和《天龙八部》对女性的美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位作者所处时代不同所致。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地位在不断地提高,男女关系渐趋平等,女性已不再是男子的附属品。尽管《天龙八部》的故事背景也设置在北宋时期,但由于金庸摆脱了《水浒传》作者所面临的时代束缚,因而他能借助对江湖自由世界的叙写,背叛、消解和解构传统的男权中心意识,并以此歌颂纯真的爱情。
中国侠文化一直处于主流文化发展的边缘地带,但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它不断地与中国主流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其独特的演变轨迹。中国侠义小说是在侠文化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其发展正好体现了侠文化的这一变化过程。《水浒传》和《天龙八部》,正是将侠文化中的侠义精神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吸取了传统文化中带有民族特质的独特表现方式,因而其分别成为古代与现代最有代表性的侠义小说之一。而金庸的《天龙八部》,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与现代文明相呼应,这一成功的创作方法,为其后的武侠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杨兴安.金庸小说十谈[M].北京:知识出版社,2002.
[2]金庸.天龙八部[M].广州:广州出版社,2012.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4]蒲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罗溥洛.美国学者论中国文化[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
[6]洪哲雄,纪德君.知其二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试绎《水浒传》的整体结构逻辑[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