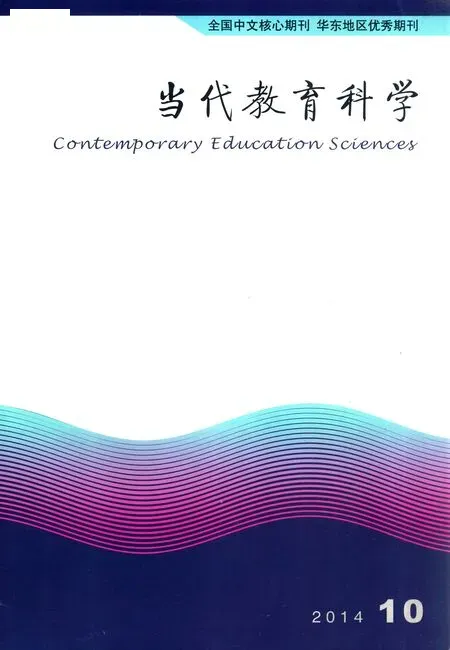时间观念中的关系性线索与学校德育生活
● 钟晓琳
一、关注学校德育生活中的“时间”
全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回归生活”逐渐被确立为德育的基本理念,它带来了一个显著的观念改变:学校德育应更多地帮助学生学会认识以及恰当地处理生活中的各种关系,而不是简单地讲授抽象空洞的道德概念。这一观念将人视为一种共在、共生的关系性存在,“每个个体都会具有他们的自我经验,这种自我经验说明,每个人都是在不同情况、不同关系中生活的……然而,各种不同的生活又都是在与他人发生联系中进行的,为此,各种自我经验都必定融合着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成分……”[1]学校德育正是要引导学生在各种关系的互动中,通过自我经验的表达与分享、对话与交流、调整与扩展等等促进学生个体的品德发展。对此,中小学的专设品德课程均明确将其课程性质界定为以“生活为基础”的“综合(性)课程”,小学低年级《品德与生活》课程内容以“儿童与自我”、“儿童与社会”、“儿童与自然”为轴线,围绕健康、安全、愉快、积极、负责任、有爱心、动脑筋、有创意地生活展开;高年级《品德与社会》课程内容围绕“我在成长”、“我与家庭”、“我与学校”、“我与家乡 (社区)”、“我是中国人”、“走进世界”展开;初中《思想品德》关注“初中学生逐步扩展的生活”,课程内容围绕“成长中的我”、“我与他人和集体”、“我与国家和社会”的展开。[2]可以看到,目前中小学德育关于人的关系性存在,更多地强调德育要帮助学生处理他们与自我、他人、集体、社会、国家、自然等方面的关系,这是基于学生个体不断扩展的生活空间展开的一条德育线索。应当指出,这条线索是重要的但却不是(也不能是)唯一的,因为空间并不能包含生活的全部维度,也不能代表人的发展的所有向度,人同时还包含着一种时间的关系性存在。
一直以来,关于时间与人的生命、生活的关系是哲学思考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说人对空间的划分可以获得相对静止的感受,那么时间则更多地带给人不稳定的、流动不息的感觉。海德尔格曾指出人的存在(“此在”)是一种“在起来的动态的过程”,它是“先行于自身的在”、“已经在世界之中的在”、“依附于世界内的在者的在”共同构成的统一完整的结构,而这三者分别代表着将来、过去、现在。[3]这也正如加塞尔所言:“生活的每一刻都包含着将来、过去和现在。”[4]时间对人的重要性在于它包含着对人的生命的度量,正是时光流逝使得人要不断地去(重新)获得和感受自身的存在与意义。这意味着与空间相比,时间同人的道德、德育有着更幽深、隐秘的关系。人需要在生活中处理自己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人对这些关系的不同认识往往导致了不同的时间观念;由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不是被置放于完全平衡的天秤上,人的时间观念本身包含着价值判断,地域、历史文化的差异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影响着人们时间观念的价值选择。比如,中国古代强调的“述而不作”“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等表达着一种古胜于今的时间观念,在这种观念下人更多地追溯、尊重甚至向往历史中的人与事,并以此为依据指导、规范人现在和未来的生活,人更多地在过去、在历史中获得归属;又如印度佛教提出的 “三世因果说”①表达着人对未来生活的寄望,未来比过去、现在更重要,人的现时生活是为了未来而存在,人要在未来寻找归属;等等。可以认为,人的时间观念牵联人在生活中最真切的生命感受并内在地影响人的生活,影响着人去处理与自我、他人、集体、社会、国家、自然等方面的关系。基于人的时间观念展开的关系性线索应当成为德育关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人的完整的关系性存在包含着人在时间与空间中的所有关系的交合,德育的空间线索与时间线索难以剥离并相互影响。
二、现代与后现代时间观念中的德育境遇
随着印刷媒体(报刊、书籍等)和视觉媒体(电影电视等)的发展,现代时间观念的变化及其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悄无声息的,这在现代文学和文化学的研究中已经被揭示。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西历(阳历)的使用③,在“现代性”所包含的时间观念中,古今被截然两分且“厚今薄古”,过去代表着陈旧、顽劣而现在则是新的、具有开创性的,这种观念在否定过去的同时隐含着一种乐观的“开创者的心态”,从而可以展开对未来的想象,它连接着现在和未来。总体而言,这种心态一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建设,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消费生活变革、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视觉媒体的广泛传播、信息技术的发展等等,带来了所谓中国的后现代现象。这种“后”现代不仅是一种时间上的先后,还包含着与现代性的冲突和对抗,杰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在后现代中没有了对未来的乐观,其时间观念里没有“独创性”而只有“复制”,这是一个“文化大规模的复制、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时代”。[5]那么,在“复制”中如何走向未来?日本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的问题,人类似乎已经无路可走。对于个人来说,由此带来的生存危机感、都市生活强烈的压迫感以及“每日生活中的焦虑感把时间压缩到现在,而现在又是很不稳定的”,这似乎已经是习以为常的问题——“我生活在现在,我不知道有将来,也没有过去”(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万语)。[6]当前,在这种现代与后现代时间观念的交合中,人丢失了对时间体验的连续感,“现在”似乎成为唯一被承认的时态,这种观念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内在地影响着人们对生命、生活和人生的看法;这给人的精神生活和人文精神带来了极大冲击,李欧梵认为其最大的危机就是所谓的人文主义、人文精神到底有什么用?而一切都以今天、当下的利益做判断。
那么,这对于中国学校德育意味着什么?
从其外部境遇来看,人们在现代生活中有两套并行的时间观念——阳历和阴历④,二者包含着不同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比如阴历与中国传统时间观念中的“载”(十年)、“节气”等相关联;而阳历则与西方传统时间观念中的“世纪”(百年)、“星期”等关联。国家与国际接轨规定公元纪年,客观地产生着扬阳历观念,抑阴历观念的影响(比如,成长和生活在新时期的人们逐渐习惯于“星期”而忽略了“节气”),传统时间观念中的文化价值流逝,同时又缺乏理解西方时间观念价值内核的文化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精神的价值真空,基于时间的生活节律失去其应有的精神价值和道德意义 (即人们感觉不到时间中有道德),这意味着教师与学生在时间性的关系存在中容易丢失具有联系感的价值链条。⑤与此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传统节日对人的教化意义被淡化。相对中国传统节日而言,外国传统节日因其带来“陌生”与“新奇”而受到青睐;但中国人对于外国节日(如圣诞节、元旦节等)没有历史文化积淀,难以感受到文化深层的精神内核,它在市场经济和消费生活中更多地只是作为一种娱乐被消费。尽管近年来中国传统节日也开始重新受到重视⑥,但它在现代和后现代时间观念中仍然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 (如中秋节的月饼经济、端午节的粽子经济等),从学校德育的角度关注得很不够⑦,还有待于有文化自觉的、较为系统的德育资源乃至德育课程开发。
从学校德育的内部境遇来看,教育理论研究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不同侧面反思现代性问题对学校教育包括德育的影响,批评工具理性对人的精神层面的遮蔽,批评功利主义、知识化、表面化、以及唯科学主义的量化评估,忧虑德育中情感与信仰的缺失等等。这些批评、追问包含着对“现代性”涵义本身如:工具理性、知识性、科学性、确定性、世俗性等的质疑,洞察到这一“现代性”往往是以“客观”、“现实”、“准确”、“时代性”等影响德育进而造成了德育的精神困境,意识到这种崇尚和追赶的“现代性”对德育而言或许是不好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它违背了德育的根本追求。但是,这些批判都难以确切地解释这种“外”的影响究竟是如何作用于德育现实的。尽管它们可能清晰明确地指证“现代性”给德育造成的病症表征及其外部影响因素,但它似乎尚未质疑德育自身是否含有现代性发生与发展的 “土壤”。应当指出,当现代性本身包含着一套观念系统(特别是时间观念)内在于人的生活时,它就不再是一种社会强加于个体的东西,而是个体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与表达。当现代时间观念及其变化内在于教师和学生的社会生活中,它必然影响并体现于教师和学生个体思考与感受生活的兴趣和方式,这是德育的重要基础,贯穿于整个德育过程,并以此带来德育生活的变化。⑧
三、学校德育的重要着力点:“真实感”
从表面上看,现代与后现代时间观念对师生生活和学校德育的影响似乎是难以逾越的,因为它内在于人的观念系统与生活方式并且难以自觉;但另一方面,人在这种时间观念中隐含着的“现代情绪”,如危机感、压迫感、焦虑感等等又迫使人来反观甚至质疑自己的生活。这些情绪源自人对现实生活最真实的感触,它似乎比理智更能使人深沉地意识到自己的困境⑨。人在感觉、态度中往往可能触碰到自身最真实的一面、找回自我存在的真实感;特别是当后现代文化呈现“那种支离破碎、转瞬即逝的刺激,能够与这些刺激做出妥协或对抗的,反而恰恰是自己瞬间的感触、瞬间的态度……可以感受到某种哪怕是极微小、片面,甚至于瞬间即逝的真实感,……也许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些真实感,我们才最终得以生存下去。”[7]对于德育而言,这意味着那些源自人对现实生活真实的情绪情感体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德育意义。对此,朱小蔓教授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倡导情感教育,呼吁并探讨德育要关注学生情绪情感品质和能力的培养、关注德育过程中的情绪情感发展等,强调学生的情感体验所具有的特殊德育意义。[8]这些年来,通过情感体验来进行德育已经从德育理念逐渐走向德育实践的方式方法层面,然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德育应当强调怎样的情感体验?应当指出,“真实感”是师生情绪情感体验的重要基础,只有首先获得真实感,其他的情绪情感才可能得以生成或产生持续、深刻的影响。
当前倡导德育回归生活,就包含着德育应当回到师生的现实生活事件、回到师生对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受和体验;在这个过程中,德育应该让学生更多地获得安全感、依恋感、信任感等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这有助于学生积累道德的生活经验,但德育不能(也不可能)一味地“制造”积极美好的道德生活,在这种被制作的生活中师生双方都难以获得现实的真实感。它所带来的可能结果之一是李镇西所说的 “玫瑰色教育”:
以“未来班”为代表作的教育浪漫主义给我带来了喜悦——我的班级的确营造出了五十年代那种温馨透明的集体氛围,朋友们都说我班的学生特别“纯”。但是,1987年底乐山市一位叫宁小燕的女中学生自杀的事件,把我从教育浪漫主义的沉醉中唤醒。这位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因不能正视社会丑恶而成为“真善美殉道者”。面对她“纯洁的心灵”,我不得不反思我们的——不,首先是我的“玫瑰色教育”。[9]
与此相比,更糟糕的情况可能是德育自身的真实性与合理性遭受质疑,因为对真实感的体认是德育得以有效展开的前提和基础。在此,有必要先区分人的两种不同的“真实感”,即生活的真实感与存在的真实感。前者是个体对生活事件的发生及其结果的客观存在的直接感受,而后者则是个体基于自身的价值判断所获得的一种合理性存在的感受(即对哲学所谓“人的本真存在”的感受)。存在的真实感往往以生活的真实感为前提,当生活的真实感与个体自身的价值判断相符合,它就可能转化为个体存在的真实感;而当二者不相符合时,个体就可能产生负面情绪。比如,师生在面对某个生活事件的第一时间可能表现出无意识的惊讶或气愤(“太不可思议!”“这不是真的!”“不可理喻!”),这意味着他们首先获得一种惊异感或愤怒感,其中既包含着对生活事件的(客观)承认,也包含着对它的(主观)不认同;这种惊异感或愤怒感恰恰表明了生活事件的真实感与个体存在的真实感之间的错位。在这个意义上,人对真实感的体认就是要不断地从获得生活的真实感走向获得自我存在的真实感,而正是这些负面的情绪使人可以进行谋划和选择⑩。因此,德育首先应当承认师生在现实生活中、在当下的德育过程中可能包含着负面情绪的复杂情感,承认师生的这种真实体验而不是回避它、蔑视它,更不是强迫师生去体验某种预设的积极情感。苏霍姆林斯基强调,人的情感是不能命令的,它是环境的产物。这不仅是说积极的情感体验不能强求,而且承认消极的情感体验的“事出有因”。教师既不能要求学生也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感受孤寂、卑微、畏惧、焦虑、愤恨、迷惘和失落等等。当然,还不能否认教师或学生在遭遇到负面情绪时可能会采取一种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11,似乎本能地想要否认或逃避这些负面情绪。这恰恰是德育应有所作为的方面——不但要承认这些负面情绪,更要正视它、学会处理它;德育过程应包含师生不断地反观与探问:自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这种反观与探问正是他们从生活的真实走向自我存在的真实、获得新的同一的真实感的重要路径。
四、学校德育应培养学生的“历史感”
直面现代与后现代时间观念所带来的德育困境,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个体内在精神时空中的意义链条的断裂,因为人只有在时间连续感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整地把握和处理人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才可能展开真正有效的道德价值学习。学校德育要建立起这种时间性的内在精神的连接,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历史感”。
什么是历史感?不同的角度可能会有不同的内涵。从德育的角度来看,历史感首先包含着个体对过去的人物事件、物质与精神环境及其变化等(这些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历史存在)的觉察;在此基础上,历史感包含着一种自我存在的真实感,即个体能够感受到“我在其中”、“与我相关”。换言之,历史感是一种“身在历史之中”的感受,在这种感受中,历史一方面有其外在于人的客观性,个体承认并尊重这种客观性;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人自身生命的连线,个体在这种承认和尊重的态度中隐含着生命存在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情感连接。这个意义上,历史感与意义感、责任感之间有着深层次的关联,在诺丁斯(Nel Noddings)讨论对物的关心的一则例子中,可以感受到这三者的微妙关系:
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和英语教学需求的变化,高职英语教学的重心落在实际运用和交际能力上,而淡化语言学习过程中语法知识和词汇的讲解与传授。但语法是语言内在结构规律的总结,语言交际的准确性有赖于语法,任何语言的准确性最终来自语法本身。
我家厨房里有一台1957年出产的搅拌机。我仍然保留着当年的使用说明书。我丈夫曾经对它进行过一两次简单的维修。这台机器现在对我们已经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意义了。它拥有我们对它的关心,它也确实值得我们关心。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对老车、旧气压计、用过多年的刀具什么的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10]
在诺丁斯所述的这种情感中,人对旧物包含着某种人格化的尊重与关怀,这意味着人与旧物之间不是“我—它”而是“我—你”的关系(马丁·布伯语),旧物被人赋予主体生命的意义从而在人的内在精神层面获得一种生命力。有趣的是,这种意义其实是对人的意义而不是对物的意义(客体的物自身无所谓意义);它其实是人在过去的时间里从对物的使用、养护关系中逐渐积累、不断强化的一种自我存在的意义。这种意义的历史沉淀,与人的意义感关联,甚至可以涵养人的责任感。意义感、责任感是当前德育面对个体内在精神危机而被更多关注的情感主题,相对而言,历史感似乎还不太引人注意。然而,历史感却是相比意义感和责任感更为深层的情感。一般而言,在特定的文化价值系统下,个体在关系性的存在中体会到自身对于他人与社会等的价值,当这种价值成为主体对自身存在的确证时,个体才会获得意义感;责任感是基于意义感而生成的,当意义感作为一种正面刺激肯定了个体对于他人与社会的价值行为,这种行为就被个体赋予一种合理性或正当性,对于这种合理性或正当性的体验便生成责任感。可以认为,责任感的获得以意义感为基础,而意义感的获得又需要两个前提,即特定的文化价值体系和个体的关系性存在。对于个体而言,特定的文化价值体系离不开传统和秩序,它包含着文化的连续性与历史沉淀;而完整的关系性存在是包含时空范畴的,它肯定并尊重历史存在以及在此基础上个体与过去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了历史感也就没有了意义感,进而失掉责任感;历史感应当成为德育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
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历史感的培养并不等同于历史知识的学习,历史知识的记忆也不意味着历史感的获得;前者注重关于历史知识呈现的准确性,后者则关注对于个体与过去、历史关系的主观感受和体验以及由此生成的价值判断。从这种区别来看,历史感的培养可以先从学生对自身生命成长的体验开始,注重拓展学生内在的精神时空,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扩展自己与他人、群体以及人类历史的联系与对话,不断丰富自我存在的意义链条。具体来说,相对于书本历史知识的学习、博物馆历史陈列的参观等,历史感的培养更多地需要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积累自身成长的历史性的生命意义,那些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具有时间沉淀意义的事物,就可能成为重要的德育资源。比如,某小学开展的“我与香樟共成长”德育活动,要求每个班级在校园里认领一棵香樟树,从一年级开始养护这棵树直至毕业,每一年都要测量并记录这棵树的成长情况(树高、树宽、树的外围长度等),在这样的活动中,学生可以获得历时性的生命体验,在感受成长的同时,他们与树的意义连接其实隐含着与“过去的我”的意义连接。校园中的设施、建筑等是具有“记忆”功能的,学生可能通过它回忆起自己的过去(在这里发生的那些重要事件及情绪情感体验等),这种回忆及其引起的生命的历时体验就可能生成历史感;特别当学生毕业后再回到学校,如旧的校园更可能会引发他们的归属感,而完全改变的校园则可能会导致陌生感和失去感(意义的丢失)。不仅如此,校园的这种“记忆”功能还具有弥散的影响力,学校的建筑往往可以散发出学校的历史气息,使后来的学生意识到这里曾经有过前人的故事,他们可能在感受或想象中获得一种历时性的体验,如近百年的老校园往往可以让人获得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从而心生敬畏。
注释:
①即前世造因、今世受果,今世造因、来世受果。
③梁启超被李欧梵认为是中国现代新的时间观念的始作俑者,他虽然并不是第一个使用西历的人,“但他是用日记把自己的思想风貌和时间观念联系起来的第一人”;随后《申报》较早在公开场合同时使用中西历。
④也称西历与中历、国历与农历,大多同时标示在台历或挂历上。
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可能是当前德育的时间性的关系线索被忽视的重要原因。
⑥比如从2008年1月1日开始,阴历的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当日作为中国传统节日被定为公众假期。
⑦虽然已有一些中小学将传统节日的部分文化元素补充到校本课程或德育活动中,但总体而言,当前学校德育对传统节日的德育价值、内容的挖掘与整合等方面还缺乏自觉意识和系统的论证与探索。
⑧从这一点来说,很难判断已有德育的现代性批判是批评的影响因素还是批评的一种“结果”。
⑨存在主义将人的体验、感觉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⑩海德格尔认为人总是有“情绪”的,这是他生存的一种方式,“正是情绪使此在可以进行谋划和选择。”
[1]鲁洁﹒关系中的人——当代道德教育的一种人学探寻[J]﹒教育研究,2002(1):3-9﹒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2011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第 2版):559-600.
[4][西]何·奥·加塞尔(商梓书等译).什么是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31.
[5][6][7]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8-89.162.107.
[8]朱小蔓.情感教育论纲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9]李镇西.从教育浪漫主义到教育理想主义[J].中学语文教学,2001(1):20-22.
[10][美]内尔·诺丁斯(于天龙译).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