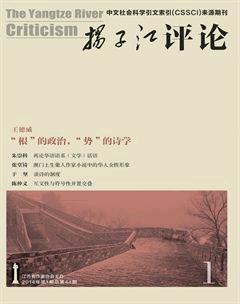历史的诗意想像
刘秀美

一、 前言
《斯卡罗人》以卑南族知本石生系统卡日卡兰部落,于1633年因飙马社拒缴贡品事件引发战争失败,导致部份氏族南迁的历史事件为主述脉络。作者巴代以日本人类学家移川子之藏等1935年于知本部落的调查资料①、宋龙生《台湾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②及曾建次神父的《祖灵的脚步》③等书中记载的相关事件作为小说创作的基础,经由文化背景的审慎考据,试图为无文字足以记录过往史事的民族达到以小说辅助族群历史文化教育的可能性。
孙大川为巴代另一部小说《笛鹳——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写序时提及:“以‘文写‘史,容或有虚拟、渲染的成份,但经过严谨的田野比对以及真诚的情感净化,小说世界所营造的历史认知,比学术文献的堆砌,更能映照历史经验的真实”④,孙氏指出这类以文写史的文本,经过“严谨的田野比对”和“真诚的情感净化”,所传达的事实上是一种“诗比历史更真实”的文学文本价值。有关历史真实性的辩证在后现代历史主义的主张中已提出了诗意想象的可能视角,海登·怀特的“元史学”观点说明了历史是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历史叙事是复杂的结构,经验世界以两种模式存在:一个编码为‘真实,另一个在叙事过程中被揭示为‘虚幻。历史学家把不同的事件组合成事件发展的开头、中间和结尾,这并不是‘实在或‘真实,历史学家也不是仅仅由始至终地记录了‘到底发生了甚么事。所有的开头与结尾都无一例外地是诗歌的构筑……。”⑤因而历史文本富含着史家诗性的想象在内。如此,则巴代试图以部落口述史为小说架构基础的“小说化”史观,要将其置放于何种位置,是值得思索的问题。
《斯卡罗人》以口传部落史为本,以小说形式企图展现部落历史,但在创作者以文人之笔进行创作时,作家的立场与想象自当成为必须考虑的问题;小说所依据的口述历史文献也是讲述者在个人诗意想象与诠释下形成的一种文本。因此,历史、口述历史传说及小说创作各有其背后之“生成”语境,该如何看待不同文本间交错而成的历史?小说文本的“选择”依据又凸显了作家何种社会关怀,此为本文所欲探索的。
二、 口述历史传说文本的生成语境
台湾原住民族历史以口头传承为主要形式,举凡神话、传说对族人而言都是信而可征的“古事”,台湾原住民族作家试图藉由小说建构族群历史的可能就在于原住民族的历史靠的就是口碑传承,过去并没有任何历史文献可供查询,因此口传也就具有历史的意义与价值。
《斯卡罗人》一书取材的主要来源有三,作者认为这些口传资料是一种大纲式的呈现,以此为本的创作恰可补足口传文学所欠缺的文学和艺术性:“……口传故事那种大纲式的呈现,无可避免的牺牲掉了文学本身所具备的艺术性,简化了作品本质上所要传达的思想、情感与细腻的文化呈现。”⑥因此藉由改写这一类的口述历史传说使之符合文学形式。然而作家所取材的口头传说,在无文字的民族经常被视为族群历史看待,这种由记忆保存与口头传承的历史似乎更符合“历史编码”⑧的说法,叙事者、记录者和整理者如何或在何种情境下编码,成为探究此类历史叙事的要点。
《斯卡罗人》一书含《序章》共分为十二章,作者于每一节开头皆注明本章取材的出处,例如第一章《磨刀之辱》:“……起初,Karimalau与卑南社交好,卑南社的人命他磨刀,他大为愤怒,将刀折断而插上屋顶,……与前记的人们一起向恒春方面出发……。(移川子之藏1935)”⑧,本章创作的依据为移川子之藏《台湾原住民族系统所属之研究》所录之文本,小说注明取材自本书的共有二章;以《祖灵的脚步》所录内容为主的有七章;取自《台湾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的二章;另一章则以陈实《台湾原住民族的来源历史:知本(Katipol)族民传说》手稿为本⑨。
小说取用材料来源,各有不同的生成时间及背景,依大致时间序为《台湾原住民族系统所属之研究》(1935)、《祖灵的脚步》⑩、《台湾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11,以下先讨论上述三本书之生成语境:
(一)《台湾原住民族系统所属之研究》
本书日文版1935年出版,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创校主要目的之一即为展开南方学研究,基于研究对象是没有文字的种族,因此调查计划是以和历史关联性较大的系谱和族群迁徙为主:
在所有的口碑传承中,比较接近史实的部分,应该是系谱和族群移动罢。当然溯及久远年代以前的传承,渺茫无边际,充满着幻想,例如种族的发祥传说,难免有神话色彩。然而,越是距今不远的年代,所传的内容,例如系谱,可以说越接近史实。12
本书便是以系谱和族群的迁徙为主要调查事项的成果。虽然系谱和族群迁徙的说法是口碑中较接近史实的,但在移川等人的调查中也发现:“世代越长,口诵者对于旁系的记忆越淡薄,甚至从记忆中消失。”13
书中有关卑南族的调查为移川的学生马渊东一所完成的,虽然马渊以严谨的态度从事每一个部落、系谱的调查,但此计划执行调查者皆为日本学者,成书之始也是先行以日文记录,因此诚如移川言及部落、人名、地名和氏族名称时说:“访问者和报导人的不同,难免产生一些相异的语音,因为接受访谈者没有文字,只用口谈的方式回答,名称和发音有别,当然是无法避免的。”14 在语言讹听的可能性与异族文字转译的误差下,日本学者调查的文字记录要完全达到原述者口述传说历史的原貌,几乎是不可能的。
再者,部落中的头目或大家长为掌握主述话语权的传承者,这些头目除了身负一族之安危外,都将系谱铭记于心,视此为莫大光荣。在口诵系谱的过程中,呈现了对自己系统所属的执着。15原住民族此种对于自己族群的认同与强烈归属感多少也影响了族群迁徙过程中与他族互动的记忆叙述,曾建次神父发表《祖灵的脚步》时,他所担心的问题正是:“……老祖先为了要显露自己的部落有多了不起有多优秀,所以讲到自己部落的优点时,会贬抑别的部落,……。”16因此往往同一件事,不同部落或氏族间便有不同说法,各自站在族群自我立场的叙事与诠释,自然是众多的事件构成了历史的多重面相。
(二)《祖灵的脚步》
曾建次神父《祖灵的脚步》是《斯卡罗人》采用材料最多的文本,书中共有四十八则叙事,每一则叙事皆于文后注明讲述者,讲述时间及讲述者个人资料则附录于书后。根据曾建次神父的说法,本书口传史料乃是1967年到1970年间德国籍神父费道宏(Rev. Patrick Veil)发现卑南祖先流传下来的历史、故事、庆典等值得记录,因此邀请山道明(Dominik Schroder)神父一起做的采访;另外一部分则取自1988年和文化大学金荣华教授合作采录的资料。17比对洪淑玲根据德文版所翻译的《老人的话》18、《祖灵的脚步》书中个别讲述时间的纪录及曾神父于书前所做之说明,曾神父于书前有关德籍神父采录时间点或有误差。《老人的话》记载山道明神父于1964年前往知本,当时他对祭司问题特别有兴趣。书中所载录的故事是1965年3月至1966年11月第二次来台时所录制、转译的。根据《祖灵的脚步》附录的讲述时间,本书主要讲述人汪美妹女士讲述年份标为1965年,因此曾神父于书前所提及的时间点(1967~1970)应该还要再往前推算,应该是山道明神父第二次到台湾的时间点(1965~1966)。
姑且不论部分数据采录时间的正确性问题,《祖灵的脚步》一书中讲述者的讲述年份从汪美妹的1965年到高先宗的1996年,横跨了三十年之久,全书为曾神父依据历史时间序整理之结果。曾神父整理的想法是将祖先的故事做“有顺序的呈现,有点像是历史过程把它们描述出来。”19事实上,汪美妹女士并不是连续性的讲述,曾神父整理时做了串联的动作,也就是他把汪美妹女士在不同情境、不同时间点所讲述的故事,以他自己对族群历史的了解,做了情节接续的整合:
在她的叙述里头,不会很有顺序的说出一个故事,她会说出一段,然后在另一个状况下又说出另一段,最后我把它串连起来。例如她向之前的神父叙说故事的时候,说得比较长,但结束之后,又有一段可以联系到上一段的,所以我听录音带时才把它衔接在一起。
这个带子是我去德国拷贝的,听录音带时觉得有些叙述不完整,但因为拷贝时分不清楚是第几个带子,因此我自己觉这应该是故事要衔接时,我就这样处理。20
曾神父不仅衔接汪美妹女士在不同时间的讲述数据而已,而且将不同讲述者的讲述内容依史事的时间脉络整理成一部具有部落史性质的口述文本。这样的叙事文本基本上已脱离了对个人口述数据的单纯记录,而是针对事件进行重新叙写。讲述者三十年的线性时间差,也在整理的过程中被置入同一时间等同看待。因此,《祖灵的脚步》一书的史料性质,事实上是经过不同讲述者所述内容串连的结果,且在整理者曾神父个人对史事的认知下,重新诠释与编码下的文本。
(三)《台湾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
宋龙生《台湾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所采用的资料,大约可分为两阶段搜集,第一阶段为1960年至1965年作者在卑南乡南王村从事研究期间;第二阶段为1994年至1998年到台东针对卑南族进行全面性了解。21书中引用资料除作者田野访谈所得外,也有日本学者的调查资料。《斯卡罗人》中取用本书为创作材料者有二章,其中一章为本书转引自Anton Quack编、洪淑玲翻译的《老人的话》中的传说;另一章为作者1994年在南王部落所采。
因为《卑南族史篇》一书兼具作者个人田调所得和文献资料之搜集,且为部落史书写性质,因此书中所引用数据的出处为多来源,其中引用《老人的话》中的叙事仍然为汪美妹所讲述。
综合上述,可知《斯卡罗人》主要依以创作的三部资料,其生成语境所衍生的问题并不相同。《台湾原住民族系统所属之研究》为日人所调查且先行以日文记录,因此本书在世代传承中的记忆消退、语言讹听、异族文字转译、掌握话语权传承者的自我执着、部落立场的诠释差异等因素下,与真正的部落历史应有一定程度的落差。《祖灵的脚步》一书则大部分出自汪美妹女士在不同时间的口述,而被整理成依历史时序发展的叙事。不同讲述者所述内容也在整理者曾神父个人对史事的认知下,予以重新诠释与编码。《台湾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已引用了多来源的资料。因此,小说所依以创作的材料可说是在不同情况下,经过整理者编码的文本。
另外,台湾原住民族口述历史传说也是一种部落集体记忆创作,汪美妹等讲述者只是部落中积极的口述史传承者,但他们都不是历史学家,叙述过程仍然具有讲述者的个人色彩与叙述当下的语境影响,但这些在转译成他种语言、文字时已经被忽略了。事实上,这些看似口述史的基础材料,在未被转化成小说时,已充满了文学的想象和小说写作的连缀与修补性质。
三、 时序交错的口头叙事文本
1986年鸟居龙藏在台湾从事调查旅行,鸟居走过的调查路线正与1893年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胡传管辖的范围一致。从胡传当时的数据与鸟居的调查报告观察,可以发现“鸟居的调查报告,不但依循了某种学术方法论的架构,也记录了来自于原住民族内部的口传记忆。对照3年前胡传的日记和书信,原住民在文献资料中被书写的角色和定位,显然有了极大且本质上的变化”22。此段用意虽说明的是日本学者进入部落内部与胡传从外部观察的视角差距。但鸟居的调查和胡传的书写仅差距三年,容或二人针对原住民族的描写或记录视角并不一致,但时间和叙事文本间的关联性却是不可忽视的。从《台湾原住民族系统所属之研究》(1935年)的调查至《台湾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中所引最近的口述数据(1994年),时间差距将近六十年,又有调查者身份、国族的差异,这些都可能是口头叙事文本已经在原有的历史记忆基础上产生变貌的原因之一。
移川于《台湾原住民族系统所属之研究》绪论中曾提及系谱为原住民族口碑中较接近史实者,但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了:“世代越长,口诵者对于旁系的记忆越淡薄,甚至从记忆中消失。”《斯卡罗人》一书的主述事件发生于1633年,距离移川等人的调查已经三百年了,马渊东一在恒春调查时,有关当初来到恒春地方的La-garuligul家始祖女头目Ranao的后代都已经是第十二代了。因此,小说创作所面对的是三百多年前的史事,所引用的口述资料则横跨了六十年的讲述,这些时序交错的文本被写入小说后,小说所保留的历史面貌是值得探讨的。以下先牦清小说与引用材料讲述时间关系(见表格):
从中可以发现《斯卡罗人》以卡日卡兰部落部分氏族南迁的事件发展时间为描写的依据,但小说创作基本上以整理后的口述文本为蓝图。全书引用口述数据的生成时间点上为交错的脉络,最早的是移川的1935年,最晚的是李成加讲述的1994年。台湾原住民族因无文字可供记录,皆由口头传承部落重要事件,一如“说故事的人的材料,如果不是他本人的经验,便是传递而来的经验。透过他,又成为听故事的人的经验”23,经由口头传承的资料皆为集体创造的成果。因此,相距六十年的口述文本在积累了讲述人的经验与呼应讲述实况的情境上自然有所不同。
所以从基础材料上我们可以想象的是这些作为小说创作大纲的口述数据,在口述文本生成时间的交错运用下,必须要考虑的是口述史料背后生成的时间因素。在“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24台湾原住民族部落迁徙过程中的族群互动关系,往往随着时间越显复杂,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见部族间的更替兴衰。因此,1935年的部落史讲述情境与1994年回忆斯卡罗遗事的讲述自然会有不同的观点与记忆。
从田野考察的实务而言,即使是同一讲述者也会随着不同讲述时间而产生内容的变异,每一次讲述活动都是一次新的开始,即便是讲述同一叙事主题也可能因为语境不同而产生出入。因此以时间为本比对口述文本,有时可以还原部分的历史现象或氛围。
小说借用材料最多的为汪美妹所讲述,曾建次神父藉以成书取自德国图书馆的录音带和Anton Quack所编的《老人的话》的来源是一样的。曾神父的《祖灵的脚步》一书仅于附录说明汪美妹的讲述时间为1965年,然而《老人的话》导言中清楚叙明费道宏(Rev. Patrick Veil)和山道明(Dominik Schroder)神父的录音带采录时间是1964年11月到1966年8月,查阅书中有关汪美妹不同的讲述时间1965和1966年各计九次25。
《祖灵的脚步》的成书为曾建次神父多次反复听取录音带后整理而成,曾神父依了解中的部落历史时间将不同讲述者和讲述时间的口述数据依时间顺序汇编整理,本书整理过程已经造成了文本讲述时间的交错。巴代选择前述三本着作为小说创作大纲时,再一次将口述文本的时间拆解。
四、部落历史的选择、诠释与缀补
台湾原住民族没有文字,部落传承以口头为主要形式,并没有历史记载文献可供查询部落历史,因此口头传承数据具有历史的价值。然而不可忽视的问题是每一则叙事都经由叙事者的选择与诠释,都是由语词建构出来的,因此也就有话语权所产生的立场问题,每一则叙事都可能添加了每一段叙事者的个人见解。
《斯卡罗人》的“序章”从知本社群卡日卡兰部落向飙马社(卑南社)的复仇写起,前因则为小说中“布利丹氏族南迁图”中提到的“滑地之战”,这就是发生在卑南历史上中古时期的“竹林战役”。这场战役使得卡日卡兰社气势大为降落,卑南社从此摆脱了向卡日卡兰纳贡的义务,最终成为卑南平原上最强势的部落。竹林战役应是小说情节起始的前因,但并未被写入小说中,然而从竹林战役的口述历史异文可以见出族群视角的话语立场,知本和卑南关于这场战役的说法分别为汪美妹和李成加所讲述。
知本部落的汪美妹于1965年讲述了这则传说,内容大要为:
当各族部落都向卡日卡兰缴交贡品时,有一次卑南社没有缴交,因此卡日卡兰派人前往卑南社询问,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卡日卡兰的人想要离开,没想到卑南社的人在路上放了多竹棍,让他们的族人都跌成一堆。卑南社的人趁机展开屠杀,只留下了祭司长,将他押回部落,把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最后切开他的胸膛,祭司长才合目结束生命。26
卑南部落的李成加于1993至1997年间两度讲述竹林战役,情节大要如下:
住知本的哥哥告诉住卑南的弟弟,因为自己是老大,所以要弟弟以后每年打到猎物要向他缴税金。有一年卑南人猎到不少猎物,派成年会所的人去送猎物,没想到中途被这些青年吃掉了。知本人不满派人到卑南理论,卑南头目查清楚是自己部落青年犯下的错,但知本人坚持要打仗。于是卑南头目命人砍了很多竹子排在部落交界处,知本人滑倒后就被卑南人杀了。最后知本战败,头目被抓回卑南部落,他们问知本头目服气吗?没想到他一直回答不服气,于是他们就割下他身上的肉给他吃,知本头目还是坚持卑南欠他们肉,结果身上的肉不断的被割下,直到气绝而死。此后知本的人每年打猎后,反过来要向卑南社缴交猎物为税金。27
汪美妹是一位女祭司,为部落中对传统事务最具权威、最可信的人28;李成加是南王卑南族的司祭长,生前对卑南族传统文化及仪式极为重视和坚持。29从相关记载中可以看出两位讲述人在部落中都拥有传统文化的主述权,且记忆力惊人,因此他们口述的部落史应该是部落普遍接受的说法。从竹林战役的口述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知本与卑南的不同立场,汪美妹所代表的知本说法,对于知本丧失了领导地位颇有起因于卑南使出小手段的说法。但卑南部落的说法却是相反,首先知本哥哥强要卑南弟弟以猎物缴税不具合理性,竹林战役也是身为哥哥的坚持要战争的结果。每一个叙事者自有不同的选择与诠释立场,由此可以明显见出。
《斯卡罗人》取材自与知本、卑南权力转换及部落氏族迁徙有关的口述史料,引用材料如前节所述,多为知本部落的汪美妹所述。作者巴代为大巴六九部落人,小说以巫术的历史奇幻之旅,衔接了自己部落与卡日卡兰部落迁移史或虚或实的关系。小说的封面介绍写道:
公元1641年,荷兰人前往台湾东部山区探险寻黄金,助理员韦斯利路经大巴六九部落时,因调戏部落第一美女而遭杀害。此举引发荷兰人与彪马社联军讨伐大巴六九社,部落女巫丝布伊因巫术闸口不平衡的情况下,召唤了三百多年后的小女巫前来协助。不料,这个拥有强大灵力的女巫在过程中,却在布利丹氏族族长的召唤下,成为他肚子里的女婴。……
小说从第四章开始出现大巴六九的女巫师直到第九章“女婴谜云”都围绕着巫术,第四章取材的是南王李成加所讲述有关卑南社沙巴彦氏族的祖先在到达台湾最南端时,梦见神明指示他们不要再往恒春方向去,否则身体会自然消失。30李成加此段说法只是以沙巴彦氏族的梦境之说隐喻着南迁的斯卡罗族(原卡日卡兰南迁的布利丹氏族)后来被排湾族同化的命运。简单的叙事在小说中却敷衍出大巴六九部落召唤三百年后的小女巫,因缘际会的协助了布利丹度过危机,成就了威震琅峤十八社三百余年的霸业。
《斯卡罗人》以口传故事为小说书写大纲,由前节表列可知此大纲以知本社所传为主,汪美妹所讲述的“入赘于南王的队长”就显现出卡日卡兰部分氏族南迁的无奈之情。竹林战役后原本前往复仇的知本小队长却为南王美女所迷惑而入赘于南王,原先知本社群因为族人既已入赘南王,遂想要化干戈为玉帛,没想到前往探望入赘南王的族人时却受到怠慢,因此愤而南迁。此段叙事充分显现了过去知本与卑南(南王)权力转换过程中,知本系统的自圆其说。在汪美妹的口头叙事中并未解释为何知本小队长会为“人粪”而神魂颠倒,小说则以“人粪巫术”解释了复仇者为人粪迷惑之因。
大巴六九属于知本石生系统,是一个多源组成的部落,与鲁凯族的大南社、卑南族的吕家社、卑南社皆有密切渊源关系,而且“部落的Rahan(祭司)和巫术系统(temaramao)承传的相当完整”31。巴代祖居大巴六九部落,部落的多源族群关系和巫术传统可能是作家以诗意的想象与虚构缀补史事传说的依据,藉由虚构与想象合理化口述传说中的断裂。从口述史料的选择看来,作家仍然有自我选择立场的一致性,也许这也是小说舍弃引发卡日卡兰氏族南迁的竹林战役而从人粪巫术写起的原因。
五、结语
《斯卡罗人》一书的创作,所运用的大部分口述史料已经过了整理者串连多次、多人讲述资料成一整体的情形,间或有语言转译所产生的出入;再加上口述数据及小说创作在依历史时序进行下,使口述史料生成时间产生模糊化的状况。因此,尽管作者写作前从事了细微、谨慎的文化背景考据,但要以小说完整的呈现历史的真实面貌仍然是值得商榷的,但对于部族传说所显现的思想真实意义却是有价值的。
书写对象既然是没有文字的种族,除了口头传承外没有各族史料可作为探索的依据,因而民族的口碑传承往往就是族人的历史,也是他们的诗、文学及生活哲学。当历史文学化后,讲述者在叙事过程中所产生的诗意想象和个人诠释、合理虚构是无法避免的。杨南郡提及日据时期两本重要的调查著作《原语によゐ高砂族传说集》和《台湾高砂民族系统所属の研究》时说:
这两本被誉为台湾原住民族研究空前绝后的经典之作,就像两座矗立在沙漠中的大金字塔一样,崇高而孤寂。75年来,台湾的原住民研究者,都知道这二本巨著,也知道里面蕴藏大量宝藏,却无法进入一窥堂奥,更无法进一步的研究,这是学术界长久以来的重大遗憾与损失。32
虽然杨氏所说的是由于对地理阅读的障碍造成的,但是这两本记录了台湾原住民族各族复杂的系统族脉及传说的经典之作,对一般人而言恐怕还不只是地理上的陌生而已。巴代以卑南族巫术连结口述历史的写作,试图创作出能为读者接受的卑南族历史文化书写,实践作为族群作家的使命。《斯卡罗人》一书的历史背景距离1935年最早采录的移川大约达三百年之久,部落历史传承人虽然拥有超强的记忆力,甚至可以一口气讲述七、八代祖先的人名和事迹33,但部落史事传说往往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经过千百回传述,讲述者对于往事的超强背诵能力却无法证明为真实的历史,况且如海登·怀特所认为的,历史仍然富有诗性的结构。因此,在让部落新一代有机会看到小说形式部落史的诉求下,以小说为无文字民族写史也可能是另一种历史叙事的出路。虽然在选择、诠释与缀补的书写过程中,未必能真实呈现“以文写史”的企图,但部族传说背后所具备的思想真实,却仍然具有部落史参考价值。
【注释】
①移川子之藏调查资料参见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学研究室原著、杨南郡译注,《台湾原住民族系统所属之研究》(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11年1月)。
②宋龙生:《台湾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8年12月)。
③曾建次:《祖灵的脚步》(台中:晨星出版社,1998年6月)。
④孙大川:《以“文”作“史”——巴代〈大巴六九之大正年间〉》,巴代:《笛鹳——大巴六九之大正年间》(台北:麦田出版,2007年8月),序10。
⑥海登·怀特(Hayde White)著、张京媛译:《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包亚明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页590。
⑦巴代:《后记:便利与挑战下的乐趣与责任》,《斯卡罗人》(台北县:耶鲁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8月)。
⑧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根据事件的时间排列来编织“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故事,但是事件的时间顺序表可以编入某些数据也可以省略掉别的数据。这些数据本身就已经被置放进数据里,它们构成历史学专业中假定的领域。书同注5,页582。
⑨巴代:《斯卡罗人》(台北县:耶鲁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8月),页12。
⑩根据《斯卡罗人》一书后记,作者说明小说的创作是以前述三书为范本改写。但小说第二章注明出自陈实的材料,据查该资料为未发行之手稿,目前未见流通。陈实着、陈明仁译编,《台湾原住民族的来源历史:知本(Katipol)族民传说》,手稿,1997。巴代表示自己也未曾看过此本手稿,主要参考自宋龙生所著的《台湾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一书。(笔者透过邮件询问巴代先生相关问题,2012年4月)。
11根据整理者曾建次神父所言,本书数据涵盖1967至1970年间费道宏、山道明两位神父所采录及1988与文化大学金荣华教授合作采录之所得。
12《斯卡罗人》中取材自本书者有该书转引自Anton Quack编,洪淑玲翻译,《老人的话——知本卑南族发展史的传说》(1981);部分出自1994年南王李成加祭司长所述。
13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学研究室原著、杨南郡译注:《台湾原住民族系统所属之研究》,页2。
14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学研究室原著、杨南郡译注:《台湾原住民族系统所属之研究》,页3。
15同注13,页xxxiv。
16同注13,页3。
17曾建次:《祖灵的脚步》(台中:晨星出版社,1998年6月),页10。
18参阅曾建次《祖灵的脚步》,页8-9。曾神父说明当时这些采录资料曾用德文整理后出版,尔后曾神父去德国从图书馆中将这批录音带拷贝带回。
19Anton Quack编、洪淑玲译:《老人的话》(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未刊本)。
20曾建次:《祖灵的脚步》,页9。
21曾建次讲述,蔡可欣采访、整理,2009年1月9日,保禄牧灵中心。
22宋龙生:《台湾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页2。
23孙大川:《台湾原住民面貌的百年追索》,书同注1,页v。
24班雅明著、林志明译:《说故事的人》(台北市:台湾摄影工作室,1998年12月),页24。
25海登·怀特(Hayde White)著、张京媛译:《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页575。
26分别为1965年11.4、8.29、8.31、9.10、10.9、11.11~13、12.13;1966年1.7、1.14、1.26、1.29、2.1、3.24、3.25、8.11、8.18。
27参考宋龙生:《台湾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页162。
28同注26,页197。
29Anton Quack编、洪淑玲译:《老人的话》,页20。
30同注26,页215。
31宋龙生:《台湾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页211。
32孙大川:《以“文”作“史”——巴代〈大巴六九之大正年间〉》,序10。
33杨南郡:《译者序》,《台湾原住民族系统所属之研究》,页xx。
34移川在台湾东部调查时发现,托博阔社60岁的头目,可以从7带前祖先讲起,总数达到225人;古白杨社40多岁头目一口气可以背诵8代389个祖先的人名和事迹。《台湾原住民族系统所属之研究》,页xx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