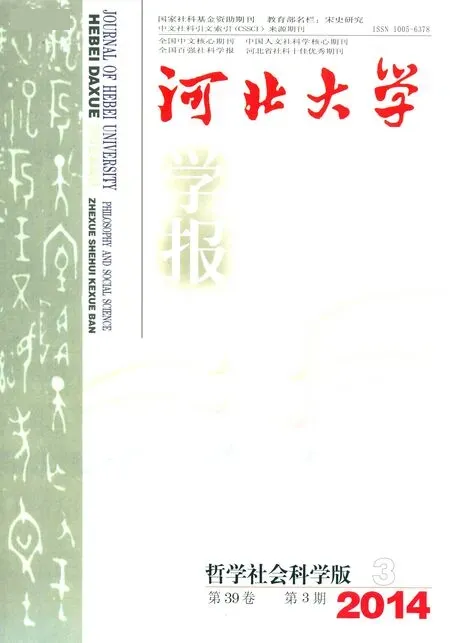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学校教材编译机构述略
吴洪成,王玉蓉
(1.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河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传教士的译书活动最早可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前,其中新教传教士翻译的关于非宗教问题的著作总数达108种,约占同期翻译著作总数的14%[1]591。鸦片战争之后,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传教士纷纷来华办学校、译西书。但是,世俗教育的规模不大,他们的译书活动基本上是各自为政,零星局部地进行。西学大规模引进,早期教会学校登陆,洋务学堂的兴办与学校教材编译的计划性、组织化几乎同步出现。洋务运动时期教会编译学校教材机构在近代教材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这项工作却是由来华以传播基督福音并借此扩张西方殖民文化的传教士承担,西学的传播、宗教的渗透与教育的革新并行,在教材编译中汇聚在了一起,发生了复杂而多元化的影响。本文拟对此加以探讨,因所涉问题复杂,加之作者学力有限,故不当之处,尚祈指正为盼。
一、近代学校教材编译机构产生的历史背景
随着新教传教事业发展,传教活动的某些领域中也出现了向专业化方向重要转变,最明显的就在医学和教育方面,当他们与单一的布道目的局部偏离或某些程度的分道扬镳以后,便具有半独立性,不论就学科教育,还是传教士本人而言,专业标准都提高了。向中国传播西方医学知识的重要媒介是医学著作,最著名的早期作者是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Benjamin Hdson),他编辑的书籍多年来都是标准读本,解剖学著作《全体新论》(广州,1855年版)被收入中国主要类书中,以此获得极高声誉。后来,美国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博士、英国传教士德贞(J·Dudgeon)博士及傅兰雅(John Fryer)等人都翻译了大量医学著作,其中包括诊断法、绷带包扎法、皮肤病、梅毒、眼病、炎症、医学原理和实践、药物学、热病、卫生学、外科学、解剖学和生理学。这些著作对读者的影响常常是传教士所不能直接作为的,他们有助于使日益增多的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接受西方科学知识。
19世纪70年代初以前,传教士设立的学校主要录取教徒的孩子,耶稣会士管理江南的江苏、安徽教皇代牧区,1878-1879年有345所男校和62 222名男学生,213所女学校和2 791名女学生,到19世纪最后几年,江南天主教学生的总数已逾16 000名[2]98。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带有世俗性的教育得到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肯定。根据1877年和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两次“在华传教士大会”的报告。教会设立的学校逐渐发展,初步统计:1876年,男日校177所,学生2 991人,男寄宿学校31所,学生647人;女日校82所 ,学生1 307人,女寄宿学校39所,学生794人,传道学校21所,学生236人。学校总数350所,学生总数5 795人。1890年,学生总数为16 336人。13年中,学生人数增加近两倍。约一万余人[3]73。
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东来,推动了西学东渐浪潮,在学校教育领域,引起了对旧式学校的非议。在中国,除了传教士办的许多教会学校外,国人也不断创设以西学为教育内容的新式学校,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并非传统儒学经典及据此而编的蒙学教材所能满足要求。于是,国内一批具有改革思想的先进人士积极谋求教材的革新,改造传统教材,使之部分地适应教育改良的趋势以及新式学校教学对新知识、新思想的要求。但是,教材建设仅靠少许改编课本并不能满足新式学校日益增加与学科课程不断细化的要求,因此需要设立专门机构以编辑教材。
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美华书馆、墨海书馆,是著名的早期译书机构。此后的一二十年间继续开设了几处译书局,传教士在华的译书活动没有很大的发展。此外,受当时译书风气炽热的感应,有的西学著作译述者还从事传播发行及推销的工作,如傅兰雅于1875年成立了格致书室,主编《格致汇编》长达15年之久,对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医学等知识都有介绍,开辟了趣味性较强的“格物杂说”“博物新闻”等科学栏目,介绍有贡献的西方科学家,成为近代最早的通俗科学刊物。格致书室同时又销售发行新式教科书,并译印了若干科技书籍。
中国近代学校教材早期发展史上最具里程碑式意义的是“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成立,这一以西学教材编译为职责的机构无论在文化、教育,还是在出版事业都有重要地位。与后继者中华教育会、广学会一样,他们都非常注重改善教会学校的实际教学困惑,编译各类学科的学校教科书,而且与中国教育有关的事务均在其关心范围。
二、学校教科书委员会
1877年5月,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根据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Mateer)的建议,大会决定成立“益智书会”,即“学校教科书委员会”(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从此正式诞生了中国近代编译出版教材的专门机构。关于该机构的产生及与新教育的关系,国外学者对此的分析或描述能增加我们的认识:
在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间,新教徒对于非宗教的教育普遍采取否定立场。但是,大约从新教传教士在华第一次大会(1877年)前后开始,情况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这次会议上,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恳求传教士同道们在教育方面负起更大的责任。虽然狄考文当时受到猛烈地批评。但是,冰层打破,后来10年间,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转而赞助他的立场了。主要有狄考文的发言引出了1877年会议的另一重要结果,即设立一个益智会,由傅兰雅董其事。此会的委员们信奉狄考文所提出的主张,即“教会学校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好的和适用的教科书”。[1]621
会议决定,任命丁韪良、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狄考文、林乐知、黎利基(Rudolph Lechler)和傅兰雅等组成委员会负责筹备编辑一套初等学校教材,以适应当前教会学校的需要。
委员会成立后,召集了几次会议,就下列各项决定取得了一致意见。
第一,议决:为筹备编写两套中文教材,即初级教材和高级教材,作好准备工作,两套教材体裁必须文理简洁;暂不翻成北京方言。
第二,决议:两套教材必须包括下列科目:
1.初级和高级的教义问答手册,以直观教学的形式,各分三册。
2.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
3.地质学、矿物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
4.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宗教地理以及自然史。
5.古代史纲要、近代史纲要、中国史、英国史、美国史。
6.西方工业。
7.语言、文法、逻辑、心理哲学、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
8.声乐、器乐和绘画。
9.一套学校地图和一套植物与动物图表用于教室张贴。
10.教学艺术以及任何以后可能被认可的其他科目。
“委员会”还商定初级教材由傅兰雅负责,高级教材由林乐知负责,并议决了教会学校教科书的编辑方针:
1.最好是编,不是译,文字用最浅显的文理、民族语言及风俗习惯,编写出将对中华民族产生强大影响的书籍。
2.这种书不仅为学生作读本,而且教员也可用于教学。
3.不仅教会学校使用,也着眼于让教会外学生使用。
4.这些书籍完成后,无疑地将为中国的学者和人民使用,因此最重要的应在使这些书籍有严格的科学性的同时,抓住一切机会引导读者注意上帝、罪孽和灵魂拯救的伟大事实。
“委员会”认为,“统一术语是另一种极为重要的事情”。为此要求作者:
1.把用来表达人名、地名和科学符号的公式列为一表,尽可能在工作之初寄给委员会秘书,供委员会对照比较。
2.对上帝、诸神、灵魂这些术语,同意每位作者自由选用,但必须在序言中加以说明。
3.完全出自本地的书籍和出自外国而发行人又不在中国的书籍应予仔细检阅,把使用的术语与名词分别列入不同的词汇表。并希望凡愿意承担这次工作中任何一部分的人都迅速将他们制术语和专有名词者所要使用的书籍名称通知秘书。
委员会应该做到:
1.应将作者或译者本人提供他们所使用的中文和英文词汇表收集起来,统一划分为三类,即(1)技术科学和制造类;(2)地理类;(3)传记类。然后印制成册,给参加这项工作的各寄一册。2.指定傅兰雅先生负责第一类词汇表的准备工作,其它二类词汇表交由林乐知牧师负责。3.请伟烈亚力先生提供专有名词的词汇表,并请麦加缔博士提供外国著作的日文编译本中使用的术语和名词表。[4]86-90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开始关注中小学教学的实际需要,在形式上有了“图说”一类的课本,在内容上开始着手将科学名词规范化和科学知识条理化,为近代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了最早的样板。所出版的有关数理化的教科书,介绍了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为数、理、化、天文、地理等学科编订了统一的中文译名,这在传播西学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5]126。
到1890年,“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自行编译出版书籍共有50种,74册及图表40幅。经审定合乎学校使用之书48种、115册,两项合计共98种、189册。这些书籍大部分都属于学校教材或教学参考用书,内容主要为自然科学知识。其中数学类有8种,科学类有45种,历史类有4种,地理类有9种,道学类(包括哲学和宗教)有19种,读本类有1种,其他12种。内容多涉及自然科学,如算学、西洋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科。教科书有《笔算数学》《形学备旨》《三角数理》《代数术》《八线备旨》《重学》等。另外,宗教书籍也占很大比重,如:《教会三字经》《耶稣事略五字经》《福音识字课本》《旧约史记课本》等[6]38。这期间,卖出了30 000多册书,该会的工作很快就自给自足起来。
在“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出版的教科书中,有傅兰雅所编写供初中或高等小学使用的图书(Wall Charts with Hand Books)13种,占37%,傅兰雅自费出版的供初级中学或高等小学使用的大纲性图书28种。也有统计称其中有12种是科学方面的,5种是附有手册的科学知识挂图,有8种科学须知[7]243。其中有关地理学的有1882年出版的《地志须知》,该书分6章,第1章略释地势名义;第2章论亚细亚洲各国;第3章论欧罗巴洲各国;第4章论阿非利加洲各国;第5章论亚美利加洲各国;第6章论太平洋列岛。在1883年出版的《地理须知》一书中,傅兰雅指出,从广义上看,“地理一学,所该甚广。如地质、地势、矿石、水泽、空气以及光热雷电、吸力、草木、禽兽、人类等,莫不属乎地理,盖地所以载物也。凡此诸事皆不能离乎地也。”因此《地理须知》中仅选择“地理至紧切者”来讨论。中国读者可以通过此书所绘制的地理学知识线,了解“西国地理大略”,能使中国人把真正意义上的地理学与“中土堪舆家专以地脉、风水、阴阳、宅寓愚惑庸众者”区分开来。
三、中华教育会及广学会
无论从扩大教务和防止“教案”来看,传教士们都一致认为,应在上层社会中传教。那么,在上层社会中传教采取什么方法呢?他们认为,“唯有广泛传播知识”,才是“医治莫名其妙的仇恨的唯一有效方法。这种仇恨集中在某些地方,使有社会影响的阶层不让外国人进入他们的城市”。所以,需要更多的科学、更多的报纸和更多的书籍,需要更多的公共演讲和科学仪器——不但要强调宗教,而且要强调健全的政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简明真理”[8]580。这实际上指明了传教重点转移到社会上层以后,传统“演讲福音”的传教方法应由科学布道和文化布道作先导。
随着传教士对宗教与教育看法的不断调整以及教材地位作用认识的日益宽阔,教材的编译机构与新教育设施的长足进展相得益彰。1890年开办了400所教会学校,包括许多专门学校和大学在内,与天主教主持的教会学校大异其趣,绝大多数新教的学校都开设有西学的教学科目。在这种背景之下,1890年,经在华基督教第二次传教士大会决定,将1877年设立的基督教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The Educal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其职能逐渐扩大。该会目标除了编辑适用的教科书以适应教学需要外,还提出“探求及研究中国教育事业,加强从事教学工作人员教授的互助”。推选狄考文为中华教育会首任会长,本年会员有35人,1893年会员有73人。1896年有138人,1899年有189人,会员均系从事学校工作的英美传教士,1915年改名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The China Christian Educational Association)。据现代出版家王云五所称,中华教育会“其目的在编译教育用书,供教员学生教学之用,期使中国青年学生由本国文字得窥西学的津梁”[9]10。1903年一年间,售出书价1万余元,所印书籍各科齐备。出版史家又称:“在革新运动时期(1842-1911年),教会经营出版事业的主要组织有二:中华教育会、广学会。”[10]382-383
中华教育会除编辑出版教科书,以适应教会学校的需要外,并审定科学与史地名词,同时还对整个在华基督教教育进行指导,举办各种讲习会、交流会、演讲会,交流和推广在华基督教教育经验,制定教育方针,教育计划与具体措施。不过,从整体来看,中华教育会在教科书编译发行方面远较学校教科书委员会逊色。从1890年至1912年的22年间,总共出书34种,且影响下降。甲午战争后,由于“开民智”与“兴学”热潮的出现,学堂自编教科书、留日学生翻译日本教科书,尤其是新式民营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会文学社、文明书局及中华书局等纷纷介入教科书事业,使得教会出版物开始逐渐冷清、低落。
传教士开办教会学校、编辑教科书,与绅士阶层发生了冲突,在传教士看来,布道会的工作触犯了地方社会代言人的绅士集团,因为布道会这样做就处在老师的地位上,发行宗教或科学书籍也会使他们受辱,因为这样也就等于认定中国传统学科体系并未保有全部真理和知识,同样,如果提倡发展西方的社会事业,就会使他们感到羞愧,因为这是暗示中国并未达到文明的顶点,而西方布道会却站得比他们更高。实际的情形虽然未必如传教士描述得那样严重,但当时中国社会上流的道德或精神主角绅士群体与中国文化之间水乳交融,更全面地坚持中国是一切文明的中心,传教士的活动与绅士阶层的冲突是必然的。广学会的创办目的就是想凭西学打入中国知识分子上层。
1887年11月1日由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在上海成立“同文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 ledge Among the Chinese),创办者是韦廉臣。1892年改称“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该会以“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相标榜。1887年版的《同文书会章程·职员名单·发起书和司库报告》对此作了较充分的记述。韦廉臣在《同文书会发起书》中写道:本会的目的归纳起来是,供应比较高档的书籍给中国更有才智的阶层阅读,供应附有彩色图片的书籍给中国人家庭阅读,目标是面向公众,包括知识界和商界,在向他们提供科学时,努力使之具有吸引力,达到他们能看懂的程度[11]35。通过发行、传播西方书籍,开发民智,是为了推动社会的变革。
1890年,韦廉臣因病去世,经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推荐,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继任。1891年精力旺盛的威尔士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它的总干事之后,他有力和富于想象力的领导下,这一组织不但大大扩展自己活动,而且采用新的方法,首先致力于劝说中国的社会精英相信西方文化的价值。而这时,中国的改良主义已逐渐兴起,他们尖锐地批评洋务派学西方的局限,提出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特别是政治制度。广学会以此为历史契机,一方面为了解决传教中来自上层的障碍,另一方面为顺应时局,希望他们所带来的信息,不仅可以解决中国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问题,还能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取得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可见,传教士的目标已对准上层社会。
李提摩太到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中国上层社会究竟有多少人可以作为广学会的读者对象,他对中央和地方的高级文武官员,府学以上的礼部官员、举人以上的任职和在野的士大夫以及全国的秀才和应试的书生都作了统计,一共得出有44 000名之众。李提摩太声称:“我们提议,要把这些人作为我们的学生,我们将把有关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育他们,直到教他们懂得有必要为他们的苦难国家采用更好的方法时为止。”[11]85
传教士通常都还没有以任何公开的方式向中国各种封建制度提出挑战,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后,中国早期的改良思潮一跃而为呼吁全面改革的维新变法运动,传教士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介绍的社会政治消息和理想,经常隐含公允激进的成分,使当时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特别是要求改革的维新派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及谭嗣同等非常地乐于引用和吸收。甲午战争后,教会的出版物流行更广。
1894年,广学会出版了李提摩太译麦肯西的著作《泰西新史揽要》,叙述了19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史和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对帮助中国人了解西方各国近世发展起到了一些启蒙作用。该书极受欢迎,中国书商一再非法翻印,据王树槐对相关文献的整理表明:
由于广学会的书籍销路日广,盗印之风愈来愈盛,因之林乐知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冬请驻上海美国总领事转函苏松太道,要求出示禁止。次年,英国总领事亦应李提摩太之请,函苏松太道,请作同样的措施。当局自然允其所请,“出示禁止”。谕禁的效果不大,盗印之风仍然不已。是年,上海英租界会審公廨曾查获盗印者罚款百元。但上海以外地区,则无人干预,盗印之风,有增无减。在杭州,《泰西新史览要》即有6种翻版。光绪二十四年,李提摩太报告,“四川一省,翻版至有9种。”其余可想而知[12]42
广学会出版物注重历史、理化、伦理及宗教等。在中日战争之前,教会出版物未为一般人所欢迎,及中日战争后,广学会刊行之《中东战争本末》因持论公允,记载翔实,实为当时唯一可靠的战事读物,并且书中内容清楚地表明作者所持改革派观点,因此,海内外争相传诵。据明恩溥(Arther H.Smith)称:清光绪帝曾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订购该年刊行的《万国公报》全部及其他一切出版物。可见该会的书籍在当时之风行,其“出版事业在革新运动时期进步之速可以概见”[10]283。
广学会在维新变法时期出版编辑的“西学”著作在维新时期的传播及作用十分明显。海外学者对之所作的评议,有声有色,颇为恳切:
1891年,李提摩太担任了出版这类著作的主要赞助机构广学会的总干事。广学会出版了他们译麦肯齐的著作(1894)和林乐知所编关于中日战争的书《中东战争本末》(1896)。每年广学会从销售出版物中得到的收入从1893年的800美元猛增到1898年的18000美元。1896年,傅兰雅兴高采烈地说:书籍生意正在全国迅速开张,这里的印刷商不能满足书籍生意的需要。中国终于觉醒起来了。广学会对扩大翻译和著作范围是有一定作用的。广学会所出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给中国维新派议论变法,改革政治以重要的依据。[1]632
梁启超曾对当时出版的一些西学书刊作过如下的介绍:
欲知各国近今情况,则制造局所译《西国近世汇编》最可读;癸末、甲申间,西人教会始创《万国公报》;通论中国时局之书,最先者林乐知之《东方时局略论》《中西关系略论》,近李提摩太之《时事新评》《西铎》《新政策》;西史之属,其专史有《大英国志》《俄史辑译》《米利坚志》《联邦志略》等;通史有《万国史论》《万国通鉴》等;《泰西新史揽要》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13]455
广学会的出版物不同于早期传教士的译书,也不同于“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及洋务派所办的译书机构—京师同文馆译书处(1867年)及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处(1872年)的译书。它侧重于编辑历史、地理、宗教等程度较高的书籍,鼓吹政治理想多于介绍政治内容,对中国维新派宣传变法、改革政治的主张有重要影响。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除纯宗教性书籍外,非宗教书籍及人文科学书籍占多数,其中,历史、传记、财经、社会改革方面占145种,教育、政治占40种,自然科学、工程学、医学书籍占31种。
除了专门机构有组织地编译出版教科书外,有的传教士在学堂教学中为解决实际教学的困惑,受早期教会学校教学改革的影响,也继承了传播西学、兴办学校的传统,依然自编教科书。以山东文会馆与苏州博习书院为代表。山东文会馆于1867年由蒙养学堂改成,创建者是传教士狄考文。文会馆的教学除了采用基督教出版机构印行的图书之外,他还与人共同编译教科书。1885年,他与邹立文共同编译《形学备旨》10卷,1891年译《代数备旨》13卷,1892年译《笔算数学》3册。1898年以后,各地一些学堂以此作为初等学堂数学教科书。其中《笔算数学》重印了三十次,《代数备旨》《形学备旨》也各重印了十余次[14]757。文会馆还编有《理化实验》《电学》《测绘》《微积习题》《英文字典》等讲义,供学生传阅。1893年,苏州博习书院传教士潘慎文(A.P.Parker)与谢洪赉合译《代形合参》3卷,次年又译《八线备旨》4卷。
上述种种,共同构成了以教材编译机构为核心的19世纪下半叶西方教会传教士在华西学教育的一道风景,并且,教材编译机构与教会学校的教育活动、办学实践及教学环节一起构建了西方教会教育办学模式的基本类型,它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传统学校教育以及由洋务派开端维新派拓展的近代新教育又构成了三足鼎立之势,显示出其与古代封建传统教育体制的本质差异,并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四、历史的影响
在教科书的编辑方针方面,“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及其后身“中华教育会”乃至“广学会”,都强调必须把宗教精神和教义贯穿在整个编写过程中。韦廉臣在第一届传教士大会上所作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科学和上帝的分离,将是中国的灾难”。如果实行分离,学生既不信仰上帝,又不相信圣贤和祖宗,将使中国崩溃,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拯救中国”[8]712。傅兰雅在1896年1月发表于英文《教务杂志》上题为《一八九六年教育展望》一文中写道:“基督教必须胜利,中国如要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要摆脱压迫者的压迫而获得自由,那就必须把智力培养和基督教结合起来。”狄考文在1877年第一届“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所作的《基督教教会与教育的关系》的报告中更强调:“虽然教育作为教会一种非常重要的机构,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它不能代替传教,传教无可争议地乃是教会最重要的工作。”[3]61
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向中国输入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及政治科学。两种使命的合轨并非偶然,如在传教士可借此一箭双雕:既可依此奇货,拉拢引诱中国一批士大夫拜服在他们脚下,又可以“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因为“这里有个暗合的逻辑”,重要的是这种科学“发源于基督教国家,……就是只有基督徒才能够发展出这种科学”[15]674。
传教士编译学校教材中当然也包括一些反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内容。但是,这部分教材的译述是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如果科学不是作为宗教的盟友,它就会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应当注意不要让“异教徒或基督教敌人来开动这个强大的机器,以至阻碍真理和正义的发展。”这说明,教会的一切活动,包括教育在内,最重要的目的在于传教,使人信教,最终要使中国乃至全世界“基督化”。在这样教育目的支配下的教材内容必然大量充斥着粗制滥造的宗教教条。对此,连狄考文都承认“教科书委员会出版的相当大一部分根本不是什么学校教科书,而不过是宗教传单”[16]239。
韦廉臣举了一个如何把宗教贯穿到数学教科书中的具体做法:“在这种场合,我将简单地介绍一下数词是上帝一切活动的基础……我将指出数学是创造论的基础,依据它而形成一切事物。可以论证:一是存在着一位上帝的意志,二是人类是由这个意志的形象所创造,因此能理解表达和阐明上帝的思想。”[8]519狄考文在《代数备旨》“序”中,讲述数学发展史后便说:“远涉中华,宣传神子降世,舍生救民之圣道,此固以道为重,望世人同登天路,而得天堂之永生也。”[5]125
伟烈亚力(Alexander Wgie)在他所译《谈天》一书的“序”中所说:“夫造物之主全智、巨力,大至无外,小至无内,罔不莅临,罔不鉴察,故人虽至微,无时不蒙其恩泽……余与李君(善兰)同译是书,欲令人知道造物主之大能,尤欲令人远察天空,固之近查已躬,谨谨焉修身事天,无失去秉彝,以上答洪恩,则善矣。”[17]42
近代自科学的成果到了传教士手里,竟变成了上帝创世论的“论据”。传教士波特永(Balduin)也承认,当时传教士编译的各种非宗教书籍,“其中都暗含有大量的基督教内容的观点”,甚至关于枪炮操作之类的书籍也不例外”[8]209。
镇江女塾是一所12年制的学校,其功课表列出第一年有“地理口传”,第二年有“地球风俗”,第三年有“地理初阶”,第四年有“蒙学地理”,第七年“地理志”,第八年有“地势略解”,第九年有“地学指略”,这里的课程名称与当时一些流行的教科书读本完全一样,如美国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编译、赵如光笔述的《地理志略》(上海美华书馆1882年版)、美国李安德(Leander W.Pilcher)著《地势略解》(1893年汇文书院排印本)、美国孟梯德著、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编译的《地理初桄》(上海美华书馆1899年版),这些学堂很有可能采用了这些译著作为本校的教科书。《圣约翰书院章程》则明确地列出了该校使用的教材,如第一、第二年地理志采用孟梯德的著作;第三年地理志采用富莱的著作。
传教士在传播基督的同时,为适应教会学校的需要,编译了学校教材,以供教会学校使用。以地理教材的使用为例,同时,有的教材也为当时中国早期的新式学堂所采用。例如,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附课程表所用数学书包括:《学算笔谈》《笔算数学》《几何原本》《形学备旨》《代数学》《代数备旨》《代数难题解法》《代微积拾级》与《微级溯源》。这些教材主要是由专门机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等组织编译的,虽然内容上强调“把智力培养和基督教结合起来”,但从教材的演变史来看,他们编译的学校教材,开始从内容、体裁以及编辑形式上都注重适应学校教育的需要,特别能充分照顾教师和学生的特点。因此,传教士专门编译教材的活动,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教材的诞生。学者就“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及“中华教育会”的历史地位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基督教东来以后,对于教育事业亦次第设施。但当时所谓“教育”仅为宗教附属品,故对于学校设备、教师资格、课程编制、教材选择,以及管理目标等皆无人研究,至于各公会间应当如何联络,如何共同策励进行,更无人顾及。及1877年举行传教士大会,教育事业始渐发达。当时一般主持教育之人以为教授上最感痛苦者,厥惟西学各科教材。于是,即将意见提出大会,而“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于是兴起。教科书大半属自然科学,算学、西洋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科,以适应社会之需要。在我国许多革新事业,都有天主教或基督教士所提倡,教科书当然不例外。1877年,即民国前三十五年,基督教徒举行传教士大会,并组织学校教科书委员会;1890年,即国民前二十二年,基督教会创办中华教育会于上海,编译出版各种教科书或讨论解决中国一般教育问题,这便是基督教传教士对于我国教科书的前驱工作。虽然他们的工作因种种关系,没有具体化。”[2]98
对这两个出版机构在教育史上的意义,著名基督教史专家程湘帆先生通过研究,得出这样的认识:
委员会颇能供给当时的需要,所编译的教科书为量也不少。中间大半属自然科学、算学、西洋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科,就现在眼光考虑起来,这些书籍的价值,似乎有限,但在50年前,实为创作,我国新学的机括,实在起端在这里。讲到委员会事业的目的,不过满足当时教会学校的需求罢了,但是间接贡献于我国教育和新文化的却是很大。[18]51-52
传教士想“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提高西方宗教的地位”,为此,他们从事许多文化活动,包括办慈善事业(学校、医院等)、办报纸、译西书,特别是专门为学校编译教科书,并且又力图把这些影响渗透到中国各个阶层,打入每个角落,特别上层社会,他们可谓费尽心机。但是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是很明显的,其结果却是将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传到了中国,使中国的整个社会风气、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新的制度、思想一定程度上战胜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思想。传教士的教育文化事业建设本身,如教科书编辑、科学名词的确定等,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受其影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维新运动及“新政”时期国家统一的教材编译机构渐次筹设,并逐渐确立近代学校教材的编审制度。
[1]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朱经农.教育大辞书[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3]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4]韦廉臣.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报告[C]//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曾钜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5]李兆华.中国近代数学教育史稿[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6]陈学恂.中国教育大事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7]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美国束华新教传教士评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8]ALEXANDER WILLIAMSON.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l[C].Shanghai:Appedix E,1890:7-10.
[9]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
[10]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18977-1931年)[C]//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现代编·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11]李提摩.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M].上海:上海广学会,1938.
[12]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13]梁启超.读西学书法[C]//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14]中华教育历程编委会.中华教育历程[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
[1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M].何兆武,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16]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7]何兆武.广学会的西学与维新派[J].历史研究,1961(4).
[18]程湘帆.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成立之经过[C]//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