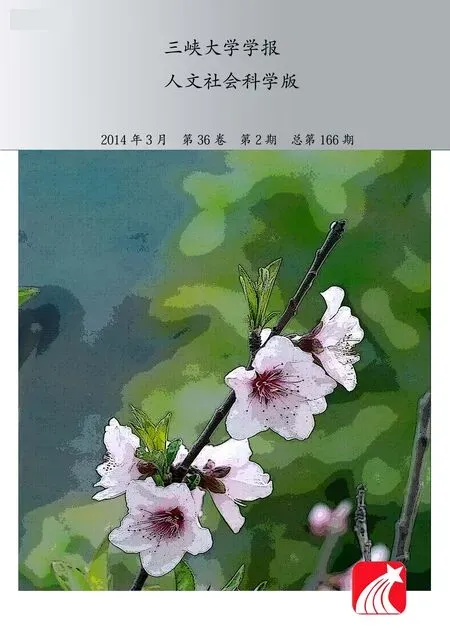在语言中诗意存在:论明“七子派”的文辞模拟观
闫 霞
(武汉纺织大学 传媒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学古人之文在于模拟古文辞
“七子派”是明代弘治时期崛起,前后影响明代文坛近百年的诗学流派,其诗学活动分“前七子”与“后七子”两个时期,追随者甚多。“七子派”在诗文创作上持“文辞模拟观”。
就散文来说,“七子派”推崇秦汉之文,认为秦汉之文有格有调,有骨有肉,有篇法、句法和字法,无论叙事还是刻画人物形象、表达情感,都有着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整个文章显得有生气、生机、生趣,堪称文章中“第一义”,所以他们主张要以秦汉经典之文为学习典范。其又认为学习秦汉之文的关键在于学习秦汉文的古文辞,即篇法、句法、字法以及语辞。
从“前七子”时期开始,“七子派”诗文创作上模拟古文辞的思想已经很突出。李梦阳云:“作文如作字,欧、虞、颜、柳,字不同而同笔,笔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长也、短也、疏也、密也。”[1]47他的这种模古思想曾遭到何景明的批评:“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镆(疑当作模),而独守尺寸。”[1]37“高处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己落近代之口。”[1]46何景明的批评使得李梦阳很恼火,他为自己的模拟行为进行了争辩:
古之工,如倕,如班,堂非不殊,户非同也,至其为方也,圆也,弗能舍规矩。何也? 规矩者,法也。仆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仆窃古之意,盗古形,剪截古辞以为文,谓之影子诚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犹班圆倕之圆,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1]46
李梦阳认为自己所模拟的只是古文辞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作文之“规矩”,即法,是文之所以成为文的关键要素,它又具体表现为篇法、句法、字法等。如果尺寸古法的前提是以我之情,述今之事,而不袭辞语,那当然可以,因为文学创作本来就是要遵守一定规矩,借鉴某些好的创作方法,包括篇章、句子结构及一定的用字技巧等。李梦阳所说的模仿诸如“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二”之类法则并无不妥,而且这种模仿也是创作出好的文章的必经之途,文学创造就是在借鉴基础上的创造。话如果只说到这里,李梦阳模拟古文辞的做法非但不是模拟,而且还是一种创造,但在义愤难平的《再与何氏书》中,他又说到:“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模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最终导出了其泥于文辞形迹的模拟观:对古文具体创作之法与古文言辞进行如模临古帖一般的模拟。李梦阳认为,只有模拟优秀的典范作品,创作法则与语辞都似之,才可能创造出与典范作品大致相当的作品。
在李、何之争中,何景明似乎显得较为开脱,不过与李梦阳一样同为学习古人文辞的提倡者,他首先仍是强调诗法、文法的不可易性,“射者不为人易其彀,琴者不为人改其操,故师可易,而法不可易也。”[2]与李梦阳所强调的“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二”、“开阖照应,倒插顿挫”之类的具体句法、篇法相比,他所强调的法较为抽象一些:“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也。”然而,他与李梦阳最不一样的是:“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1]37主张在遵守法度的基础上富于变化,守法只求大体,学古不求太似,认为这是一种“泯其拟议之迹,以成神圣之功”的高明的模古。然而在宗主李梦阳的极力鼓吹与提倡之下,追随者以模拟为能事,尤其是一些后学,没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流于简单模拟甚至抄袭,产生了很多流弊,李梦阳所说的“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变成了直接抄袭其辞,为我所用。正如“唐宋派”王慎中批评的那样:“今人何尝学马、班,只是每篇中抄得三五句史汉全文,其余文句皆举子对策与写柬寒温之套。”[3]
“后七子”登上文坛之后,又重新坚持“前七子”的模古主张,尤其是李攀龙,在诗文领域全面继承了李梦阳的文辞模拟观。李攀龙还为模拟古文辞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拟议成变,日新富有。能为献吉辈者,乃能不为献吉辈者。”[4]他以“胡宽营新丰”的典故引出他的模拟观:“拟议以成其变化”。其云:
胡宽营新丰,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鹜于通涂,亦竞识其家。此善用其拟者也。……古之为乐府者,无虑数百家,各与之争片语之间,使虽复起,各厌其意,是故必有以当其无,有拟之用。有以当其无,有拟之用,则虽奇而有所不用也。易曰: “拟议以成其变化,日新之谓盛德。”[5]
“胡宽营新丰”是怎么回事呢?刘邦得天下之后,定都长安,而“太上皇思土,欲归丰,高祖乃更筑城寺市里如丰县,号曰‘新丰’,徙丰民以充实之。”[6]能工巧匠胡宽,按照沛地丰里的模样在长安附近建造了一个与旧丰一模一样的新丰县。由于规格模样与旧丰不差分毫,所以从旧丰迁来的人,一到新丰,在路头停望一下就能知道哪室是其家,犬羊鸡鹜亦识其家。这样,太上皇又看到了熟悉的丰地,体会到了丰地的乡风民俗,如真在老家一样,也就不再思归,安心呆在长安了。李攀龙称赞胡宽营新丰为“善用其拟者也”。然而,由于地理条件不一样,与旧丰外表一样的新丰,里面的建筑定会因地理条件的不同而有新的改变,所以新丰并不等同于旧丰,模拟旧丰而又有所变化。这就是李攀龙所说的“拟议以成变化”,如此方为善拟。但实际上李攀龙在创作实践中拟议有余变化不足,甚至不惮于抄袭古文辞。
“后七子”中的其他成员如谢榛也是很赞成诗文模拟的,他所论主要在诗,但同样可以表明他论文的态度。其在《四溟诗话》中云:“学诗者当如临字之法,若子美‘日出东篱水’,则曰‘月堕竹西峰’;若‘云生舍北泥’,则曰‘云起屋西山’”。他所说学诗当如临字之法,主要是针对初学者而言的,对于初学者来说,一定要模拟经典作品,这是一个学习的必经阶段。谢榛虽主张模拟,但又说“作诗最忌蹈袭”,要求模拟古文辞做到“虽有所祖,然青愈于蓝”,能够化陈腐为新奇。王世贞与“前七子”中的何景明观点相似。何景明主张模拟不必太泥于形迹,要领会神情,临景构结,王世贞则主张“妙拟”:“分歧逞力,穷势尽态,不唯敌手,兼之无迹。”[7]不能陷于形迹之剽窃。相较于李攀龙,王世贞和谢桢在诗文创作上直接模拟古文辞的程度要轻微一些。
可见,从“前七子”到“后七子”,诗文创作一直贯彻“修古文辞”的主张,李梦阳、李攀龙更是主张字模句拟,越似越好。对于李梦阳、李攀龙等前后七子来说,他们学力深厚,文学修养与鉴别能力都高人一筹,所以,他们的模拟之作往往能够实践他们的主张,在拟作中既可述己之情,又可以有所变化。但对于学力不够的追随者来说,就势必会产生误导,一些才力不够的人以此为借口,强一点的割裂古文辞,饤字饾句,更多的人是抄袭剽窃,自谓能文,产生了很多流弊。“唐宋派”与公安派对此都有批评。
二、在互文本关系中与经典并存
受“七子派”文辞模拟观影响,其追随者在诗文创作上产生了严重的模拟流弊,李梦阳、李攀龙并不是没有看到,但是他们为什么还是力主拟古呢?这显然仅从“复古”角度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在明代,少有人反对复古、宗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反对“七子派”拟古的声音呢?而且,尽管批评声音不断,李梦阳、李攀龙还是以家长式的作风推行拟古主张。李攀龙的模拟程度更甚,其拟乐府的创作基本上奉行的就是一种“拿来主义”,将原乐府古诗直接拿来,只改动几个字,就成了他的作品了。比如他模拟《翁离》,古乐府原作为:“拥离趾中可筑室,何用葺之蕙用兰。拥离趾中。”李攀龙的拟作为:“拥离趾中可筑宫,兰用葺之艾尔蓬。拥离趾中。”只改了五个字,其它照抄不变。其他如拟《东门行》、《战城南》也只是改动了几句而已。当年李梦阳号召模拟,尚说不袭其辞,到李攀龙这里,不但主张袭法,亦不惮袭辞了,真正实践了李梦阳所说的“模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模拟理论。然而李攀龙对此却是振振有辞,说是“拟议以成变化”,自信满满。难道他真的是一个理直气壮的盗窃者吗?并不是这样的。李梦阳、李攀龙的自信说明他们这样做自有他们的道理,只不过他们的想法没有被人完全理解。可见,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此问题。
无论是前后七子,他们都主张修古文辞,而文辞是属于语言方面的要素,我们不妨借用一下现代西方语言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对以李梦阳、李攀龙为主的“七子派”的文辞模拟观进行一番研究。实际上,李梦阳主张“模临古帖,即太似不嫌”,李攀龙主张“胡宽营新丰”式的成其变化的拟议,并在创作中不遗余力加以实践,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诗文的创作可以靠与经典文本之间的关系来生产新的意义,从而获得与经典同样的存在价值。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论及福楼拜的作品时说:“这篇作品从一开始就形成于知识的空间里:它本身就处于和其它书籍所保持的基本关系之中……它所从属的文学只能依靠现存作品所形成的网络而存在,也只能存在于其中……福楼拜之于书库类似马奈之于美术馆:他们的艺术往往屹立于洋洋典籍之间。”[8]117李梦阳与李攀龙的模拟作品,与福楼拜的作品一样,是形成于知识的空间中,它与原作品及原作品同时代的其它作品之间都有着联系,即互文本关系,这些模拟作品靠与原文本及原文本同时代其它文本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而产生意义,再与本时代的语境交织,以此生产出更多的意义,作品的意义就在这些意义网络中衍生。
下面试对李攀龙作品进行个案分析对此加以说明。以《战城南》为例: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 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俳徊鸣。梁筑室,何以南? 何以北? 禾黍不获君何食? 愿为忠臣安可得! 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古《战城南》)
战城南,走城北,转斗不利号路侧。谓我枭骑:“且行出攻,宁为野乌食不逐。”驽马徘徊蒲苇中,水深黝黝,蒲苇骜骜。乌亦自不去,客亦自不豪。梁以集,乌子五,乌母六,禾黍不食攫腐肉。愿为忠臣何可覆? 伤子良臣,良臣诚可伤。远道之人,枯骨何葬! (拟《战城南》)
乍一看,李作与古作几乎一模一样,从句数上来看,两作都有二十句,每一句的句式结构、字数基本相同。两作的物象与情节也基本相同:出征、战斗、战斗之惨烈、良臣之叹、兵士之惨、乌食腐肉等情节都具;我、马、乌、水、蒲苇等物象皆有。只是李攀龙的拟作在第六句上是一个七言杂句“宁为野乌食不逐”,而古作是一个五言杂句“野死谅不葬”,其它句式完全相同。于是,读者就会有一个印象,认为李作字比句拟,全然为赝品。其实并非如此,李作在保证与原作的叙事情节、物象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打破了古作的情节顺序与物象分布,对一些物象进行了融合改写再创造,从而产生新的意境、生成新的意义。
下面就对这两篇作品进行具体分析。首二句,二作句式相同,但是李攀龙的拟作改变了一个情节,即改“乌食腐肉”为“士兵号路侧”,改变了一个动作,即改“死”为“走”,这样,李作与古作就有了不同。古作先写战争之后静态的惨状,以上空盘旋鸣叫的乌鸦加以衬托,用的是倒叙手法;而李作先写动态的战斗及战斗失利,是顺叙手法。古作以奇特的想象接着刚才的死亡场景,写死去的士兵要求乌鸦代替远方的亲人为自己哭嚎,而李作则顺接着写战斗失利后发起二次进攻,以将领与兵士对自己的马匹所言来表明这一事件的发生。
第三个情节,古作是回顾当时激烈的战斗,李作则写出征及战斗结果。在这第三个情节上,两作的本质区别显现了出来:古作对激烈的战斗进行了渲染:“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裴回鸣”,突出战斗的激烈与艰苦,而对战争结果只一个“死”字交待之,显示的是一种悲壮的英难主义;李之拟作中,战斗这一情节多了一个出征事件,“且行出攻”,战斗失利后不得已要再次发起进攻。古作中也有出攻事件,但不是像李作一样与一次战斗联系在一起,古作中的出攻事件放在了诗的最后,说明战斗是非常平常的事件,战斗之后当然会有一部分兵士死亡,但这并不说明战斗失利了。从后面虚化的情节、议论、感叹来看,古作突出的是边关将士守卫国土做出了巨大牺牲,这些爱国将士的精神是应得到褒奖,他们也应被思念、怀想的;而李作却将战斗经过省略,直接写战斗结束后的结果:“驽马徘徊蒲苇中,水深黝黝,蒲苇骜骜”,没有突出的英雄主义,诗句中突出的是“悲哀”之情。古乐府中那种悲壮的战争英雄主义在李之拟作中被消解了,战争中悲壮的牺牲精神没有了,因为“乌亦不自去,客亦不自豪”,笼罩在人们心头与盘旋于头上的都是死亡的信息。李作再接着写伤亡之状,而古作是放在诗的开头写的。再后面的情节,两作基本相同:良臣之思、良臣之伤。
李作除了在第三个情节中消解了古作中的战争英雄主义,又接着动态地渲染死亡的惨状:“梁以集,乌子五,乌母六,禾黍不食攫腐肉”。古作中也有“乌食腐肉”的情节与意象:“野死不葬乌可食”,是放在句首的,且并没有给予特别的渲染,在古作中,这种景象只是战争的正常结果罢了;李之拟作则对古作中较为简略的“乌鸦”这一意象加以突出、重构,以实代虚,将此意象具体化、群体化,以突出战争之残酷,死亡之惨烈。古作中,乌鸦的形象并不突出,重点在于战斗的激烈,而拟诗重点不在战斗本身之激烈,而在战争中兵士死亡之惨,这重点是靠“乌鸦”这一意象来加以突出的。为此,李攀龙借用了古乐府《思悲翁》中“枭子五,枭母六”这一群“枭”的形象,加以嫁接改造,一方面重构了“乌鸦”这一表现战争伤亡之严重的群体意象:“乌子五,乌母六,禾黍不食攫腐肉”;另一方面,这又使其诗与《思悲翁》发生了联系。《思悲翁》是伤功臣之诗,于是李之拟作由《战城南》中的良将之思转换为功臣之伤。由此,李攀龙的拟作不单纯只与古作《战城南》发生联系,也与《思悲翁》产生了联系,与《思悲翁》中的意象、主题产生了联系。
这些都使得李之拟作的意义再次生产,与原古作的意义也有了不同。古作之中所描写的战争毕竟是盛世的开疆拓土,在战争上占有主动位置,而明时,开疆拓土的能力已很有限,被动的卫土之战,却仍死亡无数,“远道之人,枯骨何葬”,个中滋味是何等不同,而忠臣良将在明时的结局又是多么可悲!“秦时明月汉时关”,“古来征战几人还”,汉高祖时,功臣得到的是“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而明太祖时又何尝不是如此心狠手辣,嘉靖帝时,良臣忠臣又有几个得到好的结局,比如好友王世贞之父,因战事失利而被奸臣昏帝所害,崇祯帝时的忠臣武将袁崇焕亦为帝处死。历史、现实、未来,在明这样一个帝国中,在君臣失和的政治氛围中,良臣之伤这样的事情并非只是偶尔发生。这样,拟作不仅与古代的优秀作品,亦与作品背后及作者所处时代的语境发生联系,从而生产出与古作有所联系但又不同的、更加丰富的意义。
李攀龙为钱谦益所不齿的模拟之作《陌上桑》亦是如此。李攀龙拟作《陌上桑》,字句相同的比例更大,有的句子一字不改照抄,有的改动一两个不关痛痒的字,遭到了许多人的诟病。尤其是他在这篇拟作中凭空加进了《孔雀东南飞》中的人物,作为“西邻焦仲卿,兰芝对道隅”,被钱氏冠以“窃”的罪名。
其实,李攀龙将秦罗敷与焦仲卿、兰芝扯上关系,也并非是凭空捏合,在《孔雀东南飞》一诗中,焦仲卿、兰芝、秦罗敷三人之间已经间接地产生了关系。焦母欲辞兰芝,对仲卿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李攀龙说秦罗敷“西邻焦仲卿”并没有错,还给人造成一种真实感,似乎三人是历史上确有的人物,焦、兰之事也确实发生过。如此,那么焦、兰之事便是真实之事,焦仲卿与兰芝有如磐石一般坚贞的爱情,也成为一个事实,罗敷对使君说起二人,就等于向使君说:我罗敷忠于爱情就如焦、兰二人忠于爱情一样,于是,罗敷与夫君爱情坚贞的意义便自动产生。同时,读者在阅读李攀龙的拟《陌上桑》时,《孔雀东南飞中》中描写焦、兰爱情坚贞的诗句亦会在诗外呈现,映入读者的脑中。这样,李攀龙巧妙地利用互文本关系,使其拟作在与由古代优秀作品构成的知识网络发生联系时自动生产出更加丰富的意义,且能比原作更好地表现主题。所以,李攀龙的《陌上桑》虽模拟严重,艺术美感也比不上古作,但仍然有其独特之处,也就有了与古作并存的价值,这样,他的模拟之作也就成了有意义的创作。正如米歇尔·布托所说:“从某种程度上说,哪怕是原封不动地引文也已经是戏拟。只要将某段文字单独提取出来,便已经改变了它的意义”[8]116。
所以,在互文本与互文性关系中,李攀龙的模拟之作的意义极大地得以膨胀与延伸。福楼拜等大师们的作品,往往屹立于洋洋典籍之间,并与那些典籍一样也在文学史上获得了不朽的价值,李攀龙的作品徜徉于古代优秀作品之间,其拟作与古之经典作品发生联系之后,靠与经典作品互文本的关系生产出自己作品的意义,这样,也使得自己的作品获得了与经典作品一样的存在价值。
三、为情感与精神寻求最富诗意的寓所
“七子派”所说的文辞,属于文学的语言创造范畴,他们对古文辞的极端重视,强调对古文辞的模拟,其实也是对语言自身魔力的崇拜。一方面,他们认为通过模拟古文辞,可以使自己的作品获得与经典同样的价值,像经典那样存在于知识网络中;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语言可以为自己的情感与精神提供诗意的生存空间。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寓所。人栖居于语言这寓所中。用语词思索和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寓所的守护者。”[9]93“倘无‘语言’,我们的存在必暴露在陌生与敌对世界的侵袭之下,无家可归;‘语言’恰如栖居地或掩蔽所,令‘存在’恬然安置,如在‘家’中。”[9]98
对于散文来说,秦汉与唐宋散文都非常优秀,为什么“七子派”主张学秦汉而不像“唐宋派”那样主张学唐宋文呢?关键在于“七子派”与“唐宋派”对“存在”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七子派”所认为的“存在”,是个人美学化了的情感性的精神世界,而“唐宋派”心目中的“存在”,是理性的“道”。
“前七子”崛起于弘治时期,这时期的君主较有作为,倚重正直士人,虚心纳谏,广开言路,于是士气日渐高涨。“前七子”这些郎署之臣意气风发,他们结社为文学,重气格而反对萎弱的“台阁文风”。在创作上重在表现这气格浑健的情感性的精神世界,将高昂的士气美学化。在散文的写作上,他们在秦汉优秀的散文创作中找到了这种与之相互共鸣的有美学意义的情感性精神世界。秦汉散文,自我精神肆意张扬,才气纵横驰骋,情感抒发酣畅淋漓,展现出自由精神的快意与美感,于是“前七子”选择以先秦散文为师法对象。“后七子”所处的时代氛围与“前七子”时期不同,此时政治腐坏,君臣关系紧张,文人的气格却更盛,更希望通过作品达到精神上的自由,彰显独立的人格,也更希望在文学作品中营造自由的存在世界,让心灵、情感、精神在此诗意地栖居。在散文方面,他们同样推崇秦汉之文,提倡模仿先秦之文的文辞。李攀龙更为极端,达到“非古辞不文”的程度,这从袁宗道的批评可以看出:“今却嫌时制不文,取秦、汉名衔以文之。观者若不检《一统志》,几不识为何乡贯矣。”[10]
为什么在先秦散文中寻求到类似的情感,类似的精神世界,就非要模仿其文辞呢?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语言是存在的寓所”,“七子派”所推崇的文人自由精神、气格最先正是安置在先秦之文的文辞中,是秦汉散文语言最早表现了这种“存在”,创造出他们所向往的富有诗意的精神家园。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美学曾深度探讨了语言与存在的关系,他说:“语言,凭借给存在物的首次命名,第一次将存在物带入语词和显象。这一命名,才指明了存在物源于其存在并到达其存在。”[11]这样,在原初的意义上,“语言”就不是简单或低级的表达工具,而是“存在”的呈现途径。作为呈现“存在”的语言的本质在海德格尔看来是“诗”,诗在语言中产生,语言保存了诗意的原初本性。也就是说,文学的语言,不单保留了原初意义上的存在物的命名,承传着语言原初意义上的诗性,同时,诗性语言还给情感与思、意命名。文学语言是诗意的语言,它不是形而下的琐碎的日常生活语言,也“未受到形而上学污染”,它是情感性的、美学化的,而不是体现着“道”的逻辑语言。
秦汉之文辞,包括言辞与言辞的传达方式,记录着士人某些情感与意念的最初诗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因了最初的诗性与历史意味的积淀,而显示出丰富的内涵与美的意味来。当“七子派”在现实语境中的某种诉求、情感与秦汉之文中某些由特殊结构、意味所凝结而成的文辞体现出来的情感与诉求相谋和时,他们认为那种原初创造的文辞是最好的、最有效的、最有表现力的。无论是先秦时期诸子散文中体现出来的那种自由风范,还是司马迁的叙事中显现出来的飘逸之美,都无不符合“七子派”精神世界对自由与美的诉求。秦汉古文辞为士人情感性的精神存在提供了最富于诗意的美的居所,秦汉优秀之文也成为文辞与自由之精神、情感、气格结合得最完美的典范。所以,无论是李梦阳还是李攀龙都对模拟古文辞有着强烈的执着,他们认为文辞意味的丰富性与诗性使模拟之作自然而然可以显示出某种“意”与“情”来。尤其是“后七子”,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无法找到新的思想出路时全身心转向文艺,在文艺中安顿心灵时,欲为自由的美学化的精神“存在”找到诗意的栖居之所,他们模拟古文辞营造一个与古人相差无几的诗意居所,安置那份自由的情感性的精神。
而唐宋文所表现的存在“道”,不管是“精神”、“神理”还是“万物之至情”,归根结底都是上升到形而上的某种“情感”与“精神”,而不是富于美学意味的个体精神与情感。这与“七子派”所追求的“存在”——充满气格的情感、自由的精神——是有很大差异的。而且,表现“道”的唐宋文的文辞实际上是一种逻辑语言,它是理性的而不是诗性的,因而也就缺少“七子派”所追求的美学意味,不能安其诗意的情感与精神世界,所以他们主张模拟秦汉而舍唐宋之文辞。
通过从语言的角度,以现代语言学理论的一些观点对“七子派”的文辞模拟观进行观照与分析,我们就走出了“复古论”对其无法透彻圆融解释的困境,对“七子派”的文辞模拟观有了新的认识。“七子派”在诗文领域主张模拟,模拟古代优秀的创作,一方面是着眼于创作本身。因为古文辞以它的不可替代的创造性所体现出来的经典意义,可以成为其学习的典范,并且可以成为其模拟作品的意义的起点,在因文辞的关系而与经典文本产生互文本关系之后,其模拟之作亦有了独特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是为诗性情感、自由精神寻求家园,通过模拟呈现这种情感精神的最早的语言,为自己当下的情感与精神世界营造一个与古人类似的诗意居所。这样的追求也使得“七子派”走向纯文艺,为明代营造了偏重于文艺的风气,自身也成为其他文学宗派批评与论争的对象,从而奠定了明代文坛热闹繁荣的局面。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 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何景明.述归赋序[M]//何景明.大复集:第1 卷.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王慎中.寄道原弟书第八[M]//王慎中.遵岩集:第24 卷.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徐中行.重刻李沧溟先生集序[M]//徐中行.天目集:第13 卷.明刻本.
[5]李攀龙.拟古乐府自序[M]//李攀龙.沧溟集:第1 卷.明万历刻本.
[6]班 固.汉书:第1 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王世贞.艺苑卮言[M]//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M].济南:齐鲁书社,2005:1930.
[8]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 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9]王一川.语言乌托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10]袁宗道.论文上[M]//袁宗道.白苏斋类集:第20 卷.明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