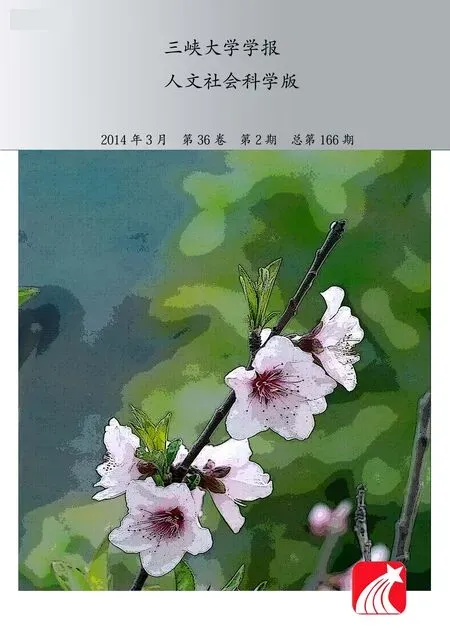试析抗战时期共产党与农民、地主之间的关系
——以三角形架构分析为视角
梁丽辉, 耿幸宏, 李静体
(1. 河北金融学院 社科部, 河北 保定 071051; 2. 天津青年职业学院,天津 300191)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与农民及地主的关系可能比较明朗,即共产党是领导者,农民是主力军,地主是既受打击又被联合的对象,所以这方面详细探讨的文章不多。但进一步考察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农民的心态,地主的行为以及共产党与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毫无价值,这对于当今共产党执政时期如何更好地了解农民需求、调整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无裨益。鉴于此,笔者拟对这些问题试做粗浅分析,恰当与否,还望广大学贤共同讨论。
一、共产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积极探索治理乡村的政权建设道路。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原有村政权之外组织农民建立农会,以行使行政、司法、武装等权力,达到“一切权力归农会”。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内,共产党不再另建一套行政系统来实行统治,而是致力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通过每年一度的村选来改造旧政权,最终使村政权移易到农民手中。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不争的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敏锐地意识到了。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曾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中国”[1]61;“除非发动农民群众的人力和物力,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2]9。彭德怀也有句名言:“人民是海洋,我们是在海洋中游泳的鱼。”[3]175可见共产党是要依靠农民为根基和主力来打这场战争,进而求得民族独立。
但中国农民对政治的冷漠麻木根深蒂固,即使他们有保“家”的防御本能,也不具备救“国”的崇高意识[4],夺取政权成为主人翁更是难以企及的精神奢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领导者,就在于其能高瞻远瞩,对农民的行为洞察秋毫。为了唤醒农民沉睡已久的政治参与意识,其在根据地积极抗战的同时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而政治和经济变革无疑又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因为“只有迅速地实行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才能得到农民的合作。”[2]9政治变革主要是通过村选使农民群众成为权力的主角;经济变革则是通过减租减息、互助合作、实行统一累进税来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生活。这两种变革起步较早——如晋察冀边区一成立就开始了村选;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宣布了减租减息——但却都是在1942年以后才逐步完善、蓬勃开展起来的[2]27-29。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从中国共产党来看,任何一项政策措施的颁布与实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时间,这可以说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除了地主的阻挠破坏,最主要的就是农民心态。
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战争是他们熟悉的一种灾难,社会变革却是一种新鲜事[5]334。他们宁可贫困下去,也不愿冒这个险。“安全第一是农民的生存经济学,它远远优于经济利益。”[6]12,36在变革初期,因为地主往往以进行报复来要挟[7]20-28,使得本来就保守的农民欲进欲退,“一些农民在地主在场的情况下,仍然有些不安。在第一次会议上,一些佃农蹲在人群前的一块大石头上,恭敬地给正被人们议论的地主让座。”[2]182因为“长期的经验告诉他们,各种军队来了又走,标语贴了又被雨水冲掉,但地主却始终存在……封建的恐惧传统不可能一天就消除”[2]183。
为此,中国共产党下了很大力气来改变农民的“奴隶思想”、屈从态度。方法主要是让农民讲述自己遭受的残酷剥削和蒙受的耻辱,帮助他们分析受苦的根源,也就是“挖苦根”、“诉苦水”。通过这一过程,农民认识到自己原来是“类存在体”[8],其低下的地位通过自身是可以改变的。这就强化了农民反抗地主的思想,提高了其阶级觉悟。但农民毕竟是小生产私有者,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一旦发动起来,便又过于激进,出现过左的现象。农民认为地主不倒,自己就不能彻底翻身,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推翻地主,平分土地”[9]187。但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始终坚持不让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党教育农民“中国的土地属于日本还是属于中国,比它属于地主还是农民更重要。减租使地主能够存在下去,又有助于孤立日本人”[2]187-188。通过深入解释,农民终于与地主达成妥协,建立了统一战线,党作为政治领袖的“精英意识”终于被普通民众所接受[10]。可以说,是共产党领导农民一步步由保守、激进逐渐走向成熟的,共产党是农民的引路人,在当时就是农民的准救世主。
但再详细分析一下政治和经济变革,我们会发现,二者有很大不同。1938年3月开始第一次村选,到1942年,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民主村政权基本上已普遍建立起来,如建立了村民代表会,实行了“三三制”、简政等。而早在1937年就宣布的减租减息,直到1942年2月才制定出详细的条款,其效果也只是到战争的最后两三年才体现出来。统一累进税在1941年才实行,大生产运动从1943年底才开始[2]27-29。很明显,经济变革是滞后于政治变革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民众意志是顺从于党的意志的。
就共产党作为领导者而言,民族独立,人民掌权是第一位的,哪怕最基层的村政权也是如此。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最主要的就是帮助群众夺取村政权。而且,在村选中一再强调“村长的人选,一定要掌握在党员和进步分子手中”[11]525-538,一定要保证党的绝对领导权。
但就农民而言,经济上翻身才是第一位的,“农民之所以投身革命,与阶级斗争、民族主义、政治参与都关系不大,他们是想借此改变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10]他们想要的就是吃饱穿暖,而不是享有什么政治权力。这是赤贫国家长期挨饿受冻的民众一种本能的反应,濒临生存边缘的农民是领悟不到政治权力会带来经济效益的。这对于初期村选有些农民不愿当村干部怕耽误生产似乎不难理解了。
但共产党并没有因为要依靠农民就完全顺应农民,其没有首先满足农民的第一要求,而是让农民先夺取政权,之后再致力于发展生产。事实证明,共产党的选择是正确的。但同时也说明,农民在当时起了重大作用,若没有农民的支持与合作,没有农民这个坚实后盾,抗战很难取胜,共产党也很难最终取得政权。总之,共产党与农民通过合作是互惠双赢,都达到了自己的意愿。
二、共产党与地主之间的关系
共产党天然的同盟军是农民,农民天然的敌人是地主。但地主在抗日战争时期却不是党的天敌,而是“不能没有或不能丧失的抗战同盟者”[2]47。抗战时期的第一要务是取得抗战胜利。因此,共产党必须集一切人力物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抗战。
在中国农村,“人”多者是农民,“财”大者为地主。共产党若想二者兼得,必须在他们中间寻求平衡,这个平衡点就是抗日,因为“敌人的这一灭亡中国的政策,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国人的,不但是对下层民众,而且是对上层人员——当然对后者稍为客气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别,并无原则之分。无论是农民、地主或商人,都痛切地感到‘活不下去了’”[2]47!所以,农民和地主这一对矛盾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但共产党与他们的关系却有很大不同。“人”是瞬间所不能得到的,但“财”却可以。党以“人”为先,把农民放在第一位,作为主力军;地主的“人”和“财”都要,“因为边区的建设极需利用他们的财力和知识”,同时,“他们就不会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导致经济状况恶化和增加军事困难”[2]12。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达到依赖地主的程度。
共产党对地主的态度很明确:要在农村建立民主政府,必须摧毁地主的统治,不允许地主维持现状。但由于抗日需要,农民和地主必须在调节各自利益的基础上建立统一战线,形成一个“异质共同体”[12],其中农民是“主导利益主体”,地主是“非主导利益主体”,换言之,农民是抗日的主力军,地主就不可能成为主力军,那地主的路就只有两条,要么被彻底消灭——这是农民的愿望;要么居于次要地位——这是共产党的意图:“让地主提供钱、粮来帮助抗战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样能把地主放在次要地位,吸收和利用他们。”[2]53
但地主不可能如农民所愿,也不会欣然接受共产党的安排。地主阶级一旦发现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就会本能地用所能采取的种种手段进行反抗。这些反抗也主要是在1940、1941年以前,因为那时对地主的政策还没有完全制定出来[2]56。对于共产党,地主阶级最初也不了解,主要采取收买政策,“他们愿意拿出枪来,拿出人来,要我们派干部去,要我们给他们名义。但是我们的干部一去,他们就千方百计引诱我们的干部腐化,他们的企图是‘枪不离手’,‘人不离土’。这样,他们有了名义,有了武装,就到处反对政权,反对合理负担。”[13]当然,共产党是不允许地主积极反抗其政策的,对“一些死硬的不听劝告的地主,必须采取暴力的斗争”[2]53。
地主笼络不了共产党,转过来就采取各种办法来对付农民。首先向农民宣传“变天”思想:共产党是呆不长久的,国军马上就打过来,要农民考虑以后的光景。这使得农民在对地主将要采取果断行动时变得犹豫起来。在减租的问题上,地主主要是向佃户进行威胁:如果要搞真正的减租,就收回土地。这使得“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广泛存在:平顺县的部分地区,只有13%的佃耕地的地租低于37.5%,有80%的出租土地的地租在40%~80%之间波动,还有6.8%的出租土地的地租甚至超过80%。在相当多的县,“人们可以发现,比率达60%的地租为数不少”[2]177。在企图控制村政权方面,也采用了一系列手段:雇用凶手暗杀积极分子以恐吓群众;搞秘密勾结雇用自己圈子中的人监视村长,揭露村长的受贿,使之丧失名誉,并设法使自己圈子中的人被选上这个职位;甚或主动提供帮助、让他们的女儿与穷人干部结婚等手法来安抚、迷惑群众。作家赵树理[14]和丁玲[15]对此类人物的描写尤为形象具体。但地主所做的一切都无济于事。农民已经被发动起来,要地主偿还的并非一日之债,地主的命运岌岌可危。
党运筹帷幄,适时调整了二者之间的关系。1941年“三三制”在村政权中的贯彻执行,1942年减租减息政策的具体实施,可以说给地主吃了一颗定心丸,减轻了地主对农民革命的惧怕心理。地主别无选择,只好把自己置于政府的安排之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能只把共产党看作是地主的掘墓人,其把地主由“死刑”改判为“死缓”,也可以说是一位比较仁慈的法官。而地主对于共产党而言,则是党成功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因子:没有地主,共产党很难燃起农民的激情,为抗日战争提供足够的人力;没有地主,共产党很难为抗日战争筹备足够的物力、财力。所以,共产党与地主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互惠双赢,而是一边倒。
三、三角形架构分析
由上分析可知,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与农民及地主之间的关系如果用图形来表示,那就是三角形,而不会是线形或圆形,更不会是四边形。
因为三者不能构成四边形;也不能构成以党为圆心、党与农民及党与地主的关系为半径的圆,因为党与农民的关系和党与地主的关系不一样;同样如果三者在一条直线上,那党与农民、党与地主的关系所构成的角度相等,反映的关系也就一样,这与事实不符。所以最恰当的图形应该是三角形。
共产党是顶角,表明其是领导者;农民与地主是两个底角,反映了基层社会两大阶级的对立。在战争初期,共产党与农民的关系最贴近,与地主的关系最疏远,所以构成的三角形是钝角三角形,即顶角与农民这个底角之间的距离最短,角度最大;与地主这个底角之间的距离最长,角度最小。随着战事的发展,共产党对地主的态度由消灭逐渐变为吸收利用,因此体现在图形上就是共产党与地主之间的距离缩短,角度变大,钝角三角形逐渐变为锐角三角形,但绝对不会成为等腰三角形,因为共产党与地主的距离再近也不能超过与农民之间的距离。简言之,共产党与农民之间所构成的角度变化范围是小于180度而大于60度;党与地主之间所构成的角度变化范围是大于0度而小于60度。也就是说共产党把农民作为主力军,而使地主居次要地位。
此三角形架构只是笔者的一得之见,期冀众位学仁共同参与讨论。
参考文献:
[1]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M].董乐山,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2] 达格芬·嘉图.走向革命[M].杨建立,朱永红,等,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3]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M].陈瑶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4] 朱德新.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J].历史教学,1994(4).
[5] 斯特朗.斯特朗文集:第3册[M].王厚康,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6] 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M].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7] 柳 林.晋察冀边区的过去和现在[J].解放,1938(51).
[8] 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J].近代史研究,2006(4).
[9]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M].邱应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10] 李金铮.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抗日战争研究,2004(2).
[11] 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上册[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
[12] 沈贞伟.论异质共同体的构建与维持[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6).
[13] 吕正操.晋中的抗战形势[J].解放,1940(110).
[14] 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1册[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
[15] 丁 玲.丁玲全集:第5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