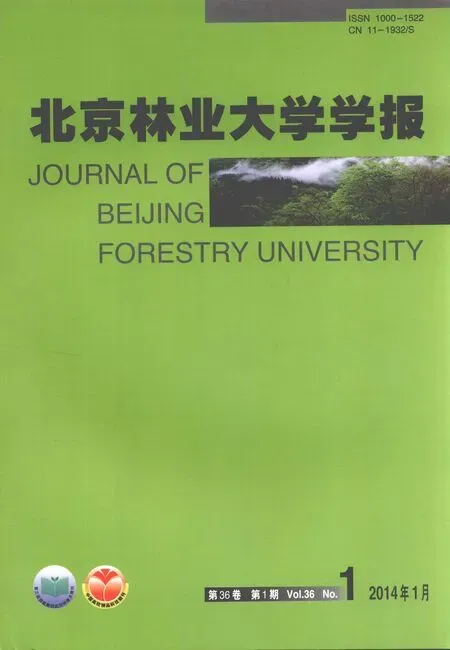论《淮南子》林业思想及其生态意蕴
高 旭
(1.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所;2.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论《淮南子》林业思想及其生态意蕴
高 旭1,2
(1.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所;2.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作为秦汉时期黄老道家的代表论著之一,《淮南子》蕴含丰富的林业思想。《淮南子》林业思想以重林、用林、植林、护林与赏林为基本内涵,从中凸显自然性、政治性与人文性的理论特点。《淮南子》林业思想的生态意蕴极为深厚,在黄老道家的历史影响下,体现出强烈的自然意识、整体意识与和谐意识,这在秦汉林业思想史上堪为卓识。就实质而言,《淮南子》林业思想是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有机融合,其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核心理念,对现代人类的身心和谐、世界和谐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和借鉴意义。
《淮南子》;林业思想;黄老道家;自然;生态;和谐
作为“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要略》)[1]的“西汉道家言之渊府”[2],《淮南子》体大思精、内涵丰富,在秦汉时期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及影响。在《淮南子》中,除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等思想外,林业思想也有着突出反映,不论是关于林业发展的基本认识,抑或是其中所蕴含的生态意识,都堪为同时期思想著作的代表。受先秦道家思想的深刻熏染,《淮南子》对自然林木充满亲近感,始终将林业的生态发展视为人类社会的应为之事,坚决反对人为因素对自然林木的过度干扰与破坏,主张人类社会的发展应与自然林业相和谐,实现天人合一的林业生态发展。
关于《淮南子》的林业思想,学界的相关论著仍较为有限,且专题性的学术探讨并不多见。现有成果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对《淮南子》林业思想直接有所论述,如陈广忠《淮南子科技思想》[3]、王巧慧《淮南子的自然哲学思想》[4]等著作;二是在探讨《淮南子》生态思想时,对其林业内涵间或有所涉及,如张弘《〈淮南子〉和谐发展生态论》[5]、章晓丹《〈淮南子〉的自然整体主义世界观》[6]、张维新《〈淮南子〉的生态自然观及其现代启示》[7]、吕慧燕《〈淮南子〉人与自然和谐思想及其现实意义》[8]、张朗《〈淮南子〉的生态和谐思想》[9]等论文。但若整体而言,现有研究仍不足以彰显出《淮南子》在秦汉林业史上的独特性、重要性,因此拙文从思想史的视野出发,对此深入探讨,进一步揭示出《淮南子》林业思想的基本内容与理论特点,阐明其中蕴含的丰富的生态理念。对现代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而言,《淮南子》林业思想非但不因年代久远而显陈旧落伍,相反,其充满人文精神的林业生态思想,既对现代人类的自然生态理念深具启示价值,也对现代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颇富借鉴意义。
一、《淮南子》论“林”之基本内涵
在《淮南子》中,有关林业发展的思考与认识虽不是核心的思想内容,但也成为《淮南子》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而且,若深入探究,我们会发现,《淮南子》实际上在黄老道家的历史影响下,包含着丰富的林业思想,这在重林、用林、植林、护林和赏林等方面得到具体表现,特别是其中还体现出崇尚自然和谐、讲求持续发展的强烈的生态意识,这使得《淮南子》在秦汉林业发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值得我们系统探讨和认识。
第一,“重林”是《淮南子》对待林业资源的基本态度。“神托于秋豪之末,而大宇宙之总。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节四时而调五行。呴谕覆育,万物群生,润于草木,浸于金石,禽兽硕大,豪毛润泽,羽翼奋也,角觡生也”,“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羽者妪伏,毛者孕育,草木荣华,鸟兽卵胎”(《原道训》),“下至介鳞,上及毛羽,条修叶贯,万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逼,处大而不窕,浸乎金石,润乎草木,宇中六合,振豪之末,莫不顺比”(《兵略训》)。在《淮南子》看来,理想的自然环境应具有“万物群生,润于草木”“草木荣华”的现实内涵。换言之,“天之所为,禽兽草木”(《泰族训》),丰盛的“草木”资源,能够成为“万物”之所以萌生、育长的良好条件,这对“禽兽”“羽翼”等自然生物的现实生存极为重要,能够促使其更好地合乎“天地之性”,实现良好发展。
第二,“用林”是《淮南子》对待林业资源的现实认识。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林业资源同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作为农业经济辅助的林业资源,成为人们获得生存的必要条件。“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修务训》),“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时则训》),“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氾论训》),“以冬伐木而积之,于春浮之河而鬻之”(《人间训》),人们的衣食之资时常取材于林业,仰赖林业的发展。而且,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不论是居住、出行,抑或器具制造、水患治理,也都离不开林业资源的积极开发和有效利用:“钻燧取火,构木为台”(《本经训》),“故六骐骥、四駃騠,以济江河,不若窾木便者,处世然也”,“伐楩柟豫章而剖梨之,或为棺椁,或为柱梁,披断拨檖,所用万方”(《齐俗训》),“水泉动则伐树木,取竹箭”(《时则训》),“禹沐浴霪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泰族训》)。正因为此,对林业资源的高度重视,自古以来就成为统治者的基本认识,在国家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故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在思想上始终强调林业资源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主张人们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对其进行合理开发与使用。
第三,“植林”是《淮南子》对待林业资源的理性认知。《淮南子》认为“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原道训》),“地不定,草木无所植”(《俶真训》),林木的自然生长不仅需要适宜的水土条件,而且“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草木之性,洪者为本,而杀者为末”(草木的特点在于,粗大者为根本,细小者为末梢),人们更要在实践中根据自然规律来种植林木,以培“本”为重,只有如此,才能“灌其本而枝叶美”,使林业发展能合乎“天地之性也”(《泰族训》)。《淮南子》特别强调,“夫树木者,灌以瀿水,畴以肥壤,一人养之,十人拔之,则必无余蘖”(《俶真训》),人们在林木种植中,应创造促其自然成长的外部环境,而非过度进行人力干预,以主观意愿取代林木生长的客观规律。此外,《淮南子》主张“上因天时,下尽地利”(《要略》),“不弃时,与天为期”(《诠言训》),认为人们从事林木种植,应具有强烈的时节观念,“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旱落”,“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时则训》),因此不论是“树杏”“树李”“树桃”“树柘”,还是“树槐”“树枣”“树栎”,这种多样化的林木种植都须根据自然时节的变化而进行。人们只有在实践中坚持“制度阴阳”的基本原则,以“天为绳,地为准,春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时则训》),才能推动林业的合理、良性的发展,实现“养长化育,万物蕃昌”的理想状态。
第四,“护林”是《淮南子》对待林业资源的可贵精神。在林业发展上,《淮南子》反对不顾自然时节的滥伐林木,主张林木应有适宜生长的外部环境,因此在一年中的“孟春之月”尤为“禁伐木”(《时则训》),而且“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主术训》)。尤需指出,《淮南子》在思想上十分强调“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对完全不顾忌林业发展的短视行为进行谴责,认为只有对林业资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才能“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主术训》)。基于此,《淮南子》一方面主张统治者在政治上能有力推动林木种植,规划林业发展,“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在林业经济合乎理性的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其服务民众的现实目的,正所谓“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主术训》)。另一方面,《淮南子》在林业发展上也对统治者提出政治诉求,反对“大构驾,兴宫室,延楼栈道”,甚至“焚林而猎,烧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销铜铁,靡流坚锻”,为满足一己私欲而破坏性开采林业资源,最终在“无厌足目”中,导致“山无峻干,林无柘梓,燎木以为炭,燔草而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时,上掩天光,下殄地财”(《本经训》)的严重恶果,为现实的林业发展造成不可弥补的自然损失。因此,不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统治阶层,《淮南子》认为都应理性地对待林业发展,利用林业资源,只要依照自然规律,实现林业经济的良性发展,才能将“收敛畜积,伐薪木”转变为长远行为,从而富国利民。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对待自然的林业资源,《淮南子》还表现出“赏林”的人文意趣。“乔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适情;无以自得也,虽以天下为家,万民为臣妾,不足以养生也”(《原道训》)。在《淮南子》看来,“古之人有居岩穴而神不遗者,末世有势为万乘而日忧悲者”,如果人们希望自己能获得生命的内在快乐,就应效法那些“遗物而与道同出”的“圣人”或隐士,在林木茂盛、环境清幽的自然环境中“适情”以“养生”。由此可见,《淮南子》眼中的林业资源,不仅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只要人们具有一定的“赏林”意识,将自身的生存状态与良好的林业环境相协调、相融合,就更易于实现心理的“自得”,获取真正的快乐。
二、《淮南子》论“林”之思想特点
《淮南子》对自然的林业环境始终表现出内在的亲近感,认为“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说山训》),丰富的林业资源无论是对自然动物,还是人类社会,都是其理想发展的必要条件。从思想上看,《淮南子》之所以具有如此认识,这与其深受黄老道家的历史影响密不可分。在先秦时期,与儒、法、墨、阴阳诸家相较,道家最为强调世间万物存在的自然性,始终坚持“道法自然”,“天人共生共荣,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和谐共存”[10]的基本理念,并从国家政治的高度出发,在林业思想中凸显出浓厚的生态意识。因此,立足道家的根本立场,《淮南子》的林业思想不仅具有显著的自然性,也内含一定的政治性、人文性。
首先,顺天植林,木性为重,这彰显出《淮南子》林业思想的自然性。从黄老道家出发,《淮南子》在思想上主张“法修自然,己无所与”(《诠言训》),“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原道训》),以“自然”为林业发展的根本原则,认为人们应“晓自然以为智”(《人间训》),最大程度上促进“木之性”的自然实现。由此,《淮南子》强调林木培植必须“顺天”而行,应合乎自然时节与规律。“天设日月,列星辰,调阴阳,张四时,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风以干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见其所养而物长;其杀物也,莫见其所丧而物亡”(《泰族训》)。《淮南子》认为,对于林木的自然生长,也是如此。“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天文训》),在林业的现实发展中,人们需要对此有所深刻认识,因为一切的林木,不论种类属性、生长规律如何,其存在的外部环境都是自然的天地,所以人们在林业实践中,只有顺应“天地之道”,才能推动现实林业的良好发展。而且,《淮南子》认为,“今夫徙树者,失其阴阳之性,则莫不枯槁。故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因此,林木种植必须遵循“形性不可易,势居不可移也”(《原道训》)的客观规律,在“顺天”治林中确保其“阴阳之性”。这就要求人们既能对林木生长的自然条件(土壤、水源等)深入认识,也能对林木生长的自然时节合理掌握,在实践上因树制宜,从而促使林业发展顺应“天地之道”,充分体现自然的“木之性”。
其次,无为治林,节制采伐,这反映出《淮南子》林业思想的政治性。林业发展,在《淮南子》看来,不仅具有其自身的自然性,而且还易于受到现实政治的强烈影响。一方面,《淮南子》认为统治者的政治行为时常能直接影响林业的实际发展,“夏屋宫驾,县联房植;橑檐榱题,雕琢刻镂;乔枝菱阿,夫容芰荷;五采争胜,流漫陆离;修掞曲校,夭矫曾挠,芒繁纷挐,以相交持;公输、王尔无所错其剞劂削锯,然犹未能澹人主之欲也”(《本经训》)。换言之,如果现实中统治者“穷耳目之欲,而适躬体之便”(《精神训》),为图享受而大兴土木,广建宫厦,甚至于“楚王亡其猿,而林木为之残”,“上求材,臣残木”(《说山训》),那么这不但是对民力国赋的肆意浪费,更是对现有林业资源的广伐滥用,最终对林业发展产生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淮南子》强调统治者应制订合理政策,积极护林,适时推动林业发展。立夏之日,“毋兴土功,毋伐大树,令野虞,行田原,劝农事,驱兽畜,勿令害谷”(《时则训》)。显而易见,正因为深刻认识到林业发展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所以《淮南子》承继“圣人处无为之事”[11],“事恒自施,是我无为”[12]的黄老思想,极力主张“君道者,非所以为也,所以无为也”,“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无欲而危者也”(《诠言训》),“人无为则治,有为则伤”(《说山训》),推崇“今高台层榭,人之所丽也;而尧朴桷不斫,素题不枅”(《精神训》)的政治行为,试图倡议统治者清心寡欲,节制伐林,对现实的林业经济发挥出积极的政治作用,而非相反。在《淮南子》看来,唯有如此,统治者在林业实践上才能避免“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横”(《说山训》)的恶性发展。
最后,养生乐林,人树相谐,这反映出《淮南子》林业思想的人文性。基于道家思想,《淮南子》认为,自然的林业环境能对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良好作用,既能有益于人们的劳作之息,“今夫繇者,揭钁臿,负笼土,盐汗交流,喘息薄喉。当此之时,得茠越下(越,通‘樾',指树荫),则脱然而喜矣。岩穴之间,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头,踡跼而谛,通夕不寐。当此之时,哙然得卧,则亲戚兄弟欢然而喜,夫修夜之宁,非直一哙之乐也”(《精神训》);也能有利于人们进行生命的自我修养,“处穷僻之乡,侧溪谷之间,隐于榛薄之中,环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户瓮牖,揉桑为枢,上漏下湿,润浸北房,雪霜滖灖,浸潭苽蒋,逍遥于广泽之中,而仿洋于山峡之旁”。在《淮南子》看来,“侧溪谷之间,隐于榛薄之中”的自然林业环境对于那些隐士们而言,非但不意味着艰苦困窘,反而成为其“内有以通于天机,而不以贵贱、贫富、劳逸失其志德者也”,真正贴近自然、修养心性的良好条件,所谓“此齐民之所为形植黎累忧悲而不得志也,圣人处之,不为愁悴怨怼,而不失其所以自乐也”(《原道训》)。由此,《淮南子》进而指出,“古之人有居岩穴而神不遗者,末世有势为万乘而日忧悲者”,“所谓乐者,岂必处京台、章华,游云梦、沙丘,耳听《九韶》、《六莹》,口味煎熬芬芳。驰骋夷道,钧射鹔鷞之谓乐乎”,认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乔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适情;无以自得也,虽以天下为家,万民为臣妾,不足以养生也”(《原道训》),将“乔木之下,空穴之中”视为人们得以养生自乐,实现人树和谐的理想环境。应该说,《淮南子》这种对森林生态环境之于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性的看法,堪称卓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秦汉时期“岩栖山居”的“森林游乐文化”[13]的历史反映,凸显出其林业思想所内含的人文性。
三、《淮南子》论“林”之生态意蕴
虽然《淮南子》并非专门的林学之作,但作为秦汉时期“通古今之论,贯万物之理”(《要略》)的道家论著,却始终表现出对现实林业发展的重视与关注。基于黄老思想,围绕如何实现林业的理想发展,如何促使人类社会与自然林业相和谐的核心问题,《淮南子》从自然意识、整体意识与和谐意识3个方面彰显出浓厚的生态意蕴,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林业思想,这极大地丰富了“秦汉关于自然与人和谐统一的生态思想”,成为“这一时期丰富的生态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4]。
首先是自然意识,这在《淮南子》林业思想上表现最突出,最能反映其内在的生态意蕴。如前所述,《淮南子》从黄老道家出发,在林业发展上坚持“法修自然”的根本原则,具有鲜明的自然性特点。现实林业的理想发展,既要求林业自身能获得良好的自然条件,也需要人类社会能给予林业稳定的生长环境,因此林业的生态化发展,实际上并非自然条件的单一满足,而是必须实现自然条件与人类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对此,《淮南子》虽无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理念,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也深刻认识到林业生态化发展对自然条件与人类实践的双重要求,并且有所反思。一则《淮南子》认为林木生长有其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应“各便其性,安其居,处其宜,为其能”(《齐俗训》),只有让林木在自然环境中合乎其“阴阳之性”地生长,而非“今夫徙树者,失其阴阳之性,则莫不枯槁”,才能促使林业实现“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齐俗训》)的生态发展。二则《淮南子》虽然认为人类实践能对林木生长发挥积极影响,但始终强调“因天地之自然”,“因”木性以树林,反对不顾林木生长习性,任意移植、拔高的主观化行为。“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岂木也?犹充形者之非形也”(《精神训》)。人们只有认识到林木自有其生长之性,合乎时节地从事林木种植,才能取得枝繁叶茂、木高林密的理想结果。三则《淮南子》对林业发展中的人类实践也并非全然否定,相反,认为只要人类能“晓自然以为智”(《人间训》),在实践中“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齐俗训》),其主观劳动便能对林木的生长发挥积极影响。
基于以上认识,《淮南子》在林木种植中始终以“因”为重,主张林业发展“因其自然而推之”,在“并得其宜,物便其所”中实现林木之性与人为之力的有机结合,促使林业更加生态的发展。“不通于物者,难与言化”(《齐俗训》),在《淮南子》看来,当人们能够深明“木之性”,如圣人那样“见其所生,则知其所归矣”(《缪称训》)时,便能避免“用己而背自然”的“有为”之举,推动现实林业走向自然生态的理想发展。
其次,与自然意识相适应,《淮南子》在林业思想上还表现出一定的整体意识,强调“万物群生,润于草木”,认为森林生态环境与自然动物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有机联系,这成为其生态意蕴的重要内涵。
《淮南子》受道家思想深刻熏染,主张“万物一圈也”(《俶真训》),“万物一齐”(《齐俗训》),“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精神训》),视万物为一体,认为自然的林业环境既是各种生物得以繁衍生息的基本条件,“故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羽者妪伏,毛者孕育,草木荣华,鸟兽卵胎”(《原道训》),“下至介鳞,上及毛羽,条修叶贯,万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逼,处大而不窕,浸乎金石,润乎草木,宇中六合,振豪之末,莫不顺比”(《兵略训》),也是各种生物赖以闲适生存的理想场所。“石上不生五谷,秃山不游麋鹿,无所阴蔽隐也”(《道应训》),“猿得木而捷,鱼得水而鹜”(《主术训》),“深溪峭岸,峻木寻枝,猿狖之所乐也”,“夫猿狖得茂木,不舍而穴”,“夫飞鸟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栖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齐俗训》)。由此可见,在《淮南子》看来,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不仅是天地万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麋鹿、猿狖与飞鸟等各种动物的理想家园,正是在这种自然一体的生态发展中,林业环境才充分展现其独特的重要性。
最后,基于林业生态的自然性、整体性,《淮南子》在思想上体现出显著的和谐意识,憧憬与追求“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被德含和,缤纷茏苁”,“万物掺落,根茎枝叶,青葱苓茏”(《俶真训》)的理想林业发展。
《淮南子》认为:“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六合所包,阴阳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阅一和也。是故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为一家”(《俶真训》),“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时则训》),在其看来,林业发展是天地自然衍生的结果,不论何种林木,具有何种特性,其实质上都同受着阴阳雨露的滋润,和谐地共存与发展。因此,人们在林业实践中只有“制度阴阳”,推动林木合乎自然规律的生长,也才能进而促使林业发展为其他自然生物创造出良好的衍生环境,实现整体的生态和谐。而且,《淮南子》认为林业能否实现理想发展,体现出内在的和谐性,这并非仅局限于自然环境本身,也受到现实政治的重要影响。当“主暗晦而不明,道澜漫而不修,弃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之时,便会出现“举事戾苍天,发号逆四时,春秋缩其和,天地除其德”的消极局面,造成“飞鸟铩翼,走兽废脚,山无峻干,泽无洼水,狐狸首穴,马牛放失,田无立禾”(《览冥训》)的生态恶果。所以,《淮南子》在政治上强调统治者应清净无为,“和愉宁静”,能“抱德炀和,以顺于天”(《精神训》),如神农、黄帝般“提挈阴阳,嫥捖刚柔,枝解叶贯,万物百族,使各有经纪条贯”,使得“群生莫不颙颙然仰其德以和顺”(《俶真训》)。从中可见,《淮南子》在林业思想上的和谐意识实际上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强调林业发展内在的自然性,讲求合乎林木生长规律的生态发展;另一方面也凸显出社会政治之“和”对于林业发展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深刻揭示出林业生态发展所具有的人文性。因此,在稳定的社会政治条件下,积极从事林业发展,“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主术训》),内在协调人、林与天地之关系,使其成为“不可偏废”的“有机统一体”[3],从而实现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淮南子》所祈望的真正的林业理想。
综上所述,作为秦汉时期黄老道家的代表之作,《淮南子》不仅蕴含丰富的林业思想,而且对自然林业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生态联系有着深入思考。其林业理想就实质而言,内在体现出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相互融合,深刻揭示出林业发展对人类社会所具有的独特影响。不论是“下尽地财”的林业资源开发,还是“乔木之下”的林业养生实践,都反映出《淮南子》基于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理念所主张的林业生态观。在其看来,人们只有始终坚持自然以治林的林业实践,从整体上注重人类社会、自然动物与林业环境之间的协调性,“在生物资源的保护利用中坚持一种有机的生态整体观”[15],才能真正促使林业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更为积极的现实影响,既有利于满足人类的各种生活所求、经济所需,也有益于发挥森林生态环境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怡情养性作用,更好地实现人、林和谐的社会发展。
应该说,《淮南子》对自然林业的这种理性认识,虽然难以与现代人类的林业生态学相较,但毋庸置疑,作为一种可贵的历史资源,其清醒地“意识到生态和谐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人类的行动潜藏着害物害己的可能”[16],因此对现实中人们无节制地消耗林业资源,破坏林业与社会之间生态协调的发展歧途有所警示,并由此进而提出人、林和谐共存与发展的理想诉求。《淮南子》的林业生态思想,虽历时千年,但并未陈旧落后,相反,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审思,以此促进现代人类社会在自然的森林生态环境中,实现良性发展,变得更加和谐。
[1]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231.
[3] 陈广忠.淮南子科技思想[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220-224.
[4] 王巧慧.淮南子的自然哲学思想[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347-349.
[5] 张弘.《淮南子》和谐发展生态论[J].济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5):12-15.
[6] 章晓丹.《淮南子》的自然整体主义世界观[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60-64.
[7] 张维新.《淮南子》的生态自然观及其现代启示[J].前沿, 2010(9):163-168.
[8] 吕慧燕.《淮南子》人与自然和谐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215-217.
[9] 张朗.《淮南子》的生态和谐思想[J].华中人文论丛,2012 (1):106-108.
[10] 党超.论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J].史学月刊,2008(5):114-120.
[11]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2009:60.
[12] 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36.
[13] 张钧成.中国林业传统与林业文化[J].世界林业研究,1994 (4):75-80.
[14] 陈业新.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J].中国史研究,2001(1): 19-26.
[15] 王巧慧.《淮南子》的生态伦理思想研究[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2(3):7-12.
[16] 谢清果.道家的生态意识管窥[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2):6-12.
(责任编辑 何晓琦)
The Forestry Thought in Huai Nan Zi and Its Ecological Connotations
GAO Xu1,2
(1.Institute of Chuhuai Culture,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ainan,232001,P.R.China; 2.School of Histor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232001,P.R.China)
Huai Nan Zi,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aoism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contains abundant forestry thoughts,highlighting natural,political and humanistic theories whose basic connotation is that forests should be valued,protected and appreciated.Under the influence of Taoism, Huai Nan Zi reflects a strong sense of nature,integrity and harmony.These thoughts are extremely profound and outstanding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In essence,they ar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natural ecology and humanistic ecology,whose core concept of nature-human integration and naturehuman harmony has precious enlightenment on and signific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body-mind harmony and harmony of the world in modern human society.
Huai Nan Zi;forestry thoughts;Huang-Lao Taoism;nature;ecology;harmony
K2
A
1671-6116(2014)-01-0020-06
2013-06-20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淮南子》与法家思想研究”(2011sk142)、安徽省社科联项目“《淮南子》与其成书背景的互动研究”(B2012001)。
高旭,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Email:gxls2004@163.com 地址:232001安徽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