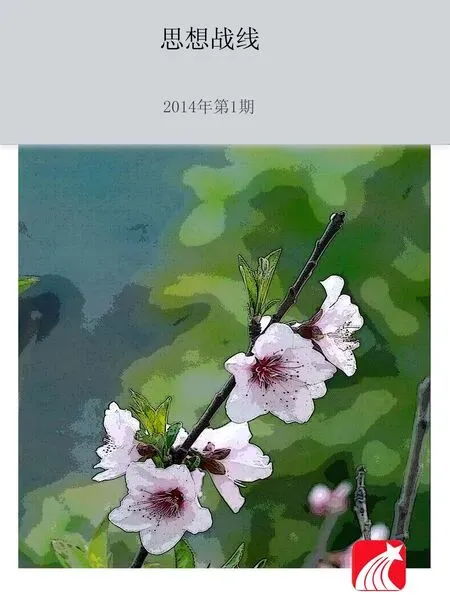王元翰与公安派诗人交游考
孙秋克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王元翰、雷思霈成进士,选庶吉士,曾可前则高中一甲第3名,授翰林院编修。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九月,考选十四名翰林院检讨,雷思霈与焉;又量授科道八员,王元翰与焉。对量授科道人员,大学士沈一贯等屡次请赐允发,但或不报,或留中,或俞旨不下,直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二月, 王元翰才得以到任吏科给事中,开始其言官生涯,次年二月,升工科右给事中。在王元翰踏上言官之路时,公安“三袁”中的长兄袁宗道,已逝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故王元翰与他无缘相逢。“三袁”中的仲兄袁宏道,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为京官至离世前的四年间,与王元翰有过重要的交集。“三袁”中的幼弟袁中道,则在袁宏道逝后继续了与王元翰的友谊。曾退如是湖北石首人,雷何思是湖北夷陵(今宜昌)人,他们二人本为袁宏道的同乡至友、同派诗友,所以袁宏道兄弟与王元翰的相识相知,并不完全出于偶然。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秋,宏道携其弟袁中道同行,入都补仪曹主事。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袁宏道任吏部主事,这一年,他们之间通过曾退如,有间接的诗歌唱和。清明时节,万历三十二年(1605年)乞归的曾退如遵父命回京奉职,宏道与其奉命陪祀,王元翰亦为陪祀者之一,并作《九陵陪祀》。这年秋天,曾退如作苦雨诗,元翰有《和曾退如馆兄苦雨》唱和,袁宏道亦有《苦雨吟和曾退如》四首、《秋日苦雨和曾退如太史》四首和之。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春,发生了王元翰被云南道御史郑继芳弹劾案,致其为时不到四年的言官生涯就上结束。史载云南道御史郑继芳劾奏王元翰贪婪不法,盗库金,尅商人奸赃累数十万。[注]参见《明实录·神宗实录》第455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8585页;《明史》第236卷《王元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152页。王元翰究竟贪赃枉法与否?分析诸多历史记载,我们只能得出否定的答案。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元翰上疏追忆此事说:“彼时臣犹不敢苟且去国,将行李数目,招呼把总刘渠并五城坊官同眼点视,暴白于正阳门棋盘街,携家眷罄身出都,拜阙辞行,至张家湾。越数日,把总将行李送至船上,此京城万耳万目,共见共闻。”[注]《明实录附录·崇祯长编》第19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103页。如果王元翰的自述尚不足为据,那么还有许多旁证。如刘宗周《聚洲王公墓志铭》、倪元璐《王谏议传》,都记载了王元翰自暴行李,以正视听之事。刘宗周《聚洲王公墓志铭》并云:“众白之而公则向阙叩头,恸哭曰:‘臣无能簪笔事陛下矣!’遂挂冠出都门。于是南北台省交章讼公冤。”[注]王元翰:《凝翠集》,《云南丛书》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432页。南北诸臣论救疏,元翰后来编为《德邻篇》,已轶。沈德符《王聚洲给事》说元翰“素负才名,慷慨论事,物情甚向之”,诸臣“救疏皆保其清操”,并赞元翰为官远胜于东汉刚正不阿,为政清廉的谏官杨震,他断言元翰绝不可能“囊金如山”。[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19卷,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2~503页。据《明史》本传记载,王元翰案实际上是朝中党人借故而兴,并清楚地表明这是郑继芳蓄意构陷:“方继芳之发疏也,即潜遣人围守元翰家。及元翰去,所劾赃无有,则谓寄之记事家。”[注]《明史》第236卷,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152页。由于神宗皇帝对此案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王元翰非常失望,三月即“拜疏去”,[注]《明实录·神宗实录》第456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8600页。暂居于河南辉县苏门山百泉之上。在王元翰弃职辞朝后,袁宏道、雷何思仍在朝为官,但他们之间的友谊,并不因处境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反而比以前更为亲密了。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春,当王元翰处于政治旋涡中心时,袁宏道升任吏部考功司员外郎。[注]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第47卷《初授司功副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98页。他在此前已看到了万历朝中吏治的弊端,曾在这年一月连上《请点右侍郎疏》、《摘发巨奸疏》。在三月升任考功司员外郎后,又上《查参擅去诸臣疏》,以期整肃吏治。从《查参擅去诸臣疏》,可见宏道对包括元翰在内的所谓“擅去诸臣”的态度。其疏道:“先是工科都给事中孙善继擅离职守,臣等具疏参劾。已而科臣刘道隆继之,词臣顾天峻、李腾芳又继之。今科臣王元翰又陛辞出城矣。该臣看得诸臣被论,情罪自有浅深。匿瑕与藏污不同,一眚与败检殊科。臣等未奉谕旨,不敢深求。窃唯朝廷有必信之命令,而后臣子有必可守之法。二百年来,未闻人臣径自去国者,亦未闻待命踰岁月而不得报者。惟其情通,故法行矣。今被弹诸臣,消阻一室,七尺俨然,谁无面孔……。方今自言路而铨政,自卿贰而抚按,无一事非权宜,无一事非变局,可惊可骇,何止一端。”[注]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第5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07页。如果我们对这道奏疏顾名思义,那就错了。宏道看似参劾擅离诸人,实则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神宗怠政和吏治混乱的不满,流露了对王元翰等人的同情。就元翰个人而言,自中进士以来不过八年时光,“待命踰岁月而不得报”和“径自去国”两种情况都遇上了。对宏道此疏和疏中的真意,刚离朝的元翰自然不难得知并体会,否则就不会有他们后来比在朝时更多的交往,元翰也不可能在之后引宏道为知己(详见下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袁宏道的声援,奠定了他们之间友谊发展的基础。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九月,在物质、仕途的双重困境中,元翰开始了他离朝后的第一次漫游,与元翰漫游差不多同时,袁宏道奉命主持陕西乡试。九月,考功事峻,他遍游华、嵩,并有《华嵩游草》纪其行。去程宏道作诗《望苏门山是日大风沙》:“我望苏门山,正值大块噫。万窍尽传声,浊响非天籁。此地旱三月,禾黍如蕉艾。夭乔各偃蹇,青山了无态。我欲见先生,长啸孤云外。庶几治病龙,千里听澎湃。”[注]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第5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43页。宏道此诗中的“先生”,当为此时隐居于百泉之上的元翰,故遇大风沙则忧其耕耘之苦。此时宏道因要赶赴陕西主试,来不及探访元翰,故只能“望”之,回程方有百泉之游。正如宏道此行之于华山,也是来程望而归程登。
袁宏道不知道,此际王元翰也正行于陕西道中,他听说宏道主试秦中,回程将登华山,故迎而与其相遇,有诗《陕州途中闻袁六休主秦试,回由华山观砥柱,喜其久别相遭》。诗曰:“途穷知己至,秋尽敝裘寒。”“闻君留太华,我亦上靑柯。”[注]王元翰:《凝翠集》,《云南丛书》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454页。穷途与宏道相逢,元翰的欣慰之情不禁溢于言表。“知己”二字,在元翰现存的所有著作中,这是惟一一次许之于他人。宏道此行,九月“遍游秦中诸胜,历中岳嵩山,登华山绝顶而还”;[注]袁中道:《珂雪斋集》第18卷《中郎先生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61页。十月过辉县游,元翰暂居的百泉,有诗《登苏门山泛舟百泉》、《再泛百泉》,散文《游苏门山百泉记》。这是袁宏道第一次游百泉,遗憾的是他在百泉探访元翰而不遇,因元翰此次出游历时四个月,岁末才归百泉,故错过了和宏道又一次相见的机会。宏道此行的日记,正可与元翰的行踪相印证。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袁宏道留京暂受部衔,以候选取,考功事峻,给假南归。二月二十四日,他和袁中道一同出京,迂道再游百泉。这是袁宏道第二次到辉县,原拟偕元翰同游,所以和中道再访元翰。遗憾的是,这一次他们仍然未能在此相会。此后,宏道和元翰再无相会的机缘。这年闰三月十五日,宏道兄弟始还家,[注]袁中道:《珂雪斋集》之《珂雪斋游居柿录》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95页。因水患,宏道由公安移家沙市,九月初六日即病卒于此。[注]袁中道:《珂雪斋集》第18卷《中郎先生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63页。元翰对宏道的怀念是长久的,天启五年(1625年)他被起复为工部尚书,于二月离滇,四月入蜀,六月由嘉定放舟穿三峡,下荆楚,至武昌,沿江景物,勾起了他对故友的深长忆念,其长篇歌行《长江行》云:“中郞长眠唤不醒,榷关使者狠于虎。”[注]王元翰:《凝翠集》,《云南丛书》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476页。可见,即令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元翰对宏道的思念之情依然没有衰减。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在元翰弃官离朝后次年,雷何思也来百泉探望他。其实在人生的低谷中,元翰也时常思念雷何思,并作五言绝《忆何思兄》,表达了对友人的感情:“风雪度卢沟,萧萧别后愁。相思宜远望,频上仲宣楼。”[注]王元翰:《凝翠集》,《云南丛书》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448页。其门生、竟陵派领袖钟惺的《告雷何思先生文》说:“记去岁六月,与先生卢沟别去。”[注]钟 惺:《隐秀轩集》第3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48页。这里的“去岁”即指万历三十八年,年初雷何思在卢沟,初夏告归乡里,趁道来百泉访元翰,并向元翰传递了京中消息。元翰《寄汪霁寰省丈》云:“何思兄来泉上相访,具道大可异事。言凡与弟契厚者,皆蒙寄顿之诮。真可笑也。”[注]王元翰:《凝翠集》,《云南丛书》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420页。唯同道者可言朝中政治事件,此可为元翰与公安派诗人志趣相投的又一见证。元翰与何思同乐共游,作诗《初夏日雨霁与何思馆兄走西郊》、《送何思馆兄》。二人相约卜筑于鹿门(在今湖北襄阳市东南)。秋末,元翰作诗《寄讯何思兄》,诗云“秋杪传君侍板舆,近来消息益生疏”,可见这时雷何思已卧病在床;又云“鹤泽耽吟龙自老,鹿门卜筑竟何如”,[注]王元翰:《凝翠集》,《云南丛书》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449页。表达了对达成心愿的期待和对友人健康状况的担忧。
对于王元翰来说,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是个令人悲伤的年头:八月初七日,袁中道由沙市移宏道的灵柩入公安(《寄王章甫》)。九月初一日,雷何思逝于夷陵。元翰有诗《诣陆州哭雷何思馆兄》二首,第一首对当年自已身处逆境时雷何思的探视深为感激,并对二人相约卜筑鹿门的心愿最终落空深表遗憾,诗云:“我昔遭谗去国年,君来洒泪百门泉。”“鹿门卜筑成虚约,目断襄江啼杜鹃。”[注]王元翰:《凝翠集》,《云南丛书》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458页。冬,曾退如逝于石首,元翰有诗《走石首哭曾长石馆兄》。至此,王元翰的四位公安派友人,唯有袁中道尚在世。
王元翰与袁中道的友谊比较特殊,实际上直到袁宏道逝后,二人才有过一次见面的机会。他们的友情,更多地基于乐山好水的共同情趣。王元翰和袁宏道同朝任职时,与袁中道没有见面的机会,万历三十八年袁宏道获假南归,偕中道游百泉时访元翰,亦无相见的机缘。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夏,宏道已去世三年,元翰和中道才第一次相会。他们的见面,有据可查者仅此一次。这年夏天,王元翰泛舟洞庭湖,游南岳衡山十日,其后在途中编成了诗集《南岳草》,而后与中道晤于仲宣楼下(位于湖北襄阳城东南),请中道为其《南岳草》作序。中道在序中引元翰为同道,并自叹其“好游”之性、“清胜之韵”皆不及元翰。他又评论元翰之人与诗道:“模写烟云,几与七十二峰争奇较丽,则伯举之于山水,予直当北面而师之,又不当以雁行请也。伯举直肠傲骨,诚心质行,而其趣韵复如此。”[注]王元翰:《凝翠集》,《云南丛书》第2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360页。原来,这年三月初八日,袁中道游太和等地,而后拟作“玄岳(武当)之游”。查中道此行纪游:三月三十日过襄阳观音阁,登水边亭;四月九日登武当山,十五日下山,旧路返回,再至襄阳(樊城),住北城关庙,登昭明文选楼(位于襄阳城中),友人为其饯行于观音阁;五月初四日,抵沙市金粟園。[注]袁中道:《珂雪斋集》之《珂雪斋游居柿录》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88~1294页。中道未记与元翰晤面事,《南岳草序》亦未见载于《珂雪斋集》。推测二人相会于仲宣楼下,当在中道登武当山后。《南岳草》已佚,《凝翠集》中仅留下中道的《南岳草序》、元翰的自序以及部分游衡岳诗作。是年秋,王元翰归滇云故里宁州(今华宁)。这次相会,既是他与袁中道的第一次会面,也是他与公安派诗人有据可查的最后一次交集。
考察王元翰与公安派诗人的交游,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当时朝臣和文士所处的政治、人文环境,并深入了解王元翰的生平事迹和创作背景,同时也促使我们深思:王元翰的诗歌数量虽不多,但其歌行风格疏放,词气超迈,其近体意趣深远,简劲清朗,无模拟之习,有清新之态,随心而发,应手而出,既不失骚人深致,又兼谏臣风骨,以其性灵之光,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采——这样的诗风,与公安派诗人的影响有无关系?我们或不妨把这看作由此文引申出来的另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