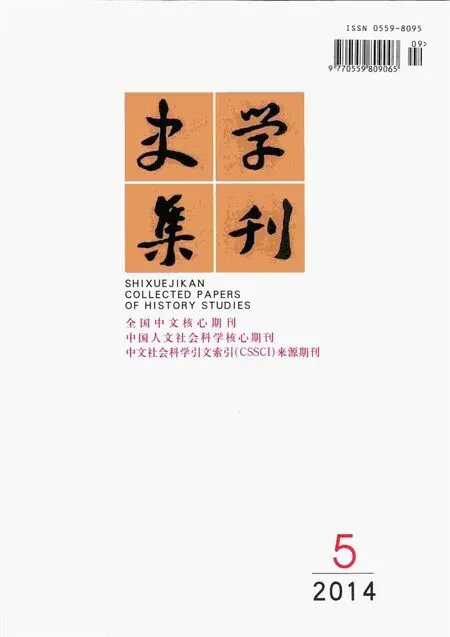傅高义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研究评析
张丽丽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美国汉学家傅高义 (Ezra F.Vogel)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亨利·福特二世社会科学讲座荣休教授,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员,曾两次出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73—1975年,1995—1999年),在美国学术界,傅高义以“中国通”和“日本通”的双重身份著称。在他的新书《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分别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与三联书店出版后,在中国知名度越来越高。实际上,从1962年傅高义应邀到哈佛大学参与有关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开始,他的中国研究已经开展了半个世纪。本文拟对这位哈佛大学著名“中国通”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研究进行简要评析,以丰富美国中国学的学术史研究。
一、傅高义中国研究概述
傅高义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著名的结构功能主义大师、社会学理论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傅高义对中国的社会学分析深受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的影响,他曾提到:“我的导师塔尔科特·帕森斯教授就曾告诉我要经常尝试着系统化地思考经济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思考不同的社会是如何与之相适应的,同时还要明白致使社会变革的源流在哪里。”①[美]傅高义著,高申鹏译:《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1968)》,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傅高义的中国研究不同于费正清,费正清是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中国,傅高义则是以社会学的思维方式解构中国。因此,在20世纪60—70年代,傅高义的中国研究一直是在社会学的视野下进行的,不管是探讨私人关系的变迁、干部的规范化,还是探讨广东土地改革体现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和中国内地的社会结构。①Ezra Vogel,“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 The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21(Jan.-Mar.,1965),pp.46 -60;Ezra F.Vogel, “From Revolutionary to Semi-Bureaucrat The Regularisation of Cadres,”The China Quarterly,No.29(Jan.-Mar.,1967),pp.36 -60;Ezra Vogel,“Land Reform in Kwangtung 1951-1953 Central Control and Localism,”The China Quarterly,No.38(Apr.-Jun.,1969),pp.27-62;Martin King Whyte,Ezra F.Vogel,William L.Parish,Jr.,“Social Structure of World Regions:Mainland China,”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1977),pp.179-204.这一时期傅高义侧重于探讨中国社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适应过程及其结果。
傅高义在20世纪60—70年代进行的中国研究,从动机上讲是对美国现实政治需要所做出的回应,当时美国中国学的选题也大多集中于“中国1949年后的全面历史发展 (包括政治、经济和日常社会现象)”。②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1968)》,第2页。需要指出的是,傅高义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研究是以广东地区为切入点进行的,与其说是中国研究,不如说是广东研究。1969年,傅高义出版了他个人第一部研究当代中国的专著《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1968)》,这部专著的完成主要依赖于通过外部观察的方式获取研究资料,再对研究资料进行社会学加工的研究方法。这是西方学术界第一部研究中国单个地区发展历史的学术著作,是第一部以中国副省级单位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广东研究为傅高义观察中国提供了可操作性,这本书也奠定了傅高义中国问题专家的地位。
在学术生涯的初期,傅高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状况、婚姻关系等较为微观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美国家庭情况》。在费正清、赖世和以及裴泽的影响下,傅高义逐渐进入东亚研究领域,他先是研究日本社会,随后又介入中国研究,这一发生于1958—1961年的短时且急剧的转向最终确定了傅高义一生的学术轨迹。在当时,傅高义的中国研究弥补了美国中国研究中主要侧重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稍显不足的状况,推动了美国中国学的社会科学化。“二战后,中国研究的范围还很狭窄,当时研究中国的学者主要是谈中国的历史、语言和文学,研究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不多”。③孙中欣:《哈佛“中国通”谈中国研究与中国模式:专访傅高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23日,第3版。傅高义将其研究起点设定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对中国历史来说,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形态与先前的历史经验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时代特征。同时,两种历史经验又在逻辑与内涵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傅高义选择这一时间点作为其中国研究的起点,有利于其中国研究的完整阐释。从一开始,傅高义就将1949年之后的历史实践同中国先前的历史经验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化经历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全面地阐释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
二、傅高义对中国新秩序的理解
傅高义对新中国成立后新秩序的构建与适应过程的理解可以抽象为四个角度:思想上,马克思主义范式开始在中国全面确立,取代近代以来传统儒学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并存的精神世界;政治上,中央政府逐步控制全国,具有历史意义的行政权向下贯彻的程度得到空前加强;经济上,计划经济体制取代近代以来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杂糅的结构;私人关系上,带有政治意味的集体主义开始取代宗族主义,“社会”在国家政治的引领下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起来。
(一)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与调和
关于儒学的现代地位,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列文森指出:“保护孔子并不是由于共产党官方要复兴儒学,而是把他作为博物馆的历史收藏物,其目的也就是要把他从现实的文化中驱逐出去。”④[美]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338页。李泽厚则认为儒家思想“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⑤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在这个问题上,傅高义认为“像他们以前的儒家学者官员一样,共产党的领袖认为,成功统治的关键在于他们的官员和干部的道德品质”。⑥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1968)》,第39页。相对于制度建设,共产党的领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关注官员的道德品质上,要求他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同时这种要求还具有禁欲主义倾向。也就是说,传统儒学体系倾向于认为个人道德是构建理想社会的起点,共产党在这层意义上并没有跳出传统。
傅高义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看做是一种扬弃与结合,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最终在政治层面与社会层面取代了儒学,但这种“取代”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一种“结合”,新的意识形态形成之后,中国人的社会参与程度大大提高,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越来越强。“1949年,一种来自外国的崇尚斗争精神、劳动光荣、尊重工农、有意识的行动主义的意识形态取代了儒学。新的结合有赖于更为广泛的政治投入的基础和更为雄心勃勃的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理想,而对革命斗争的广泛参与使之成为可能”。①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1968)》,第9页。
(二)中央与地方权力差序制度的构建
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要工作就是构建新秩序,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调整与厘清,这不仅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也是中国政治结构由中古向近世转变过程中一个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历史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秩序是一种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最大限度施展中央政府权力的制度,中央作为核心的政治惯例持续了2000多年,对地方的政治治理仅限于维持中央统治所必需。中共领导人把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和建设强大国家作为终身事业,这一事业的基础就是要组织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央政府来管理整个国家,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要向下贯彻行政权,在政治上把整个国家组织起来。
傅高义把共产党建立政权初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同中古社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比较,认为“新的情况改变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关系的本质,但基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②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1968)》,第87页。这一基本问题无关乎意识形态,而是单纯的权力结构问题,亦即地方主义问题。“在传统中国,……为获取如此庞大地域的国家的统治权,王朝建立者不得不与不同的协助其夺取政权的地方领导人结盟。”③Ezra Vogel,“Land Reform in Kwangtung 1951 -1953:Central Control and Localism,”The China Quarterly,No.38(1969),p.27.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就是中央政府向下贯彻行政权的过程,通过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政治运动、经济运动,中央政府逐步实现其目的,这一过程的意识形态动力则来源于爱国主义和对未来的希望。
据傅高义统计,到土改结束时,大约有6000名北方干部取代了广东当地干部,④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1968)》,第99页。当时广东境内县一级党委的位置为北方干部所占据,其他重要位置也进行了类似调整,中央政策在地方的贯彻程度得到大大加强。傅高义同时指出,中央控制是时代的共识与需要,“对寻求给这个国家带来秩序与准则的有效管理的渴求是整个事件的驱动力。……成功控制广东地方主义的原因之一是:这一渴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广东干部与民众的共识”。⑤Ezra Vogel,“Land Reform in Kwangtung 1951 -1953:Central Control and Localism,”The China Quarterly,No.38(1969),p.62.傅高义指出,“共产党在这头20年中实现了根本性的制度突破。在中国历史上他们第一次建成了强大的政治体系控制社会、改造社会,重要的经济、文化、教育、农村的活动都置于政府的管理范围之内”。⑥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1968)》,第332页。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后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真实情况比较复杂,“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意识到高度中央集权存在固有难题,因此,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期间进行了两次主要的分权运动”。⑦Zheng Yongnian,Contemporary China:a History since 1978,Chichester:John Wiley& Sons Ltd,Electronic Edition,2014,p.801.行政权的向下贯彻是相对于以往历史经验而言的,同时中央与地方关系也受到特定时期政治策略的影响,对地方力量的动员一直存在。
(三)经济运行的计划性
对经济运行的统筹规划开始于一五计划时期,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计划时代之后,中国社会的运行摆脱了盲目猜测,可以进行精确地预估了。然而,经济运行的计划性并没有完全坚持,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种诉求在实践中发生了激烈碰撞。“团结在毛主席周围的革命造反派是意识形态纯洁主义者。……他们号召激烈抨击日益增长的自私自利的趋势与官僚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党内当权派则是负责组织管理的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他们认为,有必要强调能力素质,即使这会有损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①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1968)》,第280页。这两种政治力量及执政理念的博弈在形式上表现为“左倾”与“右倾”之争,这里的“左倾”与“右倾”主要指经济的计划化及其市场化修正之间的区分。早期公有化使得经济活动的运行难以做到畅通自如,公有制下的经济交易过程缺乏“私利”这个润滑剂,计划经济在运行中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傅高义认为,这种经济上的计划化与政治上中央政府向下贯彻行政权的努力相辅相成,双重作用于由中古向近世转变的中国社会,“社会主义改造不只是对私人企业的征用和把管理权转换到公家的手中,它是要努力重组从事经济的企业和经济活动,……建立新的政治控制的路线”。②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1968)》,第120页。这一转变过程背后的推动力就是中共政权的社会征服,在征服的过程中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秩序被逐渐建构起来,中国社会也在被征服的过程中逐渐适应了这一政治、经济新秩序。
(四)集体与个人关系的调整
随着思想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政治上行政权的向下贯彻、经济上的计划化过程,一个自然结果就是个人权利不断地遭到来自集体的侵蚀,政治机构的增长不可避免地要求侵入以前属于私人的领域,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得以重塑,宗族主义传统遭到破坏,个人被组织到各种政治、经济组织中,作为更大集体的“社会”逐步建立起来,当然这种“社会”不是自我构建的,而是由政治力量塑造的。傅高义认为,集体主义之所以能够取代宗族主义重塑私人关系,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存在着对民族崛起的渴求,“共产党激起了人们多年的希望,希望他们的政府足够强大,能维持秩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希望比其他任何东西所起的作用更大,使强大的政治组织成为可能”。③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1968)》,第334页。集体主义适应了中国由中古向近世转变的时代要求,改变了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关系开始逐步打破封闭性与内向性,向现代意义上的私人关系转变,“新型普适伦理的发展之所以具有制度上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能够减轻政治控制意义上的风险,还因为一个正经历着迅速变迁与重组的现代化社会要求不同社会背景、地域、个人品位的人们之间能够轻易地建立起彼此关系。……这意味着同志关系第一,朋友关系第二”。④Ezra F.Vogel,“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The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Commun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No.21(1965),p.60.
三、这一时期傅高义中国研究评析
国内学术界对傅高义观点的引介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界,他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1968)》被认为是对共产主义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典范之作。在史学界有学者按照黄宗智的“三代说”把傅高义划入地方史研究序列,认为他对广州的研究是以区域社会视角探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问题的代表。⑤王日根、肖丽红:《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美国中国地方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57页。
这一时期傅高义的中国研究也得到了美国中国学界的认可,尤其是傅高义对中国副省级以下地方政治展开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这对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地方治理提供了借鉴。总体上,傅高义这一时期的研究范围可以概括为社会学视野下的新中国早期社会政治史。他不仅关注国家层面的政治运行机制,也关注底层微社会 (micro-societal)在政治体制运行过程中的参与形式,尤其是对作为体系的社会运行结构的考察,这些工作最能体现美国现代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⑥Richard Baum,“Canton Under Communism(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 -1969)by Ezra Vogel,”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9,No.4(1970),pp.931-933.
傅高义接受过严格的社会学学术训练,他的中国研究运用社会学方法展开,倾向于从社会系统的角度出发去考虑一个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过程,这种做法使得其研究成果的解释力更强,而对底层社会的整合研究强化了这种解释力,为了避免研究工作的琐碎化,傅高义兼顾了对底层社会与国家政治的考察,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傅高义的中国研究既有详细的历史叙事又有严谨的社会学分析,事实呈现与理论运用同步是其研究特点之一。他对问题的细微观察与严谨分析使其研究结论更加丰满与贴近事实,不至于陷入事实堆砌或理论空洞的境地。
傅高义声称其秉持价值中立这一社会学研究的准则,“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对共产主义提出批评,而是要努力客观地去理解它,去认识这个社会的活力和发展。……我们不会迷信于毛泽东的话语,也不会完全听信在台湾地区和美国的反共产主义者的言论”。①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 (1949-1968)》,第4页。傅高义为追求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曾坚持自费完成对广东的考察,以避免出现利益牵制的情况。
傅高义认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者具有三个共性特征,即冷淡的冷战斗士、边缘化的社会科学家和过于自信的道德家。②Ezra F.Vogel,“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Marginals in a Superpower,”In Hsin-chi Kuan(ed.),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Tokyo:The Center of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1994,p.189.在这里,他形象地描述了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主旨、学科地位及价值取向,傅高义声称这一时期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中国学研究者都是站在稍稍偏离冷战思维的主流轨道冷静观察中国的,不过,如何既作为冷战斗士又能够保持价值中立?这是引起我们困惑的地方。
实际上,“任何史家都无法完全摆脱在他生活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某些假设”。③[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9页。20世纪60—70年代,中美两国正处于冷战状态之中,傅高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介入当代中国研究,一方面其资料获取来源受限,他当时利用的资料主要是大陆的一些官方报纸或综合性晚报,接触并采访一些从广东来到香港的内地人,这对其研究成果的形成产生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傅高义也很难脱离时代语境,如前述“冷战斗士”体现的价值立场,再如其论著中经常出现的“西方中心论”的逻辑预设,虽然傅高义一直在试图避免这些因素对其研究工作的干预,但要想在实践中完全排除意识形态或理论预设的影响则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冷战时代,这种困难程度将会大大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