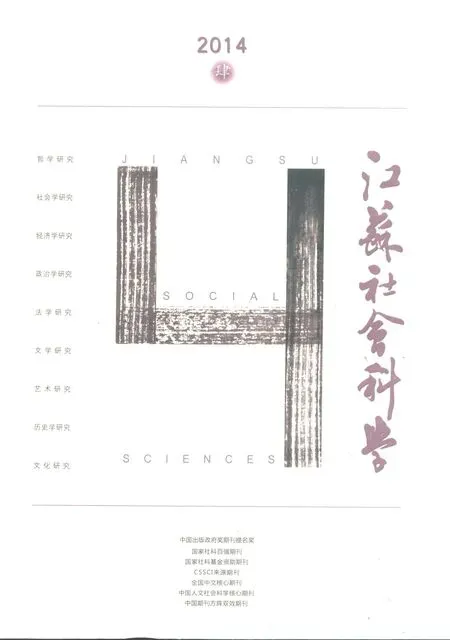“怀旧”的城市诗学
——关于“苏州形象”的影像建构
曾一果 王莉
“怀旧”的城市诗学
——关于“苏州形象”的影像建构
曾一果 王莉
在今日的城市文化热中,人们多将目光对准上海、北京,但对苏州这样一个曾经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历史名城没有给予太多关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苏州经历了哪些变化?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如何叙述和展现它?为何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影视媒介关于苏州形象的视觉再现,经常有一种浓厚的“怀旧色彩”?这些议题值得关注。本文试图对《小城之春》、《游园惊梦》、《橘子红了》和《凤穿牡丹》等影视媒介加以考察,探讨它们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社会语境中建构一套“怀旧诗学”,并分析此“怀旧诗学”所包含的内容,及其如何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动。
城市文化 怀旧诗学 苏州形象 本土认同 全球化
引言
近年来,上海城市文化研究是一门显学,特别是大众媒介的老上海怀旧引发了李欧梵、张英进、孙玮等学者的关注,但是学术界对于上海身边的苏州——一座具有浓厚怀旧色彩的城市却没有给予太多注意。不过,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两代,苏州可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之城,对苏州这样一个曾经繁华的古城,进入现代之后,它经历了哪些变化,电影等现代媒介如何叙述和展现它,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发掘本土文化资源,重建城市自我认同已为新潮流。在此背景下,对苏州这样一座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古城加以考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现代大众传媒的视觉建构,世人可以深入体察传统城市面对变化世界的一种“复杂的情感”。
张英进说:“城市在中国文化观念中呈现着迥然不同的形象。‘城’既可以指小镇,如县城或山城;亦可以指城墙,一种从小镇到故乡皆设有的防御式建筑。‘市’可以指市场(从小镇的农贸市场到都会的金融市场),亦可以指都市或都会。从形象角度看,城市的象征可以是小镇的一片城墙,一座孤塔,一湾小溪;或是古城的一坊牌楼,一座宫殿,一片花园;抑或是都会的商业区、红灯区、贫民区。从观念角度看,小镇可以表示一种宁静,古城可以表示一种秩序,而都会可以表示一种喧嚣或紊乱。”[1]张英进:《中国电影中的城市形象》,《电影的世纪末怀旧——好莱坞·老上海·新台北》,〔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古城苏州便是张英进所说的依靠城墙、农田、河流、宫殿和花园组成的一座“田园城市”。它美丽富饶、文化发达和远离政治,是帝王将相的后花园和才子佳人理想的约会场所,直到今天,电影电视等媒体中所展示的“苏州”,经常是充满怀旧的、诗意的和宁静的城市景观。
本文要特别解释一下“怀旧”这个众说纷纭的词语。“怀旧”意指怀念过去。但已有学者指出,“怀旧”并不仅仅是“对历史的简单唤起和伤怀”[2]张英进:《影像中国》,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页。,“怀旧(就像记忆、追忆和怀想)深深牵涉到对我们是谁、我们要干什么,以及……我们要去哪里的认识。简而言之,怀旧是一种我们在永无止境的建构、维护和重构身份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种方法。”[3]〔美〕戴维斯:《渴念昨日:怀旧的社会学》,转引自张英进《影像中国》,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页。“怀旧”是主体身份不断的建构过程,无论是“上海怀旧”,还是“香港怀旧”,均是对城市身份的不断建构和再建构。当然,不同的城市怀旧出发点差异很大,例如今日的上海怀旧多指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摩登的上海景观,而对于苏州,“怀旧”则更多指向乡土、诗意和田园风景,当然,“怀旧”其实是一个流动概念,在不同时期,在不同文化碰撞中被不断整合、重构。本文试图由《小城之春》、《游园惊梦》、《橘子红了》等影视剧,探讨不同时期的影视媒介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时空维度中,建构苏州的“怀旧诗学”,并分析此“怀旧诗学”所包含的复杂内容,及其是如何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动而变动的。
一、乡土情怀与诗意小城
关于苏州“怀旧诗学”的媒介建构首先要提的是费穆的《小城之春》(1948年),这部电影较早用影像手段建构了具有浓厚乡土情怀的城市怀旧诗学空间。电影开头长镜头与蒙太奇交替使用,藉助女主人公的“独白”,简洁地勾勒出一个战后江南小镇形象:小桥、深巷、古旧城墙和江南老宅,这个小城以费穆的故乡苏州为原型。江南老宅的男主人戴礼言因病整日坐在颓败的院子里;女主人周玉纹是一个对生活感到无望却又不愿反抗的传统女性,她对身患疾病的丈夫已无爱情可言,自认为“每天都是平平淡淡,似乎永远也不会有故事发生,而每个人的世界几乎都一派荒芜”。可她依然恪守妇道,唯一的活动是踱步于破败的城墙,或坐在丈夫小妹房间里绣花。但是江南小城的平静空间因一个“外来者”到来而被打破,来自上海都会的章志恒不仅是戴礼言的好友,而且是玉纹儿时同乡兼恋人,三个人在战后破败的江南老宅中戏剧性地重逢了,电影展现了几对男女人物间微妙的情感关系。
费穆为何将几个人物置于战后破败的江南小城镇空间?通过女主人公周玉纹的叙述我们可以知道,戴礼言生病主要原因是战争导致了家道没落。显然借助电影,费穆不仅思考乱世男女的情感纠葛,而且思考战后家园重建、现代与传统等话题。经历八年抗战,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对本土文化建设有很强的迫切感,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家园及文化成为当时社会主潮。《小城之春》便是战后本土文化抬头的体现,影片在具有浓厚乡土色彩、怀旧意味的古城空间中展开。“家,在一个小巷里,经过一座小桥,就是我们家的后门……”电影开头女主人公的喃喃自述,表达了对家园和本土的认同情怀,小桥、城墙和庭院,虽已破败却是赖以生存的家园。电影浓厚的“怀旧情调”,足以激发那个时代观众的“家园记忆”。香港学者洛枫在解释“怀旧”时突出了两点:一是“怀旧”有“美化过去的功能”;二是“怀旧”是建立自我身份认同(identity)的途径。“‘怀旧’不独关于过去的事情,而且是联系现在、延续将来的;人们透过对过去的回想寻找自我,然后对比或反省今日的我,再推算将来的面貌,这完全是一个自我身份建构的过程。”[1]洛枫:《世纪末城市》,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小城之春》描述了戴家从“战后的迷惘”,不断“回想寻找自我”,到影片最后“自我逐渐清晰”,家园也慢慢重建起来。这一过程的视觉再现,不断唤醒观众对家园和本土的认同意识。
不过,在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的时空环境中,《小城之春》的怀旧城市诗学空间其实是一个游移、悖论的空间。廖新田在讨论台湾本土意识时就指出“本土”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概念:“‘本土’不仅是地方主题的描写、记录与表现,而是一种具有主体建构的意义。”[2]廖新田:《近乡情怯:台湾近现代视觉艺术发展中本土意识的三种面貌》,〔台北〕《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没有一个“纯粹的本土”,本土的表现形态跟主体建构有关,随着主体认同变化而变化。这位学者进一步分析了各种表现乡村的怀旧之美,指出其实“美不在‘旧’中,而是藉由现代的凝视,即‘纯粹’的视觉(the‘pure’vision)所启动(Chris,1995)。易言之,只有用特殊的眼光才能发觉乡下朴实之质、斑驳之美。”[3]廖新田:《近乡情怯:台湾近现代视觉艺术发展中本土意识的三种面貌》,〔台北〕《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同样,《小城之春》所呈现的宁静纯粹、田园牧歌的小城风光,并非小城本来面貌,而是在小城镇与大都会、现代与传统交织的社会语境下的媒介建构,电影希望借此唤起观众的家园记忆和本土情怀。
《小城之春》对于本土其实也流露出了复杂的态度,从一开始,破败的江南家园就并非是女主人公的情感认同、归属之地,女主人周玉纹喜欢在城墙上徜徉,而不愿回到死气沉沉的破宅中;丈夫戴礼言肩负着维护家园的使命,但是战火毁坏他的家园,使其失去了重建家园的信心,并因此患上了难以治愈的精神疾病。他每日失魂落魄地坐在破败的老宅中不知所措,其“疾病形象”说明了本土重建并非易事,家、小城和整个国家似乎都像戴礼言一样需要治疗,重振信心。而且治愈疾病、重建家园不仅依靠自我(地方、传统)完成,更需要“外来者”(都会、现代)的帮助。在电影中,“外来者”名叫章志恒,他学习的是西医,来自现代大都会上海,朝气蓬勃,西装革履。他闯入了死气沉沉的江南古城,探望老朋友,但是却引发了戴家的家庭危机。作为周玉纹曾经的恋人,章志恒点燃了女主人公内心的欲望、幻想;不仅如此,章志恒的到来也让戴礼言青春活泼的妹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希望,她希望章志恒能带其到上海去读书。总之,宁静的江南古城因章志恒的到来有了生机活力却又危机四伏,他与小镇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摩登上海与传统苏州关系的隐喻,富有诗意的江南小城不仅有战争的创伤记忆,而且面临着摩登都会的“情感诱惑”。
显然,费穆很清楚,在现代性的侵入之下,“本土”已不再是一个纯粹概念。电影真实展现了江南小城宁静空间中弥漫着的骚动、渴望和梦想,这是一个交织在不同话语中的怀旧诗学空间——爱与恨、诗意与荒凉、希冀和绝望、乡土与都会、传统与现代……。不过,也正是由于不同话语的碰撞、纠缠,诚如一位学者所说:“地方认同的需求因着外在环境而更为强烈。在危机意识中,回归乡土的呼声让审美眼光投注在自己朝夕生活的土地上。”[4]廖新田:《近乡情怯:台湾近现代视觉艺术发展中本土意识的三种面貌》,〔台北〕《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在20世纪40年代,费穆将目光投射到本土家园,建构江南小城的怀旧诗意空间,正是出于强烈的本土危机感。虽然新时代来临,虽然男女主人公在旧与新、情欲与道德之间挣扎,但是传统伦理观念依然是江南小城社会秩序的基石,“发乎情而止于礼”。在电影结尾,费穆毅然安排章志恒离开小城,让江南小城重归平静,恢复往日秩序。
二、都市消费与“怀旧”江南
2002年田壮壮翻拍的《小城之春》上映,新《小城之春》试图再现费穆电影的情感世界和江南小城风貌。不过,田壮壮的《小城之春》乃是新社会语境下的产物,同样的“怀旧诗学”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认同立场与文化指向。
费穆的《小城之春》虽然不属于激进的“左翼电影”,不像《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那样高调宣扬阶级斗争与民族主义,但在20世纪40年代浓厚的民族主义社会氛围中,影片不可能是置身家国之外的单纯男女“情感戏”。在电影中,“八年抗战”本就是江南小城出场的重要背景,唤起观众的家园记忆与本土认同意识,重建遭遇战火创伤的家园(心灵、精神和现实世界)是电影主旨,所以在电影开头,便有女主人公以第一人称口吻叙述小桥、巷子和家园的空间方位,通过她的感怀,个人与小桥、江南老宅彼此连接为不可分割的“家园世界”,但在新《小城之春》中,这种强烈的家园意识大大减弱,女主人对小桥、巷子和家园的“独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小桥、巷子、老宅和人物的“自然呈现”,人物变成了江南小城诗意空间的一部分。通过这一转换,新的《小城之春》倒更像一部介绍江南风光的“旅游片”,刻意形塑没有主体情感的江南小城形象。
因而,尽管田壮壮在新《小城之春》中试图恢复原作神韵,努力还原费穆电影的怀旧情调和田园景象,但毕竟两部电影所处时代环境不同。田壮壮的《小城之春》是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商业化浪潮中出现的本土电影,其对江南小城怀旧诗学空间的营造,是对全球化和商业化的反应,当然,这种怀旧诗学的建构,本身亦是20世纪90年代商业化和全球化怀旧风潮的产物。同样的影片还有以第六代导演为主的《孔雀》、《青红》和《电影往事》等,均带有浓厚的“怀旧意识”,着力展现昔日的“城市生活”。《南方周末》记者李宏宇将这种现象称为“被消费的集体怀旧”,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导演的“集体怀旧”并不完全出于情感记忆的需要,而是“‘中国制造’的怀旧邂逅全球的‘中国情结’”,是基于一种“商业消费”的文化商品。他进一步指出,在这种商业消费环境中,西方片商和电影机构主导着“怀旧”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要拍怀旧,在选景方面就要比当下题材花更多的钱,服装、美术、道具也更贵。国外片商和电影基金在其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荷兰的弗迪西摩公司代理了《青红》与《电影往事》的销售,而因为与张杨良好的合作历史,它在更早期就介入了《向日葵》;《红颜》得到了法国南方基金,另一部分预算来自曾经投资王超两部影像的制片人。”[1]李宏宇:《中国电影:第三次集体怀旧》,〔广州〕《南方周末》2005年9月15日。《电影往事》、《红颜》和《孔雀》等电影的“城市怀旧”当然也有回忆往昔、寻求身份认同的情感需求,但本质不是为了重构个人、城市和民族历史,这些电影注重营造美学情调和都市氛围,远大于强调还原真实的过去。田壮壮回答媒体所以拍《小城之春》主要是因为《蓝风筝》被禁播10年没拍戏,才选择了“一个无伤大雅的题材,成本也低”[2]蒯乐昊:《田壮壮:所有人都关心钱》,〔广州〕《南方人物周刊》第182期。。意识形态和商业因素是其翻拍的主因。田壮壮是北京人,江南并非他熟悉的题材,摈弃原作开头女主人浓烈的“家园独白”便很容易理解,他更关注电影所营造的“江南美景”,而不是“家园情怀”,不是为了表达对地方和家园的精神认同。所以,田壮壮的《小城之春》所营造的怀旧诗学与费穆的原作截然不同。费穆努力建构的是一幅恬美沉静的“家园图像”,以唤醒人们的本土与家园认同意识,而田壮壮的《小城之春》更接近张英进所说的“民俗电影”[3]张英进:《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判重构及跨国想象》,胡静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263页。,竭力营造的是一幅渗透着都市情欲的唯美“江南场景”。
相比于电影而言,电视剧更是通俗媒介和文化工业,赢得收视率是王道。在20世纪90年代的怀旧消费潮流中,“江南”不仅是电影,也是电视剧赢得观众的重要手段。《橘子红了》、《凤穿牡丹》和《红粉》等电视剧均以江南为背景,清末民初、江南小镇和深宅大院架构了许多电视剧的故事时空,不同身份的人物被置于具有江南特色的地理和文化空间中。这些带有浓厚江南怀旧符号的电视剧并非想通过“怀旧”重构个人和集体身份,建立人们对于江南的地理和文化认同,更多的是用怀旧满足上世纪90年代以来观众的“浪漫想象”:小桥流水、江南老宅和才子佳人,都是极易唤起现代都市男女浪漫爱情想象的重要元素。陈龙就指出:“《橘子红了》是一部视觉盛宴,场景、服装、道具、人物语言等若干元素将这种浪漫化的视觉效果加以强化,在这一作品中,江南的浪漫风情被高度夸张地表现出来,成为荧屏的一道奇观。”[1]陈龙:《文人想象、唯美包装和市民趣味》,《民营的激情与想象》,〔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他认为电视剧常将江南风情夸大,将文人想象、唯美包装和市民趣味相结合,经过这一处理,“三言二拍”之类的通俗传奇便迅速转变为迎合现代市民趣味的“城市故事”,江南小镇由此成为都市青年表达浪漫爱情的怀旧诗学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跟《小城之春》一样,《橘子红了》中的“江南老宅”并非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地理空间。电视剧中的容老爷偶尔回到“老宅”,他平时是住在上海。传统江南老宅与摩登上海在电视剧里并置比邻,却有着不同的物质和文化景观。从上海到容府,是富有怀旧诗意的老宅、小桥和橘园,一旦由容府转到上海,便是洋楼、交际舞和摩登女郎;而且不同城市在对照中被“性别化”,“江南老宅”是封闭的女性化空间,“摩登上海”则是开放的男性化空间。当然,在《橘子红了》中,苏州和上海这两个文化地理空间并非完全对峙,而是互相影响。上海的流行时尚迅速传播到江南乡下,江南传统观念依旧对摩登上海起制约作用,容老爷在上海做生意,住洋楼、娶摩登女郎,骨子里却还是乡绅,不仅要再娶秀禾“传宗接代”,当二姨太寻死觅活不让他离开上海,他走时头也不回。他的地位不容动摇,摩登上海没有让他思想开明,相反,上海的商业力量只是加强了其传统男性霸权思想而已。总之,本应互相排斥的传统力量与现代市场霸权在电视剧中互相勾结,共同缔造了容老爷的“新霸权”,在新的男权世界中,二姨太、秀禾和大太太统统只是容老爷的附属物。
曾丽珍导演的电视剧《凤穿牡丹》(2008年)同样建构了具有怀旧诗意的“苏州形象”。在这部电视剧中,苏州仍然以一种“刻板形象”出现,这一刻板形象通过女性主人公郁无暇体现出来,其贤惠、安静、乖巧和淑女风范成为苏州城市形象的最好诠释,无暇的名字也有此寓意——洁白无瑕。作为一个苏州城的传统女性,无暇的妈妈告诫无暇,应该“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完全遵循传统父权制社会秩序。不过,《凤穿牡丹》没有像《橘子红了》那样,让女主人公一直沉沦在江南老宅空间中,而是让郁无暇走出苏州,到北平打拼。电视剧罕见地将苏州、上海和北平这三座城市放在同一坐标系中互相比照。三座城市在电视剧中也是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北平是一个男性政治、商业霸权和传统礼教混合的半封建城市,无暇之所以嫁到北平,是北平霍家势力大,郁家虽拥有刺绣绝技,却依然濒临破产,只能将女儿郁无暇嫁给霍家抵债;上海则是交织着罪恶与自由的半殖民都会,在这里自由、革命、黑帮和外国势力互相交织;相比北平、上海,苏州则依然是一个传统化、女性化的“城市”——安静、乖巧和悠闲,苏州女子无暇便是这座城市的代表。无瑕一到北平,便陷入了霍家的家族权力斗争漩涡中,尽管她单纯、善良和乖巧,甚至与丈夫冬青远走上海以避祸,都无法阻挡灾难的降临,霍冬青在残酷的家族内斗中遭遇不测。郁无暇由此觉醒,走上独立道路,逐步扛起家庭重任,打理丈夫遗留的家业,由一个传统居家少奶奶,瞬间转变为一个识时务的现代“新女性”。她不仅与邪恶的二叔斗智斗勇,而且在国难当头,不屈不挠地与日本人抗争,宁愿废掉双手也不愿为日本天皇刺绣。在电视剧结尾处,无暇竟义无反顾地投入保家卫国的斗争洪流中,民族主义话语成为电视剧惩罚恶人的最好手段。不过,颇令人奇怪的是,郁无暇与日本的斗争被大书特书,但北伐军在霍家血腥屠杀却被轻描淡写,其实郁无暇由传统女性变为时代新女性并非全靠自己,她依靠的是在上海滩堂口混的“大哥”帮忙。当然,电视剧是大众娱乐工业,要考虑费斯克所说的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的双重效益[2]〔美〕约翰·费斯克:《电视文化》,祁阿红、张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48页。,情节离奇生动又不违反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电视剧必须考虑的问题,至于是否合乎历史事实和叙事逻辑,那倒是次要的。
总之,《凤穿牡丹》借助郁无暇这个“女性形象”,维系了观众对于苏州这座江南古城的诗意想象,小桥流水、宁静安然和小家碧玉依然是苏州这座江南古城吸引观众的法宝,而郁无暇从一个传统女性摇身一变而为民族大义的“新女性”,亦让观众对江南古城有了新的认识。
三、文人雅趣与颓废的“苏州想象”
纪录片《江南》与《徽州》的编剧杨晓民在谈创作时说:“江南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诗化的存在。我认为,江南与当代生活的联结点,或者说传统江南与当代江南时空的联系,更多是精神上或心灵上的。”[1]转引自曾一果、张梦晗:《视觉再现:城市文明与人文纪录片的叙事镜头》,〔北京〕《中国电视》2011年第5期。这句话道出了江南怀旧诗学的本质。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怀旧诗学的媒介建构,确实经常是与文人及其生活(物质的和精神的)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园林这样的空间更是成为文人聚居游乐、表达才艺的最诗意空间,是他们远离政治纷扰、只谈风月人生的“理想空间”。陈江在《园林·书斋·茶寮》中说:“自明初以来即因朝廷的歧视、限制政策而深感压抑的江南人士,此时又因目睹富商巨贾在物质生活上的挥金如土而备受刺激。于是,他们刻意追求一种悠闲适意的、艺术化的生活情趣,以平衡满心失落,消磨胸中块垒,并力图以‘清逸高雅’的生活品味来对抗奢靡豪华的胸中块垒,从而满足其文化上的优越感,厘清日益混淆的‘士’、‘庶’之别。园林、书斋、茶寮,即为文人士夫体现其‘雅韵逸趣’的主要方式和手段。”[2]陈江:《园林·书斋·茶寮——晚明江南城居生活中的“雅韵逸趣”》,姜进主编《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7页,第349页。
刘郎导演的人文纪录片《苏园六记》(2000年)用纪录影像试图再现苏州园林所蕴含的浪漫“诗学空间”。纪录片分为《吴门烟水》、《分水裁山》、《深院幽庭》、《蕉窗听雨》、《岁月章回》和《风扣门环》六章,从不同角度讲述不同时期的“园林故事”,介绍园林里的建筑、花草、假山、亭台的文化意蕴。纪录片刻意再现园林精致美景,特别强调苏州园林与中国传统文人生活及精神的内在关联。园林的曲径通幽、亭台楼阁都象征了中国传统文人淡泊名利,不愿随世沉浮的独立品格,以及超尘涤滤天人合一的“雅韵逸趣”。纪录片告诉观众,苏州园林的高妙在于其“城市山林”,闹中取静。隐于朝市和寻常街巷的“大隐”、“中隐”,若能自持其“心”,可不拘其“迹”,故可亦仕亦隐、心隐身不隐,而山水园林、诗书茶酒,也无不可隐,只要“居轩冕之中,要有山林的气味;处林泉之下,常怀廊庙的经纶”,仕隐便可两栖。江南文人好游山水,竞筑园林,追求一种恬淡闲适、风流雅致的艺术化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的隐逸观[3]陈江:《园林·书斋·茶寮——晚明江南城居生活中的“雅韵逸趣”》,姜进主编《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7页,第349页。。因此,当园主官场失意,在苏州城中圈起一方天地,叠山理水,构筑“城市山林”,便可怡然自得。
昆曲的兴起为居住在城市里的文人们更是增添了“浪漫情调”,在园林里喝茶、读书和听曲既是文人的日常生活,同时又是他们追求艺术生活的体现。昆曲发源于14、15世纪苏州昆山,是揉合了唱念做表、舞蹈及武术的表演艺术。自明代始,苏州园林兴起造园之风,迤逦之声风行江南,园林与昆曲便注定了某种缘分,相伴相生。《苏园六记》多次直接提起昆曲、园林与文人的渊源:“拙政园中的卅六鸳鸯馆,便是园林主人与友人们欣赏并演唱昆曲的地方。而网师园的濯缨水阁、怡园的藕香榭,也都具有演戏的功能。”“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认为园林讲究布局结构,而戏曲结构也应该象园林一样。要布置得曲折幽深,直露中要有迂回,舒展处要有起伏。”园林与昆曲的迂回曲折、抑扬顿挫,用艺术的手法美妙地诠释出东方美学的特征之一,而这种风雅之美经过文人之手,浸透在苏州这座城市的精髓之中,并且逐渐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的精神资源。陈从周曾说:“老实说,我爱好园林,是在园中听曲,勾起了我的深情……”[4]陈从周:《园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昆曲是流动的园林,园林是凝固的昆曲”,昆曲与园林共同建构了文人风雅的物质与精神生活。
《苏园六记》对于园林人文精神的推崇使其与《江南》、《微商》一样,开启了电视纪录片的人文主义风潮,尹鸿等认为这股人文思潮体现了中国纪录片想“在全球环境重新认知自己的文化传统”。“通过制作人文纪录片的方式,重新承担起文化传播这样一个历史的责任。”[1]周亚平、尹鸿等:《记录、记忆与介入》,〔北京〕《读书》2006年第10期。著名纪录片导演周亚平在谈及《江南》时,更是指出之所以拍“江南”、“徽州”,主要是“电视也可以作为记忆而存在的”,他批判了现实社会的道德混乱和电视过度娱乐化所导致的“文化危机”:
我们也许没有宗教的信仰,但是应该有文化的信仰。中国本土文化的传承性、整体性、多样性都非常可贵。然而,经济高速发展中急功近利的心态,不仅带来了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恶化,而且造成精神上的荒废。在这样的背景下,《江南》等作品表现出的文化关怀,就是为了寻找精神的文化家园,展现前人的文化方式。[2]周亚平、尹鸿等:《记录、记忆与介入》,〔北京〕《读书》2006年第10期。
他希望通过媒介参与,唤醒人们的文化意识,重建人们的集体记忆——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认同和记忆。不过有学者指出,这些人文纪录片一个共同缺点是仅将传统当作怀旧审美空间,忽视了园林等诗意空间所包含的生活、历史和社会风俗等成分。吕新雨认为人文纪录片刻意排除“现实的维度”,“把影像变成了抢救性的拍摄——从现实中抢救出来。……在《江南》、《徽州》这两部片子当中,我们基本看不到人,摄制组总是赶在早上五点没有人的时候去景点拍摄,以保证游客不出现在镜头中。我相信这也是非常自觉的一个追求,要刻意把现代具有破坏性的因素都清洗干净,只留下那些象征和代表人文美好、温馨,或者说刻意寄托精神家园的‘物’的遗存,所有的现代因素都被理解为一种干扰。”[3]吕新雨:《人文纪录片意欲何为?》,〔北京〕《读书》2006年第10期。《苏园六记》亦如此,过于突出园林的“诗性存在”,忽略了园林与城市日常生活的内在联系,其实文人隐居于园林,吟诗作赋,并非完全与世事无关:“宅和园才是完整的园林面貌,而且园林生活毕竟只是‘中隐’,除了向山林的退隐意向,也还须保留入世的规范生活场景。”[4]舒可文:《城里——关于城市梦想的叙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95-96页。而且,苏州园林不仅是中国最具诗性的场所,同时也是一种不思进取、醉生梦死的颓废空间。
香港导演杨凡的《游园惊梦》(2001年)便对苏州园林展开了另一种颓废的“文化想象”,电影由王祖贤和宫泽理惠主演。与田壮壮《小城之春》一样,《游园惊梦》是全球怀旧电影浪潮的产物,而且是以跨国组合的方式生产和消费“怀旧”——王祖贤来自台湾,宫泽理惠来自日本,杨凡和吴彦祖来自香港,大陆提供拍摄场景和内地参演人员。在全球怀旧浪潮中,香港人怀旧老上海并不稀奇,王家卫、关锦鹏等人都热衷于拍摄“老上海故事”。之所以如此,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主要是香港在上海身上投射了它“自己”:“其目的是试图以权威的叙述话语帮助现代香港确立权威的殖民文化身份,并以怀旧暧昧的影像、曲折的‘小叙事’暗示出‘殖民/后殖民的香港与内地异质的政治立场。’”[5]陈林侠:《港台电影中的后殖民演绎:从“双城故事”到“台湾意识”》,〔北京〕《文艺研究》2009年第3期。“上海”和“香港”构成了互为镜像的“双城”。
尽管同是跨国资本运作下的“城市怀旧”,杨凡的“苏州怀旧”与王家卫、关锦鹏等人的“上海怀旧”还是有很大区别。王家卫、关锦鹏等人借助上海来讲述“香港故事”,在他们眼里“旧上海就是现代香港”,所以他们拍摄上海不过是拍摄香港而已。而杨凡的“怀旧苏州”并非是借苏州讲述“香港自己的故事”,而是希望通过影片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传统,他的电影为观众特别是香港观众提供了一种观看苏州园林、昆曲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在此过程中,他也试图重新审视香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关系。
《游园惊梦》以荣兰——一位现代知识女性的视角切入,通过她(现在)展现荣府过去夜夜笙歌、纸醉金迷的传统大家族生活。电影展示了一个无以复加的、优雅精致的传统文化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不再像刘郎《苏园六记》里那样只有空荡荡的“物”,而是一个融日常、艺术和文化于一体的传统“生活世界”,现实生活和舞台生活在这个空间有时彼此不分,例如电影中的“后花园”既是生活空间,同时亦是昆曲表演的舞台空间。游园和唱昆曲贯穿了整个电影,人物的感情和江南小桥流水、青砖黛瓦交织在一起。正如女主人公翠花对女儿说的,荣府是一个不同于社会的“漂亮花园”,美丽的园林和迤逦之声构建了一个令人神往、却又颓废无比的“诗性世界”,荣兰和翠花两位主人公便坠入了这个颓废的诗性空间和风月世界中不能自拔。
不过,荣府的“诗性世界”也是一个充满礼仪、等级和秩序的世界,游园、听戏和看戏的空间都已经被等级化,体现着文化和社会身份的区隔,不同社会身份对应着不同的空间位置:荣老爷可以躺在床上抽鸦片、看戏;家庭其他成员按等级秩序围坐四周,下人们则是端茶倒水,戏里的诗性空间与戏外的等级秩序构成了鲜明对照的两重世界。翠花的孤寂也揭露了荣府种种不为人知的一面,显示了荣府繁华背后的内部裂隙,而一道大门更是将荣府(“漂亮花园”)与外界(社会)隔绝开来,身在荣府空间中的人醉生梦死、糜烂颓废,荣府之外却是充满家国忧思的“现代空间”,当翠花被赶出荣府时,便立刻从衣食无忧的“花园世界”回到了柴米油盐的“现实社会”中。电影将荣府这个颓废的诗性空间置于传统与现代猛烈碰撞的民国时代语境中,这个空间的优缺都令人深思。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没有像一般的“苏州怀旧”藉由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碰撞,进而控诉传统文化空间对于女性的压迫。相反,却出人意料地展示一位“新女性”对传统文化空间的极端迷恋。荣兰作为民国以后的现代新女性,在新式学堂担任英文教师,她喜欢写日记,铭记母亲的话“要中国富强,女人就得走出闺房”。当有女学生问她为何要学英文时,她回答说:“英文学好了,可以替国家做大事”,完全是一位现代中国的“新女性”。但是,电影却出人意料地表现了这位“新女性”骨子里对传统的迷恋,荣兰迷恋昆曲甚至爱上了从得月楼赎身进入荣府的翠花。两人每天游园赏景,坠入荣府的传统诗性空间不能自拔,以致一副现代派头、英俊年轻的南京教育部特派员都无法改变她。
透过荣兰和翠花的“同性恋故事”,《游园惊梦》不仅向观众展示了中国传统世界精致、儒雅和细腻的文化气质,也深刻揭示了传统空间所弥漫的腐烂、颓败和堕落气息。电影对传统世界显然怀有“复杂情感”,这种复杂情感似乎也表明大部分香港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时所怀的“矛盾心理”:香港曾经是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城市,说英文、吃西餐、跳交际舞已经成为香港城市文化的核心,但在骨子里,不少香港人却倾慕精致儒雅、富有诗意的中国传统文化(尽管中国文化并不限于此)。杨凡的《游园惊梦》可以说为香港观众了解和认识中国诗性文化传统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结语
大卫·克拉克在考察电影与城市关系时曾指出:“都市化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扩展而来,它不仅直接彰显出人类生活模式趋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更是导致此一转变的重要动力。因此,电影中的景观,既取自步调紧凑的现代都市生活,又有助于形成忙乱、脱序的都市节奏,使它成为社会准则。”[1]〔英〕大卫·克拉克:《窥见电影城市》,大卫·克拉克编《电影城市》,林心如、简伯如、廖勇超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4页。陶瑾:《寻根热后的苏州之家》,〔苏州〕《现代苏州》2012年第19期。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从1995年到2008年,我国城镇化率由29.04%提高45.68%”[2]魏后凯:《多元化: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9月16日。,这个比例还在不断扩大。苏州这个江南古城在此城市化浪潮中迅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苏州古城面积只有22.63平方公里,但到2020年,苏州中心城区的面积估计将增加到599.2平方公里,城市扩大了好几十倍[3]根据《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中关于苏州城市的规划。。城市面积的迅速扩张改变了苏州城市的结构,“作为经济发达、现代文明的开放型城市,今日苏州已演变成‘老苏州’、‘新苏州’和‘洋苏州’的共同家园”[1],《苏州日报》、《现代苏州》等大众媒体经常用“老苏州”、“新苏州”和“洋苏州”描述苏州城市空间的“新变化”。
苏州城市空间的变化也深刻地反映在了影视剧中。近年来关于苏州的影视剧,不再仅仅是江南小城的“怀旧诗学”。在杜琪峰的城市电影《单身男女》(2011年)中,金鸡湖、摩天轮和高楼大厦等“新地标”取代了小桥、古宅和园林等常见的“老苏州景观”。苏州被放在了全球城市格局中展现,与上海、香港等城市同台竞技。《单身男女》的故事主要发生在香港,苏州姑娘程子欣(高圆圆饰)跟随男友到香港,不料被其抛弃,而后便与张申然(古天乐饰)、方启宏(吴彦祖饰)两位香港人开始了“三角恋”,香港的全球都会空间让爱情变幻莫测,不过,两个香港男人竟然都爱上了程子欣,并都飞向程子欣的故乡苏州表达爱情。在这个典型的都市爱情故事中,值得注意的是,苏州虽然已经跻身中国发达城市行列,却还无法与香港这样的全球都市相抗衡而被“女性化”,只是与《凤穿牡丹》等影视剧不同的是,程子欣已是一位游移于两个香港男人间的“摩登女性”。有香港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香港的经济奇迹让港人在大陆面前充满了身份“优越感”[2]张少强:《冻结的时间,冻结的空间——后九七香港研究的警示》,《香港社会科学报》2008年春/夏季号(第34期)。,《单身男女》中两个香港男人竞逐“苏州女孩”,可以说,依然是香港“北进”过程中自我感觉良好的体现。当然,两个香港男人为追“苏州女孩”都飞往苏州表白也说明全球化时代城市互动之频繁,以及大陆城市的快速发展。男主人公(吴彦祖饰)以子欣的影子为灵感在苏州设计了一栋“摩天大楼”,并与子欣一同飞回苏州站到摩天大楼顶层等“日出”并在摩登大厦里求婚,这个场景足以感动无数都市青年男女,但其实此摩登奢华的求婚场景并非普通人所能享有,所依赖的乃是全球资本的市场运作。
在全球资本流动扩张的世界中,《单身男女》关于苏州新城市形象的夸张展示,让人欣喜的同时亦令人感到困惑,电影中金鸡湖边鳞次栉比的摩天高楼不仅让人要问这是苏州吗?还是另外一座“全球城市”?今天的全球化塑造了同质化的城市面孔,苏州之类传统城市的独特性正在不断消失。或许在将来,任何城市都无法提供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诗学”,人们只能在影像世界中“怀旧”,甚至连影像媒介也难以记载逝去的历史,到那时,对居民来说,在任何城市中都将找不到身份的“归属感”。
〔责任编辑:平啸〕
City Poetics of Reminiscence—on the Image Construction of Suzhou Profile
Zeng YiguoWang Li
In the present craze for city culture,people are inclined to fix eyes on big cities like Shanghai and Beijing whereas they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Suzhou,a well-known historic city which used to be the most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nd culturally prosperous in China.What changes has Suzhou undergone since it stepped into a modern society?How do mass media,like films and TV plays,depict and present it?Why is strong flavor of reminiscence often attached to the visual reproduction of Suzhou profile by media of different periods and on different subject matters?All these issues are noteworthy.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review several films and TV plays to explore the ways they construct a set of“reminiscent poetics”in a social context where tradition is interwoven with modernity,analyzing what the“reminiscent poetics”contains and how it changes as time changes.
city culture;reminiscent poetics;Suzhou profile;local identity;globalization
曾一果,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系教授 215123
王莉,苏州大学2010级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215123
本文系2011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城市形象的媒体塑造与传播研究”(11TQC008)和2011年江苏省教育厅项目“当代中国城市形象的媒介建构研究”(2011SJB86000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