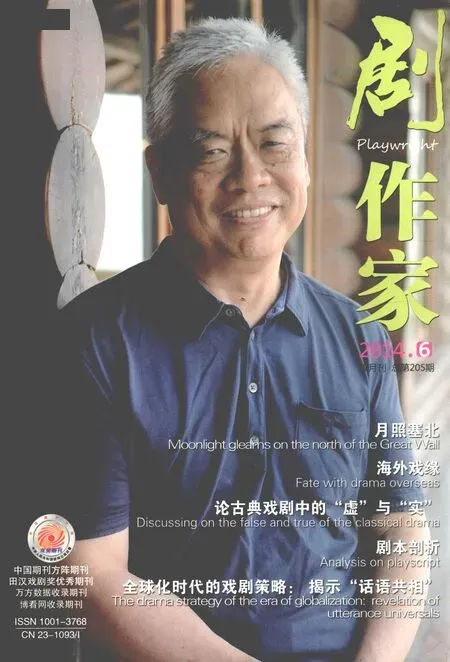浅谈张伯驹先生的戏曲研究
康 凯
浅谈张伯驹先生的戏曲研究
康 凯
张伯驹先生在中国戏曲界享名甚久,但是他的戏曲研究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一件极其可惜的事情。因为戏曲不能仅靠文字的东西流传,很多口耳相传的东西更为重要。随着张伯驹先生的去世,他所有的戏曲实践、理论方面的珍贵遗产也就随之丧失。没有能够在他生前及时抢救这些遗产,应该说是非常遗憾的。传闻张伯驹先生留有数十出余派戏的说戏录音,现在常有流传的仅是《法场换子》《盗宗卷》等几出而已。十分希望这些录音的保有者永久珍藏,也十分期待他们能够早日公之于世,使这些录音成为一笔公共的遗产,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然而我们在惋惜之余,应该开始重视张伯驹先生的戏曲研究,反思其真正价值,为当前的戏曲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因此,张伯驹先生留下的著作,就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了。其实,在建国之后,张伯驹先生的著作一直很受关注。这些著作中,和戏曲相关的主要是《乱弹音韵辑要》(建国后改订为《京剧音韵》)和《红氍纪梦诗注》。另外,《续洪宪纪事诗补注》和《春游琐谈》里也有一些,只是前者和《红氍纪梦诗注》重复了不少。由于较为专业,《乱弹音韵辑要》少受关注一些。他于1974年写成的《红氍纪梦诗注》,在1978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十年之后,《红氍纪梦诗注》在大陆宝文堂书店出版,立刻受到老派读者的喜爱。又过了十年,其书已经很难觅得,辽宁教育出版社在1998年编辑《春游纪梦》便将它全部收入,同时还收有《京剧音韵》的总论部分。同年,北京出版社再版《春游社琐谈素月楼联语》。张伯驹的戏曲研究逐渐为人全面了解。又是十五年过去了,这几本书都已难得,似乎读者对张伯驹的兴趣不减,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去年和今年连续出版《张伯驹集》的精装、平装两种版本,将他的著作尽量收齐。
随着张伯驹先生著作的不断再版,以及一系列回忆研究著作的出版,[1]方便了我们对他戏曲研究的认识和反思。这里只是对张伯驹先生的戏曲研究做初步的探索,简单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论述:一、张伯驹先生的学戏背景;二、张伯驹先生的戏曲理论;三、张伯驹先生的戏曲批评;四、张伯驹先生戏曲研究的价值。
一、张伯驹先生的学戏背景
大家一般都会认可吴小如先生的说法:“在北方的票友中,学余叔岩学得最直接,最标准,会得最多,路子也最正的,应推张伯驹先生。他以贵公子的身份同叔岩相交十年,通过丰厚的束脩,虔敬的礼数和深挚的友情,才从叔岩学到了一些‘掏心窝子’的本领。”[2]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有了误会。比如,后来去了台湾的著名剧评家丁秉鐩,就说:“他在认识余叔岩以前,简直不知皮黄为何物。与余叔岩结交以后,才开始对戏有兴趣,而且从余学老生,专攻余派,拳拳服膺。……论他的腔调、韵味、气口、字眼,那是百分之百的余派,没有话说。”[3]所以,张伯驹先生学戏,是个“纯余派”。捧之者如此说,贬之者也如此说。可是不论捧之贬之,都有这个言外之意:张伯驹不知道也就不懂别的流派,只懂余派。
这样一来,就会使得大家认为,张伯驹是在偶然与余叔岩相交的机遇之下,开始学戏的。这是他学戏的唯一背景。这对我们理解张伯驹先生的戏曲研究是很不利的。因为,我们就会像丁秉鐩一样,认为:“张伯驹自己工余派,对天下唱老生的人,也以宗谭学余的标准来衡量。遇见有不唱谭余,或是唱出花腔的人,不论内行票友,生张熟魏;不论是私人调嗓,或公开演唱,他必然怒目相视,恶言责骂,当面开销,不留余地。”[4]加之张伯驹先生的个性,其趣闻尤其多。如孙养农讲过的两个故事:
我带他去看上海某名角的《四郎探母》,他一听之下,马上离座就往外走,口中还喃喃有词,我急忙跟上,问他什么事,他不脱乡音地说:“前后门上锁,放火烧。”我被他说得一愣,就问他:“干什么呀?”“连唱戏的带听戏的,一齐给我烧”,他气鼓鼓地说。我听了不禁哑然失笑。又有一次,听谭富英的《群英会》,那个去孔明的里子老生,在台上大耍花腔,张就跑到台口,一面用手指着一面就骂:“你不是东西!”骂完回头就走,台上台下的人都为之愕然。[5]
口耳相传一久,不免越传越走样。所以,在不少人眼里,张伯驹其实谈不到什么研究,只是意气之争。充其量,他懂些个余派艺术而已。
这些看法,实际上都是忽视了张伯驹先生的学戏背景。他对于京剧的兴趣,是从幼年培养起来的,并不是因为结识了余叔岩。他五岁被过继给伯父张镇芳(生父叫张锦芳),七岁跟随张镇芳来到天津,从此开始了他看戏的生涯。天津作为京剧演出的一个重要码头,名角演出极多。根据《红氍纪梦诗注》的记述,他看过的老生名角就有谭派创始人谭鑫培、孙派创始人孙菊仙、刘派创始人刘鸿声、许(荫棠)派传人白文奎,还有“小小余三胜”时代的余叔岩。另外,武生杨小楼、李吉瑞,武丑张黑,武旦九阵风,刚出科的青衣尚小云等,也是他看过的。甚至其它地方戏他也看。
不过那时候他的欣赏水准还不够,所以两次看谭鑫培,都不知欣赏。“余十一岁时,……偶过文明茶园,见门口黄纸大书‘谭’字,时昼场已将终,乃买票入园,正值谭鑫培演《南阳关》,朱粲方上场,余甚欣赏其脸谱扮相,而竟不知谁是谭鑫培也。”[6]“先君寿日……谭扮戏时,余立其旁,谭著破皇靠,棉裤彩裤罩其外,以胭脂膏于左右颊涂抹两三下,不数分钟即扮竣登场,座客为之一振,惜余此时尚不知戏也。”[7]也就不能分辨演员的高下,他说:“当时谭、刘、孙齐名,但余在童时尚不懂戏,孰为高下,则不知也。”[8]
尽管如此,他七岁时却学会了孙菊仙的唱法。“余七岁时,曾在下天仙观其演《硃砂痣》,当时即能学唱‘借灯光’一段,至今其唱法尚能记忆。”[9]相信幼时的张伯驹,对于京剧肯定是很熟悉的。甚至还会唱几句山西梆子。“元元红山西梆子老生唱法,人谓其韵味醇厚,如杏花村之酒。有人谓其《辕门斩子》一剧,尤胜于谭鑫培。余曾观其演《辕门斩子》,其神情作风,必极精彩。惜在八九岁时,不能领会。惟尚记对八贤王一段唱辞。……童时余还能学唱。”[10]
幼年的熏陶使得张伯驹先生逐渐对于中国戏曲艺术有了深入的认识,也形成了极高的欣赏品位。我们会在下一部分中详细讨论张伯驹的戏曲理论,这里,只是简要指出,张伯驹选择余派,不是因为偶然结交余叔岩的机会,而是基于多年的鉴赏实践、高度的理论概括。说他只懂余派,显然是“想当然耳”的说法。再说,以他当时对戏曲的痴迷和经济能力,怎么会不去看看别人的演出呢?而且,张伯驹先生的确学过余派之外的戏。如,跟钱金福“学《五雷阵》《九龙山》两出,一饰孙膑老生戏,一饰杨再兴小生戏”。[11]当然还不止此。甚至,他还经常去看别的地方剧。在《春游纪梦》里,就有一篇《看河南家乡戏》,详细介绍了看戏的经过和感想。[12]因此,说张伯驹不懂余派之外的戏,纯属误会。
只有正确认识了张伯驹先生的学戏背景,我们才可能理解他为什么最终选择了余派,才可能了解他的戏曲理论。
二、张伯驹先生的戏曲理论
张伯驹先生的戏曲理论,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从宏观来看,他在多年从事戏曲观摩和实践演出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戏曲自身的特性以及和其它艺术的共性。从微观来看,他的主要贡献,是和余叔岩完成了第一本用来指导京剧演唱的韵书——《近代剧韵》,并且不断修订,试图构建一个科学严密的京剧音韵体系。而这一切,决非他一时兴起,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负有极强的使命感。
我们看到,张伯驹先生尽力奔走,约余叔岩和梅兰芳合作,于1931年成立北平国剧学会。学会不仅培训学员,而且进行研究,出版了《戏剧丛刊》《国剧画报》刊物。这两份刊物水准极高,直到今天还在重印。张伯驹的一些戏曲研究论文,就发表在这些刊物上。
他如此积极于此,正是他有意识构建戏曲理论的一个外化的表现。他希望能够和真正的同行们,探索出中国戏曲的真正意义。在《戏剧之革命》一文中,他指出中国戏剧的革命应该以认识自身的好处为前提。他说:“现在说到戏剧的本身,要负革命真意义的责任,要先革自己的命,要表扬戏剧的原来的好处。……现在我们已经瞭解戏剧对于革命的能力,还要与实演上用工。如《打渔杀家》一戏,其意义甚好,如梅、余二人来唱,就有许多人看,假如换两个劣角来演,就没有人看。……所以要达到戏剧的目的,就要先将自己的艺术学好了。”[13]
张伯驹先生一直不懈地寻找着戏曲艺术的真谛,因为,只有找准了这一点,才能真正学好自己的艺术。多年的戏曲实践和思考,他的戏曲理论已经颇具深度了。
在《佛学与京剧》一文中,张伯驹先生通过和佛学的对比,概括出戏剧自身的特色。他说:“依予研究结果,佛学与戏剧,同是彻底解剖人生,以为积极维持人生永远安宁之工作。佛学以真我置于旁观地位,而以假我为一切化身,以解剖人生。戏剧则忘其假我,以真我为一切化身,以解剖人生。一为写意,一为写实,一为由原质而生方法,一为由方法而反求原质。一为由高深而趋浅近,一为由浅近而入高深。取法不同,归宿则一也。”[14]这个讲法看似一个偶然的比较,实际却出自对戏剧本质的思考。戏剧自身的特色,很容易和历史等经验事件与学科区分出来,所以洛维特认为亚里士多德“没有一部作品是探讨历史的;与诗相比,他对历史的评价很低。因为历史只探讨一次性的事情和偶然的事情,而哲学和诗却探讨永远如此的存在者(Immer-so-Seienden)”。[15]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讨论的核心正是戏剧。容易和历史区分,又该如何与哲学区分呢?张伯驹先生这里的讲法,无疑在竭力解决这个显然更为困难的问题。佛学,是他偶然选择的一种哲学,但他的论述完全是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界定戏剧自身的特色。他认为,戏剧和哲学都是彻底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但是,哲学从抽象到具体,戏剧从具体到抽象。这和西方的主流戏剧思想并无大的差异。可见,张伯驹先生对于戏剧确有合理的认识。
如果说,张伯驹先生在戏剧的共性上,虽有正确的见解,但并无独创。那么,他在中国戏曲和其它艺术的共性上,就显示出他的原创性了。他认识到,中国的戏曲艺术和其它传统艺术具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它们具有相同的衡量标准。标准中最高的,他以“神韵”来概括。他说:“王渔洋诗主神韵,有论诗品诗,如其《过露筋祠》诗……即富于神韵者。词以到禅境为最佳,如南唐后主词‘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北宋晏小山词‘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皆臻禅境,亦即神韵。余自七岁观剧,而认为堪当神韵二字者只有五人,乃昆乱钱金福、杨小楼、余叔岩、程继仙,曲艺刘宝全也。汪桂芬余未赶上,谭鑫培、孙菊仙余曾赶上,但在童时,尚不懂戏也。”[16]所谓“神韵”,从美学上讲,是指原本在经验之中已经为我们所熟知的物在成为美的载体时,将会以一种全新的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再将之放在涵义赋予之中,从而就使得承载它的物失去了在认识能力之下确定的具体含义,这样的失去反而使之似乎具有了许多无法言说的丰衍意义,这时神韵就从中产生了。我们看到,神韵不受任何约束,比起艺术受到规律的制约,成就了心灵绝对的自由,较之艺术具有更高的美感层次。我们知道,张伯驹先生是著名的词人和词学家,这个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讲得非常明确的道理,他一定很熟悉。因此,他提出这个中国戏曲在中国艺术上的美感共性,绝对是他自己的心得,余叔岩未必能够概括出来。可见,张伯驹选择余派,正是因为在他的理论视域中,余叔岩的艺术具有典范性。
我们再来看他较为微观的戏曲理论,即构建一个科学严密的京剧音韵体系。张伯驹先生在1931年2月和余叔岩先生联合署名出版《近代剧韵》,由北京京华印书局印行,当时即注明“非卖品”。可见,那是他们还在探索阶段,没有信心将这本书作为确定可靠的成果。果然,印行之后,受到很多批评。最为激烈的是齐如山。他在《谈四角》一文中,认为余叔岩“所谈的理论,那大多数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话,他都是听得文人们说的”。其中的指责,就是张伯驹和余叔岩的这本《近代剧韵》,他认为:“皮黄最初是一种小调,只有十三道辙,与昆曲中之南曲北曲、洪武正韵、中原音韵等等,毫不相干。你要是拿昆曲的规矩来谈皮黄,那是一点也不会合用的。”[17]不过,当时并不是只有齐如山这样一种极端的观点,罗常培和王荣山都有更为中肯的意见。[18]可是,余叔岩却很怕有不妥之处,便收回其书,不再公开出版。[19]但是,张伯驹先生却非常自信,毅然决定在1932年到1935年,将其书改名为《乱弹音韵辑要》,以他自己的署名在北平国剧学会的《戏剧丛刊》第二、三、四期上连载,内容几无变化。[20]同时,他还写了《宋词韵与京剧韵》一文,力图论证京剧用韵和词曲的相通。到六十年代,张伯驹先生又将之改订为《京剧音韵》,再次出版。[21]可见,他不仅对自己的观点始终坚持,而且不断完善。不过,直到今天,我们对张伯驹连出了三版的《近代剧韵》《乱弹音韵辑要》《京剧音韵》,仍然缺乏详实的研究。可以说,构建一个科学严密的京剧音韵体系,我们仍然需要沿着张伯驹先生的道路继续探索。
三、张伯驹先生的戏曲批评
张伯驹先生的戏曲评论,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前面引述过的丁秉鐩的议论,可以作为代表性的意见。当然,我们应该承认,这并不是没有张伯驹自身的原因。出身贵公子,不免带上些习气。习惯了受人逢迎的张伯驹,往往天真地把别人的客套当做了现实,有些话看来实在太像自我标榜了。他说:“夏日院内置藤椅竹床,客坐于外,余与叔岩在室内吊嗓,彼唱《桑园寄子》,余则唱《马鞍山》;彼唱《马鞍山》,余则唱《桑园寄子》。外面客不能分为谁唱,必至室内问询,始知也。”[22]“与尚小云演《打渔杀家》,小云大为卖力,内行谓之曰‘啃’,是日对啃,演来极为精彩,台下甚为满意。后有人云‘尚小云未啃倒张某人’,一时传为话柄。”[23]那么,张伯驹的水准是否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呢?我们先来看看别人的评论。对他不很客气的丁秉鐩说:“他限于天赋,没有嗓音。在公开演唱的时候,不要说十排以后听不见,连五排以内都听不真。所以一般内行,都谑称之为‘张电影儿’;那时候的电影还是无声的,也就是说:听张伯驹唱戏,和看电影一样。至于台步、身段,也不是那么回事。但是张伯驹却自视甚高,很喜欢彩排,还以余派真传名票自居。于是内外两行,常拿张伯驹唱戏当作笑话讲。”[24]对他很尊重的吴小如先生,也这样说:“可惜伯老天赋条件不太理想,又是半路出家,故其表达能力与其所知所能的差距太大。”[25]显然,张伯驹自身的演唱水平,是达不到专业演员的水准的。张伯驹的说戏录音还有流传,带有较重的河南口音,说他的唱和余叔岩不能分辨,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毕竟是票友,缺乏专业演员高强度的幼工、演出锻炼,要和名列四大名旦的尚小云争长,恐怕只能说是自不量力。
一旦别人把他这样的习气看作自我标榜,就会认为他的戏曲艺术评论也出于标榜。比如,不少人会认为,张伯驹只捧和余叔岩关系好的演员,反之,就加以贬损。其实,这也是个误解。基本上说,张伯驹的评论还是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理论的。他既以“神韵”作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最高标准,对于其他演员的衡量,也都是根据这个标准的。“神韵”要求摆落人工痕迹和感官愉悦,就和雕凿、甜熟格格不入。所以,张伯驹最倾服余叔岩,却很不喜欢言菊朋和马连良。他说言菊朋:“菊朋后下海演老生,宗谭鑫培,自命为谭派传人。梨园内行嘲其为‘言五子’……按言亦知音韵,如阴平高念,阳平低念,上声滑念,去声远念,入声短念之类;但不知变化运用,每韵尚有三级之妙;又以嗓左,遂至学谭反而映山隔岭,奇腔怪调,无一是处。”[26]按说,言菊朋和余叔岩同宗谭鑫培,张伯驹不该对言菊朋评论如此苛刻,所以有人以为是言菊朋和余叔岩存在竞争关系,张伯驹刻意贬低言。但实际上,言菊朋学老谭,几于亦步亦趋,技巧的运用不够空灵,加上为嗓音所限,晚年唱腔更是走向险怪。这就不免于雕凿,和张伯驹的“神韵”标准相去较远。他说马连良:“马连良初师贾洪林,后亦不似,《借东风》为其拿手戏。但武侯知天文学,计时应有台风,因用火攻破曹军,非能借东风也。连良演此戏,竟使武侯如一妖道,乃腹无文学之故。”[27]这都近于吹毛求疵了,但仍然是因为马连良“腹无文学”的原因。即马连良的唱腔过于甜熟,近乎“元轻白俗”,显得缺少深湛的修养,和“神韵”相悖。可以说,张伯驹的评论还是从他自己的艺术理论出发的,和党同伐异没有关系。
对于这一点,可以举出一个反例。其实,余叔岩还有一个更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已经被人遗忘的王凤卿。余叔岩二次出山搭梅兰芳的“喜群社”时,头牌老生就是王凤卿。余叔岩一直被王凤卿压制,演出的戏码也要经常回避王凤卿的。由于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演出时,得到王凤卿的极力帮助,加之王凤卿确有实学,余叔岩无法动摇他的地位,最终自行组班。如果张伯驹真是党同伐异,对王凤卿也不应该有较高的评价,可是恰恰相反。他说:“王凤卿唱法用脑后音,为汪派传人。《过昭关》《浣纱记》《鱼肠剑》《取成都》《战长沙》皆其拿手戏。饰《战长沙》关羽,以胭脂揉脸,不打油红脸,乃取法程大老板。凤卿好书法,常临刘石庵、翁同龢书。余曾赠以刘石庵书册,彼甚宝之。”[28]没有任何贬损。究其原因,还是王凤卿的汪派古朴唱法和“神韵”是不大冲突的。
细读《张伯驹集》,不难看到:张伯驹对于中国戏曲艺术具有广博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以此做出了很多独到的评论。这些评论,也许不够全面,那是因为他过分局限于“神韵”这唯一的标准,而对其它美感有所忽视。这才会有对言菊朋和马连良的过分贬损。但从深刻性来看,确实够得上“第一义谛”。所以,《红氍纪梦诗注》历述京昆名角,简直可以作为一部民国京剧小史来读。
四、张伯驹先生戏曲研究的价值
不管怎么说,在今天,张伯驹的戏曲造诣似乎被重新发现了,一时声名甚重。尤其在票友界,假如你没有听说过张伯驹,就算不得懂京剧余派艺术,于是也就算不得够格的票友。但是,我却觉得,戏曲界的内行们似乎更应该重视张伯驹戏曲研究的价值。原因很简单,随着传统戏的恢复,中国戏曲的传统理论重新得到重视。现在的年轻演员,已经开始自觉恢复即将绝迹的老戏,自觉注意讲究京剧自身的音韵。张伯驹先生的戏曲研究无疑应该具有更大的意义。
当前大家对张伯驹戏曲研究的关注点,仍然集中在戏曲自身的鉴赏和戏曲史料的勾稽上。即使连出了三版的《近代剧韵》《乱弹音韵辑要》《京剧音韵》,也缺乏真正的研究。其实,很久以前的专家们,就注意到张伯驹的戏曲演出实践和理论研究。欧阳中石先生在给《红氍纪梦诗注》写的序文里,特别关注了容易被读者忽视的第三部分和补遗,因为这部分内容是张伯驹戏曲演出实践的精华所在。这些演出,在今天由于种种原因将要消失于舞台之上,不少有识的青年演员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抢救。在这种抢救过程中,张伯驹的戏曲研究首先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比如,京剧《伍子胥》是杨宝森先生的杰作,他唱得太好了,以致舞台上只有了杨派的唱法,使得其他流派的演法濒于消失。由于杨宝森是谭余派的传人,大家很容易认为,他的《伍子胥》应该是谭派的格局。其实,杨宝森这出戏是跟自己的姑夫王瑶卿学的,而王瑶卿的弟弟王凤卿是著名的汪派传人,王瑶卿教给杨宝森的是汪派的唱法。我们只要对比一下杨宝森和汪派的唱法,就会发现唱腔格局基本相同。但是,杨宝森把汪派的腔用谭余派的原则表现出来,就成了杨派。那么,谭余派的《伍子胥》究竟是什么样呢?
在《红氍纪梦诗注》里,张伯驹记载了《伍子胥》中《战樊城》《长亭》《鱼肠剑》的演出概况,就使得我们今天恢复谭余派的《伍子胥》有了佐证。近来上海的傅希如和天津的凌珂,都开始恢复谭余派的《鱼肠剑》,傅希如甚至演出了总名《鼎盛春秋》的三个折子:《战樊城》《文昭关》《鱼肠剑》。他们根据的是李适可、刘曾复先生传下来一种唱法,对比夏山楼主、言菊朋、谭富英等谭派诸大家的唱法,可以看出这个唱法和谭派很有渊源。但是,和杨宝森的唱法就相差太远了。就连唱词也不一样。比如,谭派的【反西皮散板】,词句基本是这样的:“子胥阀阅门楣第,我好比凤落翎毛怎能飞。父母的冤仇沉海底,空负我堂堂七尺躯。我本是英雄不得志,落魄天涯有谁知。伍子胥呀,伍明辅啊,父母的冤仇不能报,爹娘啊!”[29]而杨宝森的词是:“子胥阀阅门楣第,落魄天涯有谁知。可叹我父母的冤仇沉海底,俺好似凤脱翎毛怎能飞。伍子胥呀,伍明辅啊,父母的冤不能报,爹娘啊!”[30]和汪派的唱词一样。不过,谭派的一段【西皮原板】唱词是:“姜子牙无事隐钓溪,运败时衰鬼神欺。周文王梦飞熊夜扑帐里,渭水河访贤臣保社稷。英雄落魄异邦地,只落得吹箫讨饭吃。”[31]和李适可、刘曾复先生的唱词差距很大,他们的唱词是:“【西皮原板】姜太公不仕隐磻溪,运败时衰鬼神欺。周姬昌治西岐在灵台殿里,渭水河访贤保社稷。东迁洛邑【二六】王纲坠,各国诸侯把心离。背盟毁约失信义,图霸争强各自为。吴子寿梦立王位,力压诸侯服四夷。某单人独骑弃楚地,要见姬光恨无机。困苦的英雄似蝼蚁,眼见得含冤化灰泥。落魄天涯谁周济,只落得吹箫暂充饥。”[32]但是,这却和张伯驹记录的余叔岩唱词基本一致。词句是:“【西皮原板】姜太公无事垂钓溪,运败时衰鬼神欺。周姬昌梦飞熊宝帐里,渭水河访贤臣扶保社稷。东迁洛邑【二六】王纲坠,各国的诸侯把心离。吴子寿梦行仁义,力压过诸侯服四夷。某单人匹马弃楚地,要见那姬光恨无期。父母的冤仇沉海底,眼见得含冤化灰泥。落魄在天涯谁周济?只落得吹箫暂充饥。”并且加注:“‘王纲坠’句转板在二六、快板之间,‘眼见得含冤化灰泥’句才成为快板,此唱法甚精奇。” 这也和刘曾复先生的说戏唱法一致。虽然余叔岩并没有在舞台上演过《鱼肠剑》,但可以认为这个唱法是近于余派的。谭余派的《鱼肠剑》被恢复到现在的舞台上,张伯驹的记述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张伯驹记述的濒于失传的余派戏还有很多,如《太平桥》《连营寨》《失印救火》《宫门带》《摘缨会》《青石山》《镇潭州》《宁武关》等等,都值得在今后予以抢救恢复。他详细记录的身段、唱法,是余派艺术的宝贵资料,戏曲界的内行们应该让它们发挥更大的意义。随着更多的失传剧目重现舞台,我们可以这样说,张伯驹先生的戏曲研究除了文献价值,还将具有超过预期的现实意义。
注释:
[1]比如,林下风编《张伯驹与京剧》,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项城市政协编《张伯驹先生追思集》,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版;张伯驹潘素文献整理编辑委员会编《回忆张伯驹》,中华书局2013年版;故宫博物院编《捐献大家张伯驹》,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版;任凤霞著《一代名士张伯驹》,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寓真著《张伯驹身世钩沉》,三晋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
[2]吴小如《京剧老生流派综说》,见《吴小如戏曲文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8页。
[3]丁秉鐩《菊坛旧闻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4]同上,第33页。
[5]孙养农《谈余叔岩》,2003年纪念余叔岩逝世六十周年内部印本,第50、51页。
[6]张伯驹《红氍纪梦诗注》一三,见《张伯驹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2页。
[7]张伯驹《红氍纪梦诗注》一九,见《张伯驹集》,第14页。
[8]张伯驹《红氍纪梦诗注》二七,见《张伯驹集》,第16、17页。
[9]张伯驹《红氍纪梦诗注》二,见《张伯驹集》,第8页。
[10]张伯驹《红氍纪梦诗注》一〇,见《张伯驹集》,第10、11页。
[11]张伯驹《春游琐谈·赠钱金福金缕曲词》,见《张伯驹集》,第537页。
[12]参看张伯驹《春游琐谈·看河南家乡戏》,见《张伯驹集》,第553、554页。
[13]张伯驹《春游琐谈·戏剧之革命》,见《张伯驹集》,第557、558页。
[14]张伯驹《春游琐谈·佛学与京剧》,见《张伯驹集》,第555、556页。
[15]洛维特《世界历史和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中译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页。
[16]张伯驹《红氍纪梦诗注》一〇七,见《张伯驹集》,第42、43页。
[17]齐如山《谈四角·评余叔岩》,见《齐如山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六卷第187、188页。
[18]参看刘曾复《京剧新序》,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200页。
[19]这样,此书的传本极少。现在常见的是收录在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的《余叔岩与余派艺术》中的影印本,著作者的署名张伯驹在余叔岩之前。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藏有一册《近代剧韵》的蓝印本,没有著作者的署名,但多出张伯驹的序言。这篇序言后来在《戏剧丛刊》发表张伯驹单独署名的《乱弹音韵辑要》时刊出。这个蓝印本是用软体字印的,和京华印书局印本的匠体字完全不同,不知孰先孰后。后来香港李炳莘将此本影印流传。
[20]天津市古籍书店1993年和学苑出版社2013年都影印出版了全部《戏剧丛刊》,很容易看到。《张伯驹集》也全文收录了此书。
[21]遗憾的是,这个名叫《京剧音韵》的修订本,大概因为和《乱弹音韵辑要》有过多重复,未被收入《张伯驹集》。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编辑出版的《春游纪梦》中则收有《京剧音韵》的总论部分。
[22]张伯驹《红氍纪梦诗注》一四二,见《张伯驹集》,第57页。
[23]张伯驹《红氍纪梦诗注》一六四,见《张伯驹集》,第66页。
[24]丁秉鐩《菊坛旧闻录》,第33、34页。
[25]吴小如《京剧老生流派综说》,见《吴小如戏曲文录》,第358页。
[26]张伯驹《红氍纪梦诗注》七八,见《张伯驹集》,第33页。
[27]张伯驹《红氍纪梦诗注》八一,见《张伯驹集》,第34页。
[28]张伯驹《红氍纪梦诗注》五九,见《张伯驹集》,第34页。
[29]唱词根据夏山楼主1961年中国唱片。
[30]唱词根据杨宝森1950年香港实况录音。
[31]唱词根据言菊朋1929年高亭唱片。
[32]唱词根据刘曾复先生说戏录音。
责任编辑 原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