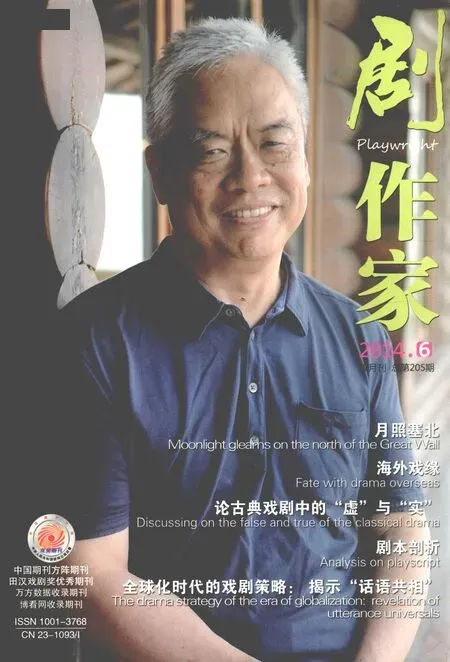论《鼎峙春秋》中的因果报应思想
李小红
论《鼎峙春秋》中的因果报应思想
李小红
摘 要:《鼎峙春秋》中曹操生前作恶,死后堕入地狱,备受折磨;关羽生前是忠义的典范,死后荣登天府,成仙成佛;体现了浓重的因果报应思想。这是传统观念使然,也是前代戏曲、小说影响的结果,更是统治阶级的需要。
关键词:《鼎峙春秋》 因果报应 曹操 关羽
清代宫廷历史大戏《鼎峙春秋》,以蜀汉为中心,演魏、蜀、吴三国鼎峙故事,自桃园三结义始,诸葛亮南征凯旋止,基本上是戏曲本的《三国志演义》,其中具有浓重的因果报应思想。
因果报应思想是《鼎峙春秋》的结构基础。一部《鼎峙春秋》基本就是关羽、诸葛亮传记,曹操成了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关羽去世后,全文分为两条线索:一是诸葛亮南征孟获之事,一是关羽等忠臣的上天堂受旌扬和曹操等奸臣的下地狱受酷刑之事。全文以第八本第二十一出《岳帝奏申彰瘅权》、第二十二出《阎君牌摄奸馋魄》、第二十三出《补行阳世三章法》、第二十四出《试取阴司九股叉》,第九本第三出《初入冥途须挂号》、第五出《二殿会三忠勘罪》、第二十四出《上四殿剑树刀山》,第十本第一出《仙眷重圆兜率天》、第二出《阴曹复演渔阳操》、第三出《授黄封修文天上》、第七出《七殿严刑诛国贼》、第十四出《遭谴堕阴冰山》、第二十一出《分善恶十殿轮回》、第二十二出《大褒崇九天翔步》、第二十三出《群魔敛迹清华甸》、第二十四出《三教同声颂太平》共十五出的戏文来写善恶的两种不同结果,非常具体地演述了善因善果,恶因恶果,报应不爽的观念。
关羽、刘备死后,掌握百灵修短荣枯的东岳大帝本着“善其善,恶其恶,刑赏自有殊施;是则是,非则非,斟酌不差毫末”[1]的原则,发现阳间曹操“恶贯满盈,当受冥诛,以伸天宪。”[2]于是奏知上帝捉拿曹操。第二十二出还直接标明:“阴阳一纸糊,善恶干官纪,书来森衮钺,笔下析几微,是是非非,并不留余地。”[3]五殿阎君说:“不是俺黑阴司装威弄势,也只因阳世上乱作胡为,人伦灭裂纲常坠。曰明曰旦,不怕天窥,为鬼为蜮,敢把人欺,全不思天尊地卑,也不思戡乱扶危。……贼曹瞒窥神器,炎汉江山他将唾手移,却逃不了俺鬼董孤直笔标题。”[4]曹操病入膏肓,鬼魂将曹操脑髓劈出,伏完、董承、马腾等人附体曹操身上,曹操自己说“大家看者,曹操欺世欺君,劈他脑袋,警戒世人,不可怀奸罔上”。[5]宫女太监们也感叹“这等看起来,果然是天理昭彰,报应不爽”。[6]
《鼎峙春秋》不但以因果报应思想作为整体结构的基础,而且依据因果报应律重新安排了人物的命运,借人物之口反复表达了善恶分明、报应昭彰的观念。如初入冥途时,忠臣们一上场就宣称:
【商调套曲·逍遥乐】荣枯天定,理欲关头,先须认清,岂无端乐死轻生,也
皆因义重身轻,但把伦常一掌擎,荣华富贵总浮萍,何着急,非设成心,不为邀名。[7]
在阳间惨死的董承、马腾、吉平到了阴间备受尊崇,他们坚信:“自古阴阳一纸糊,善恶分明彰瘅殊,不争差墨字与朱书。”[8]上帝旌扬三人的忠义,“敕简为神”,命其一同会审曹操,正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9]董卓的罪过是“借勤王之目,为篡位之谋。少帝饮鸩而崩,何后撺楼亦绞,又劫迁天子,焚掠皇都,三公被株连,百姓并遭荼毒”。[10]二殿阎君命将其“用铜锤击打一百”。曹操更是罪大恶极“蔑君叛国,趁势作威,以白练绞杀董妃,用乱棒打死伏后。目无君上,伏三尺剑于宫闱;斩绝宗支,鸩二皇子于襁褓。神人共愤,天地不容”。[11]曹操被大秤钩起,用铁鞭重打。
第九本第二十四出《上四殿剑树刀山》重又对董卓、贾诩、李傕、郭汜审问,发落至刀山受报。曹操一上来就不由分说被着实地痛打一通,四殿阎君反复质问:“为甚么君王幽许都,为甚么妃后遭屠戮,为甚么轻轻揽帝权,为甚么暗暗移天步。”吕伯奢也来告曹操无义,无端杀他一家。四殿阎君说:“语云:‘奸必残,残必忍’。若曹操者,可谓奸残而忍矣,凶恶之徒,当受重重地狱。吕伯奢死于非命,应交十殿转生。”曹操也到刀山受刑。华歆、郗虑是曹操鹰犬,弑后弑妃,被“割舌屠肠,以彰恶报”。郭嘉、程昱、许褚、张辽等都上刀山剑树受刑。华歆、郗虑受刑之后,四殿阎君唱:“【南北合套•沽美酒带太平令】既割舌还剖腹,既割舌还剖腹,刀过处血模糊,似一树桃花洒红雨,淅零零三花吐,舌根儿归何处,谁教你花言巧语,谁叫你怀奸事主。你都是城狐社鼠,一个个装龙做虎,俺呵,恼杀你这奸徒,贼奴……”[12]血淋淋的场面,惨不忍睹,都只为他们前生作孽,因而不得好报。
五殿阎君天子殿下的判官火珠道人上场时特意表白:“咱这里算子忒明白,善恶到头来撒不得赖,就如那少债的会躲也躲不得几时,呀,却从来没有不还的债。”[13]祢衡上天之前,他特意请祢衡“把旧日骂座的情状两下里演述一番,留在阴司中做个千古的话靶,又见得善恶到头,就是少债的还债一般”。[14]《鼎峙春秋》鲜明指出:“便阳间漏网,阴报却分明。”[15]华歆、郗虑、贾诩等也终于觉悟到自己的过错:“鬼犯等只顾生前,哪知身后,到了此地,才晓得报应是有的。”[16]
十殿阎君认为报应取决于自己的善恶:
【南北合套·斗鹌鹑】善恶无门,惟人自取,恶锢阴山,善登天府。絜短论长,秤锱较黍,无贤愚,无今古,问何人,不来此处。(白)莫道幽冥事不真,冰霜雨露岂无因,从来彰瘅归吾辈,看取今朝善恶人。(白)我等乃十殿阎君是也。(头殿五殿白)钦奉上帝敕旨,今日将抱忠竭志、为国捐躯、大义昭然、堪为世法者超升天府。(众同白)其大逆不道、欺君篡国、屈害忠良者贬入轮回。大昭点陟之权,以示佞奸之报。[17]
依据因果报应规律,董卓、曹操等乱臣贼子全都沦为畜生:董卓变龟,曹操变鳖,李傕变鼠,郭汜变羊,李儒变狼,贾诩变狼,张济变猪,樊稠变熊,郭嘉变猿,程昱变狼,许褚变猿,张辽变蚯蚓,荀彧变豹,荀攸变虎,华歆变兔,郗虑变兔。众阎君再次表明了善恶的结果:
【南北合套·绵搭絮带拙鲁速】您休怨,罪也何辜;再休说,命也何如。俺这里但将阴惨补那阳舒,阳间法网已多疏,阴司法律岂容逋。胎卵殊途,一切如人子,况诸奸罪犯天诛,休因他名载丹书,要想俺半星儿模糊,一分儿舒徐,但轻轻施转辘轳,推动转舆,只教你类分群区,质异形殊,人身何处。只落得身体发肤,都做了鸟兽虫鱼,乱纷纷从此出。(轮下转出各种扁毛畜生虫豸,罪人戴各色兽畜形皮从中地井入轮转,出至中场,作哭泣科,众鬼赶下。头殿五殿白)众善共登天府,诸奸尽沦恶道,报应已照,我等各回殿宇便了。[18]丁原、卢植、王允、种辑、何进、华佗、杨奉等忠臣则被列为善人,十殿阎君十分敬服:“众善台束发从君,委身事主,虽则有志而未逮,却能杀身以成仁,名震一时,忠昭万古,真足维持世教,砥柱中流也,吾等敬服。”看到众善人一同升天去了,十殿阎君对善恶的结果不无感叹“为善之人必获善报,堪笑世人不醒悟也”。[19]忠臣义士荣登天府,乱臣贼子堕入地狱,善因善果,恶因恶果,报应不爽。
《鼎峙春秋》不仅以果报思想作为整体结构的基础,并重新安排人物命运,而且借各色人物之口反复强调报应昭彰的观念,浓重的因果报应思想体现了统治阶级对乱臣贼子的痛恨,极具教化意味。那么《鼎峙春秋》中为何有如此浓重的因果报应思想呢?
一、传统观念的渗透
因果报应是儒、释、道三家兼有的思想。
我国传统观念里先秦时期就有了“报”和“报应”的思想。《易•传》“文言”中就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话。《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了“结草”的故事,《后汉书•杨震传》有“衔环”的故事。善恶报应思想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具有扶世助化、劝善化俗的使命,它是沟通世间道德实践和精神解脱的中介。它是我国古代社会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普遍信奉的观念。善恶的标准是儒家的标准,善恶报应准则是根据儒家思想来规定的,元明清以后佛教和道教的社会伦理基本上都是以儒家为基础的,保证这一伦理原则能够得以遵守,则是靠道教和佛教。
因果报应,是佛教用以说明世界一切关系并支持其宗教体系的基本理论,是佛教人生观、伦理观的思想基础。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因果报应是最早从国外输入,并产生广泛而巨大影响的宗教人生理论。因果报应说认为,宇宙人生中的任何事物的生灭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是佛教的根本教义之一,是佛教灵魂学说的集中体现。因果报应与生死轮回把人们的道德行为与命运主宰权交给了自己,后世的善报、恶报取决于自己前世的为善还是作恶。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因果报应思想在我国广泛流传。东晋名僧慧远(334~416)结合我国的传统观念,写出了《三报论》《明报应论》等著作,阐述了人有三业(身业、口业、意业),业有三报(现报、生报、后报),生有三世(去世、今世、来世),前世为因,今世为果,今世为因,来世为果,一个生命死后灵魂会依照因果报应规律投胎成为另一个生命,灵魂不灭,轮回报应不息。每个人的善恶行为都会给自己命运带来相应的福祸,积德者永脱生死,作恶者在三世六道中轮回。他系统完整地阐发了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进一步扩大了这种思想的影响,他把主宰因果报应的力量归于个人行为的善恶,现实生活中一切都有“定数”,今世之“报”是前世作“业”的结果,“业”梵文意思是“造作”,是人的一切身心活动所形成的结果,被看作是生死流转的动力。六道包括天(欲界、色界、无色界)、人、畜生、阿修罗、饿鬼、地狱。六道生死流转,多修善业多得善趣,多造恶业则堕于畜生、饿鬼、地狱受尽折磨。实质上论述了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对统治者非常有利;下层老百姓现实生活苦难,找不到原因,只能归根于前世作业,把幸福寄托于来世。因而他的理论使佛教理论在传播过程中逐步中国化,为各阶层所接受,今天它已经成为我国人生观、伦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都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因果报应不仅是信仰问题,更是道德问题,它成为千百年来维护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支柱。
道教也有因果报应思想。钟离权、吕洞宾等人主张道教易学,和《周易》、汉易学相比具有显著特点,“道教因果报应思想深深印有儒家与佛教思想的痕迹。早期道教的因果报应思想是逐渐由承袭《周易》的因果报应论发展到独具特点的因果报应论的。东晋至隋唐五代时期的道教因果报应论深受佛教生死轮回和来生学说的影响。宋明时期的道教因果报应论基本上是在宋明理学的控制之下。这种因果报应论,一方面与内丹修炼相结合。另一方面是这个时期的因果报应论深深地印上了封建地主阶级意识的烙印,主张儒、释、道融合的思想也反映在这种因果报应论中。”[20]宋元时期出现了很多道教劝善书,明清时期达到全胜,广为流传,核心体系主要由《太上感应篇》《玉历钞传》《太微仙君功过格》《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构成。道教善书的基本思想集中体现在劝善惩恶、阴骘观念、因果报应三个方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整个善书理论体系的圭臬,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是其一以贯之宣扬的伦理精义。劝善书的宗旨是要通过神道设教的方式宣扬儒家忠孝节义的道德伦理规范,为巩固封建统治,更好地处理世俗社会人伦关系服务的,它是中国宗教与中国传统道德的完美结合。
正如徐保卫所说:“果报观念所涉及的宗教体系是一个极为庞杂混乱的系列,更准确地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造神运动。在这里既没有一个恒定不变的体系核心,不同体系之间也没有相应的归属区别。从与果报描写有关的偶像崇拜来看,它既涉及佛教的神祗,如释迦牟尼、观世音,也涉及道教的神祗,如太上老君、元始天尊,而且也与儒教的上帝神如玉皇大帝,城隍与四部八班,山川海岳等诸神灵有关。……明清之际,又有一些新的神祗陆续加入这个行列:岳王、关圣帝君、财神、福禄寿星君……这些神灵们或者是独受香火,或者是共享祭祀,忙忙碌碌地司理着人间的福祸荣辱。宗教的本质特征:鲜明的排他性,就在这一片嘈杂而融洽的气氛中消失不见了。”[21]
由此可见,儒、释、道三家都把因果报应思想作为自己理论体系的基本思想,因果报应思想是三教融合的一个契合点。因果报应的道德律和多世轮回的实现原则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
二、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的影响
因果报应是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共同具有的一个重要母题。“因为果报说与儒家文化有一定的内在精神联系,取得了与正统文化精神的认同和谐调,或者说其中体现和宣传了儒家思想并有利于儒教推行,故尔果报才在中国小说以及戏曲中广泛存在,畅通无阻。”[22]佛教对中国人产生最大心理冲击、引起最强烈心灵震撼的是因果报应学说。佛教带来了三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三界、六道的观念。人们思维的时间、空间扩大了,想象的世界也随之扩大了。前世、今世、来世的三世说延展了艺术世界的时间维度,人间、地狱、天堂和六道轮回说则延展了艺术想象的空间维度,多层次的空间可以让文人充分发挥想象,产生无限的创造力。
因果报应的观念,论及人的道德观、生命观、生死观、命运观、来世观,体现了人对现世的关切和终极关怀,并从理论上把因果律、自然律、道德律统一起来,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观察人生命运、价值、意义的新视觉,以及对待人生行为、活动的新方式,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人生和社会的基本准则。“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目的在于说明人生苦难之根源以及摆脱此种苦难之前途,因果报应的归宿是天国或地狱。肖彬夫认为这种因果报应的观念反映在古典戏曲上,则表现为五种形式:出世入佛式、得道成仙式、鬼魂复仇式、起死回生式、因果报应式。[23]
中国古代戏曲自诞生之日起,就承担了高台教化、劝善惩恶的功能,果报思想正是实现这种功能的手段。最早的南戏《王魁》《赵贞女》都被置于因果报应的大框架之中:王魁负桂英,终被鬼魂索命;蔡伯喈中举负心马踏赵贞女,终被暴雷劈死。《琵琶记》第一出副末开场“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24]开了戏曲宣教的先河,后世作品纷纷仿效。元杂剧、明清传奇无不具有浓重的因果报应思想。李渔的戏曲理论更是极力强调戏曲的两大功能:娱乐和劝惩。统治阶级也提倡劝善的戏曲,《大明律》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25]义夫节妇,孝子顺孙都是劝人为善的戏曲,所以不在禁演之列。
中国古代的小说一经产生就带上了浓重的因果报应色彩,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宋话本、明拟话本乃至明清长篇章回小说,都难脱其俗。《警世通言》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目的就在于用果报不爽、天道不移的观念教育少年子弟要检点自己的行为。《三国志平话》中司马貌断狱的情节,《三国演义》中曹氏家族、司马家族的权势流转,《金瓶梅》中西门庆一家的兴衰,《醒世姻缘传》的冤冤相报,《西游记》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红楼梦》绛珠仙草、神瑛侍者前世今生还泪之说,无不蕴含强烈的因果报应的思想。
劝善惩恶是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律,智慧、勇敢、公正、完美,都是善的表现,凶残、邪恶、奸诈、都是恶的表现,在小说、戏曲冲突中,善与恶两种道德伦理的对立和较量,常常表现为善对恶的永恒胜利,反映到戏曲、小说中则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局。可以说,因果报应的内结构模式是决定戏曲、小说大团圆结局模式的原因之一。
三、统治阶级的需要
历代统治阶级无不痛恨奸佞,推崇忠臣。满族皇室以蒙古为关羽,自称刘备,他们以自己为正统,视曹操为反叛。《鼎峙春秋》中曹操无恶不作,而逼帝迁都、弑后杀妃、残害皇子被列为首罪,统治阶级自然对曹操恨之入骨;关羽过五关斩六将、镇守荆州,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是忠贞的典范,臣子的楷模,统治阶级自然要大力旌阳。
《鼎峙春秋》由乾隆敕命周祥钰、邹金生等编撰。周祥钰和邹金生,都是御用文人,御用文人必然要为统治阶级服务。《鼎峙春秋》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愿,它体现了对忠孝节义纲常伦理的维护,对关羽等忠臣倍加推崇,对曹操等奸臣痛加挞伐。
戏曲以满足观众的需求为目的,《鼎峙春秋》是宫廷戏,他的观众自然是王公大臣和娘娘嫔妃等贵族。观众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鼎峙春秋》必然对乱臣贼子的曹操大加挞伐,对关羽、诸葛亮大力旌阳,让曹操等一般乱臣贼子堕入地狱,让关羽等忠臣义士升入天堂,也是为了警示在座的文武大臣们:前生的忠奸行为自有后世的不同报应,死后不同的报应向人们昭示着生前应做的选择。
娱乐和劝惩是戏曲的两大功能,《鼎峙春秋》既体现了娱乐性,更具有强烈的劝惩、教化意味。树立关羽这样忠孝节义的典范,教化臣民像关羽一样为朝廷尽忠,宣扬因果报应思想,正是宫廷演绎《鼎峙春秋》的目的。《鼎峙春秋》用戏曲的形式图解了统治阶级的意图,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浓重的教化意味。
以上诸种原因,使得《鼎峙春秋》具有明显的、强烈的因果报应思想。它在作品结构上以果报思想作为整体结构的基础,故事止于关羽升仙、诸葛凯旋,基本上是大团圆的结构模式。全文以关羽、曹操作为善、恶的最典型代表。关羽前世是佛门红护法,今世是忠义的典范、忠臣的楷模,死后成神、成仙、成为伏魔大帝;曹操今世作恶多端,是奸残的化身、奸臣的魁首,死后在地狱十殿中受尽折磨,最后变为畜生;他们的生死轮回,都严格依据因果报应规律。
注释:
[1]《鼎峙春秋》,第八本第二十一出《岳帝奏申彰瘅权》,第35页。
[2]《鼎峙春秋》,第八本第二十一出《岳帝奏申彰瘅权》,第35页。
[3]《鼎峙春秋》,第八本第二十二出《阎君牌摄奸馋魄》,第38页
[4]《鼎峙春秋》,第八本第二十二出《阎君牌摄奸馋魄》,第39页。
[5]《鼎峙春秋》,第八本第二十三出《补行阳世三章法》,第43页。
[6]《鼎峙春秋》,第八本第二十三出《补行阳世三章法》,第44页。。
[7]《鼎峙春秋》,第九本第三出《初入冥途须挂号》,第12页。
[8]《鼎峙春秋》,第九本第五出《二殿会三忠勘罪》,第22页。
[9]《鼎峙春秋》,第九本第五出《二殿会三忠勘罪》,第22页。
[10]《鼎峙春秋》,第九本第五出《二殿会三忠勘罪》,第23页。
[11]《鼎峙春秋》,第九本第五出《二殿会三忠勘罪》,第25页。
[12]《鼎峙春秋》,第九本第二十四出《上四殿剑树刀山》,第54页。
[13]《鼎峙春秋》,第十本第二出《阴曹复演渔阳操》,第6页。
[14]《鼎峙春秋》,第十本第二出《阴曹复演渔阳操》,第7页。
[15]《鼎峙春秋》,第十本第十四出《遭谴堕阴冰山》,第8页。
[16]《鼎峙春秋》,第十本第十四出《遭谴堕阴冰山》,第9页。
[17]《鼎峙春秋》,第十本第二十一出《分善恶十殿轮回》,第27页。
[18]《鼎峙春秋》,第十本第二十一出《分善恶十殿轮回》,第31页。
[19]《鼎峙春秋》,第十本第二十一出《分善恶十殿轮回》,第29页。
[20]刘国梁:《道教易学略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6期,第47页。
[21]徐保卫:《话本戏剧中的因果报应观念与多神教和市民文化运动》,《汉中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第32页。
[22]谢伟民:《因果报应——中国传统小说的一种内结构模式》,《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5期,第111页。
[23]肖彬夫:《佛道思想对中国古代戏曲悲剧结局的影响》,《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第44页。
[24]王季思:《全元戏曲》(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25]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责任编辑 原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