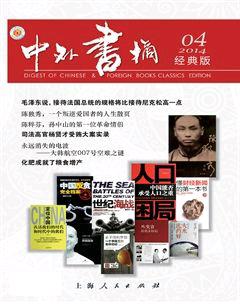上海东台路笃底——我们成长的摇篮
集体回忆+施良驹+整理
施燕华,曾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驻卢森堡大使,其父母共生育了9个儿女,本文是他们的集体回忆。
迁入上海东台路
抗日战争期间,全家于1939年迁到南阳桥安纳金路(现在的东台路)。就此一住就是好几十年。我们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四个在这里出生,而前面几个哥哥姐姐则是在这里成长和走上工作岗位的。所以每当我们说起东台路时,总有一种割舍不去的亲近感。
东台路南起肇周路,北到崇德路,原本是直通的。后来因为在复兴中路以北的一块地建了房子(东台路180号),把路分隔成南北两段。我们家就在这北段靠近最南端的地方。如果叫三轮车或告诉别人如何寻址,说“东台路笃底”就行。180号里住的是一户有钱人家,一栋三层的与众不同的大楼房很气派,至少有十几间房间。楼前还有一个小花园,用竹篱笆与外界隔开。平时大门紧闭,养着一条大狼狗,我们不太清楚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到了20世纪50年代,大狼狗不养了,夏天乘凉时我们经常进去与他们家的小孩一起玩,摘凤仙花染指甲。“文革”中,这里的房子被没收分给许多家老百姓,也变成了乱哄哄的“72家房客”。小花园现在成了社区老人锻炼的场所。我们家是175号,斜对着他们。
离家不远有一条街叫顺昌路。路的北段是“小吃一条街”,阳春面、生煎馒头、菜肉馒头、油豆腐线粉汤……价廉物美,应有尽有。这就是有名的“太平桥”,可以催出我们兄弟姐妹许多口水的地方。儿时的记忆历历在目:每当下午有客来访,爸爸就会派我们小孩去太平桥买生煎馒头招待客人,我们抬起“飞毛腿”直奔太平桥,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因为我们肯定可分得一两只吃吃解馋。这个地方现在建成了太平桥绿地和新天地商业区。
沿着东台路向北走,穿过自忠路不远,就到了有名的“杀牛公司”。杀牛公司的后门在东台路的北端、崇德路和柳林路的交界处。如果哪天正好有牲口运到,又是刮北风的话,一股难闻的臭骚味会随风飘进我们家。有时经过杀牛公司,正好有一车猪或牛送到,它们沿着一个斜坡被赶入屠宰场,猪哇哇嚎叫着不肯往前走,牛则是默默地流着眼泪,没有鞭抽就钉在地上不走。我们见状觉得它们很可怜,以后就不想经过那里了。
沿自忠路往东100米就到西藏南路,那是法租界和老城区的分界线,曾经是用铁门分割开的。
在180号的两边各有一条小弄堂,它们通向复兴中路、吉安路和西藏南路。这条笃底马路看似封闭,其实是四通八达。电车11、17、18、23、24路的车站都在五分钟内可以到达,非常方便。
笃底马路风情多
笃底马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和乐趣。首先,没有车辆经过,整条马路很安静。尤其是冬天从阳台上往下,看行人稀少,有一种凄凉的感觉。而在夏天,则是我们乘凉的好去处,可以肆无忌惮地把小板凳放在马路中央围着坐,讲故事、做游戏、看天上的点点繁星(现在由于地面的光污染,已经看不到多少星星了)。有的邻居甚至用两条板凳搁上一块铺板睡觉。其次,我家的二楼阳台就好像戏院的包厢,可尽情欣赏平民的众生相——三轮车夫坐在小矮凳上,端着一大碗粥喝,遇到有卖臭豆腐的小贩,买上一串油炸臭豆腐,涂上鲜红的辣椒酱,有滋有味地嚼着;有时一群苏北老乡围在一起拉琴唱淮剧,旁边围着一群小孩看热闹;我家斜对面有一家道观,做起道场来几乎占半条马路,我们就在阳台上看道士们念经,大热天还穿着长袍走来走去……有一对侏儒夫妇每天从这里经过,却总是被不懂事的小孩们追着骂:“老牌矮子!老牌矮子!”令人同情。而小小的良骝看到他们,以为是怪物吓得直哭,往屋子里面逃……夏日之夜,当时(20世纪50年代)的居委会经常在这里拉起幕布放宣传卫生的幻灯片,还搭起舞台举办纳凉晚会,沪剧、越剧、活报剧、滑稽戏应有尽有。对我们小孩来说,真是“不出钞票看白戏”,很开心的。
东台路住的多数是贫穷的外地移民,还有一部分是做小生意的,很少是有钱人。人口大部分来自苏北,其次是浙江,还有就是山东、广东等地。
从解放前到20世纪80年代,这条马路上开过不少店。有茶馆、烟纸店、木器店、道观、纸盒店、老虎灶、裁缝店、脚桶店等等。随着时间的迁移,这里的店差不多都关掉了,只有小小的烟纸店和一家老虎灶倒是一直开到21世纪。
夜晚,小孩们入睡不久,会听到宁静的街道上传来清脆的叫卖声:“桂花赤豆汤!白糖莲心粥!”那香气宜人、煮得烂烂的桂花赤豆汤经常进入我们的梦乡。住在楼上的,可以把碗和钱放在一个竹篮子里面,然后用绳子把它们放下去。不多久,一碗热气腾腾的点心就放在篮子里,把绳子拉上来就可以吃了。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家很少买这种“闲食”(零食)。
清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楼下就喧闹起来了。车夫们把门板缷下,用板凳一搁,就成了一条长桌。于是他们就围着长桌吃早茶(饭)。小贩们不失时机,跑来卖草萝饼、油条、唔酥豆,还有大壶的热茶。半根油条裹上几粒焐酥豆,咬一口,喝一口茶,味道很香,真是一种享受。车夫们吃饱肚子后出车,又开始他们一天的劳作。在他们吃早饭时,还可看到有人牵着奶马缓慢地走街串巷,马身上披着薄毯子,脖子上挂的铃铛清脆作响。这是现挤现卖马奶的,一般只有富裕一点的人家才吃得起。
在东台路上最吸引我们的,就是每天搭在人行道上的“小书摊”了。书摊上琳琅满目地摆着各式连环画书,我们称之为“小人书”,交一分钱就能坐在很矮的条凳上,看《西游记》《水浒传》里的故事,如《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野猪林》等。看完一页,用舌尖舔一下食指,翻一页。有的书已经很破旧,虽然“其貌不扬”,但内容很吸引人。爸爸不允许我们在那里租书看。他说书太脏,要染上毛病的。没办法,我们有时站在别人的后面猫着腰,伸着头“揩油”,还看得津津有味。我们称这为“张小书”(张,宁波话念jiang,张望之意)。爸爸在阳台上如果见我们在“张”别人的小书,认为是没志气,也要毫不客气地叫回家来。解放后小人书就叫连环画了,而且越画越好,我们在学校、单位里就能看到了。每当我们看到小人书时,还总是想起东台路上的小人书摊,那是孩子们的最爱啊。“小书摊”不仅租书,还有许多糖果、杏梅、芒果干之类的小吃卖,花一分钱就可解馋。endprint
到了春节前夕,小书摊扩大了地盘,增加了爆竹、面具、大刀等等孩子们喜欢的玩具,晚上张灯结彩十分喜庆。元宵节晚上,大人小孩提着各种灯笼在街上庆祝,爸爸经常用竹子给我们扎兔子灯或圆灯,让我们提着灯笼到街上玩,这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
延续几十年的简陋生活
上海的老房子没有自来水,每幢楼的后门外有一个水龙头,家家户户用水都到这里来接。我家在二楼,所以备了一个水缸和两个水桶:一个桶是用于去楼下提水并倒在大水缸里备用;另一个桶则是暂存污水用,存满了再提到楼下倒掉。提水的活大人可不好干,因为楼梯踏板很窄又陡,大人只能踏上半个脚多一些,楼道内又很暗,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水一起滚到楼下去。那时候夏天洗澡很简单,用一个大木盆,倒上一些水,人就坐在里面搽肥皂或清洗。有时为了消毒,爸爸还在澡盆里放点来苏尔。那时用水很节约,一家人一天大约就用一缸水。衣服被子什么的都到下面去洗。一到暑假,妈妈就要催我们到楼下自来水龙头洗布鞋、球鞋,洗干净后整整齐齐地排在阳台上晾干。水费是整幢房子按人头摊,全家一个月才几毛钱。
老房子也没有厕所,家家户户都用“马桶”,马桶放在屋内。许多家庭只有一间房间,那就吃喝拉撒睡全在这几个平方米的天地内。马桶一般放在很隐蔽的地方。有的人家还把它放在一个做工挺精致的“马桶箱”里,既掩盖了异味,也美观了外表。
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就会听到清洁工拉着粪车在楼下喊:“倒马桶!”“再不来就走了啊!”家庭妇女们纷纷把马桶提出去交给清洁工人倒入粪车,随后是稀里哗啦的刷马桶的声音,伴随着妇女们的笑声和闲言碎语。不久,一切恢复正常,天也就亮了。我们上学的途中,人行道上摆满了一个个洗干净的马桶口朝天晾着,这是老上海的一道风景线。
烧饭的炉子就放在房门口的过道上,冬天有时就放在屋内。每天清晨,家家户户第一件事是生炉子,我们小时候都有生炉子的经历。生炉子时,炉门要对着风来的方向。引火是用旧报纸点燃木柴,然后由木柴点燃煤球。不顺利的时候,旧报纸烧没了,煤球仍没烧着。且不说弄得人一脸灰尘,呛鼻的煤烟味使全家咳嗽不止,还会影响生炉子人一天的情绪。后来发明了蜂窝煤和新式炉子,就可以把炉子封过夜,早晨起来打开炉门,加个煤饼就可用了,节约了劳动力。但这样做会散发很多的一氧化碳,所以一到冬天,常听说有人家煤气中毒的事。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发生,我们家厨房一年四季都开着小窗通风。寒冷的冬天,早晨起来会看到水缸里的水已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夏天,我们经常开着门和窗,在通风的地方摆两个长凳,搁上一块门板睡觉。奇怪的是,那时蟑螂老鼠臭虫肆虐,却没有蚊子。
在东台路笃底处有一个垃圾桶和小便处,小便池的墙上经常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啼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那是有经常哭闹的孩子家长所贴,他们希望许多人念了此帖孩子就会不哭。我家阳台正对着楼下的这个秽物集中处,一到夏天气味特别重。来运垃圾的是一辆马拉的平板车,老上海叫它“老虎塌车”。因为车身长马路窄,为了掉头,不得不来来回回倒多次才能转过方向来。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垃圾桶边上还搭建了一个木制的活动房,我们叫它草棚棚的,里面住了一家好几口人。在如此简陋的生活环境中,人们还努力改善卫生条件。后来草棚棚拆走了。垃圾桶也修得正规了些,而且经常喷药,小便池也搬走了。谢天谢地,笃底马路的卫生状况大为改善。
尽管条件差,这一地区的居民仍很爱干净。人行道是他们交流的场所,甚至还是露天饭厅,大家从不乱扔垃圾。每天一大早,住在一楼的人家都端着脸盆,用清水冲刷街面,街面总是很干净。这也是老上海居民的习惯。燕华从北京回来,总要夸奖楼前的马路干净,没有痰迹。
七十二家房客
20世纪50年代有部电影,叫《七十二家房客》,讲上海滩住房的拥挤和邻里关系。我们那个楼内虽没有七十二家,但住的房客也是鱼龙混杂。
我们家虽说是住在175号,但实际上还包含177弄上面的两间过街楼。这条弄堂是我们进出的必经之路。以前弄堂装有雕花铁门,很好看,像法国建筑的铁门,因为这里曾经是法租界嘛。可惜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雕花铁门被拆去进炼钢炉了,代之以难看的粗木条。进弄堂面对着的是三座比较正规的石库门房子。这三幢房子比我们的好,里面主人的家境要比周围的邻居都富裕些。三家的门前形成一块空地,就成了我们小孩子玩“造房子”“踢毽子”的地方。天冷时,弄堂就成了一些“叫花子”避风、御寒、躲雨的港湾了。有一年冬天特别冷,就有人冻死在弄堂里。尸体被拉走时,我们只看见一条席子和一些破布、烂棉花,当是御寒之物。
我们这幢房的一楼灶披间,八平方米的地方,住着三代人:一个苏北老奶奶,两个儿子和一个跛脚女儿,还有孙子孙女。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她家用轿子抬来了漂亮媳妇,大家都叫她“新娘子”。这个称呼一直叫到老,我们也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新娘子十分勤快贤惠,天不亮就起来帮人家倒马桶刷马桶,白天帮人洗衣服,做衣服,我们没见过她有停歇的时候。她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和经济来源,培育三个孩子上了中学、技校。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老奶奶虽然不识字,但待人处事却不比文明人差。年纪很大了还每天主动擦洗楼梯,一直擦到二楼我家门口。两个儿子都是卖苦力的,拉黄包车或蹬三轮车,没什么文化。几十年后碰到新娘子的儿子女儿时,他们都说老奶奶经常教育第三代:要向施家的孩子学习,好好读书。现在她的孙辈或重孙辈都有了出息,有的还上大学和读研究生了。
我们的楼上三楼住着姓李的山东人。这家人完全是帮地痞,靠武力吃饭,动不动就打架。大儿子李国臣曾是铁路警察,因偷铁路的枕木被判刑入狱,解放前就死于狱中。二儿子则是个混混,解放初期死于肺痨病。一个女儿后来也迫于生计卖淫……不过,兔子不吃窝边草,他们在东台路上倒不惹事。
一个亭子间里住着一家本地人,我们叫他们“好公”“好婆”。好公是个老实本分的人,解放前是“邮差”,解放后归入邮局当邮递员,那时他看上去已经很老态了,每天还要背着个装得满满的大包步行给家家户户送信送报,我们看到此情景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同情。好公还经常在外面捡香烟头,把里面的烟丝取出归在一起,用一个简易的卷烟设备自制香烟抽。好婆则把一包白色的粉末倒在一张锡纸上,下面点着自来火烧,她则张大嘴吸食烧白粉冒出的烟。endprint
另一个亭子间里住着一个看上去很干净的苏北小脚老太太,我们叫她小脚姆妈。她的丈夫叫吴四,是拉黄包车的。其实这个老太太并不老,当时20世纪50年代最多也不过五十岁左右。她很会打扮,经常梳头,修脸;用黏黏的刨花水,擦在头发上,头发显得乌黑锃亮;还用一段棉纱线对折,一头含在嘴里,两手把棉纱线绷开,在脸上来回地绞,直至绞光脸上的汗毛,使脸皮变得细嫩。这是那时的一种土法美容术。
三楼顶上的晒台上搭出一间约十平方的“房”,住的也是苏北人。男的是警察,子女一大堆,有些是良驹、燕婷的同学,经常到我家来玩。他们全家语言能力很强,讲的上海话最纯正。解放后,因为属于住房特别困难户,政府分配房子,搬到福建路去了。
还有一家宁波人住在只有8平方的一个亭子间,人口最多时住了祖孙三代共六个人。儿子在外地工作没有上海户口,故迟迟没有分配房子。因为房间太小,又没有兄弟姐妹,他们的儿子经常来我家玩,有时还住在我家。难怪爸爸说他是我家的“半个儿子”。以后我们一直是亲如兄弟的好朋友。
我们楼里所有人家白天都敞开大门,邻居之间可以自由出入。和我家较近的邻居,如果有人过生日,或者做好吃的东西,就会端过来,让我们尝尝。我家包汤圆或炒年糕,也会盛一碗给邻居。外地的兄弟姐妹回上海,常常是才进弄堂口,就有人嚷开了:“施家××回来了!”
我们家虽然占有过街楼和前楼两大间,但是兄弟姐妹九个加上爸爸妈妈外婆总共十二人怎么住得下。大房东在楼梯边上天花板下面的地方(老房子屋顶很高)搭建了一个大约两三平方米的阁楼,可以容纳两三个小孩睡觉。阁楼的门就设在楼梯半腰处。只要门一关,那就是“暗无天日”的地方。小孩很喜欢,睡在一个小小的封闭“盒子”里特别有安全感。那时良骏良骐已经是热衷科学的小青年了,这小阁楼就成了我们的家庭电影院。他们经常用自制的幻灯机和幻灯片放幻灯给弟妹看,后来又借来手摇的电影机放电影。电影很短,记得就是一个外国人进门脱帽挂大衣几个动作。就这简单的片段让我们懂得了,啊,电影原来是许多照片连续起来播放所形成的,真是扎劲!
我们家有六个男孩,个个健康,所谓“人丁兴旺”,在那时,被认为是“有福之家”。哪家结婚了,就要请妈妈去替他们缝新被子。哪家生男孩,为保孩子平安健康,就要求把孩子“过房”给我们的父母,即做“干儿子”。爸妈有两个“干儿子”,其中一个是豆市街的宁波邻居,另一个是我们附近菜场一个卖菜妇女的儿子,因爸爸常去买菜,认识了。当她知道东台路“施家伯伯”家人丁兴旺,施家伯伯人缘好,就要求把她的儿子“过房”给他。
每年大年夜,爸爸都要准备一席年夜饭,两荤、两素,一碗白米饭,上面放一颗红枣,放在竹编的红漆食品篮里,让良骅或良骥带着弟弟们给两个“干儿子”送去。
亲朋好友中有人结婚,想沾点喜气,就要请我家的男孩去做小傧相。有一次良驹、良骝还被接到人家的新房,睡在新郎新娘的床上过夜,这叫“压床”。据说,这样新婚夫妇就会“早生贵子”。
严格的家教
这就是当时我们家周围的环境:穷人居多,人员复杂。爸爸妈妈担心我们受不良影响,对我们的管教很严厉,特别注意不许我们“轧坏道”。如果见到我们有与不三不四的“野蛮小鬼”玩在一起,就要教训。家里“规矩”很重:上学去时要说“爸爸妈妈我走了”,回来要说“爸爸妈妈我来了”,吃完饭离席要说“(你们)慢慢吃”。平时坐着腰板要挺直,稍有弯曲,就会遭到猛力一掌把你敲直。“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行如风”这十二字是爸爸经常要求我们做到的。还有大人讲话小孩不能插嘴,小孩吃饭不能说话,不能双手搁在桌沿上,第一次动筷不能夹荤菜,红烧肉一般只能吃一块等等。有时我们乘大人不注意时赶紧偷夹一块肉塞进碗底,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爸爸怎么会不知道,睁只眼闭只眼而已。严格的家教使我们兄弟姐妹在这鱼龙混杂的环境里保持好的传统。爸爸妈妈对我们的教育重在人品,而对于我们的课余爱好,学习计划的安排,甚至个人恋爱结婚等具体事情是不会过分干涉的。爸妈的教育加上哥哥姐姐们带头读书学习,孝敬父母,关心弟妹,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于是就使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人都很争气,远离不良习气,在以后的日子里,各人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随着时间的推移,施家在东台路的名气越来越响。当外地子女回来,一起走在东台路上时,坐在人行道上择菜的“阿姨”们会小声议论:“这是施家伯伯的小囡,看人家多有出息!”爸爸在世时,这条路上没有人不知道“施家伯伯”的。爸爸不在了,我们在路上走,也常有人来打招呼,有的讲了他们对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及其子女“个个有出息”表示非常羡慕,有的说他们就是以施家为榜样来教育自己的小孩,以致他们的子女现在都是研究生了,等等。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一个地离开了家,去外地学习和工作了。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东台路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是我们魂牵梦萦的地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