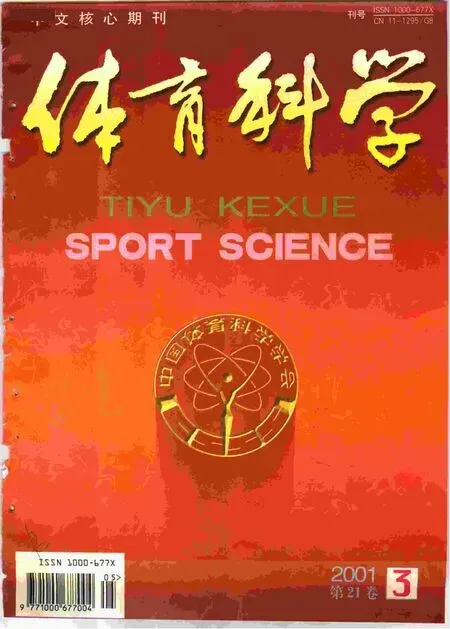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与身体运动文化形成的文化生态学分析
——东巴跳与达巴跳的田野调查报告
万 义,王 健,龙佩林,白晋湘,杨海晨,王 涛
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与身体运动文化形成的文化生态学分析
——东巴跳与达巴跳的田野调查报告
万 义1,2,王 健2,龙佩林1,白晋湘1,杨海晨2,王 涛2
运用文化生态学理论与田野调查方法,比较东巴跳与达巴跳的文化生态结构,并对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与身体运动文化形成的内在逻辑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人类在原始宗教观念支配下,以身体肢体动作与神灵沟通,藉此畏神敬神、祛灾祈福,是身体运动文化形成的最初动力;祭祀神灵仪式中幻化鬼神的祭神舞,图腾崇拜仪式中模仿动物的象形舞,驱鬼辟邪仪式中镇鬼消灾的法器舞,涵化了身体运动文化的内容习得;原始宗教强大而稳定的宗教场域,促进了身体运动文化的传承发展;传统社会结构里,原始宗教中的身体运动表达,具有慰藉群体身心,调整人际关系,调节社会张力,维持社会秩序,维护阶层利益,稳定社会结构等功能。
纳西族;摩梭人;东巴跳;达巴跳;文化生态
:This paper comparatively analyzes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structure of Dongba dance and Daba dance and probes the internal logic between minority primitive religion and formation of body movement culture by using cultural ecology theory and fieldwork.The result shows that,under the domination of primitive religious ideas,people communicate with gods by body gestures to worship gods and dispel the disaster and pray blessing.This is the initial impetus for the formation of body movement culture.Ritual dance to fantasize ghosts and gods in the worship gods ceremony,pictograms dance to imitate animals in the totem worship ceremony and talisman dance to quell ghosts and eliminate disasters in the ceremony of getting rid of ghosts and avoiding evil cover the content acquisition of body movement culture.Strong and stable religious field of primitive religion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body movement culture.In the traditional social structure,body movement expression in the primitive religion has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as comforting bodies and minds of groups,adjusting interpersonal,regulating social tension,keeping social order,safeguarding classes’ interests and stabilizing social structure.
1 前言
现代体育出现以前,宗教与体育的联姻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社会结构里,许多身体运动都植根于原始宗教仪式而存在,并没有脱离原始宗教的范畴而形成独立的体育文化表现形态。纳西族聚居于云南省丽江、玉龙、维西、中甸等地,信奉东巴教,东巴祭师在宗教祭祀活动中的东巴跳,逐渐从历史禁锢中走向时代舞台,发展成为丽江旅游的城市名片和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居住在金沙江东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木里县与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之间的摩梭人,信奉达巴教,常年举行各种宗教祭祀性活动,达巴跳是摩梭祭师在宗教祭祀活动中以身体肢体运动为主要特征的仪式总称。史书记载,达巴跳和东巴跳同源于古代氐羌族群,氐羌族群“畏秦之威”,离开故地湟河流域,向南迁徙[26]。饱受高寒地理环境、残酷部落纷争、政治利益博弈的古代氐羌族群,在不断分化的同时,也与当地土著部落逐渐融合,形成了同源异质的东巴教文化圈和达巴教文化圈。
2012年3月,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科学分会主办,华南师范大学、纳西文化研究会、东巴文化研究会等单位承办的“体育人类学丽江论坛——文化建设与体育发展研讨会”与会代表到东巴文化辐射区域丽江市玉水寨观摩第6届东巴大会,对纳西族东巴祭祀活动及其不同流派的东巴跳进行了定性观察,并对和力民等东巴资深学者进行了深度访谈。次日,与会代表到四川盐源县前所乡,对金沙江流域生态环境进行观察体验,并对80岁高龄何鲁佐达巴的达巴跳传承活动进行实地调查。东巴跳和达巴跳是祭司根据不同祭祀需求,按照传统的仪式规程所表演的一种身体运动,表面虽多为跳神、驱鬼之类的宗教祭祀动作,实际上体现了人类精神世界的身体动作叙事,是体育人类学研究的“活化石”[25]。本研究运用文化生态学理论与田野调查方法,梳理东巴跳与达巴跳身体运动文化的历史演变历程,对比分析两种身体运动的文化生态结构,进一步探讨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与身体运动文化形成的内在逻辑,以期促进乡土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 东巴跳与达巴跳身体运动文化的形成
2.1 藏彝走廊两个扩张型文化实体的竞争
依据现代民族学的族群理论,一般把远古时期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以河湟流域(今天青海、甘肃的黄河、湟水、洮河流域)为中心的戎、氐、羌等,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古代民族,统称为氐羌族群[27]。不言而喻,常年长途迁徙的原始牧民,把一切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都归结于灵魂的存在,形成了信仰和崇拜的超自然神灵,产生了“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万物有灵”是自然界的人格化,在人类的意识中,已经将生存的世界变成人与神共存的世界,人类屈服于神灵的安排,出现以神灵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为主的原始宗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氐羌族群原始牧民的思想观念和思维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知和要求与日俱增,常常举行祀神驱魔、爙灾祈福的各种集体性活动,将个体的心理活动转变成社会集体意识,用神灵观念和宗教体制构成“个体——群体——社会”的内在关联,形成原始氏族社会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宗教秩序。在宗教祭祀活动中,为了保证祀神驱魔、爙灾祈福的顺利进行,进而突出巫术活动的祭祀效果,群体自发地推选本族族群的杰出人物,形成酋长、巫师、舞手三位一体的职业化巫师和专业化的巫舞。这种情况在我国解放前的少数民族中依然存在[24]。
氏族社会末期,原始社会制度逐渐被奴隶制度所取代,私有制的出现,经济的不平等,带来了规模空前的生产、交换、战争、迁徙等社会群体活动。西北氐羌族群南迁,定居在怒江、澜沧江及金沙江并流的藏彝走廊。秦汉之际,随着封建统治的巩固和深化,政权和神权高度集中,氐羌族群巫师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神权,巫舞和巫术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氐羌族群南下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旄牛种,越嶲羌是也”。《葛天舞》记载:“博南(今永平)……,一人吹笙前导,众人手持旄尾随之[29]”。所谓旄牛羌,就是现今摩梭先民,金沙江流域四川境内的摩梭人还以旄牛尾巴为饰,以跳旄牛尾巴舞为祭。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藏彝走廊是两个扩张型文化实体的竞争地,一个是在走廊东方的中央集权政府,以谋求改变少数民族的信仰及生活方式,扩张自己的政治版图和文化范围;另一个是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统治集团,藏传佛教改变了周遭族群的信仰,让它们转向以神权及来世为导向。藏彝走廊两个扩张型文化实体的存在,为后来氐羌族群的原始巫舞分化,发展成为东巴跳和达巴跳产生了深远影响。
2.2 氐羌族群四大氏族部落的利益博弈
隋唐时期,氐羌族群居住在东起雅砻江流域,西至金沙江流域的一块狭长横断山区,氐羌族群部落分化成各自为政、互不统摄的“星列酋寨”。其中,四个氏族部落逐渐繁盛壮大,分别是:世居雅砻江流域的禾氏部落、世居金沙江流域的梅氏部落和世居江湾地玉龙山脚下的束、尤氏两个部落[15]。梅氏部落地处南诏北犯、吐蕃过境的兵家必争之地;禾氏部落境内富集中央王朝、南诏、吐蕃急需的盐铁等战略物质。所以,梅氏和禾氏部落所辖领域常年累月战争不断,子民背井离乡。梅氏部落被强制离开故地,东渡金沙江,迁徙到远离故地的永宁地区。为了与当地吐蕃居民消除族群之间的分歧与隔膜,有意识地弱化、改变自己固有的原始巫教,梅氏部落推崇与当地藏传佛教相互融合,效仿吐蕃执举的政教合一的政体组织模式,发展成为摩梭达巴教文化。达巴教与当地藏传佛教相互融合之后,被藏传佛教光芒所掩盖,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所以,现今的达巴教仍然停滞在唐代以前木刻画具象符号的古老阶段。达巴教在隋唐时期历经短暂的辉煌之后迅速衰落,仅在民间得以保存。目前,四川境内盐源、木里与云南境内宁蒗的少数摩梭达巴师能诵达巴经、跳达巴及主持各种宗教祭祀活动。
而世居江湾地玉龙山脚下的束、尤氏部落,三面环江背靠雪山,地理交通环境闭塞,绕开南诏北犯、吐蕃过境之险。束、尤氏部落所辖境内也无盐铁资源,加之部落酋长长期坚持内援外交的生存方略,获得了长期安定和平的生存发展空间。束、尤氏部落在长期稳定协调的社会结构中,生产方式从狩猎采集型过渡到高原游牧,最后演变成生产力水平更高的山地耕牧经济,区域经济极大富足为东巴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条件。原来固有的原始巫教,从万物有灵的神灵崇拜,到亲缘化的图腾崇拜,再演变成半亲缘化和半神灵化的祖先崇拜,最后发展成为多神原始宗教——东巴教。东巴经书与东巴舞谱也从岩画符号过渡成为木刻画符号和木牌画符号,最后发展成为高级阶段的象形图画的文字符号,为现今东巴经书和东巴舞谱列入世界记忆遗产提供了可能。所以隋唐时期,是氐羌族群原始宗教分化的重要阶段,梅氏部落在战争迁徙过程中,将原始宗教与藏传佛教结合在一起形成达巴教,但其光芒被藏传佛教所掩盖。束、尤氏部落稳定的社会结构、富足的区域经济、安定的政治格局,使东巴教获得了长期、独立和持续的发展空间。东巴教逐渐有了象形图画文字符号的东巴经书和东巴舞谱,东巴跳也逐渐形成了完善的程序和动作体系。
2.3 屏藩定位施政方略与木氏土司崛起
历代中央集权政府为了巩固政权,一直推行弹压、隔离、征剿的政策,导致中央集权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对抗性矛盾的加剧,少数民族地区屡次爆发大规模的起义。元末明初,中央集权政府对待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由原来“以夏制夷”政策,调整为羁縻政策,实施“招抚”、“招安”,同时,设立所、营等地方行政机构分而治之。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束、尤氏部落首领阿德率众首先归附明军,“钦赐木姓”。《皇明恩纶录》记载:“大军既临,渠魁以获。尔丽江土官阿德率众先归,为夷智识,足见摅诚,今命尔木姓,从听总兵官傅,拟授职建功”,并“授尔子孙世袭土官知府,永令防固石门,镇御蕃鞑”,木氏土司代代承袭,一直沿袭到清代初期。木氏土司在260年的执政中,坚持“辑宁边境”、“明国藩篱”的施政方略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14]。
崛起的木氏土司摆脱了南诏和吐蕃的掣肘,紧紧依靠中央皇权,获取自主的民族地位和自立的经济条件,对东巴教和东巴跳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木氏土司王朝积极营造本源东巴文化,吸纳和兼容域外多元文化:当中原儒家文化涌入纳西边陲时,木氏积极学汉文、学儒礼,借此希望与中央皇朝施政意识形态接轨;木氏从内地聘请道教法师作为顾问,赐予院宅基地,待以优厚俸禄;木氏也把汉传佛教引入纳西地区,在域内盖建庞大汉传佛教寺庙;木氏力倡民间百姓学纳西象形文字,读东巴经典教义;木氏还在塔布丹设立东巴学校,集中一批博学的东巴教授,拨以土地(东巴田),作为东巴教授的世袭俸禄[16]。所以,明清时期的木氏土司在域内积极引入儒、释、道精粹,营造多元一体的东巴文化环境,为丰富东巴跳的形式和内容创造了优越条件。
2.4 原生态东巴文化保护工程焕发生机
1954年,根据本民族意愿,经国务院批准,由古代氐羌族群分化出的“纳日”族群被定名为纳西民族。纳西世居地区推行土地改革运动,纳西族许多传统民俗由于掺杂着各种宗教祭祀活动,统统被视为封建迷信的复辟被禁止;纳西境内村村寨寨捣毁宗教庙宇、菩萨具象、祖宗牌位,东巴书籍和东巴舞谱抄没后付火焚毁;誉为“东巴文化活化石”的东巴师因传播封建迷信而备受批斗。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祭祀活动中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才得以重新认识。万宝、方国瑜等知名学者呼吁抢救纳西东巴文化,成立东巴文化研究院,大力整理出版东巴古籍和东巴舞谱。2003年8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东巴古籍文献(含东巴舞谱)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自此,纳西东巴文化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原生态东巴文化保护系列工程被提上日程。2003年底,纳西族聚居地丽江成立了群众性的民间文化团体“纳西东巴文化传承协会”, 推动东巴文化的挖掘、整理、传承与发展。2009年,开设了“玉水寨东巴传承学校”,配备专职教职工6名,招收10~14周岁纳西族少年学习东巴跳、东巴画、东巴经、东巴工艺等传统文化。自古以来,东巴一般是家族内世袭传承,父传子、舅传甥,连拜师收徒者都甚少,办学培养年轻东巴、传承东巴文化的模式从未有之。2012年,成立了“东巴学位评定专业知识考核小组”, 东巴学位评定分为东巴法王、东巴大师、东巴师、东巴传承人、东巴学员,不同学位的东巴通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考试后,分别给予2 000~6 000元/年不等的学位补贴。原生态东巴文化保护系列工程的推广和实施,构筑了东巴跳发展的良性生态机制,东巴跳呈现出传承有序的和谐发展景象。
3 东巴跳与达巴跳文化生态圈的生态结构层次比较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安利·斯图尔德(1968)将文化生态视作“一个包括内核与若干外核的不定型的整体,从外而内约略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等生态结构层次”[19]。东巴跳与达巴跳虽然一脉相承,但历经时代的变革,两种身体运动文化的生态结构层次仍然呈现一定的差异。
3.1 东巴跳与达巴跳物态文化层比较
物态文化层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形态的文化事物,直接反映人类对自然界认识、利用、改造的深入程度,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3]。东巴跳和达巴跳在镇鬼驱邪的祭祀仪式中,都有手持镇鬼法器的身体肢体运动。但是,东巴跳中常使用刀剑、神箭、镇妖器、降魔杵、法杖、祭水壶、神堂、打鬼竹杈等法器,镇鬼法器多样,动作体系完整,动作刚劲洒脱,而达巴跳仅在较少的镇鬼驱邪仪式中使用长刀等法器。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东巴教和达巴教鬼神观念的不同。达巴教中的鬼是与神、人共生的系统:一种是正常死亡者,归入祖先,是善鬼,统称“库初”;另一种不是正常死亡的,祖先不收留他们,统称为“比初”;还有一种称凶死鬼,如吊死鬼、难产鬼、溺死鬼,专门作祟,统称为“兜”。“在摩梭人的任何一个驱鬼撵妖的仪式中,首先要用好酒好肉服侍,好言好语相劝,尽量劝他们走,实在劝不走(如病人不见好时),才动用一些刀之类的武器吓唬一下,这可能是母系社会观念的一种折光反映”[8]。而东巴教的教义中融入了道家思想,认为鬼是与神、人对立的系统,即神造了天地万物和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变化后产生了360个各种类型的鬼卒,所以对待鬼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武器和手段镇压或驱除。纳西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小孩斗敌力量不足,求助于弓箭和大刀;主人斗鬼神力量不足,求助于祭祀和占卜者”[28],就是鬼与神、人对立观念的客观体现。

表 1 东巴跳与达巴跳物态文化层比较一览表
达巴服饰具有典型的藏传佛教特征,比如:五佛冠、佛珠串、燕尾袍等,但是服饰的样式相对比较单一,也没有严格的祭祀场合区分。而东巴文化很少受到战火的纷扰,加上儒释道多元文化的融合,使东巴服饰的形式、色彩、配饰多样,东巴可以根据祭祀内容和场合选择不同的服饰。此外,达巴师与东巴师在法事辐射区域的分布上也呈现一定的差别,达巴都有自己特定的法事辐射领域,一般情况下达巴师法事辐射域不存在交叉。而东巴根据法力高低的不同(根据传承历史长短、掌握经书仪式多少、法事灵验高低等经验区分),法事辐射域存在一定交叉现象。达巴跳所活跃的区域,人们以高原草场畜牧型为主。这种经济文化类型对自然物质和资源条件的需求较高,氏族家庭往往需要圈定一定的自然环境,才能满足自己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种草原畜牧的经济生产意识影响到达巴跳的分布和达巴法事特定的辐射范围。而东巴跳活跃的区域,人们以山地耕牧型经济文化类型为主,山地耕牧经济文化类型需要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生产方式的团结协作以及互帮互助的人际关系,这种集体意识形成了东巴的等级和法事辐射的交叉现象。
3.2 东巴跳与达巴跳制度文化层比较
由人类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社会组织构成制度文化层。达巴教无固定的宗教组织和寺庙,宗教教义、宗教信仰、宗教秩序和宗教仪式依靠达巴口诵经传承和传播。达巴口诵经主要内容是对自然诸神,动植物诸神和祖先的颂歌,以及驱逐鬼邪的巫术咒语,相传有117部之多,现在幸存下来的不过60余篇章[9]。达巴教由于没有纸本经书,也缺乏相应的舞谱记载,达巴跳的传承仅仅依靠老达巴的口传身授,这种口传身授的传承模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传承内容的逐渐残缺或消失。东巴教最初也没有固定庙宇,仅在野外山头或在岩洞里设祭坛。后来受域外道教、佛教的渗透和影响,部分地区的东巴将神坛从野外山头迁入家庭庭院,甚至相互邀约筹款,建立过规模较小的东巴庙宇。东巴教有自己的东巴经,东巴经是一种手抄经。据有关统计,中外共收藏东巴经23 000余册[10]。东巴跳有相应的东巴舞谱记载,现存东巴舞谱6卷共记录了158段东巴跳的身体动作,老东巴在传授东巴跳的时候,依照东巴舞谱的内容进行传授,徒弟掌握后也可以融入自己的理解和创新。
虽然东巴跳和达巴跳都是基于宗教祭祀仪式的身体运动,但是,传承有序的东巴经赋予东巴跳深刻的宗教文化内涵,东巴舞谱是东巴跳有效的承载方式,所以,东巴跳比达巴跳内容体系要更加完整。在传承方式上,达巴跳一般通过家族世袭传承,父传子或舅传甥,很少收外族外姓徒弟。东巴跳最初也以家族世袭传承为主,明代之后有东巴学校传承和师徒传承的方式出现,特别是2009年,“玉水寨东巴传承学校”开设,纳西后代、外族儿童、东巴文化爱好者都可以到学校接受正规的东巴文化学习。2012年,东巴文化传承协会主管的“东巴学位评定专业知识考核小组”成立,东巴跳和达巴跳都由原来的家族氏族管理,纳入东巴文化传承协会稳定、有序、高效的管理模式之中。
3.3 东巴跳与达巴跳行为文化层比较
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行为文化层,行为文化层以礼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达巴跳的内容体系将宗教仪式动作与生产生活技能培训结合在一起,如《阿什撒里搓》即纺麻线舞,《帮泼搓》即播种舞,《帮收搓》即秋收舞,《如古鲁搓》即编草席舞等。东巴跳的内容体系将宗教仪式动作与宗教教义紧密结合。东巴跳通过楚里拉姆神舞、丁巴什罗神舞、端格优麻神舞、达拉米悲神舞、格称称补神舞等仪式,宣扬半人半神祖先的事迹和功绩,从而熏陶祖先崇拜的宗教信仰观念。现存东巴舞谱共有6卷,记录了158段东巴跳的谱文,除去重复性的动作和种类,共3大类52种东巴跳的基本动作,涵盖祭神舞、图腾舞、跳步舞、法器舞、武舞等类型,是反映纳西民族族群迁徙、生产生活、宗教信仰、民俗文化和群体心理的百科全书。

表 2 东巴跳与达巴跳制度文化层比较一览表
东巴跳中还有两类身体运动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一类是以图腾崇拜为主要特征的象形舞。氐羌氏族从北方迁徙到南方,将具有强大生殖能力的动物作为本部落的图腾,寄期获得部落人口的繁荣,并根据图腾属性进行生产资源分配和血缘亲缘的认定。纳西先民最早有熊、蛙、蛇、猴4个图腾,随着人口繁衍壮大,氏族分支增加了羊、虎、龙、孔雀、蟒、牛、鹿等图腾,这些图腾崇拜仪式最终演变成山羊舞、龙舞、孔雀舞、蟒舞、牛舞、虎舞、狮舞、马舞、鹿舞、象舞、蛙舞等17种动物的模拟动作,被誉为“人类身体运动意识的活化石”;另一类是以驱鬼辟邪为主要特征的武舞。东巴武舞主要表演者为东巴或参加祭祀仪式的族人,一般在与祭祀神灵、驱撵鬼魂的祭典仪式中举行。东巴针对鬼的类型种类、鬼的魔力大小、祭祀场合和方位,选择刀舞、剑舞、弓弩舞、叉舞、长矛舞、盾牌舞、护法神舞等不同的镇鬼法器和镇鬼动作,动作刚劲有力、柔韧洒脱、庄重肃穆,用以驱鬼辟邪、祛灾祈福、治病救人等。1955年,云南省首届滇西民族体育表演大会,东巴武舞首露锋芒。1982年,第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东巴武舞得到国家体委、国家民委和新闻媒介的一致好评。1989年,在全国武术论文报告会上,东巴武舞被誉为“最古老的拳谱”。

表 3 东巴跳与达巴跳行为文化层比较一览表
3.4 东巴跳与达巴跳心态文化层比较
由人类社会实践特别是思想意识活动长期积淀而成的价值标准、审美观念、思维方式等构成心态文化层。东巴跳与达巴跳同根同源,但是达巴跳在政治、军事势力争夺与藏传佛教强势介入的夹缝中,失去了独立自我的发展空间。东巴跳则依靠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融合儒释道等多种宗教文化,得到稳定、持续的发展。达巴跳目前仅在摩梭人聚居地区,在民间底层以祭祖祭祀、祛病救人、驱灾祈福的形式存在着。随着以“寻觅女儿国”为宣传口号的泸沽湖旅游线路的火热,达巴跳以母系氏族文化代名词的身份,走向旅游表演的舞台,但社会影响力有限。从2001年起,东巴教圣地“玉水寨”都会举行每年一度的“东巴法会”,各地东巴不约而同相聚于此,举行盛大的东巴法事活动。游客蜂拥踏至、慕名前来观赏风格迥异、特点分明的各种流派东巴跳,东巴跳已经发展成为丽江文化旅游的名片。各地东巴也可以利用此难得的机会,相互切磋东巴跳的技艺,提升彼此的技术水平,“东巴法会”也因此成为东巴跳文化交流的平台。
现在的东巴跳除了延续了民间宗教职能以外,也有部分内容已经发展成为纳西群众全民健身方式之一。比如,传统祭祀活动中的“窝热热”,原是丧葬祭祀中的一种群体性仪式活动[4],只能在老年人丧葬时跳。“窝热热”以足踏地为节拍,伴着哀怨的歌声,边跳边唱边落泪。每当唱到驱鬼杀鬼之时,舞者便做驱鬼、杀鬼之状,反复唱跳,通宵达旦。现在每天黄昏的丽江古城四方街广场,也能见到许多身穿民族服装的纳西群众,参与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窝热热”。所以,东巴跳和达巴跳的发展都应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逐渐向满足群众物质经济增长的需求,日益丰富的娱乐休闲需求演进。

表 4 东巴跳与达巴跳心态文化层比较一览表
4 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与身体运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4.1 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思维与身体运动意识的产生
体育理论界对身体运动的起源大多持多元论的观点,认为原始宗教信仰的需求是身体运动起源的重要方式之一[17]。英国人类学家麦克斯·缪勒长期关注宗教学研究领域,认为宗教本质上是对无限的体认,并提出原始人是从三类自然对象中形成原始宗教的观念。第1类是能够完全把握的物体,如石头、甲壳之类;第2类是部分能把握的物体,如树木、山岭、河流等;第3类是可见不可及,完全不能触知的物体,如苍天、太阳、星辰等[13]。这些东西被人赋予神秘性,构成内心的崇拜对象,形成“万物有灵”的观念(爱德华·泰勒,1871)。人类在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念中,神灵是和人相通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引起神灵的高兴与不悦,不可避免地崇拜他们或希望得到他们的怜悯[20]。原始人类群体在能与神灵有效沟通的巫师带领下,将神灵转变成为“人格化的对象”或者“自然的人格化”(路德维西·费尔巴哈,1845),利用咒语、神歌等手段之外,主要以人的身体动作实施巫术,以人的肢体动作与神灵相通[11],或以动作降神,或以动作媚神,或以动作驱鬼,或以动作送神。正是在这样的宗教祭祀过程中,没有从宗教仪式中分离的身体运动形式得以呈现。
具体到纳西祖先的氐羌族群,南迁定居怒江、澜沧江及金沙江并流的藏彝走廊。所谓“藏彝走廊”就是以川西高原为中心,包括四川、云南西部和西藏东部的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地区。“这些河流犹如一把把利剑,在崇山峻岭中开辟出一道道急骤下切的深沟峡谷,从而形成了该地区最具特点的地貌形态——即主要呈南北纵列的山系与无数深沟峡谷”[18]。氐羌族群生活在恶劣的自然条件、闭塞的地理环境之中,“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1],其生存、繁衍和发展对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的依赖性极高,于是形成了十分虔诚的万物有灵、鬼神崇拜意识,并由个体意识逐渐演变成为群体意识和行为。东巴跳和达巴跳包含“祭天仪式”、“祭署(自然神)仪式”、“祭风仪式”、“祭祖仪式”、“祈寿仪式”、“诞生仪式”、“成年礼仪式”、“开丧超度仪式”、“放替身攘灾仪式”等宗教祭祀仪式,这都是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文化遗存。此外,纳西地区每村每寨遍地可见的玛尼堆(石的自然崇拜)和挂有红绸的许愿树(树的自然崇拜)也是群众浓厚宗教意识的客观表现。
4.2 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仪式与身体运动内容的习得
在人类学的经典研究中,仪式通常指带有明确宗教意义和喻指性的行为。维克多·特纳凭借长期的“仪式过程”研究,提出了社会戏剧的重要概念(维克多·特纳,1974),“仪式中的范式具有一种促成欲望的功能,它既可以促使人们去思考,同样也可以驱使他们去行为”[23]。但在涂尔干的概念体系里,仪式是反映及维持社会制度结构的一种方式或手段(涂尔干,1912),“仪式有助于确认参与者心中的秩序”[21]。
综观纳西族的东巴教和摩挲人的达巴教,通常就把宗教教义融入祭祀性的身体动作中,在统一的文化语境之中构建参与者心中的秩序。例如东巴跳中的“磋姆”,是东巴教教事活动中最重要的部分,“磋姆”记载了60 个宗教仪式动作都以服务于东巴教义为目的。东巴师诵经的同时,运用肢体做挥刀劈刺、摇铃击鼓等驱鬼动作,达到降恶助善、祛灾祈福、稳定社会结构的作用。纳西族原始宗教崇拜中的图腾崇拜,也是东巴跳经常表现的内容。东巴教承认男性生殖力量的作用,将梅、禾、束、尤母系氏族的熊、蛙、蛇、猴4个图腾物父亲作为崇拜的具象符号。随着氏族部落的演进和分化,纳西族氏族分支里又增加了羊、虎、龙、孔雀、蟒、牛、鹿等图腾,这些图腾崇拜仪式最终转化成东巴跳中17种模拟动物的象形舞。
在东巴跳体系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仪式动作分支,包含金刚杵舞、刀舞、剑舞等的镇鬼武舞。镇鬼武舞的动作具有为患者祛除病魔,催眠治病的功效。参与仪式的群众在东巴师的引导下能放松紧张神经,使肌体得到快感,甚至会进入催眠状态,缓解身体的病痛。纳西族世居地区拥有现代医疗卫生条件之前,这种催眠治病的身体运动,能够解决群众医疗需求,调节社会张力,当地的东巴师也由此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可见,“东巴师-宗教信仰-巫术或仪式-信仰受众”构成了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巫师通过灌输宗教信仰,借用巫术或仪式的有效运用,构成强大的、神圣的、信仰的宗教场域,自己则成为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精英阶层,发挥着统治阶层的力量。原始先民通过接受宗教信仰,成为巫术或仪式的受众,构成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平民阶层,稳定了阶层关系和人际关系。巫术或仪式是社会结构中的调节剂,东巴师根据社会发展或统治阶层的需求,利用它调节社会张力,维护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
4.3 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秩序与身体运动规则的建构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稳定存在,离不开习俗、宗教、道德、法律等社会规范的制约和影响,于是,形成了特殊的习俗秩序、宗教秩序、法律秩序等。宗教秩序属于社会秩序的范畴,是一定的社会控制机制发挥效能的结果。正如卡尔·马克思(1883)所说:“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要摆脱单纯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12]。东巴主要采取家族世袭传承的方式,父传子或舅传甥,后辈男性自幼在其长辈的口传心授之下,耳濡目染而渐修成东巴,直到能独立主持东巴各项仪式为考核标准(明清时期的木府虽然创办了东巴学校,主要服务于纳西土司贵族,实际上并没有脱离家族世袭传承的范畴)。虽然,少数地区的东巴也招收徒弟,称为“比喳”或“哈司比”,但是,“比喳”或“哈司比”一般不识经典,亦不能主持重大的宗教祭祀仪式,只能充当东巴的助手,配合进行宗教活动。东巴作为东巴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者,掌握东巴经、东巴跳、东巴画、东巴雕塑、东巴纸、东巴服饰等东巴文化的核心要素。东巴平时参与生产劳作,也通过主持宗教祭祀获取经济收入,祛病救人获得尊重,驱灾祈福获得名利、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现代社会飞速发展,许多传统体育传承和发展都面临着青黄不接或断代的问题,很多年轻人宁愿在沿海打工也不愿学习民族本土文化,许多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体育变成了濒危项目,我们可以试图从东巴跳传承的宗教秩序中寻求答案。
现在许多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与发展还面临着传承内容逐渐萎缩的现象,它是时代发展进程中新陈代谢的结果,但是,口传心授、言传身教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不稳定的传承结构,必然会造成传承内容逐渐流失、萎缩的现象。东巴跳传承体系中的东巴舞谱对东巴跳核心文化传承就起到文本记载、符号交流、文化创新等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存东巴舞谱6卷:1)《舞蹈的出处与来历》记录了18种舞名及谱文;2)《东巴舞谱》记录了62种舞名及谱文;3)《神·祈年寿东巴舞谱》记录了30种舞名及谱文;4)《舞蹈来历》记录了17种舞名及谱文;5)《舞谱跳谱》记录了18种舞名及谱文;6)因缺封面,书名无考,记录了24种神舞及谱文。以上6卷舞谱共记录了158段谱文,除去重复,计有不同舞名及谱文的东巴跳3大类52种[2]。这些传承有序的古籍古谱是学习东巴跳的教科书,是东巴跳传承的摹本,每一代东巴都可以在参照摹本的基础上增加自己的理解,融入新的文化表现形式。此外,东巴学校的建立,东巴教义普及都为东巴传承奠定了群众基础。东巴跳与生俱来的宗教性质、强大而普及的信仰基础、稳定有序的传承结构、尊重教义基础上的时代创新等构成了东巴跳良性的生态发展方式。
4.4 少数民族原始宗教功能与身体运动功能的融合
西方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对宗教功能的强调,使人们意识到宗教对社会群体、对社会秩序、对个人心理状态的维护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托马斯·奥戴将宗教的功能分为6种“正功能”和6种“负功能”(1966),并指出宗教的功能从来就不是孤立发挥作用的,特定的宗教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发挥它的价值[22]。在国内,胡小明等学者也长期关注宗教巫术活动的功能与价值(2005),“在这类准宗教的行为中,原始人类通过经常的、大运动负荷的、高激情的活动和舞蹈客观上实践着体育的行为,同时实现了原始体育的功能”[5]。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地理环境闭塞、生产方式落后、政治格局多变、战争烽火不断的区域,往往需要一个凝聚民众的媒介,原始宗教就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样的义务。参与东巴跳或达巴跳的社会成员,无论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都有一个或几个共同崇拜的对象,形成共同崇拜的心理,强化族群成员的文化认同,群体性身体运动就构成最直接、最客观的认同表达方式。例如,东巴跳中的“窝热热”和“阿哩哩”,在祭祀祖先、祭奠亡灵等宗教仪式中,通过集体祭祀亡灵、追忆祖先的方式,表达同祖同源、血脉相依的族群认同。
现在“窝热热”和“阿哩哩”也发展成为全民健身方式之一。每一天傍晚,在纳西古城四方街广场上,许多纳西群众自发地集聚于此,参与“窝热热”和“阿哩哩”,边唱边跳、时快时慢,变换队形,成为健身性、娱乐性、群体性十足的健身方式。所以,娱神的乐舞,正是对娱人形式的补充,也是民众观赏需求的补偿,即在娱神、娱人的同时满足着群众身体与精神的内在需求。
体育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人、社会、社会关系3个层面。与宗教结缘的许多身体运动,诸如东巴跳或达巴跳,具有现代体育中所强调的运动频度、运动时间、运动强度、运动负荷等基本要素,通过长期有效的肢体运动能提升人的身体机能、身体素质和生命质量。但是,在传统社会结构里,此类具有浓厚宗教信仰和民族情感基因的身体运动,更多地体现在消除群众日常生活中恐惧、焦虑、不安的心情,满足身体和心理双重需求,发挥着慰藉群体身心,调整人际关系,调节社会张力,维持社会秩序,维护阶层利益、稳定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5 结语
原始宗教与身体运动分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一个是唯心主义,一个是唯物主义,两者却在传统社会结构里形成了合二为一的独特社会文化现象。特别是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村落,原始宗教与身体运动形成的内在逻辑值得关注:1)人类在“万物有灵”等原始宗教观念的支配下,以人的肢体动作与神灵沟通,藉此畏神敬神、祛灾祈福,是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反映,是身体运动文化形成的最初动力;2)祭祀神灵仪式中幻化神灵的祭神舞、图腾崇拜仪式中模仿动物的象形舞和驱鬼辟邪仪式中镇鬼消灾的法器舞,把原始宗教灵魂融入祭祀性的身体动作之中,涵化了身体运动的内容习得;3)原始宗教通过灌输宗教信仰,借用巫术或仪式的有效运用,构成强大的、神圣的、信仰的宗教场域。宗教信仰奠定身体运动的群众基础,经书舞谱构成身体运动的传播载体,祭祀仪式形成身体运动的有序结构,宗教融合促进了身体运动的内容革新;4)原始宗教中的身体运动能提升人的身体机能、身体素质和生命质量。但是,在传统社会结构里,则更多地体现在慰藉群体身心,调整人际关系,调节社会张力,维持社会秩序,维护阶层利益,稳定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价值和作用。
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止变革的车轮,社会变迁和进步必然会构成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正在转型,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俗化将成为宗教发展进程中的趋势,必然也会对身体运动文化产生影响。比如:宗教仪式作为旅游产品深度开发,身体运动文化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宗教领袖由传统祭师身兼旅游表演演员、文化展演名片、传统文化代言等多种角色于一体,是否会影响身体运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某些宗教仪式中的身体运动已经发展成为群众健身方式,脱离宗教的束缚后又能走多远等。总之,宗教世俗化必然将宗教仪式带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与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相互契合,是原始宗教和身体运动文化共同的期盼和憧憬!
[1]范晔.后汉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4:1260.
[2]费孝通,郭大烈.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纳西族卷)[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195.
[3]何晓明,曹流.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2-4.
[4]和云峰.和云峰纳西学论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301-317.
[5]胡小明,陈华.体育人类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82-185.
[6]胡小明,张洁,王广进,等.开拓体育文化研究的新领域——以探索身体运动对原始文化形成的作用为例[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2,36(2):1-5.
[7]蹇河沿.感受戏剧——戏剧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196-205.
[8]拉木·嘎吐萨.摩梭达巴文化[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602-608.
[9]喇明清.纳人口传“达巴经”的现状及保护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2):52-58.
[10]丽江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丽江地区志(中)[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626-628.
[11]路德维西·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M].荣振华,李金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36-499.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893-895.
[13]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M].陈观胜,李培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1-12.
[14]木光.木府风云录[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56-62.
[15]木丽春.东巴文化通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3-21.
[16]木丽春.纳西族通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84-88.
[17]邱丕相.民族传统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0-13.
[18]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34.
[19]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52-154.
[20]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412.
[21]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初级形态[M].林宗锦,彭守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518-528.
[22]托马斯·奥戴.宗教社会学[M].刘瑞忠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6-33.
[23]维克多·特纳.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M].刘珩,石毅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1-52.
[24]巫瑞书.简论巫与巫歌巫舞的产生演变[J].民族论坛,1987,(1):78-81.
[25]向有明,向勇,韩海军,等.身体动作和文字形成的双向实证研究[J].体育科学,2013,33(8):57-63.
[26]杨帆.“南方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它相关问题[J].中华文化论坛,2008,(2):38-43.
[27]杨士宏.我国古代氐羌族群的原始文化形态探微[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66-73.
[28]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云南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谚语集成(云南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2002:762.
[29]中华舞蹈志编委会.中华舞蹈志(云南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870.
CulturalEcologyAnalysisofMinorityPrimitiveReligionandFormationofBodyMovementCulture——FieldInvestigationReportonDongbaDanceandDabaDance
WAN Yi1,2,WANG Jian2,LONG Pei-lin1,BAI Jin-xiang1,YANG Hai-chen2,WANG Tao2
Naxi;Mosuo;Dongbadance;Dabadance;culturalecology

1000-677X(2014)03-0054-08
2013-08-19;
:2014-01-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0CTY005);国家体育总局民族体育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2jdz6037)。
万义(1977-),男,湖南张家界人,讲师,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体育与文化,E-mail:wanyi2007@163.com;王健(1963-),男,河南南阳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E-mail:jwccnu @163.com;龙佩林(1964-),男,苗族,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传统体育学,E-mail:lpl45102@163.com。
1.吉首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2.华中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1.Jishou University,Jishou 416000,China.;2.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G80-0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