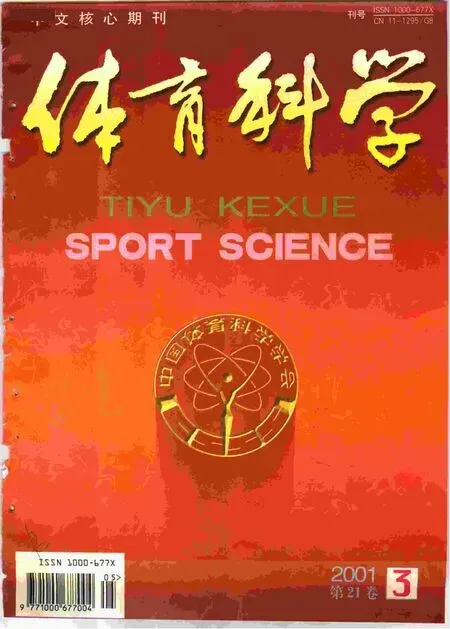中国古代体育竞赛的历史文化研究
——以先秦射礼竞赛为例
张 波,姚颂平
中国古代体育竞赛的历史文化研究
——以先秦射礼竞赛为例
张 波1,姚颂平2
通过对先秦两汉88部原典著作的全文检索以及部分甲骨文、金文资料,考察先秦时期的射礼竞赛,并从体育竞赛构成条件——参赛者、裁判员、竞赛场地、竞赛规则、竞赛结果的角度,对射礼竞赛进行了历史梳理和意义解读。研究认为,中国商代已出现射礼竞赛的雏形,至两周时期发展为与当代体育竞赛性质相同的射礼赛会,其兴盛程度不亚于古希腊竞技会,甚至不输当今体育赛事;其人员、场地、器具、规则完备,竞赛组织化程度高,文化教育价值丰富。从儒家哲学思想中提炼出的“以德引争”竞赛观,可以展现中国古代体育竞赛的文化特质。
体育史;先秦时期;体育竞赛;射礼赛会
:Through the Pre-Qin and Han 88 Texts works full-text search and some Oracle,Jin data,this paper focuses on Chinese Archery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analyzes the history meaning of Chinese Archery constitutes conditions:participants,the referee guard,competition venues,contest rules,contest results.The result shows that it already appeared prototype archery competition in Shang Dynasty,until Zhou Dynasty,archery competition has developed to the same nature of morden sports competition.After it become into a tournament,its flourishing was no less than the ancient Greek athletics,even today's sporting events.Its personnel,venues,utensils,rules and complete contest come into a high degree of organization,rich i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values.The concept of "Courtesy competition" abstracted from Confucian philosophy can show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Chinese sporting competition.
1 前言
现代体育竞赛基本是按西方的定义被认识和理解的,古希腊竞技会是其源头。那么,中国古代有没有体育竞赛?如果有,其存在的历史时期、规模以及文化价值是什么?聚焦先秦射礼竞赛来回答这些问题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另一个出发点在于:从体育竞赛视角切入的体育竞赛史研究几乎属于空白。笔者以“体育竞赛”为主题进行了文献检索,截至2013年6月5日,体育竞赛研究较多,但加上一个“史”字之后,相关研究极少。体育竞赛史不同于单项运动史的研究,更注重一些共性的构成条件,如参赛者、裁判员、竞赛规则等,这些构成条件可以打通古代与现代的通路,在古今之间进行比较和对话,从而进一步丰富体育史研究视域。
何谓体育竞赛?综合各家对体育竞赛和运动竞赛的定义,本研究对体育竞赛的操作性定义是:有组织的竞争性身体活动。本研究使用“有组织”一词来指称各种不同的组织方式。古代体育竞赛的组织方式可能非常简单,只有一两条规则即可。只要人们建立起规则并遵守这些规则,便会产生丰富的社会意义,并构成一种文化现象延续下来;“竞争性”是界定体育竞赛的另一个种差。体育竞赛中的“竞争”不同于出自本能的身体较量,如因利益或者利害关系而表现为身体冲突的打斗以及战争。体育竞赛中的“竞争”体现了人类如何将攻击性本能导向“文明社会”的和谐秩序之内,有一种“文明教化”的功用,这也是体育竞赛的独特之处。
体育竞赛的构成条件。在《运动竞赛学》一书中有体育竞赛构成条件的一种说法,叶庆晖博士也引用了此说法:“任何一项运动竞赛的活动,都需要由参赛活动人群、竞赛活动物质条件及竞赛活动组织管理这3个系统所组成”[12];肖林鹏在研究体育赛事时也提出了同样的说法:“体育赛事一般由参赛活动人群、场地物质条件及比赛组织管理等3个基本系统所组成”[10];王亚琼所编的《运动竞赛学》同样强调以上3个方面,即过程规则、场地设施、组织者和参加者[9]。史国生则在以上3方面基础上增加了竞赛保障和媒体宣传作为竞赛的构成要素[7]。显然,后两者是从现代体育竞赛的角度出发的。综合诸家观点,本研究认为,体育竞赛的基本构成条件为:参赛者、裁判员、竞赛场地、竞赛规则、竞赛结果。竞赛规则主要是指如何开展竞赛,即比的是什么,以及怎么比。竞赛结果是指如何来判定胜负。
根据体育竞赛的种差界定和构成条件,集中考察中国先秦时期的射礼活动是否构成体育竞赛,并分析其构成条件的文化特色。在史料选取时,注重实证性材料的考察,主要对象是先秦、两汉时期留存下来的古典文献,另外,结合各种出土文物,如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研究通过网站“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中所收集的88部原典著作进行关键词检索,再对照出版物逐条核对。在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体育竞赛构成条件的角度分别展开对射礼竞赛的历史考察,分析射礼竞赛的文化特色。本研究立足于儒家思想观念,通过“意义诠释”的方法[14],解读先秦射礼竞赛的社会意义和哲学内涵,诠释古代体育竞赛的文化意义。
2 射礼竞赛的构成条件分析
2.1 参赛者——从贵族到精英
射礼竞赛中最早出现的参赛者是柞伯、小子、小臣,在西周早期的柞伯簋铭文中有记载。周王举行大射礼,柞伯10次举弓,10次射中,获得了周王十钣红铜的奖赏。据袁俊杰博士的考证,柞伯簋是西周早期康王时代的产物[13],其中的柞伯应该是有史料记载的较早参赛者。早期参赛者的历史意义在于他们的身份,柞伯是当时较大的贵族,其他参与者小子、小臣都是贵族及其子弟。其他西周青铜器所载与射礼竞赛参赛者相关的史料均为贵族,如令鼎铭文中的职官和小子;噩侯鼎铭文中的驭方和周王;长甶盉铭文中的邢伯和大祝;静簋铭文中的王、职官等。从众多史料中可以确知,早期的参赛者都是贵族身份,后来到了礼乐文化盛行的时代,大射礼、宾射礼、燕射礼和乡射礼等赛会成为定期举行的大型社会活动,就像今天的全运会一样。参赛者的身份也从最高的统治阶层扩展到社会的中坚力量,尤其是以乡射礼为代表,参赛者扩展到整个“士阶层”。
从参赛者的角度看,射礼竞赛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最早的参与者是王和贵族。随着射礼竞赛社会教育价值的凸显,更多的社会精英加入到射礼赛会中。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思想活跃,社会统治力量越来越多地依靠政治精英而非血统贵族。这些思想家的政治理想需要上通下达,射礼是一种非常合适的社会性活动,既能教育贵族子弟,又能影响社会中坚力量——“士阶层”。因此,射礼赛会自然与实现培育君子的政治理想相融合,参赛者需要具备“其争也君子”的道德品质。当时的社会精英如孔子,便亲身参与过射事。《礼记·射义》篇载:“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2]。
体育竞赛在早期只能在社会闲暇相对充裕的贵族内部展开。这种贵族内部开展的特性为射礼竞赛成为礼仪道德教育的社会性活动创设了条件。当“出身贵族”让位于“知识贵族”时,射礼从祭祀中的仪式转化为通过赛会的形式来教化社会精英、培育君子的社会活动。这也是射礼竞赛能够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兴盛的重要原因。
2.2 裁判员——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融合
体育竞赛中的裁判员相对专业,而且更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活动和娱乐活动的特点。先秦射礼竞赛明确设有裁判员这一角色,这也是认定其体育竞赛性质的原因之一。最早的史料是西周中期穆王时代的静簋铭文,“王命静司射学宫”。“静”的身份是小臣。“司射”便是“静”的职务,即掌管射礼事务[13]。司射的身份在西周早期很难界定,既有主持的意思,又有裁判的意思,还有教官的意思。在后来的礼书中,司射主要是裁判射礼竞赛的角色,而且在整个赛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仪礼·乡射礼》篇为例,“司射”共出现63次,是整篇中出现最多的角色。另一位重要角色,即主持性质的“司马”仅出现39次。《大射》篇中“司射”出现44次,同样是最多的。“司射”作为裁判员不仅要在竞赛中多次亮相,而且要熟谙礼法。“司射”这个角色一般由“射人”充任,“射人”在《周礼》中的解释为:“掌国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以射法治射仪[6]。“射法”即射箭的技术性操作,“射仪”即射箭的精神性内涵,这说明中国古代最早的裁判员要能文能武。
在乡射礼中,司射确实需要亲自进行诱射,即给所有的参赛者示范怎样进行射箭才是符合礼仪的,这对裁判员的专业素养要求是极高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射礼竞赛的发达程度。总体而言,先秦时期体育竞赛的裁判员已经发展到了专业化的阶段,不仅要公平执法,而且要精通所执法项目,与今天的裁判员别无二致。不同之处在于,当时的裁判员更需要领会规则背后的理论基础,即“以射法治射仪”。
2.3 竞赛场所——学校之源,育人之地

此外,不仅射礼竞赛的场所存在一定的延续性联系,射箭场所与学校同样渊源深厚。《孟子·滕文公上》对于这种延续性有明确记载:“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16]。三代时期的学校有着明显的延续性,虽然叫法不同,但功能一致。不仅如此,商代的“序”作为学校,主要是开展射的地方,所谓“序者,射也”。通过这种文献之间的前后联系,可以推断,射箭竞赛的场所与学校同源,而且“射”也确实是“六艺”之一。既然学校在三代有明确的延续性,那么,射箭场所同样有历史延续性。因此,笔者认为,周代射礼竞赛场地是从商代发展而来,且自产生之日起便与教育密不可分。
体育竞赛开展的场所与学校合二为一并非偶然,亦不足为奇。古希腊的竞技场同样也是古希腊哲人教育民众的最佳场所。根源在于体育竞赛的社会性,在我们界定体育竞赛的概念时,已经指出这一特性。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将大众在同一时间内聚集到同一场所,而且,不管是参赛还是观赛,体育竞赛都是一种集体性的活动,人们会有一种更为专注的投入。这也是对人施加教育影响的最佳机会,因此,中、西方才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体育竞赛场所作为教育之地。射礼竞赛场地与学校的同源助推了射礼竞赛的兴盛,也使其占据了更多的历史篇幅。
2.4 竞赛规则——社会观念的投射
射礼竞赛最早的规则可追溯到商代末期甲骨文中的“亡废矢”,即全部射中而没有未射中的箭。根据袁俊杰博士的考证,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的卜辞中有一个词“不”,意思说的是“无废矢”[13]。另外,商代末期的青铜器——作册般铜鼋,刻有“王射,射四,率亡废矢”的铭文[1]。在西周青铜器柞伯簋铭文同样有“无法(废)矢”的记载,意思是箭无虚发。宋镇豪先生认为:“此器用语‘无废矢’,与晚商铜鼋铭文相一致,也是射礼场合班赞品论竞射优胜的评语”[8]。由此可见,两处青铜器与甲骨卜辞中的记载有着内容上的一贯性。这表明,在商代已经出现了专门用于表示竞赛的规则,即无废矢。
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出土的卜辞中,还有一个关键词可以向我们展示当时竞赛规则的专用语,即“获”字。“获”在商代卜辞中多次出现,成为一种表达射中的专有名词。到了后来的射礼赛会中,如《仪礼》所载,“获”字也确实用来报告比赛的结果给所有在场的人听,而且专门设有“唱获者”这一角色[5]。至西周时期,射礼竞赛发展出了一套更为完备的规则系统,具体表现在“三番射”中,即第一番射,只报告结果,但不计数;第二番射开始计算射中个数,规则为“不贯不释”[5],意思是射中但没有贯穿箭靶的也不计数;最为精妙的环节在第三番射,要求匹合音乐进行射箭,既考虑射中,又增加了是否与音乐合拍的规则。整个“三番射”是一种通过规则设计,实现参赛者精神升华的过程。先秦文化的精髓在于“礼乐”,孔子说:“立于礼,成于乐”[3]。《礼记》中有“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2]。之所以第三番射要配合“乐”,原因在于对人内在品德的培育。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理性启蒙的活跃期,因而,人在合礼仪方面的道德修养是一个亟需解决的社会议题。在这种社会观念背景下,射礼竞赛中的规则设计自然也就投射出了当时整体的社会制度设计理念。
2.5 竞赛结果——通过公开保证公正
分出胜负是体育竞赛不同于一般社会活动的另一特点,给出一个明确的竞赛结果,能够进一步激发人们参与这项活动的兴趣。射礼竞赛不仅即时给出竞赛结果,而且更加突出公开性原则。商代射礼竞赛虽然有了“获”这样专门表达射中的语词出现,但并没有判断胜负的概念出现。从现有史料来看,最早明确给出竞赛结果的射礼竞赛出现在西周时期,如柞伯簋铭文中,柞伯10次举弓射箭,10次射中,没有作废的箭。于是周王把十钣红铜奖给了柞伯[13]。噩侯鼎铭文中,驭方和周王射箭,二人都未射中,依礼均饮罚酒[13]。比射之后往往都会有奖励一同出现,这就更加意味着比赛的结果必须马上给出,否则无法奖励。从史物的记载看,西周早期射礼竞赛的结果是以能否射中目标以及谁射中的箭数多来判定胜负的。
此后,东周时期的竞赛结果开始出现标准化。据《仪礼·乡射礼》记载,主宾分成两队,每队三人,匹配成三耦,每人轮流射四支箭,最后计算射中个数[5]。对于竞赛结果的计算也有一套标准系统:专门设有“唱获者”高声报出是否射中目标,另外还专门有“释获人”,每射中一矢,放一枝筭筹在地以计数。最后,“释获人”在主裁判的监督下计算总数并宣布最终结果。整个竞赛结果的产生具有极高的透明度,符合公开性的原则。只有结果的公开,才能保证竞赛的公平。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这种竞赛结果的公开性已经被发挥到了极致,不仅有专门的人、专门的工具来展示结果,而且要让在场所有人都能够听到,同时还有裁判员的监督。就射礼竞赛结果的历史意义而言,通过竞赛结果的公开保证了竞赛本身的公正,从而使得这种体育竞赛能够在当时推行。
2.6 小结
射礼竞赛在中国古代是典型的有组织的竞争性身体活动。这种竞争性最早的目的是用来选拔人才或其他政治用途,后来竞射演变为一种意义更为丰富的社会活动。到了“轴心时代”①“轴心时代”是由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的概念。他指出,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在北纬30度上下的不同地区,同时出现了人类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古印度的释迦穆尼以及中国的诸子百家等,这些人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被孔子等先贤加以改造利用,其中的原始意义慢慢退去,“礼”的意义逐渐增多。出于“礼”在仪节上的要求,射礼竞赛的组织化程度极高,程序也越来越完备,最终发展为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射礼赛会,并盛极一时。中国古代体育竞赛的文化精髓在射礼竞赛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争也君子”是代表。本研究将专门围绕射礼竞赛的历史文化意义,探究中国古代体育竞赛的独特文化内涵。
3 射礼竞赛的历史文化意义
3.1 “三礼”中射礼竞赛的教育意义
“三礼”是指《周礼》、《礼记》和《仪礼》3本记载古代社会政事的经典文献。当时的政治制度设计主要围绕“礼”来展开,所以,这3本文献的,学术价值极高。“三礼”中,“射”字出现503次,其中,属于射箭意思的493次。专门记载西周礼仪的《周礼》一书,将“射”纳入“六艺”。从“三礼”中,可以看出射礼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文献记载中,可以确证,射礼曾经作为一种典型的竞赛形式出现。《仪礼·大射》篇记载了规格最高的射礼竞赛,一般由君王亲自主持,很多时候王亲自参射。“大射”最初的主要目的是选拔诸侯,《礼记·射义》说:“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2]。在比射选拔的过程中,更容易看出一个人技术以及技术之上的综合能力,因而,才受到“圣王”的重视。从选贤的比射中,也可以更加清楚地确认射礼的竞赛性质。
最初射礼竞赛的目标是选拔人才,后来教育的价值越来越被看重,并推行到整个社会中。尤其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大射礼的规格降低,乡射礼兴盛起来。射礼竞赛从上层社会逐步推广到整个社会中,用于教化民众。《周礼》中有“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6]的记载,到了“乡射礼”之时,射礼作为一种竞赛形式已经普及到了整个社会中,如乡、州等社会基本构成单位,参与者也主要是大夫、士等阶层。
射礼赛会能够发展到如此高的组织程度,与其较高的教育价值有紧密的联系。当时的射礼竞赛兼具社会教育意义和个人教育意义。《礼记》专门有《射义》篇,其中记载:“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2]。中国文化传统强调的等级有序渗透于射礼赛会之中。不同等级身份的人,采取不同的器具、不同的距离行射,奏不同的音乐,以明尊卑有别之理;在同一个等级内,大家是公平竞争的,但仍要相互之间行礼以表示尊重。整个赛会本身是一场很好的教育展示会。同时,对于个人而言,射礼竞赛可以培育人的君子之德。在《射义》篇中记载:“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2]。射箭这种静力性的体育竞赛,不同于跑步等动力性的体育竞赛,它更需要人内在的专注,而不是外在的力量释放。因而,它更容易通过内在的专注实现一种精神的修炼,当你能够表现出一种“内志正,外体直”的状态时,不仅容易射中,同时也是一种德行的表达。
3.2 射礼竞赛仪程中的文化特色
《仪礼·乡射礼》篇中记载,比赛分为主宾两队进行,共进行3轮竞赛,即“三番射”,每轮每人射4支箭。整个竞赛的组织化程度非常高,完全可以用现代意义的“赛会”来称谓。整个射礼赛会的规程有32项之多,我们将其归纳为9个阶段,射礼竞赛的礼仪特色尽显其中。
第1阶段:邀请和准备工作。1)邀请:“主人戒宾,宾出迎。主人答再拜,乃请”;2)布置场地:宾接受邀请后,“乃席宾”然后布置洗、侯、乏等。乡射礼由主办方邀请宾参加,类似于今天的邀请赛。
第2阶段:开幕式。3)宾入场:“主人朝服,乃速宾。宾及门,主人一相出迎于门外。”主宾三揖三让之后入场;4)行燕礼:此一程序主要是揖让敬酒、作乐等礼仪;5)运动员就位、主裁判(司射)入场:“三耦(三对射手)俟于堂西。司射升自西阶,曰:‘弓矢既具,有司请射’”。开幕当天,主人需再次去请宾,相互行礼,入场同样需要多次行礼,处处体现着先秦时期文明礼仪之发达。
第3阶段:赛前准备。6)器具准备:“司射命弟子纳射器”;7)主持人(司正)入场:“司正为司马,司马命张侯。”司马由主办方选人,兼副裁判之职;8)运动员就位;9)主裁判诱射:“司射东面立于三耦之北,揖进;当阶,北面揖;及阶,揖;升堂,揖。当左物,北面揖;及物,揖。诱射”。“物”是指十字标识的射位。这一阶段,裁判员的诱射环节极具特色。司射在诱射过程中作揖6次,可见礼数之细。
第4阶段:预赛。10)第1轮射者就位:“上耦揖进,上射在左,并行。上射先升三等,下射从之,中等。上射升堂;下射升,上射揖,并行”;11)主裁判宣布注意事项:“司射命曰:‘无射获,无猎获!’”意思是不要射伤获者,不要惊扰获者;12)比赛开始:“上射既发;而后下射射” ;13)助理裁判报告结果。“获者坐而获,获而未释获。”此番射中只高声报获,而不计数;14)第2、3轮射者依次比射。对阵运动员入场时,极为注重礼节,即孔子讲的“揖让而升”。另外,在射仪上也有很高的要求,《周礼》记载:“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6]。《论语注疏》中进一步解释为:“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体和;二曰和容,有容仪;三曰主皮,能中质;四曰和颂,合《雅》、《颂》;五曰兴武,与舞同”[3]。由此可见,射礼竞赛完全体现出礼仪化的特点。
第5阶段:正赛准备工作。15)裁判员准备:“司马命弟子设楅(古代插箭的器具)”;16)射者入场;17)主裁判宣布规则:“司射升,请释获(计算射中个数)于宾,宾许。北面命释获者设中(放筹码的容器),曰:‘不贯不释!’”这一轮的规则是不射穿箭靶不计算个数。由此可见,射箭竞赛在当时对于身体力量还是有一定要求的,虽不像“贯革之射”那么推崇竞力,但其体育竞赛的性质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与后来的投壶礼在性质上有所不同。
第6阶段:正赛。18)正赛开始;19)裁判员计算结果:“司射北面视筭,释获者东面于中西坐,先数右获”;20)宣布比赛结果:“释获者遂进取贤获,告于宾。若右胜,则曰:“右贤于左。”若左右均,则曰:“左右均”;21)饮罚酒。司射命三耦及众宾:“胜者一方皆袒左臂,手持上弦之弓。不胜一方穿好衣服,右手把解弦之弓。”胜者先上堂,然后不胜者上堂,站着干杯;22)答谢助理裁判。“司马洗爵,献获者于侯。司射献释获者于其位。”正赛中出现了饮罚酒的阶段,这种对于竞赛结果的奖惩办法极具特色。负者仅仅是象征性的饮酒惩罚,而胜者的奖励纯粹是一种荣耀,这将体育竞赛的目标定位到一种精神追求。
第7阶段:配合音乐的比射。23)第3番射:“司射请以乐乐于宾,宾许”;24)宣布规则:“司射北面命曰:‘不鼓不释!’”,意思是射箭凡不与鼓节相应者则不释筭;25)比射:“司射退反位,乐正东面命大师奏《驺虞》”;26)计算结果:“释获者执馀获,升告左右卒射,如初”;27)宣布结果:“司射释弓视算,如初;释获者以贤获与钧告,如初”;28)饮罚酒:“司射命设丰,如初;遂命胜者执张弓,不胜者执弛弓,升饮如初”。本轮竞赛,是对射者最高的要求,也是体现礼乐文化的独有规程。
第8阶段:竞赛结束。29)收拾比赛用具:“司射命拾取矢,如初”;30)收拾场地器材:“司马命弟子说侯之左下纲而释之,命获者以旌退,命弟子退楅;司射命释获者退中与算。”
第9阶段:宴饮。31)酬酒:“宾北面坐,阼阶上北面酬主人。主人以觯适西阶上酬大夫。若无大夫,则长受酬,亦如之”;32)互敬酒:“众受酬者拜、兴、饮,皆如宾酬主人之礼”[5]。
整个赛会有始有终,过程仪节极为复杂,竞赛性质明确。专门设有主持人员、裁判团、工勤人员等,规则极为细致,设有专用器具计数。不仅有公开的结果宣告,而且对参射者还有仪容方面的要求,乃至精神道德层面的规范。可以说,整个竞赛的组织程度较高。通过竞赛程序的完备,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体育竞赛盛况,丝毫不亚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竞技会。
3.3 儒家哲学观念与“射”的“以德引争”
有关“射”的记载,在中国先秦时期非常之多。在本研究所考察的20本儒家著作中,共出现448次。在诸多记载中,通过两个直接与孔子有关的事件,探究孔子本人看待“射”的不同视角;另外,通过孔子的两段文本,力争诠释出儒家对于射礼竞赛的哲学认知。
事件一:《论语·子罕》篇有“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3]。当有人说孔子博学但没有专长时,孔子说,自己应该射箭还是驾驭马车呢,还是马车吧。笔者认为,孔子这是一种自嘲式的说法,并非说他善于驾车,并能够靠驾车来成名,即他并非以技术性专长来要求自己。另有记载“孔子曰:‘若夫不肖之人,则彼将安能以中?’”意思是:如果是无德无才的人,那他怎能射中[11]?可见,在射和御这类活动中,道德层面的要求较之技术层面的要求更高。
事件二:《礼记》中也记载了一段孔子与射的故事。“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射至于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曰:‘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其馀皆入。’盖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觯而语,公罔之裘扬觯而语曰:‘幼壮孝弟,耆耋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盖去者半,处者半。序点又扬觯而语曰:‘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旄期称道不乱,者不?在此位也。’盖仅有存者”[2]。从这段故事可以看出,孔子之时,礼崩乐坏,从礼尚德者,“仅有存者”。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射事本身有着较高的礼仪道德期待,已经延伸到了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方方面面。
文本一:《论语·八佾》篇中有一段记载影响颇深:“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3]。“主皮”的意思是射穿甲革,强调的是力量。这一段中出现了对于体育竞赛来说极为重要的概念——“力”。射箭作为一项身体活动,是力量与技术的结合,尤其在历史的早期,更为强调力量,如“主皮之射”、“贯革之射”等。后来,出于道德和礼的需要,射箭被发展出了另一种“力”,即区别于主皮射之力的“礼射”之力。虽然仍然需要有力量,但重点已经不在身体力量上,而是道德之力。儒家哲学对于射礼竞赛进行了精神上的提升,甚至完全压过了身体层面。
文本二:儒家文本中与射礼有关、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论语·八佾》篇:“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3]。后世文献对此段颇多引用,这里两次出现“争”的概念。这个概念源自人类对于资源(土地、食物、异性等)占有的本能,后来发展为对人性中一种“比”的心理情结以及这种心理情结所产生的社会后果的深刻认知和综合概括。此段文本表达了对于“争”的综合认识,“其争也君子”,将“争”导向君子之“德”的理想状态。宋代朱熹注疏此段说:“言君子恭逊不与人争,惟于射而后有争。然其争也,雍容揖逊乃如此,则其争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争矣”[16]。“君子之争”已经是中国文化直到今天被广泛认可的概念,笔者认为,其用于表达中国体育竞赛的内在精神极为适用。体育竞赛的竞争不仅注重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过程的价值。对于君子品性的修炼可以与不断超越,取得冠军的价值并行不悖,在尊重对手、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取得的冠军才是最高的荣耀。笔者将“君子之争”提炼为“以德引争”来表达中国古代体育竞赛的文化特质。
儒家关于射礼竞赛的记载中,不仅孔子强调精神层面的道德力量,其他先贤同样如此。《孟子》中有这样的记载:“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4]。这段话是孔子说的,但收录在《孟子》中,至少说明孟子对这一观点的认同,也更能反映出这种思想在儒家思想中的经典性和广泛性。而且《礼记·中庸》篇有:“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2];《射义》篇有:“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然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2]。这种“反求诸己”的思想实际上是对前面“君子之争”的完美诠释,君子之间的“争”和“比”,不会产生“乱”,因为“反求诸己”只能造成自我精神道德的升华。因而,孟子说:“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4]。身体的力量只能决定能否射到目标;射中目标的“力”是“圣,譬则力也”[4],意思是说,内在精神力量决定能否射中目标。对于道德层面“圣”的理解能够产生一种“力”,这个“力”的概念有形而上的成分,是一种精神力量,这才是应该追寻的终极目标。在《荀子》中同样有许多这种隐喻,《劝学》、《儒效》、《王霸》、《正论》篇中都有将射御一并用于隐喻为人为政之道。
中国古代曾经出现过跑步、角力这种力量型的体育竞赛形式,但并未进入到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相形之下,射礼竞赛却在儒家的思想论述中大量出现。通过对儒家思想文献的解读,可以发现,儒家之所以能容纳射箭这种静力性的体育竞赛项目,原因在于:射礼竞赛与当时的社会思想观念产生了有机的融合。射礼属于静力性项目,需要内在的专注,其实质是对自我的控制,因而,很容易将竞赛的胜负归因于自我,不会像动力性的项目容易诱发攻击性的冲动,即儒家所最为忌讳的“乱”,这也是儒家“秩序情结”[15]产生的心理根源。儒家思想家深刻地认识到“争”作为一种生存本能,不可能去除,只能引导,所以才创造性地从射礼竞赛中提炼出“其争也君子”。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射礼竞赛带着一种“以德引争”的文化色彩留存于中国历史中。
4 研究结论
中国古代有没有体育竞赛?就本研究所涉及的史料而言,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表明,中国古代的射箭活动曾经以竞赛的形式出现过。
其存在的历史时期如何?通过对先秦射礼竞赛的历史考察,其竞赛场地和竞赛规则雏形出现于商代末期,其他构成条件至西周时期发展完备。
其规模如何?西周时期的社会生活中,上至天子,下至卿大夫、士各个阶层,都会举行射礼赛会。记载于东周礼书中的大射礼、宾射礼、燕射礼和乡射礼的规模丝毫不亚于古希腊的竞技会,甚至不输当今体育赛事。
文化价值何在?先秦是中国文化的启蒙时期,经历了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伴随此进程,体育竞赛萌生并发展兴盛,其历史文化价值在于:残酷的生存之争被纳入社会秩序中的德性修养之争,表达了人类开始以道德的方式来面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与世界。在对射礼竞赛的历史研究中,可以看到中国先人对于原始蒙昧文化的超越和突破,即用人类理性的“德”来疏导自然本能的“争”,这也是儒家哲学思想的精华之一。本研究将这一思想提炼为“以德引争”来表达中国古代体育竞赛的历史特色与文化内涵。
[1]李凯.试论作册般鼋与晚商射礼[J].中原文物,2007,(3):46-50.
[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史国生,邹国忠,体育竞赛组织与管理[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宋镇豪.从新出甲骨金文考述晚商射礼[J].中国历史文物,2006,(1):10-18.
[9]王亚琼.运动竞赛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0]肖林鹏,叶庆辉.体育赛事项目管理[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
[11]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2]叶庆晖.体育赛事运作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3.
[13]袁俊杰.两周射礼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0.
[14]张波,姚颂平.中国体育史学的方法论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3,28(1):56-60.
[15]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社会学诠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6]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StudyontheHistoryandCultureofAncientChineseSportsCompetition——FocusonChineseArcheryCompetitioninPre-QinPeriod
ZHANG Bo1,YAO Song-ping2
sportshistory;pre-Qinperiod;sportscompetition;archeryrite;courtesycompetition
1000-677X(2014)03-0076-06
2013-09-26;
:2014-01-28
张波(1981-),男,山东潍坊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史、体育社会学,Tel:(021)67703708,E-mail:zhangbo20042008@163.com;姚颂平(1947-),男,江苏常州人,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体育竞赛学,Tel:(021) 51253003,E-mail:yb@sus.edu.cn。
1.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 201620; 2.上海体育学院,上海 200438 1.Shanghai Uin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1620,China.2.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G812.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