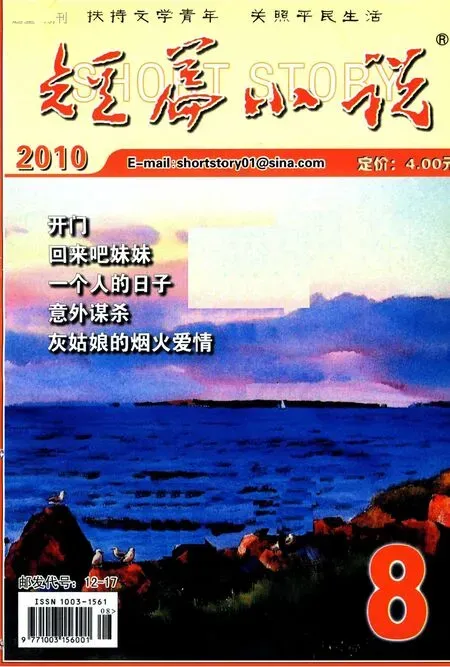养女
◎未 止
养女
◎未 止

一
她刚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饺子,五块钱二十个,很实惠味道却很一般。
今天之前她从没在街角这家店吃过饭。她每日都要从这家店门前走过两次,早晨上班一次,下午下班一次。每次经过这家店她都会扭过脸看着店铺里那个女人映着热腾腾的热气的脸庞,大多数的时候她看到的只是一个侧脸或者一个后背。女人并不窈窕,脸上密密的一层皱纹,嘴角总是下意识地抿着。女人倒是生了一头好发,乌黑浓密,只是随便地扎了垂在肩膀上,乍一看过去倒以为是一川黑森森的流水。
今日下班回家她下意识地朝店里看过去,女人这时也正好转过身来,两人的目光就这样直刺刺地相遇了,她愣住了,不由停了脚步。女人的眼神很空洞,只是那样扫了她一眼,像是看见了她,又像是直接越过她看向某个不知名的地方去了。女人把手搁围裙上擦了擦,就那样微微扬着下巴睨着她,说不出那目光里到底有着什么,她一遇到那目光整个人再次呆愣住,继而满腔的怒气噌噌地从胸口往外冲——她分明在挑衅她。瞧不起她么?又是为了什么?她们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她自嘲地笑了一下,觉得自己神经质得可笑,这一两年她愈发神经质了,尤其是待在家里,总觉得压抑得胸腔都要炸开一般,偏偏每日都要带着一张脸笑。
就这样她进了店,女人转过身继续忙自己的,并不看她。
家在七楼,她没有坐电梯,一层一层地慢慢爬上去,脑子里不时掠过一些乱七八糟的思绪。邱何是她妈妈,听说已经结婚了,过得很好,她听着也并没有多大的感伤。以前邱何还在这个家里时,总是趁她玩玩具时打量她,一脸犹疑不定的警惕,像是一只竖着毛但拿不定面前是敌还是友的老猫。大多数时候,对她还算好,但也都相当敷衍。邱何是一个喜怒不定的女人,随时都会炸雷一样跳脚,下一刻却又能安安静静地看着窗台出神。邱何心情好的时候喜欢给她梳头,但她的头发稀稀疏疏的,泛着黄,梳着梳着邱何火气就上来了,说她一点儿都不像她,直扯得她头发生疼,胡乱地给她扎两个小鬏鬏了事。
邱何给她买过很多书,童话故事、漫画书、女生杂志,都是些女孩子看的王子公主类型的书。她最近总是会想起邱何。邱何离开这个家时,她只有九岁。
“宣宣——”邱何看着她,居高临下地,开始目光里还带着一贯的那几分探究和几分警惕,又冷又厉,像是直捅向人心窝的一柄薄薄的利刀子,闪着寒光。但后来她的眼眶真的就湿了起来。姚宣宣那时候还是小小的一点儿,仰着脸看着她。邱何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看见的只有她的那两个大大的倔强的眼睛。她感觉到姚宣宣伸出小小的手爪儿扯着她的裙摆,一脸怯懦,心间方才氤氲出的那一丝怜惜瞬间冷了下来,看也不再看那小小的一团儿,抱着东西转身就走了。
姚宣宣笑了起来,微微地扬了扬下巴颊儿。每次想到邱何当初离开时的样子,她都习惯性地做出这样的动作。
推开门果然见他靠在沙发上看报纸,戴着厚框的眼镜。听到声音他从眼镜上方看着她。
姚宣宣不自觉地皱了一下眉,旋即扯出一张灿烂的笑脸,一边换鞋一边道:“爸,你还没吃吧?”
姚之城垂下眼睛继续看报纸,脸色淡淡的。
姚宣宣的心头突突地跳了两下,站住脚步冷冷地看着他,也不说话。
姚之城终于抬起头,含糊沙哑的声音道:“宣宣,你们公司今天加班?”
“没有加班。”姚宣宣垂下眼睛,淡淡地道,存着一分的狠心,就要看他待要如何。
“怎么?我还不能问问你?你现在就开始嫌我了?小时候我把你养大,都没嫌你,现在才叫你养了两年,你就开始嫌了?”姚之城的声音也不沙哑了,一声比一声高,蹦出的每个字都像是敲在了冷硬的铁块儿上。
姚宣宣顿了一下,无力地看向他,慢慢地笑开:“爸,你还是这个脾气。我妈都被你气走了,你还不改改性子?”
姚之城余怒未退,也不看姚宣宣,只把报纸翻得哗哗啦啦作响。
姚宣宣做了吃的,端到他面前,嘻嘻地腆着一张脸,笑道:“爸,你怎么还跟个小孩一样,这么爱生气。”
姚之城还是不说话。
姚宣宣的眉头下意识地皱了一下,旋即又是一脸笑容,在他旁边坐下,扯着他的胳膊,几分撒娇地道:“爸,你都多大年岁了啊,还小孩子脾气。”
姚之城笑了起来,紧绷的面庞慢慢地舒散开来,抚着姚宣宣的头发,骂道:“你这个小妮子,你以为我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被你哄住了?”
姚宣宣忽地低着头笑了起来,忍不住地。方才冰凉空荡的心房也在这一笑之下慢慢地温暖柔软起来,生活满满的。
二
姚宣宣昨夜跟姚之城说今日有一个喜欢的电影上映,下班后要去看。脸上的笑容还没来得及绽得十分开,姚之城却不咸不淡地怪声怪气一笑,拿眼睛觑着她,问:“跟谁一起去啊?”
姚宣宣本来还笑着的脸立时冷了下去,像是骤然冻住的寒冰还倏倏地冒着寒气。抱着胳膊直着身子挑着眉冷睨着坐在沙发上的姚之城。
姚之城也意识到姚宣宣的不高兴,神色间有些紧张,但还是跟着也寒了脸,沉声道:“怎么,把你养大了,翅膀硬了,知道给人脸色看了!早知道你长大是这样,小时候就该掐死你算了——白教我操心受罪,还不落好!”
姚宣宣抿着嘴唇定定地垂着眼睛看着姚之城,任他说完,方冷声一笑,扭身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门还能听见姚之城在外面摔得东西砰砰作响,叫叫嚷嚷骂着姚宣宣的狼心狗肺。姚宣宣坐在床上,背对着门,听着姚之城的声音刺过木门戳进耳膜里、捅进心窝窝里,瘦削的脊背挺得笔直,像是不存了这一口气,就会被外面的那些声音压断了脊梁骨。
第二日拎着包要上班时,姚之城忽地从厨房探出半个身子,眯着眼睛和蔼地笑着叫住姚宣宣,道:“宣宣,今儿早爸爸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煎荷包蛋。”
姚宣宣冷硬的脚步陡地滞住,惶惑地回过头看着姚之城,看了他半日也不说话,像是想从他那样自如的笑脸上看出什么端倪来。但什么都没有,他的一言一笑都是那样自然,这么些年来每次挑了她的脊梁骨后他都能这样坦然地摆出一脸慈爱、祥和来,叫憋着一腔怒气冷着脸、狠了心的姚宣宣措手不及,只能败下阵来。
但都已经这么二十八九年了,还嫌不够么?还要多少次才够?
姚宣宣默默地垂了垂眼睛,扭过脸不去看姚之城那张慈爱的笑脸,慢慢地道:“我不吃了,你自己吃吧。”说完轻轻地带上门。
上班的路上她一直在想,门后面的姚之城会有着什么样的表情,他那样和蔼地笑着的一张脸会在她掩上门的那一刻纷纷凋颓么?姚之城每次无理取闹惹得邱何翻脸后,他都能端出一张受伤的脸到姚宣宣面前长吁短叹,就连姚宣宣和他顶一下嘴,他也能皱巴着眉头、死命地抽着烟,一边咳嗽到眼泪出来,一边用满是失望的受伤目光瞟着她。每次看到这样的姚之城,姚宣宣无论摆出再冷的姿态,都只能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想到姚之城强自抽烟,一边咳嗽一边揉眼睛的样子,姚宣宣的心里隐隐作疼,像是被又尖又细的针密密地在心窝窝上扎出一个蜂窝来。姚之城不会抽烟,人前也从不抽烟,独在姚宣宣面前,动辄就摸出不知藏在哪个抽屉旮旯里的烟呛得他自己心脏都咳出来。全然拿捏准了她,吃定了她的姿态。
工作也没有心思,心烦意乱,看什么都不顺眼,同事季白照旧每日端着一脸贼眉鼠眼的猥琐笑容在她面前晃,没话找话说,姚宣宣还得费力地挤出一个微笑来应付,心里烦躁得只想端起热茶泼到他的眼睛里去。
姚宣宣耐着性子,摆出一张空泛的笑脸任凭季白在一边说得唾沫四溅,全不往心里去。同事小王见了抿着嘴笑,说季白这是揣着热脸倒贴人家美人儿的冷屁股,白白惹了美人儿嫌,直说得季白脸上挂不住,讪讪地笑两声看着姚宣宣,一副想走却又不甘心就这样走了的样子。
姚宣宣心思一动,忽然抖开眉毛,对季白笑得粲然,道:“季白,今天下班一起看电影吧?”说话间眼风冷厉地瞥了一眼小王。小王正弯着腰找东西,没有瞧见。
电影也不知讲了什么,只听季白一直在耳边聒噪不休,臭虫一样搅得她心慌气躁,几次想甩他一耳刮子,叫他闭嘴。好容易熬到电影结束,已经将近十一点钟,理所当然地他得将她送回家。
到了楼下,瞥了一眼还在亮着的灯光,姚宣宣忽地一个人在黑夜里笑了一下,然后转过脸对季白道:“真是麻烦你了,这么冷的天,到我家喝杯热水吧!”
季白一脸受宠若惊,犹疑不定,不知道自己深夜造访,姚爸会不会喜欢,一直怯怯地拿眼睛看着姚宣宣。姚宣宣只是敷衍地笑着,也不说什么,季白到底不舍得错过这样大好的机会,还是上了楼。
一开了门,就看见姚之城坐在沙发上脸色阴沉得像是要平地卷起飓风一般,面前放着一杯喝尽的茶。灯光下姚宣宣骤然瞥见他灰白的头发闪闪地亮着,分外刺目,她顿时泄了气儿,懊恼得直想抽自己一巴掌。但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姚之城慢声冷冷地嘲讽道:“二十八九岁了,也不能瞧着没人要了,急得见了男人就往家里带。也不怕人瞧着臊得慌,自己没脸没皮,我老了,还顾着脸呢!”
季白堆的一脸笑一下子僵在脸上,愕然地看向姚宣宣,见她沉着一张脸垂着眼睛,又惊愕地看向姚之城。姚宣宣自是把他的表情全部收进眼里,一颗心又冷又硬,恨不得此时戳着他的鼻子骂个痛快。
姚宣宣冷冷一笑,挑眉看向姚之城,道:“爸,您也别说出这样叫人笑话的话来,没个当爸的样子!”说完也不看姚之城脸上的表情,狠狠地摔上门,扯着还是一脸惊愕的季白走了。
三
季白沉默地跟着姚宣宣漫无目的地走着,冷风呼呼吹着,刮得人骨头哆嗦着打颤儿。
姚宣宣忽地停住脚步,转过脸对落后两步的季白灿烂地笑了一下,柔声道:“真是对不起,叫你瞧到那样的笑话了——我爸他有间歇性精神病,总是这样子——”说到这里姚宣宣目光忽地散了,漫过季白身后不知名的冷夜里,眉目间带着几分忧伤。她一个人默默地静了一晌,忽地笑了一下,有些无可奈何地又说了句:“叫人没办法——”说完用含着盈盈笑意的眸子看向季白的脸庞。
季白忽然将她抱住,她本能地要推开他,方才暖了些的血肉也在那一刻迅速地冷冻,寒气逼人,手都推到了季白身上,却听他柔声道:“宣宣,苦了你——觉得难受就哭一场吧——”
姚宣宣整个人忽然就呆住了。苦,有么?这一切不是本就该这样么?哭一场,至于么?那人是她的爸爸,又不是旁人的。姚宣宣慢慢地笑了,她想推开季白,叫他不要这样一副哄骗小女生的情圣模样,叫人看了恶心得慌,但是季白那沙哑的声音里分明带了哭腔——姚宣宣惊住了。
后来姚宣宣竟然真的站在冷风里,伏在季白的肩头无声地掉了半日的眼泪,不知道是为了配合季白,还是真的觉得委屈、觉得苦。
第二日姚宣宣下班回家时,姚之城依旧沉着一张脸,看也不看姚宣宣,见她回来冷冷地哼了一声摔下报纸就进了自己的房间。姚宣宣忽地笑了一下,寡淡的心情瞬间明快了许多。她也没有说话,一个人做了吃的,给姚之城留了些,又一个人回房间。第二日晨起发现感冒了,满抽屉找药没找到,看看时间已经快晚了,姚宣宣吸了吸鼻子,揣了一包纸巾,蹬上鞋子就急急地出门了。
午餐时季白很殷勤地给姚宣宣打好了饭端到她面前,姚宣宣头晕脑涨,瞧着季白那一张脸就觉得厌恶得慌,那样的笑、那样的神情,似乎他们之间真的就有了什么一般,那样一副了解内情的表情瞧得她心烦气躁,好容易敷衍了他回到办公室,却见桌上一包东西。打开一瞧,竟是冬瓜炖排骨的盒饭跟几盒感冒药。
冬瓜炖排骨幽幽地冒着热气,香味儿引来了正在打印东西的小黄。
“我说宣宣同志,怪不得你不愿意嫁人,守着这样一个会疼人的老爸,谁愿意给人洗衣做饭,自甘堕落地当一个黄脸婆?”小黄去年十一结的婚,那日她笑得像是一朵怒放的花儿,惹得不少人艳羡,就连姚宣宣瞧在眼里,心里也酸酸涩涩地一阵怅惘,说不出的滋味儿。
姚宣宣眯着眼睛笑了起来,接了杯热水喝了药,坐下来慢慢地吃着饭。邱何走后,姚之城的厨艺就突显了出来,尤其是姚宣宣喜欢吃的冬瓜炖排骨,做得更是香飘十里。有时姚宣宣有事不能回家吃饭,姚之城就用这个饭盒做了便当给她送到学校。那时姚之城总是穿着一身休闲的衣服到学校接送她,高大挺拔,笑得温和有礼,老师同学们都喜欢他,姚宣宣一放学就喜欢赖在他身上撒娇。然而到了大学,离家一年之后,姚宣宣骤然发现以前那个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姚之城陡地变得臃肿不堪、絮絮叨叨,脾气古怪、喜怒无常。大学一毕业,他就给她在城里找了工作,姚宣宣不愿意,吵了几次,但最后还是敌不过他,只得留在这里。工作后,朝夕相处,更是磕磕碰碰,没个消停,姚宣宣又恨又累,几次萌生远走高飞,抛下他不管不顾的心思,但是气一消,立即就被自己这样歹毒的心思惊住。
下班再次路过那家小店,出乎意料那家店竟然没有一个顾客,冷冷清清,只有女人抱着一只灰色的肥胖的猫坐在门口。女人轻轻地抚着肥猫,神色淡淡,像是在想着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有想。姚宣宣看她的时候她也抬起头来看向她,目光冷厉像是两把冰锥子,但仔细看过去偏偏又是涣散着没有实质。姚宣宣再次被她的目光惊住,慌忙地凑出一个笑容,对她笑了一下。
“你会养猫么?”女人的声音竟出奇地好听,细细的柔柔的,像是浸着江南的春水,听得人心头跟着起了一层涟漪。
女人打算出门旅行,说她高中时就想去西藏、云南住一阵子,现在都四五十了还没有去过。她打算关一段时间的店,四处走走,只是不放心她的猫。女人说话的时候神情很安静,眉眼里竟透出些漠然和倦怠来。
女人的手很粗糙,因为常年和油盐打交道,所以指尖熏染了一层黄色。她温柔地抚着怀中的猫,慢慢地说道:“人呐,总得为自己活一下,为谁活都是白活。”
姚宣宣被女人这样的话刺得浑身一悚,惊疑不定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女人看着这样的姚宣宣,轻轻地笑了一下,这次是真的带了几分莫名的嘲弄,但姚宣宣却忘记了发怒。
女人笑了一下,然后微微仰着下巴,望着天出神道:“有时候瞧着她长得那么好、那么招人喜欢,心里也高兴,但有时瞧着她那样又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她不是我生的,这样我就可以尽情地恨她、厌恶她。”女人轻轻一笑,看向姚宣宣,打量着她,半晌,忽地又笑了一下,道:“想是一回事,得怎么做、会怎么做,又是一回事。”
姚宣宣被女人这一番话弄得莫名其妙,女人看着她疑惑的神情,只是淡淡地道:“我女儿在外地念大学,三年没回来了。总之,还是不能短了她的钱。”女人说完静静地抚弄着怀里的肥猫。
姚宣宣不喜欢猫,尤其是这样一身灰、吃得肥胖的老猫,瞧着像是一个肥胖的老女人,被岁月剥蚀掉所有的神采和颜色,只剩一堆死尸般的皮囊,叫人厌烦。但女人那样慢慢说话的样子打动了她,所以她还是把猫抱回了家。
“小乔喜欢吃鱼,她只吃鲫鱼,要鲜的活的,这才好——”女人抚着猫笑得温柔慈爱,絮絮地说了一堆猫的喜好,告诉姚宣宣该怎样养猫。一只肥猫却叫了一个这样温婉艳冶的名字。
“你好好地替我养着小乔,别委屈了她,我一回来就来接她。”女人还在不放心地说着。
四
姚宣宣很不喜欢那只猫,但姚之城却很喜欢,整日在家抱着,沙发、地板上都是灰灰的猫毛,姚宣宣几次恼得想拎着猫尾巴把它从七楼丢下去。
两人相对时,姚之城几次欲言又止地看着姚宣宣,顿了一下最后还是问了她季白的事。姚宣宣垂着眼睛,做着自己的事情,慢慢地答着。答完,不等姚之城再说什么就起身去睡了。
没隔几日姚宣宣就带着季白第二次上了家门。季白拎了一堆的东西,全是老年人的保养品,准备了一堆的笑容,礼貌周到地同姚之城问候着。姚之城神色极为冷淡,看也不看季白,只顾着看自己手里那张已经翻了两遍的报纸。姚宣宣靠着门抱着胳膊站着,不动声色地把这一幕看着,一脸的无动于衷,全然不顾季白几次三番投过来的求救的目光。
季白一走,姚之城就表态,说他不同意。
“你就是急着嫁人,也要带着眼睛去瞧人,他长得那獐头鼠眼的,满嘴抹了蜜一样,一瞧就是靠不住的——你找这样的一个人带回来,别人瞧着都笑话——”
“我就要和季白结婚。”姚宣宣冷声打断姚之城的话,一副不容动摇的语气。
姚之城自然不会这样轻易罢休,只要一见到姚宣宣的面就开始数落不休,说来说去无非是季白不是良人。姚宣宣垂着眼睛听着他黏在自己身后一遍一遍地说个不停,终于抬眼看向他,冷笑道:“我交的男朋友,你哪个瞧上过眼?”
从姚宣宣初懂人事起,就不断听到姚之城小心试探地询问她有没有喜欢的人,那时姚宣宣只是羞涩地用小手捶他,姚之城攥住她的小手,也跟着笑起来。后来大学,姚宣宣交了第一个男朋友,姚之城一知道,第二日就风风火火地赶到学校,找到那男孩说人家拐骗姚宣宣、不是什么好东西,言语极尽难听,那次恋爱就这样不了了之。再后来工作,有个温文尔雅的男人说挺喜欢她的,姚宣宣虽然不是那样有感觉,但他那挺拔身影和似曾相识的儒雅叫姚宣宣说不出的好感。满心欢喜地带他回来给姚之城看,姚之城却三言两语将人打发走了。自那之后,姚宣宣再也没有恋爱过,一晃已经是即将二十九岁的人了。
姚之城听姚宣宣这样说,也恼了,点着姚宣宣的鼻子骂她,说她没出息、一心想着男人——越说越难听,姚宣宣转身进了房间,锁住门,背靠着墙眼泪就这样簌簌地掉下来,无声无息。
姚宣宣很少再回家,不是到朋友同事家,就是一身疲惫地顺应了满脸期待、怯怯地看着她的季白,到了他家。
工作时,她常走神,盯着电脑屏幕,二十多年来因为姚之城流过的那些泪水再次翻涌了出来,恨得把牙齿咬得生疼,心里却抑制不住地绝望。她觉得自己就像是被黏住了翅膀的鸟儿,挣扎着冲撞着网,生活里的一切都是在不断地重复,陷入了一个无休止的死胡同。
这次,她要坚持到底,真的再也经不起重复。
现在,她有一副铁石心肠,她什么也不害怕。
姚宣宣挺直脊背,一脸冷色。
她已经做好大战一场的准备,太过于紧张,心头反而生出些跃跃欲试的兴奋来。她底气十足,饱含期望,所以在骤然听到姚之城摔倒住院的消息,人一下子蒙了,身上那些方才还叫嚣着跳动着的不安分神经立时死绝死尽。兀坐了半晌,整个人傻掉了一般,一张脸木然着。
不等她赶到医院,姚之城已经回了家,说是血压突然升高,现在已经好了许多,只需要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挂了电话,姚宣宣慢慢地沿着街道走着,心里空得厉害。她怎么都觉得姚之城还有什么没说完,却又不敢去猜想——冬日的太阳暖洋洋地将她整个人包裹着,她却还觉得冷得厉害,人也禁不住哆嗦起来。
她觉得害怕,害怕到发慌,害怕到想找个角落藏起来。
终于鼓足了勇气推开家门,却没见姚之城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准备好的笑脸一下子散落开来,本来慌乱着的心也倏地静止了,呼吸就这样滞在胸腔,憋得要炸开,泪水不自觉地就滚落下来。
“宣宣?宣宣——”
听到声音,姚宣宣鞋也没换就奔进房间。姚之城躺在床上,一脸的苍白和颓败,姚宣宣低下头,眼泪簌簌地落下了,掉得到处都是,奇怪的却是一点儿声音都没有。
“宣宣,你和季白的事,爸不反对了——”姚之城怯懦地看着姚宣宣,像是做错事的孩子一般,眼里甚至流露出无助的惶恐来。几日不见,他整个人变了。先前脸上的那种狂躁的尖刻神色全然不见了踪影,他像是一下子老了,比以前更老,已经锈迹斑斑,没有半点锋刃可言。他的脸似乎又臃肿了许多,皮肤松弛得不像是活着的人。
姚之城一脸的讨好,卑微地对姚宣宣笑着,伸出粗糙无力的手要去拉姚宣宣。姚宣宣却呆住了,忘记了掉泪,也没有去拉住他的手,只是那样站着,看着他。姚之城的手慢慢地垂下,恐惧地瞥了一眼姚宣宣,就像家里那只老肥猫每次被姚宣宣打了之后流露出来的神色。终于,姚宣宣又默默地低下头,眼泪再次滚落下来。
姚之城一直看着姚宣宣,姚宣宣去倒水,慢了一会儿,他就哑着嗓子满屋子喊着:“宣宣——宣宣——”姚宣宣根本没有办法去做饭,只好给他弄了些季白那次拿过来的补品吃。姚之城吃着东西,还不住地拿眼睛偷偷地看着姚宣宣,全然孩子的模样,一刻也离不了姚宣宣。姚宣宣抹去滚烫的泪水笑了起来,笑着笑着,泪水又一次淹住了她的世界。
他在怕她。姚宣宣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将这句话重复着,最后终于哽咽出声,伏在姚之城的床边哭了起来。
姚之城惶然地看着她。姚宣宣哭完,擦去眼泪,对他笑了一下,姚之城这才坦然了些许。
姚之城好不容易睡去,姚宣宣疲惫地回到房间,看到四个未接来电,全部是季白。姚宣宣心头一阵厌恶,怒气噌噌地冲出胸腔,咬牙低声骂道:“贱人!”骂完,直接将季白拉进黑名单,把手机丢在床上。
走到阳台,她探着身子向楼外倾着,像是要栽下去一般。她咯咯地笑了起来。举目四望到处都是凄迷的灯光,瞧得人心间都溢满了悲凉,走不出去,逃不掉一般。冷风呼呼地刮着她裸露在外面的肌肤,方才流过泪的脸庞经冷风一吹,皱巴巴的像是要裂开一般,她觉得自己整个人似乎要从这具慢慢裂开的皮囊里走出来,穿过林立的楼房,然后飘散在风里,像是一阵烟一样。
半年后,女人还是没有来接回她的猫,姚宣宣下班经过已经转让的店面一个人默默地站了半晌。回到家,一眼瞥见窝在沙发上的那只老肥猫,眉头不禁皱了一下,走过去拎着猫,把它丢到墙角垃圾筐里。老肥猫凄厉地“喵”了一声,惶恐地瞟了一眼姚宣宣,一溜烟儿跑进了姚之城的房里。
责任编辑/董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