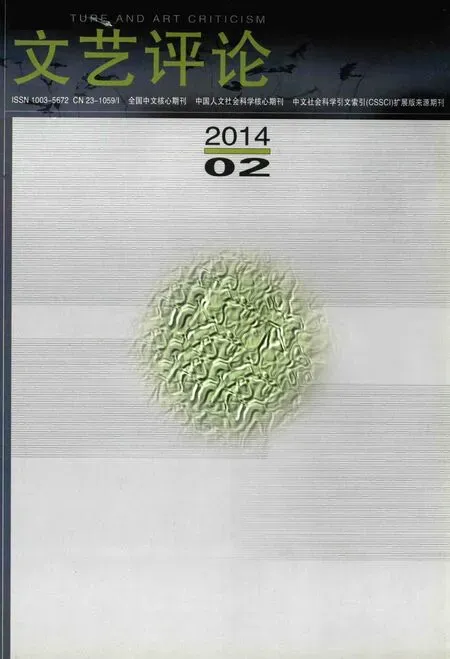从《世说新语》旷观魏晋士人的生活美学
张泽鸿
美学家宗白华曾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①;鲁迅称魏晋时代是文学艺术的“自觉时代”;刘大杰认为魏晋时代是“浪漫主义”的时代;冯友兰称魏晋为“风流自赏”的时代。这诸多大学者从不同角度殊途同归地指向魏晋美学的同一个主旨:魏晋时代的士族文人以精神上的自由与解脱,情感上的细腻和热烈,人生情趣上的优雅和“风流”,以高度艺术化和深度审美化的态度来经营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从而创造了中国古代生活美学史的第二个高峰期。从《世说新语》、《晋书》或魏晋文人的书法札记、诗文篇章中,就仿佛可以呼吸到一股浓郁的中古时代士人生活审美化的浓郁气息。
《世说新语》②是南朝宋刘义庆(403-444)编撰的一部笔记体小说集,主要记载了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二百多年间士族阶层的逸闻琐事,其中以魏晋,尤其是东晋时期的内容占据主要部分。书中涉及重要的士人多达五六百人。全书分门别类地表现了士族名流的思想、性情、生活、交往的各个侧面,总体上彰显了魏晋名士的精神风貌、言行举止和生活方式,并反映了魏晋时期的社会政治、历史、道德、哲学、艺术和审美等诸多方面的基本特质。从中可以看到3-4世纪“风流自赏的名士们的生动形象”③,成为探索中国古代“风流”传统的经典文献。本文拟从当代“生活美学”观出发,以《世说新语》为依据,对魏晋士人的“生活世界”进行审美分析。
近十年来,“生活美学”正逐渐成为国际国内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从生活美学的中西渊源看,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分析美学”、杜威-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以及马克思的“生活实践”的哲学等,共同构成了“生活美学”的理论来源;而从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看,中国传统美学和传统的艺术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活化”的美学。中西美学重视“生活”的传统共同促成了当代生活美学的勃兴。简单来说,生活美学主要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两个理论维度④。从《世说新语》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士人的“人生艺术化”、生活审美化的程度最高,堪称中国思想史的一道人文奇观。魏晋士人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两个维度彰显了这一时期生活美学的兴起。尽管与儒家重视经世致用、世俗伦理的生活态度迥然有别,但作为新道家派别的魏晋士人“并没有把‘人’之‘在’安放在彼岸世界。对于日常生活,士人始终是‘在’的。”⑤魏晋士人的生活美学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哲学生活化的“清谈玄理”、人生艺术化的“人物品藻”、日常生活艺术化的“饮酒服药”、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寄情山水”。
一、哲学的生活化:“清谈玄理”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大量的名士清谈。魏晋时期,王朝更迭,皇室内讧,统治阶级内部充斥着勾心斗角和权力纷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名士因言(行)获罪或被杀。处于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魏晋名士们内心充满了恐惧和彷徨,许多人不愿意涉及政治,也不敢评议时政。一方面为了全身远祸,另一方面为了填补精神生活的空虚,缓解心灵的压抑和痛苦,规避政治专言玄理的清谈自然成为一种理想的精神消遣方式。流风所及,竞相仿效,逐渐成为魏晋士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清谈玄理的过程中,很多文人借此来展示自己的哲学智慧和口辩才能。这一时期,涌现了诸如何晏、王弼、夏侯玄、王导、谢安、许询、支道林、司马昱等清谈名士。宗白华曾指出魏晋时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⑥。清谈玄理主要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为本而加以申论发挥,探讨天地人万事万物的形而上问题,形成了著名的几个论题:如有无之辨、言意之辨、名教和自然、声无哀乐、才性四本等。
冯友兰曾指出:魏晋清谈的艺术性“在于运用精妙而又简练的语言,表达创意清新的思想。由于它的精微思想和含蓄而富妙趣的语言,因此只能在智力较高、又互相熟悉、旗鼓相当的朋友之间进行,而被认为是一种‘阳春白雪’式的高水平智力活动。”魏晋清谈不仅体现了名士们的智慧风采,更彰显了一种“哲学生活化”的风尚潮流,使得中华民族的抽象思维得到空前发展。正如鲁迅所说,当时“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的资格”。名士们相聚谈玄,一般采用辩难和讲座的形式进行。其中辩难最为精彩,如《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孙盛与殷浩辩难,互不相让,双方苦苦交锋而难分高下,激烈到顾不上吃饭的程度。王弼在辩难中挫败何晏后意犹未足,于是“自为客主数番”,自问自答,得意忘形。与辩难相比,讲座的形式较为安静,一人单独讲演,听众和讲者不辩论,气氛较为缓和平静,但由于讲演精彩,在听者内心也会掀起波澜。由此可见,魏晋士人通过谈玄的方式突破和解体了汉代“独尊儒术”的一元化思想禁锢,形成了春秋战国后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时代。并且,魏晋玄谈所带来的玄理盛行并普遍渗透于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士人生活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反过来它能提升士人的生活情趣、思想智慧和人格境界。魏晋玄谈之风在整体上塑造了魏晋时期“哲学生活化”的时代风尚,进一步奠定了魏晋士族文人生活审美化的思想基础。
二、人生的审美化:“人物品藻”
与清谈玄理一样,品藻人物也是魏晋时期流行的一种生活风尚。人物品藻源于东汉察举制度中的乡党评议。此后曹魏时期采用九品中正制,根据门第世系擢升官吏,人文评则失去了往日的“为国选才”功能,而逐渐演变成为对理想人格和美化人生的探索。品评的内容和标准也不再局限于儒家道德或才干的单一考察,而拓展到对人物个性、容止、风度、气质、才华等全方位的评鉴,这体现了魏晋时代的一种独特的审美风潮:即对“人”本身(身体和人格)的审美考察。这一时期,人物品题虽淡化了政治功利色彩,但仍对士人的名誉、地位、声望等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受到时人的高度重视。
品藻人物最看重的是人的神明。在形神关系上,魏晋人认为形神相表里,互为观照,神为主形为客,精神主宰形骸。基于这种认识,“以形求神”和“得意忘形”便成为考察人物的两种主要方法。所谓“以形求神”就是通过人物外在的容貌、气色去探求神明,把握内在的精神禀性。如王戎评论王衍,见他容止上“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就说他“自然是风尘外物”,是一个超逸尘世的人物。所谓“得意忘形”,即认为神明高于形骸,即使容貌不佳,只要精神气质不同凡俗,也能得到赞赏。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身短貌丑,但并未影响时人对他的飘逸洒脱风度的欣赏。“以形求神”和“得意忘形”均表现了魏晋士人对人物神明方面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人的精神之美的执着追求,魏晋人物品题正是以神明为中心而展开的对人物多角度的审视和评价,从而体现了魏晋时期丰富的人生审美情趣。并且这种人生审美化的重视和追求有时近乎“偏执”,因此也造就了“魏晋风度”(魏晋士人多维度的立体的人格风度之美)的千年流传。
宗白华称魏晋时代是“人格的唯美主义”时代。从《世说新语》的记载看,王戎评山涛“如璞玉浑金”,山涛评阮咸“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王导评王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殷浩评王羲之“清鉴贵要”,孙绰评许询“高情远致”等等,这些都反映了魏晋士人追求的自然率真之美、超逸脱尘之美、沉澈明净之美、清峻拔俗之美、器识明慧之美等。这种种美的类型风尚都体现了魏晋士人从超道德、的视角看待人生,将超越身体的精神之美看作是人的最高价值。人物品题是魏晋时代生活美学的精粹体现。
三、日常生活艺术化:“饮酒服药”
魏晋士人在道德伦理和生活方式上极力反对儒家传统,他们蔑视名教礼法,率性任诞,展现了一代士人独特的超道德的审美化生活方式。魏晋士人提倡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审美化方案有二种:一是饮酒,二是服药。《世说新语》对此有充分的描述。鲁迅先生作过一个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讲演,就是探讨魏晋士人的饮酒服药问题。
魏晋名士的生命史中弥漫着酒的醇香。魏晋士人多饮酒成癖,如王忱慨叹:“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课件酒在士人生活中的地位多么重要。阮籍虽是孝子,但在居母丧期间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一般来说,魏晋士人好饮的因由,一是为了借酒逃避现实政治,全身远祸;二是通过自我麻醉来寻求精神上的暂时的自由解脱。一方面,魏晋士人沉溺于酒,与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和个人遭际是密切相关。狂饮酣醉,以求借此排遣内心的悲哀和愁闷;并借酒来对抗和逃避政治迫害,为的是全身远祸。南宋叶梦得《石林诗话》中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⑦嵇康、阮籍、刘伶等都是以豪饮酣醉为全身之计,尤其以阮籍的借酒自我保护最为成功。另一方面,魏晋士人还想通过醉酒达到暂时的精神解脱,如王蕴曾说:“酒正使人人自远。”即是此意。
饮酒之外,魏晋士人还通过药物作为护身符和麻醉剂。当时流行服用具有兴奋和麻醉功能的五石散。五石散对人体的毒副作用很大,严重时会危及生命。服药本是不可取的生活行为,但魏晋士人却乐此不疲,其主要目的是想暂时忘却政治的黑暗和精神的痛苦,寻求服药后的飘飘欲仙和精神解脱。酗酒服药还会引起一些较为荒诞可笑的举动,如刘伶、王平子、胡毋彦等人在醉酒后的“裸奔”行为。从儒家道德礼教和正统风俗习惯看,这些士人的行为是在不值得提倡,但是从魏晋时期的大背景和生活语境看,又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通过种种荒诞行为来亵渎、解构、颠覆儒教道德,反映的是一种通达、任诞、自由的生活态度,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其最为出格的言行无外乎如此。饮酒服药,从身体健康的角度说毫不足取;但从思想史和心灵史的角度说,它又具有积极的意义。饮酒服药彰显了魏晋士人在普遍压抑的时代语境下并未沉沦堕落,而是通过这种近乎“自残”的方式来追求精神的超脱。追求任“自然”而不是循“名教”的处世方式,这也是魏晋士人生活美学的意义所在。
四、审美日常生活化:“寄情山水”
作为生活艺术化方式之一的饮酒服药毕竟伤身,相比而言,寄情山水则是全身远祸、舒畅身心的一种更为高尚的生活形式。因此,魏晋士人冶游山水、栖逸林泉的风气甚为流行。士族文人积极投身天地自然的怀抱,在饱览山川风物之美的同时,也深切地体验着生命的真意和精神的超脱。魏晋士人在对山水审美的过程中发现,山水自然的真正的美不在其外在的形态,而在于山水环境本身的“真性”之美和“自然”之感。山水和人一样,真正的美在其“真”。《世说新语·言语》第61则记载东晋简文帝司马昱游华林园,顾左右而言:“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山水有情,鸟鱼有性,于是物我交流,悠然心会。魏晋士人不仅在山水林园之中寻找“真性”和“自然”,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
魏晋士人将对待山水的那种自然而然、顺兴而为的方式也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创造了一种“大道至简”的艺术化生活态度。魏晋士人普遍鄙视功名利禄,不拘儒学礼教,一切顺应自然,率性而为,追求一种安闲自得、张弛适意、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任诞》第47则记载了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由此可见,魏晋名士不为外物所累,无意于物欲的享乐,只求率真放任、适兴尽情,体现的是一种“率性的生活”⑧方式。王子猷是王羲之的第五子,也是性情潇洒的风流名士,《世说新语》中关于王子猷的故事就有好几个。王子猷爱竹,他曾暂居在一户人家的空宅里,便令人种竹。有人问他:“暂住何烦尔?”王子猷啸咏良久,手指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可见王子猷爱竹深入骨髓,这种纯粹的近乎偏执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追求也只有魏晋名士才能做到。可见,这些“风流”倜傥的名士们“富于深沉的敏感,胸中块垒自然与常人不同;在别人无动于衷的地方常会怵然于心”。⑨他们对精神生活、人生和宇宙常常“一往情深”而不能自已。
从以上论述可知,魏晋名士崇尚清谈玄理,品藻人物,饮酒服药,同时又超越礼教束缚,追求真我本相,任性适意。对宇宙人生的一往情深,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态度,这些雅兴风范和精神特质,被后人誉为“魏晋风流”(或曰“魏晋风度”)。何谓“风流”?冯友兰曾解释说:从字面上看,“风流”是荡漾着的“风”和“流水”,与“人“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它似乎暗示了有些人放浪形骸、自由自在的一种生活风格”⑩。从魏晋思想史和生活风尚史来看,“一个人超越事物差别之后,得以不再依循别人的意旨生活,而率性任情地过自己的生活(‘弃彼任我’)。这种思想和生活方式乃是中国古人称为‘风流’的实质。”⑪由此可见,《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风流”,本质是指一种遵循内心而不是迎合时尚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冯友兰先生曾归纳说“魏晋风流”有四个条件,即有玄心、有洞见、有妙赏、有深情⑫。所谓“玄心”可以说是心灵的超越感;所谓“洞见”,就是不借推理、专凭直觉而得来的真知灼见;所谓“妙赏”就是深切精妙的审美能力;而所谓“深情”,真正风流的文人,对于万事万物、宇宙人生都产生一种深厚的同情。这说明魏晋时期的士人能将整个宇宙人生化为自己的“生活世界”,并且能以审美的心态面对这个生活的世界。魏晋士人“从来没有把人的生活仅仅作为人的自然的或世俗的日常活动,而是使生活本身成为诗意的存在”⑬。因此,《世说新语》文本所记载的“魏晋风流”,在一定意义上彰显了魏晋士人的生活美学观,昭示了现代人所向往的“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生活化”的双重价值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