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之维
陆丹++陈彦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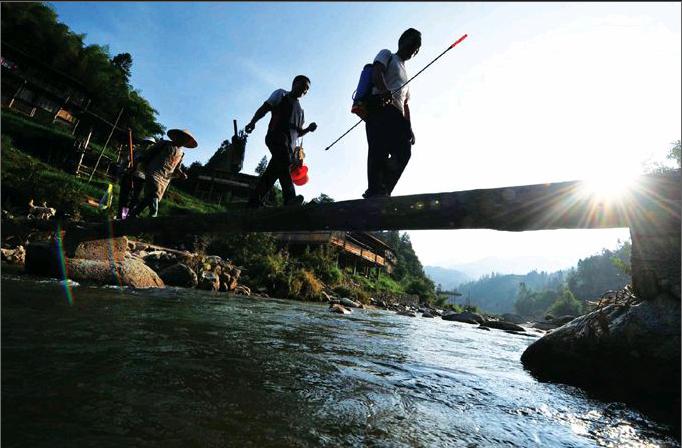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
敞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之维,对我们的重要性不亚于总结和学习世界现代化国家治理的经验。
吏治的效率与公平
按照儒家史观,古代中国5000年国家治理分为三个时期。尧舜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理想的大同社会;大禹之后的夏商周三代,“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但奉行王道,社会依从传统的礼义秩序运行,是和谐的小康社会;秦始皇奉行武力统一天下,变封建为郡县,利用从上至下的官僚体系统治社会。
重点看从秦到清2000多年的国家治理。这段集结构基本稳定与社会生机勃勃于一体的历史,虽一直受与家天下相伴的党争和王朝百数十年便倾覆的循环困扰,文明却能延续两千年,不能不令人正视其在国家治理上的独到之处。
我们并不是从现代角度出发去审视其执政治理的历史合法性,比如阶级论、道德观等视角;我们的出发点是观察其治理的有效性,比如以更小成本、更小风险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与生活祥和等目标。
其一,君主世袭,虽是所谓自证合法,但统治家族若常思为政以德、时刻正己修身,居安思危、适时改易更化,则常能积累丰富的执政资本和治理经验;一旦立嫡以长、继位有序,也会起到在最高权力转移时定纷止争的效果,有利于人心和社会的稳定,减少社会成本,降低运行风险。
其二,选官制度,封建变为郡县,君主孤立无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从察举到科举,历代王朝不断总结经验,建立起历史上能达到的最具广泛性、普遍性、公共性、公开性的选官制度,不仅为官僚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有识有才之士,而且有效地整合了跨地域、跨族群、跨文化的复杂多样的中国社会。
其三,家国一体,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上,通过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机巧地化解了执政可能引发的种种道德诘难,反而确立了家天下的多重合法性。
更值得重视的是吏治。我国古代的吏治一般有两个基本旨向。
一是效率。帝王的雄才大略、社会殊死的生存斗争和后继者维系大一统局面的惯性等,构成中国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共识,这种共识是疆域辽阔、地方差异巨大、区域文化多元的东亚大陆形成大一统治理结构的基础要素。封建帝王要长久统治如此巨量而复杂的社会,就需要庞大的官吏队伍行使国家治理职能。庞大再加复杂,使得吏治的首要目标是效率,政情上达与政务下达成为中国吏治首要解决的难题。
二是公平。中华文化在轴心期就形成了民惟邦本、政在得民的政治观念,统治的合法性与民众的意愿必然关联。人类因为个体安全繁衍和生存最初基本需要而结成社会,个体在受组织支持的同时受组织约束。这是社会的一般常况。但是,中国百姓很早就意识到这种加入社会的“自由换保障”方式带来的其他弊端,担心摆脱自然的侵害又跌入人类的束缚乃至压迫,所以,特别重视并普遍接受社会公平的观念,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可以,机会和劳动成果分配不均不可以,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
中国社会所有基本的合法性、合理性、合乎道德性的前提条件,都是国家治理要保障安全和发展生产,处理公共事务要主持公平,前者是功,后者是德,当然,执政者自己也要以身作则、行为世范。儒学关于执政合法性的功德观念成功影响了中国吏治两千多年,也成为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的一个重要吏治传统。背离此传统基础,其他一切的附加现代治理成果都失效。
治世倾向公平,乱世倾向效率
治国以治吏为先,古代中国积累了吏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在效率和公平的价值排序上,2000多年中相对的治世和相对的乱世是不一样的。治世一般倾向于公平优先,效率也因为得人心而获得保障;乱世则倾向于效率优先,公平疏于保障,效率也因为失人心而难以落实。而吏治不靖,就常常发生在官僚体系在皇权驱动下对社会的过度汲取之时。国家治理若长期奉行单一的效率优先,往往弊端丛生。
其一,效率优先带来长官意志盛行,上层官僚权力过大,不顾地方和个体的合理需要,容易造成治理的武断太多和人性化不足两种危机同时并存。积久就消弭下层和个人动力,蔓延则失却人心,前者引出社会静止,后者诱发社会动乱。
其二,效率优先的价值主导通常带来公权私用的普遍合法化。在农耕文明时期,抵御游牧民族入侵、惩处社会越轨和脱序、防范内部权力觊觎等国家公共开支总是巨大,而有限的吏治队伍、成本巨大的防范开支与管理幅度过大、社情过于复杂等几者之间往往存在紧张关系。
长期的紧张关系倒逼产生非正式委托的治理方式,国家把主要精力用于防范方向,默认也等于纵容非正式的基层委托治理,这样,就随之滋生两种吏治弊端:一是对官吏的公平和道德考量指标权重自然下降,忠诚主子(组织、上级)体大,其余事小,个人道德是小节,不碍官场规矩是大节。如此,则官吏普遍不介意公平立场丧失和个人道德评价下降;二是客观上为官绅勾结、官商勾结开通了“合理”渠道。既然国家治理支付有限,五花八门解决治理问题、保一方平安就在情理之中和政策法度默认之内。随之,基层官吏替人“消灾”(公务之内的糗事)就要拿人钱财;“帮忙式治理”一旦成习惯,“合理”收费就相沿成风。这样,腐败就成常情常理,就成社会潜规则和官民间的私暗文化,一定程度上,公权私用就普遍合法化了。
其三,公权私用容易造成官官相护。在传统大一统治理目标和治理结构的条件下,囿于治理技术能力和治理目标偏颇的两重缺陷,即便国家法度一致,往往实际上政令却难畅通。政令稍有松弛,上层一旦默许地方治理花样百出,也就难免公权私用随后盛行,随之,贪污就一定会酿成大害。古代家天下社会,除了榨取百姓和官商勾结两途,官吏贪污就总是拿了皇帝的钱,法理上皇权不容,所以,基层官吏需要在皇帝身边找靠山,这样,宦官专权、外戚专权、大臣专权以及其他党争轮轴上演就成为我国历史上吏治不变的循环老故事。endprint
考虑到传统经济局限、社会公共支付成本有限、对官吏监控条件不足、公正评价困难等等,吏治迟早会回到失序状态,周期性失序便倒过来会成为常态。这是中国历史上吏治的基本状况,一朝创业,官场谨言慎行;一朝中兴,官场气势如虹;一朝老迈,官场腐败横行。历史经验记载和百姓口耳相传记忆,教会了官吏如何应付,教会了百姓如何应对,一切因循,周而复始,吏治顽疾难去,中国社会治理没有前途。
从“当官不易”到“当官容易”
有人喜欢把现代条件下出现的吏治问题归咎于封建传统的遗留,这其实是一种回避矛盾的做法。
传统吏治是中国社会在既有自然环境、经济条件下政治策略竞争淘汰、社会生存选择策略的“优选”结果。当中国历史找到进步的方向,追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候,我们今人需要厘清哪些传统的顽疾还在影响当代吏治,哪些是我们对传统中国家治理成功的经验借鉴尚不够,又有哪些是我们公天下的体制机制优势还没有找到更宜落地的现实路径。
现代中国社会,政府受人民委托,官场贪污就都是拿人民的钱。人民不满,则政府不容,但中间隔了“代表”(委托)的复杂关系,阶段性上难以随市场和社会迅速变化而跟进明确清晰的诸事“代表”细则来每每一一对应权力和权利,所以需要一个司法机构独立判断官员代理行权当与不当。当然,如果政府不自觉、人民不介意、司法不独立,则贪污依然会回到传统朝廷方式即到上层(宫廷)寻找庇护人靠山的旧路,党争与政权更迭也会逻辑推演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腐败问题,不只是贪污公款、接受贿赂、设置市场准入门槛等这些政府与人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偏离,还会是官官相护和具体的官员欺压百姓等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畸形。党纪国法如何成为官员的内在信仰和外在约束,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如何在国家治理中切实有效实现,一切都需要我们在夯实法治和完善吏治两条线上不断推进。
现代社会,公权力无处不在。中国是人情社会,官员与民间自然联系广泛,官员之间也联系紧密,对此需要设限:官商不能勾肩搭臂,官官不能有兄弟圈子,官民不能形成朋友圈子,中央的“三严三实”要成为为政做官的门槛,“当官不易”,应该成为官场的新常态。
这个“不易”,是官员达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素养培养和业务能力满足岗位起码要求的不易,也是违法乱纪后逃脱制裁的不易,更是恰当把握“效率”与“公平”尺度这个为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不易。
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治理失序一定是这个天平不平衡。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社会治理与现代吏治,也正面临这个大考,也必须越过这个门槛。
理想状态是,“当官容易”,因为国家形成了法治条件下风清气正的官场生态,官场形成了官员凭态度、能力、道德和政绩升迁的公正环境。当然,必然产生新问题,真正没有了为官做老爷封妻荫子的动机和环境,没有了养不了廉的高薪条件和制度,如何让做官为人民服务成为内心动机和社会风尚,使公天下的价值优势、制度优势选项变为实践和人心的常态,如何把握好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促进稳定又繁荣、国强民也富,中国社会还需要加力、加速探索。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克服党治经济条件下的党弊、国治发展阶段过程的国疾、民治民生相应的因应策略文化下的民俗、社会治理传统某些遗传基因缺陷可能隐藏的毒瘤,等等,其前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需要倍加警惕的是,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可能是顽疾暴发的条件,而社会随经济发达而理性觉醒与行动,才是根治顽疾诱发暴力的社会条件。
社会觉醒,是人民有制度、有平台、有能力、有意愿当家作主。社会觉醒并不必然带来根治,社会觉醒时选择何种策略才是根治的主导条件。就目前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各国已经成功的经验总结,选择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并且国家得遇雄才大略和开明坚定的领导者,才是根治的开始。
换句话说,从历史敞开道路,夯实法治,严格吏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官僚主义的顽疾才有根治的开始,中国吏治走向公正开明才会有前途。
(陆丹:海南三亚学院校长兼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陈彦军:三亚学院讲师、硕士)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