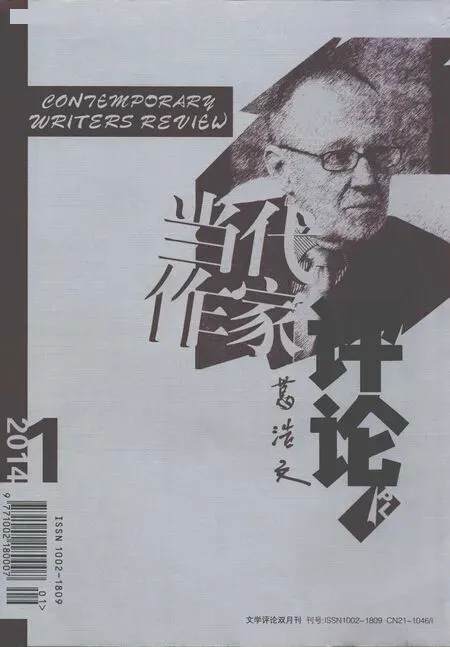情智共生的雅致写作:叶广芩小说论
李翠芳 施战军
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似乎充满了太多要夺人眼球的凌厉劲儿,诸多的作品把生活的匪夷所思和不可思议一遍遍安插其中,结果是戏剧化的尘土扬得过头了,但是现实体验和价值判断常常处于一种悬空状态,在一番熏眼呛鼻之后,阅读者毫无例外都会感到失落和空虚。于是,人们更期待一种自然的宁静的写作,那种将人生际遇和生存感喟相结合的写作,那种字句流畅、节制优雅的写作。叶广芩的写作就是这种,她有一种特别的讲述能力,能深入故事的内部获得一种超然的体验。细腻,而不煽情;雅致,而不做作——在众声喧哗的时代,也许这种能使我们沉入静默之中的作品更为难能可贵。
一、经验与想象:真诚而灵动的写作
在新时期文学语境中,代群投靠和类型写作无疑是追求速效和高效收益的捷径。为了进入期刊策划和批评言说的视野之内,诸多写作者在叙述技巧和题材选择上趋同舍异,跻身文学潮流之中,结果却是潮起潮落,很多人被吞没于“合唱”之中。相比这些藏在作品背后趋风就势的作家,叶广芩的写作可谓稳实质朴。她处身于文学的热闹之外,真正沉到了自己人生经验的底子上,去娓娓讲述那些与她自己有关,更与普遍的历史记忆和人性思索有关的故事。而这种写作必定是出于更为自然的写作欲望和更为真诚的文学精神。
叶广芩的写作明显与她的人生轨迹相贴合,她经历丰富,于是她的创作移步换景,也表现了多样的世态人情。她的作品题材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根植于她曾经显赫但难免落魄的家族历史的家族小说。叶广芩祖姓叶赫那拉,“皇亲国戚”的身份使她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钟鸣鼎食的满族世家在时代巨变中的衰败没落。从一九九四年开始,叶广芩视点回溯,着力挖掘那些饱含眷恋和痛楚的家族记忆,创作了《谁翻乐府凄凉曲》、《梦也何曾到谢桥》、《状元媒》、《豆汁记》等一系列家族小说,最终结集成系列长篇《采桑子》和《状元媒》。二是旅日生活的经历所激发的对中日两国文化反思的小说。一九九○年,叶广芩留学日本,近距离接触了日本文化,并客观深入地反思了战争历史,创作了诸如《风》、《雾》、《雨》、《到家了》、《注意熊出没》等作品,最终结集出版《日本故事》。三是基于她挂职生活感受的动物主题小说。二○○○年叶广芩到陕西周至县挂职,并深入到秦岭山区,开始以广博的生命关怀意识考量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创作了《熊猫碎货》、《山鬼木客》、《老虎大福》、《长虫二颤》、《猴子村长》等一系列生态系列小说。与那些有着相对稳定的写作领域和相对集中的写作对象的作家相比,叶广芩显然是一位很难定位的作家。长在京华古都,摸爬滚打于社会底层,参考了异域文化的对照,她的笔触历史和现实交汇:既写满族世家和贵胄子弟的故事,也写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既涉笔战争和域外生活,也关注自然和生态——因而悲喜兼容,雅俗共赏,怀旧、怅惘、反思,所有的情绪欲说还休,形成了创作古雅、清丽的风格。
虽然,九十年代以来,女作家一度都极为迷恋自我经验世界,但是她们所谓的“私语体验”可能更多是梦呓般的幻想或者揽镜自照的想象,既与生活无关,更与世界无关。叶广芩坚持状写自己所经历过的生活和思想情感体验,这是极为难得的。也许,写作是叶广芩的生活本身予她的馈赠。所谓“文章憎命达”,从理论上说坎坷的人生和危机的体验是文学的摇篮。因为文学创作的本身就是对苍凉人世难以逃脱的苦难和创伤,以及超越和救赎的关怀和烛照。家族衰败、落魄心酸、被迫离京、政治批斗、种地、做医护、做记者编辑,等等,叶广芩的人生磨难和生命历练等种种现实照进写作,“如树上的果子一样,大约也是到了该熟的时候”,这是文学之幸,亦是读者之幸。因为叙写的是内心真切的人物、情境和情感,所以叶广芩的文字的展开就格外自然,语调流畅,情思丰盈。当前文坛有时候让人感到贫乏,其实并不是缺乏戏剧性或者离奇性,恰恰相反,是因为在作品中我们常常感觉到作者缺乏足够的常识和诚意。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乏有想象力的创作者,很多人靠着影视、网络以及道听途说也能洋洋洒洒写成长篇巨著,但是不可否认,这种写作不管在人物关系上设置多复杂、情节上设计得多紧凑,字里行间总还是流露出一种惰性和懈怠。我们缺乏的是真正有生活有故事并且能将之讲述出来的人,一如叶广芩。因为这样的写作才真正接地气,有人气,有真气。
我们赞赏这种实在的写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写作紧贴地面,缺乏轻盈。恰恰相反,在叶广芩的作品中,真实的体验与虚构的情境相辅相成,在人物追念、文化反思和历史感怀之中,既有着追宗念祖的庄重,也尽可能进行细致的构思和灵慧的叙说,因此她的作品最终飞扬出一种自由的质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虽然叶广芩的写作奠基于经验的土壤,但是她采取了鲁迅说的“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的写法,用笔看似随意,实则别具匠心,举重若轻,收放之中世事人情皆现。
她的《采桑子》和《状元媒》是由中篇连缀而成的,分别写了既相关又游离的家族故事,这种结构非常富有意味。如《采桑子》由“九个既相关又游离的故事,像编辫子一样,捋出了老北京一个世家及子女的命运历程”,这使小说内部自然形成了一种场——独立成篇使作者对每一位人物命运和心态的展示更为自由和充分,同时内在的潜流相通和血脉相连又足以将表面上看似散漫的东西完整地统率在一起,而呈现出一种较为纯粹的历史氛围和浓郁的场域,使我们更能沉潜入人物的内心深层,展现出命运的皱褶和心灵的浮沉。
叶广芩写家族故事,重要的不是描摹钟鸣鼎食的满族世家在历史的车轮中被碾压的窘相和落魄,而是更多将笔力聚焦于时代大潮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冲击,写出了他们被裹挟前行的格格不入和步履维艰。覆亡的王朝将末世的贵族子弟悬置到了时代的尴尬境地,旧有的生活方式已难以为继,但是对新的社会他们既无心适应也无力融入。叶广芩尤其书写了他们在自我实现道路上的挣扎与困境,虽各不相同,但都隐现时代的悲哀。冲出家门追赶时代潮流的长子金舜铻和三女金舜钰,一个加入国民党,泯灭了亲情,断根而行;一个加入共产党,忠于事业,以身殉志;而依然故我、抱残守缺的人同样免不了失落的境遇:《谁翻乐府凄凉曲》中的大格格虽然始终没有勇气和力量冲出大宅门,但是董戈以及他身上带有的正面力量(孝顺、体面和专注)与戏剧融汇在一起,激活了大格格自我实现的意愿。但是,这种内心的呼唤和无意识的追求随着社会的质疑、夫家的打压以及董戈的失踪,最终被逼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大格格被弃、丧子,精神崩溃,落魄而亡;《三击掌》中的老五金舜锫不学无术,玩弄女人、抽白面儿,最终被赶出家门;《醉也无聊》中的老姐夫完占泰虽然出身显赫,也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性情散淡,有学问却不致用,偏居于岳父家偏院,整日纵酒、吃药。金舜锫与完占泰一个颓废不羁、玩世不恭,一个放达任诞、性情散淡,虽然表现不一,但是这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消极避世,实际上都是自我失落的表现。即便像《雨也萧萧》中的老三金舜钅其一样向市井缴械,却也难免承受那种“咬噬自己的心”的心灵之痛,以及精神的失落和灵魂的失重。尽管金家的子女选择各有不同,但是显然这些选择或者碰壁,或者不及物,其命运实质都是相似的生命悲剧。在这样的作品中,不同的人物生命形式相互彰显,显现出末世贵族无处逃遁的历史宿命。叶广芩对家族故事的叙述表现了家族的衰亡,在书写人物的命运沉浮时并不乏清醒理性的历史视野,但是在情感上,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作者对灵魂无从安置的喟叹和对意义追寻的惋惜。家族的式微,以及血脉相连的人物所遭受的毁灭,使一种优雅的感伤在字里行间弥漫开来。
这就是一种写作的巧。《采桑子》和《状元媒》两部家族小说着力呈现的并不是外在化的戏剧,而是那种内在的、潜隐的、萎缩的生命内核。表面云淡风轻,内里却深藏面对历史主体所承受的前所未有的神经痛觉。真正的极品小说应该是这样浑然天成的,里面除了作者所营造的外示于人的在人物关系和社会环境中挣扎奔走的主人公,总要有这样关于人生、命运和世态等的深在底衬。叶广芩的小说就是这样,有的甚至让人感觉叙事的目的性并不是那么急切,而正是因为这种从容,使这些她亲历目睹的故事讲来不动声色、不温不火,却又深深触动着人心。面对覆巢之下的家族,一切均已繁华落尽,叶广芩叙述中表现出来的淡淡伤怀恰到好处地点染了内在的无穷意味,令人心有所触,但又无法淋漓吐露,最终窖酿成悠悠袅袅的酒香。
还有一种写作之巧体现在叶广芩的日本题材小说中。叶广芩在日本的学习和生活使她接触到了大量的关于战争的资料,而且明显感受到了两国的不同角度和审视,正如她说的:“那是两个民族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是打人的和被打的同时捂着脸的思索,尽管脸上都有伤痕,但内心的滋味毕竟不同。”这些文化分析和思考最终转换成了文学。显然,就写作的难度而言,以小说来书写对战争的反思并非易事。因为对战争的反思极容易变成就事论事,或者空洞干瘪的言说。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叶广芩的写作之智之巧。正如有评论者所言,她“始终站在主流题材的边缘,又往往能以极具个人风格的作品切近所谓‘主流’所关注的议题”。她选择的人物在身份上都具有某种模糊性或者边缘性。这就使她避开了被战争风云所裹挟,而更能深入到对历史的复杂记忆之中进行书写,进而使她的反思具有了普世意义的价值。这里所说的“边缘性”是指人物的社会身份难以清晰界定,而且往往处于某种尴尬境地。如《雾》中的慰安妇,《雨》中的广岛原爆幸存者,《霞》、《到家了》、《注意熊出没》中的归国残留孤儿,以及《风》中的汉奸。
《雨》反映的是广岛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生活遭遇和人生态度。叙述者“我”是以“家属滞在”的身份随丈夫在广岛生活的中国作家。故事的主人公是“我”的邻居——一对日本姐妹,文本几乎没有对主人公进行直接的描摹和刻画,而是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来呈现她们的形象。在日常的交际中,“我”从自己的热心和不修边幅,以及老姐妹的疏离和优雅中,不时发掘着中日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处世方式,不断地强化着两者之“异”。但是最终这种“异”被战争对人的生命和生存带来的相“同”戕害所取代。这对老姐妹由于原子弹爆炸的放射性污染对身体带来的影响被社会嫌弃,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战争给人的正常生活秩序和命运带来的影响是深层而难以磨灭的。尤其是她们每到雨天就无法正常生活这一细节,更是从心理的内在层面上揭示了战争的永久创伤。显然,文本中的老姐妹是作为二战罪恶之国中的受害人这样一种身份存在的,叶广芩对同样承受战争之痛的日本人的悲悯观照使我们看到了一种生命的高度。而在《雾》中,叶广芩则选择了更为敏感的“慰安妇”作为表现对象。现实中,“张高氏”被推搡着到现代日本告状的经历和历史中“张英”被迫沦为“慰安妇”的遭遇相互交叉。“慰安妇”这一历史标签不仅昭示了主人公身体上遭受的日本兵的暴力,更带来了国人的鄙视和凌辱。这个一生中曾经叫过张鱼儿、张英、“高”、张高氏等名号的女人在与入侵的日本鬼子狭路相逢之后,就坠入了生命的噩梦之中。她不仅目睹了战友被残害的惨状,而且变成了“慰安妇”。她的“慰安妇”经历显然是对日本侵略者践踏人性的有力指证;但是更为深刻的是,当她历经万难死里逃生之后,同胞们也掷来了鄙视和侮辱的石头。叶广芩再一次从一个有意味的切口,丰满地表现了关于“民族身份、性别政治与话语暴力的复杂内容”。
显然,在叶广芩反思战争的作品中没有炮火硝烟的战场或者枪林弹雨中的英雄,她更多关注的是战争的烟云暗影中的生存和命运。这是对宏大战争叙述所遮蔽掉的空白和盲点的发现和表现,正如叶广芩所选取的,这种巧妙的叙述视角,窥视到了许多隐藏着的不为人知的鲜活生命以及真实的细节和碎片,而通过这种细致的历史寻访,她不仅还原了一些普通人在战争年代或记忆中的命运沉浮,也同时切入了关于人性与苦难、战争与命运、历史与现实等一系列深层主题。
二、节制开阔的叙事
诗人肖开愚曾经将中年写作概括为抑制、减速和开阔,在这里,“中年”概念并不完全是一种年龄的特征,更是对人生的特殊感悟和生命形态的成熟。叶广芩的写作就体现了这样一种“中年”诗学。她的写作总体叙述是平静的,但这种平静并不表示寡淡或者无力,其中自有一种感人至深的情感灌注。所以,叶广芩写作的娓娓道来和质朴无华,从本质上看其实是一种内心翻江倒海而表面不动声色的表达。
就写作技巧而言,这显然出自难得的克制。叶广芩的家族小说创作最大的真实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她生命中种种无法抹去的刻骨铭心的记忆,正如邓友梅所说的:“作者曾从属于那个社会群体,文学写作什么都能作假,惟感情作不得假,于是她在批判、否定那些过时、陈腐、消失了的一切时,字里行间又剪不断理还乱地流露出认同、怀恋的情结。”回顾周遭曾经的没落的人生与失落的生命,叶广芩定也五味杂陈,但是我们却很少看到她倾倒伤痛和怨尤。《采桑子·曲罢一声长叹》中的七哥舜铨被大哥舜铻抢走挚爱并受牵连在“文革”中吃尽苦头,但是他谨守儒家的温良恭俭让,即便相向而对,他也未出一句恶言;《状元媒·逍遥津》中的大秀,面对游手好闲、不事生计的父亲和弟弟,独自默默支撑着,典当家什,补花苦挣,硬着头皮借债,尽力付出,直至父兄去世,淡泊存活;《状元媒·豆汁记》中的莫姜一生坎坷悲凉,但是即便她被满身恶习的丈夫抛弃流落街头,即便当走投无路的丈夫归来直至瘫痪在床,她都毫无怨言,淡定以对,而且还努力保持体面的生活姿态。在关于《豆汁记》的创作谈中,叶广芩曾动情地说:“老太太无儿无女,悲苦一生,命运坎坷,除了厨艺之外,让我敬佩的就是她的平淡随和。仔细回想,我竟从未听到过她的抱怨,无论对别人还是自己,无论对命运还是人生。她默默地活着,默默地操作着,在自己的天地里,那个天地对她来说广阔无垠。”这样的人物身上有着作家深情端详的微温,很显然,这是作家极为珍视的现实人格和处世方式,那是一种困顿之中的华丽。无论生存境遇的优劣和结局的悲喜,人物都拒绝用粗鄙而破落的方式来屈就生活的这种自尊自傲,其实是一种难得的精神气度。特别是当面对屈辱和伤痛的时候,这种不动声色更显现出一种人格的光华。在《采桑子·不知何事萦怀抱》中,四格格金舜镡在“文革”期间,脖子上挂着写着“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的沉重的铁板,一头秀发被推个精光,面颊上淌着鲜血,却也“任凭推搡打骂,脸上只是出奇地平静,不呻吟,更不讨饶”。在《状元媒·凤还巢》中,回京列车上,“我”心里默默细数自己十三个兄长和姐姐或逝去或受辱的命运,轻描淡写,没有追问也没有声讨,说到最后,只一句“我到陕西插队”交代完毕;作者的回溯一如既往没有水深火热的控诉,但是语势的紧凑无疑昭示了她内心深重的伤痛。显然,在这样的写作中,作者并非是以人物的悲凉人生换取读者的同情或悲悯,这不是她的初衷。正如她自己在访谈中说的,之所以在《状元媒》中写到父母的死时很节制,只用了“无枝可栖”一笔带过,是因为“书里死的人多了,再写父母的死就太重复。如果我写得详细了,读者会觉得有点絮叨,好像我叙说苦难博得同情”。而正是这种对苦难和痛苦的节制叙事使她的作品获得了一种开阔的情怀,也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温情的力量。
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中说:“文学的力量,不在开扩,而在集中,不在放纵,而在节制。”真正成熟的创作依靠的绝不是情节的繁复或者情绪的奔涌,而是在情绪和感受的支撑下,从容自如的叙述节奏和平衡节制的开合状态。而这首先得益于她苦难与丰富人生的馈赠。没落之家的出身和文化背景,以及多样的人生阅历锻造了叶广芩不同寻常的宽阔的文化视野和深远的历史意识。格格插队、被批斗示众、务农养猪、做护士记者,直至写小说,叶广芩的人生可谓沉浮多舛,但是她没有像祥林嫂一样逢人就敞开自己的伤疤喋喋不休,这种言说往往会适得其反,只能被人厌弃。叶广芩的作品中有一种真正的成长和成熟,就是并不一味沉浸于“伤逝”的情感旋涡中,而是让一切趋于平淡,以超然和平静的心态将自己的感伤潜隐于对往事旧人的追忆之中,在平淡朴实的叙述中自然流淌出历史的沧桑感。对作家而言,写作并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因为情感的过度充盈和言说激情的挥霍喷洒往往会对想象力挥金如土,这样的文本情感汹涌澎湃,但是缺乏静水流深的内涵和张力。因为一旦这样做了,就会堵住读者想象和融入的可能。叶广芩的写作之所以舒缓从容、节制开阔,是因为她对家族物事的深情眷恋之中有一种理智的突围。正如欧阳江河所阐发的:“中年写作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极其相似: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叶广芩对生活的洞察非同凡响,这种转换体现在作品中就是怀旧与反思交织,体现出情感与理智的交融。
这首先表现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因为叶广芩在小说中融入了自己的文化理想和文化选择,因此虽然我们在作品中能感受到她对所钟情的人物的心醉神迷的叹惋,在情感上她寄托了太多的认同和感情,但是情感的皈依并未遮蔽理性的光照,所以我们虽然在她镇静的讲述口吻中能真切感受到深藏的人生和时代的痛感,但是自成体系的审美转换从内部冲淡了悲剧的黏滞,从而营造出了一个平衡的精神空间。《瘦尽灯花又一宵》就集中体现了作家对传统没落家族的固执可悲命运的哀悼与反思。“我”每年过年都不得不到阴气沉沉的老王府中去过年冲晦气。王府中只有两个孤老太太,是“我”分别唤作舅太太和舅姨太太的福晋和侧福晋。舅太太们所代表的那一套烦琐礼节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已然褪尽优雅,只剩下了陈腐僵化的外壳。问候行礼、起卧行立,舅太太们的做派依然按照王爷府上的规矩来,而且言谈举止之中还紧端着尊贵的架子,这种自以为是和不知魏晋的自我认同可悲可叹又可笑。其中最富有象征意味的是舅太太从精美的饽饽盒里拿出的萨其马。舅太太以赐给“我”吃这种出自有名的桂英斋的宫廷点心为傲,并直言是“我”的福气。但是,事实上,这块萨其马年月已久,坚硬而且有一股难闻的哈喇味儿。这种施者与受者的感受之悬差自然彰显出了“我”对舅太太所代表的没落文化的反思与摒弃,但是当写到孤苦舅姨太太对儿子宝力格的思念的时候,当说到无依无靠的舅姨太太被我家收容后的生活的时候,双目失明的舅姨太太内心不安但是闻声便脸上堆笑以示满足和感激,甚至暗地里用满文详细记录下了在“我”家生活的吃喝用度流水账,以便让儿子宝力格将来如数偿还,我们又那么真切地感受到“我”内心的沉痛,这是一种牵筋扯骨的感伤。
叶广芩对传统文化的怀恋和对不随流俗的人格精神的肯定与赞美显示出一种精神上的选择,也正因为如此才有论者这样说:“她的视界显然比她那位同宗族的词人(指纳兰性德,笔者注)要高一些,写没落而不颓废,叹沧桑而终能释怀,感伤的同时更有历史的审视意识,同情的同时更有批判的深度,叹往却不忘今天的历史尺度与高度……”这种选择对当下欲望化的世界有一种明显的对照和反拨,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叶广芩小说中的对比结构正体现出一种理智的现实意义。
特别是面对家族内部的质变时,作家沉痛的笔触中隐含着一种隐忍的愤激,甚至那种近似批判的情绪也呼之欲出。在《雨也萧萧》中,整个家族包括老三舜钅其集体疏离隔弃了二格格舜镅,只因她执意嫁给了经商的人家,而金家以世家自居,鄙视甚至痛恨重利忘义的经商之人。但是,几十年后,厌恶商人的舜钅其却利用家世背景做起了坑人自肥的买卖。在鉴定文物时,他利用人们对世家子弟眼光的信任,将真说假,从而低买高抛,从中渔利。舜钅其不仅从了商,而且还是奸商。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当时被鄙弃的沈家则远离商界,富而不骄易,贫而无怨难,真正拥有了宁静之心。在这种对比中,叶广芩深深关注到了人生于世的一种悖论:人心在物质的追逐中日益膨胀,但是心灵却饱受被蚕食的苦痛。
在《状元媒》和《大登殿》中,半个多世纪前的母亲在新婚夜喊叫哭闹大打出手,是因为知道了夫家还有一位夫人,而母亲在乎名分,做妻不做妾。为此,母亲与其弟陈锡元远赴天津找状元媒人讨要说法,直到听到媒人刘春霖的回答是“媒妁之言……明媒正娶”之后,方才认账。老一辈对名分的在意其实事关人格和尊严,母亲对自我身份的坚决确立和决不妥协的辛苦求证令人敬仰;而同时穿梭讲述的现代女性——六姐之女博美的人生选择和态度——大学毕业,一事无成,到最后甘愿给商人做“小”,吃喝玩乐,而且乐在其中,还自诩这是“社会进步了”。叶广芩在这里对这种代际之间的反差用了“变异”一词,并且直接质问:“年轻人,你缺了点儿什么……”一贯平和的叶广芩竟然表现出少有的愤慨,由此可见对这种精神危机和情感缺失怀有极其强烈的忧患。
而同样的“变异”也发生在《雨也萧萧》中的三哥舜钅其之子金昶和《曲罢一声长叹》中七哥舜铨之女青青,以及《醒也无聊》中五哥之子金瑞的养子段发财这些金家晚辈身上:金昶不满于父亲归还祖母留给姑母的帽饰,而且认为父亲信守承诺太傻;青青为了拿到商家的钱,跟母舅一起强迫父亲舜铨违心题写广告语,以致舜铨盛怒难抑,病重入院;段发财这个跟金家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人在新时代改名为爱新觉罗·宓,因为少数民族身份会有一些现实的实惠,比如孩子高考加分之类。这些金家的晚辈们不再具有世家子弟的儒学门风,他们的彻底市民化与市侩化也似乎意味着传统文化的颓败已触目惊心。作者在这里的强烈批判态度与深层的文化忧虑均不言而喻。在崇高和理性渐被消解的新世纪,有很多的作家意在连缀生活的碎片,以及宣泄自我情感,叶广芩的这种批判意识显示出了作品的理性,也使作品在自我追忆和情感缅怀的同时仍然保持了比较博大的历史格局,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有力的历史主体自我意识。
其实,她的理性观照并不仅仅局限于家族内部,更投射到满族这个民族的命运之上。叶广芩是满族贵胄出身,但是她只生逢民族颓败时分,又加上她半生的生活历练和文化养成,她的作品在对民族的本然认同之中毫不掩饰地包含着批判。她在不少作品中都对末世贵族的人生态度和现实选择进行了表现和评论,尤其是在《状元媒·逍遥津》中,末世贵族们把花鸟虫鱼侍弄得风生水起,充满了艺术情趣和贵族格调。“七舅爷”和儿子青雨对自家上顿不接下顿的现实困顿毫不上心,却不惜耗费大量的财力和精力去伺候蛐蛐和鸟,甚至用城郊的一亩七分坟地去换一只蝈蝈。他们现实贫寒的生活在提笼架鸟的姿势映射下充满了美学的质感。但不可避免,这其中也包含着一种现实生存的反思:这种八旗遗风包含的不仅仅是表面的自由和超逸,事实上更是对生存艰难的逃避。叶广芩在很多的作品中都对八旗子弟在清末民初的生存现实和精神失落作了观照,他们从骑射勇猛蜕变成遛鸟票戏,其中的退化和散漫在更深层面上是人性的萎缩、衰弱,提笼架鸟以避困境的情形,传达出的其实是一种软弱和麻木。
叶广芩这些自我体验式的文学虽然展开的是前清贵族的挽歌式叙事,但是浓郁的亲情和深沉的缅怀并没有沉醉于伤感的泥沼,温文尔雅的叙述也未曾放弃批判的锋芒。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叶广芩的写作具有“中年诗学”的特征——成熟流畅,因为很明显她的写作并不仅仅是凭借激情和才华,更依靠的是对激情的控制。也正因如此,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剑拔弩张的冲突或者血泪成河的嘶吼,但却更容易让人陷入深思。狄德罗说过,艺术“所要争取的真正喝彩不是一句漂亮的诗句以及陡然发出的鼓掌声,而是长时间静默的压抑以后发自心灵的坐卧不安”。一如叶广芩的作品风格——貌似轻松实则刻骨铭心,具有别样的艺术力量。
三、存照与铭写:一种民族志诗学的解读
所谓民族志是指对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思维以及制度体系等方面进行系统描述的一种书面文本形式,其基本作用在于展示不同族群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叶广芩是满族出身,对于继承到了发肤血液和精神内核的母族,她有着深厚感情,满族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精神内涵都深深印入她的记忆和情感的最深处。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叶广芩的作品包含着旗人的生活史、人物志以及风物志,在这种写作中,作者对世界的个人感知与民族的象征图式交融在一起,世俗生活与文化世系以及精神传统互为表里,特别是在当下社会空间、生活经验和文化表征日益趋同的情况下,这显然具有民族志的诗学特征。
叶广芩曾不止一次提到,“我是旗人,祖姓叶赫那拉”。作为满族后裔,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文学创作中,叶广芩都有着自觉而鲜明的民族归属认同。她与生俱来的满族意识以及深浸其中的文化熏陶使她对满族历史兴衰的书写不仅充满着深入的历史反思和现实对照,同时也记录和展示了旗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内涵。她的《采桑子》和《状元媒》在温婉的语调中冷静反思了没落的晚清家国历史,同时回瞥旗人生存境遇与京味文化的流韵,也进一步开掘了文化写作的路径。满族统摄中国之后,为了弥补本族文化的薄弱,提高旗人的文化素养,帝王下令旗人只习文练武,专事统治事务。这改变了旗人只会骑射的状况,但同时也断绝了他们在游牧历史中延续的生存技能,以至于清朝覆灭之后,旗人贵族的社会特权一消失,他们都从云端跌下来成为窝囊废。叶广芩将这种社会现状和满族的这种文化变异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来。《采桑子》中,金家子弟似乎各有所长:大格格舜锦京剧唱得名满京都;老七舜铨的工绘画不输名流大家;老五舜锫书法遒劲飘逸,颇有功底……百年来的民族规训使这些贵族世家子弟的言谈举止充满超逸的气质和潇洒的浪漫,七舅爷和青雨即便放风筝也放得精致、精巧,引来啧啧赞叹。但是他们的才艺和情调在改朝换代的巨轮中仅仅成了掩饰自己现实困顿的苍凉姿势:大格格和老五未得善终;老七一生清贫,虽然内心的坚守着实难得,但是现实的退避令人心酸……叶广芩将彼时的社会现状和文化表征尽数展现在了小说创作中,这种写作显然具有了难得的文化内涵。
作为满族作家,叶广芩对满族文化的叙述不仅仅是对自我情感和血统的追溯,更是在群体意义上实现着对本民族的自我形塑和言说,在这些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情绪和思考实际上也指向与一个民族的历史、存在和命运休戚与共的集体意识。因为,母族群体的生存境遇和文化命运意象是少数民族作家难以规避的主题。特别是,满族是现实中民族意味和文化传统逐步失落的民族,叶广芩的写作本身就是作家凭借读写能力进行的针对时间侵蚀和物质消损过程的对抗,正如本雅明所说的,“对事物的短暂性的欣赏,以及为了不朽而挽回它们的想法,是语言中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一”。
在汹涌的城市化进程之中,现代社会呈现出同质化、一体化的生活景观,而那些在时间、空间和精神要素上不能归属于现代的异质性文化就失去了容身之地,关于母族的记忆不可避免地日渐涣散和淡漠,民族仪式和风俗传统渐渐失落,甚至民族语言和伦理秩序也遭到了严重的侵蚀而岌岌可危。在此语境之中,叶广芩对旗人生活和文化的表达不仅是一种再现式的记录,即把“正在消失”的民族经验和记忆从即将逝去的时间中解救出来,更是一种唤起式的重构,已然衰退的民族传统引起了作家对母族命运的探照。她的对民族文化的“存照”式书写包含着明显的怀旧情绪,这种追忆模式通过对过往生活的视觉记忆提供美的见证,表达作者对美好时代的哀悼和怀念。
旗人文化或生活图景中最重要的是“优雅”。在这里,作者沉酣其中的优雅是一种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在《豆汁记》中,穷门小户出身的母亲和宫里出来的莫姜是两种饮食文化的代表:母亲代表的是炸酱面、疙瘩汤、炖萝卜等大众吃食,虽然简单粗糙,却顽强恒久,正如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令“我”啧啧称奇并大费笔墨的却是莫姜做的精致饮食:花生仁要泡过再炒;豆汁是用锯末熬成的;“熟鱼活吃”要取活鱼开炸;就连下里巴人的麻豆腐也做得精致无比:羊腰肉切丁,香油烹炒,放入青豆、雪里蕻、胡萝卜丝,单搁出,再炒黄酱,加麻婆豆腐,炒至香味四溢时加作料,充分融合,起锅,盛入淡青色盘中,中间打个窝,浇上现炸的辣椒油,四周撒上青韭,方才上桌。这种精致极容易让人想到《红楼梦》中曹雪芹所描摹的生活,但又比那种奢华的精巧更家常一些,而且唯其有着日常的底子,这种精致才更为动人:小米粥熬得黏稠腻糊,小酱萝卜切得周正讲究,这种赏心悦目甚至在极为困顿的时候也不改其雅。在《逍遥津》中,艰难度日的大秀只能端上清水疙瘩汤,但是桌上却摆着一个个小碟,碟里有各种咸菜,看着热闹而已。叶广芩直言:“北京的穷旗人想来爱摆谱,所谓的倒驴不倒架……”这其中虽有自嘲讽人的文化影射,但是从情感上来看,显然叶广芩是认同这种姿态和雅趣的。
在《曲罢一声长叹》中,淡泊儒雅的七哥舜铨做的精细万分的糖醋白菜,是金家传统食品:取白菜心切成棱状,再与雕成梅花形状的红胡萝卜同用白糖和上好白醋腌制,吃时再配以鲜绿香菜,红绿白相间,好吃又好看。七哥家饭菜简单,但餐具精美,这也是舜铨在力所能及的情形下所能保留的优雅之风范了。在《醒也无聊》中,王玉兰端来的浆水菜是陕西特有的腌菜,将新鲜蔬菜窝在缸里以面汤泡制,使之发酵,有一股死酸傻酸的臭味,“我”只能勉强吃一口,而金瑞更是不客气地说这是“喂牲口的饲料”。作家对两种小咸菜的态度其实是两种美学取向,这在新的现实背景中并不关乎贵族血统或者世家出身,只是一种对生活质量和人生姿态的追求,就像尘埃中开出来的花朵,叶广芩所欣赏的就是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坚持情调和风雅的人生方式。英国批评家克莱夫·贝尔认为美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我们惯常所说的“文化”其实就是指人类各种外显或者内隐的行为模式及其符号化,它更多体现在人们习焉不察的饮食起居中。
叶广芩的小说还再现了大家族中严整的旗人礼仪和人伦观念。《风也萧萧》中,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现代北京,舜钅其回到家之后,抢上几步挡了年迈母亲的下床迎接,“给母亲请了安,问遍了家里一切好,这才转身落座,接过我端上的茶,接受舜铨和我的问候”。正如“我”所感慨的,舜钅其的一举一动都透着旗人的礼数,渗透着从容不迫,渗透着大宅门儿的教养。而在《雨也萧萧》中,被认为背叛了金家的舜镅要求沈家的后人要谨守金家的礼节,四十年后的沈继祖在电视剧拍摄现场见了“我”还能按照旗人的规矩行礼,做出了地道娴熟的满族请安姿势,引得演员们前来请教。在这里,我们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到仪式本身所含有的文化魅力。同时,沈继祖所行礼数受到的关注和临摹在一定意义上也彰显了叶广芩文化写作的必要性和意义。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对儒家家长制的批判和离弃,传统的孝文化精神在现代中国已然涣散,礼数更是知者甚少。事实上,精神的内涵和外壳之间必定有着不可隔断的关系,礼数是一种仪式,成熟的仪式会使人的姿态行为呈现艺术化的美感,更能时时促使人内心的自省和修养。在日渐淡漠和自以为是的人心环境中,叶广芩对礼数的描写不仅仅是对形式本身的追溯,其实更是对传统优雅恭敬的人心的呼唤。
而作品中那些对旗人传统节日、婚丧嫁娶、唱戏,甚至宫廷生活等富有文化特性的场景的描写已经超出了仅仅对满族文化的执著,而是对更广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珍视。建筑就在其中占有很大的篇幅,她对中国古代建筑有着不厌其详的描绘,她笔下人物对东直门和成王府等都表现出由衷的欣赏和不舍。建筑本身所具有的艺术和精神的双重性,都充分展现了可贵的文化形态,而且建筑之美并不只体现在美轮美奂的戏楼等飞檐立柱、彩画和玺等极尽讲究的建筑实体本身,更体现在建筑精神和技术上。传统的阴阳五行之影响使中国建筑讲究“风水”,正如《不知何事萦怀抱》中的廖世基、《全家福》中的萧益土所说的“中国建筑的气运”和“气势”,比如他们这样说到东直门:“北京城八座城楼,彼此不可替代,各有各的时辰,各有各的堂奥,各有各的阴阳,各有各的色气。城门是一城之门,是通正气之穴,有息库之异。东直门,城门朝正东,震位属木,五季占春,五色为青,五气为风,五化为生,是座最有朝气的城楼。每天太阳一出来,首先就照到了东直门,它是最先承受太阳的地方。”这其中所包含的玄妙而神奇的艺术精神和历史理解为我们开启了理解建筑和传统的窗口,更使她的作品具有文化志的内涵;更进一层,建筑师们所珍视的“水鸭子”和“玉坠”等建筑工具所意味着的,并不仅仅是“找北”或者“吊线”等操作用途,更是“平如水,直如线”的行业规矩和做人准则,而且由此延伸出来的坐北朝南、方方正正等规矩更是人伦秩序的象征。
叶广芩喜欢穿旗袍,她说:“我是旗人,穿旗袍是当然。”她在写作过程中所流露出来的对文化的审美展示,并不仅仅是碎片式的捡拾,更是充盈于小说叙述中的一种情感,“即叙述的张力或整体象征,或与此相关的那些活跃在叙述背后的‘弦外之音’”。对叶广芩来说,家族和文化的叙述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情感责任的,叶广芩出身于八旗贵族,其后虽历经世事沧桑的变化和现实生活的磨难,然而那曾经浸润其中、与之血脉相连的旧式生活和古都文化风习始终是她挥之不去的精神缠绕。她在作品中所呈现的这些携带了个人丰富记忆的文化景观,是关于母族满族的文化寻根,也是关于北京大院的日常怀旧。作品还有很多对往昔生活的描述,如“生炉子,老北京叫‘笼火’,是居家过日子一件寻常又麻烦的事情。笼火需用劈柴、刨花将乏煤点燃,再装硬煤,冒半天大烟,旧时的北京一到早晨满城是煤烟味儿”(《豆汁记》)。在《状元媒》中,她所描述的卖打虫子药的“虫子铺”,卖满族糕点的“饽饽铺”,院子里树上的枝杈上爬满的“杨剌子”,炕桌上的“糨子盆”,沿街“锔碗”的手艺人,等等,这些已经罕见或消逝的文化礼仪或者生活场景,因为是隔着时光的回望而尤其显得温婉,怀念之中含有脉脉的温情。在这里,作家实际上充当了发掘者和阐释者的角色,她写作的民族志性质本质上是将一种文化传达于当下。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叶广芩是采用理性观照的方式来书写自己所钟情的文化的,视角并不全然是内部的经验,更有超越的审视,她的策略基本上是通过一种“过去/现在”的双向观照来实现传统文化的“存照”式书写:对“过去”的再现闪回在作者片段式的回忆之中,包含怀旧情绪的追忆模式,一方面通过对过往生活的视觉记忆提供美的见证,另一方面则指向对“现在”的缺失性参照,对“现在”的书写集中于对“失去”的结果和过程的表达。正如有论者曾经指出的:“后现代民族志……意图在读者和作者心中唤起一种关于常识现实的可能世界的创生的幻想,从而激起一种具有疗救的审美整合”。这是文化书写的真正意义。诚如戴锦华所说:“任何一种怀旧式的描写,都并非‘原画复现’,作为当下中国之时尚的怀旧,与其说是在书写记忆,追溯昨日,不如说是再度以记忆的构造与填充来安慰今天。”
作为一位真诚而达观的作家,叶广芩稳中求变的写作姿态和悠远哀婉的审美品格,使她对家族、历史和自然的书写既沉酣其中,又清醒理智,既细腻生动又从容舒展,在不慌不忙的“微温”叙述之中寄寓了作家对世界的理解和深情。在我们这个浅阅读成风的时代,很多的所谓“艺术”都陷落在功利的旋涡中,但是她既不迎合潮流,也不配合市场,只倾力于表达那些细微的感伤情绪和优雅的文化书写,这些文字熨平了我们被粗粝的物质忧虑和急促的行走脚步所促生的皱纹,让人不自觉能拥有最令人舒适的呼吸,这就是小说存在的理由,正如米兰·昆德拉说的,它总是“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