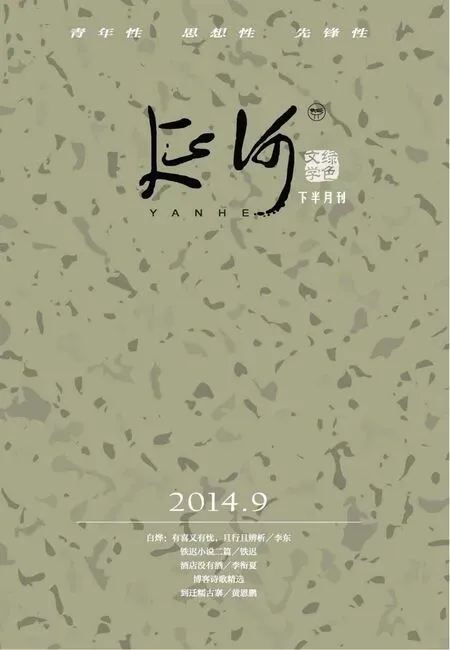置于碎片化现实中的人性透视
——短篇小说《酒店没有酒》阅读札记
△ 芦苇岸
置于碎片化现实中的人性透视——短篇小说《酒店没有酒》阅读札记
△ 芦苇岸
芦苇岸,笔名映晴,土家族,诗人,诗歌评论家。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1989年发表作品,迄今已在《人民文学》《诗刊》《十月》《山花》《江南》《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过小说、诗歌、评论近百万字。现供职于浙江省嘉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吴越出版社。
在我印象里,80后新锐李衔夏有些“急”,不过这“急”非“着急”,而是类似于欧仁·尤奈斯库认为的“前风格”。这可以理解,勃发的年龄,如老态龙钟状,断然是不合拍的节奏。最先,知道他眼光紧盯一些平庸刊物所发的无效诗歌很是起劲地评点,有些担心他如此而失去文字的根性与锐度。确实,他的诗歌样式受浸不浅,还好有小说,比较充分地展示了他的自在与自如,似乎真是如此,每个人终有属于自己的拿手表达。这篇《酒店没有酒》,让我真切地看到他那名副其实的“急”:带劲儿、热烈、极富穿透力。
小说《酒店没有酒》以一个反讽植入式的定调在阅读层面打开了特定群体的现实经验,显然,这是一篇解构宏大叙事而前置倡导人性真实的断面浮雕的短制。
《酒店没有酒》的故事不复杂,但这并不影响小说的丰富性。培训机构的宣讲师李勿常年奔波于各大城市,这个预设的伏笔意味深长。这里,“奔波”是带动叙述游走的巨大诱因,也成了生活意识与人事发展的重要“触点”,更是“当下人”生存状态的影像缩略。城市的夜晚,一个在没有选择余地的男人与一个因家庭问题离家出走的女人“拼居”于酒店的最后一间空房,而且是双人房。这本身就潜在着好看的“故事”。在这个并不新奇的“故事”容器里,“人”的可能性被玻璃折射从而发生了变异。如果男人的本能冲动在可控之列,属于常态的话,那么,女人的理由,则反映了当下市井里微妙的婚姻观,“她”找了七家酒店都没房不想露宿街头,于是向李勿提出同房的请求。伤心诱使的潜意识里隐约希望以出轨来报复丈夫。这在道德评判方面看,似乎不可理喻,而在具体的人具体的心境中,就“没有什么不可以”了。
但这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向,也是,仅仅停留于此层面,小说就会很“没意思”。生存压力与青春激情在深夜的异性面前,充满慌乱、激动和许多言而有趣的细节。大李勿五六岁的“她”有着现实中的多数家庭妇女一样的正派,一个并非水性杨花的女人在特定境遇下的“出格”似乎就理所当然地带有戏剧感。“我想我需要一点酒。”这个“她”用以突破防线的理由比较荒诞,但结合人物性格细察,也算是在合理的范畴。
没想到在关节上,飞奔到前台去买酒的李勿却被告知:酒店没有酒。这无异于急待起脚怒射空门时突然崴了脚一般的“意外”让故事在高潮中陡生转折,并增强了可读性,对此,小说的落笔是,情急之下的李勿终于冲破了性格的局限,简单粗暴地实现了人性的最后释放。
阅读中,不免生疑,这是情色题材吗?答案是否定的,作为主干线索的“情节”本身是不具备“艺术”深度的,它需要作家的创造智慧的介入。索尔仁尼琴在《为人类的艺术》中写道:“艺术家之有别于常人的,仅仅在于其感觉敏锐;他较易察觉世界上的美与丑,并予以生动描绘。”其中的几个词“感觉敏锐”、“较易察觉”、“生动描绘”是最为关键的,是横亘在“艺术家”与“常人”之间的“三座大山”,什么时候,常人拥有这些高峰,就能够彻底地艺术人生。
作者李衔夏的“感觉敏锐”在于,能让简单的“情节”生变,并在“变”的同时将小说的“意向”导入高度现实化的语境及生活现象之中。从“偷拍”到“窥”到“围观”,私密被暴露和人性的社会化直播,以及由此而影射的欲望乱码,加大了小说的内涵,正是“偷拍”这个“节外”的覆盖让小说不至于笔止意尽,有了更大视角的深刻。小说分成五节,第一节和第四节是主角视角,第三节是偷拍者视角,第二节和第五节是真正叙述者的视角。写法上,作者起先故意让读者以为是“全知”视角,在最末尾才亮出叙述者的身份,打破全知视角格局。作者的结构意图告诉读者,主角和偷拍者的视角都是真正叙述者模仿而生出来的,真正的叙述者是购买碟片来看的人,而这个人是认识男主角的。这能让读者感觉到,男女主角发生在酒店的过程随时能被他们认识的朋友看到,这是小说要达到的效果之一。不过整体看,感觉还是浅表了一些,尤其是结尾一段的交代,笨拙、饶舌,桎梏了小说的延展性。
今天,当享乐成为一种时尚,是非的界限已陷入模糊混淆的无奈时,文学作品的关涉就显得很有必要,小说描写的是焦躁生活背景下碎片化的凡人情感状态,反映了人性的凋敝及其精神荒芜,揭示了市井小人物在阴暗而琐碎生活中内心的茫然和虚无。这种微茫的人生凸显了时代洪流中的“这一群”必须面对的挫败感和漂浮感,精神建构与个体生活之间找不到有效的关联点,个人生活中缺乏积极的现实维度和主体意识,表现为以一种近乎“油滑”的态度面对生活和他者的虚无主义。肉体的堕落与灵魂的挣扎组件,将时代背景下支离破碎的人性无情地形象化,并暴露无遗时,人们对人文精神的呼唤,期望唤醒温暖情感的在场就越是强烈。这样具有自觉的语言意识,以人性观照为向度的写作涉猎其实是对接了“五四”时期鲁迅、郁达夫等作家的小说风范,市井中人性深处的欲望煎熬与精神彷徨,是文学迷人的风景。
当然,这种审美对人本主体感官的迷恋,以及对当下人的困顿与挫败的缠斗无疑冲淡了创作主体的高迈情意,尽管要赋予这么一个短小作品更多意义的承载,和更大精神建构的要求未免过分,但作为执手灯塔上的那一抹光源的作家,眼光可以越过“沉郁”之外的视距,找到更远的激情穿越。那些高亢昂扬的质素,不应该在“此一群”作者的笔下缺席。我曾与茅盾文学奖得主之一的杭州作家王旭峰聊起当下文学的状况,她认为目前中国的小说创作缺少作家个人与现实生活高度统一的大气之作,写小情调,看新闻编故事,以阅读经验替代个人洞察的文本泛滥成灾,因此出挑的作品不多,所以有“文坛暮气”之说。
以此参看当前文学新军的状态与状况,会发现,“生活热力”的缺席是一个普遍现象,真实、丰满、鲜活的文学形象难道非得都是“向下”的?但愿这些絮语不是题外话。
责任编辑:李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