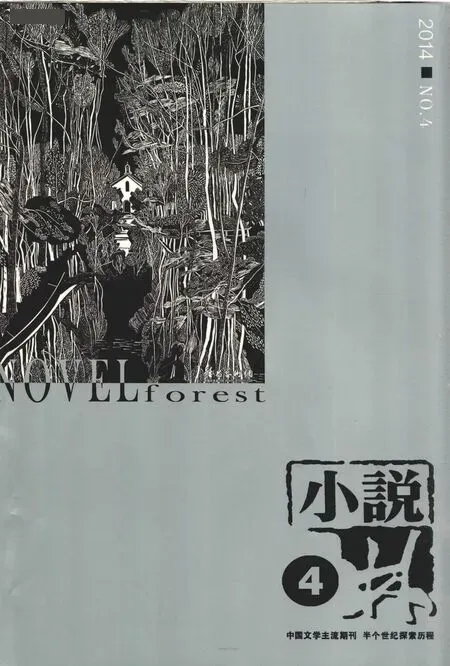除了人我现在什么都想冒充
◎阿 丁
马尔克斯有一位擅讲睡前故事的外婆,这位不知名的老人是他的第一位文学导师。然后才是卡夫卡、鲁尔福、海明威与福克纳……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对于有志于文学写作的青年人而言,有一个会讲故事的姥姥很重要。
此处的“姥姥”,未必就是指一位具体的老人,“她”的本质是“传统”,文学传统。
我的确有这样一位姥姥,她曾经作为一个温暖而柔软的肉体在人世存在,而今她老人家已过世多年,墓木早拱。然而作为对我曾施加影响的“传统”,她还活在世上,在我的记忆中活灵活现。至今我还能轻易地从芜杂的记忆中辨析出她的声音、强调和讲故事时的神态,当某个故事需要她卖个关子时,老人狡狯而调皮的眼波流动在我的记忆中依然鲜活无比。作为外孙,我以回忆来缅怀她。当我拥有足够的写作能力之时,她在我的小说中复活,虚构的姥姥与真实存在过的姥姥一样慈爱而真实,以这种方式,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变回孩童之身,随时随地钻进她的怀里,抱她,亲吻她,听她讲那些我至今还能记得的故事。
姥姥的故事是一切农村老太太的故事,不外乎鬼魂精怪。那时故事里的鬼魅就隐伏在窗外,随时会探出尖利的爪子破窗而入。她发觉了我在她怀里的颤抖,就不再讲,哄我睡觉,可我不干,尽管我的鼻尖已经感觉到了鬼魂阴冷的呼吸,可我还是缠着姥姥讲下去。再后来,大些了,识字了,姥姥却失明了。我就捧一本《白话聊斋》读给她听,姥姥听得饶有兴趣,几个故事读罢,老人松开盘坐的腿,两只小巧的足尖交替摆动,她不无得意地跟我说,“这不跟姥姥给你讲的差不多嘛——”
我因此而更爱她,从来不觉得这是对蒲松龄先生的贬低。两位不同年代的老人是有共通之处的,茶棚下的蒲松龄与我的外婆,同属文学传统的薪火相传者,都可亲敬。
郭沫若曾为蒲松龄故居题楹联一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聊斋志异》的确高人一等,它的高人一等即对人性的描摹呈现超乎他作。鲁迅先生也说,“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诞,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鬼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为什么“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当然是“多具人情”,当然是因为蒲松龄为其笔下的花妖狐魅注入的人性。有人每每提到文学性,那么何谓文学性?我的看法是,文学性即人性,即便二者不能等同,至少可以说,流溢出真实人性的文字,就是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反推之,比如有人写人,读者读到最后一个字,也嗅不到丝毫人味儿,这可说就是文学性阙如。另有人写鬼写兽,却依然可撼动人心,这个本事,西方的杰克·伦敦与西顿,麦尔维尔和福克纳也是有的,他们笔下的狗狼鲸熊,在其毛皮之上,同样泛着人性之光。于这一层面之上,放之世界文学范畴,假如总是捧出四大名著晾晒,堪与今人以四大发明壮阳媲丑、媲鄙陋与狭隘,骨子里漫溢出的虚弱感实无不同。能与西人比一比且不落下风的,《聊斋志异》是一个,《唐传奇》算半个。在世界短篇小说殿堂中,聊斋的成色并不输于其他作品。其世界声誉稍弱的原因,我想你可以从我的幼时读物《白话聊斋》中找到,那种蠢笨浅薄的现代汉语完全湮灭了蒲氏文言的美感,灵性与灵动毁之殆尽,堕落为货真价实的“失魂落魄”之作。少女婴宁的“我不惯与生人睡”变成白话文之后全无娇憨之感;《罗刹海市》里美丑媸妍的荒谬反差,被胡乱翻译之后荒诞感几乎不见;陶生醉酒幻化为菊,在白话文中根本就无法读出那种轮回寂灭的怅惘。所以啊,假如你热爱聊斋,就去读它的原文。假如你古文不够好,就让它够好,好到足以读出原文的妙处。别无他途。
而我最近在做的,并非将聊斋重译,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该算是多年的一个不死心吧,犹如见猎心喜的猎人,如果不能将之变成自己的囊中物,难免心有不甘。对我来说,《聊斋志异》就如同一座储量丰富的小说之矿,不开采一番并化为己有实在说不过去。古人也说,遇宝山不可空手而归。重述聊斋——这是我认为的,向蒲留仙老先生致敬的最佳方式。这种事写《故事新编》的鲁迅干过,写《东方故事集》的尤瑟纳尔干过,而据我阅读所得,卡尔维诺的《祖先三部曲》,也丝丝缕缕发轫于意大利童话(卡尔维诺亲自整理有上下两部《意大利童话集》)。既然先贤做过,我也斗胆试上一试。您现在读到的这篇,就是据《席方平》而做。假如您读过原著,你会发现二者的不同——我已“狂妄”地将之重述得面目全非……
在蒲松龄的《席方平》中,阴间终究是有指望的,二郎真君最终以正义之神的角色为席氏父子伸了冤。而在我的“席方平”中,冥界没有任何指望可言,那里没有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单调的颜色与呆滞的几何体是我认为的无望之地的标志,凡此种种,皆是我内心投射,已与原作无关。我的席方平最后所遭受的酷刑,反而是无损躯体、也绝无疼痛地活着。
世上每一块无望之地,肉身的存活在我看来都是顶级的酷刑。
此后我还会写更多的篇目,我会变身为花妖树魅灵狐怨鬼,竭力勾勒“心中之鬼”。驱使我这么做的另一个缘由是:当你年齿渐增,当你阅世日久,当绝望不断打扮成希望,将更多更重的生而为人的屈辱与刺痛注入你的血脉与髓腔之时,会有一朵善恶杂交的花在你心里孳生,而此时我正在做的,就是拼力超越道德伦常、善恶生死,心如止水地端坐在花之前,来一次不动声色的写生。
譬如一个勇气不足的厌世者,他之所以还苟活于世,原因或许只是基于这样一个念头:除了人我现在什么都想冒充。虚构写作无疑是“冒充”他者、冒充世间万物、所有生灵的唯一可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