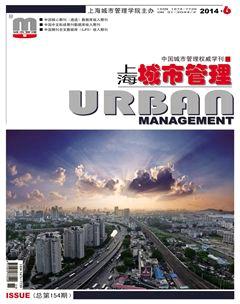微时代下城市网络的舆情危机及治理对策
徐世甫
导读:微时代下,由于微博微信类自媒体使个体的主体性得到充分释放,“沉默的大多数”第一次真正开口说话传话,而那些具有爆炸力的负能量的话语更易传播,特别是与城市的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对接时,城市网络舆情危机一触即发。这些危机根本上来说,大都是城市现实危机的延伸,微时代下它们传播得更加快速,呈现弥散化、谣言化,危害性更大。城市的政府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发挥政务微博、微信公共平台“定心丸”的作用,释放正能量,并利用大数据的优势,研判动态,及时纠错,化危为机,最终为城市创造安全的舆论生态环境。
关键词:微时代;城市网络;舆情危机;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4.06.008
近年来,随着web2.0的蔓延,网络发生了阶段性质变,网民主体性的复归具备了最重要的技术支持,而现代性在中国持续深入地推进,人们的主体意识,权利观念越来越凸现,主体性又获得了人文推力。更值得一提的是,微博和微信的崛起及其爆炸式的增长,特别是其对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渗透与重构,这些叠加彻底激活和更新了网民的主体性。人们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微世界”——微博和微信建构的主体化世界,由此,一个由微博和微信定义的时代——微时代诞生了。
一、微时代:城市网络舆情危机发生的境域
微时代,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指以微博作为传播媒介代表,以短小精炼作为文化传播特征的时代。可见,微时代的“微”是直接取自微博微信类与“微”有关的网络新技术,这是一种关注个体的人的“微技术”。“微”直接说来就是指生活在现实中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作为主体而非客体的人,单个人是“微”的最小单位,无数“微”“主体—主体”关系合成了微时代。微时代的命名除了技术的标志外,更重要的是,这种关注个体的人的技术,彻底激活了人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彻底激活了人的能动性、参与性和创造性,个人终于回归到自己天赋般的主体性,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1]压抑了多年的个人终于在微技术中找到了突破口,饱和般地释放着主体性,这是目前微博微信爆炸式蔓延的重要原因,也是城市网络舆情危机得以爆发的重要原因。主体性是微时代的文化基因,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基因。总之,技术和文化的结合最终产生了微时代,一个关注主体化的个体,聚焦主体化的个体间平等自由的时代。
微时代“绽出”了个体的主体性,这直接源自微博微信的最典型特征——主体性,即“我的”微博微信。但是仅仅只有个体的主体性是不可能有强大生命力的,也就是说这种“我的”微博微信如果只局限于我一个人,如果只是我的自言自语式的表达,就像自己记录的纸质的日记一样的话,是个纯粹私人空间,那么微博微信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家喻户晓。微时代必须在关注个体的同时,更强调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主体化联合。也就是说,以关注个体的主体性为基础,同时必须使这些主体化的个体走向平等自由的共同体。具体表现为“我的”微博微信必须要被作为主体的他人关注——阅读、评论、转发,实现私人空间公共领域化,这是微博微信爆炸式发展的又一个原因,是城市网络舆情危机得以爆发的又一重要因素。
正是由于微时代下每个微博微信用户在微博和微信平台上自我的主体性得到兑现,因此当城市中某一重大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去除了在场面对面压力的微用户就能在微博和微信上大肆吐槽。在这些吐槽中,往往一些过度批评城市政府的负面信息更能吸引眼球,产生轰动效应,特别一些号称在城市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现场的了解所谓内幕信息、发表所谓与主流意见不同的“异见”更易被其他人阅读、评论、转发,这些信息随着参与人数向极限的递增,往往呈现越来越偏激的“极化”的特征,大量的负面信息、意见、情绪像滚雪球一样膨胀,最终形成网络舆情危机。所谓城市网络舆情危机就是指由大量微用户针对城市中发生的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在网络上生成的负面的否定性的群体性情绪、情感、意见、看法,给城市政府的公信力和城市的正面形象带来损害和否定性影响。它是微时代下城市公共危机的新形态,威胁政府与公众的良性关系,影响城市的安定与和谐。
总之,微时代下“沉默大多数”第一次真正开口说话,说话的欲望和能量极限般释放,彼此之间高分贝地对话传话,众声喧哗,网络舆情如洪水般蔓延开来,网络舆情危机的可能性也随之生成。“那些在传统媒体时代可能根本不会引起注意的事件,通过网络传播可能一夜之间酿成重大危机。网络对危机事件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有些危机本身就发端于网络。”[2]一定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微博和微信这些自媒体及其生成的微时代的出现,大量的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的信息只会局限在少数的事件相关者之间,更不要说越出发生地城市的地域界线而成为万众瞩目的舆情,这已被前微时代多次证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微时代成为了城市网络舆情危机发生的境域。
二、微时代下城市网络舆情危机的特征
(一)从产生的根源来看,大都是城市现实危机的延伸
近年来,改革真正进入深水区,毎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巨大的压力和阻力,而城市又处于深水区的前沿,这是由中国改革“农村包围城市”的国情决定的,这决定了城市必然是危机爆发的前沿阵地。目前城市进行着两种转型,一是来自外在的传统乡村向城镇的转型,二是来自城市自身的转型。这两种转型不仅要有观念转变作支撑,还涉及到真实的利益调整与分配。而在转型期,由于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善,在利益调整与分配中出现了许多的不公正,这些不公正催生激化了城市的矛盾,这些矛盾常常以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的形式爆发出来。这从人民网发布的最新的“2013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反映的热点可看出,在2013年前20大热点网络舆情事件中,主要集中在司法腐败、民生问题、公权力滥用、食品安全、政治议题等领域。此外,还可从在网络舆情中发挥中坚作用的意见领袖经常关注的词汇也可看出,主要有政府、改革、自由、儿童、腐败、司法、举报、道德、谣言、公平、城管、房价、校长、移民、上访、强拆、民生、雾霾、转基因、性侵等。这些词汇涉及的问题也是近几年来网络舆情的重灾区,同时也是城市转型过程中产生问题的重灾区,网络舆情与城市问题具有同构性、一致性,网络舆情正是城市问题的反映和晴雨表。endprint
当直接深陷突发事件中的当事者认为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会在第一时间想到把相关信息发布到微博、微信等网络上,力图求救于网络的力量。以微博为例,据北京网络协会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提供商缔元信提供的数据,“有96%的用户表示会通过微博了解、发布对大事件、突发事件的观点,微博已经成为一个大事件、突发事件的传播舆论中心”。[3]再以2013年的热点舆情100件为例,由网民和网络认证用户通过微博微信类自媒体曝光的则接近半数,达到47%。[4]从事实上看,微博和微信常常也的确在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掀起舆论风暴,刮起舆情狂潮,倒逼相关部门出来解决现实中的矛盾,这渐渐形成一种“惯习”(布迪厄语)——“上访不如上网”。因此,一旦城市现实中的矛盾不能较好地解决时,就会选择新的突破口,这时上网就成了较好选择,于是由矛盾而衍生的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就以舆论的形式通过首选的微博微信平台蔓延到网上,通过公众持续的转发、评论而发酵。如果城市政府不能较好地应对,就会引起更大的否定性的负面舆情反弹,舆情危机进一步扩大化、恶性化。
(二)传播更加快速,呈现弥散化
在城市网络舆情初步形成后,人们往往更加关注那些否定性的信息,这是由当下中国矛盾频发的现状和微博微信弱把关机制以及发言的门槛低与易操作等决定的。处于矛盾漩涡中的人都想把自己的问题和困难讲出来让更多的人知晓,而微博与微信为这种讲出提供了便利,真的是手指一按信息就传输出去,省略了传统媒体的一系列审查把关机制。既然讲出的是矛盾与问题,因此否定性的信息占据主导,而这些否定性的信息往往又能够触动微博与微信用户的敏感神经,触动他们在同样转型背景下或多或少曾遇到的那种内心深处的隐痛,这使这些负面信息像磁铁一样把越来越多的人吸引住。信息的负面性也符合群体性事件的特征,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曾说,目前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是“非阶层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其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民怨很深”,[5]这也决定了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发生时,负面消息满天飞。而且从新媒体的特征来看,更强调吸引眼球,那些偏激化的具有爆炸力的负面信息远比赞扬的话抢网民的眼球,况且广大微博微信用户刚开口说话,还处于网络说话的学徙期,不成熟决定了他们更易讲一些非理性的话,因此完全不像在传统媒体中赞扬声远压过批评声,相反在微博微信上,在突发事件没有妥善解决之前,常常是批评声大大盖过赞扬声,甚至充斥大量的批判,负面舆情一家独大,这也符合媒体监督的重要功能,监督更多的是关注负面信息。以《2013年中国企业舆情年度报告》为例,该报告指出,不同行业的企业财经舆情事件性质的分布存在显著性差异,整体以负面舆情事件为主。[6]
在实践中,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的直接相关人“秒速”地把信息发到微博微信后,许多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同样“秒杀”这些事件,借事件把平时积累的旧怨新气喷发出来,一时间,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迅速弥散开来,波及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许多新时期意见领袖“大V”的加入,真的是一呼万应。在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上,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常常超过媒体和政府在微博微信中的传播力。据统计研究显示,大约有300名全国性的“意见领袖”影响着互联网的议程设置,[7]直接决定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危机的速度、深度与广度。事实也是如此,许多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的舆论正是由于这些意见领袖转发和评论,然后其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粉丝接力后,才最终弥散开来。据统计,“如果每个人有100个粉丝,10%的粉丝转你的一条微博,以此类推,转帖4次,几秒钟内就可以达到1亿人次。很快天下人就都知道了”。[8]对于这些粉丝数达百万级、千万级的意见领袖来说,其影响力、传播力无法估量。当下意见领袖也偏好关注负面信息,对负面信息的关注好似更能体现他们的道德良心,“转发是一种责任”,“围观改变中国”,他们对负面信息的关注经过粉丝们非理性的进一步加工,常常使这些负面舆情越传越偏激,形成网络舆情“极化”和“弥散化”,网络舆情危机随之不断地蔓延,损害着城市的公共安全。
(三)呈现网络谣言化,危害性更大
当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作为网络舆情危机之载体的负面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随着传播链条的延伸,信息在传播者间相互传递过程中常常被删改、增减,呈现失真,这一方面来自于记忆不准等客观原因,另一方面来自一些不满的人和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对负面信息进行有选择地升级,这些越来越失真的负面信息最终变成了网络谣言。不过在转型期由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在微博微信上生成的谣言与传统谣言不同,有学者把其称为新谣言。“传统谣言多为‘缺乏事实依据的谎言,而新谣言则多为‘真实的谎言,即仅就新谣言的具体内容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虚假的,但是,我们所处时空的社会真实,恰恰在新谣言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9]这就是说,针对某个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而言,某个负面消息被证伪为谣言,但就谣言反映的问题而言却又被证实为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事实。正是这种二律背反,使新谣言更显得扑朔迷离,甚至更有吸引力,一时间难以辨明。其在被证伪前,往往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微博微信用户参与其中。
对于谣言的传播,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提出了经典公式:谣言的流传=重要性×模糊性。越重要、越模糊则越易传、越易信。而微博与微信又进一步强化这种易传性、易信性,甚至出现了“以谣言倒逼真相”的乱象,危害性极大。以“杀伤性望远镜”谣言为例,2014年6月7日,微信平台上曝出“有人兜售杀伤性望远镜”消息,称“有假军人街头兜售望远镜,并唆使人试用,一旦望远镜聚焦便弹针伤人,假军人再趁机将人带走偷肾或眼角膜”。无时间无地点,一时难以辨清。该谣言经微信熟人圈发出,得到众多网友的“证实”后进一步扩散。观察网友留言,不少人竟然表示在现实生活中遇见过这种情况,并将原信息浓墨重彩地深加工后二次传播。随着谣言的传播,全国各地都有谣言说出现了此事,从兰州到上海、北京、南京等等,一时间所谓发生此事的当地市民神经紧绷,外地亲朋好友因担忧本地市民的安危,也纷纷转发至各大社交平台,迫使谣言规模扩大,恐怖氛围加重,受众危机感加强,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市民的生活生产秩序,也极大地损害了城市公共安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