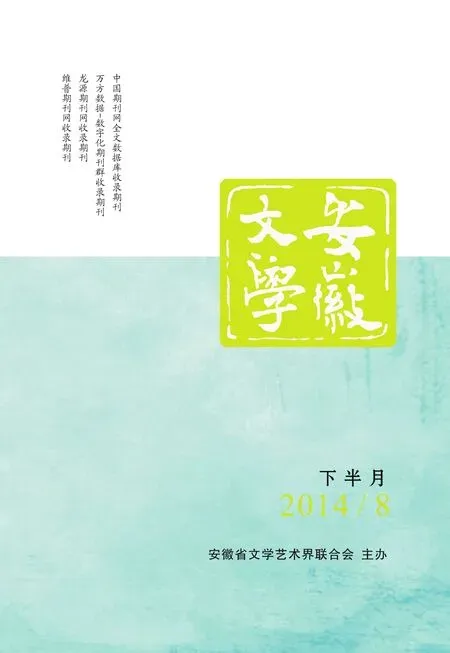世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众人看不穿
——达尔人格之精神分析
李爱宁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世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众人看不穿
——达尔人格之精神分析
李爱宁
(广西师范学院师园学院)
达尔(Darl)是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创作鼎盛时期的经典力作 《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中的突出人物。该作品结构、人物及故事情节相对独立完整,但其新奇的叙事方式﹑多变的写作技巧等却给读者带来诸多困惑。本文拟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的人格学说理论解读达尔的内心世界及其悲剧的成因。
达尔 精神分析法 本我 自我 超我 非我
美国南方作家威廉·福克纳的代表作 《我弥留之际》于1930年出版,是继《喧哗与骚动》后的又一力作。这部“奥德赛”式的中篇小说叙述了安斯·本德伦(Anse Bundren)按照其妻艾迪(Addie)的遗愿,和他的子女们把她的尸体送到其娘家杰弗生墓地埋葬的苦难历程。十天的旅程中,他们经受了水与火的考验。在此过程中,本德伦一家各有所图,个个粉墨登场,极尽表演之能事。
达尔(Darl)的内心独白在全书达19节之多,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从他的叙述中,读者发现他的眼睛似乎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着周围的人和事。他的心理叙述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许多评论家,包括福克纳本人,都曾将此归结于达尔的“千里眼”功能 。在整个故事中他似乎也是唯一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他敢想、敢说、敢干,却也因此而成为书中最悲剧性的人物。然而,达尔的内心世界究竟如何?又是什么导致了达尔最后的发疯呢?
文学具有表现心理甚至无意识的传统,精神分析学一经诞生便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以来,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为中心的精神分析法异军突起,在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文学文本分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三个层次组成: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其中本我(id)处于心灵最底层,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它冲动、毫无理性,按照 “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行事,盲目地追求满足。自我(ego)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充当本我与外部世界的联络者与仲裁者,是一种能根据周围环境的实际条件调节本我和超我的矛盾、决定自己行为方式的意识,代表的理性或正确的判断,按照“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行动。超我(superego)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尤其是在父母给他的赏罚活动中形成的。超我的主要职责是指导自我以道德良心自居,去限制、压抑本我的本能冲动,按 “至善原则”(morality principle)活动。本文拟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人格结构学说,透视他的内心世界并试探性地探讨其悲剧的成因。
一、无奈的安排——缺乏关爱的本我(id)
达尔出生在一个缺乏关爱的家庭。他的出生伴随着母亲的诅咒。他的母亲艾迪聪明、好强而且固执。她当过教师,但由于深受其父亲“活着的理由就是为长期的死做好准备”的虚无主义悲观思想的影响,她不爱人任何人。她是个孤儿,和同样是孤儿,但自私、窝囊、一事无成、遇事只会“搓着手”抱怨的安斯结婚后,艾迪自述道:“接着我发现自己又怀上了达尔。起先我还不肯相信。接着我相信自己会把安斯杀了。这好像是他骗了我,他躲在一个词儿的后面,躲在一张纸做的屏幕后面,他捅破纸给了我一刀……而我的报复将是他永远也不知道我在对他采取报复行为。达尔出生后我要安斯答应我等我死后一定把我运回到杰弗生去安葬。”②艾迪的这一段独白里,达尔的存在是父亲欺骗的已然结果以及母亲筹谋报复的手段。在达尔的幼年时期,他的自我就期许着另一个满足他快乐本能的理想自我。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儿子的恋母情结是天生的、强烈的、执著的。因此他对艾迪的爱坚如磐石,始终不渝。这样一来,问题就产生了。一方面,艾迪根本不爱、甚至仇恨达尔;另一方面,达尔却强烈而执著地爱着艾迪,长期下来就形成了一种顽固的恶性循环,也为达尔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达尔的本我自始至终都带着悲剧色彩。
二、自由发展——张扬的自我(ego)
达尔的个性发展是自由的。母亲的漠视和父亲的无能给了他宽松的发展空间。达尔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其母亲艾迪的基因。他机敏、睿智、善思、果敢。在他的映衬下,大哥卡什(Cash)的刻板、呆滞,妹妹杜威·德尔(Dewey Dell)的愚蠢和四弟瓦德曼(Vardaman)的弱智都跃然纸上。凭借某种特异功能,也就是后来被许多评论家,包括福克纳本人称为“千里眼”的功能,他知道三弟朱厄尔(Jewel)是艾迪和其情夫惠特菲尔德(Whitfield)的私生子。艾迪偏爱朱厄尔,从他的名字就能看出(Jewel是“珠宝”的意思)。艾迪自述道:“他当时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我甚至都没有要求他给我他本来可以给我的东西,那就是非安斯。接着他死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已经死了。”从艾迪的这段独白中,不难看出在她心中安斯已经死去,她怎么会去爱一个和自己不爱的人所生的孩子呢?在与朱厄尔争夺母爱的过程中,达尔也明显处于劣势。送葬的路上,为了使朱厄尔难受,他一再追问朱厄尔:“你爹是谁?”而骄傲成性的朱厄尔则恶狠狠地反诘道:“该死的狗杂种!”在故事的全过程中,达尔既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又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和心直口快的评论员,因为他强烈的自我意识促使他对事事都要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评论。这使他最终未能超越自我、达到超我,沦为非我。站在书中各人物的立场上,他很难受到别人的欢迎。
三、悲剧的产生——超我的缺失(superego)
有自我意识自然是好事,但如果一个人不接受父母和老师的教育并上升到会用社会标准批评自己的言行,达到超我的境界,那就未必是好事,甚至会物极必反。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超我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尤其是在父母给他的赏罚活动中形成的。达尔得不到父母——特别是母亲——的教育,在作品中读者也看不到能证明他上过学的蛛丝马迹,因此他的自我完全处于自我发展,继而到了膨胀的地步。看着一家人在大热天里用马车拉着艾迪的尸体要送到四十英里外的杰弗生去埋葬,而且尸体腐烂,招来阵阵秃鹰在头顶盘旋,他感到这完全是场闹剧,使受了一辈子精神痛苦折磨的艾迪的尸体不得安宁;他此时甚至感到艾迪要把自己的遗体远埋在娘家墓地的遗愿也是荒唐的。于是,他干脆放了把火,想把尸体烧掉完事。
关于本德仑家发生火灾的一幕,福克纳删去了手稿上的一段话,这是达尔决定放火焚烧母亲尸体时的一段独白。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达尔的人格及心理活动,依据兰登书屋版约瑟夫·布洛特纳《福克纳传》(1974年)所提供的资料,笔者有心将这个删去的段落补充进来:
有一次我死的时候听见悲哀的号角声。当大地再次打起盹儿来我听见号角哀呼上帝。我小时候也曾有过弥留之际。我父亲让我处在弥留的状态。这真是件好差事,但我不适合做这个。我不想做这个。因为,不是所有人生来都是木匠,像基督那样的好木匠。基督给母亲造了条船,他父亲却弄翻了它。因此他说好吧,这回我用火来安置她,你总弄不过火吧?③
这段独白进一步揭示了达尔纵火烧尸的动机。不难看出在决定放火烧尸之前,达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非意气之举。这段情节应是故事的高潮。对达尔放火烧尸的做法,应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对达尔来说,想到艾迪一生受的磨难,他不想让这场闹剧再演下去,决心用自己认为合理的方法结束生活对她的折磨。这样,他放火烧尸的做法并不是不可理解的。但在别人眼里,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儿子把自己母亲的尸体烧掉,成何体统。和昆丁一样,达尔在周围的世界里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归属。他这样做授人以口实;再者,从法律层面上讲,这完全是犯罪;因此他被送进疯人院是“理所当然”的了。
四、悲剧的降临——达尔的非我(non-ego)
“杜威·德尔第一个扑上去”后,达尔被捉住,被送进了疯人院。“达尔到杰克逊去了。他们把他押上火车,他哈哈大笑,走过长长的车厢时哈哈大笑,他经过时所有的脑袋都像猫头鹰的头那样扭了过来。”“你笑什么?”我说。“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达尔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兄弟达尔。我们的兄弟达尔被关在杰克逊的一个笼子里,在那里他望外观看,嘴里吐着白沫。”④在达尔疯狂的笑声中,整个世界因此幻化成内心的映照,充满着喧嚣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达尔的笑意味深长。在旁人看来,那是疯子的狂笑,而站在达尔的立场来看,那又何尝不是无奈的笑,何尝不是他为失去的本我和自我的哀叹。笑声过后留下的是一个只有非我的达尔。我们无需探究达尔在疯人院里会得到什么样的治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本我和自我永远不再是他自己的了,而且疯人院不可能把他的精神提升到超我境界。这样达尔不再是过去的达尔,也不可能是按常理可能有超我意识的未来的达尔了。他将变成非我,这场闹剧最悲惨的牺牲品。
五、发人深省的悲剧结局
达尔的悲剧发人深省。人生来具有本我,这是无法选择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本我会逐渐发展为自我,这是自然而然的。但要从自我上升到超我却并非易事。在心理成长的这个阶段,人必须接受父母和老师的悉心呵护和耐心教育,用社会标准规范自己的自我意识,不让它恣意发展,从而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融入社会,并能从中发挥自己自我的人。心理成长的这一过程是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稍有差池,就会重演达尔的悲剧。福克纳总是把人生描写成一次“苦难的历程”。在生命的全过程中,人一直努力地由无知学习智慧,在迷惘的黑暗中走向光明。在此过程中,人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永远在进步。达尔这一文学形象可以说是这一理论强有力的佐证。正如 《押沙龙,押沙龙》中昆丁所说的:“不,不,我不恨,我不恨南方!”福克纳也不恨世居美国南方的人们,更不恨人类。福克纳在这里为人类竖起了一面狭窄的镜子,使人类看到了自身灵魂深处的一部分,从而经过苦熬,战胜低劣,恢复高尚。
注释
①此为笔者自造.意为:非我。
②李文俊.我弥留之际[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176.
③约瑟夫·布洛特纳.福克纳传[M].纽约:兰登书屋,1989:89.
④李文俊.我弥留之际[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220.
[1]李文俊.我弥留之际[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2]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
[3]李文俊.福克纳评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4]黄希庭.人格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5]许志强.我弥留之际的一个评注[J].外国文学评论,1999(2).
[6]詹树魁.论我弥留之际的叙述方法[J].外国文学研究,1999(2).
[7]约瑟夫·布洛特纳.福克纳传[M].纽约:兰登书屋,1989.
[8]William Faulkner.As I Lay Dying[M].Random House,1930.